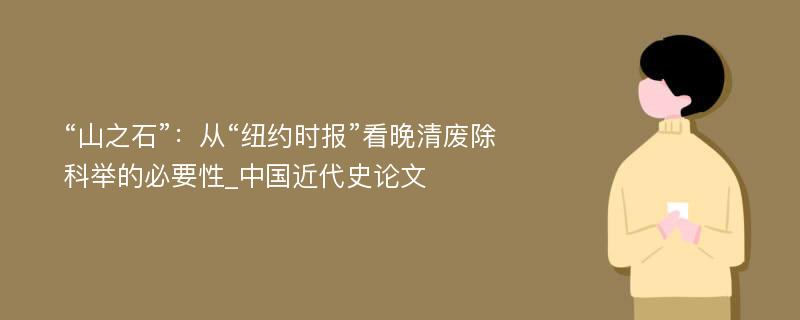
他山之石:从《纽约时报》的视角看晚清废除科举的必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他山之石论文,晚清论文,科举论文,纽约时报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4)05-0082-06
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美国即开始对中国的战事进行跟踪报道,正如2003年春中国的新闻媒体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事,向国人提供最早也是第一时间的信息,体现出国人的国际关怀精神。雄踞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权威报纸《纽约时报》从1853年开始即对中国战事进行跟踪报道,不仅是战争,清国的政治、外交、内乱、人口、地震、宗教、纺织、农业、邮政、妇女问题、低价的苦工、财税征稽等文化的诸方面也进行全方位的跟踪报道,作为一个旁观者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些是从我们自己的史料中所查找不到或是史书根本就不记载的极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最初美国尚未参与侵华战争,它只是作为一旁观者在冷静的观察和分析战况的发展,因而其报道更显真实和可信。本文试图透过“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步入“危机”的根源——特殊的科举导致的教育失败。
一、停留在“过去”的教育
1.清国的教育模式。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之题记“清国青少年的教育与功名的授予”[1]的通讯,即以“他者”的身份和“他者”的视角强调晚清废除科举的必要,揭示了中国科举制度的致命弱点。这则通讯转载于《伦敦日报》,作者是驻北京的英国记者,报道中随时加有作者的观点和尖锐的批判。记者发现,传统的“填鸭式”即背诵课文的教育模式,似乎贯穿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这一教育方式旨在灌注“道”理而不关心学生能否理解,其结果是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事实上,这一传统的教育范式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而非清国一朝。而背诵的内容,非儿童入门之书而是儒家经典著作,如孟子之书。于是这位记者评论说:拘于儒家经典并延用了上千年的考试制度,“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此刻它决不可能再适应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把人的知识的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否定对古代知识的研究,但把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方式限定在一条狭窄的思想道路上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开放人类知识的整个殿堂。宣称‘世界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到昨晚10点半’的美国教育无疑是正确的”[1]。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作了彻底否定——科举已经不合时宜。这个论断虽然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却抉中了中国科举最致命的本质,因为儒学以“仁”为根本,排斥自然科学,因而我们传统教育的“成果”皆为恪守儒家君臣之仪的谦谦君子,这种优雅的“风度”之于使国家安定的治国是必须的,但仅凭仁义道德却不能使国家富强,因而尽管上述报道口吻严厉但却反映了我们教育的实际“问题”。我们的教育所培养的皆为忠诚之士,这于动乱时期尤为需要,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具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勇气和精神,并自翊为社会的中坚,具有“与陛下共治天下”(宋文彦博语)[2]的责任感,在中国社会中长期扮演着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但是,在晚清时期,由于自明朝以来的“八股”科举将本为中国的这批精英终于一股一股地紧紧裹在了一条狭小的只“为稻粱谋”的求生之路上,使他们变得麻木,难以奋扬起创新和求变的精神。同时,由于晚清对科举制度的亵渎,“将封官晋爵作为奖赏已成了大清政治生活的陋习,并且获得了广泛的运用。有些人只要花钱,未经任何考试便能得到功名”,而实际上,“为国家作战负伤的伤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寒窗数年、埋头苦读的读书人不能公平地取得一官半职”[1]。因而历来视读书为唯一进身之阶的士人此时亦对“读书作官论”感到了迷茫,科举已受到质疑。
2.清国教育的内容——四书五经。《纽约时报》1876年2月20日发表题为《“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1]的述评,认为“不管用欧州人的标准来评判它的真正的价值如何”——十分明显,其态度上已经否定了我们所崇奉的近千年的经典——“四书五经”,“从其影响了千百万人的思维这方面来讲,它们都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并对“四书五经”在清国之意义和价值作出评判:“这些闪烁着东方智慧之灵光的典籍比我们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宽泛,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东方世界确实远比其他任何宗教信仰更有效地指导着人类。我们衡量其价值时不能不从它具有的这种效果来评判。”[1]
由于作为“圣人”——中国士人的永远的偶像——孔子的诞生,“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因而中国知识分子——士就拒绝接受外来的东西,如对电报、铁路等,有极强的排外情绪。对于晚清新兴的报业,《纽约时报》的“述评”中说:“中国人不怎么懂得什么是新闻的职业道德,但他们印出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读者用出得起的钱买报看,他们无需等待其他人收集消息,然后以欺骗的手法卖出去,就像他们企业生产的商品一样。”[1]事实上的极端保守及其结果,使“这些受过中式教育的人,就连形成一种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所必须的初步知识都没有”。十分尖锐的批判但切中肯綮并一针见血。他分析这种教育制度之所谓的优点即“要让一个男人成为其他男人的统治者,其所需的全部学识仅仅就是那些经典著作”,因为这些儒家经典是经过历代统治者所筛选和确定的,它对于“那些坐在自己的家中来支配和规范我们自己社会体制的人而言,肯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1]。
《纽约时报》在《清国社会新闻几则(二)》中描述了清国皇帝的求雪:“快到秋末了,而北京还未下雪。于是,皇上命令诸位亲王到各庙宇求雪。他说道:‘鉴于迄今片雪未降,以致土地干旱,朕拟亲往圣殿上香求雪。’”[1]这则报道并没有对清国皇帝求雪的行为进行评论,但其向全世界进行宣扬的潜在目的则十分明显:皇帝尚且如此愚昧,何况国人!
国民的教育和觉醒,非旦夕之功。要让一个被孔孟之道驯化了数千年的农耕民族从灵魂深处萌生出脱胎换骨、自我革新的决心将是怎样的艰难。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谭嗣同希望以自己的血唤醒民众,而毕竟看热闹的观者众而升腾起革命血气的勇者寡,晚清时期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究其本质乃我们教育的失败。
3.获得精英的最佳方式即是科举。由于国家权力集于一人手中,而“这个男人”——皇帝需要这个社会的精英帮助他治理国家,因而“一次又一次,清国的男人们千里迢迢进京赶考,直到他们渐渐老去,头发变得灰白和稀疏”。因为如此持之以恒的终极目的即获得功名,儒家所重者“忠”和“孝”,“忠”指对皇帝,那要等待机缘,比如科举即其一。“孝”则对父母,而“显亲扬名”则又是“孝之最也”,所以这种坚持的精神中包含有“忠”、“孝”的意识,还有功名之外但与功名相伴随的地位和金钱。这已非清国,自科举产生以来便伴随这一现象的不断发生,如唐代诗人赵@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3]甚至有年长的考生死于考场的事也时有发生。《“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的述评中还说:“清国的社会体制使得科举成为人们通往荣华富贵的唯一道路,并且清国法律让政府把这样的机会摆在每一位志愿参加竞争者的面前。”[1]通过这种方式,使儒学经典禁锢住人们的自由思维空间,限制人们思维表达方式,并且“倾向于压制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创造性”[1]。整个科举旨在迫使文士们沉湎于“科举生涯”,并将他们的思想以纲常名教归并到统治者的思想中,造就出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奴隶”。
长久的四书五经的教化已经使洋人“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像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1]西方人尚且对我们国民的麻木流露出深深地遗憾,而我们自己仍旧怡然自乐,以至于晚清西方基督教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入侵以其强大的攻势进军中国时,慈禧太后“决意用孔夫子的学说去反驳他们”之举受到美国《纽约时报》的讥讽(注:见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中“慈禧太后以孔子伦理反击西方”。)。
4.关于中举后的仕途官场。《纽约时报》对于清国教育所培养的“良民”作了事实的否定,即清国官僚的极端腐败,其1897年2月25日的发表的《述评:清国的财税稽征制度》中说:“虽然本质上很荒谬,但在平时地处北京的皇家政府总能获得充分满足其需要的金钱。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甚至约略地知道,各省不同的地方长官在人民身上榨取了多少钱财,但是,其数量肯定是可观地超出,甚至远远超出最后上交到国库的数量。”[1]从这里可以了解到,《纽约时报》对清国之财政亦了如指掌,“皇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总体关系可以用下面的话总结:北京政府总是企图尽可能多地捞取,而地方政府则总是企图尽可能少地付出”。对于清国的军事装备,《纽约时报》1895年3月11日《述评: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中又说:“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英国人迄今在军备贸易方面和清国人之间的成交额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商号比较重声誉,因为他们拒绝付给清国官员所要求的大笔佣金。而那些不拘小节的外国公司则签了大量会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合同。”[1]清国政治中心的官僚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而只求一己之私利,这就是我们的科举所培养出的优秀良民。《纽约时报》在《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中对于清国大使的“评论”说:大清国“外交使节的委派完全是通过徇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有一位被派到一个大国去的公使,出任之前是大清国一位出色的学者,这位学者通过欺诈的方式帮助一位清国高官的儿子获取了功名,其获得功名的文章是这位学者替他写的,而这父子两人表示感激之情的办法就是委派这位学者去当了大清国的驻外公使”[1]。对于清国公使的印象则是“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全部认识也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奢侈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当他们回到国内并获得官职后,他们的这种奢侈倾向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诱使他们做出更具欺诈性的劣行”[1]。因此《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官僚体制不仅提出了严厉批评,庶几作了彻底否定,在《清国大臣建议废除捐官制度》中说道:“现在是发布诏令采取法律手段铲除这类官僚的时候了,否则朝廷和民众的利益将会很快被这些利欲熏心的人丧失殆尽。”[1]
从美国人的眼中,可以看出,这种致命的考试制度已经将国人的灵魂异化为朽木。中国图存的唯一途径即科举改革,唤醒国人的精神。
二、教育的本质——塑造麻木的灵魂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外国人得到了到中国境内旅游的特权。法国公使葛罗一行于1858年7月11日游览了象征中国人智慧的长城,当他们到达长城脚下时,被守卫边境的清军所阻拦,在交涉中当葛罗了解到“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军人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在战争状态时,惊讶程度可想而知。什么广州事件,什么大沽海战,什么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他们都一概不知”。一位英国记者于1860年12月10日得到美国海军军官的邀请游览广州的“水上世界”。他在《广州的水上世界》中写道:乘船到达珠江口,看到河两岸的山脚下都修筑了许多军事防御工事,但他发现“这些防御工事的后部都没有设防。设想英国佬从山背后登陆,爬上山顶,居高临下,发挥攻击火力,那么,这些碉堡就毫无价值了”[1]。旅游者的眼光充满军事家的睿智。当他询问清军为何不背后设防时,清国军官竟天真而自负地说,“如果这样交战就太不公平了”,战争的游戏准则是枪炮的坚利,战场上何为仁义道德?公平——那是中国的特产,西洋人如果讲公平,他怎么会来侵略?这是儒家教育的悲哀。事实证明了这个记者的预见,“直到最近的这次战争,清国人从未预料到英国海军能够让一支地面作战部队登陆”[1]。对于战争的仁义的希求又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清国教育的失败。
至于在中国建造电报线路和铁路,中国政府持不同意的态度在美国人看来原因有三:其一是担心浩大工程一旦建造起来,可能会导致许多苦力、车夫和船夫的失业,因而会引起人民反清起义。其二是假如同意修建,而一旦建设成功,清庭又担心外国的势力会因变得更为强大而造成交往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其三是迷信思想,在《铁路和电报有望在清国出现》中报道说,清国人“担心类似如此大兴土木的工程会破坏国家的风水,因而影响农业的风调雨顺,带来洪涝灾害,甚至会让太阳发怒,烤焦他们的庄稼”[1]。这些担忧证明了国人的保守,而迷信则又再次证明了中国教育的失败。
西方的大炮轰开我们紧闭的国门,迫使向来自以为是的民族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必须投入到民族斗争的洪流。过去沉积并隐藏了千年的污秽终于暴露于光天化日,西方文明以其强大的攻势证明了我们儒学的文弱和不堪一击,当恭亲王奕在甲午战争后期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还十分自负地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这是怎样单纯而天真的表白,所谓的“法度”、“仁义”、“道德”,那是为我们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这个“法度”何以能漂洋过海去“规范”他人?在以炮舰为外交手段的时代,我们千年所尊崇的“规范”被枪炮的轰鸣而“规范”了。
清廷第一次有意于西方知识是在天津条约之后的咸丰十年(1860),客观的形势产生了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同年有第一道诏书准备接受学习“夷语”(注:王先谦编《十一朝东华录·“咸丰”朝》卷97。说恭亲王奕等奏请从上海和广州遣送两名通晓夷语的人,并经皇帝谕准,挑选八旗子弟,学习夷语。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同治元年(1862),京师设第一个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次年应李鸿章所请上海又设一外国语学校广方言馆。于是各省重臣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及京师大臣恭亲王奕和大学生文祥是一批最早意识到西方知识之重要的人。他们创设军工厂、翻译局、语言学校、派遣留学生、致力于吸收各种西方技术。这些大臣流露出现代化的意识,但后来在中法战争中国战舰一战即溃,反思失败的原因,正如后来成为科举制度批判者的王先谦所认为的,改革的当务之急“唯在商务、海军”(注: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一“江西乡试录前序 ”:“道、咸之际,知有海国矣,情事末灼也。同、光以来,知列国所以驾吾上者,端绪可究矣,而势弗棘也。朝廷之上,振兴商务,封疆之吏,习勒海军。吾财弗外流,而势足自振……虽不改制科,无害也。”民国十年(1921)刻本。),终于未能觉悟到根本原因在于科举制度所塑造的“人”。
当清国特使伍廷芳出使华盛顿,在其演讲中即有基于“爱国”的自夸,他说仅清国一省的煤炭产量即可供全世界享用1000年,这使美国人深感担忧。在《清美两国自然资源比较》中写道:“根据清国过去或现在的煤炭生产能力所做的测算都不能充分估计到觉醒以后的清国生产能力到底会达到多高的水平。”[1]清国还是个沉睡的雄狮,美国十分担心这个睡狮的觉醒。我们天真的特使还“预示未来清国境内长达数千英里的新铁路将可能由美国滚滚而来的股票资本来修筑和经营,而这些铁路将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由机器制造出来的新商品”[1]。对于特使的美丽幻想,遭到《纽约时报》的嘲讽,“在这一点上,这位清国大臣却犯糊涂了。他在一周内聘请了两名美国教授到清国去讲授美式耕作法。如果这两位美国人是负责农业商务信托事业的专家尚可理解,因为美国在农场经营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称世界第一,但是,在单纯的农业种植技术上却处于相当初级的水平。我们在农业理论上有明显的优势,在实践上却乏善可陈。尽管我们有世界上最丰沃的土壤,但我们每英亩的单位获量却少得可怜。大清政府竟要从我们这里来请农业耕作专家,真是匪夷所思”[1]。
当法国公使葛罗一行到达广州的当天,享受到了中国贵族的饮食招待,吃饭一直到深夜12点,他深感此种餐饮方式实属浪费时间从而否定了清国贵族的生活节奏。第二天,这个旅行团乘坐中国的人力轿子进行广州城市观光,他们所感兴趣的首先是与法律有关的审判和行刑,因为法律是国家的命脉。《纽约时报》在《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中记述:游览盐狱,看到了狱中人所受的非人的肉体折磨。刑场上,有20多个犯人被处决,而围观的“每位清国人都在东张西望,仿佛此时此刻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当轮到他们自己时,似乎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他们就这样死去了,人的生命被看得一钱不值”[1]。这个旅行团游览的真正目的是考察中国的国情——到底这个神秘的帝国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抵抗西方先进科技(这已经与本文无关,故不作展开探讨),我们独特的教育模式驯化了国民民族性格上的自抑本能,所以欧美记者到清国所见即是麻木无知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国民教育的结果,是长期的皇帝独裁专制的驯化的结果。这种民族自抑对于和平时期的皇帝治国是极为有利的,但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却贻害无穷,其害之最大者即它隔绝了民众与上层统治阶层的沟通,使国家大事变成少数几个人的私事,而恰恰这些事又与民生息息相关,国民无权参与决策,然而当事态变得异常紧急时,国民还被蒙在鼓里。这就使得政治决策者在处理国政时难以获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而在他们最需要国民援助时,国民却报之以冷漠。
国人的国事冷漠即是吾国近代危机政治的最大失败,而向来自视为中流砥柱的读书入仕者,面对西洋文化的大量涌入,突然发现自己面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竟是如此无知!光照千秋的中华文化,在与异族文化进行比较时,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和恐慌。怎么与外族进行斗争?怎么打赢新概念下的战争?如何解决这个严峻的、事关民族生死的问题,砰然降临于国人面前,古老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举国上下所感到的茫然究其根源,仍回归到教育的失败。这一点洋人也看到了,《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分析说,1894甲午战争以李鸿章苦心经营了近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终,这个事实使美国感到“欠日本人很大一个人情,因为日本人向我们展示出了已经病入膏盲的政治腐败、深入骨髓的野蛮习性和无可救药的愚昧无知正在怎样地让这个腐烂之中的巨兽摇摇欲坠”[1]。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使我们认识到,“船坚炮利”非救国良药,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制度,因而废除八股,尤为当务之急,因而张之洞力论八股之弊:八股“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4](P577)。认为科举禁锢人的智慧,败坏人的心术,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4](P577)。国人不仅开始对科举之弊进行反思,更为可贵的反思之后的觉醒——呼吁并强烈要求废除科举:“熙朝科目取士,沿朱明之旧。然国初制艺尚理法,中叶乃尚墨卷,已非先辈风矩。同、光以还,国势浸衰,论者始归咎八股取士之失。慈圣惩庚子之变,谋以新政收人望”[5](P900),“同、光以降,国势寖衰,论者始归咎于八股取士之失。”[5](P900)
康有为为变革而“绝意试事,专精学问,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6]。而“大攻西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光绪24年(1898),光绪帝在颐和园接见维新变法的代表康有为,康有为所谈主要即科举之弊,他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剖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6]但由于慈禧的镇压,维新百日又失败了。《纽约时报》发新闻专稿:《光绪皇帝驾崩,曾推动改革功不可没》说:“1898年,当人们得知光绪皇帝表现出了鼓励改革的愿望时,世界被震惊了。在维新派改革家康有为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下达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法令。这些法令的内容归结为国家信贷、契税、军制改革。教育改革……建新式学校和大学等,如果这些法令真正实行的话,将意味着大清国全盘西化。”[1]
三、关于鸦片的态度
由于清政府对鸦片的警觉,于是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纽约时报》1863年4月26日述评《罪恶的鸦片贸易》一方面客观描述中国的失败之后不堪设想的后果,“这场可耻战争的结果正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文明世界终于在远东获得了贸易上的极大胜利,而大清帝国却丧失了它控制毒品进入其国境的全部权力”。并且由于国人“对现状不满和抵制情绪而直接导致的叛乱和暴行正在大清国的领土上不断地发生和增长”,因而预言“如此发展下去,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大清帝国的解体和崩溃!”并对清国烟民表示深深地同情,“他们缩着蔫巴巴的脖子,满脸菜色,在鸦片烟瘾的折磨下吃力地喘着粗气”[1]。而参与了列强对帝国的瓜分但最初尚能主持公道的旁观者的美国对英国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清国人不得不签署《南京条约》,向英国人赔偿100万美元,这笔赔款完全是英国人无耻地勒索和欺诈。《南京条约》之后,虽然又达成了第二个协议,承认清国人有权没收走私品,然而,据称在英国当局的纵容和默许之下,走私照样进行”。“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一个以往一直对别国有所帮助的民族,现在正在把罪恶强加于一个有着3亿6000万人口的帝国身上,根本不顾这个帝国的人民是否担当得起如此的灾难”[1]。对于欧美,中国对美国的信任超过任何别的国家,美国的一些商人曾经采取断然的立场反对鸦片,并一直运用他们的影响反对这一罪恶,以唤起西方国家的道德意识。
然而后来,随着战事的进展,美国目睹了英国通过鸦片所获得的巨额利益,再也终于经受不住远东帝国的巨大贸易市场的诱惑。《纽约时报》在《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中写道:“英格兰国库确实得到了极其丰盈的进项,这也是她创作出那些悲惨需求所获得的巨大回报。”[1]这个巨额利益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伯驾迅速回国到国会作慷慨激昂的演讲,以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他说:“对华贸易作为舒适和健康奖赏的来源对我国的重要性是无需多加评论的,中国人的道德价值应是我们这些自由的和开明的基督教国家最欣赏的,一旦贸易停止,道德价值也会丧失。还不应忘记的是,每年大约12,000,000美元的(美中)贸易是值得维持和保护的。”[7](P55)鸦片已经使中国奄奄一息,《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文中美国人甚至怀疑“大清国非否还有新的希望?”“这希望能否发源于有着无限黄金储备的加利福尼亚或澳大利亚呢?”美国感到中国自身已经没有自救的可能,中国的救亡图存需依靠美国,因而便以“救世主”的姿态参与了侵华战争,其理由是:“大清国当然有未来,而且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毋庸置疑。清国正像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每一个新成员那样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1]因而美国理直气壮地充当了“挽救”清国的角色。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甚至认为:“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明智干涉而得以拯救。”另一位传教士雅裨理更认为:“为了与中国进行文明国家认可的自由、友好、安全和体面的交往,必须诉诸武力和强制手段。”传教士还为鸦片而辩护,认为“对一个自认为是世界中心并把其它所有民族都当成一小撮只能分享其恩赐和怜悯的蛮夷的国家来说,也只能采取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P73)。此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清国有彻底的洞悉的基础之上,因而是具有十分把握的宣言。美国认为中国需要变革,但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美国。他说:“对于那些什么都很好的地方,变革有可能越变越坏,但对于那些一切本来就很糟的地方,变革的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越来越好。进而,大清国对于我们乃至英格兰所生产制造的有用产品的需求就会涌现出来。这个沉睡了多年的辽阔国度将会经历世界贸易新的冲击,并从中学会发展和进步的法则。”[1]断言中国的觉醒需要依靠英美。
伴随清国的日趋衰弱,美国由最初的尊敬到终于看清了清国人的“夜郎自大”的本性,于是,在《纽约时报》中便改变了报道的语气,在1895年3月11日的《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的述评中说:“现在,我们认识大清国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当今世界的秩序下,大清国的继续存在对世界和平来说永远是一种威胁。在我们的地球上,大清国是一个既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1]从美国由最初的同情到最终的欲将大清国从地球上清除的过程,我们再次深深感受到落后挨打这一永恒的真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曾是怎样的固步自封,透过晚清的血泪,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强大的泱泱大国怎样地沦落成为远东的“乡巴佬”,看到了一个曾经昂然屹立的民族怎样地被残酷地肢解,从这个血淋淋的教训中我们终于学会了现代游戏法则,我们终于认识到:科技救国,科技兴国,晚清,我们付出了国家与民族进步图存所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思索出这个沉睡了多年的辽阔国度是怎样艰难地谋求发展和进步。
收稿日期:2004-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