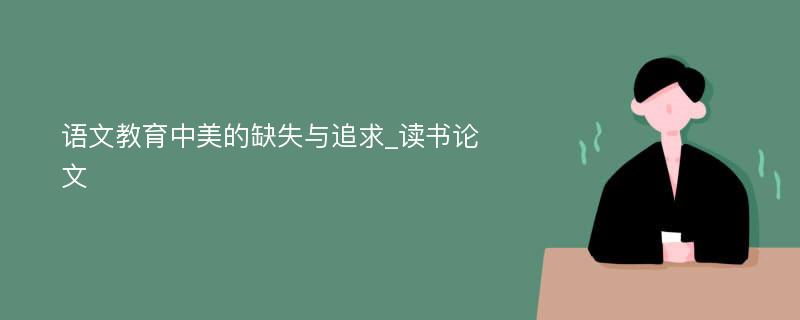
语文教育中美的缺失与追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缺失论文,语文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教育天然地含有美的因子,对人精神属性中的“情”影响至巨,是最有资格谈美的,本不会存在“美的缺失”的问题。但是因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侵袭,如古代的为功名、为仕进,现代的为应世、为谋生,加之上个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的盛行、工具本体的张扬、情感本体的受抑,导致语文教育中美的淡化、边缘化,乃至失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从民国时期蔡元培、王国维等人对美育的倡导,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对语文之美的探索,还有当下“诗意语文”、“情境教学”、“真语文”、“语文味”等语文理念的风起云涌,不难一窥消息——理念纷呈、形态万千,无一不体现了追寻语文教育之美的可贵努力,但同时也说明:语文教育中美的弱化与缺失,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不过,追寻语文教育之美,人们多局限于课堂教学这一环节,且停留在“技”的层面,对决定“技”的“道”,或者说语文教学中的教师人格魅力、创造活力、审美素养等,虽有所涉及,却鲜有深度的关注和自觉,也鲜能持续地践行。随着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一切以紧扣知识点为原则,追求所谓的“效益当先”,使很多语文教师深陷追分逐利的泥潭;加上教育界名目繁多的资料评估,还有教师自身的惰性、奴性因素,使他们也无暇读书、思考、写作,甘愿跟随成规滑行,匍匐于流行话语之下,于是眼界狭隘、学养匮乏,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的萎靡成了可怕的常态,语文教育从一开始便丧失了最具决定性的美的动力,还谈何审美? 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唤“卡理斯玛”型教师,追寻、建构、捍卫语文教育之美,便显得尤为迫切。 “卡理斯玛”是个社会学概念,由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强调的是在危机时刻,人的体质和精神上所表现的“一种特殊的、被视为超自然(非能力所及)的才能”。[1]这种才能具有排斥传统原则,创造全新秩序的独断性和革命性;有超脱成规的使命感,凭能力、效力撑起权威,形成凝聚力的力量感。卡理斯玛所引起的革命不同于基于理性的革命,它不是由外而内,由制度而人,而是“由内而外”,即先是精神上的革命并由此波及外在世界。 基于此,有学者将之概括成一个公式:“祛俗性”=“英雄主义”,卡理斯玛型的英雄主义体现为祛俗性,卡理斯玛型的祛俗性使之具有英雄主义特色。[2]这种反叛的、祛俗的、活力郁勃的英雄主义,天然地具有美学意味,对语文教师如何反叛成规、拒绝奴性,以强大的精神能量、个性化的智慧魅力、渊深的学养积淀,引领学生与优秀的自我相遇,畅享语文之美,均有着丰富的启示。 一、反叛:不安现状,拒绝奴性 在韦伯看来,管理的体制有三种:理性型、传统型和卡理斯玛型。 通俗地说,理性型就是以制度治天下,认“物”不认“人”;传统型即子承父业,萧规曹随的那种;卡理斯玛型则天生反骨、不安现状、不甘平庸,一如当年的蔡元培管理北大,他是卡理斯玛型校长,又萃聚了一大批卡理斯玛型教师,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辜鸿铭、黄侃,皆为不按常理出牌之俊杰。 反传统、反成规,当然不是泼洗澡水连婴孩一起泼掉的极端,而是对陈腐、落后始终心怀警惕,力图不断规避、不断超越的伟大追求。语文教育固然也可以作用于人的其他精神属性——知、意,但作用于情更为显著,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谈美,也应最具美感——朱光潜先生早年不就著有《谈美》一书吗?但因为惯于因袭——如一套教案重复使用一辈子;乐于跟风——乐呵呵地学习这个“式”、那个“法”,唯独没有自己的“法式”;懈于积淀——放逐内核素养、外围素养的积淀,导致文本解读了无个性和深度,教育指导或熏陶乏善可陈。于是,美不知不觉地远遁了!一个学生曾告诉我,他一上某语文老师的课就犯困,因为所说的内容全在复习资料里,既然这样,还听个什么劲呢!这便是反叛精神沦丧的跪伏式教学,心甘情愿地接受常规、平庸思想的奴役,却将自我消灭于无形,也就无美感可言了。没有美感,育从何来? 不断超越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会使语文美育中的卡理斯玛型教师自觉地反叛旧我:拒绝重复、拒绝肤浅、拒绝奴性。北大学者夏晓虹坦言:“我对上课感觉很有压力。一般来说,我会在文章发表前讲授,就是担心我讲的内容缺少了新鲜感和冲击力。”[3]特级教师李镇西对自己下过绝对命令:实施“五个一”工程!即每天上好一堂语文课,找一个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读书不少于一万字,写一篇教育日记。他们这种苦行僧式的苛严,正是对旧我的反叛和拯救。育前的忙碌、紧张甚至狼狈,都是为育时的从容、潇洒、自信张本。如此,他们的语文教育怎能不生机勃发呢? 但是,反叛并非无原则的解构或摧毁,而是有着神圣、庄严的价值和意义追求。连以解构著称的后现代主义都认为是“现代性”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而意义却是更高的价值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去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了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4] 真是一针见血!没有被工具理性束缚,津津乐道于“技”的肤浅境界,而瞩目于大道之行的境界——追求更高意义和价值的引领,释放人类最高、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这样的教育岂能没有崇高的美感?不禁想起现代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在他那里,教育的最高意义和价值引领就是调和发达,陶养灵肉一致之人。对当时只懂知识传授、毫无人格接触的学店式教育,他深恶痛绝。对教师自降尊严,以教员自认,他深感可怜,因为“教育毕竟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够得上‘师’的称呼的人才许着手”。[5]遗憾的是,先生当年不满和忧虑的现象,至今仍有增无减,语文教育中尤其如此。灵魂的陶冶早被视为无用的花架子,再优美的文章都会被抽绎成干巴巴的几个知识点,语文教育在与数理化等学科同质化的道路上疯狂飞奔。语文老师也不再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荣,而是精心盘算着如何让学生嫁接组合或直接套作。有的干脆以教学为副业,以培训为主业,大肆兜售阅读、作文心法,机械训练,贪婪捞金,斯文扫地罄尽!如此熵化、异化的教育,美又从何来? 晓之以理,谈不上;动之以情,谈不上;化之以美,更谈不上。没有崇高意义和价值的引领,语文教育即使技术再纯熟、应试再厉害、捞金再成功,也永远只能在渺小的境界里打转儿。语文教师被其他学科教师轻视,语文学科被很多学生列为最不喜欢的学科,与语文美育中失却崇高意义和价值引领,以及自我放逐反叛、超越的品质,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杜威曾将教师视为上帝的代言人、天国的引路人,强调的正是教师优秀人格的重要性。教师的职责并非只是传授知识、训练技能,更重要的是熏陶、培育学生的精神,因此教师首先必须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而走向崇高的前提就是独立——独立观察、独立体验、独立思考。要想独立,则必须具有反叛的精神。正像著名学者周国平所说的那样,“对心灵发生的重大影响绝不可能是一种灌输,而应是一种共鸣和抗争。无论一本著作多么伟大,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和抗争,它对于我实际上是不存在”。[6]抗争说的其实就是反叛和创造,共鸣则是指吸纳与继承。既然读书的目的是在吸纳与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反叛性地创作,那么对于彰显语文之美的教育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二、个性:自信引领,以达完美 引领,自然也包括方法的引领、体验的刷新、智慧的启悟,这与反叛精神一起构成了追寻、创造语文之美的个性。 民国时期,一位署名“天民”的老师在《国文教材处理法》一文中这样写道:“儿童之读书也,当先为预习,次为机械的读法(但读而不求意义之谓),又次为研寻意义之论理的读法,更进而及于美的发想之读法。”层次井然,从从容容,他谓之“渐明法”,“如昏夜将晓而万物形状渐次分明然”,不仅求懂、求悟,而且求美,这种慧眼独具的引领是深解语文之美的真谛的。 当下被炒得火热的“非指导性教学”,一味地放任学生体验,教师以甘当“哑巴”而自豪,表面上看是尊重学生的体验,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为教师的无能和不作为寻找堂皇的借口,与鲁迅先生当年反对的神而明之的“暗胡同教学”[7](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如出一辙。缺少深邃、个性的智慧点染和引领,也没有深度精神对话的教育,哪里还有资格谈美?永不作为,还要老师做什么? 当然,一味地逞才,使学生如坠五里云雾,不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也无美可言。就像夸美纽斯批评的那样:“谁要是教学生,却不按照他们能领会多少,而是按照教师所希望的多少,这完全是愚笨的行动。学生所要求的是扶持,而不是压迫。”[8]但是,又的确存在美感葱郁的满堂灌。那是潜对话悄然进行,学生被教师言语营构的气场或美境感染,置身其中欲罢不能的课堂,就像上海复旦附中的黄玉峰老师、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他们的满堂灌早已成了教者言语的舞蹈、学生心灵的节日,堪称美不胜收,哪里还会有半点的压迫?体现语文教育之美的课堂,一定是师生个性充分绽放的课堂。尤其是教师的个性魅力,直接决定了他的教育是否能产生一个磁场,将思想之美、情感之美、人格之美濡染学生。 教师引领了,似乎也具备活力了,但无从谈美的课堂仍然有。据说一位语文老师,为了将毛泽东的词《咏梅》上得生动,在朗诵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忽然藏到了讲台下,接着又高举双手,站了出来,大声念道:“她在丛中笑”。学生笑得爆棚,可是这种引领完全是庸俗的、错误的,因为词的美好意境被他彻底糟蹋了。 教学中的趣味性应该是引领学生去想象情境、润泽情感、启动思维,特别是通过情感的陶冶抵达思想的深处,通过智慧的点化进入生命的澄明、豁达之境,这才是美育的方式、趣味的方式,而不是诱使他们关注一些无关核心的内容,傻傻、浅浅地一笑而过,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方面,李镇西老师拿捏得颇为到位。学生集体朗读《荷塘月色》第一段后,他请学生点评,有的说读得结结巴巴,有的说掉字、换字,有的说读得太快,他趁机幽了一默:“嗯,对。是读得太快了。给人的感觉,朱自清不是在散步,而是在跑步。”学生轰然大笑,却一下子明白了朗读的症结所在,再读这一段,效果奇佳,很轻松地把握了节奏,想象了意境,体味了情感。这样的教学才是真正的美育,自然、生动而又育在其中! 于漪老师的教学趣味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理性之美。比如讲《孔乙己》,她这样导入:“鲁迅先生在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最喜欢《孔乙己》。为什么他最喜欢《孔乙己》呢?《孔乙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艺术形象?鲁迅先生是怎样运用鬼斧神工之笔来精心塑造这个形象的?过去有人说,希腊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是性格上的悲剧,而易卜生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孔乙己》这篇小说写的是悲剧性的人物。悲剧往往会令人泪下,而《孔乙己》读后,眼泪不是往外流,而是感到内心的刺痛。究竟是怎样的悲剧呢?”这种高屋建瓴的激疑,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具有极强的思想能量。话语甫出,便让学生站在了问题探究的制高点上。虽然令学生仰之弥高,但又并不感到高不可攀,探究的兴趣由此滋长起来。 王国维指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的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9]虽然有将美育置于手段、工具的附庸地位的嫌疑,但在那个实用至上的年代,对美育有如此的发现,并力图密切关注教育的和谐,以激发教育的生机,这对文质彬彬、美智相济的语文教育是一种褒扬,而对美智失谐,甚至有智无育、无智无美的语文教育,不啻是当头棒喝。当下的语文教育,对所学内容重识记、重操练、重验证,却将思辨、鉴赏、批判抛在一边;答题只求全面、不求深刻,只求规范、不求个性,使语文学科涵养心灵、提升生命质量的功能严重退化,整个语文教育开始肤浅化、庸俗化、恶质化……此时的审美教育,如果停留在附庸的地位,甚至连这级别也够不上,那么,说它“误尽苍生”也就一点儿也不冤枉了。 三、学养:倾情积淀,绚丽绽放 卡理斯玛型教师的“超自然能力”实际上是主体生命积淀的高效施展与实践,在追寻与创造语文教育之美的过程中则体现为学养的绚丽绽放。不仅要讲得明,而且要讲得美。将每一个问题视为生命拔节的营养,将每一次对话视为生命能量的分享,将每一节课上成张扬本质力量的精品…… 如许的思想已成了每一位优秀老师语文美育的自觉追求。上海特级教师卢元上《过秦论(上)》一课,从文气入手,组织教学,并提供了《古文观止》的点评,还有钱钟书先生关于该篇文章表现手法的评论,使学生不仅深入感受了秦孝公的虎狼之心,而且对一词统帅多句、叠用相同的调子、有意识的句式错综等形式秘妙有了非常具象的把握。辽宁欧阳代娜老师上《岳阳楼记》一课,从文中的两个“异”字入手,引导学生思考: ①既然前人之述备矣,已经说尽了,作者写这篇文章是不是多余? ②作者用什么词使自己的思路又打开了大门?其中哪一个词最关键? ③难道这篇文章只是一般性地描写洞庭风光吗? ④既然作者不同意悲、喜两种心境,为什么还要把它写出来? ⑤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不是多余? 上得新意迭出、贴心贴肺,上海师范大学的王荣生教授对之赞不绝口:“欧阳老师发现这篇课文‘美’的所在是‘思路与结构’的美”,“所谓‘美’,也就是优秀作品的核心价值,意思是说,阅读教学中合宜的教学内容要切入文本的精华、精髓所在”。[10] 可以说,这些老师举重若轻的背后,皆有深厚的学养在策策而动。没有渊深的学养,思想的爆发力、情感的冲击力、美的融化力,一切都无从谈起。追寻与创造语文之美的最高境界绝不是仅限于技术的竞争,而一定是指向学养的争奇斗艳的。这也是许多语文老师热衷于集体备课,指望着蹭蹭别人智慧,想使自己备课劳动量减轻,却无法育出理想效果的真正原因。 学养、美育不只表现在课堂,也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之中。一个语文老师,如果喜好阅读,视阅读为精神的旅行,他一定会将阅读的清新、淡逸传递给学生;如果他倾情写作,将写作当作自我生命的确证,他一定会令学生体悟到言语表现的神圣与美好。哪怕是寻常的聊天,他的热情、浪漫、智慧、爱憎、风骨、淑世情怀,也都会像荷花一样清芬四逸,令学生觉得他就是一首情韵丰富的诗歌、一支荡气回肠的乐曲、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 很多老师爱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不时有深山得宝的喜悦。殊不知,此书正是木心与弟子们闲聊出来的,可是轻松的闲聊之中,又处处洋溢着他智慧的灵光和高雅的情趣,给人以无尽的美的享受。比如聊到阿方斯·都德,他说: 都德,可说以心肠取胜。这个人一定好极了,可爱极了,模样温厚文静,敏感,擅记印象,细腻灵动。偶现讽刺,也很精巧。其实内心很热烈,写出来却淡淡的,温温的,像在说“喏,不过是这样啰”,其实大有深意——也可以说没有多大深意,所以很迷人。[11] 没有深度的生命融合,没有对人物性情的移情体验,没有对作品风格特色、言语表现之美的精心玩绎,说不出这样平易而深邃、大俗而大雅的话语。读他的文字,感觉就好像面对一位传说中的武术大师,随便的一招一式都透出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道、无法拒绝的美感。语文老师若臻此境,又何惧追寻与创造语文教育之美的效果不熠熠生辉? 但是,学养又不是临阵磨枪所能奏效的,必须有长期乃至一生的倾情乳入和历练。一如根深实遂、膏沃光烨,学问的根必须扎得深、扎得广,学问的油必须添得勤、添得足。甲骨文中的“育”字,状如妇女生子,上为“母”及头上的装饰,下为倒着的“子”,生子需要十月怀胎的发育生长,积淀渊深的学养同样需要长期地吸收和不断地内化。惟其如此,语文教师才能在追寻与创造语文之美的实践中驾轻就熟、化用裕如。既可以使学生在美的氛围中得到熏陶,也可以使自我在美的追求与建构中得以不断提升。 从这个角度说,“卡理斯玛”型教师对追寻与创造语文教育之美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