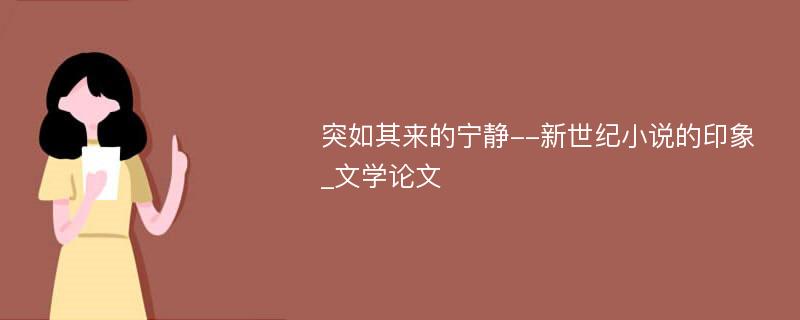
突然风平浪静——新世纪小说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风平浪静论文,印象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5-0058-06
一
我们有幸,在有生之年赶上了一次世纪交替,而且是千年之交。对自然时间来说,上 世纪最后一天与本世纪第一天不会有什么差别,人间世事也不会因为进入了新世纪就变 得焕然一新。所以我历来觉得每当换日历时便要大做各种文章,也就是图个热闹,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回顾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却感到真的有点不一样。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思潮与流派一个接一个始终未曾中断过。大致回顾一下( 不是科学的概括,也不严格按时间顺序),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接踵而来,到80年代中后期更是进入多元状态,现代派、先锋派 、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不一而足。进入90年代更加热闹,王朔现象、王蒙现象 、余秋雨现象、陕军东征、留学生文学、家族小说、新都市小说、女性文学、现实主义 冲击波、官场小说、新生代、断裂派、新体验、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等纷至沓来,差不 多平均一两年就会诞生一个喊得出名称的流派、思潮或现象。有人概括20世纪末的中国 文学是“众语喧哗的时代”,是说得很恰当的。[1]新世纪虽然才四年,但按上述频率 ,至少也应有两三个新的流派思潮产生,可是至今几乎一个都没有。有个“80后作家” ,影响似不太大。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映?
1986年秋,时值新时期文学十周年,中国文学界召开了几个颇为隆重的会议,其中在 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大家对十年的文学成就一片赞誉之时,一位年轻的文学博士发出了 惊世骇俗之声: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与会者多数是不能对此认同的。事隔两年,1988 年秋在无锡召开的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学术研讨会上,正是在当时不能接受危机论的学者 们中间,危机感像流感病毒般在会议上弥漫。前后两种危机感实际上是出于两种完全不 同的文学观。前者是对那时的繁荣感到危机,后者是因前几年那种繁荣不再感到危机。 我转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非正常态势中的正常化趋向》,认为这种令人担忧的局 面才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文章第一节“思想解放与艺术开放共同构筑的多元结构的 文学新格局”,就是集中阐述这一看法的。拙稿本拟在一家学术刊物发表并已发排,但 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我临时将稿子撤回。现在看来这次撤回并无必要,因此将有关的 一段话抄录如下:
新时期文学是冲决了在“文革”期间得到空前强化的极左思潮的压制与禁锢而崛起的 。它轰动社会、震撼读者,主要依靠其锐利和强劲的思想锋芒。对革命前辈的哀思,对 “文革”伤痕的揭露,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对改革的呼唤,展现了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观 念方面的超前性。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从文学观念上看,它基本是重视反映社会现实、注重文学的认识与宣教功能的传统文 学思想的复归,它的功绩在于否定了极左思潮对传统文艺观念的曲解,用“拨乱反正” 来加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它所复归的“正”,实际上只是文艺功能的一个方面 ,文艺还应有更为开放的姿态。这种复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既符合社会(读者)的需求,也受到作家队伍的思想与艺术准备的制约。因而,它显然 取得了成功,产生了至今仍使许多作家、评论家怀念不已的轰动效应。但读者与作家都 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社会思想的解放,也必然导致艺术思想的解放。于是,到了80年 代中期,主要不是以思想解放的深度见长,而是以艺术开放的广度为特色的各种新流派 、新风格、新手法的探索之作风起云涌,新时期文学进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艺术开放新 阶段。它是前一段传统文艺思想复归后的一个突破,是“拨乱反正”之后朝另一方向的 反拨。但是,它承袭了思想解放的发展趋向,因而并不是一次倒退。新时期文学的这个 发展轨迹,颇像一江春水不断撞击礁石而高潮迭起,后来注入平滩向四面八方流注,变 得开阔而平伏,难以形成高潮,覆盖面却宽广得多了。这种态势在1986年已经形成,所 以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人们已经很难概括当时文坛的主潮究竟是什么了。这几 年的文学形势正是沿着艺术开放的路逐渐形成开放的文学。以多元结构为特点的文学格 局已经形成,这是一种不带过多时代的政治风云印记的更为正常的文学构成,标志着新 时期文学走完了它的草创阶段,卸脱了我们的文学原先所肩负的过量的政治化与社会化 的历史重任,可以比较轻装地回到文学自身。
今天读这段话,是不是感到那时有点过于乐观了?但大意应该还是不错的。前些时看到 一篇文章,提到1988年10月18日,王蒙以“阳雨”的笔名在《文艺报》发表《文学:失 去轰动效应之后》,认为作家、艺术家应该关注文学艺术的常态,不要对文学的轰动效 应期待太高。看来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我说有点过于乐观,意思之一是政治的干 预确乎减少很多,但经济的制约却以高速度增强。文化产业提到日程上,通俗文艺方兴 未艾,对所谓纯文学来说,真正要回到文学自身依然步履艰难。但主要还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的金钱万能、物欲膨胀等负面效应,造成社会心态的浮 躁,自然也对文学创作队伍产生影响。一方面文学在按照自身的规律比较正常地发展, 另一方面又被社会转型期难以把持的骚动不安弄得六神无主。20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国文 学对社会的轰动效应失却了,其自身却仍众语喧哗热闹非凡,这也可以说还是一种繁荣 ,其实是正常化趋势中的非正常化态势。我感到,我们的文学既承受不了政治压力之重 ,也承受不了经济驱动之轻。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了20世纪文学的后半期。这样说不又过 于悲观了吗?那么,我想用另一个说法:中国当代文学既经受了政治压力之重,又经受 了经济驱动之轻,现在应该得到涅槃,能够软硬不吃刀枪不入地进入新世纪。由是,从上世纪末的众语喧哗到新世纪初的突然风平浪静,就不是偶然现象,正是顺理成章之事。时间只有四年,还不足以证实这一论断,但愿能预言成真。
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 平,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锻炼了百姓适应市场经济的承受力。许多过去不能想象难 以接受的事物,现在变得司空见惯,有些人甚至如鱼得水。都说中国人比较守旧,接受 新事物慢,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中国大地上近三十年变迁之大之快,在世界史上也不多 见,我们不还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吗!首先,这种奇迹般的变迁不是被洋枪洋炮打开而 是中国人自己自觉操作的;其次,开风气之先者总是少数,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其实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受到习惯势力的阻碍,这恐怕是全世界概莫能外的,关键是 新事物是否顺乎民心。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了20世纪后期的阵痛,已经进入了 一个比较平缓的时期。不是说没有矛盾问题了,有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尖锐和严重,但大 家已能比较冷静地面对。整个民族的心态相对比较成熟了。文学确确实实是社会的反映 ,我这里主要不是说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指作家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他 们的一切言动,也是社会现象的一种。21世纪中国文学相对平静的状态,正是这种社会 心态大趋势的必然体现。
20世纪末期中国文学众语喧哗的大合唱中,有一个重要的声部是国外文学思潮流派在 中国的回声,主要是20世纪以来各种现代(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有人说, 我们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介绍和演练了一遍。我感到 这未必是坏事。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进程是当代文艺的一股世界性潮流。由于国际交流更 加广泛和频繁,虽然各个民族和地区有其不同的审美传统和行进轨迹,但总的趋势是世 界文化的认同倾向。(当然世界文化的认同趋向不可能消解民族和地域文化特点,事实 上世界文化的认同趋向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点的强化是同步的,此处不详述。)交流是 双向的,可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个科学文化的现代化程度的差距,我们或许不愿意 却不得不承认,这种交流的双向发展是不平衡的,现代审美的潮流是向西方倾斜的。这 在建筑、服饰等方面表现最突出,文艺方面也有反映。在社会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共同性的问题。譬如环境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批评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的环境污染,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也不小。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必然也会在精神领域 内得到反映,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现在我 们遇到了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有些问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得到呼应也就不足 为怪了。由于以上种种积极面或消极面的原因,又由于建国之初近三十年对西方文化的 基本拒斥,近二十多年匆匆忙忙的“恶补”,是无可回避有利有弊的过程。现在“补” 得差不多了,可以立即引进的现成思想资料也已不多,需要的是原创能力,难度就更大 ,这可能也是新的思潮流派不再雨后春笋般疯长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与上述两点有关,但我认为更加重要。今日作家更具主体意识,心态 也更趋成熟,他们将主要精力投入自己的创作,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轻易跟风,也 不轻易提口号发宣言。流派蜂起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确实是文学繁荣的表现之一;相 对寂静不一定是好事,冷冷清清也不是正常的文坛。我们期待的是脚踏实地的创新而非 哗众取宠的喧嚣。
二
看待事物的发展,当然不能只看它消失了什么,更要看它产生了什么。无所作为也就 无从体现其价值。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不断有力作诞生,常常使人眼前一亮。虽然没有旗 帜鲜明、队伍强大的流派涌现,但宏观地看,各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追求中,却也有着 某些不约而同的相近特点。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2003中国中篇小说年选·序》中,以 不长的篇幅,用漂亮的文字精当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从中也体现了他的 文学观。在对当代文学某些现象进行批评之后,他对当前文学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虽然 依旧有所保留:“很多人注意到了,当前的文学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正在酝酿 着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可能性。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当然 也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2](P5)我认为,这样归 纳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发生的变化,或者说新世纪一部分作家的追求,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把2000年的作品也算入21世纪文学的话,毕飞宇的《青衣》可以说是新世纪小说 的一朵报春花。这个中篇的故事框架是由京剧演员筱燕秋与师傅和徒弟的两次争台构筑 而成的。表面上看,争台就是争风,争风就会嫉妒。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内涵要丰富得多 。小说中有一段关于青衣的妙论,这不仅是一段戏经,而且是解读作品的钥匙。“青衣 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或者说,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是女人的极致境界。”筱燕秋是 天生的青衣。《奔月》就要真正的青衣来演。看了筱燕秋的彩排,团长由衷地说:“你 真的是嫦娥。”这戏台本应是她的,不必去争才对。可惜,筱燕秋既不能真像青衣那样 虚无,更不能像嫦娥那样奔月,她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带给她的只是深深的痛,这里用 得上一句老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毕飞宇说:“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 一,性格,二,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的和虚拟的双重世界。筱燕秋的 身上最让我着迷的东西其实正是这两样。有一句老话我们听到的次数太多了,曰:性格 即命运。这句老话因为被重复的次数太多而差一点骗了我。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想说, 命运才是性格。”[3]这是说,虚拟的(又是实有的)命运决定了性格。套用这个句式, 似乎可以这样说:小说中的人物也有两样迷人的东西,一是故事,二是心理,它们构成 了现实和虚拟的双重世界,筱燕秋让我们着迷的东西也是这两样。读了这部小说,我想 说,故事要走向人物的心性世界。
在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上,《青衣》名列中篇第一;在2003年的排行 榜上名列魁首的则是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后者依托了一个入户抢劫案件来展开 故事,但破案只虚晃一枪,引出的是一对原本恩爱和美家庭的感情危机。这也是一部透 过故事直奔心理的作品,对一个现代女性精神世界、心灵奥秘的展现丝丝入扣,细密精 致。须一瓜就这样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举重若轻地叩问人性,意味隽永,令人深思。
举一些个别的例子来得出某个宏观的结论,是很不可靠的论证方法。任何观点都不难 找出个别的例证。那么,我们再作一次随机的观察。我手头有一本最近的《人民文学》 (2004年第9期),卷首编者“留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本期的小说中,鬼子的 《大年夜》、王松的《血疑》、须一瓜的《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赖妙宽的《 右肋下》,它们恰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灵魂’,我们的不堪直面但必须直面 的灵魂。”“灵魂”是什么?不就是精神,就是人内在的心理、心性、心灵吗!这里说几 句我们天津的作家王松。“留言”中提到的《血疑》和“三红”(《红汞》、《红风筝 》、《红莓花儿开》,分别发表于《收获》2002年第3期、2004年第1期、2004年第4期) 是王松近年创作的“童年系列小说”。王松生于1956年,“文革”开始时正好10岁。他 的有记忆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的。王松的这组多数用童年视角言说的童年小 说,观照的正是无邪的童年灵魂是怎样被无形的罪恶之手所扭曲的。“审恶”和“拷问 ”是王松小说的两个关键词,所涉及的对象就是人的灵魂,即“我们的不堪直面但必须 直面的灵魂”。在上述作品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谢有顺所说的“对文学本身的追问, 当然也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
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 ,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4](P81)文学大师如鲁迅者,也 是把对灵魂的追寻看成文学的至高目标的。这么多年绕来绕去,有些根本的东西总是绕 不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得到体现。新世纪小说中我们看到了 作家的新追求,这新追求其实还是文学本原的东西,但确有新的风貌。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有过一次“向内转”的潮流。那次重心理世界的探求 由于更多考虑文本实验,重叙事形式而轻故事轻性格,脱离了大众审美习惯。正如当时 有人所说,文学“向内转”,读者“向后转”。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派与先锋小 说潮落,“向内转”不再提起。上述新世纪小说一般不离开故事,也重视叙事形式,但 小说的叙事却是透过故事直逼人物的心性世界,无情地揭示人物灵魂最隐秘与最不可告 人的深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作品的叙事既重视故事又超越故事的建构,更超越 了叙事的则是对人的心理世界、精神蕴含、人性观照乃至生命意识的探幽。这是新时期 文学的又一次“向内转”,比之于前者则更为沉实而不虚幻,它既不排斥故事又不拘泥 于故事,追求叙事的创新又不沉溺于纯形式的技艺探索,用艺术的表现手段,深入到心 灵与精神层面,使文学名副其实地臻于人学的领域。面对这样的“向内转”,读者是不 会“向后转”的。我想,这应该是文学(或者说“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向。
有一位作家在本世纪初提出“现实主义的现代化和先锋小说的本土化”[5]作为对当前 文学现象的一种概括,是很有启发性的。在新世纪初比较有影响的作品,确实有不同创 作方法与思潮互相交融的现象。所谓第二次“向内转”就是具体表现之一。20世纪80年 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可以说是一次类似的尝试,本世纪初的小说虽不标榜或被定义为某一 流派,但不拘于一格的创作取向显然更趋成熟了。
当然,文本实验不会也不应终止,叙事形式的创新也是作家永恒的追求目标之一。较 近的作品,长篇如韩少功的《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莫言的《四十一炮》(春 风文艺出版社,2003),中篇如晓航的《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人民文学》2004年第 8期),虽不一定是先锋文本,但叙事都别具一格。
这里要解释一下,本节所述新世纪小说的特点,只是从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内概括出来 的,肯定是局部的乃至片面的,只能说是一个初步印象。按说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长 篇小说的创作应该更有代表性,但本文基本没有涉及。一是我对中短篇小说相对更熟悉 一些;二是我感到中短篇小说能更迅速地反映创作的发展动态。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我 国新时期至今的文学,以中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尤其中篇小说的繁荣是新时期文 学的一大亮点。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二十多年是中篇小说最辉煌的时代,即使在世界文 学史上,这个现象恐怕也是值得一提的。而且在新时期文学中,代表小说创作最高水平 的,是中篇小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文体,如唐诗、宋词、元曲,如果要说迄 今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文体是什么,我认为是中篇小说。中篇小说在新世纪仍方兴未艾, 这个现象值得专门研究。以前曾有人对此关注,现在有了更丰富的实践成果,研究当可 更深入一步。
三
进入21世纪,中国新时期文学随之进入了新世纪文学阶段。新时期文学当然可以延伸 到新世纪,但这样无限延伸,毕竟会遇到一些难办的问题。例如,中国现代文学才30年 ,而当代文学已经55年了,看来还要延续下去。但“当代”应是一个有一定时限的概念 ,延时太长还能叫“当代”吗?“新时期”也一样,一个“新”字也限制了它的时长, 一旦(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更加新的新状态,那么又该怎么命名。所以,曾有过“后新时 期”的提法。这使我们想到了“后现代主义”。说“后现代”是对现代主义的推进也好 ,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也罢,它毕竟与现代主义关系紧密,加一个“后”字虽然缺乏创 造力,但也无不可。对“后新时期”大概也可作如是观。如对已经有55年历史的中国当 代文学要是加一个“后”字,就有点不伦不类了。有学者运用了“共和国”文学的提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似不应简称,而应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因为“共和 国”是一种政体,全世界有好多个,没有指位性,所以还是讲准确了为好。在大学中文 系将“中国当代文学”课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回归前 的港澳文学与尚未统一的台湾文学怎么办,恐怕就要另设一门台港澳文学的必修课以在 教学中保持祖国文学的完整统一。
其实,文学史的分期与命名可以用各种参照系作为标尺,既可不拘一格,也难有十全 十美的界定。参照历史学的分期,将文学纳入其中,我们现在说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正是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构成一个系统,是能自圆其说的。如将当代文学改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学”,现代文学则应称为“中华民国文学”,古代文学本来就有先秦文学 、汉代文学、唐代文学一直到清代文学,这原是沿用了许多年的传统提法,当然也不失 为一种文学史分期的命名体系。有人反对按照政权更迭来进行文学分期,因为文学有其 自身发展规律,不一定围绕政治变迁而转变。这肯定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 政权变化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非惟现当代如是,古代也一样。所以 用诸如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来分期与命名,要比6世纪文学、7世纪文学、8世纪文学等 更能说明问题。但作为一个时期特殊的文学状态,我认为提出“20世纪文学”这一概念 是很有创见的。将20世纪的百年文学贯通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肯定能开拓研究视野,达 到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段观察所难以实现的宏观把握。但是实际上,在 20世纪文学研究中,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还是客观存在的,在整体中肯定有个体, 在联系中肯定有分野,只是整合方式的不同而已。我提出这个看法是因为中国文学进入 21世纪后,它既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延伸与发展,又可以说是当代文学或更确切地说 是新时期文学的延伸与发展。如果视为前者,即使是延续,也不能说是20世纪文学发展 的一部分;如果视为后者,它虽有变化,但依然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学(称之为当代文学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均可)的新阶段,仍是整体的一部分。由此可见,“20世纪文学 ”的提法,往前看,确实是把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的文学整合起来,十分科学; 但往后看,这样以世纪划分却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文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隔裂开 来了,产生新的弊病。所以我认为文学分期也应允许多元共存,可根据研究、教学等不 同需要采用不同参照系统的分期法。
最后我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如果还保留中国当代文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这个大概 念不变,从1949年10月起,可以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 时期文学(大致从1987年开始)、21世纪前十年文学,此后如无特殊情况,则以年代为序 ,如21世纪20年代文学、21世纪30年代文学等依次类推。也可不用“后新时期”的提法 ,改称20世纪90年代文学。这未必是科学的分期法,只是为了表述与教学的方便姑妄言 之。
收稿日期:2004-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