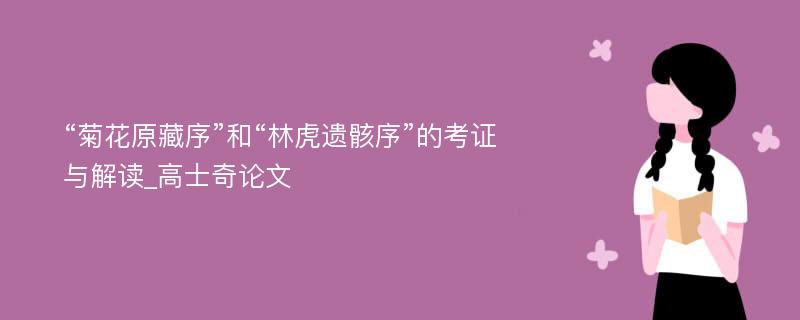
《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稿论文,菊磵集原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0)06-0134-11
在《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中,有人寻出南宋王晞《林湖遗稿序》,序中有“该二十四品”一句,惹人注意。束景南先生撰《王晞<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辨伪》(载《中国诗学》第五辑第45-47页。以下简称“束文”),经束先生论证,判断王晞《序》为伪托之作。我读“束文”,觉得所举证据多有不实,伪托之作的判断不可靠。特就来历相同的《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加以考释,聊表愚见。
上篇
一、《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的来历
为便于说明问题,交代一下《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的来历是必要的。《四库全书》集部四收录南宋人高翥《菊磵集》。此集前有元人姚燧撰于元贞元年(1295)的《菊磵集原序》,原序后又有高氏后裔清康熙间高士奇的《后序》。《后序》曰:
菊磵……淳祐元年(1241)卒于湖上,年七十有二,葬葛岭谈家山。……余十四岁从先君子归姚江……自是住深柳读书堂者两月。堂为先曾祖讲学之所。……高氏家祠在堂之西偏,规模弘敞,堂室门庑毕具,族人子弟肄业其中。堂后楼五楹,藏当年诰勅书籍,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缺略不全。询诸父老,云自明嘉靖间遭倭寇焚掠,散失殆尽,亦无从得其遗本补辑之。若节推(高远)、县尉(高迈)之诗,仅存数首。又有质斋、遁翁,谱失其名,诗亦清逈。余恐残板久复漶漫,洗而录之。顷在都门,从御史大夫徐公(徐乾
学)所藏宋板书籍中,得“菊磵诗”一百有九首,合向之所录三十二首,又于他集中得十三首。顷同年朱竹垞从宋刻《江湖集》中搜示四十七首,统计重出者十二首,前后凡五七言近体诗一百八十九首。窃念先贤遗稿忍使湮没不传,遂併南仲(高鹏飞)、节推、县尉之诗同付剞劂,而附质斋、遁翁诗
于卷尾。
高士奇这段叙述的核心在于“堂后楼五楹,藏当年诰勅书籍,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缺略不全”几句。我们要考查的问题,这几句已点出了题目:《菊磵集》可是真的?“南仲诗”——《林湖遗稿》可信吗?“姚承旨原序”(即姚燧《菊磵集序》)是真的吗?“王学录原序”(即王晞《林湖遗稿序》)是真的吗?
为什么有些疑问?问题在于“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的录存者、刊布者皆是晚生数百年的高士奇一人,旁证较少;他的叙述可靠与否,值得逐项考查。待考查后自然会得出结论。
二、今见的《菊磵集》,确为高翥所作
关于高翥的生平,在元人姚燧《菊磵集原序》、清人高士奇《菊磵集后序》中有记载,《四库提要》从而有简要说明。《提要》曰:
《菊磵》一卷,宋高翥撰。翥字九万,号菊磵,余姚人,孝宗时游士也。
所谓“游士”,姚氏《原序》曰:
讳翥,号菊磵,世居越之余姚;少颖拔不羁,抗志厉节,好读奇书,厌科举学……隐居教授,师道尊严……萧然游憩,操觚咏歌。凡所交皆硕士。既而游钱塘,越金陵,浮洞庭、彭蠡……耄年耽西湖之胜……遂卒于寓舍,葬杭之葛岭谈家山。
高翥的具体生卒年代,高士奇《后序》曰:
淳祐元年(1241)卒于湖上,年七十有二。
据此可知:高翥生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
今见的《菊磵集》存“五七言诗一百八十九首”(见《四库》本)。这“一百八十九首”诗是怎样搜求、编辑成书的,上引高士奇《后序》已经说明,不赘。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徐乾学、朱彝尊两位当时有声名的学者曾从旁协助高士奇搜寻“菊磵诗”,足见徐、朱两位是《菊磵集》成书的知情人。又,高士奇撰《后序》时,徐、朱两位都健在,这表明高士奇不敢牵扯徐、朱两位来作伪骗人。因此我认为,今存的高翥《菊磵集》,虽是经后人之手辑录而成的,但所录来自宋本、元抄本(即姚序所说的“家传”本),可信。
还有一点旁证。姚《序》说,高翥的侄儿高鹏飞,痛惜高翥叔父“文墨外遗,十亡八九,残编缀之,断简拾之,仅存百七十章,成集而家传焉。今曾孙师鲁者持其集属予序……于是书其要于卷首。”姚《序》中所记的“一百七十章(首)”,与高士奇所录存的“一百八十九首”这两个数字,共同证明一个问题:从元高师鲁到清高士奇,搜寻高翥诗,搜来搜去,两种本子数字极其相近。这也从旁证明今见本《菊磵集》是可信的,而不是高士奇伪造的。
三、“南仲诗稿”—《林湖遗稿》,仅存十九首
据宋·王晞《林湖遗稿序》、元·姚燧《菊磵集原序》、清·高士奇《后序》记载:高鹏飞,字南仲,南宋光宗“绍熙壬子,治《诗》领乡荐,其后屡屈廷试,遂弃仕进,隐居林湖,日与士大夫讲明正学”(“正学”指“理学”—笔者),并以吟咏自娱。曾为族叔高翥辑录散失诗稿,“成集而家传焉”。由此可知他有重视家族先贤遗稿的美德。在今见的《菊磵集》中,有《喜南仲侄来》一律,诗曰:
自从清晓到黄昏,间坐间眠深闭门。犹子雨中来息担,老夫灯下起开樽。
故山坟墓何人守,旧宅园亭几处存?问答恍然如隔世,若非沉醉定消魂。
这首诗反映了他们叔侄之间的亲情,也透露了他两人年龄差距不太大,否则为叔的不必“灯下起开樽”以示款待;为侄的已能主持家务、关注家族,这才能与叔父对饮答问。为叔的自称“老夫”而为侄的尚可“雨中来息担”,暗示叔侄都在壮年,不过叔叔年长几岁罢了。
高翥此诗作于何年,无可考。
“束文”说:“绍熙壬子,高翥方二十三岁,时高鹏飞领乡荐,当亦二十来岁,同高翥年龄相差不多,这同高翥在高鹏飞面前自称‘老夫’相矛盾。”—请容我问一句:凭什么判定高翥此诗作于绍熙壬子(1192年)?高翥已是壮年,在侄儿面前称“老夫”,有何不妥?欧阳修虚龄三十九便称“醉翁”,你没奈何吧?应该说,所谓“相矛盾”的大前提是束先生强加的。
高鹏飞诗,今存十八题,计十九首,附录在《菊磵集》后。在“高鹏飞”名下,注《林湖遗稿》。显然,这“注”是编辑者加的。
这十九首诗,就题材看,不外“湖上”、“咏梅”、“晚兴”、“游鄞江”、“深夜风雨怀故人”之类,表明其作者安于生活在“林湖”(地在余姚西境),偶尔到过“鄞江”(今宁波境南),生活圈子较狭小。从诗的抒情角度看,“最喜今朝雨,川原足暮耕”(《窗轩》)、“对人不敢语,仰面数归禽”(《孤呤》)、“原草正肥黄犊饱,汀苹未老白鸥间”(《文亭渡阻风》)、“松荫满迳归来晚,醉看岩花笑白头”(《晚兴》)等,显示一点村夫子的闲情逸趣。王晞在《序》中夸高鹏飞诗“脱弃凡近”、“绝无蔬笋气味”,似是溢美之辞。
高氏后裔,如高师鲁、高士奇有意录存先贤遗稿,可借此宣扬诗书门第,人们可以理解。如果从文学史角度看,这十九首诗何足道哉。
高鹏飞的十九首诗,是由高士奇录存、刊布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怀疑这十九首诗是托名高鹏飞的伪作,我就不再饶舌了。
四、姚燧《菊磵集序》疑点可解
高士奇在《后序》中说:他见过“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曾见过“旧刻”?没有,我们只好听之而已。
今传本《丛书集成·牧庵集》(即姚燧的诗文集)中不见《菊(同磵)集序》,这是否意味着所谓“姚承旨原序”是伪托之作?我以为这不足以断定姚《序》是假的,因为《牧庵集》乃是后人缀辑成书的,多残缺。《四库提要》指出:
刘昌辑《中州文集》,所选(姚)燧诗,较《元文类》多数首,文则无出《(元)文类》之外。(刘)昌跋称《牧庵集》五十卷,今所得乃录本,多残缺,视刻本仅十之二。
显然,我们不能根据残缺本一口断定姚燧《菊磵集原序》是假的。
我认为姚燧《菊磵集序》可信,依据有三:
甲、姚《序》明确交待此《序》是应高翥的曾孙高师鲁的请求写的,又说:“予与高氏斯文久契,序可得而辞乎?”这也侧面表明:写此序,出于人情酬应而已。《序》末写明“元贞元年春三月”,是年姚燧五十八岁(见《牧庵集·附录<年谱>》)。又,高翥卒年为淳祐元年,享年七十二。按通常二十五岁左右有下一代计算,元贞年时,高师鲁年在五十左右。姚《序》提及高师鲁以长者口气出之,乃是当然的。
乙、姚《序》末署衔“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与刘致所撰姚燧《年谱》记录基本相符。《年谱》曰: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先生五十七岁
……书遗直省舍人札哈勒台,以朝请大夫翰林学士召,与高道凝同赴。
元贞元年乙未
先生五十八岁
与道凝同修《世皇实录》。
附白两点:一是我之所谓“基本相符”指元贞元年姚氏已有“翰林学士”衔,而此衔后加“承旨”二字则后几年的事。不过我以为《原序》原是手抄稿,在传抄中加了“承旨”二字。在传世旧籍中,这类事何止一端!二是《元史·姚燧传》中提及“侍读高道凝”,《牧庵集》诗词标题中亦提及“高侍读”。这位“高侍读”与余姚高氏家族有无关系,待考。
丙、姚《序》叙高翥生平、家世较具体,这是根据高翥的后裔提供情况(或材料)才能如此。这也表明姚《序》的可信性。
以上四部分,算是“上篇”,所论无对立面,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下文将讨论王晞《林湖遗稿序》的真伪问题,因有判定王晞《序》为伪托的意见在先,因而行文不得不从对立面说起,标为“下篇”。
下篇
一、关于高鹏飞“领乡荐”问题的讨论
“束文”说:
《序》称“绍熙壬子领乡荐”亦不实。康熙、乾隆、光绪诸《余姚县志》“选举表”中,载有各年乡贡之人,而于绍熙壬子之下,独无高鹏飞,可见均不信《序》中之说。
上引一条,看来好似举出了否定王晞《序》的有力证据,实际乃是对“领乡荐”与“乡贡”理解有差误。请看史实,《宋史·选举一》:
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初,礼部贡举, 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 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
景德四年……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 复审察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诸州解试额多而中者少,则不 必足额。……
(元祐)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 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 听习一经。
又《宋史·选举二》曰:
绍兴元年,当祀明堂,复诏诸道类试。
这里,先解释几个词语:
“领乡荐”—领,受也;“领乡荐”,即士子受到了州县的推荐去应试(省试)。
“乡贡”—由州县荐举,经省试合格者称乡贡。
“取解”—解,送也。“秋取解”,即秋季各州向礼部上报选拔乡贡名单。
“类试”—乃“类省试”的简称。宋周密《齐东野语·二李省试》条:“李壁季章、埴季永,同登庚戌科,已酉赴类省试。”可知“类试”是宋代考试的名目之一。
现在,再说明高鹏飞“绍熙壬子,治《诗》领乡荐,其后屡屈廷试”的问题,同时说清“束文”对“领乡荐”的误解。
高鹏飞于“绍熙壬子”受到州县的荐举,理由是他“治《诗》”符合当时规定的“听习一经”条例;但他在类省试中不合格,当然没有“乡贡”头衔,后世修《余姚县志》也当然不列他的姓名。请看,宋·徐铉《稽神录·赵瑜》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又,生当宋元之际的方回,有《滕元秀诗集序》,曰:“绍兴二十九年已卯,以《书经》领乡荐,屡上南宫,不第。”这都可以视为高鹏飞“屡屈廷试”的先例。“绍熙壬子”与“其后”相呼应,表明屡遇廷试之年,高鹏飞皆屈不能伸—参加廷试而不第。
我检阅了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九《选举表》,所列高氏家族的,在“乡贡”栏中有“宣和五年癸卯,高选”(原注:“康熙志题‘乡举’、乾隆志题‘举人’”);“绍兴十八年戊辰,高选”(原注:王佐榜,武当军节推);“隆兴元年,高翥”(原注:累征不起)。又,《余姚县志·选举表》乡贡栏自绍熙元年庚戌(1190)至绍定五年壬辰(1232 ),历时42年,期间只有“开禧元年乙丑”(1205)有“赵彦(悈)”一人,其余全为空白。“束文”所谓“于绍熙壬子之下,独无高鹏飞”,流露出耸人听闻的神情。何必呢?
二、王晞《序》末那样署名,可疑吗
“王学录原序”末,署曰:“时嘉泰甲子秋九月望后三日国子监学录致仕王晞平父序。”这就是关于王晞的直接资料。又,《宋会要辑稿》第一五三册《食货》六二记载:“(乾道)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前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王晞言:乞依行在省仓监官体例、任满推赏。户部下司农寺指定:欲依绍兴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降指挥,比附行在省仓监官体例,与减二年磨勘推赏施行。从之。”(中华版第5979页。又同书《食货》五四所载,与引文全同,只“王晞”误作“王晞”,见第5742页)但“仓监官”王晞是不是“学录”王晞,待考。
现在,我们来考查“王学录原序”的署名:
“嘉泰甲子”即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
“国子监学录”,官衔。《宋史·职官五》曰:“凡诸生之隶于太学者,分三舍。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以试补中者充外舍。斋长、学谕,月书具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呈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学正,次博士,然后考于长贰。岁终校定,具注于籍,以俟复试。”
“学录”主管什么?《宋史·职官五》曰:“职事学录五人,掌与正(学正)录(学录)通掌学规。”
“学录”为几品官?《宋史·职官八》曰:“国子太学正(学正)录(学录),武学谕,律学正……为正九品。”
据上述,可知王晞是个国子监里的教辅工作人员,位九品,相当于今时的正科级干部。
“致仕”在宋代有规定,《宋史·职官十》:“咸平五年,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王晞末称“致仕”,表明他在嘉泰四年时(1204)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
“王晞平父”:表明王晞字平父(“父”通“甫”,男子之美称也)。
王晞《序》末署名,未提乡贯,我们也难于考查。我曾因《序》中“集诗数百以示予,而请予序以遗子孙”句,揣度王晞与高鹏飞乡贯有关,于是遍查南宋时绍兴府所辖八县(会稽、山阴、嵊、诸暨、余姚、上虞、萧山、新昌)旧志,也不见“王晞”的名字。我们无法断定他的籍贯。
王晞《序》那样署名,有什么破绽吗?我以为所署官衔、名字,皆符合当时文人作序作记署名的常情。这只要翻阅多产作家苏轼、陆游的诗文集,便可取证。
然而,“束文”说:王晞是“王氏中有声望者”;王晞)《序》末那样署名,“宋人亦无此用法”。恕我直言,这是夸张失实的判断。王晞,九品微官,算不上有声望,此乃事实,不必多说。至于署名“宋人亦无此用法”,那就让我举几个实例以见问题的真相。试就陆游《渭南文集》举例:
甲、《云安集序》,文末曰:“且属通判州事承议郎山阴陆某为序。(乾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序。”
乙、《范待制诗集序》,文末署“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山阴陆某序。”
丙、《王侍御生祠记》,文末署“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议郎通判军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陆某记。”
丁、《铜壶阁记》,文末署“(淳熙)四年四月乙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陆某记。”
按:上列类似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宋人亦无此用法”的判断站不住脚。附带说一下:宋人为他人写序作记,署名带官衔与否,视情况而定,权衡在于作者,别人不能硬性规定。
三、王佐与《赠王佐时思庵》诗,全不相干
“束文”中,有这样一段考证,令人惊诧。文曰:
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四《尚书王公佐墓志铭》云:“公(王佐)娶同郡高氏,早卒。”《林湖遗稿》中亦有《赠王佐时思庵》诗。据此,疑王晞与王佐为同宗同辈人,可见高王二家关系甚密,载之二家宗谱,故高氏后裔冒用王氏中有声望者作序以相鼓吹也。
按:这段考证的要害在于把“王佐”和“王佐时”视为一人,更进而把“王佐”和高鹏飞、王晞联系起来。这种张冠李戴的考证,怎不令人惊诧!容我申述如下:
(1)人们读《尚书王公佐墓志铭》,不应忘记“惟公讳佐,字宣子,会稽山阴人。”他没有“时思庵”这个雅字。又根据古人名字连署的习惯,《赠王佐时思庵》的受赠者姓名“王佐时”字“思庵”。此乃常识,不赘。
(2)据《尚书王公佐墓志铭》,王佐于绍兴二十九年、三十年,亦即三十四、三十五岁时,官“起居郎,遇事直前献纳”,“除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权户部侍郎。”淳熙六年,王佐五十四岁,因平乱有功,“徒公知扬州、平江,遂知临安府”,是宋孝宗所依靠的重臣。如果说,《赠王佐时思庵》诗受赠者是王佐,而作者是“绍熙壬子,以治《诗》领乡荐”的青年举子高鹏飞,竟敢在诗题中对王佐直呼其名,岂非怪事!可以断言,这是社会礼俗不容许的。
(3)王佐生于靖康元年(1126),卒于绍熙二年(1191),享年六十六。这有陆游《尚书王公佐墓志铭》可据。而高鹏飞《赠王佐时思庵》诗,如果作于绍熙壬子(1192),则王佐已死一年,怎会有诗相赠?如果把高鹏飞作赠诗之年向上推移,则越暴露对王佐直呼其名的荒唐性。
归总两句话:王佐不是王佐时,明乎此自然不会有如此荒唐事。
(4)“疑王晞与王佐为同宗同辈人”。请问,靠“疑”来判断问题行不行?我以为,猜测的事不经证实,是不能肯定的。王佐“娶同郡高氏”是事实,但不能凭这点事实作为大约六十年后王晞为高鹏飞诗稿作《序》的证明。何况王晞与高鹏飞是不是“同郡”还得不到证实。
四、凭空揣测的提问
“束文”中有这样一段提问:
奇怪的是,宋以来历经战乱焚掠,质斋、遁翁、高翥、高鹏飞的诗稿十亡八九,高士奇说高氏家祠藏的《菊磵集》已只有三十二首,质斋、遁翁诗仅存二三首,而何以独姚燧、王(同晞)二序能完好一直留存下来?
请注意,这段因为“奇怪”而产生的提问,其依据摘自高士奇《后序》,不过两者意图恰恰相反。《后序》叙亲见亲闻,目的在于使人相信;而“束文”提问,只是凭空揣测,目的在于使人生疑,进而否定“姚燧、王晞二序”的存在。读者在“可信”与“生疑”之间,不得不加以辨别。我的辨别如下:
(1)《菊磵集》抄存“旧刻”残遗三十二首,后经徐乾学、朱彝尊帮助成书,可信。
(2)《林湖遗稿》只剩十九首小诗,附录在《菊磵集》后,此乃余姚高氏家传抄本,我们凭什么生疑而否定其存在?
(3)“束文”提问的潜在大前提不真实。请看,高士奇《后序》说,高氏家词藏书,“自嘉靖间遭倭寇焚掠,散失殆尽”—殆,几乎也。“殆尽”即有少量还存在。而“束文”暗暗认定“姚燧、王晞二序”“历经战乱焚掠”而被焚或只剩残稿,从而提出疑问。显然,这提问的大前提,无实据,不可信。相反,高士奇说,据“旧刻”残余,录存了“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我们仅凭张冠李戴、误解史实的考证加以否定,斥之为“伪”,行吗?照我看,不行。
“束文”为什么提出奇怪的提问?让我一语道破,只因王晞《序》中有“该二十四品”一句触犯了他的主观愿望,于是撰文斥王晞《序》为伪托,姚《序》跟着遭殃。
五,对王《序》评高诗的失常“理解”
王晞《林湖遗稿序》评高鹏飞诗曰:
予阅南仲诗,词体浑厚,风调清深,脱弃凡近。……其始其终,绝无蔬笋气味,无斧凿痕迹,可见其能参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得藻丽之妙,诚能全十体、备四则、该二十四品、具一十九格,非浅陋粗疏者所能窃也。
“束文”就上引王《序》评语大加训斥而有失常的判断,文曰:
此说荒谬绝伦,令人笑倒。……如此不可能之大话,唯有出自无知之高氏后裔吹捧高氏先贤之口,才可理解。作序者之对“二十四品”等诗说如此之一无所知,也只能证明此说是出自无知之高氏后裔盲目抄袭搬用他人之说。
面对以上两条资料,我这么思忖:
(1)王《序》为高诗吹嘘,夸张太过,是可以理解的。应人之请为之作序,因而吹捧几句,虽在大家,亦所难免,如杨万里于嘉泰元年撰《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说:“《训蒙》之编,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乎晚唐之味矣!”杨万里对《训蒙》读物不得不如此吹捧,王晞对“南仲诗”吹捧几句,何必大惊小怪。应该说,这也属于人之常情。
(2)说王《序》吹捧高诗,有“搬用他人之说”的缺点,这只表明作序人诗论水平问题。试检旧籍,可知王《序》搬弄的是唐人李峤《评诗格》、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及流行于宋的作诗讲究“字、句、意、趣”的所谓“四则”(或称“四体”。参见陆文圭《跋陈元复诗稿》)。我以为,这正反映“王学录”的诗学水平,不足为怪。
(3)我所大惑不解的是:这篇被判为“荒谬”的序文,束先生凭什么能断定它不是王晞之作,而是“出自无知之高氏后裔之口”?
“束文”曾说南宋王佐“娶同郡高氏”,并进而经数百年演变,而有“高氏后裔冒用王氏中有声望者作序以相鼓吹”的事—这只是凭空揣测,算是“大胆假设”吧,那也应该“小心求证”嘛。“证”在哪里?“束文”未作任何明确交代。因此我不得不说:训斥“无知之高氏后裔”,姿态虽高,却不是证据。
顺带说一点:我为高士奇庆幸,他是著名的多见异书的学者,是“高氏后裔”,当不在“无知”之列。他不视“王学录原序”为“荒谬绝伦”,故录存之。岂料这篇序却成了今日某几个论者的眼中钉。
六、结束语
下篇所述五部分,指明“束文”多处论证失误,而其失误的总根源,我以为在于他对“陈汪的考证,我以为证据确凿”,从风跟进。请看,“束文”说:
陈尚君教授与汪涌豪博士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中,提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不是晚唐司空图,可能是明代景泰年间嘉禾(今浙江嘉兴)人怀悦。在怀悦的一部专论作诗与观诗之法的《诗家一指》中,有一部分名为《二十四品》,不仅与《二十四诗品》品名相同,而且每品韵文也相符,由此推断今传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实出于《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部分,是明末人将其取出,伪题为司空图之名行于世。陈汪的考证我以为证据确凿。
于是束先生接到陈尚君教授寄给的《林湖遗稿序》后,加以考证,考出:
这篇伪王晞《林湖遗稿序》的“全十体,备四则,该二十四品”是抄袭了怀悦《诗家一指》的“明十科,达四则,该二十四品”。
听束生先的口气,原来“可能是”的问题,经他一考,便正式证成“《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明代景泰年间嘉禾人怀悦”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张健先生觅得元人托名虞集撰的《虞侍书诗法》,其中录有《二十四品》,也有“由此可以明十科,达四则,读(该)二十四品,观之不已,而至于道”云云。这便有力地推翻了“《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明代景泰年间嘉禾人怀悦”这一新论。当然,这也推翻了“束文”的根本论点、论证。
又是张健先生,觅得刻于明“成化二年岁次丙戌”、署名“嘉禾怀悦用和编集”的《诗家一指》。怀悦在《书<诗家一指>后》中说:
余生酷好吟咏,然学而未能。……一旦偶获是编……日阅数四,稍觉有进。今不敢匿,命工绣梓,与四方学者共之,庶亦吟社中之一助耳。
这是铁证,证明:一是怀悦花钱刻印前代留下的《诗家一指》,他也是这书的推销者;二是他老实地自称“编集”。“编集”不等于“作者”,这不用多说。
最后,我想说一下,《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是真是伪,还可以讨论;我的《考释》是不是一偏之见,听候方家裁判。不过,我认为“束文”所论无实据,站不住脚,则是无疑的。
庚辰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