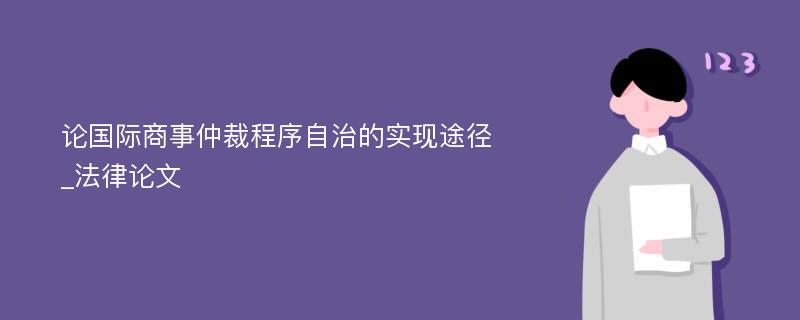
论国际商事仲裁实现程序自治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事论文,路径论文,程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普遍地采取领域标准决定仲裁程序法的适用,但仲裁程序法范围内的仲裁程序自由却非常之广泛与充分,可以说,仲裁程序的自由化程度几乎已成为衡量一国仲裁法治现代化程度的标尺。一方面,仲裁并非完全存在于法律真空中,它受到国际、国内仲裁程序立法的制约,但另一方面,在仲裁程序的进行中,仲裁立法一般却很少有干预微观仲裁的机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仲裁程序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这个角度说,仲裁程序的自治在以仲裁地为确定仲裁程序法主导因素的属地主义与当事人仲裁意思自治之间存在张力。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自治如何在此种张力中得以实现,值得探索。
一、当事人仲裁程序意思自治首要地位在仲裁立法中的确立
(一)国际仲裁公约的立法规定
现有国际仲裁公约虽未专门就仲裁程序规则作出规定,但在规定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时多涉及仲裁程序的自治问题。1923年《仲裁条款协定书》最早承认了当事人决定仲裁程序的意思自由。该协定书第2条明确规定:仲裁程序,包括仲裁庭的组成在内,应当依照当事人的意志和仲裁地国的法律规定。1927年《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第1条规定: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仲裁庭必须依据当事人所同意的方式组成,并且符合支配仲裁程序的法律。从这两个公约可以看出,有关仲裁程序的具体塑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仲裁程序法应共同发挥作用。而《纽约公约》第5条则明确将“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同当事人间协议不符”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理由,而未提到仲裁地国的法律控制。《纽约公约》是国际社会中成员国最为广泛的仲裁公约,其规定基本可以代表国际立法对当事人程序自治的态度。后来的《欧洲仲裁公约》与《美洲仲裁公约》也基本上继承了《纽约公约》的态度。①当然,以上这些国际公约的调整对象仅限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并不及于仲裁程序的整个过程。但从理论上说,当事人将争议交付仲裁,其目的就是获取一份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裁决,仲裁员受理和审理争议的目的也在于作出一份公正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裁决,这就要求仲裁员在整个仲裁过程中,都应牢记当事人的合理期待,并应为实现这一期待而谨慎从事。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约规定裁决不符合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协议不能得到承认与执行,就间接暗示着当事人的意思对仲裁程序具有主导地位。
(二)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公约精神的继承
上述国际仲裁公约的立法精神为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的规定所继承。《示范法》的制定实际上是由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发起的,目的在于通过协定的方式补充《纽约公约》,使当事人选择的仲裁法优先于各国国内仲裁程序法的适用。所以在示范法立法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极端建议:如果当事人的协议违反仲裁程序法的规定,仲裁庭依据当事人协议作出的裁决不能被撤销。该建议虽由于触及诸多国家仲裁立法主权效力的原因而最终被拒绝采纳,但程序自治仍然成为示范法所坚持实现的目标。其中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主要是《示范法》的第19条:“(1)在不违背本法规定的情况下,当事各方可以自由地就仲裁庭进行仲裁所应遵循的程序达成协议;(2)如未达成此种协议,仲裁庭可在本法规定的限制下,按照它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授予仲裁庭的权力包括确定任何证据的可采性、相关性、实质性和重要性的权力。”
对此规定,有学者总结出《示范法》关于仲裁程序自治包含了三条规则:首先,当事人可以自由地就仲裁庭进行仲裁所应遵循的程序达成协议,但应服从《示范法》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在无此种协议时,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但应服从示范法的强制性规定。最后,仲裁庭的权力,包括确定任何证据的可接受性、相关性、实质性和重要性的权力。当事人既可选择适用一套规则或适用某特定国家的程序规范,也可就有关程序问题达成协议,而不选择一套详细的规则体系支配仲裁程序。③
换句话说,根据《示范法》实现仲裁程序自治也相应有三个途径:其一,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法,仲裁程序由当事人所选的仲裁程序法规定,仲裁协议可以选择特定的程序法为准据法。我国新近出台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仲裁协议准据法的规定即遵循了此种作法,但在仲裁实践中并不常见。其二,由当事人约定仲裁程序规范或仲裁规则,④这种情况在实践中运用最为普遍;其三,由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详细约定或由仲裁庭决定仲裁程序进行的方式,这种方式一般与第二种途径结合使用。
(三)国内和地区立法对仲裁程序意思自治的普遍接受
当事人可以选择支配仲裁程序的规则或自由决定仲裁程序进行的方式,也已被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所承认。例如,荷兰1986年颁布的《仲裁法》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进行的程序规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88年《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法典》赋予当事人确定仲裁程序的自由权;在日本,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仲裁程序的细节。此外,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42条规定:“当事人得自由决定或援引一套仲裁规则而决定程序,除非本编有强制性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且本法也没有规定,则仲裁庭应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1998年《比利时司法典》第1693条规定:“在不妨碍第1694条(强制性规则)规定之情况下,当事人得协议确定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地。如其在仲裁庭规定之期限内未达成协议,应由仲裁员确定。”瑞士1989年《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82条规定:“当事人可直接或按照仲裁规则确定仲裁程序;他们也可以按其选择的程序法进行仲裁程序。当事人没有确定仲裁程序的,仲裁庭应根据需要,直接地或者按照法律或仲裁规则,确定仲裁规则。”其他还有1993年《俄罗斯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第19条第1款以及奥地利类似立法等。在美国许多判例也确认了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的自治权。⑤
这些仲裁法有关仲裁程序意思自治的规定大多强调两点:首先,当事人对仲裁规则的选择或对具体仲裁程序的确定不得违反仲裁程序法的强制性规则;其次,在当事人未约定的情况下,授权仲裁庭或仲裁员决定仲裁程序。由于仲裁庭及仲裁员权力直接来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因此仲裁庭及仲裁员决定仲裁程序的行为与当事人的程序自治并无二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国1981年《民事诉讼法典》第1494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可以直接或通过适用仲裁规则确定审案时所遵循的程序,也可以确定所要遵循的仲裁程序法,如果仲裁协议中没有约定,在需要时,仲裁员可直接或通过适用法律或某些仲裁规则确定程序。”它明确地把国家的仲裁程序立法都纳入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而不仅限于民间性的仲裁规则。⑥但在不少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法律对在伊斯兰国家举行的仲裁具有强制性,不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予以排除,必须予以适用,这体现出在这些国家进行仲裁程序的刚性。如也门、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巴林等国,即遵循这一基本原则。⑦
从立法上来看,中国1994年《仲裁法》,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为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贡献殊多,但也难掩其在程序规则适用上僵化、不自由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仲裁程序自治。例如,该法第63条甚至要求仲裁机构制定的涉外仲裁规则应依照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而在该法第四章仲裁程序的规定中,立法者对仲裁的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的开庭和裁决都作出了相当详细的规定。由于这些有关仲裁程序的规则规定在仲裁法中,且并未说明当事人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约定加以减损或排除,一般认为这些规则具有强制性规则的性质。这样的话,无论当事人的约定,还是间接代表当事人意思的仲裁规则对于有关进行仲裁的程序性规则,只留下相当逼仄的空间。换句话来说,当事人程序自治的权利基本上为中国仲裁立法所侵蚀了。所以有论者认为,“我国仲裁法有关当事人仲裁自治的空间很小,仅允许与其所规定的仲裁程序不相抵触的某些程序,步子迈的不大,有待于积极创造条件,跟上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⑧究其原因,我国不少立法者长期即认为仲裁地法应当作为国家干预仲裁意志的集中体现,仲裁程序犹如诉讼程序、仲裁员犹如法官,管理仲裁程序的法律无论如何都应强制适用仲裁程序,因此无论仲裁程序法的整体,还是具体的仲裁程序规范,都没有当事人选择适用的余地。这一观点完全误解了仲裁的契约属性,亟待在立法中进行彻底的变革。
二、仲裁规则的适用与仲裁庭对仲裁程序自治的实现
(一)适用仲裁规则中的仲裁程序自治
真正现代化的仲裁立法一般只调整涉及诸如仲裁地确定、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等普遍性的仲裁事项,而不涉及到例如证人陈述或庭前证据提交时间等具体的程序规则。在极端情况下,如美国联邦仲裁法对具体的仲裁程序性事项完全没有规定,全部留给当事人意思自治。⑨但就当事人而言,在仲裁进行的每一阶段,他们都需要知晓详细的仲裁规则,从而澄清每一步他们应如何行事。例如,申请人的请求陈述是仅仅略述支持其请求的事实,还是随附依据文件及可能的法律意见,等等。对于这些详细的仲裁规则当事人当然可以在仲裁协议中加以约定,但在国际仲裁中,当事人经常来自不同背景,对于诸如会见证人、披露文件等等采用不同的方法,要在仲裁协议中对这些事项逐条达成合意的难度可想而知。⑩因此,一些仲裁机构为了补充当事人自主意思之不足,制定了仲裁规则,可由当事人援引适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仲裁规则的适用也是当事人自己塑造仲裁程序的重要方式,仲裁规则适用的本身即为仲裁程序自治的重要体现。
在实践中,仲裁规则对仲裁程序进行中当事人的意思变更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一些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规定,即使当事人选定了某个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也可在仲裁程序进行中由当事人予以合意变更,甚至约定适用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例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条第1款即规定:“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凡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交付仲裁,该争议应根据本规则予以解决,但双方当事人书面约定对此有所更改时,则从其约定。”其他诸如1992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16条、1992年《日内瓦商工会仲裁规则》第19条、1991年《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第1条、《米兰仲裁院仲裁规则》第34条以及1988年《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条、第16条也规定,当事人可以适用本仲裁机构以外的仲裁规则或者书面协议变更本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其二,有些仲裁规则将当事人选择本仲裁机构的行为视为选择了该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既不允许完全依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的意愿进行变更,也不允许当事人选择其它机构的仲裁规则。例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5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审理案件的程序受本规则管辖,本规则没有规定的,受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或当事人未约定时,受仲裁庭决定的仲裁规则管辖。仲裁庭决定适用的规则时可决定是否援用某国程序法。”此间可以看出,在国际商会仲裁中,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后,除非仲裁规则对某些程序事项并未规定,当事人尚有约定空间,否则当事人不得作出与仲裁规则相反之约定。(11)这并非国际商会的独特做法,1999年《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20条规定:“仲裁庭将根据仲裁协议和本规则的规定,并适当考虑当事人的意愿,确定进行仲裁的方式。”显然,仲裁程序进行的方式是由当事人事先订立的仲裁协议与仲裁院的仲裁规则所决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进行中的意愿只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改变了1988年规则中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他仲裁规则的规定。其他诸如1998年《荷兰仲裁协会仲裁规则》第3条、1998年《德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第1条、《韩国商事仲裁院商事仲裁规则》以及1999年中国的《CIETAC仲裁规则》第7条规定均有类似规定。
不少学者认为,第一种做法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贯彻最为彻底,充分体现出无论何时何地,仲裁程序必须以当事人意思为依归;第二种做法中否定当事人协议变更仲裁程序的观点,则有违反当事人程序自治之虞。(12)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仲裁规则本身具有契约性质,仲裁规则的适用正是当事人选择的结果。既然仲裁规则是契约,它的适用也不仅取决于当事人单方意思,其间包含当事人与仲裁机构达成的合意,当事人一方对已经达成的合意单方变更,可能导致合意基础的丧失,仲裁机构有权不再对有关仲裁案件实施管辖。而且,仲裁庭接受当事人仲裁任命的前提可能就是当事人接受仲裁规则的条件,仲裁庭虽然无法积极违反当事人指令,但可以消极方式,例如辞职等方式对当事人不符合仲裁协议的指令提出异议。实际上,仅就机构仲裁而言,要求该仲裁机构仲裁适用该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以外的仲裁规则仲裁,其不便性是非常明显的。仲裁本身也系一种产业,仲裁机构作为提供仲裁服务的单位,不能不考虑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在一味主张仲裁机构应当允许适用其他仲裁规则时,虽然充分考虑了当事人程序自治的权利,但不能不说缺乏对同为私人主体的仲裁机构立场的思考。当然有的仲裁规则给当事人以更大的选择自由度,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其他仲裁规则或协议改变仲裁规则,这都是各个仲裁机构吸引仲裁的竞争手段,每个仲裁机构发展战略不同、盈利模式各异,对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成本的看待自然也不同。所以,笔者认为,有关此问题的不同做法,与当事人的仲裁程序自由程度没有直接关联。
然而,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对仲裁程序有明显不同于仲裁规则的约定,除非当事人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改变当初的合意或者当事人所选仲裁规则中禁止当事人作出不同约定,仲裁庭不得以仲裁规则的规定为由违反当事人的约定。例如,在世界谷物和饲料贸易协会(The Grain and Feed Trade Association,以下简称GAFFA)受理的一起仲裁案件中,中国大陆的Z公司与香港的D公司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合同项下的争议应依据GAFTA第125号仲裁规则(13)仲裁,仲裁地在香港。争议发生后,D公司向GFTA申请仲裁,Z公司依仲裁规则指定了仲裁员并参加了仲裁程序,仲裁审理在香港进行。经过两审仲裁程序后,上诉仲裁庭作出了终局裁决。与当事人约定不同,终局裁决认为仲裁地在英国。裁决作出后,D公司依据《纽约公约》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Z公司则抗辩不予承认与执行。Z公司提出的不予承认与执行的理由之一是,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即仲裁裁决确定仲裁地为英国与当事人约定香港为仲裁地不符。(14)对于本案,GAFTA仲裁规则虽然明确规定其项下仲裁的仲裁地应为英国伦敦,但该仲裁规则并未规定当事人不能对其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变更,当事人对仲裁地与仲裁规则相反的约定并非无效,当事人的意思应予尊重。
(二)当事人意思缺失时仲裁庭对仲裁程序自治的实现
从实践层面考察,仲裁程序自治还体现在仲裁庭对仲裁程序自治的确定上。一般来说,仲裁庭对仲裁程序规则的确定一般遵循这样一幅路线图:当事人仲裁协议中的约定→仲裁规则→仲裁程序法中的相关规定。换句话说,仲裁程序首先由当事人的协议约定,对于协议未约定事项由仲裁规则决定,仲裁程序法中的相关规定则对仲裁规则进行补充。但在有的情形下,仲裁规则与仲裁程序法对相关程序问题均未规定。对此,通说认为,仲裁庭在程序中“可以”,但不“必然”比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例如,在一起仲裁地为英国的裁决中,仲裁庭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英国《1996年仲裁法》支配仲裁程序问题,而主合同受他国实体法调整。作为程序问题,由于英国仲裁法中并没有关时效的规定,仲裁庭即适用了英国时效法中的有关规定。对此,有英国学者批评道:仲裁不适用英国时效法并不会导致裁决的撤销,英国《1996年仲裁法》中的强制性规则中并没有关于时效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时效法有关仲裁时效的规定与国际普遍做法并不一致,当事人总是期望适用国际社会一般性的法律规定,适用某国国内法中独具特色的规定通常是不合适的,因此,该案仲裁庭的做法违反当事人的主观愿望。(15)这在有关英国外国法查明规则的适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英国法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将外国法的内容作为案件事实向法院提供,法官应将外国法的内容视为在有关事项上与内国法的内容相同。这种有关外国法查明的规定即是英国比较具有特色的规定,如果仲裁员比照内国法规定查明仲裁主合同所要适用的外国法,很可能会对不熟悉英国法的当事人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所以,为避免适用某国国内法的狭隘,以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少学者主张在仲裁规则与仲裁地仲裁程序法均无规定的情形下适用所谓的“一般仲裁法律原则”决定仲裁程序,更能符合当事人的意图。(16)例如,在一个仲裁庭决定是否应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部分裁决中,仲裁地约定为瑞士,仲裁规则为日内瓦仲裁规则,仲裁庭发现瑞士国际商事仲裁法并不禁止仲裁庭行使此项权力,但为了决定仲裁庭进行财产保全是否适当,仲裁庭一方面检视先例,另一方面考察了欧洲数国对此问题的规定。通过综合比较、分析,最终认为仲裁庭行使此项权力是适当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商事仲裁中究竟有哪些广为接受的程序性原则,在不同学者间有不同的认识,各个原则在不同国家被接受的程度也不尽一致。其中有些程序法原则,如举证责任分配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等,早已跨越不同立法甚至法系的界限,为各国立法所认同,但更多的原则是从国际较为普遍的实践所归纳出来,并非要求其具体内容在每个仲裁实践中都遵照执行,不可更改。(17)总的来说,作为仲裁实践一般做法的一般仲裁原则虽然在不同仲裁立法中表现可能并非完全一致,但这些法律原则作为这些不尽一致规则背后的核心理念,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普适性。
三、仲裁强制性规则对仲裁程序自治的规制
(一)仲裁强制性规则的国际性
前文已述,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自治,由当事人选择或决定仲裁程序进行的具体规则已经为国际公约、各国立法和仲裁实践所广泛接受。有些国家,如法国、美国以及瑞士等,甚至本国仲裁立法根本不对仲裁程序规则作具体规定,而完全留给当事人自由约定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加以确定。(18)但是,这是否说明当事人仲裁程序自治的权利不受限制,当事人能否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仲裁程序?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当事人的程序自治至少受有关国家仲裁法强制性规则的制约。(19)
对于强制性规则的概念,理论界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所谓仲裁法中的强制性规则,一般是指当事人和仲裁庭必须遵守、不许损抑的程序规则。一国之所以承认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合法性,并给予国际仲裁不同于国内仲裁的特殊地位,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商事争议的特殊性,并期望争议能按照符合本国公平、正义、效率的观念的程序得以解决。为此,各国立法普遍通过一些强制性规定,保证仲裁出程序能在最低限度内实现公平、有效解决争议的政策目标。”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但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仲裁法设置所谓的“正当程序条款”,(20)并普遍将其提升至强制性规则的高度。这并非偶然现象,也并非仅仅出于保护一国公平、正义解决争议的政策目标,其背后实际上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世界性及区域性的人权公约有关以公平、正义的方式解决刑事、民事争议的条款,已要求相关立法应履行相对应的国家义务,因此相关国家在仲裁法中设置有关仲裁员独立、公正以及当事人平等的条款,是国家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表现。从更广的范围来说,国际人权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内的渗透已使得仲裁正当程序演变为带有国际强行法的色彩,而不再仅限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了。因此,当事人的程序自治受“正当程序条款”的制约既是国家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表现,也是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必然要求,当事人不能自由变更或排除,仲裁庭也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否则裁决很可能被撤销。
例如,在国际商会审理的Ivan Milutinovie PLM v.Deutsche Babcock一案中,(21)当事人约定发生的争议在瑞士苏黎世仲裁,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而支配仲裁的程序法为仲裁地苏黎世州民事诉讼法典。仲裁开始后,三人仲裁庭中的一名仲裁员宣布辞职,仲裁院裁定拒绝该仲裁员辞职,并认为该仲裁员有继续进行仲裁的义务。在该仲裁员未参加且未签署的情况下,首席仲裁员和另一名仲裁员作出了部分裁决,仲裁院批准了此裁决。围绕着该裁决是否应撤销的问题,瑞士法院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审理,最终依据瑞士联邦宪法第58条“任何人不得剥夺由正常法官审理的权利,因此,不得设立特别法庭”以及瑞士参加的《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任何人在决定其民事权利与义务时,都有权在合理的期限内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公平的法庭的公正和公开地审理”的规定,将仲裁裁决撤销。当然,更多的强制性规则并不体现国家的国际义务,而是某国国内仲裁法出于本国的法律政策目标对自治性、民间性的仲裁所施加的控制。国内法对仲裁的控制通过内国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来实现,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仲裁地法院及仲裁据以作出裁决所属国的法院有权撤销仲裁裁决,因此仲裁地与仲裁程序法所属国的强制性规则是仲裁程序自治应尊重的对象,违反他们的强制性规则,尤其是仲裁地的强制性规则可能招致被撤销的命运,这也是强制性规则强制性效力的来源。
(二)仲裁地强制性规则的优先效力
仲裁程序自治所应遵守的强制性规则之间也可能产生抵牾。一般来说,仲裁地有撤销仲裁裁决的绝对权力,其对仲裁的控制力不容置疑,仲裁庭只有尊重仲裁地的强制性规则才能获得有效裁决。但是,有些国家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地以外的仲裁程序法,对于当事人选择的仲裁程序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事人应予遵守。从《纽约公约》接受仲裁程序法所属国有权撤销裁决效力角度而言,仲裁程序法的效力也应获得尊重。但若仲裁地国强制性规则与当事人所选择仲裁程序法并不一致,且两者强制性规则产生冲突,仲裁庭究竟应以哪国强制性规则为准则成问题。
其实,细分起来,强制性规则可分两类:一类具体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它的规定通常比较明确,可以作为仲裁程序规则的一部分加以适用,因此通常直接适用于仲裁程序,如某些伊斯兰国家在仲裁法中规定当事人在仲裁中必须履行某些宗教仪式等,即属于此类强制性规则;另一类是抽象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它虽也适用于仲裁程序,但因其抽象性,并不能具体规定仲裁程序的内容,当事人的程序自治只要不违反其要求即可,例如仲裁员独立、当事人平等以及仲裁庭公平等等都属于此类强制性规则。对于抽象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而言,由于其一般规定正当进行仲裁程序所应遵循的基本义务,所以各国间一般不会产生冲突;而对于具体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由于两者都争相适用于仲裁程序,如果两者在同一问题上规定不同,势必产生实际冲突。在此种情形下,一般认为仲裁地的强制性规则强制适用,(22)当事人所选仲裁程序法难以发挥真正意义上支配仲裁的效力,当事人所选仲裁程序法最终受制于仲裁地国强制性规则的规定。实际上,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法也好,不选择仲裁程序法也好,都是在仲裁地强制规则的控制下自由地塑造仲裁程序,如果选择仲裁地以外的仲裁程序法,还需额外受该仲裁程序法中强制性规则的制约,等于增加一道无形枷锁的束缚,这或许也是当事人在实践中基本上不选择适用仲裁地以外仲裁程序法的重要原因。
一言以蔽之,仲裁庭要实现当事人获得有效裁决的合理期待,至少有义务遵循仲裁地国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再以GAFTA仲裁为例,当事人约定仲裁地在英国,适用GAFTA仲裁规则,则除非当事人之间明确排除裁决的可上诉性,该仲裁庭所作的裁决是可上诉的。即该裁决没有终局的效力。因为GAFTA的仲裁程序规则允许对裁决进行上诉,英国1996年仲裁法也没有对仲裁一裁终局的强制性规定。但如果当事人约定仲裁地在中国,则根据仲裁地的强制性规定,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效力,即使作为当事人之间契约的仲裁规则允许当事人上诉,仲裁地法律也会强制适用。所以,仲裁地仲裁程序法作为仲裁地规范控制其领域内仲裁活动的法律,首先表明了仲裁地法允许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倾向,有关仲裁地法院所能提供的支持与帮助,仲裁所必须遵循的程序性事项等也体现在仲裁程序法中,仲裁地程序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并不允许当事人依约定减损其适用。(23)
(三)仲裁强制性规则规制仲裁程序自治的具体方式
虽然仲裁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当事人必须遵守、不得损抑等等,但在具体仲裁实践中识别某一规则究竟是不是强制性规则有时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关强制性规则的立法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如英国《1996年仲裁法》的规定那样,将所有的强制性规则明确标明,列入附录,当事人不得协议变更。另一种立法方式是不统一规定哪些条款是强制性规则,哪些不是强制性规则,而要分析具体条文,考察其中有无当事人约定的余地。例如,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42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各方当事人应平等对待、并应给予每一方充分陈述案件的机会”;“律师不得被排斥充任授权代理人”,这其中完全禁止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当事人意思自治违反该规定的任何一项,当事人即可提起撤销裁决之诉,所以这些条款属于强制性条款当无疑义;而该法第103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由就委任仲裁员的程序达成一致”;“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另一方当事人收到委任仲裁员通知后,一方当事人应即受该委任约束,”这些条款就为当事人约定留下很大空间,应属于非强制性规则。总的来说,各国仲裁法中有关具体仲裁程序的规则罕见有强制性规则,(24)但仲裁正当程序条款以及涉及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和支持的条款一般是强制性规则。在中国立法中,“应”或“应当”一般是强制性规则的标志,而“可”或“可以”等立法用语则是非强制性规则的特色。在中国仲裁法“仲裁程序”一章中,立法者较多使用“应”这一用语,而适用“可以”的条文不多,甚至对于具体的程序操作规范,也规定了当事人或仲裁机构“应当”如何办理。也就是说,中国仲裁法对于仲裁程序的规定以强制性规则为主流,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非常狭小。
绝大多数情况下,具体仲裁程序事项在相关仲裁法甚至根本不会涉及,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程序自治的权利也即顺理成章。如在一个仲裁地在瑞典,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规则为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仲裁案中,申请人为亚洲某国人,被申请人为加拿大人,某瑞典仲裁员作为独任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当事人申请公开有关文件,独任仲裁员否决了当事人的申请。他认为:在本案中,瑞典仲裁法作为支配仲裁的法庭法,并没有公开仲裁文件的规定,因此当事人的申请不能满足。显然的是,该独任仲裁员的推理有不当之处,只有在瑞典法律将公开仲裁文件作为“程序不当”,违反该项规定可能导致裁决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下,才有权否决当事人的申请。但瑞典仲裁法只是没有从肯定意义上规定仲裁员有此项公开的权利,而并未从否定意义上禁止仲裁庭为此行为,所以当事人对该程序事项达成的合意应受仲裁员尊重。(25)
另外,在极端情况下,当事人的意思与强制性规则明显相违背,仲裁员或仲裁庭究竟应以当事人的意思为准还是以强制性规则的要求为指针亦成争议。关于这个问题,理论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仲裁协议,也即当事人的意思是仲裁庭仲裁管辖权及其他一切相关权力的来源,因此,即使当事人的意思与仲裁规则明显相悖,仲裁庭也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2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仲裁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但仲裁庭一获任命,有权排除任何外在压力(包括当事人的压力)作出独立裁决,因此仲裁庭为保证裁决的有效性,应尊重强制性规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仲裁的目的便在于获得有效裁决,仲裁庭尊重强制性规则的目的最终还在于满足当事人的意思。(27)我们认为,仲裁庭之所以尊重仲裁程序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有效的仲裁裁决,使裁决尽量在更多的国家得以承认与执行。倘若当事人对仲裁裁决的效力并不在意,或者说当事人自身可以保障裁决的执行,那么当事人不管作出什么意思表示也不足为奇,仲裁庭也必须尊重当事人意思,毕竟仲裁庭是当事人设立的仲裁庭,而非国家公共权力设置的仲裁庭。一言以蔽之,仲裁程序的塑造必须以当事人的意思为根本指针,即便遵循其意思可能造成裁决无法执行的结果。
四、结语
简言之,仲裁意思自治虽为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但却并非存在于法律真空,在仲裁中实现程序自治须通过一定的路径。首先,国际仲裁立法已经普遍规定了仲裁程序自治的理念,这一理念也为绝大多数国内仲裁立法所接受,但反观我国仲裁程序法的规定,当事人程序自治的空间较为逼仄,须要从立法理念上进行彻底变革。其次,仲裁规则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仲裁程序自治的重要途径,仲裁庭对当事人程序自治亦可发挥能动作用。最后,仲裁程序自治也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它至少要不得与仲裁地程序法的强制性规则相抵触。
注释:
①参见朱克鹏:《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3页。
②参见[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③See Georgios Petrochios,Procedure Law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83-88.
④在多数情况下,当事人选择了仲裁机构就意味着选择了该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⑤参见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⑥荷兰《民事诉讼法》第1036条、葡萄牙1986年《仲裁法》第15条、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83条第2款、1993年阿尔及利亚《民事诉讼法》第458条、埃及1994年《民商事仲裁法》第25条以及意大利1994年《民事诉讼法》第816条作出了与法国立法基本相同的规定。See Fouchard 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p.652.
⑦参见前注①,朱克鹏书,第76页。
⑧肖志明:《关于在涉外商事仲裁实务中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载《商事仲裁法律报告》(第1卷),第10-12页。
⑨当然,也有国家,如捷克,虽然本国仲裁法并未对仲裁程序作具体规定,却要求仲裁程序的进行要类比本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在实践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另类。
⑩参见前注②,[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书,第87页。
(11)参见汪祖兴:《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12)See Edward Brunet,Arbitration Law in America:A Critical Assess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03.
(13)根据GAFI'A仲裁规则,GAFTA仲裁规则下的仲裁,仲裁地应为英国伦敦。
(14)参见杨弘磊:《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特殊冲突规则》,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9期。
(15)See supra note 3,Georgios Petrochios,p.219.
(16)See supra note 3,Georgios Petrochios,pp.219-223.
(17)See supra note 3,Georgios Petrochios,p.220.
(18)See Marc Blessing,Mandatory Rules Versus Party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1997(4),p.26.
(19)参见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4条。
(20)如参见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33条第1款;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42条第1款;1998年《西班牙仲裁法》第21条;《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816条;1994年《捷克仲裁法》第19条;《葡萄牙仲裁法》第15条等。这些规定一般对仲裁庭施加三项强制性义务:仲裁员独立、仲裁员公正与当事人一律平等。
(21)转引自前注(14),杨弘磊文。
(22)参见前注②,[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书,第88页。
(23)参见前注(14),杨弘磊文。
(24)See supra note 18,Marc Blessing.
(25)See supra note 3,Georgios Petrochios,p.118.
(26)See supra note 18,Marc Blessing.
(27)See supra note 18,Marc Blessing.
标签:法律论文; 仲裁程序论文; 意思自治论文; 纽约公约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仲裁法论文; 仲裁协议论文; 商事主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