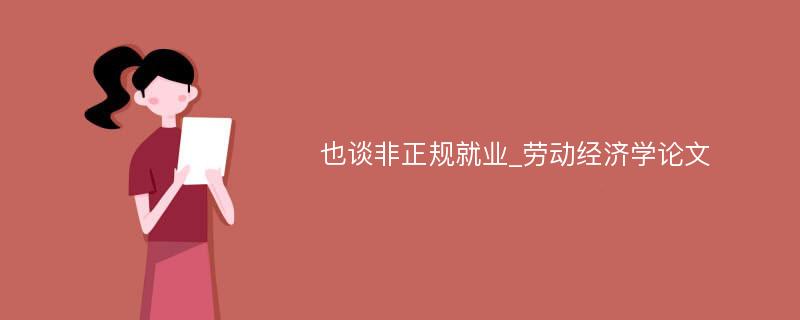
也谈非正规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谈论文,非正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组织关于非正规就业有关概念的研究
目前为止,国际组织采纳并界定的统计概念有两个:一个是非正规部门就业(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一个是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
非正规部门就业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并于1993年1月的第15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the Fif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进行了核准。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什么是非正规部门,一层是什么是非正规部门的就业。非正规部门是个限定词,它决定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正规部门就业首先关注的是“非正规部门”。联合国1993年7月修订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采用了非正规部门的概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2年出版了《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Measuring the Non-Observed Economy-A Handbook)。该手册列出了未观测经济的四个方面:地下生产(Underground Production)、非法生产(lllegal Production)、非正规部门生产(Informal Sector Production)、住户最终使用的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 for Own Final Use)。其中第10章专门论述了非正规部门的定义与测算。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将非正规部门纳入到了更为广泛的空间——整个未观测经济来讨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非正规部门本身的问题,这就使人们对非正规部门的相对位置及其与其他相关概念,如地下生产、非法生产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未观察到的经济是从统计范围不全、影响数据质量的角度切入的,所以,将未观测经济的四个方面统称为“问题区”(Problem Areas)。Problem指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需要解决,没有继续保留并加以发扬的意思。
联合国德里非正规部门统计专家组成立于1997年,其成立背景之一就是第15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界定的非正规部门概念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从某种程度上看,弹性的存在为各国的灵活执行提供了可能,从另一个方面看,灵活性的存在使其统计结果不具有国际可比性,当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失去了该指标存在的意义。德里非正规部门统计专家组致力于依据国际通行的定义框架来协调各国关于非正规部门的定义,交流非正规部门统计的经验,提高非正规部门统计的质量和可比性。阶段性研究成果体现于自1997年以来召开的7次会议及其报告中,最终研究成果将体现于联合国2008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中。
在对非正规部门关注的同时人们发现,第15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定义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有些单位未包括在内。如按定义,有些人员(在很小的企业中工作或偶尔的自我雇佣人员等)的活动也属于第15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定义的“企业”单位,但是,很多情况下,人们不认为他们是“企业”,因此,未包括在内。其次,“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不能反映就业“非正规性”的所有方面。在非正规部门发展与变化的同时,非正规性的就业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特点,如非标准的、非典型的、无规律的和不稳定的就业等。非正规就业多样性变化引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非正规性就业不仅发生在非正规部门,也发生在正规部门。面对这些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第15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定义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是个不完全的指标,无法用于非正规就业所有方面的统计与分析。
德里专家组最初的视角也是锁定在“非正规部门”的,后来发现,非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是不同的,因此,在新德里召开的第5次会议上(2001年)提出应用“非正规就业”指标作为“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补充。
“非正规就业”也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并在2002年的第90届国际劳动大会(90th Session(2002),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上进行了讨论,在2003年11~12月的第17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上进行了核准。
非正规就业是一个实际问题,因此,早期的研究多是实践性的、具体的、个案式的。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深层比较。比如,不同地区间、不同发展阶段间的变化特点,其发展趋势与不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联系,特定历史条件下非正规就业发展框架的约束条件等等。在面对这样一些新课题的同时,人们也面对缺乏国际可比的困扰。其一,切入角度不同。有的关注是否是法律实体,有的关注是否有就业合同,有的根据是否属于灵活性的工作决定。其二,范围不同。如是否包括第二职业,是否包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是否包括技术性的自我雇佣人员(如自有账户的会计、律师、医师等)。其三,边界的确定具有随意性。如同是按就业人数来界定,有的将低于5人的归为非正规企业,有的将低于10人的归为非正规企业。其四,术语混乱且混用。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就业、非正规经济就业等都是常用的术语,有些作者并未严格区分,常常混用,对读者产生一定的误导。其五,资料来源不同。有的来自劳动力调查,有的来自住户调查,有的根据抽样收集第一手资料,有的采用间接估算法等。
面对这些情况,近十几年来,国际组织将概念界定作为研究重点。
二、国际组织对概念的界定仅仅是统计意义的
统计意义的概念以经济学概念为基础,又不同于经济学概念。
一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辩证的,亦此亦彼的,允许交集的存在。统计学的概念强调边界的划分,强调有界外延,其结论是非此即彼的,这是统计概念完备性与互斥性的要求。完备性指统计范围内的所有对象均包括在内,它强调不遗漏。互斥性指所有统计对象都要归为一类且仅可归为其中的某一类,它强调不重复。
二是,经济学的研究关注过程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连续的,渐近的。统计意义的概念也强调外延的可变性与可延展性;但这种可变性是经过一定时期后对原有边界的调整,所以,如果将时间作为横坐标,将统计范围作为纵坐标,形成的散点图是间断的水平线段,其变化呈阶梯性。
三是,任何经济理论只有在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才具有指导意义,所以,经济学研究以本土化为前提,又服务于本土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立足于特殊性。国际组织制定的统计概念具有超国家属性,统计概念一旦获得国际组织的通过,即成为国际标准,各个国家均应按此标准执行。虽然各个国家在执行时有权采取变通做法,但是这种变通都在国际标准框架下的变动,是“操作概念”层面的不同,非基本概念和框架的不同。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是在联系国SNA(1993)框架基础上建立的。这意味着中国的统计制度也是按国际标准来规范的。
四是,统计“道德与操守”要求对客观存在予以全部承认,但是,这种承认仅仅是统计目的的,没有任何政策导向性。比如,国际统计标准规定将走私的货物、性工作者提供的服务等非法生产包括在增加值计算中,将非婚生子女、犯罪人口统计在人口总数中,这并不等于说国际组织在鼓励走私,鼓励提供性服务,鼓励非婚生子女,鼓励犯罪。
五是,统计定义强调实际资料的可获得性。理论上应该包括的内容,由于实际统计的困难,也会暂时放弃,这时就会出现统计学概念与经济学概念不一致的情况。如目前,国际组织对非正规部门的界定,不包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部门,不是因为它不属于非正规部门,只是因为统计上不可行。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统计学概念虽然以经济学概念为基础,又不同于经济学概念,根据经济学概念可以推衍统计学概念,反之,根据统计概念反论经济学概念则不合逻辑。
三、中国在引入国际统计概念时存在的理解误区
近年来,中国非正规就业问题的研究备受关注,其中很多研究是从国际组织定义的统计概念谈起的。它把人们拉到国际视角,使人们能够在更高层次的认识空间理解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把握中国非正规就业状况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有利于追踪国际发展趋势。这种研究思路无疑值得推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有些人在引入国际统计概念的同时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区,主要表现在:
一是国际社会关于非正规就业方面的研究先是由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开始的,统计定义则是后来的事情。在初期的个案研究阶段,在不以国际比较为主要目的的情况下,出现不同的术语是难免的。与此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时,国际组织已经界定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统计定义,因此,很多人将其引入中国,并在国际比较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这些人只注意到“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术语,并未注意到它们本身是经过严格定义的统计概念,因此,根据自己的理解反推出“中国特色”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或非正规就业概念,再根据自定义的经济概念论证用什么指标反映之。这种研究方法存在三点质疑。首先,它是由统计概念反推经济学概念,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其次,什么是“非正规部门就业”,什么是“非正规就业”,国际组织已经严格定义,作为个案研究只有严格遵守国际标准其结论才具有国际可比性。当然,作为学术研究,采用自定义概念或自创指标不能不说是一种研究手法,问题是将一个自创指标拉向国际比较的平台,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作为读者,对专业词汇了解的并不一定很深,他们会误以为这些自创指标与比较国的指标口径相一致,以致误导读者。最后,无限扩大“非正规部门”的范围。有些人在自创指标中,无限扩大非正规部门的范围。如果通篇看过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做出的《关于非正规部门就业统计的决议》(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adopted by the 15[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就会发现,该决议不仅界定了非正规部门的基本概念,也界定了非正规部门的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还对一些特殊情况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也就是说,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部门的定义是严格的、详细的、具体的。
二是对概念的引进断章取义或未及时跟踪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国内研究用到较多的是“非正规就业”,引用较多的是1993年第15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核准的定义。殊不知,第15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核准的定义是“非正规部门就业”,非“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是在意识到原有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概念无法达到统计上的完备性之后,在第17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上核准的概念。还有一些人未注意到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引用一些早期的、过渡性研究成果。
三是较多关注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文件,未注意到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成果。前面已经提到,联合国、OECD、德里专家组等都参与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其中,联合国SNA(1993)发表至今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中国官方统计“引进”的也是这个版本,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非正规部门”仅仅是“住户部门”的一个子部门(注:SNA(1993)将整个国民经济分为五个机构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公司部门、一般政府、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住户部门。中国分为四个机构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公司、一般政府、住户部门。),虽然它也用了“部门”、“企业”这样的词汇,但是,这里的“企业”仅仅指“非法人”企业。
四是与“地下生产”、“非法生产”等概念相混淆。如有的认为“非正规经济又称‘地下经济’”(苏振兴,2001;周国富,1999)。将非正规部门生产与非法生产、地下生产相联系。实际上,不论是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都有可能从事地下生产或非法生产。有研究表明,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反倒大多是合法的,隐蔽或地下经济活动常常由“正规部门”所为,如账外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低报或少报金融交易或财产收入、高报或多报可抵扣的税款、私下雇佣工人以及瞒报已申报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加班时间等(吴涧生、左颖,2001)。
五是误认为是国际组织鼓励发展的。有的研究在论证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必要性时将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搬到了前台,认为国际组织已经承认了该概念,因此,应该大力发展。这又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定位错误。首先,国际组织定义的仅仅是统计概念,统计角度的“认可”与发展取向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我们前面举过走私、性工作者的服务、非婚生子女、犯罪人口的例子。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例子比较偏激,我们再举不偏激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三次修订的《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简称ISIC)将整个国民经济分为17个行业,这是不是意味着联合国鼓励所有国家都要发展这17个行业,果真如此,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岂不完全一样。其次,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看出,该手册将非正规部门生产与地下生产、非法生产一起列入“问题区”(注:当然,从其它角度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则另当别论。)。
四、非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国际概念框架(注:本文以国际劳工组织最新修订的、经第17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核准的、提交给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统计分委员会会议(2004.2.18~20,曼谷)的《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测量》(Defining and Measuring Informal Employment)为准。其中,非正规部门就业采用的是第15届会议界定的概念,非正规就业是在第17届会议上新核准的概念。)
非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最大区别是观察单位不同。非正规部门就业以“企业”(Enterprise)为观察单位,在非正规企业工作的所有人都统计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不管该就业人口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是第一职业,还是第二职业。其中,非正规企业的界定标准是:私人非法人企业、生产目的用于销售或实物交易、就业规模低于规定人数、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
非正规就业的观察单位是“工作”(Job),它是指非正规性工作的总数,不管该工作是在正规部门还是在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不仅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还适用于发达国家,非正规部门就业与发达国家相关程度则较小。
生产单位按性质可分为三类:正规企业、非正规企业和住户。工作种类按国际就业状态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Status in Employment)共分为五类:自有账户工人(own-account workers)、雇主(employers)、无酬家庭工人(Contributing family workers)、雇员(employees)、与生产者合作人员(members of producers' cooperatives)。按生产单位性质和就业状态分组形成的棋盘式分类表列于表1,根据表1可以得到非正规部门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指标。
表1 按生产单位性质分组的就业状态分类表
按就业状态分组的工作
自有账
雇主
家庭
雇员
与生产者
按性质分组户工人 工人
合作的人员
的生产单位
非 非非 非 非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规 规
规 规
规 规
规 规
规
规
正规部门的企业 1 2
非正规部门的
企业(a) 3 4 5 6 7
8
住户(b) 9
10
(a)不包括雇佣有酬家务劳动人员的住户。
(b)指为自身最终使用从事货物生产的住户、雇佣有酬家务劳动人员的住户。
非正规部门就业=3+4+5+6+7+8
非正规就业=1+2+3+4+5+6+8+9+10
表1是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非正规就业概念框架,该框架将“企业法”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与“工作法”的非正规就业联系起来,两个概念互相补充,不能替代。为了更好地理解非正规部门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与关系,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部门中“企业”的界定是很宽泛的,它指为销售或实物交易进行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所有单位,不仅包括雇佣劳动力的单位,还包括由单独的个人以自我雇佣的形式经营的生产单位,如自我雇佣的沿街摊贩、出租车司机等都被认为是企业。为了避免无限扩大其范围,一定要牢记,非正规部门中的企业指的是“非法人”企业。
二是,非正规就业指的是工作岗位数,不是就业人数。由于有些人同时从事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工作,按就业人数只能统计为1人,按工作岗位数应统计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以工作为观察单位不以就业人数为观察单位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将“工作数”分解到相应的生产部门中去,进而,再按企业性质分组,以利于非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对应分析(如表1所示)。如某人从事两种职业,第一职业在正规部门,第二职业在非正规部门,按就业人数只能统计为1人,不论将其归入正规部门还是归入非正规部门都不合适。
三是,非正规生产与地下生产、非法生产的关系。非法生产指法律禁止的生产活动,或由未授权的生产者进行的生产。如毒品经销商或没有行医执照的人从事行医活动。非法生产被认为是违反了刑法。地下生产指按规定,其生产活动是合法的,但故意隐藏起来。如合法的货物和服务未经上税就销售了。地下生产违反的是民法。实践中,地下生产与非法生产界线的划分并非易事。但从概念的角度看,可将其分成合法非地下的活动、合法地下的活动、非法的活动三种。每种生产单位(正规部门的企业、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和住户部门)都有可能从事这三种生产活动(见表2)。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非正规部门生产既不是地下的,也不是非法的,他们的生产方式比较简单,生产目的仅仅为了自身或家人的生存(Ralf Hussmanns,2004)。
四是,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不等于非正规部门生产与正规部门生产之和。有些学者采用简单的二分法,自认为“非正规部门”是相对于正规部门而言的(东方社奇,1999),人为地将非正规部门添加了一个对应项——正规部门,这与“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价值判断非常类似。实际上,很多客观现象很难用简单的二分法进行归类,国际劳工组织采用的是“三分法”。如果说,非正规部门有对应项的话,应该是两项——正规部门和住户部门(见表1与表2)。还有,目前国际组织对非正规部门的划分未包括农业生产活动,而整个经济总量是包括的。
表2 按生产单位性质分组的生产活动性质分类表
按生产活动性质分组
按生产单位性质分组
合法的 非法的
非地下的
地下的
正规部门的企业
非正规部门的企业(a)
住户(b)
(a)不包括雇佣有酬家务劳动人员的住户。
(b)指为自身最终使用从事货物生产的住户、雇佣有酬家务劳动人员的住户。
五是,国内引文提到较多的还有国际劳工组织2002年的“体面的工作与非正规经济”(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该文提到了“非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就业”的概念,但是,出于统计目的,第17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是建议使用“非正规部门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因此,国际劳工组织最新修订的Defining and Measuring Informal Employment只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和“非正规就业”。
五、结束语
国际组织关于非正规就业有关问题的讨论有两次值得一提。一次是: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统计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于2004年2月18日至20日在曼谷召开,国际劳工组织将2003年11~12月第17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核准的、最新修订的《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测量》提交给该届会议讨论,并列入该届会议的议程。一次是: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统计委员会第35届会议于2004年3月2日至5日召开,联合国德里非正规部门统计专家组向大会提交了《德里专家组关于非正规部门统计的报告》,大会肯定了德里专家组取得的工作进展,确定了今后的工作目的(联合国,E/2004/24-E/CN.3/2004/33)。非正规就业方面的问题不断列入联合国有关会议议程,反映出该问题的讨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专门问题的国际组织或专家小组,分别由国际劳工组织和德里专家组提交的报告和政策建议将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指导意义,其概念解释将更具有权威性和导向性。
国际组织对非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虽然已进行多年,且几经修订,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1)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非正规就业问题,如何按就业状态对非正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分类;(2)非正规就业包括了所有的经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个非同质的指标,指标的非同质性又会限制非正规就业的深层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按行业(或经济活动类型)进行细分组;(3)人们广泛认为,有些工作是界于两种就业状态之间的,很难将其按就业状态进行归类,因而容易产生归类错误,如何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来减少分类错误等。
说到底,国际组织的统计定义仅仅是一个概念框架和指导手册,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需要制定相应的操作标准,这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非正规就业问题的研究已有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缺少规范的、权威性的统计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统计制度的建立落后于经济学的研究。虽然滞后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滞后期过长将会限制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这也是中国非正规就业问题研究不够规范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