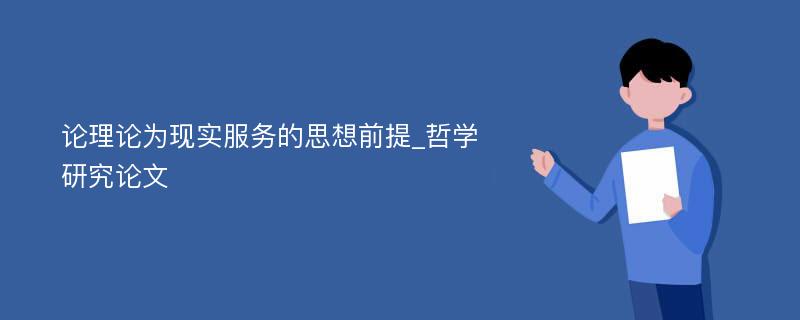
论理论服务于现实的思想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理论文,服务于论文,前提论文,现实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研究应该面向、关注和服务于现实,这种主张在当今中国的大多数理论研究者那里已获得巨大的共鸣,并逐渐达成广泛的共识,它反映了理论工作者们对于当前中国火热的现实生活急切的参与热情,反映了人们对理论成为远离现实的抽象玄谈这种学风的强烈不满,这种认识是可贵和重要的。但是,如果拒绝简单的答案,把问题引向深入,就将看到,理论与现实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理论要真正有效地研究和服务于现实,必须对一些重要的思想前提有明确的自觉把握。本文仅从几个方面出发,对此问题谈一些个人观点,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重新、深入地加以审视和反思。
一、究竟什么是“现实”
理论要真正有效地服务于现实,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弄清究竟什么是对人而言的“现实”。乍一看,什么是“现实”,仿佛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有着健全常识感的人都会认为,现实不就是在人之外,为我们每天所见、所感、所闻的一切客观事实吗?然而,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对于动物而言,自然界就是它最现实的世界,它们产生于自然,生活于自然,按照其物种的尺度生存,自然是它们天然的乐园。但是,对人而言,自然却不是真正的“现实”。对于神而言,一个超凡入圣、永恒至善的极端理想性世界才是其现实的世界,神的“现实”与动物的“现实”完全相反,它彻底摆脱了有限性和被动性,达到了绝对的圆满和自由。对人而言的“现实”,其复杂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既不同于“动物的现实”,也不同于“神的现实”,而同时又是把二者的合理成分包含其中的否定性统一体,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特有的实践活动。
把现实“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它表明,对人而言的现实,既不是“现存”的自然界,也不是抽象的纯粹观念存在,而是一个以实践活动为基础所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体。
从实践观点出发,纯粹的自然对于动物而言无疑是最现实的存在,但对人而言却并不构成为真正的现实。毫无疑问,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而且自然界从始至终构成人生存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却决不是天然给定的自然世界,而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属人性世界”。自然界固然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并不能现成地满足人作为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只有在实践活动能动的、创造性的改造活动中,它才能提升为“人化自然”并生成为对人而言的“现实”。因此,从实践观点出发,自然就只是“潜在”或“可能性存在”而不是“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论对“现实”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偏失,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其结果是把“潜在”或“可能性存在”当成了“现实”。
从实践观点出发,纯粹的观念世界也不是对人而言的“现实”。不可否认,观念世界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是人能够超越自然、从死寂的自然王国中跃起的关键因素。它表明了人虽然来源于自然,但又能够超越自然的限制、能动地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规律,在观念中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如果说纯粹的自然存在对人是“潜在”,那么,纯粹的观念世界对人就是体现着人的目的、意志的“理想世界”。没有这种理想世界的引导,也就不可能有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但是,“理想世界”却决不是人的现实世界,尚未进入人的实践活动的纯粹的观念存在属于尚在追求中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它也不直接就是对人而言的“现实”。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转化,它才能够成为对人而言的直接性现实。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唯心论对“现实”所作的抽象的能动性理解,因为后者把理想性、观念性存在当成了“现实”。
因此,“现实”这一存在,一方面区别于“潜能存在”,另一方面又区别于理想、观念存在,但同时又内在地包含自然的“潜能存在”与观念的“理想存在”两个内在环节于其中,这个统一的基础便是人的实践活动。通过能动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潜在的自然被提升为对人而言的现实存在,“正是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页。)与此同时, 通过实践活动,理想的、观念的存在也被转化为现实存在,“成为人的现实,……就是成为人自己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125页。)二者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现否定性的统一,于是生成对人而言的“现实”。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看到,如果真正贯彻实践观点,从它出发来理解对人而言的“现实”,那么,可以看到,它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最基本的特点:
1.“现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统一体。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组建而成的人的现实决不是某种单一本性的存在,而是具有两重矛盾本性的存在。它既不能归结为单纯的自然存在,也不能归结为纯粹的观念存在;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属人的,既是客体性的又是观念性的,既是因果性又是目的性的,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它是矛盾性的因素和力量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否定性统一体,只有这种矛盾的否定性统一体才是对人而言的“现实”。
2.“现实”不是静态的、停滞的实体性存在,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超越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为“矛盾统一体”,现实总是处在动态的运动之中,“矛盾的统一”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否定性统一”,而“否定性”意味着这种统一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地解决矛盾,又不断在更高层面产生新的矛盾,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推动着人的生活现实一步步走上跃迁和提升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强调:“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5页。)而所谓使“现存事物”革命化,就是要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和提升对人而言的“现实”。
3.“现实”是一个总体性的价值世界。这是前两点引申出的必然结论,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来理解,现实不是丧失超越性向度的“现存世界”,而是一个内在的蕴含了人的价值性内涵和取向的价值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自然原本具有的进程,它通过人向自然的生成与自然向人的双向生成,在改造人的对象世界并改造人自己的同时不断推动人的现实世界向更高的阶段提升。因此,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对人而言的现实就是一个基本的价值生成过程,而决不是死寂的、“纯物质”的自然世界。
可以看出,“现实”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哲学加以反思的而不是自明的常识性问题,是一个需要哲学理性予以澄明才能得以解决的极为复杂的问题。人们每天生活在现实之中,但往往最不了解也最难了解的恰恰是人的现实,这正像中国一句古诗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二、理论面向现实,能否真正把握现实
清醒地意识到理论“要面向现实”与“能把握现实”间所存在的距离,并自觉到这种距离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所依系的哲学世界观和理论思维方式内在相关,这是理论能有效地把握现实的又一重要思想前提。
只要作一番简单的词语梳理,就可看出,“要面向现实”与“能把握现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而后者则是人们认识和行动的客观结果,“要面向现实”决不等于就真正“能把握现实”。
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并不缺少理论要关心现实、服务现实的倡导和主张,甚至曾有过理论服务现实要“立竿见影”等极端的提法,然而,在这种主张最流行的时候,恰恰也是我们所犯主观主义、唯意志主义错误最严重的时候。对理论“现实关怀”的强调并没有使理论成为推动现实发展的有效动力,反而使它越来越偏离现实,这一强烈反差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理论“要面向现实”与“能把握现实”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距离。
反思这种距离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变理论“要面向现实”为“能把握现实”的十分重要的前提。我们认为,这种距离的产生,与人们究竟依据何种世界观和理论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是本质相关的。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从片面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出发,来分裂和瓦解现实,贯彻这些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不管它口头上是何等积极倡导和鼓吹理论要服务和关注现实,但其结果不但不能使完整的现实得以澄明,而且将遮蔽和扭曲现实,理论服务现实的愿望也必然会落空。
回顾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方式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对什么是“现实”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并形成了以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两种对立立场。柏拉图只承认“理念”是真正的现实,而现存的可感的一切恰恰都是“非现实”的,它们不过是理念的影子;与柏拉图等相对,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哲学家则把原子在虚空里的运动所形成的世界称为“现实世界”。在近代哲学中,对现实的理解更是不尽相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坚持用力学规律去说明一切现象,提出了世界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的观点。德国哲学则表现出与法国哲学明显不同的精神气质。康德既反对莱布尼茨等唯理论者把“现实”理解为脱离纯粹的如单子一样的精神实体,又不同意休谟等经验论者把现实等同于人的感觉经验,当然也不同意法国哲学的“机器现实观”。因此,他在其“先验逻辑”中,对“现实”作了这样的规定:“凡与经验的质料条件即感觉相关联者,是现实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92~193页。)即是说,只有把先验范畴与感觉经验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的“现实”。康德之后的哲学家们不同意康德的折衷主义和二元论立场,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走向了一条把人的现实完全精神化的唯心主义道路。黑格尔明确指出,“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他从其绝对唯心论立场出发,认为“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295页。)。也就是说,现实就是真实的、必然出现的东西,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黑格尔留下了他著名的论断:“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自然,他所谓的理性是以“绝对精神”为内核的“客观理性”。
从哲学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对现实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否认哲学要关注现实,甚至可以说,现实生活是所有哲学的起点和终点。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研究现实,而在于究竟遵循何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来研究现实。其中最为常见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只懂得“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从它出发,“现实”就等同于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自然存在,事物越与人的活动无关,越“客观”也就越“现实”,把主观的东西完全剔除,所剩下的东西就是纯粹的“现实”。这种对“现实”的理解以“客观、公正”自诩,曾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然而,如果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我们将发现,这种对“现实”的理解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把现实当成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对人而言的“现实”乃是一个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由两重矛盾关系所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是一个由主观与客观、自然性与观念性、因果性与目的性等两重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否定性统一体,直观唯物论仅仅看到了这种矛盾关系的一个方面,抽象地发挥了客观性这一个片面,完全忽视了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人的“现实”,它不懂得,“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性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被抽象的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很显然, 支持旧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必然导致人的现实这一矛盾统一体的分裂和瓦解,因而在根本上与实践观点相冲突,是不可能真正把握到完整的现实的。持着这种对现实的理解,如果要求理论来关注现实,必然会导致理论离真正的现实越来越远,如果要求理论来服务现实,必然会使理论成为现实发展的巨大障碍。在历史上我们曾再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一个重大的根源就在这里,——因为它坚持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的旧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因而在根本上与立足于实践观点来理解的完整的现实是相违背的。
还有一种分裂和瓦解现实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那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发挥了人的“能动”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这种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来看待一切事物,认为客观性不过是由主观性所创造的对象性存在,客观性只有适合于主观性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哲学史上如柏拉图、贝克莱、费希特、黑格尔等就持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从生活中常常见到种种“从教条出发”、“从本本出发”、“从原则出发”的思想惯习,也常常见到用长官意志、个人臆测来决定行动的工作作风,更可见到用过时的信念、虚幻的理想来指导生活的人生态度,这些,都表明了这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仍然潜在着,并作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前提在发挥着作用。
通过如上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倡导理论关注和服务于现实,并不意味着理论就真正能够认清现实,并促进现实的发展。在此,究竟以何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对于变“理论要关注现实”为“理论能关注现实”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如果在思想中贯彻的是一种瓦解现实、分解现实,使现实抽象化的实体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其结果都只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自觉地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现实”真正当作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去理解,是理论有效地服务于现实的重要前提。
三、理论的自主性——理论服务于现实的重要前提
把现实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使完整的现实得以彰显,避免了对现实的抽象化理解;同时,它还启示我们,倡导理论关注和服务于现实,决不是要使理论依附于现实,恰恰相反,这一目标的实现正是以理论的自主性为基本前提的。
如前所述,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现实”决不是某种单一本性的存在,而是一个由主观观念性与客观自然性、目的性与因果性、潜在的自然性与超自然的理想性等多种二重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极其复杂的否定性统一体。从这种观点出发,理论作为人类自觉的观念创造性活动,就不是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作为现实生活创造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发挥着作用。在此意义上,把现实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同时也就把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固有的内在关系,就是把理论的本性看作是实践活动的本性从而也是对人而言的现实生活的本性。这样一来,理论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就成为了理论的固有本性和使命,这就从最根本处解决了理论与现实的内在统一问题。
理论的自主性,是指理论具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具有超越常识、超越世俗的权力、政治和经济的干预并能运用人的思维创造力来反思实践活动的特点、规律和矛盾、寻求现实生活发展道路的独立地位和品格。这就是说,理论的自主性,意味着理论能够运用自己独特的概念系统和思想方法等“理论的方式”把握现实,意味着理论真正成为了“思想中的现实”。理论的自主性,当然也意味着理论与现实之间确实是存在着“间距”的,但这种间距的存在不是要割裂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正是要发挥人思维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使理论更“全面”地反映现实,更“深入”地透视现实,更“理性”地解释现实,更“自觉”地引导和提升现实。所以,承认理论的自主性,其结果不是离现实越来越远,而是更加接近了本质性、规律性的“事物本身”,从而使理论有效地服务于现实成为可能。要实现理论的自主性,首先必须使理论与形形色色的常识性见解划清界限。
常识性见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现实的经验性见解,它来源于人们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被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所确认为不证自明的基本信念。然而,作为“社会预先构建之物”,常识是未经理性投射和反省的知识,它存在的根据不是来源于理性的反思而是来自于“自古皆然”的信念,因此,在其“不证自明”、为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后面,恰恰有可能隐含着“不合法”的内容,在其关于“现实”的习以为常的见解里恰恰有可能包括着扭曲现实、掩盖现实的成分。在此意义上,强调理论的自主性,就是要解除常识性见解对本真现实的遮蔽,以一种批判的姿态质疑常识性见解的可靠来源,自觉地去反思“一贯正确”的东西可能还有“另一面”。所以,与常识性见解划清界限,体现了理论“区别现象与本质的努力,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注:霍克海姆:《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体现了它要求破除种种虚幻信念、“回到事物本身”的顽强意向。很显然,要求理论超越常识性见解以获取理论的自主性,其目的不是要使理论远离现实,而恰恰是为了让理论更好地把握和服务于现实。
其次,要实现理论的自主性,还要求理论研究者具有这样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即理论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成发展规律,它的唯一职责就是对实践活动的规律和矛盾、对人类的生活现实严肃认真地贯注理性。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附加的责任和义务,既不能把“高于”理论的东西强加在理论身上,也不能人为地降低理论的地位和作用。
所谓把“高于”理论的东西强加在理论身上,是指过分抬高理论的作用和地位,把理论本来不具有的职能赋予在它身上,甚至制造出种种“理论神话”,让理论成为包治百病、立竿见影的“法宝”。在过去,就曾有过“全党学理论”、“全民学哲学”的热潮,这样做,看似理论地位很高,但其实是使理论丧失了“自性”,丧失了应有的真实本性和职责,一句话,丧失了理论应有的自主性。
所谓人为地降低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指过分漠视理论、把理论视为无用的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采取庸俗化态度,认为实践无非就是“实干”,与之相比,理论是纯粹“务虚”的“坐而论道”;还有人把历史上由于理论的教条化和滥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归结于理论本身,并因此理直气壮地得出“理论无用”的结论。这种态度在表面上与前述的“理论的神化”截然相反,但抽象的两极内在相通,二者在实质上遵循着完全一致的逻辑,即否定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理论的神化”和“理论的淡化”都不是理论所应有的存在方式。真正意义上的对理论的尊重,最重要的莫过于尊重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任何对理论地位人为地抬高和降低,都是理论尊严的丧失,其结果都将必然因理论不能发挥其在实践活动中特有的作用而使现实生活饱受磨难。
最后,要实现理论的自主性,还要求理论工作者对理论研究所必具的基本学术规范有充分的自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学术规范的问题。如果从理论与现实关系角度来理解,学术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理论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有助于理论更好地把握现实、保证学术研究科学性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学术纪律、学术规则和学术评价标准。在此意义上,学术规范不是一些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对它的重视也不是要把理论封闭在象牙之塔里,而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为了更有效地研究和服务于现实。
尊重学术规范,意味着理论研究者应该具有自觉的学术意识,即具有从理论的视野出发,运用学术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来回答人类实践活动提出的、在学术体系上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这样一种自觉意愿和要求。理论研究与自发思考之间的区别之一在于它有着特有的操作过程、思考工具、话语方式和工作方式,有着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历史传承,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些,充分尊重并遵循它们,才有可能获取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可见,对学术意识的强调,其目的不是使理论研究成为少数人垄断的特权,而是为了把严肃认真的理论研究与似是而非的常识、偏见和臆断在根本上区别开来,因此,自觉的学术意识是获得现实生活和人类实践活动真理性认识的必要保证,从而也是理论最终能够卓有成效地服务于现实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