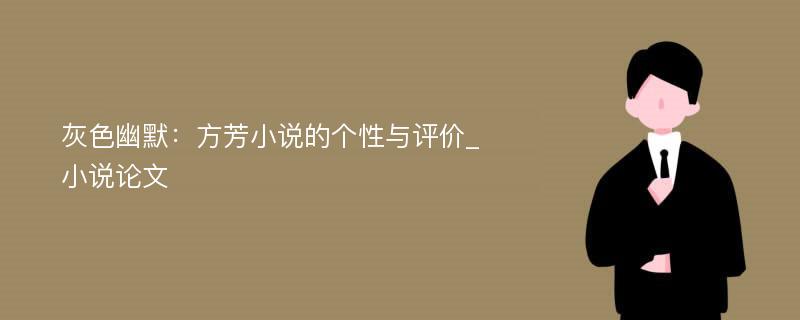
灰色幽默:方方小说的个性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灰色论文,评价论文,幽默论文,个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82年以小说走进文坛始,方方迄今的创作已有14年。她已有了已出或即出的10本小说集。她的小说无论是在评论界还是阅读界都有了相当的声誉与定评。作为一名当代小说家,她已具有了自己虽不甚稳定但却仍属明晰的个性或风格。幽默,即是其个性或风格的一个重要或突出的方面。
关于方方的幽默,已有论者指出并予以讨论,对方方早期(1982—1986,以《白梦》为界)作品中色调明朗的幽默,论者似有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幽默大约与方方其时的年轻、热情、浪漫、思想深度、社会氛围以及题材(主要是青年男女)等因素相关。此时的幽默是清丽而轻快的(作为个性却不是突出的),对其自《白梦》(1986)以后有显著变化的新一阶段(1986—1993),以《行为艺术》为界)创作中的幽默却存在可资探讨的问题。曾有论者指出:“……沉重是方方的都市小说的基调。她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有助地我们去体味都市化的发酵过程。”“方方也许感到这一都市化过程过于的沉重,她在自己的写实中加进不少的幽默。有人说她是黑色幽默,这恐怕有一点误解。方方的作品并不包含对病态和恐怖的内容作荒诞的处理,她几乎没有荒诞过,总是冷静的面对现实生活。也许是一位女性的缘故,她便在沉重之中加进一点幽默,但不是黑色的。”[①]设若我们也承认此一幽默不是“黑色的”,那么它是否就是我们久已习见或可称之为亮色的幽默呢?倘若不是,它又属何种色调并其内核何在?这正是笔者意欲讨论的问题。
作品的幽默与否或其幽默的色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者或小说“叙述人”(如方方《风景》中的小八子和《一波三折》中的“我”)的语调。不同的语调产生不同风格(喜剧的或悲剧的)的作品。让我们从几个实例开始,感受并体会作者或叙述人的语调,以求准确把握方方的幽默。
例(一)
……父亲揪住母亲的头发……母亲声嘶力竭地同他吵闹……于是左邻右舍来看热闹……他们一边嚼着饭一边笑嘻嘻地对父亲和母亲评头论足。母亲朝父亲吐唾沫时,就有议论说母亲这个姿式没有以前好看了。父亲怒不可遏地砸碗时,好些声音又说砸碗没有砸开水瓶的声音好听。不过了解内情的人会立即补充说他们家主要是没有开水瓶,要不然父亲是不会砸碗的。所有人都能证实父亲是这个叫河南棚子的地方的一条响当当的好汉。[②]
《风景》
例(二)
……父亲亲眼看见一根铁棍砸向熊金苟的。父亲喊了他一声。结果在他迟钝地一扭头时,铁棍正砸在他天灵盖上。他连哼也没哼便“噗”地倒地。血浆流淌着把他的头变得像个新品种西瓜。[③]
《风景》
例(三)
陆建桥又合上了眼。他觉出自己正在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中下坠。一直坠着坠着,没完没了。怎么没有底呢?倘若坠穿了地球,会不会从地球上掉下去呢?他想。[④]
《黑洞》
例(四)
麦子同香香交往常常只动用百分之一的智力。这就使麦子产生一种从头皮到脚板心都彻底放松了的感觉。与此相比,便想往日里曾没完没了地同夏春冬秋默然相对以心交谈简直同码头扛大包一样累人。
那时候总仿佛有一只手把心给捏住而且搓揉而且使命往下拽,拽得周身沉甸甸的。……香香叽叽喳喳又丢媚眼又扭屁股的使你轻飘得宛如没有了心。只此一点,麦子觉得香香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已远远在夏春冬秋之上。[⑤]
《白驹》
例(五)
头一天练歌是高人云去的,结果是开会。学校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先讲了为迎接“五一”劳动节唱歌之意义一二三,并说知识分子比方在座的各位教授也都属于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工人阶级是劳动人民,所以在座的各位教授也是为自己的节日讴歌。教授们想反正也没什么个专门的知识分子节,搭着工人阶级的份儿一块过“五一”也挺好,便纷纷点头说是呀是呀。[⑥]
《行云流水》
例(六)
言午现在才认识到劳动人民为什么总是那么乐观那么豁达。因为整日劳作使他们不被思想所困扰。他们从不苦思苦想,也没力气在劳作之余钻牛角尖。言午原先觉得干体力活的人可怜,而这会儿,却悟出他们才是真正活得如神仙,觉得可怜他们的人倒更可怜。[⑦]
《言午》
从以上涉及5部作品的6个例子中,看不到乐观的情绪、健康的心智、优越的心理、积极的态度与聪敏的机趣这些构成我们久已习见的幽默的基本元素。它自然不是亮色的。同样,它也(基本)不存在黑色幽默以恐怖与惨烈的事物为对象作欣赏式的玩味、对人类与世界抱悲观主义的绝望态度、以嘲讽和自嘲面对荒诞、从叙述人与对象情感“距离”的间隔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中求得无可奈何的快感一类东西。我们似可发现,方方正介乎习见的幽默与黑色幽默二者之间。
在例(一)中作者(借死去的小八子的亡灵为叙述人)以嬉笑的语调所描述的是一幅生活在底层的市民社会庸俗猥琐的日常闹剧。它的实质是令人痛心、厌恶而又不能不付出同情的。但作者埋藏了自己内心的痛切而予以游戏式的言说(这几乎是贯串《风景》全篇的基本语调)
在例(二)中,一颗在码头斗殴中被砸开的血浆流淌的脑袋被作者描绘为“像个新品种西瓜”。这是一种对惨烈事物的冷漠描述。在修辞的意义上,它已是类乎黑色幽默式的东西(约瑟夫·海勒在《第22条军规》中描述一只跳楼自杀者血肉模糊的尸体“像只装满草莓冰激淋的毛呢口袋”。)而方方似乎也终止于修辞的意义。
在例(三)中,为一间居室所苦、想尽了办法受尽了折磨仍看不到希望的主人公终于绝望了:他觉得自己掉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洞”。“会不会从地球上掉下去呢?”一句玩笑点染了氛围,但内在的沉重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例(四)中,有思想的麦子与无思想的女歌星香香其实除了肉体之交外并无灵魂的对话。在短暂的放纵之后必是内心无言的沉默。方方以调侃赞美了香香的“轻飘”,内里当然是否定的。但面对既红且香的香香,这种否定并不明晰轻快而是含有苦涩。倘若我们把视野从小说移向生活,这种苦涩即刻释然:在否定中隐含着方方面对现实感受的无奈。
在例(五)中,扑面而来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且是高级知识分子)尴尬地位的呈示。中国知识分子对“一部分”说来之不易深有体会。从“纷纷点头说是呀是呀”的谦卑与自嘲中可以感知极为丰富的内涵。这种纠结于心的东西并未因方方调侃的语调而化解。
例(六)取之于《三人行》。因受迫害在大牢中蹲了13年的主人公言午平反获释了。他从当年狂放的大博士变成了如今猥琐的清洁工。此时他明白了例(六)所示的“道理”。这自然是作者的笑言。但这是笑不出声的幽默。这一作品最早在《鸭绿江》(1991年8期)发表时,《文学报》有文称其为黑色幽默。客观地看,它只是以平静漠然的外貌更深地隐藏了痛苦,并无荒诞哲学的根基,较黑色幽默仍有距离。
以上六例的点评只是就例证本身而言,倘兼及这几部作品,再扩大到包括《白梦》、《白雾》、《纸婚年》、《一波三折》等作品便不难发现,这种有明显苦涩味道的幽默是方方许多作品的基调。这一语调成为方方1986—1992年间大部分小说突出的个性与特色。
出现于1986年之后的这一语调何以产生并形成呢?除了作者的体验、阅历、思考、社会氛围的变化诸因素外,似与作者的小说视点、视域密切相关。
方方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小说评论》,1991年3期)。关于生存环境,方方更关注的是“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是人“在困厄中挣扎和彼此间殴斗”[⑧]。因此,方方人物的命运几乎无一例外是坎坷、不幸、艰难、失败的。无论是知识分子人物群中恃才傲物的严航、慎独自守的高人云(《无处遁逃》、《行云流水》)、自信阴冷的言午、木讷冬烘的禾呈、时乖命蹇的金中(《三人行》),或是市民人物群中的父亲、母亲、七哥、五哥、六哥(《风景》)、粞、华、娟(《桃花灿烂》)、陆建桥(《黑洞》)以及一夜暴富的卢小波(《一波三折》),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生活的失败者(卢小波的暴发并不意味着成功,他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又坠入赤贫)。
这些人物何以有此困厄或失败的命运呢?
有时,方方将其归因于主人公自身。在谈及1991年的佳作《桃花灿烂》中的主人公粞与星子的悲剧时,作者说:“一个人失败的原因实在太多,而自己败在自己手上大概应占最大的比例。有很多思想深刻、目光犀利的人常常能理智而冷静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社会,但却不能正视自己。不知自己所短能使自己功亏一篑。常言中有‘一念之差’之说,这‘差’或许能左右人的一生。”在《一波三折》中关於卢小波作者又发表了相似的议论。
有时,方方则将原因归之于社会(环境)在发表于1992年、可与《风景》并称为方方代表作的《随意表白》中,作者写道:“一个人面对庞大的社会,他是一个极小极小的生物。他十分地软弱,十分地卑微。当这个社会大轮子转动时,无论快与慢,人都只能顺着轮子一起转动,否则难免被一辗而死……你唯一要做的便是:人家怎么过,你便怎么活;叫你怎么过,你就怎么过……。”[⑨]“我”的言说,雨吟的困境,肖白石的选择都是此一认识的证明。
有时,方方又归因于支配神秘命运的“偶然性”。这是构成方方小说的戏剧性情节(技术的)与关于人生与世界解释(内容的)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风景》中的二哥之死缘于偶识杨家兄妹;《桃花灿烂》中的粞仕途的突然逆转缘于靠山沈可为突然冒出个美国姨母;《三人行》中金中的命运铸定于解放前夕贪吃一只火腿作了国民党军医;《一波三折》中的卢小波一系列阴凄的经历肇始于在街头斗殴中上前多说了一句话。甚至在方方晚近的《何处是家园》(1994)这部传奇式作品中又下面涉及了“偶然性”问题:主人公曲折悲惨的一生都开始并决定在一个明丽春日因一只风筝与一位叫凤儿的市民少女的邂逅相识。作者甚有哲思意味地写道:“它深让我们感到了生命的无常,或说是人生的无法自控,而这种无常和无法自控制是我们一生中都想要参透却又无力参透的内容”。[⑩]
当方方把命运归之于个人的时候,既显示了她对理性、意志、个人力量的乐观主义的肯定(她相信个人可以支配自身),也表露了她某种意义上的浪漫与浅薄(粞正是以理性对环境作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却一次又一次为偶然所戏弄)。当方方把命运以社会或生存环境解释、尤其体味到个体在面对系统(社会、群体、机制等)的无能为力感时(方方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无可奈何”的字眼或表述),她具有了可称为现代或当代意识的深刻(巴尔扎克说我可以征服一切障碍时表现的是古典的理性、乐观与自信;卡夫卡说一切障碍都能征服我时表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悲观与深刻,卡夫卡恰恰在包括此一认识在内的现代意识上决定了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伟大)。当方方以感觉中的经验意义上的“偶然性”去解释人生与世界时显示了她的困惑、彷徨与悲观,也同时传递了她非哲学化的信息。但,无论是个人原因、社会环境还是无法言说的神秘“偶然”或是它们的“共谋”,方方人物的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却是一个笃定的事实。对这一事实的正视与表现决定了作为叙述人的方方的“沉重”。方方不愿或不想“沉重”。她企图“笑”(幽默)说“沉重”,以求化解或宽释。但内在的沉重仍使她无法保持乐观的情绪、优越的心理、聪慧的轻松、积极的态度,以致她终于失去了习见幽默的明丽亮色;同时,又因为她不曾彻底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对理性的肯定、对个人意志的推崇、对未来的希望,又使她与以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荒诞”观念立足、以荒诞技巧(变形、极端化等)存身、以死亡痛苦恐怖为题大开玩笑的黑色幽默保持了距离。这正是有人以为方方是幽默的又有人以为是黑色幽默的原因所在。方方,既不是习见幽默的,也不是黑色幽默的,她是介乎二者之间的“灰色幽默”,这正是方方小说的艺术个性。
十分有必要强调指出:“灰色”一词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是一个令人敏感且不快的词。它往往与否定或批判相系。笔者只是也仅仅是在艺术的色彩——犹如花之颜色——的意义上使用它。它是一种幽默的色调,犹如它是百花百色之一种。它享有平等于任何花与色的地位与权利。再进一步,在对幽默的表现领域的拓展与表现力的丰富的意义上,灰色幽默更应受到特殊的肯定与赞许。或者由于方方或其他类似作家的努力,如同墨有五彩,幽默亦有了三色(亮色、灰色、黑色)。
灰色幽默是方方的贡献,也是方方小说的艺术个性(这种个性在典型的《风景》、《白驹》等作品中已坐实为特定的语调、方方式的长句、排句与相应的修辞手段等,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展开)。它使方方在当代小说中具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对方方的广泛关注与赞赏恰是自《风景》始)。并且,它也显示了方方对於复杂人性、大千世界、幽深人性的解释的日渐深刻。浪漫的理想多有浅薄的种籽;现实的悲观常有深刻的基因。在现代意识中,人类早已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唯我独尊与自我陶醉,从理性与智慧无所不能无所不至的自大狂妄中冷静下来而正视自身的有限性。在方方灰色幽默的“无奈”中(这种“无奈”在非幽默作品的《随意表白》中则是以悲剧故事呈现的),已多多少少包含了上述的内容。方方似乎正站在一个走向远方的临界点上。
正如前文已限定的,方方这一个性虽明晰但却是不甚稳定的。自1986年的《白梦》始,这种个性较为突出地出现并保持在诸如《风景》(1987)、《白雾》(1987)、《黑洞》(1988)、《白驹》(1989)、《言午》(或《三人行》,1991)等作品中。以《风景》与《白驹》为最(有论者甚至因此称《白驹》为荒诞小说[(11)])。在同时或稍后的《桃花灿烂》(1991)、《行云流水》(1991)、《祖父在父亲心中》(1991)、《随意表白》(1992)、《无处遁逃》(1992)等佳作中,这种“灰色幽默”或以一个句子或以一节文字偶尔闪现,几乎荡然无存了。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题材所致(如《祖父在父亲心中》,主观的投入与用情使作者融入灰暗的人生故事中);有的则是因为方方对生活的感受与表达的“沉重”已使作者没有力量与勇气“开玩笑”了(如《无处遁逃》、《随意表白》)。沉重与伤感压迫了幽默的生发与存在。它既是方方思想的神经脆弱的暴露,也是方方对真善美执著追求的证明。从纯粹的风格意义上讲,这是方方小说个性的丧失(这当然可以从另一角度解释为作家的另一套笔墨)。今日文坛善以伤感情怀讲红尘故事的作家大有人在,尤以女作家为多,但善“灰色幽默”者有几人?能写出看似凌厉刻薄、失之厚道,品之则内涵苦涩、富于张力的句子的有几人?令人注目的是,包括1993年的《行为艺术》在内,方方受到读者喝采的《何处是家园》(1994)与《埋伏》(1995)等作品已通俗化、故事化了。它似乎显示了对生活与现实的逃避,对“严肃”与“沉重”的逃避。没有了幽默、轻飘了内容,留下了引人入胜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聪明的构思、由于熟练操作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作者说,“写这篇小说(指《埋伏》)一点也没有费劲,就像当初写《行为艺术》一样,很快,好像在玩玩打打中就完成了……”[(12)]。诚然,它们都是很好读亦可读的作品。但正如作者自白的:“当你看完了这个故事后,也就只是看完了。”[(13)]然而,这是作者真诚的希望还是一种文饰性的表达呢?作者在《四十岁,不甘心》的告白里,向自己的四十岁发出了挑战:“虽说写出天下最好的小说未免大口大气,难免不是调侃。可写出一部自觉最好的小说又有什么太难?未必真就会不如四十岁以前?另外有多少作家不也都是在四十岁以后才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的?”[(14)]。显然,方方雄心依然,她并不安于现状,而是有更高追求的。但,什么是“好小说”却是至要的问题。《风景》与《埋伏》,决不在一个层次上,但都可以称为“好小说”的。好读,是技术性质的,一个熟练而聪明的写作者即可为之,耐读(无论是语言、人物还是以文字承纳涵载的一切可资咀嚼的东西)却是内质的。它需要除却技术性质之外的思想、智慧、想象与创造力。《埋伏》是好读的,《风景》是好读亦耐读的。《风景》是方方四十岁以前具有纪录性的高度。它是方方小说艺术个性的辉煌闪现。对于方方,最好的小说似乎应该是好读、耐读且又属“方方式”的小说。而“灰色幽默”与方方曾有的成就与高度紧密相系。
自以为是的评论家历来讨嫌。但无论是作为读者与论者都厚望于已有成就且仍具潜力又不断追求的作家再上层楼。尽管方方极正确地说过“读者或评论家是永远都不可能通过作品参透作家的内心所思的,他们是永远也弄不明白作家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在怎样的心境下写完每一部作品的,”[(15)]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读者或论者仍然饶有兴趣地试图打开作家心灵的“黑箱”,企图走近并走进作品的世界。对方方,读者与论者均有厚望:她已走了很久,前面的路却依然长远,但愿她能走进一片新奇而美妙的“风景”。
注释:
①贺绍俊 潘凯雄:《方方——对都市文化的发酵现象来一点幽默》,《钟山》,1991年2期,第171页。
② ③ ⑤ ⑥ ⑧ (11)方方:《行云流水》,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83、89、229、289、80—85、329页。
④ ⑦ (15)方方:《无处遁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57、243、2页。
⑨方方:《随意表白》,《当代》,1992年6期,第185页。
⑩方方:《何处是家园》,《花城》,1994年5期,第4—5页。
(12) (13)方方:《怎么写了个〈埋伏〉》,《小说月报》,1995年3期,第21、5页。
(14)方方:《四十岁,不甘心》,《中华读书报》,1995年3月22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