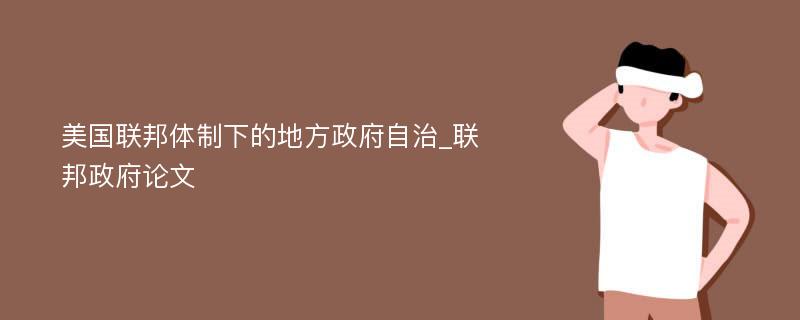
美国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自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制论文,美国论文,地方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由于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一门心思去划分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并没有努力为州以下的政府实体勾画蓝图,甚至没有在宪法中简单提及对地方政府的授权①。这在当时(18世纪晚期)是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那时的地方政府数目众多且权力很大。自从1789年宪法被采纳后,一个地方治理体系就发展起来。该体系依赖于对地方的正式授权以及赋予其广泛非正式权力(informal power)的地方自主传统。在美国的50个州内,每一个州都已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地方政府体制,划分了州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责任。
本论文考察美国地方政府拥有多大的权限以及地方政府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发挥多大作用。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实体抑或州、联邦政府②明显地限制着地方的行为?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各层次政府之间的分权充其量是很模糊的。部分是因为缺乏宪法上的明示,还因为不同州以及各个政策领域之间的差异。
在回答地方政府是否是具有重大政策制定权限的自治实体这一规范性问题时,首先要对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进行经验性评估(empirically assessing)。美国地方政府经常因反民主的倾向而受到抨击:从进步党人攻击城市政治机器的腐败到民权领导人与南方地方政府的抗争(后者支持种族隔离),再到谴责郊区排他性的区域规划,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一直因为不够民主而饱受诟病。不过,也存在着同样强烈的呼声,将地方政府提升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相对较小的面积和对公民生活的直接影响,提供了公民积极参与政府决定的最佳途径。这样,地方政府时而被描述成美国民主的救世主,时而又被刻画成民主最强大的克星,因此,呼吁州和联邦遏制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要求继续加强地方自治的呼声并存。
为了弄清楚这场地方政府是否有利于美国民主化的争论,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地方政府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而这也是本文的任务。论文第二部分分析地方政府正式的宪法地位和相关司法实践。但是,正式的规则只讲述了一半的故事。因此,第三部分考察地方政府拥有的非正式权力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地方影响力的原因。当我们考虑地方政府自治时,要认识到权力的非正式资源比权力的正式资源更加重要。接下来的部分探讨了地方政府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论述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增长、执行高层级政府的政策、提供一线服务以及政策创新中如何发挥作用。最后,从美国权力下放和地方自治的经验教训中总结一些想法。
二、地方政府的宪法地位
19世纪,州和地方政府经常就权力的合理分配发生冲突,冲突都交由法院来决定地方自治的程度,如果确实存在这一自治的话。“迪龙规则(Dillon's Rule)”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产物,它假定地方政府是“州的创造物”,没有固有的宪法上的自治③。这项规则是以法官约翰·J.迪龙的名字命名的(由他首次明确地阐述),赋予了州在其区域内对地方完全的控制权。布赖福尔特完美地概括了这个逻辑:
在和州的关系上,一个地方政府正式的法律地位可以用三个概念来概括:“创造物”、“代表”(delegate)、“代理”(agent)。地方政府是州的创造物,只是依据州的一个法律而存在。而州,作为造物者,拥有充分的权力自行决定改变、扩大、缩小或者取消任何或全部的地方单位。地方政府是州的代表,只拥有州选择赋予它的那些权力。由于州宪法没有明确的限制,州可以增修、删减、撤销它已经委托的任何权力,同样州也可以施加新的义务或者取消旧的特权。地方政府也是州的一个代理,在地方层面代表州行使有限的权力。④
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在“亨特诉匹兹堡市案”⑤和“特伦特诉新泽西州案”⑥中采用了“迪龙规则”之后,这项规则被普遍遵守⑦。然而,最高法院有时又会偏离这个逻辑。这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涉及教育的案件。在“圣安东尼奥诉罗德里格兹案”⑧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尽管传统的以房地产税为基础的教育集资会带来不平等,但部分地基于地方自治的缘故,这一做法是合乎宪法的。鲍威尔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坚持说:“拒绝将平等保护条款延伸到学校集资(领域),主要是为保存地方学校的自治,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自治。”⑨许多州法院也已支持学校财政来自房地产税的合宪性,其理由是“地方控制不能和地方的财务责任相分离”。因此,州对学校财政的均衡化将会削弱地方对教育的控制权⑩。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制的议题上,法院也诉诸了相似的逻辑,要求某一个特定学区内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制,而不是跨学区进行。在“米利肯诉布拉德利案”(11)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密歇根州一个联邦法院强制推行的跨学区校车接送计划,部分是因为此项计划将损害地方对学校的控制,并提出了一个隐含的前提:“市政府对地方自治有着不可侵犯的权力。”(12)这些例子证明了“迪龙规则”的适用是有选择性的:美国最高法院并不总是把地方政府视为“州的创造物”,在一些政策领域,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自治。尽管“迪龙规则”已经成为正式规则,但在实际运用中依然受到限制。
先将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放在一边,大多数州也没有充分使用它们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是通过立法或者宪法的条款将权力下放到地方,限制了“迪龙规则”的适用性(13)。因此,尽管“迪龙规则”剥夺了地方的权力,但是很多州又自愿背离了这项规则。授予地方政府某种程度自治的州宪法和成文法条款一般被称为:“地方自管”(home rule)(14),通常有两种形式(15)。《单一辖区内主权划分宪章》(Imperium in Imperio)授予地方控制所有本质上属于地方事务的权力。然而,判断什么是“地方事务”尤其困难,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区分出那些是应该由地方控制的事务(16)。确定何为“地方事务”的权力普遍地落入了州法院的手中,它发布了一些限制地方控制可能性的解释。比如,科罗拉多州将地方自管宪章的选择权给予地方,几乎让出了对地方事务的所有控制权。然而,该最高法院却在一份此项立法的支持意见中声称,如果州执意要涉足某个特殊问题,那么,就其性质而言,它就不再是地方问题了,也不包含于地方自管的宪章中,从而允许州随意干涉,削弱了地方自管的有效性(17)。诸如此类的解释已经严重削弱《单一辖区内主权划分宪章》给予地方独立于州政府之外的自治能力(18)。
由于《单一辖区内主权划分宪章》普遍无效,全国城市联盟(NLC)提出了一种地方自管的新模式,通常被称为“全国城市联盟的模式”、“美国城市协会(American Municipal Association)模式”,或者立法模式。(19)全国城市联盟在1953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这一宪章,基本颠覆了“迪龙规则”:地方不仅有明确授予的权力,还具有所有不是由州来承担的权力。州仍然可以随意干涉地方事务,但是在任何州不涉及的领域,地方享有自由的支配权。推动这场变化的主要动力源于限制法院在仲裁州和地方政府争端中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将这些决定推向政治领域。(20)现在,不再诉诸法院决定“地方事务”,州立法机关就能有效地决定什么事务留给地方政府。目前实施的大多数地方自管条款都遵循了这一模式。
地方自管条款因州而异,因地方政府的类型(州经常授予城市比县和学区更多的地方自管权)而不同,甚至在某个特定的大区域内(比如说跨市)也会有差别。一些州有浓厚的地方自治传统,在征税、政策执行、独立于州行动的方面,授予地方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一些州则严格限定了地方在征税、政策制定的权力,施加名目繁多的强制令,限制地方的行动范围。(21)除此之外,地方自管的制度化也呈现出差异性。在一些州,地方自管被庄严地写入州宪法,需要公众的投票、立法机关内大多数人的投票,才能改变。但在另外一些州,州立法者或者州长就可以改变或者取消成文法中的地方自管条款。
法院在应用“迪龙规则”时的前后不一,再加上地方自管条款本身的含糊和易变,导致学者就美国地方政府享有的自治程度展开争论。一些学者将“迪龙规则”和地方自管条款的无效作为地方无权的证据(22)。另外一些学者则看到,地方政府系统在制定和推进政策中拥有重大的权力,能够独立于高层级政府之外运作(23)。如果我们只看正式的权力,“地方无权派”的结论看起来更令人信服。毕竟,授予地方的任何自管权力,都可以被州取消,如果它选择这么做的话。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宪法地位,一个决心已定的州政府可以自定规则。然而,正式权力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半,因为地方政府拥有的权力要比其法律地位所暗含的大得多。现在我们就转向对非正式权力的介绍。
三、地方权力的非正式资源
“地方自治”必须依据对“权力”的定义,一个经常被用到但却很少被定义的词。用纯粹的法律方式来定义权力,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难题。很显然,影响地方政府自治的不止是权力的正式授予,还有非正式的惯例和流行的政治文化。为了超越一种墨守成规的概念,罗伯特·达尔这样定义权力:“A控制B的程度达到了可以让B做一些原本不想做的事情。”(24)这种行为主义路径也存在缺陷。正如达尔的众多批评者所指,没有发生冲突,权力也会存在。B可能预计到A的反应,从而做A期望的事情,甚至是在没有受到公然强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或者,A可能用一种让B不能依据自身利益行动的方式来确定议程。(25)更有甚者,A能够影响B的信仰,用一种使B相信做A期望的事情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来实现。(26)最强有力的个体或许是那些并不积极行使权力,却拥有足够的权力资源来实现其目标的人。(27)
把这场争论运用到政府间关系的分析中,我们便不能仅仅考察那些州强迫地方做一些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或者地方政府积极抵制高层级政府的案例,就来评估地方政府的权力。即使这些是行使权力的例子,但是聚焦公然的冲突不能展现地方自治的完整画面(28)。地方避免冲突的能力——防止州干预地方事务——与一旦冲突产生时地方获胜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有鉴于此,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营造情势的能力,它可以让州政府要么选择遵从地方控制,要么甘愿接受地方影响为先决条件。所以,理解地方自治需要我们去考察地方拥有的权力资源,正是这些资源给地方带来了自治的动力。下面将讨论地方权力的这些资源。
执行权力
地方政府经常是州或者联邦政策的一线执行者。因为对所有地方政府采用标准化的规则过于麻烦且无效率,有些时候,就有必要将政策的细节留给地方来自由裁量。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高层级政府允许地方有一些灵活性,希望此举将带来更好的结果。交通政策就是一则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70年里,联邦政府资助州和地方政府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但是允许它们在公路的选址和资金的用途上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每一个地方面临着不同的交通类型和问题,交通政策的本质适用于地方裁量权。尽管原则上,联邦政府可以命令工程开工,但是联邦官员更喜欢制定一些宽泛的指导方针,让较低层级政府自己解决细节问题。许多州也出现了相似的过程,州长和州议会遵从地方的偏好,比如交通工程的可取性和选址(尽管有些州选择更加集权化的控制)。(考虑到)直接控制政策的执行并不总是符合高层级政府的利益,在执行它们确定的政策时,就允许地方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地方官员拥有不同的目标抑或不是其州和联邦同僚偏好的话,他们经常利用其作为执行者的位置,朝着自己更喜好的方向去塑造政策。“社区开发整体拨款”(CDBG)计划就是一则典型的例子,它是联邦政府用来促进中低收入居民社区复兴和经济增长的。该计划以赠款形式拨付给城市,给予城市在如何使用拨款上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尽管这项计划旨在惠泽中低收入居民社区,但是许多城市将资金用于中产阶级的社区和富裕阶层社区,因为这些社区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则地方使用(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例子事关国土安全赠款。“9·11事件”过后,联邦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以便加强它们防范恐怖袭击的预警能力。这笔资金专门用于以下项目:第一时间反应设备、紧急反应系统和改善执法能力。既然各个地方面临不同的威胁,有着不同的需要,联邦政府就允许地方在这笔赠款的使用上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结果,一些地方将这笔钱花在了和反恐只沾点边的项目上。总体来看,它们基本上用来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花在保障国土安全上。联邦官员试图遏制这些滥用,但是,获得赠款的地方数量庞大,再加上“国土安全”的模糊性,使得这项任务很难完成。
如果高层级政府在起草政策时没有给予明确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地方政府经常通过重新解释政策夺回这种权力,或者用一种最小化消极影响的方式来执行这些政策。(29)它们能够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是因为高层级政府不能总是有效地监督地方的执行,并且强迫不服从的地方政府去执行其不希望的政策需要广泛的监督。即使这种监督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高层级政府也不愿动用更多的资源去这么做。从联邦和州官员的立场来讲,通过一项立法的政治行为本身常常比它的有效执行更加重要,因为公众往往关注的是立法的通过。(30)因此,地方经常能够以违反高层级政府偏好的方式来执行政策,且不受惩罚。
消极抵制
高层级政府经常下令(mandate)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某些措施或者执行不同的任务。(31)联邦政府通常会为这些要求提供资金,起码是部分资金。然而,州在要求地方采取行动时却不提供相应的资金。下令是美国三个层次政府争吵的中心,州迁怒于联邦的下令,地方又抱怨州和联邦的要求。尽管如此,地方无论多么的不情愿,通常都会遵守这些要求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果认为这些要求太艰巨,它们就会尽量通过消极抵制来逃避。地方将无限期地推迟执行要完成的任务,或者做些表面文章来应付,而不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在许多政策领域,州和联邦政府拥有对付此类行为的武器——主要是通过扣押专项拨款或者罚款。但是在一些政策领域,监督上的困难、又缺乏采取惩罚性措施的政治意愿,消极抵制便能成功。
一种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抵制法院判决方面。州和联邦法院经常要求地方政府停止相应的做法,因为它们违背了宪法或者州和联邦的法律。然而,法院系统依靠其他政府部门执行其判决的现实,给予地方政府在抵制这些判决时的优势。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各州普遍抵制联邦法院取消种族隔离制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5年)取消了学校的种族隔离制。但是,直到数年以后,许多地方学区才正式取消种族隔离制(甚至从那时起,它们找到了非正式的途径来维持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新近发生的一则例子是,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做出的“芒特劳雷尔乡镇”(Mt.Laurel)系列判决(32)。法院认定阻碍建造中低收入人群房屋的地方土地规划条例违宪。法院的最初判决是在1975年下达,但是,直到1983年作出第二个相关案件判决时(它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地方才最小限度地服从了1975年的判决。这个判决还因州立法而有所削弱,因为后者减轻了惩罚力度以及允许地方政府规避服从。尽管州最高法院的立场坚决,但新泽西州的城市和县仍能够有效地避免建设保障性住房。
信息控制
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尽管是老生常谈,但却适用于美国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了解“现场”发生的事情,对政策的效果掌握第一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用于劝说高层级政府制定、调整或拒绝某些政策选项。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地方政府雇佣说客影响州和联邦的政策制定者;美国主要城市在各自的州首府和华盛顿都有这样的说客,并且像市长协会这类的组织也积极游说。(33)当然,地方知识的重要性会因为政策议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一些地区,高层级政府能够收集它们自己的信息,而不需要地方政府来获得信息。此外,随着新技术的运用,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变得更加简单,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可能正在减弱。
选举权力
各州在过去能够比现在更多地限制地方自治。即使许多州宪法限制了立法机关的权力,大多数州仍能够通过额外的政策要求(mandate)和限制,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此外,州立法机关更加积极地参与州宪法的修订,增强它们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毕竟,没有一个州被要求将自管权授予地方。如果地方政府破产或者经营不善,许多州也制定了“接管”地方政府事务的应急条款。这些条款在表现不佳的学区最为常见。(34)无独有偶,联邦政府也承担一些地方职责,在更大程度上干预地方治理(尽管它们比州政府更无权这么做)。尽管如此,高层级政府仍然不能对地方政府完全施展权力。州偶尔确实干预地方事务,限制地方自管权,甚至接管管理不善的地方政府,同时联邦政府有时也的确会强行要求地方有所作为。但是,这种干预的程度并未达到极致。因此,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取消(地方自治)”?
主要原因是,选举背景(electoral context)经常阻止了高层级政府干预地方事务的力度。州和联邦的民选官员不太可能经常行使他们对地方政府的权力。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要么提高竞选对手在当地的支持力,要么给地方当局反对他们落下口实,从而对其当选造成不利的影响。州或联邦的许多政治候选人是寻求提升自身职业的地方官员,他们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针对州和联邦现任官员的潜在的挑战群体。因此,后者不愿采取将引起地方敌意和增加在下届竞选中竞争可能性的行动。举例而言,在许多州,立法机关本可以接管对居民区和商业区规划权的控制,决定未来发展的类型和程度。但是,这会带来重大后果,因为地方官员、社区积极分子和许多普通市民将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接管行动。一个附带的结果则是,由此产生对州议员的敌对情绪,为后者的竞选对手提供了良机。此外,地方政客和地方政党组织经常通过表态支持某位候选人(endorsement)以及动员选民去投票,而对州和联邦选举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迫使州官员在侵犯地方自治之前三思而行。尽管全国性政党组织的兴起及其权力的壮大,使得地方影响在竞选中比以前考虑地少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对州和联邦的选举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
当然,有时出于选举的利益,高层级政府也会干预地方事务,因为选民不满地方政府的现状。州和联邦一窝蜂地参与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十二年义务教育(K-12 education),就很能说明问题。传统上,十二年义务教育一直是地方的职责,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教育体制“漏洞百出”,选民转而希望州和联邦官员在这一议题上“有所作为”。鉴于选民的不满,他们为此制定一部新立法,极大地限制了地方的管辖权(参见下文)。选举利害关系的重要性会有所变化,取决于地方政府在与特定的选举或候选人关系中所处的立场,以及饱受质疑的具体政策。选举政治虽不总是有助于地方政府保持其自治,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却是解释高层级政府不能对地方施加更多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方控制”话语(discourse)
地方政府权力的最后一个资源涉及美国历史悠久的“地方控制”话语。美国有一个地方政府独立的浓厚传统,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该传统已衍生出一种地方政府乃美国自由和民主堡垒的大众话语。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就捕捉到这一点,他在书中盛赞新英格兰的乡镇会议是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训练场。(35)诺曼·罗克韦尔的一副名为“言论自由”的油画也抓住了这一话语的本质。(36)该画描绘了一位农夫在一次新英格兰乡镇会议上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多美国人认为地方政府“更加贴近人民”,他们将削弱地方自治视为一种对民众治理(governance)和自由的威胁。这一观点并非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说法。有时美国人还会认为“特殊利益集团”或政治老板(machine bosses)正把持着地方政府。因此,如上所述,地方政府有时被描述成美国民主制度的救星,有时又被刻画为美国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克星。(37)但是,“地方控制”的故事承载着强有力的涵义,给予地方官员在捍卫他们权力时有一种话语上的优势。
“地方控制”话语经常被用来证明地方自治的正当性。举例而言,与迪龙法官同时代的托马斯·库利法官主张,地方自治是一种自然权利:“库利学派的法官和学者坚持说,自古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各个地方就已享有自治的权利。这项权利是古老而固有的,理应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民的又一项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即便没有成文宪法的专门保护,它也无伤大雅。”(38)托马斯·杰斐逊也认为,地方控制将通向民主和自由。在他晚年,杰斐逊甚至提议将国家分割成5-6平方英里大小的行政区,每个行政区享有对道路、警察和其他“地方性”事务的重大权力。每一个行政区意味着是一个免受高层级政府侵犯的主权实体,通过把决策权转向更小单位的政府,公民拥有了更多的参与权,美国民主因此得到加强。(39)即使由库利和杰斐逊提出的权力下放途径并不总能成功地保护地方自治,但是在试图规避州和联邦的侵蚀时,它们却构成了地方官员的又一个额外资源。
综上所述,尽管地方政府缺乏宪法地位,它们在美国却拥有任由其支配的充足资源。盖拉德·弗鲁克、戈登·克拉克和其他人作出的地方政府“无权”的推测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过多地关注法律条文,却对实际的政治运作关注不够。地方政府的确在它们能做的事情上饱受限制,人们可以列举出许多高层级政府限制其行为的例子。但是,这不足以改变一个事实,即地方政府拥有多重权力资源,可以用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际政策的结果。
四、地方政府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
地方政府影响美国公共政策的力量因时而异,因政策领域而变。各级政府间关系绝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过去一百多年的趋势一直是联邦政府以牺牲州和地方的利益来扩大自身的权力,但是,任何特定政策领域内的具体权力平衡未必紧跟这一潮流。尽管存有差别,地方政府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方式来影响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下面将围绕着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四项关键性地方职能,来讨论地方政府的影响力。
提供基础服务
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职责是为大众提供基础服务。对诸如供水系统、下水道、输电网、公共交通和地方道路之类的核心基础设施,地方政府要么直接控制,要么行使广泛的影响力。它们也对治安维护、消防安全、垃圾处理、修葺公园和图书馆承担起主要职责。地方政府履行这些职责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凸显了它们在维持居民高品质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州和联邦政府也参与规制这些活动的许多方面,因而地方政府为上述服务完全承担责任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正如莫顿·格罗津斯在一本研究美国联邦主义的颇有影响力的书中所言,美国的政治体制就像一个“大理石花纹的蛋糕(marble cake)”,职责在三级政府之间(以旋转的方式)分配,没有谁能够完全包揽。(40)即使提供基本服务是一项共同承担的职责,地方政府也对提供这些服务的方式、成本和效率有着重大影响。
十二年义务教育提供一则地方政府是相关服务提供者的例子,尽管州和联邦政府在此项计划中共同承担职责,且参与力度日渐加大。如上所述,传统上,美国的教育是由地方控制的,州拨付部分财政资助。但是,二战后,州开始在规制教育方面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譬如,制定课程标准、建立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尽管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校的日常管理一直掌握在地方学区委员会手里。它们作出像如何教孩子,由谁来教以及如何管理学校之类的重要决策。20世纪90年代却见证了州对学校规制的井喷式发展,这是由于大众普遍对教育质量不满所引发的。州开始批准考试制度并且建立其他问责机制,以便确保学校充分地执行政策。(41)
然后,联邦政府在2001年通过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法》(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A)。该法规定了考试制度,针对不达标的学校制定一系列惩罚措施。这代表了联邦参与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力度有重大进展。在《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法》颁布之前,联邦政府为不同的教育职能(如资助残疾儿童或者为贫穷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拨付赠款,但是,从未惩罚过表现不好的学校。按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对教育没有任何权威,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法》是自愿性质的安排。然而,如果州和地方不参与这项法案,它们就会失去联邦在教育领域的赠款(大约占教育总支出的10%),这样一来,所有的州不得不参与其中(尽管有些勉为其难)。(42)《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法》以及州参与地方教育力度的加大,表明地方对教育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地方学区对教育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话虽如此,地方对教育仍旧拥有重大的影响力。在一些州,地方学区为筹措教育经费,可以确定财产税率和影响岁入征收的数量。它们也可作出教师聘任的决定,与教师协会和其他学校人员谈判工资及福利。即使所有州都要求制定一份核心课程规划,学区仍然在选修科目上有一些灵活性。它们也会作出诸如如何授课、使用哪种教材以及教学方式的决定。(43)它们也在执行《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法》和州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因为这些法律在实施的细节上有一定的灵活性。(44)地方学区的权力虽受到明确限制,仍旧是教育政策的相关制定者,尽管最近州和联邦一窝蜂地参与这一领域。(45)
规制土地使用和促进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最有影响力的政策领域是土地的使用。传统上,地方政府一直控制着本地区的土木兴建。除了几个例外——联邦所有的土地、印第安人保留地和环境保护区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大多数土地使用是一种地方特权,表现在土地规划(zoning)条例和发放建筑许可证。土地使用政策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公民的生活质量都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作出的有关建设决定可以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市的宜居度。然而,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这两个目标经常发生冲突,因为快速的发展将导致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人口拥挤和其他降低居民宜居度的因素。这种冲突导致一些学者主张,土地使用的决定以及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产生的冲突,已经成为美国地方政治的核心内容。(46)
在经济的发展中,美国市县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既影响到土地的使用,又把本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47)在他很有影响的《城市发展的边界》一书中,保罗·彼得森已经分析了地方发展经济的努力与其后果的内在逻辑。(48)彼得森说明,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为了在财政上站稳脚跟,城市深受促进经济增长的压力。城市必须平衡它的预算开支,(49)但是也面临着来自居民的压力:他们既想拥有高品质服务,又不愿多纳税。居民对政府服务无限制的要求,对提高税收的反对,再加上“硬性”的预算限制,三者共同置地方官员于政治上的脆弱地位。由于城市的绝大多数收入来自不动产和销售税,因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促进经济增长,这样它们才会有更多的可以课税的不动产和销售额。经济增长将会产生额外的岁入而不用提高税率,然后将其用于服务居民。这就产生了一种“经济增长的动力”:正是既想满足居民需求又要维持财政稳定,促使城市去推动经济的增长。
这对我们理解城市政治有重要意义。首先,由于所有的城市都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压力之下,它们都争着吸引工商业和居民落户本地。这种竞争促使城市建立一个有利于招商引资的市场机制,但是,它也刺激城市去关注富人——他们交纳税多,需要的政府服务少——而不是穷人的需求。出于竞争的压力和保持低税率的愿望,城市不愿参与有利于穷人的重新分配政策(比如,福利或医疗补贴)。彼得森总结到,增长的动力孕育出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刺激了城市的有效运转,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而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50)彼得森主张,既然城市不愿为穷人提供服务和福利,那么,这些再分配的职责最好由联邦政府来履行,因为后者没有硬性的预算限制。(51)
彼得森的理论遭到从经验和规范两个方面的批评。托德·斯旺斯特龙已经证明,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在同一水平上竞争,至少部分城市可以避免竞争的压力。(52)许多学者已经接受了彼得森关于城际间竞争程度的经验研究,但却声称竞争的结果弊大于利。为吸引工商业投资,许多城市给予优惠政策,常常给失去这些商机的城市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在这种城际间竞争的情形之下,经济增长的速度是零(zero-sum),因为一方的获胜是以另一方的失败为代价的。即使“赢家”在这次竞争中获利,这些益处也会被其他领域的失败所抵消,根本落不到一点经济增长的实惠。(53)此外,一些学者已经证明,吸引工商业的竞争性压力,迫使城市不能向急需的居民提供它本应该提供的服务。城市努力去吸引工商业和富裕的居民,却往往忽略了中低收入居民的需求。皮特·艾辛格最有力地发展了这种批评意见,论述说竞争的压力导致城市只关注旅游业和娱乐业(这两项产业能增加税收)的发展,而这是以牺牲本地居民所使用的基本服务为代价的。(54)
不论城际间的竞争有多少优点,毫无疑问,城市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城市能够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们控制着土地使用的决策权:城市决定哪里建企业、哪里建居住区、城市人口的密度以及谁能得到建筑许可证。这些决定对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城市的宜居度产生决定性影响,使得规制土地使用成为美国地方政府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能。
执行政策
地方政府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涉及执行高层级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特别是县,它作为州政策的执行者起着重要的作用。县通常没有被给予多少地方自管权,常常听命于州政策的摆布,导致许多城市专家仅仅专注于城市。(55)然而,不应该忽视源于政策执行的权力。州依赖于县有效地执行政策并遵守其规制。即使州最终能够惩罚那些不顺从它们意愿的县,但是强制执行所带来的成本(时间和政治上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州愿意遵从县的做法。县可以用以下方式影响州政策的性质:改变州计划的执行方式,或者游说州作出更符合它们利益的转变。
城市也经常执行州和联邦的政策。具体说来,联邦的许多计划有赖于城市政府,有时还要与州、县政府相配合来执行。《1993年开发区/产业园法》(EZ/EC)的执行情况就是一则典型的例子。该法系联邦政府对1992年洛杉矶暴动的最重要的回应。这项政策的基本框架是向贫穷的内城(Inner-city)提供资金,以期实现社区复兴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然而,联邦政府并未明确说明如何使用基金或者如何实现复兴。相反,它只是要求城市提交描述基金用途的提案,通过竞争的程序,由联邦官员选择哪些城市获得资助。尽管城市需要遵守指导方针,但是,在获得赠款后,它们在基金的花费和落实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这项方案的实施就是联邦政府通过给予城市广泛的执行权力,凭借它们来完成一项政策目标(本案是城市复兴)的一则例子。城市影响着计划实施的最终结果,这就造成不同城市的执行方式出现重大偏差。(56)
政策创新实验室
最后,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作为政策创新的实验室。许多研究联邦主义的学者已经证明,通过增加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联邦主义就能推动政策创新。(57)次级国家政府(Subnational)可以实验新的观念,与此同时,在政策推广的过程中,其他行政区可以从它们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58)地方政府成为规制有关竞选捐款和支出政策的创新者,就是一则很好的例子。这一问题是美国政治生活永久的话题。联邦政府在1974年对竞选基金条例作出重大调整,但是这一改革的很大部分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从此在联邦层面再没有任何创新或实验。然而,这并不妨碍州和地方从事它们自己的改革。纽约市在1989年率先制定了里程碑意义的竞选基金改革法(洛杉矶在1993年紧随其后),建立了第一个关于法律竞选中公众基金的全面制度。(59)州和地方政府在“干净钱(clean money)”的改革运动中走在前列,向那些同意放弃私人募捐基金的候选人提供大量的公众资金。因此,尽管联邦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改革全国性竞选的资金筹措方式,但是,次级国家政府已经在实验另外不同的政策选择。
城市为学者研究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环境。城市的特点千差万别,不仅在面积和人口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还在政治倾向、舆论、隶属党派以及影响政治冲突的其他因素方面不同。再者,城市的内部组织也不同,比如城市议会的规模、市长权力、选举体制和部门结构。举例而言,一些城市拥有强势的市长和相对较弱的市议会;而另一些城市则拥有大体上是礼仪性人物的市长,因为市议会是政治控制的中心。所有这些变量都能影响到采纳及执行政策的动力,还会影响到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地方环境营造了一个实验室,政策学者和政治科学家可以在这儿分析竞争性政策路径的优点。
五、结论
尽管存在着“迪龙规则”和经常无效的自管条款,地方政府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依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地方政府权力的主要资源,不是州或联邦政府正式授予的权力,而是源于刺激高层级政府允许其采取某种程度自治的政治动力。州和联邦官员经常留意地方的偏好,不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必须这么做,而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在一些政策领域,最典型的就是土地使用,有着悠久的地方控制的传统,州和联邦政府官员就会遵从地方的管理。甚至对于高层级政府已经扮演积极角色的政策领域来讲,地方政府也经常有一定的能力去影响或塑造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种说法认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有限,今天所拥有的权力比50年或100年前要少得多。人们也同样可以说,就像盖拉德·弗鲁克富有说服力的看法,地方政府本该拥有更多的自治,因为它将加强民主,提高政府效率。(60)加强地方权力可以带来显著收益。但是,我们不应该混淆这一规范性结论与地方没有什么权力的经验式结论的区别。地方虽不像一些学者(和大多数地方官员)所喜欢的那样富有影响力,但是它们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探究地方在美国多层政府系统中的作用,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与美国其他政治机构相比,地方政府还未得到充分研究,现有的许多研究只聚焦在少数并未与政府间关系直接相关的问题。考察那些支持地方应享有更多自治的人们的经验性主张,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具体说来,许多人都主张,授予地方更多的权力将提高公民的参政水平与民主程度(步托克维尔和杰斐逊的后尘),但是,试图建立这一因果联系的实证性研究却没有多少。盖拉德·弗鲁克已经沿着这些路线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称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公民的参与度:如果城市政府有更多的权力,那么公民将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61)现在已经有一项探究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无定论),(62)但是,鉴于民主化论据是地方自治支持者的核心内容,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
还需要努力将美国地方政府的研究与比较非集权化研究的文献联系起来。对全球范围内非集权化的研究已经产生大量的文献,很大程度上是对国际性捐赠组织(比如世界银行)推动非集权化的一种回应。(63)然而,美国研究地方政府的学者仍未以任何富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类文献。如果美国城市的研究专家和关注其他国家非集权化的学者进行互动,通过引进新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前者的研究水平将会提升。在理解美国地方自治的性质和程度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利用研究其他国家非集权化的大量文献,可以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注释:
①在本篇论文中,“地方政府”指的是所有州以下的政府实体,包括市、县、镇、村、学区和特别区。
②在整篇文章中,联邦和州政府被通称为“高层级政府”(higher tiers)。
③对迪龙法则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Richard Briffault,"Our Localism:Part I: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Law",Columbia Law Review,90(1),1990:1-115; Richard Briffault,"Our Localism:Part II:Localism and Leagal Theory",Columbia Law Review,90(2),1990:346-454; Gordon L.Clark,Judges and Cities:Interpreting Local Autonom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5; Gerald E.Frug,"The City As a Leagal Concept",Harvard Law Review,93(6),1980:1057-1154; Gerald E.Frug and David J.Barron,City Bound:How States Stigle Urban Innova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④Briffault,"Our Localism:Part I",pp.7-8.
⑤Hunter v.City of Pittsburgh,207 U.S.161[1907].
⑥Trenton v.New Jersey,262 U.S.182[1923].
⑦尽管美国最高法院采纳了“迪龙规则”,但不是所有的州法院在诉讼时都把它作为一项成文法的解释规则来使用。可参见Jesse J.Richardson Jr.,"Dilion's Rule Is from Mars,Home Rule Is from Venus:Local Government Autonomy and the Rules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Publius,41(4),2011:662-685。
⑧San Antonio v.Rodriguez,411 U.S.1[1973].
⑨Joan C.Williams,"The Co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y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The Polities of City Status in American Law",Wisconsin Law Review,83,1986:107.
⑩Briffault,"Our Localism:Part I",p.28.学校资金的贫富不均是否违反州宪法,州法院的判决各不相同。正如布赖福尔特所证明,即使一些州允许学校财政的不平等,但是另外一些州则要求将学校财政均衡化,尽管这将会导致地方对其控制权的丧失。
(11)Milliken v.Bradley,418 U.S.717[1974].
(12)Williams,"The Co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y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p.84.
(13)Daniel Elazar,American Federalism:A View from the States,3rd e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4.
(14)为了与更为抽象的local autonomy(自治)有所区别,故将home rule翻译为“自管”。——校译者
(15)地方自管的发展历程,可参见David J.Barron,"Reclaiming Home Rule",Harvard Law Review,116,2003:2255-2386。 对“地方自管”一词不同使用方式的讨论,可参见Richardson,"Dillon's Rule Is from Mars,Home Rule Is from Venus"。
(16)Morton Grodzins,The American System:A New View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Rand McNally,1966: 320-325.
(17)Elazar,American Federalism,p.205; Clark,Judges and the Cities,pp.171-181.
(18)Gordon L.Clark,"A Theory of Local Autonom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74(2),1984:204.
(19)Barron,"Reclaiming Home Rule",p.2325.
(20)Barron,"Reclaiming Home Rule",p.2325.
(21)地方自治如何因州而异的经验性数据,可参见Ann O'M.Bowman and Richard C.Kearney,"Second Order Devolution:Data and Doubt",Publius,41(4),2001:563-585; Dale Krane,Platon N.Rigos,and Melvin B.Hill Jr.,Home Rule in America:A Fifty State Handbook,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2001; G.Ross Stephens,"State Centralization and the Erosion of Local Autonomy",Journal of Politics,36(1),1974:44-76。
(22)Gerald Frug,City Making:Building Communities without Building Wal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Clark,"A Theory of Local Autonomy".
(23)Briffault,"Our Localism,Part I"; Briffault,"Our Localism,Part II".
(24)Robert A.Dahl,"The Concept of Power",Behavioral Science,2(3),1957:201-215.
(25)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Baratz,"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An Analytical Framework",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7(3),1963:632-642;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Baratz,"Two Faces of Powe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4),1962:947-952.
(26)Steven Lukes,Power:A Radical View,2nd ed.,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 John Gaventa,Power and Powerlessness: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Urbana: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0.
(27)Alvin I.Goldman,"Towards a Theory of Social Power",Philosophical Studies,23(4),1972:221-268.
(28)David J.Barton,"A Loc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 Federalism",Duke Law Journal,51(5),2001:377-433.
(29)有关事例可参见Martha Derthick,New Towns in-Town:Why a Federal Program Failed,Washington D.C.:Urban Institute,1972。
(30)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
(31)Joseph F.Zimmerman,State-Local Relations:A Partnership Approach,2nd ed.,New York:Praeger,1995.
(32)两起重大案件: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1975); South Burlington County N.A.A.C.P.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92 N.J.158(1983)。
(33)事实上,在首都华盛顿,所有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即那些参与某种类型的正式游说活动的实体)中有11%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可参见Kay L.Schlozman,"Who Sings in the Heavenly Chorus? The Shape of the Organized Interest System",in L.Sandy Maisel and Jeffrey M.Berry(eds.),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34)David R.Berman,"Takeovers of Local Governments:An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of State Policies",Publius,25(3),1995:55-70; Peter Burns,"Regime Theory,State Government,and a Takeover of Urban Education",Urban Affairs Review,25(3),2003:285-303; Peter Burns,"Race and Support for State Takeovers of Local School Districts",Urban Education,45(3),2010 :274-292.
(35)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1835].
(36)该幅油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进行反法西斯宣传而出版发行的“四大自由”宣传油画之一,影响非常广泛。——校译者
(37)对“地方”等同于“民主”观点的抨击,可参见Mark Purcell,"Urban Democracy and the Local Trap",Urban Studies,43(11),2006:1921-1941; K.Newton,"Is Small Really So Beautiful? Is Big Really So Ugly? Size,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 in Local Government",Political Studies,30(2),1982:190-206。
(38)Anwar Hussain Syed,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New York:Random House,1966:54.
(39)Anwar Hussain Syed,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pp.38-41;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New York:Penguin,1963:240-249.
(40)Grodzins,The American System.
(41)Diane Ravitch,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School System,New York:Basic Books,2010.
(42)一些州已经起诉联邦政府,声称《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法》侵犯了州的主权,是不合乎宪法的。但是迄今为止,这些诉讼无一获胜。
(43)一线教育工作者——教师和校长——通过他们的行动也可以影响教育政策。可参见Micahel B.Berkman and Eric Plutzer,"Local Autonomy versus State Constraints:Balancing Evolution and Creationism in U.S.High Schools",Publius,41(4),2011:610-635; Melissa J.Marschall,Elizabeth Rigby,and Jasmine Jenkins,"Do State Policies Constrain Local Actors? The Impact of English Only Laws on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Public Schools",Publius,41(4),2011:586-609。
(44)对《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后法》执行情况的讨论,可参见Frederick M.Hess and Chester E.Finn Jr.,"Held Back:No Child Left Behind Needs Some Work",Policy Review,144,2007:45-58。
(45)Michael Mintrom,"Promoting Local Democracy in Education:Challenges and Prospects",Educational Policy,23(2),2008:336; Jeffrey R.Henig,"The Politics of Localism in an Era of Centralization,Privatization,and Choice",in Robert L.Crowson and Ellen B.Goldring (eds.),The New Local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Malden,MA:Wiley-Blackwell,2009.
(46)John R.Logan and Harvey L.Molotch,Urban Fortun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47)统上,财产税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但是,近些年来,它们减少了对财产税的依赖,转而偏向于销售税和非税性收入(比如罚款)。可参见Dale Krane,Carol J.Ebdon,and John Bartle,"Devolution,Fiscal Federalism,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Municipal Revenue:The Mismatch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14(4),2004:523-525。
(48)Paul E.Peterson,City Limi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49)所有的州要求城市平衡自身的营运(operating)预算。城市只能为公益项目借钱,即使这样,它们借贷的能力也常常受制于州。
(50)彼得森部分借鉴了查尔斯·蒂博特那篇研究地方间竞争性优点的经典性论文(Charles Tieb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5),1956:416-424),另见Mark Schneide,The Competitive Cit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uburbia,Pittsburgh: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
(51)Paul E.Peterson,The Price of Federalism,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5; Paul E.Peterson,Barry G.Rabe,and Kenneth K.Wong,When Federalism Work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5.
(52)Todd Swanstrom,"Semisovereign Cities:The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Polity,21(1),1988:83-110。 也可参见Baodong Liu and James M.Vanderleeuw,"Economic Development Priorities and Central-City and Suburb Differences",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32(6),2004:698-721。
(53)对非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的批判,可参见Richard C.Schragger,"Decent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Virginia Law Review,96,2010:1837-1909。
(54)Peter Eisinger,"The Politics of Bread and Circuses:Building the City for the Visitor Class",Urban Affairs Review,35(3),2000:316-333.
(55)有关县域研究的综述,可参见J.Edwin Benton,"An Assessment of Research on American Countie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65(4),2005:462-474。
(56)Michael J.Rich and Robert P.Stoker,"Rethinking Empowerment:Evidence from Local Empowerment Zone Programs",Urban Affairs Review,45(6),2010:775-796; Marilyn Gittell,Kathe Newman,Janice Bockmeyer,and Robert Lindsay,"Expanding Civic Opportunity:Urban Empowerment Zones",Urban Affairs Review,33(4),1998:530-558.
(57)Michael C.Doff and Charles F.Sabel,"A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Experimentalism",Columbia Law Review,98(2),1998:267-473; Robert A.Schapiro,Polyphonic Federalism:Towards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58)有关事例可参见Michael Mintrom,"Policy Entrepren-eu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1(3),1997:738-770; Lora Cohen-Vogel,William Kyle Ingle,Amy Albee Levine and Matthew Spence,"The 'Spread' of Merit-Based College Aid:Policy,Policy Consortia,and Interstate Competition",Educational Policy,22(3),2008:339-362; Lina Y.Newton and Brian E.Adams,"State Immigration Policies:Innovation,Cooperation,or Conflict?" Publius,39(3),2009:408-431。
(59)对这些方案有效性的评估,可参见Brian E.Adams,Campaign Finance in Local Elections:Buying the Grassroots,Boulder,CO:First Forum Press,2010,Chapter 8。
(60)Frog,City Making; Frug and Barron,City Bound.
(61)Frug,City Making,p.10.
(62)Dale Krane and Platon N.Rigos,"Municipal Power and Choice:An Examination of Frugs 'Powerlessness' Thesis",该文提交给2008年8月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会议。
(63)Pranab Bardhan and Dilip Mookherjee(eds.),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IT Press,2006; Tim Campbell,The Quiet Revolution: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atin American Cities,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b Press,2003; G.Shabbir Cheema and Dennis A.Rondinelli(eds.),Decentralizing Governance:Emerging Concepts and Practice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7; Richard C.Crook,"Decentralis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The Polities of Local-Central Rel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3,2003:77-88; Merilee S.Grindle,Going Local:Decentralization,Democratization,and the Promise of Good Govern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James Man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9; Daniel Treisman,The Architecture of Government:Rethinking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