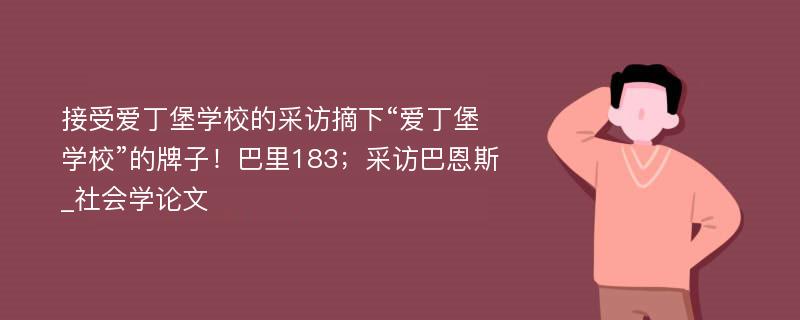
爱丁堡学派访谈录——3.卸下“爱丁堡学派”这张招牌吧!——巴里#183;巴恩斯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丁堡论文,学派论文,巴里论文,访谈录论文,这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3)04-0013-10
在场人物:巴里·巴恩斯(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以下简称“巴”)
黄之栋(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博士,台湾国立空中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以下简称“黄”)
方芗(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以下简称“方”)
高璐(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翻译团队:朱容萱(高雄餐旅大学应用英语系专案助理教授)
黄之栋(台湾国立空中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
黄:您一开始受的是科学的训练,后来却成为社会学家,是否可以请您先谈谈您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激发了您从事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还有,您所受的科学训练与爱丁堡学派的研究路径在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冲突?
巴:因为我是催生爱丁堡学派的人之一,所以我并不需要如此专注于此。于我而言,要与某个自己参与创造出来的理论相契合,不会很困难。
人们猜想科学与相对主义(relativism)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对我来说,相对主义是排在自然主义(naturalism)之后第二顺位的。如果你是受过训练的科学家,你会看见一个可以拿来做实证研究的物质世界。你会把自己看成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与其中的其他东西一样,都是经由同样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你对这个世界会有一元论的看法,会有一种单一的视点。我是在这样的科学态度里受训练的,而这也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坚信且悦纳的观点。我把这种源自我的自然科学训练而来的态度称为“自然主义”,这很像是“科学自然主义运动”(scientific naturalist movement)的那种路径,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在19世纪的欧洲才正要崭露头角而已。
当我涉足社会学的时候,我以为社会学是研究人类行为或社会行为的一种社会科学。不过,社会学有个非常奇异的特点。虽说社会学在某些方面很像自然科学,而且也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认为自然科学标举了一种对多数领域的事物采取实证或客观态度的榜样。不过,即使科学本身明显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社会学却没有用上述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在科学是怎样被研究,以及部落社会、日常活动、政治运动等又是怎样被研究这些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举个明显的例子好了:如果你是位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就会对大家所相信的东西、所认定的世界很感兴趣。在面对这些人的观点与看法时,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这些都是他们出生的那个社会里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多年以前,大约是1960年代末吧,当时的我正要开始从事研究工作,那时已经有一些研究科学的社会学成果了,只是还没有科学文化的意识,认为它的存在也像传统一样是代代相传而来的。第一个让这种观点在西方科学著述中脱颖而出的是托马斯·库恩,库恩当时因为表述了那些现在看来明显已极的观点而蒙受了诸多敌意。
有一点你得记得,我之前是自然科学老师,我一生中肯定教了不下两千位自然科学学生。虽然知识都牵涉到科层制度与权威,但我从未发现自然科学学生会对从老师那儿学来的知识都牵扯着科层制度与权威这件事感到不解。他们听课、读教科书,同时也意识到这些权威性的资源是做研究时不可或缺的。但在四十年前,哲学家与许多社会学家对此抱持着一种相当奇怪的态度。他们认为,那些主张知识是经由“传承”而不单是通过观察后习得的想法是对科学的批评。
我的看法是,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了。如果我们想让人类行为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就得用一以贯之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说,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也必须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与其所研究的对象一样,都是实证的现象。我们应当借鉴社会科学对人类普遍行为的研究,然后将这些推论运用于研究科学家之上。因为科学家也是人啊!让我再强调一次,四十年前这是个惊世骇俗的想法。事实上,现在仍有很多人还未改变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们认为,把科学描绘成人类行为就是对科学的批评。比方说,那种认为科学与社会科学家在其他脉络下所做的人类行为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就被认为是对科学的批评。我想改变这种想法,我想让人类的社会学研究也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成为彻头彻尾自然主义式的。不过,事实证明,这远比我想象的要难办得多。
希望现在你对我所谓的自然主义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它是一种一元论的观点,一种坚决反对二元论的看法,它不容许我们在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做出区分。现在,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可以用“相对主义”这个词来展现自然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用同一种方式,也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当然,这种方法可以运用于科学、数学、社会科学或哲学等上。有些人无法理解这点,而我则无法理解这些人的问题出在哪儿?(大家都笑了)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旦你是个严格的自然主义者,相对主义就会接踵而来。他们难以理解相对主义是自然主义推论下的必然产物,这本就该如此!
你听过庞加莱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吗?当代的数学家试图破解这类著名的难题,好引起大众的关注并藉此宣扬他们的学科。所以四年前当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破解了庞加莱猜想时,引起了好一阵骚动。其实佩雷尔曼最初根本不是研究这个问题,他当时研究的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他根本忽略了庞加莱猜想。之后当他回过头来再看时,才发现他也顺道破解了庞加莱猜想,不过那是个意外的收获。一个本应是第二顺位的成果却变成外界眼中真正的成就了,这当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解开庞加莱猜想的人会获得巨款。
我是以相对主义是自然主义推论下的产物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相对主义的。相对主义是可以被辩护的,因为它隐含了我认为相当重要的自然主义在其中。也就是说,要一贯地将科学或自然主义的方针运用于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上。每当有人对这些观点大惊小怪时,我仍颇感不可思议。
黄:您可以向我们说明一下爱丁堡学派——或是有人称之为强纲领——的历史背景吗?爱丁堡学派与强纲领是一回事儿吗?
巴:我想就实际操作上来看确实是一回事儿。当然啦,你应该去问问使用这个词的人怎么说了。(笑)你知道奎因曾说:单身汉就是还没结婚的人。有时确实是这样的,但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喔。(笑)所以,我怎么能说爱丁堡学派与强纲领永远都是一样的呢?但是不管怎样,对很多人而言,二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黄:大卫·布鲁尔说您倾向于不用“强纲领”这个词,有什么原因吗?
巴:可能确实如此,但这没什么,我想我可能不那么喜欢谈“纲领”吧。不过用这个字是引人注目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卫用了这个字也许是件好事。当初是大卫采用“强纲领”这个词的,也许在当时是个很好的做法。
不过因为想法一直在改变等,后来这个词可能就有些局限了。相比之下,“爱丁堡学派”比较不那么严谨,囊括了环绕同一主题的各路人马。就探讨历史的演进而言,用“爱丁堡学派”一词也许比“强纲领”要好一些……
黄:您刚才说这在“当时”是个好主意,那么请问这些年什么东西改变了呢?
巴:喔!因为做这个议题的人愈来愈多了。刚开始时,只有大卫与我两个人讨论而已。当大卫称其为强纲领时,那是个很不错的主意。现在大家可能都以为当时我们有很多人,但一度(也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几个人闭门讨论而已。现在实在很难说清楚整个情况是如何演变成今天如此奇妙的局面的。如果你去参加像4S(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学社会研究学会)这样大型的研讨会,会有几百人参加呢。
有件事我觉得蛮有趣,1992年我去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任教,我离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转到了普通社会学领域。当时我没怎么去参加研讨会,有好些年我都变得有点脱节了。后来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事情大为改变,听到大家正在谈论“正统派”的缺失,我这才惊觉原来正统派也包括我在内。(笑)他们说我这种正统派的看法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等,无疑地,上个世代的创新到了下个世代就成了教条。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事发生,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大家都想继续前进,而且也真的向前进了。
黄:所以与某些中国学者所说的不同,你到埃克塞特大学不是去为强纲领“布道”的?
巴:不是,刚好相反,我做了些别的事。喔!也不能这样说,让我再回头来把事情说清楚。
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我本来受的是科学训练,是后来才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我渐渐相信社会科学里有好些研究都是不错的——主要是在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我们都还在研习的经济学这块儿,好研究倒不是很多——好的研究应该被拿来用于了解自然科学上。我做的这部分研究算是爱丁堡学派的一部分,我认为做得还可以。我们从研究科学家的所作所为上,学到了很多关于人类行为的事情,研究这些行为是很有趣的。我一直都觉得很惊讶,之前大家从未用我们所用的方法来研究过这些东西。我惊讶的原因在于,从诸多方面来看,这些都是极端的人类行为——极端的行为是很适合拿来研究的。想一想数学家好了,再想想他们有着怎样的文化,那都是些很不寻常的文化。如果你是学文化研究、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学生,你应该会对这些文化感兴趣,因为它是如此非同寻常。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部分研究工作看成是对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大体上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行为。若能把这些东西再带回当初那个启发它的领域,并用以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普遍的问题,我想这会是个很好的主意。所以说,与其像我以前的做法,也就是用一般文化的知识来解释科学文化,现在我想用科学文化的知识来理解一般文化。这里的想法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对科学文化的研究是相当成功的,所以现在可以把这些成果视为可以启发我们对其他文化研究的范例或资源。举例来说,也许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把已经从自然科学家这些身分团体上学到的东西,拿来理解社会上其他各式各样的特殊身分团体。
我认为这就是做社会科学研究时应有的态度——你应该要有个自己很在行的领域,也应该重视那些细节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仔细记载并证实某些特殊案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你也应该要很愿意从中再跳出来,还要有想将这整个领域向前推进的责任感。所以长久以来我一直尝试着在做的事情就是:穿梭于特定的科学社会学问题、普遍的社会学问题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有些人称这些基本的问题为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这是我整个学术生涯中不断尝试的事。
有一位真的把这个拿捏得极好的社会学家就是默顿,他除了对功能社会学理论有莫大的贡献外,终其一生都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你在默顿的研究里可以看到的是,科学社会学家与社会学理论家这两个角色极具研究效率的有益互动,这是一个说明怎样把社会学研究搞好的典范。那些一味搞理论的理论家极易成为堆砌辞藻而冗长乏味的人,这些人别无所谈,尽说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东西。不过,如果你全然囿于狭隘的实证圈,虽然比前一种人好一些,但你就几乎无法得到那些能够有效拓展研究所需的广泛资源的襄助。所以我深信我刚才提及的“穿梭互动”之重要。
1980年代在去埃克塞特大学之前,我早已深入钻研过几个社会学里最普遍的问题,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即是其中之一。经由1970年代所做的研究,我开始逐渐认识到:知识的问题与行动的问题其实是同样的问题。
黄:他们是“同样的问题”?
巴:是同样的,不同的只是我们如何看待而已。换个方式来说,不管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中权力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还是社会中知识的问题,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在那之前,我已经做了哲学家称之为指涉(reference)问题的研究,还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有限论的文章,当时我拓展并详述了人们如何运用语言指涉世上事物的有限论观点。当然,这不是原创的概念,我们可以在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中看到与有限论非常相关的观点。大卫·布鲁尔做了很多研究,都是利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来展开有限论的。美国的民族学方法论者(Ethnomethodologist)及其他学者也用非常类似的立场做了些不错的研究。像以往一样,我尽量将指涉的研究泛化——有限论者并不都是乐意这样做的。但是这又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指涉我们指涉的这个动作。如果对如何指涉事物的问题有大致的了解,总会被迫去处理自我指涉(self-referencing)的问题。在1982年那篇文章之后,我意识到,自我指涉行为的系统存在成了一个亟待探索的重要社会学难题。我当时根本不太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很确定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后来总算写出了一篇文章,即“作为像解靴带式的归纳法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as a Bootstrapped Induction)。这是一篇非常难而且也写得很不好的文章,我对这篇文章的艰涩难懂感到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法儿把它弄得更好了。因为我当时的理解还在发展中,我现在也还未完成概念厘清的工作。我当时虽然知道这些观点的重要,却还是没法儿将其漂亮地表达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奇妙的原因,(笑)文章还是被刊登出来了。在刚登出的前十年里,没有人因为这篇文章感到兴奋或对它有兴趣,就连大卫·布鲁尔也不感兴趣。但到了1990年代,大家开始对它感兴趣了。刚好那时候,我也完成了一本书,即《权力的本质》(The Nature of Power)。这本书把社会描绘成自我指涉的知识系统,比较简明也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与这一概念相关的东西。知识的自我指涉系统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这些系统是那些相信这些知识是正确无误的知识承载者运作而来的。这里的“知识”指的是某些事件的状态,这些状态的建立来自一群相信这些知识是对的、且根据这些知识行动的人。当人们相信这一知识的时候,就创造出了一个让其变得有效的指涉对象(referents)。因为这个被指涉的对象没有指涉到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而是指涉到那个被人们相信的自己身上。通过这种对知识的共享信念,一个集体就可以协调每个独立的行动,而进行共同和集体的行动——这些共同和集体的行动所能达到的成效远比那些没有条理的独立行动要来的多得多。
如果你想谈一个集体能够做到什么,就必须谈这个集体知道什么,但你也就正在说明其“权力”(powers)——知识与权力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大部分的权力从何而来呢?一群人在共同知识、表述、语言、技术、技能、工艺等上面相互协调,因为这远比那些我们称为“个人”的荒谬独立个体所能做的要多上几百万倍。所以,几乎所有内在于集体知识中的权力都来自于组织与共同的文化,而不是来自孤立个体的力量——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存在的。换个角度来看,你只能凭借观察人们对知识的运用,来了解他们的知识是什么。如果忽略了知识的表现,你就无法了解知识,因为知识适用其实就是权力运作的另一种描述。知识系统的问题与研究权力系统的问题,其实都是在谈同样的问题。
黄:我了解集体行动与权力,但我们要怎样把有限论放人你刚才提及的那个体系里呢?
巴:如果你是个有限论者,那么权力就会有些有意思的次要意涵。举例来说,假设你是阶层制(hierarchy)里最上层的人,就说一个官僚体制好了。你知道有些启蒙的幻想吗?让我先快速而夸张地说一下。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力量被认为是从反对宗教天启而开始发展起来的。欧洲的世俗精英都生长于相信理性力量的环境中,像康德就论及很多理性的优越之处。这种想法从何而来?是从欧洲专制制度来的,最主要是从法国和普鲁士来的。除非你重新诠释启蒙的定义,否则英格兰就没有启蒙运动。那里的“解放”(liberation)一词比较多是来自于经验主义,而理性主义反倒是次要的。在欧洲,对从宗教与压迫的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历程而言,经验主义是处于次要角色的,合理性或理性才是首要推手,像这种从宗教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发生在像腓特烈大帝暴君统治的普鲁士。普鲁士的公务机关创建时,是把部分军职阶级的将官转调为文职的角色,军队的阶级孕育了行政管理阶级。当时的想法是,比方说由最高指挥官腓特烈大帝来下命令——这就是刚才所谓的“幻想”——他们幻想说,这道命令会下达到制度里那个必须听命行事的人身上去,然后这个终端的执行者会去拉腓特烈大帝要他拉的那根操纵杆。这里的想法是:命令的意义可以毫无改变地传达下去,因为命令的意义就内存于该指令中。这个指令本身既传递着指挥官对受命者的意图,也传递着指挥官下令时所必须具备的可靠权力运用在其中。
你可以看到有限论对此的不同看法。有限论认为,任何一道命令都必须通过类推受令者当时所处的特定情境来理解,而你延伸这类比的方法不会被这个命令本身所决定。基本上,命令里并没有固定的“不变意义”(fixed meaning),不管你是口头宣召,还是将命令书面传达下去。
即使召令里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事情还是在召令的另一端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呢?有限论者认为,这里有个无法根除的问题,即欠缺联结与控制的问题——你永远不可能把命令订得精准到可以完全具体地告诉受令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可以整本书来尽可能精细地描述你的命令,但还是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给自己带来愈来愈多语言上的麻烦罢了。顺道提一下,有个学者——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对此颇有研究,其《民俗学方法论研究》(Studies in Ethnornethodology)是社会学有限论的圣经,就像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是哲学有限论的圣经一样。所以就是说,在任何权力的授权系统中,都会有控制的问题。你不能假设腓特烈大帝一定“有”所有的权力,然后说他的部属都只是他权力的展现而已。从头至尾,在阶层制环环相扣下的每个环节都有这个问题。
很巧地,当我正在撰写并思索这个主题的时候,经济学家也恰好开始思索这件事。虽然他们当时也想了个很类似的解决办法,但是他们一定有什么东西打从一开始就出错了。(笑)经济学上有一个“委托—代理人理论”。“委托—代理人理论”对授权问题的看法与我在1988年出版的《权力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的看法是很接近的。但我认为经济学家不像我这样的“纯”,所以他们没将其看成是根本的问题。虽然他们确实已经知道,当委托人试图掌控本该代表他来行动的代理人时,就会出问题。
甚至还有更巧的呢!注意“代理人”(agent)这个字的含义,是指代表委托人行事的人,就像是替你做生意或是替你签约的代理人一样。比较一下近来英国社会学界如何使用“行动者”(agent)与“行动”(ageney)这两个字——他们与传统上所谓的代理人也就是代表委托人行事的想法恰恰相反。你应该洞悉到为什么当代社会学会觉得要正确理解“代理”这个概念是如此困难了。
不管怎样,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明白,意识到有限论的观点以后,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研究权力:有限论问题化了如何将作为一种指示的命令从科层体制里传递下去的过程。那些认为科层体制像个大机器一样,从顶端发号施令,指令就会自动且可靠地在体制下层转换成该命令所“蕴含”的动作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所有有限论者所谓关于拓展科学知识的看法,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在讨论如何在权力的科层体制脉络中下达指令的问题,这两种潜在的难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你现在知道他们与有限论的相关性了吧。
让我再回到刚才提到的权力与自我指涉的知识系统上。如果你去看一个指涉的动作,我会说在这些动作的另一端,会有个东西在那儿,即所谓的指涉物——被指涉的东西。所以如果我跟你说:“把笔递给她。”(巴恩斯教授指着桌上的一支笔)在我说完这句话后,你会看到有个东西在那儿——一个你可以伸手去拿的东西,一个我话中的指涉物或是某些人所谓的言辞行动(speech act)。这个概念不难,就是说,东西真的在那儿,然后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指向那些东西。也许这是因为我受过化学系的训练,那是科学里感觉最真实的科目,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些摸得着的实际事物上。不管怎样,我跟大部分人一样,是自然实在论者(natural realist)。当我说“这支笔”,然后挥手示意,我就假定这支笔就是我要说的东西,这就是我话中的实际指涉物。不过,当我说腓特烈大帝的权力如何时,这里的指涉物是什么?什么构成了这儿我所谓的权力?它在现实世界中是怎样存在的?一般共通的想法是,他所拥有的权力就在构成这些权力的东西里。更普通的说法是,当所有人都相信你有权力的时候,你就有权力;当大家都认为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构成腓特烈大帝权力的知识自我指涉系统是怎样环绕在他的周围了。因为人们相信他是很有权力的,所以才顺从他;又因为人们都顺从他,所以也就相信他是有权力的了一当然,这里我过度简化了很多东西。
同样的,钱之所以为钱,也只有在钱被认为是钱且钱可以发挥其钱的功能时,钱才是钱——这是从相信钱是钱的信念中来的。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理解自我指涉的循环机制有如此大的实际重要性了。如果这种循环缺失了一角,也就是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像货币、财产权、价格等“经济”体(“economic” entities)是那般管用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是我们之前相信的那些东西了。因为这些东西是什么,全凭我们相信他们是什么而定。把这些想法继续向前拓展的是唐纳德·麦肯齐,他对选择权市场与选择权定价做了很多漂亮的研究。看到这些重要的东西有人研究,令我非常高兴。
黄:之前我们访问了大卫·布鲁尔,也同他谈了有限论的问题,今天您又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有限论的历史诠释。虽然我无法具体指出您对有限论的理解与大卫的有何不同,但我认为您与大卫的诠释是有些不一样的,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的误解而已。因为您与大卫很熟,请问当您在谈有限论时,您认为您所说的与大卫所说的是一样的吗?
巴: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话里有些语病:什么是“一样”?(笑)对这其中的任何一点,我都不认为大卫与我有什么根本的歧异。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无法一直用说的方式来解释有限论。以实在论者的角度而言,这有一部分是沟通的问题,但在大部分情形下,这也意味着我们简化或忽略了有限论的观点——也许大卫和我有时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简化它。
就像维特根斯坦在《论数学的根基》(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里所做的一样,严格的有限论可以激发你去质疑2加2是否或是为什么等于4,甚至说1是不是或为什么等于1。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把每件事都想成有问题的,结果你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如果你真的说了什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启了无止境的思索——你会思索这些词的意义,想着这些句子可能的声称意涵,及各种无止境被误解的方式。当然了,在实践上,我们把每个人习惯或惯性地接受“2+2=4”这件事,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譬如说,当我们说话时,我们会仰赖听众的习惯与习性。大卫和我试着向有着不同习惯与习性的人说明有限论,也许这就说明了我们表述有限论时的不同之处。大卫比我更常面对哲学家的听众,而我也许在表述有限论时比他更随性一点。我也不知道是否如此。
有本大卫也曾善用过的好书《证明与反驳》(Proofs and Refutations)就是在谈这个,那本书是关于数学证明和如何把既有证明与新事例相联结的问题。比方说,当一个新例子出现时,我们就要决定这个新例子是否已经构成了某个证明的否证;或是说,视之为与原证明相容,只要我们可以稍微以不同于既有习惯的方法来理解这个原有证明的话。这是本引人入胜的书,漂亮地描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有限论议题。
黄:可以谈谈您最近的作品吗?听说您在研究基因和基因技术,您是怎么把刚刚提到的理论运用于这个特定的基因研究上的呢?
巴:随着现代基因组学的兴起,这当中有件令人感到惊异的事就是:大家开始用全然不同的角度,以一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角度,来看遗传学的历史。结果整个基因的概念都被质疑了,如果现在要为此提出个不光是哲学上的、甚至是实际上全然合理的说法,我会说根本没有基因这样的东西。当然啦,如果你想把现行很多教科书的定义当真的话,就现有的知识而言,没有哪个东西可以完全无误地符合这些定义。虽然说继续用“基因”这个字仍然有不少实用上的功效,但这也是因状况而异的。所以,最好是将其想成是一种有用的虚构物,这个虚构物不能指涉到任何“真正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因为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谈“基因”已经开始没什么用了,或者应该说它事实上造成了很严重的误导。
遗传学的历史已经被漂亮地改写了,罗伯特·科勒的《蝇王:果蝇遗传学和实验的生命》(Lords of the Fly:Drosophila Genetics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一书就是一例。果蝇的研究被拿来作为证实孟德尔遗传学(Mendelism)的证据,科勒的书让我们看到,要培育出符合孟德尔定律的果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符合这定律的果蝇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会被珍藏起来,但不符规律的那些就会被抛弃。也就是说,与其说是果蝇验证了定律,倒不如说是现有的理论形塑了果蝇。当然,当初的目的是要促进研究的进行。即便如此,就当作是种后见之明好了——孟德尔遗传学之所以被接受,部分的原因是靠创造符合这一理论以及摧毁那些与理论不符的现象来的。
那故事的细节很是迷人。当时有个叫布里奇斯(Bridges)的人负责照顾果蝇,他知道哪些是好的果蝇,知道他们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他也知道怎么保护这些果蝇,更记录下果蝇培育的过程——所有这些都成了支撑孟德尔果蝇遗传学的基础——布里奇斯其实才是整个研究的关键,但大家总是忘记有这个人。在这本书中,你就会看到他的重要。他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而且总是惹来麻烦,他就职的大学和学校高层有时会因为他夸张的行径而想解雇他。不知道他如果到中国去,会不会过得比较好?(笑)嗯!也许他在中国会混得下去。但是实验室的负责人摩根就得看紧他,他后来没被炒鱿鱼,想必是因为领导说了诸如“不管他做了什么,我就是要这个人!”之类的话吧。
我最近很凑巧地踏入了这个领域,同时又很奇妙的,这个领域也刚好总括了我早期的研究兴趣。在我开始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工作后,我跟一位在西部综合医院(Western General Hospital)遗传学研究部的女士结了婚。当时她正在做有关人类性染色体(human sex chromosomes)的研究,然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时,我对遗传学极感兴趣。当然啦,当时有关IQ研究的詹森(Jensen)事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社会学家与遗传学家有着诸多激辩,但要是他们能够更仔细地阅读对方作品的话,就可以让辩论变得更其精彩,这当中有很多争辩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做秀而已。
撇开那些不谈,我当时就对遗传学以及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很感兴趣。回头看看自己年轻时花了很多时间的东西,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验。我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看见了其中的改变,然后再来观察现在的遗传学研究。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是受过化学训练的人,不是生物学家。但这个背景是很好的,有助于我了解基因体学与分子遗传学。即使这样的背景不比生物科学的背景来得好,但也差不多是一样好了。因为即使我对某些领域有些生疏,但这些领域对传统的生物学家而言,也同样是陌生的。
现在正好快到我“法定”研究生涯的终点了,我也正想着要退休。我之前写了一本关于“行动”的书,还不错,包括了一些基础的社会学理论。那本书之后,我就想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后来我去申请了基因体学的研究计划,2002年通过了。所以,这还算是个蛮自然的过程。我从一般性的理论又回到科学研究上,这样的推移是我迄今为止都还喜欢的。当然,我现在只工作半天了,不过这却是种很棒的转变。因为我许久以前所了解的生物科学已经以颇令人振奋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虽然以前很难让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但现在情形已然非常不同了。除了人们倾向帮自己取个新称号,称自己为“STS学者”什么的之外,也许真正的原因是,有些社会学家还保有一些对待科学的特定态度:他们认为科学不应该在自己的兴趣之列。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对自然科学研究似乎不怎么感兴趣,我也不明就里,因为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对科学的“社会学”兴趣一直很浓厚。
黄:科学研究部有些人很担忧,也许还称不上担忧,应该说他们在思索爱丁堡学派接下来的十年要往哪个方向走?要如何达到目标?您对此有怎样的建议或意见?
巴:我看到很多人做了一些不错的研究。有一年我回这儿来审查博士论文的时候,你在这儿吗?审唐娜(Donna Messner)的博士论文时,你在吗?她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管制领域中药物开发的问题,我认为那是个把有限论运用得非常好的研究。她的研究展现出,不论哪一年,政府管制机构的正式规定与指导方针都倾向于将前一年的成果描述得比当时正在做的要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倾向于先去改变他们当时正在做的事,然后再将当时做的事合理化。就像是一种重新诠释既有规定的权宜之计,只有这样,才能把既有的规则变成一个较自然且明显符合改变后的实践的新规则。所以如果你懂我在说什么的话,就会知道:实践先行,规则跟着实践跑,而解释又跟在后头。她的博士论文用一件接一件的案例,细腻地把上面的现象谈得非常清楚。她不是信笔胡诌而已,她引了相关研究,举了访谈资料,也列了法律规定。那本论文给了我们清晰的描述,告诉我们政府管制机关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似乎是西方学界越来越感兴趣的内容。无疑地,欧盟非常着迷于管制,很多美国人也对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规范错综复杂的高科技进程感兴趣。与加萨诺夫一起研究的人就做了许多像这样的不错研究,世界贸易组织里有一整群人在做这个主题,欧洲的机构也有人在研究这些议题。所以说,这个主题的研究明显地已经有不少“里程碑”(mileage)——我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应该还OK吧,也许在中国你们说“公里碑”(kilometre-age)。总而言之,这是个可以拿到很多研究经费的重要领域,但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很多人仍对它存有误解——他们认为,规则一定有个内化于其中的明确意涵;若是能钻研这个意涵,就可以提出些不同的观点。
当然啦,法律研究也是个不错的领域。律师们很有趣,他们既意识到却又没真的意识到有限论所说的规则。正因为他们是律师,所以他们总是在改写或扭曲法律来迎合他们想主张的案件。所以说,没有人比律师更懂有限论的精髓,知道怎样在形式上操弄法律来达到想要的东西。但律师们不喜欢谈这个,他们喜欢把自己包装成是在提出折服人的论辩,然后说自己的任务是要维系法治(rule of law)——不是一般所说的人治,而是法治——所以,律师早就在实行有限论了。当然,在法律这个领域里,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应用有限论的观点。林奇(Mike Lynch)与其同事有本关于DNA指纹的书,与此有些关联。
同样的,我们也有数不尽的机会可以做官僚行政的有限论研究,这当中包括了研究的行政与科学实验室的行政问题。在拙著《权力的实质》讲官僚体制的那章,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线索。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书了,所以你不能期待太多。(笑)不过,书中有好些观点还是没被采纳。此外,该书也有一些有关哈贝马斯的讨论。
在基因组学的领域,有很多关于管制问题的有趣例子。比方说,像干细胞管制的问题若是采取有限论观点的话,就会很令人惊艳。再说一次,由于干细胞是会变且多变的,所以科学家也非常清楚,对于不同种类的干细胞,无法订出一套固定的规则来规范。由此,在要求明确分类的司法专业与不理会这些而自己变来变去的干细胞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当然,类似的冲突也围绕在高度“政治化”的胚胎上,而来自宗教团体的意见更增添了这项争辩的复杂性。
贝克(Ulrick Beck)有这么个论点,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纪,搞政治就像在搞科学一样,而我们以前所谓的政治变成了媒体上娱乐大众的喜剧。贝克想隐射的是:那些专业政治家对如何辨识和定义一些重大议题都力不从心,这些重大议题是在实验室或是在管制机关里决定的。虽说他当时使用的辞藻稍嫌夸饰,但这个论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确实如此,当你在看科学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看政治,虽然那并不代表你没有在看真正的科学。
黄:我们决定在访谈最后,要问每位受访者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在中国,科技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都在蓬勃发展中,请问您对这些新进成员或新加入的国家有怎样的建议呢?
巴:嗯,我对你们的传统了解得不够多,但我们的传统不可能一模一样。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是:社会学在英国是属于一种理性的传统。即便是现在,社会学还是有一种倾向,即太柏拉图化(Platonise)及太想要具体化(reify)。在你们的传统里,可能比较容易用像辩证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每个东西都处于变化之中。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对于融西方资源于当地传统这件事,你们都不必太过忧心。除此之外,我实在很难再说些什么了。因为你们才是最知道该怎么做的人,而不是我。(笑)你们知道自己具备哪些资源,哪些我们的资源最能与你们自己的东西相契合。我从自然科学进入社会学,当时感觉除了社会科学的资源之外,自然科学这个背景是我唯一可用的资源了。你们的资源就是那些丰富且又令人慑服的传统,所以我不相信你们的文化里没有极为有趣的观点。就某些方面来看,西方就显得相形失色了——因为你们对我们的了解渐渐透彻,我们对了解中国文化所应该做的努力却还不够。以前我在读科学社会学时,看的第一批东西包括了李约瑟的著述。他的著作非常推崇中国科学史,他还将科学史及其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结构与生产方式相联结。但也不知何故,我当时没有再多读这方面的历史。当然,李约瑟是1950年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但后来大量丰富的想法与题材却被集体冷落了。像过去这样有害于社会学史与科学历史社会学的事是不该发生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这些也释怀了,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把广博的自然主义研究路径带入他们的科学研究中去了。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在柏林举办的分子生物学史研讨会,许多那个领域的著名科学家都参加了。他们说这个领域现在已经衰亡了,再也没人会讨论分子生物学了,这领域就这样不见了。但他们却为此雀跃,甚至说:你知道吗,仔细想想,其实这个领域反正从来也没有真地存在过。(笑)除了写计划申请书之外,我们并不会称自己是分子生物学家。听他们这样说,我心里就想:如果一群社会学家聚在一起讨论这样的历史问题,应该不会是这么个谈法。他们应该或说他们绝对会谈社会学的危机,也会讨论该如何做才能防止社会学的消失。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些分子生物学家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着深刻的体会,知道自己的研究影响周边相关科学的程度有多深,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已经被运用于有着其他各式各样称号的领域里去了。他们可以随意往其他领域看去,然后看见自己的研究对现在科学的实践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研究要叫什么,或这个研究以后会怎样被记住。事实上,社会学家也做了大量极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就缺乏这种身分上的安全感。社会学家完成的重要工作不仅限于科学,也旁及其他领域。这些成果现在被向前拓展,也被运用到许多不同的领域和脉络下,只是他们没有被冠上社会学成果,而是被叫成其他名字而已。社会学家应该试着多对自己所做的研究感到自豪,也要对不被认同这种事采取更轻松的态度才好。
就拿强纲领来说好了,不管作为一个名称、一个招牌,还是什么的,强纲领继不继续得下去都没什么关系。它那些可作为经典成果的东西早已被采纳,也被运用到其他领域上了,在历史领域或许尤其如此。强纲领的自然主义研究路径体现在很多实例中,且一直以来都对其他领域颇有助益。
终于,我要回答你的问题了。不要去问你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科技与社会研究里可以做些什么,也不要去问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应用到中国或东亚去。直接去看那些特定的研究,然后问:哪些可以拿来当成模型,哪些可以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经典成果,哪些又是在修改后就可以帮助你研究的东西。假使有哪个模型在某个应用上让你惊艳,就假设它可以用于你自己的研究脉络里。模型本身不会说话,它无法告诉你它合不合用,也无法告诉你它是限定的还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就放手去用吧,这样才知道到底合不合用。当你为了要它管用而用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发现自己在改造它。如果你慎选的话,它一定在某些地方是合用的。在运用的过程中,你既要依循惯例,又要原创;既要保守,又要创新。换个角度看,不要想找个理论来追随,也不要找哪个论点来局囿自己的视野。你应当去寻找可用的资源,以类比的方式把经典的研究成果拓展到其他例子上,创造出有意思的研究。对自己说:这是个好研究,它是如此之好,所以一定可以用某种方式用到别处去才是——就是要这么想才行。去寻找可以运用到你研究上的资源,找到你感兴趣的领域,把名号这件事置于第二顺位——不管你成为“北京学派”或其他什么学派,这些一点儿都不重要。
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经典就是唐纳德·麦肯齐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他的研究把经济活动看成是自我指涉的系统。我认为现在经济学还有好大一部分研究等着与“强纲领”相联结,我想你(巴恩斯看着方芗)一定有个可以让这些东西变得特别有趣的背景吧!
方:是啊。我就是来自那糟透了的经济学背景。(笑)
巴:大体上而言,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你们能用的、对你们而言有价值的东西。但必须仔细地评估,然后鼓起勇气决定要用它来做什么,这些东西上是不会有标识来告诉你的。
黄:非常感谢您!
巴:抱歉,我还没问你的背景呢。
黄:(笑)我是专门扭曲规则的人:法律。(齐声大笑)
巴:嗯,非常的有限论。
注释:
①本访谈录首刊于台湾《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1期第339-374页,其英文版Dropping the Brand of Edinburgh School:An Interview with Barry Barnes刊于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0年第4期第601-6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