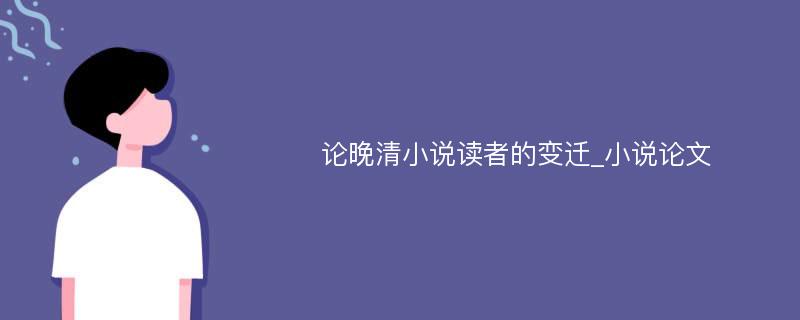
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试论论文,读者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崛起联在一起,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设,到底是怎样联系的,还是有许多个体情况需要论证。城市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市民的存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通俗小说却似乎要到唐代以至北宋方才崛起。中国古代的长安、汴梁、临安、北京都有百万人口,市民不可谓不多,话本白话小说也问世了,但它们的数量、传播过程,市场情况,与当时市民的关系,因为缺乏资料,至今还没有说明白,也就留下许多问题。
古代的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由于缺乏资料,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近代以来的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关系,表面看来是已经解决了:近代的都市化产生大量的市民,市民读者的大量增加是通俗小说崛起的原因。这一结论假如细究起来也有许多问题,其间的因素其实是复杂的。
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从一个小县城变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它又是中国通俗小说出版的最重要基地,它的都市化过程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典型。上海是1843年开埠的,1843年开辟英租界,1848年开辟美租界,1849年开辟法租界,这些租界当时都是农田,从农田到都市是要有个过程的,一直到1853年英租界还只有500人。 (注:上海旧县志与朗格的《上海社会概况》都是这个数字。)同时期的华界人口则有54万多人。此后,华界人口增长不快,一直到1910年只有67万多人,而租界人口则很快地上升,1865年英美的公共租界已有9万多人,法租界也有5万多人,到189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是24万多,法租界是5万多。这时的上海租界,不算华界,也已拥有30 万人口,加上华界,则有80多万人口。到1900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增加到35万多,增加了近11万,法租界也增加到9万多,增加了4万。租界人口合起来有44万多,加上华界要达到100万。 (注:本文关于上海的人口统计俱根据邹依仁《旧上海的人口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其间人口在逐步增长,上海的通俗小说的数量增长,则似乎也在缓慢发展。这时的小说以狭邪小说为主,因为这时的租界男女之间的比例最初大约是3∶1,到1895年则为2.5∶1,到1900年至1910年则不到2∶1。性别比例的失调,促使妓院畸形发展,也促使“狭邪小说”不断问世。但是,实际上早期狭邪小说大多出在上海外的地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上海的狭邪小说较著名的有《绘芳录》、《海上尘天影》、《海上花列传》等不多几部,后来比较畅销的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都问世于1900年之后。这样看来,上海狭邪小说的繁荣,反倒是在上海性别比例失调下降到不到2∶1的时候。1900年以前上海出版的通俗小说数量并不多,1892年问世的小说杂志《海上奇书》也只维持了一年就停刊了。上海通俗小说的发展,似乎有一个滞后的情况。
进入二十世纪后,尤其是在“小说界革命”后,上海的小说种数如洪水一般增长,晚清的小说数量激增,其中大部分都出版于上海,而且都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晚清最著名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除了《新小说》第一年在日本编辑,在上海发行,其他杂志都在上海编辑发行,《新小说》第二年也转移到上海编辑发行。期间上海的人口数量有所增长,公共租界的人口在1905年是46万多,法租界仍是9万,还略有下降;1910 年公共租界增加到50万人,法租界也增加到11万多人,加上华界增加到67万多人,合起来大约130万。也就是说上海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而小说数量却是成几倍几十倍增长。倘若按比例计算,这十年间的人口增长比例并不比前十年高,但是小说种数的增长却是前十年无法相比的。
按理说,小说数量激增意味着小说市场的急剧扩大,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小说增长的速度又是不成比例的。显然,小说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数的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内部,扩大了小说市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从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士大夫原来是鄙视小说的,现在受“小说界革命”影响,重视小说了,成为小说的读者与作者。这种情况虽然缺乏具体的数字统计,但在当时人的评论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如钟骏文就指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注:钟骏文《小说闲评叙》,《游戏世界》第一期。)老棣看到:“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注: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载《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六期。)黄人在1907年也提出:士大夫“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注: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期。)他们都说出了士大夫对小说态度的变化,士大夫以前是不读小说,或者是很少读小说的,现在则形成了读小说的风气。士大夫本来是小说的潜在市场,他们有文化,有闲暇,有购买力,一旦形成读小说的风气,自然急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从1900年到1912年,又是士大夫大批移居上海的时期,先是庚子事变,后是辛亥革命,上海的租界成为士大夫避难的庇护所,从而也扩大了小说市场。到1908年,据徐念慈估计:“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注:徐念慈曾写过《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载《小说林》第九期。)徐念慈很注意小说市场的情况,专门做过调查。(注:觉我《余之小说观》,载《小说林》第十期。)他的估计应该还是较有说服力的。当时小说读者中士大夫与市民的比例即使不到十比一,但士大夫读者占了多数,那是毫无疑问的。
士大夫原来就阅读文言小说的,事实上,文言小说原来就进入士大夫的阅读视野,连乾隆时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将文言小说列入目录之中。士大夫原来拒绝参与阅读的,主要是白话小说,也就是通俗小说。(当然并不排斥士大夫私下阅读,在笔记里发表评论,有的士大夫如金圣叹还高度赞扬白话小说)通俗小说原来主要是由市民阅读的,“市民”不包括士大夫。如我们在探讨古代的“市民意识”时,往往将将其与士大夫意识对立。但是晚清不同了,士大夫既然阅读了小说,“市民”也就包括了士大夫。这就形成新市民——“公众”。原来,“市民”是低于士大夫的,随着科举废除,士大夫消亡,“市民”包括了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小说数量激增是“市民”急剧膨胀造成的,大量士大夫进入了“市民”的队伍。此时不是没有对小说的鄙视,如章太炎评价他的老师俞樾:“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注: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第2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流露出对小说的鄙视。但是他又为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作序,称赞演义“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注:《洪秀全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他还是认为小说应该是给里巷百姓读的。甚至连提倡小说的夏曾佑也认为是给普通百姓看,士大夫不必看。(注:参阅夏曾佑《小说原理》,载《绣像小说》第三期,1903年出版。)梁启超在1915年惊叹:“举国士大夫不悦学之结果,《三传》束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注:梁启超《告小说家》,载《中华小说界》二卷一号,1915年出版。)很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士大夫事实上违背了“小说界革命”倡导者的心愿,加入了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小说也不顾某些士大夫的鄙视,进入了文学。小说一旦进入了文学,就逐渐取代诗文,居于文学的的中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因此,从晚清开始,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受到文学的排斥。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小说,已经代表了当时的文学。
梁启超於1902年在日本发起“小说界革命”,似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包天笑后来回忆:当时的小说杂志都是模仿《新小说》的,确实是《新小说》登高一呼,群山响应。(注:参阅包天笑《钗影楼回忆录》。)其效果连梁启超自己后来都深感惊讶。尤其是这场小说运动最初是以“政治小说”来发动的,它为什么能吸引众多士大夫和市民呢?
对于士大夫来说,这是稍微简单的问题。1902年是“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亡国危机已经是迫在眉睫。士大夫本身负有救国的使命,自然要寻找救国的方略。现在“戊戌变法”的宣传家主张“小说”是救国的利器,并且能说出一大通道理,符合士大夫对文学的理解,自然容易接受。(注:参阅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但对市民来说,应当是另有原因了。有一件事或许不是偶然: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也是在1902年成立的,名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后来演变为“上海总商会”。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这样的商会团体表明了商人祈求自治的愿望。1905年,上海市民为了抗议美国迫害华工,举行了抵制美货运动,这次运动扩大到全国。从1902年到1905年,上海的先进士大夫如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曾多次在张园演讲,宣传政治主张,有不少市民去听演讲。这意味着这一阶段,正是上海市民政治热情极为高涨的时期。按照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市民应当是在政治上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自由,形成“公共领域”。上海的市民当然还没有达到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但是这一阶段,无疑是上海市民争取独立自由,获得“公共领域”的时候。市民的需求与士大夫是一致的。所以包天笑自己认为:“我之对于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后,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翻译,后来也有创作了。”(注:参阅包天笑《钗影楼回忆录》。)这“时代需求甚殷”,说出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也包括了市民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使得以“政治小说”为本位的“小说革命”成为一场应者云集的小说运动。
晚清大批士大夫阅读通俗小说帮助通俗小说崛起,却混淆了原先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在中国古代,这条界限原本是十分分明的。士大夫创作的阅读的文言文学是文学,非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化名创作的小说戏曲是“小道”,不是文学。现在小说戏曲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就没有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从晚清到民初,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界限也就复杂化了。同一位作家,既创作纯文学,又创作通俗文学,如李伯元。同一位编辑,可以既编纯文学的报刊,又编通俗文学的报刊,如吴双热。同一本杂志可以既有典雅的纯文学专栏,又有弹词等通俗文学的专栏,如《绣像小说》。或者既有古文骈文的文言小说,又有白话小说,如民初的许多小说杂志。这种状况以往以后是个别的现象,在清末民初则很多。它显示的,便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界限的不明确。这种不明确又与士大夫进入市民,出现了价值观念的混同,是连在一起的。
然而,士大夫大量加入通俗小说的读者作者队伍,必然要将他们的修养、兴趣、价值观念、语言带入通俗小说,这就导致通俗小说改变了面貌。小说的题材、思想、形式、语言,以及看小说的眼光,都有很大的改变,造成雅俗合流。原来面向市民的小说是以娱乐性为主,晚清的“谴责小说”却将小说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不过在“连篇话柄”之中保持了客观存在的娱乐性。原来小说大多不触及政治题材,即使触及也只是把它当作野史。晚清的政治小说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理想社会。原来小说中的思想以民间的百姓价值观念为主。晚清的小说却是知识分子化了,小说中出现大量自由民主的新思想、许多改变中国社会的构想,以及对落后中国社会的批判。原来,小说就是通俗的,尤其是白话小说,表现了与士大夫不同的市民社会心态与价值观念;晚清,小说表现的实际上是市民意识与士大夫意识的结合。例如:当《官场现形记》写“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注:《官场现形记》第六十回。)时,这很可能代表了当时市民与士大夫的共识。第五十四回写冯彝斋评论六合知县梅飏仁设立保商局之举道:“照着今日此举,极应仿照外国下议院的章程,无论大小事务,或是或否,总得议决于合邑商民,其权在下而不在上。如谓有了这个地方,专为老公祖聚敛张本,无论为公为私,总不脱专制政体。”这更是既体现了当时先进士大夫的思想,也符合商民的利益。这二者的结合,使得小说面向“公众”。
通俗小说在士大夫进入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语言。而语言的变化,实际也显示了士大夫的欣赏趣味。这时的翻译小说大部分用文言翻译,出现了林纾这样不懂外语全凭古文做得好而成为优秀翻译家的人。徐念慈曾经分析:“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注:觉我《余之小说观》,载《小说林》第十期。)就连当时的白话小说,也有许多趋向文言,成为类似于《三国演义》式的半文言小说。此时的白话小说,普遍的倾向是文言成分加重。这既由于小说作者大部分是士大夫,也由于小说市场上士大夫占了主要的份额,作家不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尽管清政府先是在科举考试上变八股为策论,其后又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士大夫已经断了根。但由于新开之学堂学的课程中,经学仍占较大比重,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以前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加上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进入小说作者读者队伍,文言小说在民国初年反倒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相比白话小说而言并不算发达,如果剔除那些笔记,只以虚构的故事来算,数量远不能与白话小说相比,而且很少有长篇小说。林纾在晚清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为文言小说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民国初年,文言长篇小说异军突起,又出现了一批骈文小说。何诹的《碎琴楼》,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势的《孽冤镜》等,都是当时极为畅销的著名作品。其中《玉梨魂》到二十年代就印了二十多版,还不算盗版印的。作者徐枕亚凭稿费自己开了一家出版社,起名叫清华书局。他的续弦刘沅颖是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女儿,也是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因崇拜他写的《玉梨魂》、《泣珠词》而嫁给他。由此可见当时文言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民初最著名的白话长篇小说《广陵潮》与《留东外史》都遭遇过退稿的命运。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远远不如文言小说。
民初文言长篇小说的流行为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以往我们一直认为:鸳鸯蝴蝶派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它的崛起与上海近代都市的崛起是分不开的,市民是它的主要读者。我们认定的通俗文学应当是语言通俗,它的读者主要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它缺乏超前意识,思想上与俗众同步,因此它在文学上缺乏新的探索,不能领导整个社会的文学发展。但是,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适应民初的文坛。
首先,作为通俗小说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语言必须通俗。很难想象语言不通俗的小说,也能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所接受。古文和骈文用的显然不是通俗的语言,尽管文言长篇小说所用的古文与骈文已经不是古代的古文与骈文,它们为了适应小说的需要,已经出现了“俗化”,如古文、骈文的用典大大减少了,但是,它毕竟还是典雅的文言,并不适应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它比起古化的白话章回小说,显然要艰深很多。因此,民初文言小说的读者并不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
其次,民初小说并不缺乏超前意识,它只是缺乏五四时期才有的思想解放意识。确定超前意识的依据,是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而不是它比后人少什么。民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许多突破。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是最早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恋爱的和尚可亲可敬,富于人情味,其恋爱还不止一次。它写出了和尚在感情与戒律之间的徘徊矛盾,显然具有超前意识。徐枕亚《玉梨魂》是最早描写“寡妇恋爱”的小说,恋爱的寡妇与追求寡妇的青年在小说中都是值得赞颂的正面人物,他们处在“情”与“礼”的冲突中难以自拔,只能以悲剧结局。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令人同情、为之洒泪的恋爱的寡妇,其超前意识也是显然的。更不用说像《孽冤镜》对包办婚姻的抨击,对家长制的控拆了。诚然,民初小说有着维护旧道德的一面,不敢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但是,在这些作品问世时,陈独秀、鲁迅、胡适都还没有说出“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口号,我们怎么能要求这些作家超越历史呢?
第三,民初小说家对小说的艺术也曾经做过不少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小说的描写引向人物内心世界。晚清的言情小说《禽海石》、《恨海》已经敢于描写悲剧,不再是大团圆的结局,造成悲剧的原因,是社会环境。民初的言情小说也写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人物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他们对礼教的崇敬和他们对不被礼教容忍的爱情的执着,构成了他们的内心冲突。为了表现这一冲突,他们引进了当时还只有外国小说才有的“日记体”与“书信体”。他们大量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运用第三人称限制叙述,以特定的视角,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在民初才第一次出现长篇日记体小说,专门的书信体小说。这些艺术探索都为五四新文学的问世作了铺垫。因此,今天讲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离不开讲民初小说,它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民初作家也与一般通俗小说家不同,他们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创作典雅的诗文。这些典雅的诗文也在他们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南社”成员,这意味着他们被当时纯文学界所接受。徐枕亚的骈文得到当时著名诗文家樊增祥的欣赏,他的第二次婚姻还是樊增祥帮忙,才获得成功。民初小说家不像一般通俗小说家那样懒于探索,他们乐于在小说形式上创新。他们主编的小说杂志,有时专门标出“新体小说”一栏,刊载探索小说。他们还喜欢模仿外国小说,吸收外国小说的形式技巧。托尔斯泰的《复活》翻译出版后,包天笑马上模仿《复活》的故事梗概,创作了小说《补过》,表现出很大的吸收外来影响的兴趣。因此,他们此时的表现,更像纯文学作家,而不像通俗文学作家。这些作家也领导了当时的文坛,就连鲁迅、刘半农、周作人、叶圣陶等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当时小说杂志上发表作品,用的也是文言,其风格与他们在五四后发表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而与民初小说的风格,却有许多切近的地方。作家毕竟不能超越历史,新文学作家也不例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说它的某些文学作品是通俗文学,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出现的同时,另有一些纯文学的作品。由此形成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并立。但在民初不然,民初小说就代表了当时文坛的水平,没有另外的纯文学与之对立。民初小说家的创作探索,就代表了当时小说的水平,他们为文学的发展,也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把民初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民初的文坛上就没有另外的纯文学小说。贬低民初小说,也就贬低民初对文学作出的贡献。因此,对民初小说,似乎不应完全作为通俗小说来看,这样会贬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民初小说的承担者,鸳鸯蝴蝶派不完全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至少在民国初年,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小说的水平。
于是,中国市民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也就显示出来。表面看来,它随着都市崛起而崛起,随着都市发展而发展;但是,在晚清它经历了一个急剧膨胀的过程。大批士大夫介入小说,成为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后,市民小说也就“雅化”了。民初小说是这一“雅化”的典型。一般说来,市民小说很难达到当时纯文学的水平,民初小说借助于雅俗的合流,却达到了这个水平。但是,中国文化正处在新旧嬗变的转折期。由士大夫与市民融合而成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渐渐不适应纯文学的发展需要。士大夫几乎是一进入小说就断根了,士大夫的断根,使得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弱。加上鸳鸯蝴蝶派受市民社会的影响,一直有种“媚俗”的倾向,自己也处在困境之中。(注:参阅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于是,“文化激进主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治了文坛,文化改良主义的鸳鸯蝴蝶派则成为一个通俗文学流派。
1912年教育部通令在小学“废止读经”,改变了清末学堂的课程设置,也在营造五四新文学的社会基础。1917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正是这一批学生开始走上社会之时。随着新的学生不断毕业,新文学的社会基础也就越来越雄厚。其实,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与新文学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如提倡白话文,如吸收外国小说影响等等。当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后,取代了鸳鸯蝴蝶派在文坛上的地位,鸳鸯蝴蝶派才完全转入了通俗文学。此时中国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又再次分明起来。在二十年代,新文学作家决不会写章回小说,鸳鸯蝴蝶派也很少再像民初统治文坛时那样,努力去探索“新体小说”,章回小说成了他们创作的主流。这就形成各自的市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越来越趋于用白话,那些坚持用文言写小说的作家如徐枕亚,尽管在民初曾经那么受到读者欢迎,却在二十年代被淘汰了,因为他的作品日益缺少市场,不再符合通俗小说的要求,难以适应新的市民的需要。
但是,士大夫文化在鸳鸯蝴蝶派身上依然留有痕迹,它表现在章回小说的回目设置上,也表现在章回小说夹杂的诗词中,更表现在章回小说那凝练的语句、细致的描写上。假如有人写一部章回小说史,他会发现与古代的章回小说相比,不是就某一部作品而论,而是从一个时代来看,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很可能是最成熟的,最精致的,最能体现章回小说的特点,也最富于士大夫文化的气息。而一个时代的章回小说竟然在这时能取得新的突破,恐怕还得归功于民初文言小说在市民中造成的阅读氛围。
因此,中国近代都市化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新旧文化的交替,“市民”成分的不断变动,教育体制的急剧转变,种种因素拧在一起,造成通俗小说急剧的雅俗对流,给小说的雅俗划分带来复杂的因素。这一复杂过程也是中国特有的,它与西方的自然演变不同。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