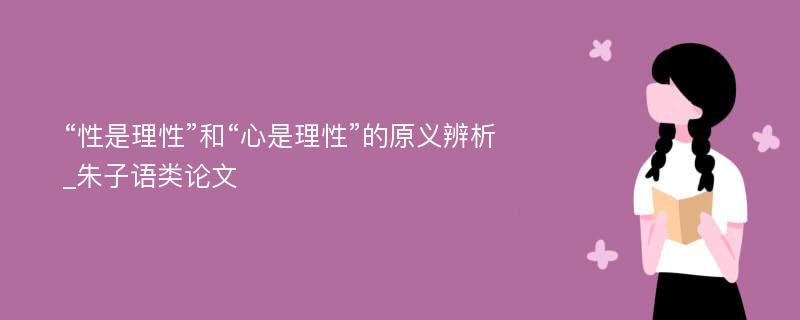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义论文,性即理论文,心即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244;B 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1)05-0023-09
研究宋明道学①的学者,凡论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哲学路线上的差异,都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互异。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定式,这深深地左右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比较研究。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致思上的根本区别已认识得十分透彻,无须再探讨。其重新探讨的必要性就在于:尽管我们一提及“理学”与“心学”的区别,立即就能回答其不同就在于一个(理学)主张“性即理”一个(心学)主张“心即理”,但除了将其不同从性质上归结为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对立外,我们并不能进一步清楚而扼要地说出两者是怎样的不同?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具体分析“性即理”与“心即理”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希望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比较研究的深入能有所促进。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只能有待大方赐教了。
以往一般是笼统地将“性即理”提法之始作俑者归在二程名下。但根据朱熹等人的记载,最早提出“性即理”者,当是程颐。对于程颐提出“性即理”的意义,南宋学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或深许之以“自古无人敢如此道”(滕珙《经济文衡前集》卷十六),或激赏之以“说得极善”。那么,这一论断何以说得好?朱熹认为它好就好在此说“大纲统体”,准确地把握了“千万世说性之根基”:“伊川说话,如今看来,中间宁无小小不同,只是大纲统体,说得极善,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1]308朱熹这样评价程颐首提“性即理”的意义,也就明白地告诉世人:在他看来,程颐之前的种种“性说”,并没有把握“说性之根基”,说得不如程颐讲得那般精深。问题是,程颐是从什么意义上提出“性即理”而博得朱熹如此高的评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程颐是怎样论述“性即理”的。他这样说:
又问:“如何是才?”曰:“如才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为轮辕,可以为梁栋,可以为榱桷者,才也。今人说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资质,循性修之,虽至恶可胜而为善。又问:“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又问:“佛说性如何?”曰:“佛亦是说本善,只不合将才做缘习。”[2]292
这段论述见于《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编者已明确定为“伊川先生语”。可以看出,程颐的这段话,并不是旨在论证“性”为何是“理”,而是侧重说明“性”所以是“善”的乃因为“性即理”:既然“性即理”,而“天下之理”又“未有不善”,则“性”也就“本善”。原本就是“善”的“性”,当其处在“喜怒哀乐未发”时,怎么能不是“善”的。那么,“性”分善、恶,也就只能从“性”已发(情)这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善)是指“发而中节”,合乎规范;一个(恶)是指“发”而无约束,不合乎规范。程颐这样论证,显然是想在定“性”为“善”的同时,对人何以为“恶”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但是,他的上述论说虽然回答了“性”发而“中节”就会处处为“善”,可他没有回答由“善”的“性”发出来的“情”(喜怒哀乐)何以会不“中节”而为“恶”。可见,他的“先善后恶”说,就只包含了这样的含义:人性就先天来说绝对是“善”的,但从后天来说,就有实现“善”和转变为“恶”的两种可能,其可能实现的条件就是是否“发而中节”:能“发而中节”,人就呈现了其本性,处处为“善”;不能“发而中节”,人就背离了其本性,走向为“恶”。
问:“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杨,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2]204
这是伊川明确提及“性即是理”的又一段论述。与上面那段论述相比,它不是旨在强调由于“理”是善的所以“性”就是善的,而是强调这样的看法:对任何人而言,“理”都一样是善的,则从“性即是理”推论,人性善对任何人都适用;也就是说,不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在本性上都一样是善的,不存在所谓善恶之别。可见,荀子主张人性恶,杨雄主张人性善恶混,都是没有了解人性的实质。而孟子所以独出于诸儒,就在于他真正了解人性的实质,能明明白白地指出人性本善。
我们从《二程遗书》中所能找到的伊川明确提及“性即是理”的论述,就只有转引在上面的那两段。从我们对那两段的分析不难看出:伊川所以要以“理”定“性”,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性只能是善的。问题是,既然人性善的根据在于“理”无“不善”,那么“理”是什么?它何以决然是善的?伊川似乎无意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我们从他的论述中看不到他关于“理”的定义,看到的只是他关于命、理、性、心的分疏:
问:“心有善恶否?”伊川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譬如水只可谓之水,至如流而为派,或行于东,或行于西,却为之流也。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有不善,性则无不善。”(《近思录》卷一)[3]19
从这个分疏可以看出,伊川所谓“性”,不具有形而上含义,是特指人的“性”。此人之“性”,作为决定人之所以为人者,可以由不同的称谓来揭示:当称之为“命”时,是说人之“性”随人之出生自然具备;当称之为“理”时,是说人之合乎其“性”的行为也就是合乎道义的行为(即对人来说乃合宜的行为);当称之为“心”时,是说“性”就是指支配人之形体做感性运动的那种能力。正是从命、理、性、心“其实一也”的立论出发,伊川不但强调“性即理”,而且强调“心即性”:“孟子曰:‘尽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2]204
伊川虽然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即性”,但他并没有合逻辑地推出“心即理”的论断。他为什么不这样推?就表面理解,他不这样推论,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心”只是一种主宰形体的能力,不可以直接等同观念形态的道义(理)。他说:“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2]205;他又说:“在义为理”[3]19,并指出:“义训宜”[3]18。由这些论述可见,他所谓“理”,就是指对于人作为人来说是合宜的东西。对人作为人来说是合宜的东西(理),当然就是决定人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而对人来说最本质的东西,当然只能是人的本“性”。可要问这一合宜于人之做人的东西具体指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指仁义礼智信。所以伊川明确地指出:“仁义礼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2]168。而人所以异于禽兽,就因为人有“仁义之性”[2]323。
伊川的“性即是理”说为朱熹所肯定。朱熹不仅高度赞扬伊川“性即理”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而且明确要求学生们论性先要明白伊川所说,真正认识“性即理”:“曰:‘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甚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4]191由于朱熹对伊川的“性即是理”说高度重视,积极予此说以多方面的阐释,使得“性即理”说在朱熹的阐释中变得更为清晰与周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说。
其一,“性即理”是以“理”定“性”,则此说的关键在于界定“理”,但伊川对“理”是什么缺乏应有的说明。这个缺陷,应该说为朱熹所弥补。朱熹在论及以“理”定“性”时曾这样说:
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底,便是性,便只是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如曰“恻隐之心”,便是心上说情。又曰:“邵尧夫说:‘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此说甚好。盖道无形体,只性便是道之形体。然若无个心,却将性在甚处。须是有个心,便収拾得这性,发用出来。盖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若是指性来做心说,则不可。今人往往以心来说性,须是先识得,方可说。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于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谓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朱子语类》卷四)[4]191-192
朱熹在这里告诉学生,以“理”定“性”,固然是要将仁义礼智确定为人的本“性”,但仁义礼智没有形状,所以以仁义礼智为人的本性,决不是指以一个感性的存在物来确定人所以为人的性质,而只是强调在人唯有“这一个道理”。既然“只是这一个道理”,则人亦“只有有如此道理”,即照这个道理(仁义礼智)行事,才能合乎人的本质(能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不失作为人。所以,要问人“性”是什么,那么只能说人“性”就是存在于人心中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简称为“理”),只能是仁义礼智。儒家以人性为“实”,就是从仁义礼智乃“实理”的意义上强调的,而不是“以心来说性”,将性说成“根于心”,因为“心即性”,“心”只是使“性”得以“发用出来”者,而决不是“性”之所出者。
其二,对于“心即性”,伊川说得极为简略,朱熹却说得较为明白:
(1)今人往往以心来说性,须是先识得,方可说。必大录云:“若指有知觉者为性,只是说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气质。……又曰:“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皆在其中。至于喜怒哀乐,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说出语言,理会得。只见事多,却不如都不理会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会得个名义着落。”
“天命之谓性。”命,便是告札之类;性,便是合当做底职事,如主簿销注,县尉廵捕;心,便是官人;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情,便是当听处断事,如县尉捉得贼。情便是发用处,性只是仁义礼智。所谓天命之与气质,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朱子语类》卷四)[4]192
(2)履之问未发之前心性之别。曰:“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说得。盖主宰运用底便是心,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性则一定在这里,到主宰运用却在心。情只是几个路子,随这个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朱子语类》卷四)[4]225
(3)性、情、心,惟孟子、横渠说得好。仁是性,恻隐是情,须从心上发出来。“心,统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个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则既有善,亦必有恶。惟其无此物,只是理,故无不善。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朱子语类》卷五)[4]229
(4)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问:“心之发处是气否?”曰:“也只是知觉。”“所知觉者是理。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如何得贯通为一?”曰:“不须去贯通,本来贯通。”“如何本来贯通?”曰:“理无心,则无着处。”“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心者,气之精爽。”“心官至灵,藏往知来。”……“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朱子语类》卷五)[4]219-221
(5)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生之理谓性。性只是此理。性是合当底。性则纯是善底。性则天生成许多道理。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
问:“性既无形,复言以理,理又不可见?”曰:“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
问:“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禀得言之否?”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个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朱子语类》卷5)[4]216
(6)尽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尽心只是诚意。知性却是穷理。心未有尽,便有空阙。如十分只尽得七分,便是空阙了二三分,须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孝便极其孝,仁便极其仁。性即理,理即天。我既知得此理,则所谓尽心者自是不容己。如此说却不重叠。既能尽心、知性,则胸中已是莹白浄洁。却只要时时省察,恐有污坏,故终之以存养之事。尽心者,发必自慊而无有外之心,即《大学》意诚之事也。问:“尽心莫是见得心体尽?或只是如尽性之类否?”曰:“皆是,尽心以见言,尽性以养言。”(《朱子语类》卷六十)[5]1934-1935
朱熹在以上论述中强调这样的看法:以“心”定“性”,乃是以“知觉为性”。知觉未发(喜怒哀乐未发)时,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浑然不分。天命之性不是指有个物事在,它“只是理”,“便是合当做底”一个道理。此道理(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人得是理以生,谓之性”,此“性”(理)存在于人身,成为主宰感官之“虚灵知觉”者,就“谓之心”。“理”在“心唤做性”:“性只是此理。”“性是合当底。”“性则纯是善底。”“性则天生成许多道理。”“性是许多理散在处为性”。理无不善,性既“本乎理”,则“性”亦为善。“性”既为善,则“推本而言心,岂有不善”,“心”也应是善的。正是从天、理、性、心本质一致的意义上,朱熹最后认同了孟子心性论的认知逻辑,将“尽性”问题最终归结为“尽心”问题,强调“尽性”“皆是尽心”。“尽心”与“见性”都意味着得“理”(心之本体),所不同仅在于一个(尽心)以“见”言,一个(尽性)以“养”言。“见”在这里如字读,还是当读为“现”?这直接关系着如何理解朱熹所谓的“尽心”与“见性”之别。“见”字如字读,则“尽心”是指认识了“心之本体”(理),而“尽性”则是指保养“心之本体”(理)。“见”字如读为“现”,则“尽心”是指呈现“心之本体”(理),而“尽性”仍是是指保养“心之本体”(理)。究竟取哪一种读法,一时难以决断。但就朱子学的立场来断,将所谓“尽心”解释为“心之本体”的呈现,似乎不妥,因为将“心”的发用解释为乃“心之本体”非分解性的直觉呈现,当为阳明学的立场。
朱熹对伊川“性即理”说的阐述,固然如上所论,深刻与清晰了“性即理”论断的意旨,但同时也严重的改变了“性即理”说的主旨。伊川“性即理”说的主旨在于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对伊川“性即理”说的阐述,就其主旨讲,当是用“天”的概念来确定“理”的客观性。“理”本是观念,是主观的设定,如何将这主观的设定又变成人性的本源,所谓“性本乎理”,是朱熹所侧重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使用了程颢首创的“天理”范畴(这个范畴,程颐在论“性即理”时,未见使用)。朱熹使用“天理”这个范畴,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不妨先看下面五段论述:
(1)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然而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朱子语类》卷四)[4]194
(2)伊川说话,如今看来,中间宁无小小不同,只是大纲统体说得极善,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理是个公共底物事,不解会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坏了着修。
明道诗云:“旁人不识予心乐,将为偷闲学少年。”此是后生时气象眩露,无含蓄。或问:“明道五十年,犹不忘游猎之心?”曰:“人当以此自《检》须见得明道气质如此,至五十年犹不能忘。”(《朱子语类》卷九十三)[1]3108
(3)“生之谓性”一条难说,须子细看。此一条伊川说得亦未甚尽。生之谓性,是生下来唤做性底,便有气禀夹杂,便不是理底性了。前辈说甚性恶、善恶混,都是不曾识性。到伊川说“性即理也”,无人道得到这处。理便是天理,又那得有恶。孟子说性善,便都是说理善;虽是就发处说,然亦就理之发处说。(《朱子语类》卷九十五)[6]3191
(4)又问:“‘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无人如此说。若不是见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复问:“昨夜问‘生之谓性’一段,意有未尽。不知‘才说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禀时说,已禀时说?”曰:“就已禀时说。性者,浑然天理而已。才说性时,则已带气矣。所谓‘离了阴阳更无道’,此中最宜分别。”(《朱子语类》卷九十五)[1]3193
(5)问:“程子说性一条云:‘学者须要识得仁体。若知见得,便须立诚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是那句?”曰:“是诚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会看文字。它说要识仁,要知见得,方说到诚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这几句说得甚好。人也会解得,只是未必实见得。向编《近思录》,欲收此段,伯恭以为怕人晓不得,错认了。程先生又说‘性即理也’,更说得亲切。”曰:“佛氏所以得罪于圣人,止縁它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万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己理会。”又问:“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论枯槁,它本来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镕做金用,便无此理。”曰:“‘《西铭》之意,与物同体’,体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见得意思是如此?与物同体固是仁,只便把与物同体做仁不得,恁地,只说得个仁之躯殻。须实见得,方说得亲切,如一椀灯,初不识之,只见人说如何是灯光,只恁地抟摸,只是不亲切。只是便把光做灯不得。”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一段”,说话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朱子语类》卷九十七)[1]3266
在这五段论述中,朱熹已经不讲“性即理”而是讲“性即天理”。这不仅仅是个称谓的改变问题,这个称谓之改变是为了在以“理”来定“性”之前,先以“天”定“理”。以“天”定“理”,就决定了“理”不只是与人之“心”相关联的概念,而是表示“理是个公共底物事”,是独立于“心”的客观的存在。独立于“心”的“理”(天理)浩浩不穷,它之“生下来唤做性底”,“性”只意味着“理”成为生物之功能。成为生物之功能的“理”,因与气禀相杂,“便不是理底性了”,已经不是那个本体意义上的“理即性”含义的“性”,而成了一类一类事物的具体的“性”,所谓“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这种决定物之类本质的“性”,也就是存在于一类一类事物中的“理”,所以万物皆有“性”,也就意味着万物皆有“理”,“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镕做金用,便无此理”。问题是,此成为一类一类事物之“性底理”,已经不是那个“天理底性”,因为“性者,浑然天理而已,才说性时,则已带气”。而那个与天理浑然一体的“性”,实际上也就是那个绝对客观的“理”本身。这样的“理”、“性”,是个非说就说得明白的绝对客观存在,除了知道它用以揭示“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4]196这一点外,我们对“性即天理”再也无法说得更明白。
如果说朱熹讲“性即天理”是沿着伊川的理路发展伊川的“性即理”说的话,那么陆象山首提“心即理”是否就是为了背离伊川“性即理”的致思理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分析陆象山究竟如何论述“心即理”。在陆象山的论著中,严格意义上的“心即理”之论述只出现了一次,是这样论述的:
《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此心有所不灵,此理为之不明,是谓不得其正,其见乃邪见,其说乃邪说。一溺于此,不由讲学,无自而复。故心当论邪正,不可无也,以为吾无心,此即邪说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贤者、智者之过之,亦未得其正。溺于声色货利,狃于谲诈奸宄,梏于末节细行,流于高论浮说,其智愚贤不肖固有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于其私,而使此道为之不明不行,则其为病一也。
周道之衰,文貌日甚,良心正理,日就芜没,其为吾道害者,岂特声色货利而已哉。杨墨皆当世之英人所称贤,孟子之所排斥距绝者,其为力劳于斥仪衍辈多矣。所自许以承三圣者,盖在斥杨墨而不在衍仪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谓固有,易而易知、简而易从,初非甚高难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学以克其私,而后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学》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则知自至,所知既至,则意自诚,意诚则心自正,必然之势,非强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当是时,天下之言者,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后,天下方指杨墨为异端。然孟子既没,其道不传。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实也。指杨墨为异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实也。往往口辟杨墨而身为其道者众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诸人交口称道门下之贤,不觉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櫽栝,其辞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傥有夫相孚信处,当迟后便。②
从以上二段论述看,陆象山提出“心即理”,并不是针对伊川,作为“性即理”的反命题来立论的。他只是从孟子的道德“心”(仁义之心)立论,以证明人“心”既然“具是理”则“心即理”。他所说的“是(读作“此”)理”,显然是指本乎“四端”的仁义礼智。仁义礼智是天地间的“正理”,它不是外在的物事,它就内在于人,是人的“良心”,故他云“良心正理”,将“良心”与“正理”并提,强调“良心”就是“正理”、“正理”就是“良心”。从这个意义(“良心”即“正理”)上讲,若“心”有所不灵,则理便因之而不明。理之不明,则所见为邪见,所知为邪知。因此,要得“正理”,首先要“心正”,因为“心当论邪、正”,只有“心正”才能得见“正理”,若“此心未正”,则“此理未明”,“心邪”决不能得“正理”。所以,就求“正理”来说,关键在于“正心”,而“正心”的前提是“诚意”,所谓“意诚则心自正”。以“诚意”作为“正人心”的根本保证,这是陆王“心学”的基本立场。但这个立场的确立,就陆象山首提“心即理”来看,它决不意味着是对伊川“性即理”立场的反动,而只为了反杨墨异端。为什么陆象山要反杨墨异端?因为他要反当时士人的恶习。当时的士人,虽然称道《诗》《书》《论》《孟》,但这无非是博取科举功名的手段,并不是为了认同儒家的生命精神(道)。当时士人出于科举目的所形成的这一恶习,在陆象山看来,就无异于“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出于护卫儒家生命精神的考虑,陆象山于是效法孟子当年反杨墨异端做法,站出来反对将儒家做人的学问变成博取科举功名的学问(即变成功利的学问)这一不良风习。
从陆象山提出“心即理”确实看不出他有反“性即理”的思想倾向。但王阳明之所以重提陆象山的“心即理”,其出发点义的确是反程朱的“性即理”。《传习录》中的二段论述,间接地回答了这一点:“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有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③理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于事父便是孝,发之于事君便是忠,发之于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7]在这里,就徐爱问他的致思立场与朱熹的致思立场是否悖反,王阳明作出了明确回答:他的立场与朱熹不同。朱熹讲“性即理”,是“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义外”,是将“理”当作超绝于事事物物、又独立于“心”的“至善”;而他自己则是就人心论“至善”,将“至善”当作“心之本体”,实际上它(心之本体)就是指将人固有的“明德”明到“至精至一”处的一种生命境界。“天理”就是指称“此心无私欲之蔽”的明觉境界,而不是指在此“心”之外还存在一个“定理”,它必然内化为决定“心”之趋向的“至善”。
将“至善”定为“心之本体”,进而将“心之本体”解释为“明明德”所达到的“至精至一”的明觉境界,这是王阳明以“心即理”取代程朱“性即理”所强调的基本观点。所以,他关于“心即理”的有关论述,从本质上讲,都没有背离这个基本观点。为明这一点,不妨先看下面三则论述:
(1)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又问:“释氏于世间情欲之私不染,似无私心,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成就他一个私已的心。”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明儒学案》卷十)[7]229
(2)问:“程子云‘在物为理’,如何云心即理?”曰:“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是也。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便有许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慕悦其所为,要求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取于义,便是王道之真。”(《明儒学案》卷十)[7]242
(3)董实夫问:“心即理,心外无理,不能无疑。”阳明先生曰:“道无形体,万象皆是形体;道无显晦,人所见有显晦。以形体言,天地一物也;以显晦言,人心其机也。所谓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氲,谓之气;以其脉络分明,谓之理;以其流行赋畀,谓之命;以其禀受一定,谓之性;以其物无不由,谓之道;以其妙用不测,谓之神;以其凝聚,谓之精;以其主宰,谓之心;以其无妄,谓之诚;以其无所倚著,谓之中;以其无物可加,谓之极;以其屈伸消息往来,谓之易,其实则一而已。(《明儒学案》卷二十五)[7]681
在第一则论述里,王阳明强调所谓“心即理”是就心之取向“当理”这个意义上讲的。而所谓“当理”,也就是指心在取向时“无私心”,因此,不能将“当理”与“无私心”截然区分开来,因为“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当理”与“无私心”本不能分;在第二则论述里,王阳明强调“心在物则为理”。那么“心在物”何以证明“心即理”呢?原来王阳明所谓的“心在物”是就“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的意义上讲的,它无非是说心之本体(至善)一旦呈现,就是“理”,如在事父上呈现,就成为“孝”之理;如在事君上呈现,就成为“忠”之理。所以,从“心即理”(心理是一个)立论的话,求“理”不当就外物致知,只要“来心上做工夫”就可;在第三则论述里,王阳明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对他的心学诸概念加以分疏,以说明其心学诸概念无非是对其“心即理”论断的各种角度的揭示。这表明王阳明心学体系是以“心即理”为核心范畴来架构诸概念。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乃“心即理”,这对于阳明后学来说,似乎不容易理解,否则,其后学也不至于一再追问“心何便是理?”有关这一追问所求得的有代表性的解答,有三则,我们先转录在下面:
(1)问:“理气如何分别?”曰:“理气虽有二名,总之一心,心不识不知处,便是理。才动念虑,起知识,便是气。虽至塞乎天地之间,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视是心,而视所当视,有视之理当循;听是心,而听所当听,有听之理当循,心岂便是理乎?”曰:“此正学问窽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则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视所不当视,听所不当听,声色牵引得去,皆知识累之也。知识忘而视听聪明,即心即理,岂更有理为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气,心之知识可无耶?”曰:“即理即气,所谓浩然之气是也。不识知之识知,所谓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谓。”曰:“动处是气,静处是理否?”曰:“静与动对,静亦是气。”曰:“人睡时有何知识?”曰:“无知识何能做梦?”曰:“不做梦时如何?”曰:“昏沉即是知识。”……无着便是理。……问:“此事究竟如何?”曰:“心安稳处是究竟。”问:“学力只是起倒奈何?”曰:“但恐全不相干,无有起倒可言。今说有个起,便自保任;有个倒,便好扶植,莫自诿自轻。”……问:“亦偶有所见,而终不能放下者何?”曰:“汝所见者,是知识,不是真体。”(《明儒学案》卷三十六)[8]116-119
(2)夫心即理,理即心,人心天理,无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于理者,是形气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于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正。性命合一,天人不间,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亚圣也。
气之存亡,间不容发。一念之得,则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即堕落体肤。是故孟子论养气,必以集义为事。此气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义与心俱,何以待集,盖忘助间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则义集,人欲冺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谓勿忘勿助与鸢飞鱼跃意同,正谓是也。
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黙而识之,随处充足。烟花林鸟,异态同情,俯仰之间,万物一体,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义袭工夫,到底止得圣门所为难耳。
不覩不闻,即吾心本来中正之体,无生无弗生,无存无弗存。苟有丝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谨恐惧,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明儒学案》卷三十八)[8]182-183
(3)夫天之生人,除虚灵知觉之外,更无别物。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便是天理。以其已所自有、无待假借,谓之独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无差别,谓之公共可也。乃一以为公共,一以为独得,析之为二,以待其粘合,恐终不能粘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则为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行于事物之间,则为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万物者,谓之理一;将自心之主宰以其不离形气,谓之分殊,无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视理在天地万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即理,则自不至为无星之秤,无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释,而视理与佛氏同,徒以闻见训诂与之争胜,岂可得乎?阳明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释界限,而以禅宗归之,不几为佛氏所笑乎?阳明固未尝不穷理,第其穷在源头,不向支流摸索耳。(《明儒学案》卷四十二)[8]317
以上依次为周汝登、吕怀、黄宗羲语。而黄宗羲语旨在批评杨时乔的看法——将“理”与“虚灵知觉”截然分开,以为“虚灵知觉”只是对“心”外之“天理”的认知。那么,根据以上三则论述,可知阳明后学对阳明所谓“心即理”的解释,重在说明这么几点;(1)“心即理”不是从知性认知的意义上立论的,而是从“忘知”的意义上讲的,所谓“知识忘而视听聪明,即心即理”。这是说心之本体直接呈现就是理,所以不能将“心即理”讲成“更有理为心所循”;(2)“心即理,理即心”,是从人之“本心”的角度立论的,是说人的“本心”即“天理”。这也就是说“天理”乃“吾心本来中正之体”,所以说非“出于理者”的“性”,不是“性之真”;“不根于心者”的“命”,不是“命之正”。这也就是说,“性命合一”,都是从“天理”“根于心”的意义上立论的,而决不是说有一个独立于“心”的“天理”来决定“性命合一”;(3)所谓“心”,无非指“虚灵知觉”,所以阳明讲“心即理”,无非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讲的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便是天理”。
注释:
①等同于广义的“理学”。下文所谓“理学”,一律是指狭义的“理学”,即程朱“理学”。
②这两段论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象山集》中,见于卷二(具体见该影印本1156册第269—271),但在中华书局1980年1月出版的《陆九渊集》中却见于卷十一(具体见该书149—150页)。《陆九渊集》乃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本为底本,并参考其它明、清刻本校勘。由此可以推测,这一舛误,当是在《象山集》抄入《四库全书》时产生的。至于其原因,一时难以考定,只有俟之来日。
③通常是在此“理”字下标冒号或句号。我之所以标问号,是因为我将此句理解为是以反问的口气表达其不同意“事父不成”就从父这方面去求孝这样的看法(这意外着“理在心外”,是阳明所反对的)。如果标为冒号,就成了阳明赞成“事父不成”就从父这方面去求孝这样的看法。
标签:朱子语类论文; 朱熹论文; 儒家论文; 伊川论文; 心即理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论文; 二程遗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