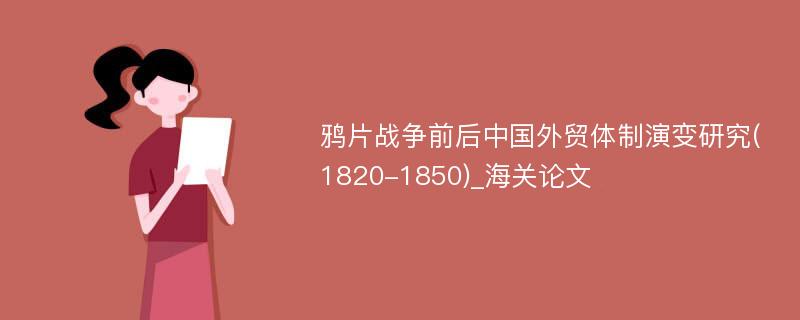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贸体制演变研究(1820-18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中国论文,体制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10-0106-07
史学界对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对外贸易体制问题已有一定关注①。一般对作为中国外贸体制特色的行商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该制度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需要,其必然终结的命运不可逆转。相应地,史学界对行商制度解体、条约制度逐渐确立后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给予高度关注,普遍认为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外贸体制开始向南京条约要求的协定关税方向转化。笔者认为,行商制度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对外贸易需要有限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因传统经济结构惯性的影响,并未显著呈现转变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察鸦片战争前后,从1820年代到1850年代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以期增加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鸦片战争前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特色的行商制度的合理性
1、行商制度的合理性
行商制度被史学界普遍定性为一种不合理的贸易制度,理由是不符合贸易自由原则,自身陋规烦琐而容易滋生腐败。笔者认为行商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清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行商制度做改良努力。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中国,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理所当然地与重商主义的西方经济思想有不同的利益考虑。中国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于几个口岸,甚至最后限制于广州一地,便是基于这种重农抑商的考虑。另一方面,行商制度被指责更主要是由于其贸易代理性质的间接贸易,有悖所谓自由贸易原则,当时即被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所抱怨,也是后世史学家诟病行商制度的主要理由。其实,行商作为获得政府特许专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集团,不仅行使着贸易中介的职能,而且承担着管理外商的担保责任,其行为超出一般商业流通意义,其商业利润理应包含一定合理的管理成本,不应一概视为过度勒索。如清朝主要税收收入田赋的行政管理费用占到税收总额的1/5至1/4。②因此行商索取一定规费,从行政成本角度考虑,尚属合理。更何况标榜自由贸易的英国,其对华贸易长期由东印度公司垄断,自由贸易身份的港脚商人的地位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废除后才得以确立,又何必苛责农业中国贸易特许性质的行商制度。
因此行商制度反映了农业中国的有限通商要求,其实质是贸易特许制度。在行商制度的实际运作中,风险与巨额效益并存。《粤海关志》载行商制度渊源:“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船,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洋商具有财产担保资格,“凡粤东洋商,承保税饷,责成管关监督于各行商中,择其自家殷实,居心笃诚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由此可见,洋商具有官方特许资格,承担代表官府办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在与外商交易过程中,行商负责代理外商与官方海关纳税。“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船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③行商的官方代理性质决定其在对外贸易中的流通枢纽地位。对外商而言,“行商是中国政府唯一承认的机构,因之通过行商可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由行商出名报关。行商代洋商(指外商)购入蚕丝地毯绸缎夏布与其他许多次的物品。这些商品依照官定章,只是外侨个人的必需品。但是事实因大宗出口而发了大财”。而对中国官方而言,“行商对海关监督(通称户部)负责出入口关税,只有他们才能与海关官员办事,外人免了报关交税的麻烦”。由于行商对外商存在担保责任,因此“东印度公司购买货品时,依照股份,按比例分与行商”。行商的官方贸易特许资格是行商付出一定代价换取的,“商行的地位是由付给北京方面一大笔金钱而获得的”。贸易特许的回报也是丰厚的,“执照虽如此费钱,但领到准许,他们就可长期享受巨大经济利益”。但是贸易特许的政治风险也随之而来。“政府常向他们勒索巨款,迫使捐献,如公共建筑、灾区救济、江河工程等。”④作为进出口贸易中介的行商,必须为外商的交易承担担保责任,这种责任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当货物准备起岸或下船时,‘户部’便派来一名管事一名录事和一名公差;担保该船的行商也派来一名管事,通事也派来一个帐房兼翻译,到场检查货物。无论外国船载的是进口货或出口货,政府总是责令行商负责交纳一切税钞”,所以,“行商必须把向政府交纳税钞看做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如果任何一家行商不能如期交纳税钞,他的洋行房产和一切财产便将由政府没收,售卖现款以资偿付;如果罄其所有仍属不敷,该行商便将被提出监狱,流放到新疆的伊犁,并命令其他行商共同代他交纳”。⑤
与行商制度配套的粤海关,其关税收入与清朝财政制度的行政方向基本一致,也可证明行商制度的合理性。清朝财政制度的特点是,“通过冬估、户部拨饷、春秋拨、奏销等财政制度的实施,外省正额钱粮的收支全部归由中央户部支配,地方官衙只是作为代理对收支进行保管而已”。⑥粤海关关税的征收与放解符合上述特点,征收和上缴均属正规,符合清朝税收制度成例。“粤海关征收税课,均有户部颁发商人亲填簿册,年终送部察覆。并广东督抚,亦每月造具货包清册,密行咨部覆对。”⑦清朝对海关税执行严格报解制度。粤海关“征收正杂银两,向例一年期满,先将总数奏明,俟查核支销确数,另行恭疏具题,并分款造册,委员解部”。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例,“大关各口共征收银一百四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两一钱二厘,除征足钦定盈余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外,计多收银六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两一钱二厘”。税银具体分拨为,“酌拨湖北省辛巳年兵饷案内拨粤海关税银二十万两”。⑧这与清朝其他主要税收的报解形式相同。另据道光十九年(1839年),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九钱九分三厘,“实解户部银一百万二千七百九两八分八厘,实解内务府银四十一万两,又另解平余等银六千六百三十两二钱八分五厘,查此项平余等银可遵照户部奏准,历于每年奏销盈余折内按数剔除,入于本案报销,向不归并盈余项下”。⑨可见,户部仍然是海关税的最主要归宿,说明海关税仍然是清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2、清朝整顿行商制度的努力
为规避行商“勒索”,英商采取与中国商人合作投资方式,变相改变清政府规定的以货易货贸易方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即上奏朝廷:“夷商航海,前赴内地贸易,向来不过将伊带来之货物售卖,就粤贩买别货,载运回国。而近年交结夷商,多有将所余资本,盈千累万,雇请内地熟谙经营之人,立约承领,出省贩货,冀获重利。即本省开张行店之人,亦有向夷商借领本钱,纳利生理者。”⑩可见,英商借向中国商人投资打进中国内地市场,达到规避行商环节的目的。清政府严格限制行商的贸易行为,禁止行商接受外商投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行商颜时瑛等违例吸收外商投资,因欠巨额债务而“任听夷人加利滚算”。广东巡抚李湖奉旨查办,“所有泰和裕源行两商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夷人收领,期于银两,著联名具保商人潘文岩等合作十年清还,庶各行商人不能私借夷债”,并告诫外商“嗣后不许违禁放债,如有犯者,即追银入官,驱逐出国”。李湖分析债务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向来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商交易,行上惟与投本行之夷人亲密,每有心存诡谲,为夷人卖货,则较别行之价加增,为夷人买货,则较别行之价从减,只图夷人多交货物,以致亏本,遂生借饮子换票之弊”。行商虽为对外贸易代理,其实也是独立贸易主体,赚取商业利润本无可厚非,况且行商承担代理职能本身就存在风险。广东当局为规范行商行为,维护行商制度的正常运转,防止行商为外商操纵,决定“请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货物,令各行商公司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务使交易公平,尽除弊窦,所有行用余利,存贮公所,先定钞饷,再照分年之数,提还夷人”。(11)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更进一步规定外商当年交易完成即还清利钱:“夷人回国时,亦止准于立定年限内,按本起利,如逾限托故不来,即停止利限,尤不得以利作本,违利滚剥。”(12)嘉庆八年(1803年),清政府重新整顿行商。粤海关监督德庆奏称:“今欲整理关务,须察商情,欲除弊窦,须专责任,惟有于各洋商中,择其自家殷实居心公正者一二人,饬令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货物,务照时价一律公平办理。”(13)总之,仍以维护行商的代理性质为要务。但由于行商经营成绩不佳,到道光九年(1829年),“止有闭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粤海关监督延隆认为,这是由于“从前开行,止凭二商保结,即准承允。今则必需总散各商,出具联名保结,方准承允,在总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实与否,不能调悉底里,未免意存推委,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事允”所致。在延隆看来,前任德庆的公推总商办法过于拘泥担保所需道德要求。他希望稍加变通,建议:“嗣后如有身价殷实,具呈情愿充商,经臣察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其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税项不致亏短,即请仍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其总散各商联名保结,应请终止,如此略为变通,于国课商情均有裨益。”(14)但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两广总督邓廷桢会同粤海关监督文祥上奏仍称暂行试办办法也有“人心叵测,安知其不于试办一二年内巧作弥缝一求遂其承商骩法之计,迨至限期取法,漏庀已形”之弊,因此“仍请复归联保旧例”。(15)其实,寄希望于商家弃私为公,本来就是水中捞月,而以承包方式变通,又会有竭泽而渔之弊。作为贸易代理的行商,在公私之间自然难以两全。
3、东印度公司垄断结束前后英国的自由贸易要求
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时代,英国商业利益集团就向清政府提出规避行商“勒索”。1826年英国商务代表加拉威礼拜会广东巡抚董教增,转达英国方面对行商制度的不满和自由贸易的要求。萧令裕《英吉利记》载:“初粤人贪番人之财。横索欺凌,又长吏缙绅夷夏之辨太严,持之太过急,而视之甚卑。一买办,一仆使皆官为制置尺寸,不能逾越。夷性犷悍,深苦禁令之束缚,粤海关之官商吏胥,于归公规费之外,又复强取如故,或加甚焉。英吉利积不能平,故欲改图,请互市于宁波天津。”英商猛烈抨击行商的过度勒索:“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担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16)行商事业风险巨大。中介贸易的性质使行商必须具备雄厚财力,一方面换取当局贸易许可,另一方面需要替外商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预付资本,以保证贸易的顺利完成。道光九年(1829年),行商流动资金链断裂导致信用危机,引起外商抗议。东印度公司大班部楼顿等,“以洋行连年闭歇,拖欠夷银,欲求整顿”,恳请“嗣后不用保商,不用买办,并在省城自租栈房,囤贮夷货”。(17)
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是东印度公司垄断结束后,英国商人表达其自由贸易要求的集中表现。清政府当然也注意到“该国公司已散,即经饬商妥议,务使事有专责”的情势,但终究碍于“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牵就”的故例,最后认定“该夷目不遵传谕,声言伊系夷官监督,非搭班人等可比”为无理要求(18),而断然拒绝其诉求。总之,广东官员不认可律劳卑的商务代表名分,要求“仍饬洋商,令该散商等寄信回国,另派大班前来管理方可相安”。(19)清朝经办官员对英商自由贸易要求装聋作哑,墨守行商制度故例。两广总督卢坤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奏称:“近年以来,洋商与夷商买卖,一切出口入口,货价及核算行用等项,悉照旧章办理,历久相安。凡有交易,悉出彼此情愿,不能勉强成交。如各洋商中,偶有买卖不分,该夷商尽可不与成交,另投别行交易,且可随时禀管查究,何至窜往江浙山东洋面。”(20)总之,鸦片战争前,行商制度与英国的自由贸易要求之间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二、鸦片战争后至1850年前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演变趋势
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贸易体制很自然地向条约通商口岸过渡,(21)但问题恐怕没有如此简单。鸦片战争并未显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贸易体制。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辟,短时期内暂时未对中国内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条约对海关税率的修改甚至客观上对中国对外贸易有利。上海开埠后,作为新型贸易代表的买办逐渐兴起,成为对外贸易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新因素。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中心。1842-1850年间英国尚未取得贸易优势,茶叶和生丝仍然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宗。(22)
英国本想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口在北纬二十九度至三十二度之间,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也是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地域”,特别是获得“在以上各地,英商须有与本地华人直接交易之权”。(23)南京条约规定“凡英国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24)但英国并未因此在通商口岸开辟后取得显著的对华贸易优势。如粗哔叽的输入量,从1843年的93405疋、1843年的98214疋,跌落到1847年的72488疋,虽然1850年回升到82100疋;呢绒的输入量,从1845年的62731疋,跌落至1847年的60931疋,再跌落至1850年的57050疋;染色及印花布的输入量,从1844年的242197疋,陡落至1845年的100615疋,最低跌至1847年的81010疋,虽然1850年回升到126970疋。总之,“英国对华输出没有稳健的增长,前途没有什么希望”。(25)条约订立后,英国对华商品输出曾一度激增,从1842年的96.9万英镑增加到1843年的145.6万英镑,1844年的230.5万英镑,直到1845年的239.6万英镑。但是很快就遭遇空前下滑,“在一八四六年对外输出的总额不仅降到了一八三六年的水平以下,而且除此以外,一八四七年危机时期从事对华贸易的伦敦行商的倒闭还证明了: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六年对外输出总额的名义价值,即如官场报告表中所载明的价值,完全与实际价值不相符合”。中国市场开放以来,“中国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整个讲来没有变化”。总之,“中国在中英贸易中总是占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不断增长”。(26)正如马克思所评论:“一八四三年的条约,不曾扩大美国和英国对华的输出,反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一八四七年的商业危机”。(27)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华贸易就已受到严重影响,各类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借贷成本激增,“银铺利钱,亦长至六分”,“茶叶价钱长至加二,虽然价长,各庄茶叶尚不肯卖”。(28)虎门硝烟后,据加尔各答新闻纸1839年12月16日称:“现在停止英国贸易之事,大有利益于中国贸易之船,因为他们在中国买茶叶,已占价值便宜,而带到此处茶叶卖价又贵。”(29)据兰顿新闻纸1839年12月2日称:“现在中国茶叶如此畅销,以致下等之黑茶绿茶价值亦如平时之好茶叶,并工夫茶之价钱一样。”(30)这充分说明英国市场对中国传统出口产品的依赖。战后,中国两项传统出口产品茶和丝的增长业绩显著。茶叶输出从1844年的150万磅,激增到1846年的1000万磅。生丝也从4815包激增到15926包。1846年,“上海出口的茶叶也许占到英国茶叶消费量的五分之一,生丝占自中国进口的三分之二”。(31)只是,茶叶和生丝的贸易已由行商转而操纵于英国商人手中。“华丝对外贸易,几全操于英商之手,惟一英人所购买华丝,初非自用,乃系转售于法以该国丝绸工业之需。又红茶贸易事实上亦为英商所垄断”。(32)
英国资本对中国的渗透效果也尚不显著,原因在于中国仍是传统农业社会,“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对于大工业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33)英国毛织品、棉织品在中国市场的黯淡,也可证明这一点。五口通商式的渗透暂时只能影响沿海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特别是主要“依靠少数经纪人作为外国人沟通消费者,或进而与本地制造家相竞争的唯一中介人。这些经纪人的主要目的是出卖而不是购买,他们之所以接受所交换的货物,并不是因为这些货物在内地有销路,而是因为那时现存的货物,并常常是唯一的交换品”。(34)上述中国茶叶和湖丝出口的增加即说明这一点。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辟,短时期内暂时未对中国内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以江西大余为例,“道光二十一等年,英夷在粤滋扰,茶贩及各货赴粤者较少,致赣关额课均有短绌,而此等人夫,并未有失业滋事之处,此南安府大庾县之实在情形也。至各处船户亦均设有船行,有保家层层防范,且船户以船为业,其船之大者,值数百千文,小者亦值百余千文,皆系出本谋生之人,即使夷港分开,客货略少,而内地之贸迁,商旅之运载,往来不绝,营趁有资,似不至因此而失业为匪也。现在各处客商货物络绎往来较前当无减少,该脚夫等均相安如旧”。(35)中国方面遵条约清理行商财务作为中英协定关税之根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粤海关“命库使夏君,将税课定额陋规实数,并洋商抽提行用,彻底清查,至是开册造报。余(黄恩彤)逐款钩稽数日,颇得其要”。中国方面认为:“今欲改定税则,办法有二:撤退洋商,将抽提行用及海关各项陋规,一并裁正归公,则岁入可加三倍,一也。酌留洋商,将出入口大宗货物茶叶湖丝棉花洋布之类,逐件加增,冷僻货物如钟表洋参洋缎之类,逐件议减,则所增之数二也。”终为英方搪塞。结果税额普遍在原额基础上提高,但英方比较行商陋规仍然接受。如茶叶每担税由每担一两三钱提高至二两五钱,棉花由每担一钱五分提高至四钱。(36)这说明,根据条约对海关税率的修改,在英国方面满意中国大宗商品茶叶的关税低于行商时代的同时,中国仍然保持对英方大宗商品棉花较高的进口关税,海关税收并未减少,客观上仍对中国对外贸易有利。(37)
特别是上海开埠后,作为新型贸易代表的买办逐渐兴起,成为对外贸易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新因素。上海也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中心。(38)买办不同于官方代理性质的行商,属于个人事业。买办事业的拓荒者是宁波商人穆炳之。穆氏“颇得外人之信用,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而穆又另收学徒若干,教以英语,教以外人贸易之手续法。及后外人商业益繁,穆一人不能兼顾,乃使其学徒出任介绍,此为上海洋商雇用买办之始”。(39)由于传统的湖丝生意路线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买办在湖丝生意中起到关键的居间联络作用。“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已不少。”(40)
但是尽管中国贸易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而且中国丝茶出口的优势远远超过英国从条约通商口岸开辟得到的商业利益。但是由于鸦片贸易被默认合法化,因此“虽然有出超的商业,而中国的财政和金融,因鸦片输入总额约达七百万英镑之多而陷于厉害的破坏状态”。(41)对于鸦片贸易事实上的合法化,时议也有激烈批评。夏燮认为:“约内绝不提烟土一字,若以为既抚之后,听其私售,则内禁之驰,姑勿具论,而该夷牟利于中国者,实即以此为大宗,今货物有税烟土无税,是得小遗大,官课日形其绌,抵久曾无了时也。若竟以此定其税则,如许乃济奏请开禁之原议,则彼逞其桀黠,势必闹关闹税,听其夹带偷漏而后已。是我徒博收税之虚名而受漏厄之患而已哉。”(42)另外,传统大宗贸易如茶叶,外商得以通过条约,借助通商口岸,直接深入到原产地采购。“自海口通商以来,洋商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地方红茶,议价颇昂,茶之出海者不可胜计。”(43)行商垄断时代茶叶价格本由中国商人操纵,而自通商口岸开辟后,外商得以直接干预市场行情。“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便向何处售买。”(44)迎合外销需要的茶叶初级加工也相应产生。“华商对华贸易极盛时代,国外需要激增,内地交通不便,消息不灵,常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上海沪商乃采买毛茶在沪改制,所谓‘土庄茶栈’者,应运而生,成为专业矣。”(45)其他中国传统出口产品也随通商口岸的开辟受到冲击。如厦门开埠后,“迨至(1843年)九月间,夷人开市通商,其在厦门行销者,无非棉花布匹洋货等物,内地之棉布不复畅销。”(46)宁波开港后,“(1841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47)。上海开港后,传统的松江棉布受到冲击,“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48)只是,这种变化这时更多出现在沿海地区。
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开始向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汇兑贸易网转变。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不仅是体现特定政治忠诚关系的国际政治关系,也是建立在一定商业交易基础上的贸易关系。“顺治初年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求不拘期限,由部移文户部,先拨库使收买,咨覆到部,方出示差官监视,令公平交易。”(49)这一关系在16世纪至17世纪明清交际时开始因欧洲国家的参与而扩大。而私人贸易伴随朝贡特使参与贸易,则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而使朝贡贸易圈日益呈现出白银流通圈的以白银作为支付媒介的国际贸易特点。(50)鸦片战争前,被鸦片贸易所加剧的白银短缺问题,以作为战后条约最主要标志的五口通商的实现,使白银短缺的中国和急需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之间,形成了英国棉织品和中国茶叶之间的现货贸易,它促成了两个进程的发生:一是以英国的棉织业为轴心,二是将中国的金融市场整合进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并将其与三角贸易联系在一起。资本的需求促使英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51)所谓三角贸易关系,是指“以伦敦的金融市场为媒介,英国的产业资本在支付自身需要的美国棉花的部分价款时,因为美国购进中国茶的缘故,因而购入美国的汇票进行结算”,从而形成中、美、英三国之间的结算关系。(52)另一方面,1842年开设于孟买的申打剌银行,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后,于1845年将总行移至伦敦,改名丽如银行,并于1851年绕过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取得皇家特许,得以在东方开设金融机构。以这家银行为代表的在中国从事汇兑业务的新机构,几乎全部来自印度,“其原因是由于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额的庞大,因而使银行无法弥补印度对伦敦直接开出的汇票”。结果,“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将对印度本行开发的汇票售卖给如中国的鸦片进口商,用这笔收入购买英镑汇票,然后将汇票寄往伦敦,用以弥补印度本行的英镑提款”。(53)
综上所述,行商制度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对外贸易需要有限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因传统经济结构惯性的影响,并未显著呈现转变趋势。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开始向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汇兑贸易网转变。
①相关研究参见:顾卫民《广州通商制度与鸦片战争》,《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吴义雄《广州外侨总商会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英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李宽柏、凌文峰《鸦片战争前英国散商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冲击》,《郧阳师专学报》2007年第5期;郭华清、朱西学《十三行贸易体制与鸦片战争的关系》,《五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朱新镛《广州的英印港脚商与鸦片战争》,《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俞如先《鸦片战争前的行商》,《龙岩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沈毅《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姚贤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政权丧失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房德邻《港脚商与鸦片战争》,《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6期;黄福才《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并未垄断中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等。
②王业健:《清代田赋刍论》,高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③粤海关志,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一,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④威廉亨德著,林树惠译:《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一,第256-257页。
⑤(31)(32)《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242,561,567页。
⑥[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⑦(17)(18)(19)(20)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鸦片战争》一,第67,76,119-120,132,114页。
⑧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道光关税案,《鸦片战争》一,第191-192页。
⑨军机处档案,《鸦片战争》四,第165页。
⑩许地山辑:《达衷集》,《鸦片战争》一,第35页。
(11)(12)(13)(14)(15)粤海关志,《鸦片战争》一,第180-181,182,188,198,189-190页。
(16)萧令裕:英吉利记,《鸦片战争》一,第29页。
(21)张明之:《从朝贡贸易体制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2)相关研究参见:张坤《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茶叶易货贸易》,《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
(23)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二,第654页。
(24)筹办洋务始末,《鸦片战争》四,第151页。
(2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491-492页。
(26)(41)马克思论中英条约,《鸦片战争》一,第12-15,18页。
(27)马克思论鸦片贸易(第一篇),《鸦片战争》(一),第1页。
(28)(29)(30)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二,第418,455,456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96-497页。
(34)《阿礼国上香港总督报告书》,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96-497页。
(35)吴养原:《吴文节公文镕年谱》,《鸦片战争》四,第624页。
(36)黄恩彤:《抚远记略》,《鸦片战争》五,第419-422页。
(37)相关研究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8)相关研究参见:仲伟民《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复旦学报》2012年第5期;吴乾兑《鸦片战争与上海英租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9)姚公鹤:《上海闲话》,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1页。
(40)周庆云:《南浔志》,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2页。
(42)夏燮:白门原约,《鸦片战争》五,第522页。
(43)清代钞档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左宗棠奏,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3页。
(44)清代钞档同治五年十月初八日左宗棠徐宗幹奏,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3页。
(45)实业部中国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88页。
(46)清代钞档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璧昌奏,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94页。
(4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94页。
(48)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95页。
(4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0,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9页。
(50)(51)(52)[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27,180,155页。
(53)《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4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