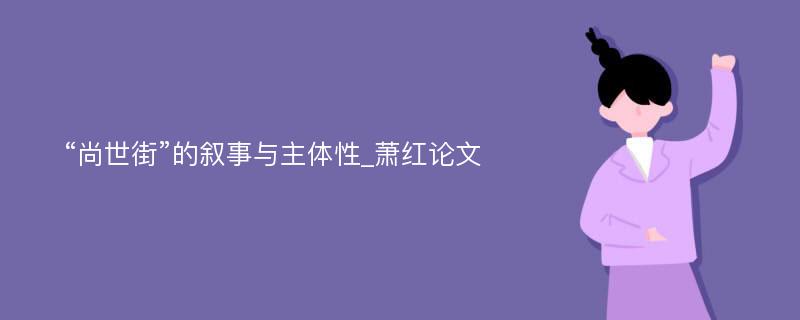
《商市街》中的叙事性与主体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市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市街》作为一部回忆性作品,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和萧红生平史料两个方面进行,而相对忽视文本中的叙事性因素。事实上,萧红写作《商市街》,既是现实生活中精神苦闷使然,也包含着挽救爱情、建构自我的积极诉求。本文力图通过对《商市街》的文本分析,发掘文本内外的多重寓意,呈现萧红一些人生重大抉择的内在心理动机,重新建构其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的主体性,从而把学术界对《商市街》和萧红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 开端的意义
哈尔滨的生活在二萧的笔下都得到过表现,但是两者表现的内容和立足点却有很大不同。萧军在《烛心》和《为了爱的缘故》中从不同角度写到了他和萧红的初识和生活,通过“英雄救美”、“医院逞威”等情节设置,强调了他的拯救者姿态和为爱做出的牺牲。而萧红在《商市街》中以入住欧罗巴旅馆为开端,回避了自己的创伤经验,使二人在平等、纯粹的两性关系中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二萧对爱情与生活的不同理解和表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与个体差异。
在《烛心》中,萧军描写了自己苦心炮制作品、卖文为生的惨淡生活景象,而他找出来的“旧作”表达的就是他去解救萧红时所感受到的复杂心情:既同情她的悲惨处境,又为她在逆境中所展现出来的才情和勇气所震撼。萧红在这篇小说中被命名为“畸娜”,不仅病弱、单纯得像个孩子,而且还有着人们所说的“疯狂症”。在《为了爱的缘故》中,萧军讲述了在医院中看护“芹”、逼迫医生给“芹”治病的过程,以及为了留下来照顾病弱的“芹”而不能入伍打仗所做出的牺牲。不难看出,在这样的叙述中,萧军一再选择了那些男/女、强壮/病弱、拯救/被拯救、支撑/依附等具有二元对立结构关系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他凸显了自己的男性英雄姿态,而将萧红置于处处受保护的依附地位。甚至在萧红逝去三十多年以后,他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还表达着这样的立场:“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①。萧军的本意也许是指他没有过多地要求萧红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妇在生活上的职责和重担,却不期然地暴露了他的“主权者”②心态,即他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萧红,他的男权意识、英雄情结都使他在强调萧红的病痛、弱小时突出自己的健康、强大,获得男性权威,以此凌驾于萧红之上。但是,即使是在萧军自己的文本中,萧红(畸娜)也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潜在地消解着他的男性优越感:在萧军的回忆中,二人初次会面时,萧红说“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③。在《烛心》中,畸娜说“谁知你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无所有的流浪儿哟”④。这样质朴、率真的话语,恰恰揭示了男性拯救者自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贫穷与落拓。因此,在二萧不平凡的会见中,萧军强调的是一见之下被萧红激发出来的,混合着爱与悲悯的拯救激情,体现出男性作为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性别优越感,而萧红感受到的却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精神共鸣。这就形成了一种文本的缝隙,同时也是二人在情感与认知上的缝隙。这个微小的缝隙在后来的共同生活中日积月累,越来越大,最终不可弥合。
萧红在《商市街》中,以入住欧罗巴旅馆为开端,就回避了萧军在小说和回忆录中津津乐道的“英雄救美”和“医院逞威”。前者隐含的是萧红未婚先孕、几乎被卖入妓院抵债的性别屈辱,而后者遮蔽的是萧红初为人母却不得不抛弃孩子的人生巨痛。“作为一个女性,萧红从女儿到女人的道路中,有着太多不堪回忆又不可磨灭的东西,它们作为一种创伤记忆大概只能以象征形式出现,也只能以联想的方式去回忆、表现和宣泄。”⑤因此,在萧红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父母双亡、流离失所的小环,受尽欺凌、难产而死的王阿嫂,都不同程度地凝结着萧红自己的生命体验,是萧红本人在作品中的双重投影(萧红最初的学名叫张秀环,创作时的她已经有过同样痛苦的生育经验)。王阿嫂的死既是其命运发展的必然结局,也在象征意义上体现着萧红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期许:她潜意识中也许正是想通过这个不幸的女人的死,来告别此前的种种不幸,开始一种新生活——具体到《商市街》中,就是从入住欧罗巴旅馆开始的二人世界。可是这样的新生活很快就显出贫穷、破败的本相。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丧失了生活的意趣,使彼此陷入精神隔膜的境地。如果说鲁迅在《伤逝》中通过涓生的视角描写了男性启蒙者对于生存和启蒙的无力承担,责怪子君在贫穷、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爱的附丽的话,那么在《商市街》中,萧红则通过女性视角写尽了娜拉出走后可能遭遇的生存艰难和精神伤痛,肯定了日常生活对于人生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当爱的激情迅速被贫穷破败的生活所泯灭时,她们曾经奋力与命运搏击的勇气也在这一次次惨痛的生存教训中丧失殆尽,由一个曾经充满反抗精神的现代女性不得不沦落成为一个坠着男性的衣角艰难生存的附庸者。在几乎是同样窘迫的生存处境中,涓生选择了放弃,最终导致了子君的死;现实中的萧军选择了忍耐、克制与迁就,结果是二萧在经受了长期的精神痛苦之后劳燕分飞。不同的选择,相同的悲剧,充分说明在生活贫困和精神隔膜的双重重压下,爱情终究是一件脆弱的事情。
萧红以入住欧罗巴旅馆为开端,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取消了萧军文本中拯救/被拯救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设置,使二人在平等关系中开始共同生活,体现了萧红强调性别主体间性的价值立场。如果说萧红在哈尔滨时迫于生存的压力多少有些麻木和无奈,那么到了上海,再来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萧红是具有反思意识的,体现为文本中处处浸透着追求人格平等和精神共鸣而不可得的精神苦闷。无论是困居欧罗巴旅馆,还是在商市街艰难度日,萧红都没有找到家的感觉。充斥在文本中的,除了穷困、饥饿、寒冷、病痛以及隐约的情感创伤外,一再重复出现的就是对“家”的质疑和反诘,比如,“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⑥(《搬家》),“这就是‘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穷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家”⑦(《他的上唇挂霜了》),“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⑧(《患病》)。与此同时,在描述“我”的种种生命感受时,也大量使用了物化修辞,如“我好象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⑨、“我不是也和雪花一样没有意义吗?……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象”⑩。这样的叙事声音,既表达了当时经验者“我”的真切感受,也包含着已经成为作家的叙述者“我”的理性反思。经验与叙述之间必要的审美距离,使《商市街》没有流于一般的记录和控诉,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审美意义。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寒冷、饥饿、病痛、空虚、寂寞等,既是现实中萧红艰难生存处境的真实描绘,也是她精神苦闷的外化与投射。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谬的叙述效果:她本意也许是想通过回忆哈尔滨时的患难真情,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生活和情感的珍惜,唤回萧军的感情,却在不期然之间,发现自己在如此深情回忆的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可言。虽然《商市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奠定了她散文家的地位,但她的心依然是寂寞而悲凉的。遗憾的是,萧军既没有理解萧红创作《商市街》的良苦用心,也不懂得欣赏萧红展现出来的文学才华,更没有意识到萧红在梳理并书写往事时心智的成长。他一如既往地简单、粗暴地对待她,贬低她的文学才华,丝毫没有预料到萧红会在日后主动提出分手。
萧红从入住欧罗巴旅馆开始写《商市街》,就暗含着在私密化的个人空间中对两性平等的积极诉求。她不得不屈服于生存的需要,却在创作中进行着深刻地反思。她一生的悲剧命运既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更是因为她始终不肯屈服于绵延了几千年给女性带来深重苦难的性别文化。对她来说,萧军渐渐成为这性别文化中最切身的一环。她没有能力改变他,就只能忍痛离开他,正像当年离开她的父亲一样。这与其说是她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二萧在政治立场、文学观念、性别意识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分歧的结果,而端木的出现不过是恰逢其时罢了。
二 结构:“到达—离去”模式
从《商市街》的文本叙述来看,无论是整个篇章结构,还是小的事件叙述,都或隐或显地体现出“到达—离去”的叙述模式。这种模式取消了情节的因果逻辑,使小说中的时间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在不得不离去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萧红早年的不幸遭遇带来了身心两方面的严重创伤,使她由一个勇于反抗的女性主体被强塑成一个极其隐忍的女性主体。
《商市街》从到达欧罗巴旅馆开始,到最终离开商市街25号为止,形成一个完整的“到达—离去”的叙述模式。其中,以《搬家》为界,根据居住地的变迁又分为欧罗巴旅馆和商市街25号两个第二层次的叙述单元,也呈现出“到达—离去”的叙述模式。这两个叙述单元中,根据生活内容的不同,又可再划分出若干第三层次的叙述单元,如是形成三层嵌套式的“到达—离去”模式。
首先,这种模式取消了叙事的因果逻辑关系,使各级叙述单元都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人伤痛的书写。每一个“到达”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随着生活真相的逐渐敞开,现实渐渐变得让人难以承受,最终不得不离开。“离开”既是现有状态的结束,同时也在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中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如是循环往复。《欧罗巴旅馆》从悄吟拖着虚弱的身体艰难地上楼开始写起,并没有交待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但可以看出其处境不佳。到了房间之后,迎接他们的是生活粗陋的真相,悄吟忍住劳累、饥渴和虚弱,度过了入住欧罗巴旅馆的第一天。忍耐从此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萧红写到:“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11)这句看似多余的闲笔无疑在提醒读者,在此处一带而过的叙事空白处,有着一段因为某种原因痛失家园而不得不寄人篱下,结果又遭到驱逐的尴尬、伤痛的“到达—离去”经历。在《借》中,他们来到女子中学,找梁先生借钱,因为梁先生在开会,只好茫然地离开。归途中,寒冷、跌伤、生病,写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惨状。《买皮帽》一文也是这样。二人在卖旧货的“破烂市”上,东挑西拣,因为囊中羞涩,最后给郎华买了一个皮帽,悄吟想吃点瓜子的小小心愿却不能实现,乘兴而来、扫兴而去的沮丧心情跃然纸上。他们在商市街,虽然暂时有了一个寄人篱下的安身之处,但此前一直困扰他们的饥饿、寒冷、病痛、寂寞如影随形地追到这里,又加上了感情的烦忧和政治上的恐怖,使他们最终不得不再次离去。这样,整个《商市街》就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被朋友逐出来)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挣扎后,又回到一种更加危急的不平衡状态(因为害怕遭受日本宪兵队的迫害而逃离家乡,走向未知的远方)。文本开始和结束时的艰难处境,加之萧红用优美的文笔生动传神地表达出来的日常生活的种种艰辛,使《商市街》所描绘的生活成为一段伤痕累累的人生旅程,激起了读者的极大同情,散发出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其次,这种模式取消了时间的连续性,使其人生故事成为一个个片断式存在。对于萧红和萧军这样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来说,日常生活不仅是单调重复的,而且充满了生存的焦虑和苦闷,饥饿、寒冷、创伤、病痛既充斥在生活中,也充斥在文本中。在欧罗巴旅馆和商市街这两个叙述单元中,有一些内容在结构上呈现出对称的关系,形成了《商市街》中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如在商市街25号这个单元中,在《借》中,去母校找梁先生借钱没有借成;在《十元钞票》中却意外地得到了来自胖朋友的十元钞票,让“我”充满了力气和勇气;《饿》与《患病》又构成身体感觉方面的对称。最典型的对称出现在《家庭教师》和《广告员的梦想》中。在《家庭教师》中,郎华出外找工作时,悄吟在家中依门而望;等他一身疲惫回来时,悄吟对他百般照顾,可是在《广告员的梦想》中,当悄吟有机会找到一份广告员的工作时,郎华却百般阻挠;当悄吟工作到深夜回家时,等待她的却是郎华的醉酒和争吵,最终导致悄吟的自我怀疑和失业。郎华对于悄吟找工作的消极态度以及悄吟很快失业的结局,加剧了郎华和悄吟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和悄吟作为女性的附属性,有力地表达了新女性在社会和男性的双面夹击下不得不无所寄托地消磨青春的不甘与无奈。
这种“到达—离去”模式,就其深刻的心理动机来说,是一种逃避和重复。《商市街》中的空间叙事往往直接从到达之地开始,隐含着告别往事、重新开始的心理期待。每一次到达,都孕育着一个新的开始,然而这新的开始又无一不是在重复过去。昔日的悲凉感受又一次充斥心间,往事重现,与当下的处境形成一种情感共鸣。不断地到达和离去,既反映了生活的困顿和人生的艰辛,也显示了萧红屡败屡战的乐观和积极:虽然她感受到的多是冰冷和嫌恶,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她对于温暖和爱的“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这些一个个独立存在的片断,又统一于萧红在文本中凝聚着的情绪状态中。在每一个“到达—离去”中都或隐或显地表达着失望与忍耐乃至绝望的情感基调,这样,在一层又一层层层叠叠的失望与忍耐中,形成了文本自身的韵律和节奏,具有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叙事特征。如果说鲁迅在其著名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结构模式中还有一个“故乡”可供怀想、归来和再离去,让他可以藉此来反抗绝望的话,那么萧红却连这点虚妄的慰藉也没有,她只能在一次次到达之后再一次次地决绝离去。她这种无家可回、无枝可栖的孤绝状态更深刻地体现了萧红的寂寞与绝望。她和鲁迅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别,既有萧红早年被父亲开除族籍的个人因素,也有性别差异的文化因素。男性作为文化主体,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反叛者;而女性作为性别文化的客体,既没有优秀的精神资源可以继承,也没有基本的物质资源可以利用,只能在隐忍中前进,在挫折中探索。在这种意义上,萧红笔下的“到达—离去”模式同时也是她作为一个探索者的行为模式,她以自己一生的漂泊伤痛和文学创作为我们揭示了在那样的时代中一个女性能够承受的苦难深度和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
三 场景:投射和隐喻
尽管结构简单,情节松散,《商市街》仍然为读者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虚幻的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萧红在表现女作家自我时,极少直接议论或抒情,而是创造了一些具有丰富含义的场景,使其发挥着投射和自居作用,具有隐喻和象征的功能,有些甚至还极其巧合地预言了萧红的悲剧命运。
在《欧罗巴旅馆》中,那几乎是高耸入云的楼梯,一方面象征了萧红的人生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也象征了萧红卓越的文学成就。接下来在那幔帐一样洁净狭小的房间里,正当郎华和悄吟为意外获得的铺盖而庆幸时,俄罗斯女茶房劫掠一般为他们揭开了这个生活世界的面纱。快得仿佛只有一秒钟,破木桌和大藤椅就露出了它们破败不堪的底色。这旋生旋灭的美好生活幻象无疑是此前和以后一系列精神和价值遭到破坏和毁灭的象征。不仅如此,晚饭后那几个不请自来的警察带给他们的惊慌,也预演了一年后由于组织剧团、出版《跋涉》而被日本宪兵跟踪的恐怖。如果说《商市街》是一出完整的生活剧,那么在这第一天中,男女主人公即将遭遇的一切已经得到了高度浓缩的暗示。
在《饿》中,悄吟为了抵御饥饿、寒冷和寂寞,索性披了棉被站到窗口,她看到一个母亲在无助地讨钱,孩子在哭。悄吟在这不幸的母亲身上辨认出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凄惨也感染了她,使她同时感受到自己情感和身体的饥饿。当她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时,却发现“窗子一关起来,立刻生满了霜,过一刻,玻璃片就流着眼泪了!起初是一条一条的,后来就大哭了!满脸是泪,好象在行人道上讨饭的母亲的脸”(12)。情感的饥饿与身体的饥饿内外交织,世态炎凉与窗外的冰霜互为喻指,这流泪的玻璃窗,最大程度地表征着萧红对自己平生创伤的内心郁积,成为萧红内在自我的投射。孩子一样单纯、敏感又脆弱的萧红,毫不设防地把自己袒露给这个世界,而这世界强加给她的却只有剥夺和伤害。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连哭都找不到地方。这个充满了艺术灵气的想象,自然而贴切,显示了萧红对现实困境的艺术性超越,以及“那种在极其具体琐细的事物上发现情趣,对那微小平凡的事物保持审美态度的令人羡慕的才秉”(13)。
随后曹先生来访的场景,体现了萧红对自己作家身份的积极认同。当曹先生问她是不是一个人住时,悄吟说“是”。这个事实上的谎言恰恰反映了萧红的潜意识,体现了一种试图修改自己生命轨迹的强烈愿望:“好象这几年并没有别开,我仍在那个学校读书一样”(14)。然而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她的人生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再也回不到从前。于是,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你喜欢文学,就把全身心献给文学。只有忠心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只有艺术才是美,才是真美。……爱是爱,‘爱’很不容易,那么就不如爱艺术,比较不空虚。”(15)这与其说是曹先生的谆谆教诲,更像是萧红的内心独自,是萧红要离开萧军这一想法的初次流露。萧红在创作《商市街》时,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爱的痛苦,她的女作家身份已经确立,自我意识正在觉醒,她不可能再安于过去备受压抑的旧生活,与其因为爱异性而痛苦,不如爱艺术更有价值。但是,在当时,这样的想法还只是处于朦胧状态,表现在文本中,是曹先生的话被女儿所打断;表现在创作上,是萧红自己及时地打住了自己的思路,没有继续阐述,因为这时的她还不足以坚定这样的信念;表现在行动上,她还要经过再三的犹豫和痛苦之后,才能痛下决心,坚定无悔地选择自己作为女作家的人生道路。因此,在曹先生来访的这个场景中,已经蕴含了日后二萧在西安分手的一幕。她拒绝去延安,而选择与端木一道南下,正是要“把全身心献给文学”的具体体现,并在此后创作出《呼兰河传》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在《同命运的小鱼》中,萧红心理投射的意味就更突出。小鱼是买来做菜的,死亡是它们的宿命。可是它们那惨烈的挣扎竟使悄吟泪流满面,诅咒起这个凶残的世界来。最后只剩下一条小鱼还活着,它先是快活,然后就忧郁起来。郎华认为它是由于不自由才忧郁的,应该把它送回江里,而悄吟认为送回江里,它会冻饿而死。在二萧关于鱼的忧郁的主观解释中,显而易见地投射着两个人绝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追求。萧军为了照顾萧红而不得不放弃去前线打仗,他一向为此感到遗憾,因而他把自由当做人生的要义;而萧红长期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游离的生活,更关心温饱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对萧军有着深深的依恋。这既是二人相识以来的分歧所在,也是二人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小鱼最后还是死了,甚至一只眼睛都跌了出来。这不幸早早死去的盲目的小鱼几经挣扎的生命历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萧红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追求,而萧红竟以“同命运”为题与小鱼积极认同,无疑折射着萧红本人的死亡意识,是她内心深处的死亡本能由无意识冲向意识的表现。萧红在精神和情感上屡受人生重创,加之身体的病弱,死亡主题从《王阿嫂的死》开始,经由《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到最后的《小城三月》,一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而萧红为了躲避战乱一路南下,孰料战火却仿佛在追着她的脚步漫延,直到她在香港死于疾病和战争。因此,萧红像黛玉写《葬花吟》一样写下的《同命运的小鱼》,竟一语成谶,成为她自己短暂人生的一个隐喻。
在《患病》中,悄吟明明是腹痛难忍,却先是请来了一个治喉病的中国大夫,后来被俄国女大夫领去做妇科检查,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的种种误会使看病这样严肃的事情几乎成了一场闹剧。在这一场景中,由于药不对症、答非所问,错讹百出,治病于是成为一个不断被延宕、最后不了了之的过程。身体的病痛,隐喻着个体与社会和家庭的严重失调,本应引起疗救的注意却一再被忽视、被延误,最终不治。这既是萧红人生的写照,也是二萧感情的隐喻。如果说鲁迅在《药》中通过华、夏两家药与病的双重悲剧揭示了启蒙的困境、大众的愚昧,那么萧红则通过她作为患者的现身说法,消解了医生/拯救者的权威,传达了对现实人生的悲观与失望,萧红最后在香港死于庸医的误诊,更是有力地揭示了救赎的无望。在《十三天》中,悄吟由于生病被送到朋友家休养一事,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病人被打成另类,遭到放逐的处境,女性、病人的双重身份,准确地隐喻了由于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萧红在文学史上被双重边缘化的命运。
《商市街》绝不是过去生活的简单实录,它必然连通并凝结着萧红文本内外的生命感受。她从私人生活空间入手,在性别、阶级、民族的框架内对个体的现实与文化处境进行了深入思考,通过描绘那些和她一样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使一种本来是极其个人化的忧愁和悲惨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又在群像式的描绘中突出了个人,进而传达了一种对人也对己的悲悯情怀。因此,《商市街》是经过了充分的艺术加工的产物,具备了叙事性作品应有的诸多要素,与《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作品一样,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
萧红这种凝聚着自我投射和生存隐喻的片断式书写方式,与她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巨大的人生痛苦——未婚先孕,又作为母亲放弃了自己的孩子——并不符合针对女性的性别规范,因此她总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保持缄默,以至于萧红早期生平研究中至今还存在着许多无法解开的谜团;在文学创作中,她几乎是被迫地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在这种文体中,她既投射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痛苦,又仿佛是在诉说别人的事情,以此产生一种文本间离的叙事效果,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诉说,也是遮遮掩掩的,以至于她只能片断式的、欲语还休地讲述“她”或“她们”的故事。那些来不及细细体会的美好瞬间,旋即被粗暴的现实所中断,人生由此成为一种刑罚。代代相传、几乎是一成不变的生活,取消了时间性,使这样的痛苦显得几乎是毫无止境。唯其她自己尝到了这种生活中最为痛苦的部分,她才能在自我经验的基础上洞悉人生的真相;唯其她自己的痛苦是难以言说的,她才会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像冰山一样为我们揭开现实的一角,让我们由此看到女性群体生存中无尽的伤痛;唯其她自己是超越的,她才能以一种不可想象的冷静,形象客观地表现出这种生活现实乃至历史文化“吃人”的本质。这使萧红的创作在思想上继承了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传统文化的总结与批判,在艺术上体现出以鲜活的女性经验和细腻的女性心理表达见长的叙事特征。
注释:
①③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②骆宾基:《萧红小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④萧军:《萧军全集》(1),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⑤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⑥⑦⑧⑨⑩(11)(12)(14)萧红:《萧红散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89、23、7、6、19~20、20页。
(13)赵园:《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15)萧红:《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