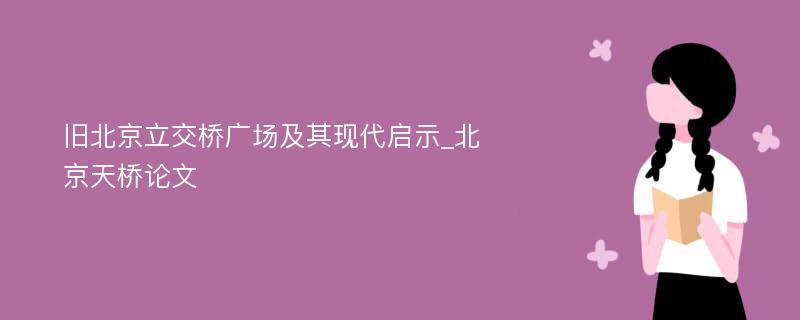
旧北京天桥广场及其现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桥论文,北京论文,启示论文,广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9)04-0012-06
一、中国传统街道广场空间
城市广场,如果不是按照当代西方广场文化的定义来看的话,在中国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城市规划观念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而逐渐改写着中国古老的城市格局,广场空间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重中之重,也在西方城市殖民的语境中向西方广场观念看齐。大连的尼古拉广场(今大连中山广场)、长春南满洲附属地区域广场空间、1929年规划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城市空间改造,以及辛亥革命后在北京进行的天安门广场建设、前门广场建设等是西方城市广场观念登陆中国比较显明的例子[1](PP.180—182)。建国之后一直到80年代,中国城市建设在风雨飘摇中前途难卜,城市广场空间建设的观念也是付之阙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重新提上日程,但此一阶段的城市广场空间体现出的是脱离城市整体实际的官僚意志,而与城市个体真正的空间需要渐去渐远,造成了今日中国城市广场的诸多问题。可以说,百年来中国城市广场的发展,如同百年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对于中国传统广场空间观念的偏离,正是这种偏离使我们失去了在中国本土化城市语境中建设健康的城市广场空间的启示资源。下面我们即以中国传统城市空间中的街道广场空间的典型一例——自明至民国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天桥——的分析,来考察中国传统广场空间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现代启示。
从夏代到19世纪末,中国传统广场空间依据发展历程可以依次分为,“祭祀性的坛庙广场、政治功能为主的殿堂广场、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并行的寺庙广场、以娱乐功能为主的广场、与市场功能相结合的广场、以军事操练与检阅为主要功能的阅武场广场等。”[2]中国传统广场空间的演变规律可以总结为,从体现神圣权威意义的围合空间向逐步满足城市市民需要的半围合空间的转变。街道广场空间正是后一种城市广场空间的典型代表。
街道广场空间的出现发生在北宋。有宋一代,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城市自身的发展逻辑要求突破前此体现统治者意志的城市规划格局,为市民趣味的表达和满足提供空间,于是在北宋东京城中第一次突破了唐代城市规划中集中设市的传统,将“市”与居住区混合,买卖贸易行为与市民生活世界融合在一起,开创了与城市规划空间构成张力的、表达城市市民意愿的市井空间。市井空间在空间形式上不再是唐以前由围墙划分的全封闭的围合广场,而是由街道两边的商户、住户围合形成的半开放的街道广场。街道中的行人在其中徜徉、购物、交流、娱乐休闲,在尺度适宜的空间中实现着人和人、人与空间的相互参与,清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以精妙的画笔描绘了这一街道广场空间的盛貌。北宋之后,街道广场空间随着城市市民阶级的盛衰而起落,南宋平江府(今苏州)的乐桥,元大都(今北京)的积水潭一带,明代南京的秦淮河沿岸、苏州的虎丘、北京的后海与前门一带,都是大放异彩的街道广场空间,而旧北京天桥则是中国传统街道广场空间的最后一笔,它的鼎盛时期实际上已经是西方城市空间规划观念强行登陆中国的初期,在两种观念的冲突下,北京天桥极具典型意义。
二、天桥广场空间的非规划特征
旧北京天桥广场空间的地理范围很大,清代康钧在《天咫偶闻》中就说, “天桥南北,地最宏敞”,其确切的地理位置是北至珠市口,南接天坛、先农坛,东临金鱼池,西至虎坊桥,东西南北有方圆好几里。天桥虽然面积广大,但在北京数百年的城市规划史上却一直是一处逃逸于城市规划之外的“飞地”。
北京,自古以来以为皇权重镇,在城市空间规划上为体现皇家权威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尤其是以明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尤为后人所叹服,但今天的天桥地区却独独被遗忘了。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元大都大体空间位置是:南墙在今东西长安街偏南,北墙在今安定门和得胜门外土城遗址一线,今天的天桥地区是不在城之内的,其时的天桥地区是一片大水及沼泽,极富野逸之美,为当时文人墨客寄托山林之思的所在。但此时的天桥又并非与都城完全没有关系。按照中国古代建设都市的要求,元大都在京城四郊建立了祭天、地、日、月的四坛,其中天坛即在今天的丽正门东南七里,永定门外,天桥地区之南,因此从空间区划上,天桥地区正处在皇帝天坛祭拜的中途。如果说天桥之北的大都城和之南的天坛代表着政治权威的话,那么天桥就是在两大权威符号中的“遗落”之地。
由元入明,天桥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其被“遗落”的野遗形象,明初北京城举世瞩目的城市规划盛举并没有对天桥产生多大的触动,而其闲情娱乐的意味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桥空间区域内的自然风光在北京城整饬的格局下愈加个性鲜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天桥之南于1414年又增广皇家行幸游猎的场所——南海子。明永乐年间,朝廷在大建宫殿的同时又在天桥东南修建了天地坛,在天桥西南修建了山川坛(先农坛)。自此之后,从南海子、天地坛、先农坛至京城,天桥更是必经之途,其边缘夹心的空间位置愈加凸显。明嘉靖年间,明政府又整修环抱南郊的外城,第一次使得在城外的天桥进入城内,但这仍然改变不了天桥地区在空间规划上的被“遗落”性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天桥地区与大栅栏地区的对比。早在永乐初年,明政府已在大栅栏地区建“廊房”,“召民居住,招商居货”,被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蓝图之中,更在后来将廊房四条发展成为全国文明的大栅栏商业区。但与此相距颇近的天桥地区,明政府基本上没有经过任何规划,只是放任自流而已。到了清代定都北京的时候,将整个城市分为东、西、南、北、外五城,天桥被划归外城。
天桥在北京城市规划中的被“遗落”性质使之避开了皇权政治通过城市规划而进行的格式化,在被“遗落”的同时,没有任何束缚,从另一种意义上获得了自由生长的良好契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力自我表达,形成了天桥广场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
早在元代,天桥地区就出现了零星的贸易活动,明代在天桥之南的天地坛、先农坛落成之后,商业贸易就发展起来,在天桥北面的东西两侧出现了最初的三个市,蒸饼市(饮食小吃)、日昃市和穷汉市,都是较初级的贸易活动。后来,天桥的商业贸易活动日渐兴盛,规模也越来越大,占据了天桥几乎所有的空间,并根据商业逻辑形成了传统天桥基本的“街市”空间形态。“街市”既是“街”又是“市”,是买卖贸易行为构成了街道的空间形式。天桥的这种“街市”空间结构与前门大栅栏的商业空间布局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一种“街市”空间,但天桥的街市空间是自发形成的,因此并不规整,而大栅栏的街市商业空间是经过规划的,因此相对整齐。但是,天桥与大栅栏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天桥地区的休闲娱乐功能十分发达突出。按照历禁,京城内城不得娱乐,因此城内的居民的娱乐活动更多地在外城展开。而同是外城,天桥却能吸引着出城的人们跨过繁华的大栅栏以之为乐土,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桥空间更加自由,极富平民意味,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天桥空间中有一些带有神圣意味的广场空间,比如天桥南部的天坛、先农坛、金鱼池附近的药王庙、天桥西侧的灵佑宫,以及天仙庙、斗姥宫、万明寺、仁寿寺等寺庙道院不下十几处,这些带有神圣色彩的广场空间为人们释放现实焦虑、精神升华提供了独特的条件,使人们更容易摆脱现实的局限而焕发自由自在的娱乐精神。明人刘侗、于弈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就记载了明时京都男女穿越天桥到天坛游玩的情形:“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无江城系丝投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游耍。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梁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3](P16)。可以想见当时天桥的热闹情形。正是因为天桥负载了商业贸易功能之外的休闲娱乐功能,所以在空间形态上在“街市”的空间中又叠加了新的空间结构——演艺空间。
天桥的演艺活动是适应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这些演艺活动在根本上也属于天桥众多职业的一种,与买卖贸易活动一样都是通过出卖“商品”而获取利润,但他们与天桥其他的通常贸易活动之间构成了奇特的空间张力关系。
第一,这些演艺活动往往是流动演出,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就是行话所说的“撂地”卖艺。这些流动的演艺活动见缝插针地填充在“街市”空间之中,使“街市”空间被离析、疏散,产生了流动而富有弹性的“街市”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是天桥广场最有意义、最富有启发性的空间形态。第二,演艺空间对于整个“街市”空间布局是构成离析张力的,但同时又起着极大促生力量。事实上,天桥地区混乱、初级的贸易活动与相对规范、发达的大栅栏商业区相邻而不萎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地独具特色的演艺活动的拉动作用。通常的贸易活动满足的是人们实用的实用需求,而演艺活动满足着人们从感官直到内心深处的精神需要,因此演艺活动会在更加深层、持续性的意义上吸引着人们的参与,聚拢人气,繁荣着天桥世界,同时也就为当时的商贸活动提供了“顾客”。民国评书大师连阔如先生在《江湖丛谈》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江湖中的艺人,无论练好了哪种艺术,都有百观不厌的长处。他们在哪里做艺,游逛的闲散人们就追到哪里游逛。不怕某处是个极冷静的地方,素日没有人到的,只要将江湖中生意人约了去,在那个冷静地方敲打锣鼓表演艺术,管保几天的工夫就能热闹起来。如若得罪了他们,或是由空块净盖房,盖来盖去将生意人挤了走啦,管保不多的日子,那个繁华热闹所在立刻就受影响,游人日稀,各种的买卖就没人照顾,日久就变成了个大大的垃圾堆。”[4](P20)
总之,从空间形态上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天桥广场逃逸出京城空间规划的格式化命运,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契机;在内部空间上,则是完全遵循着商业贸易自身的逻辑和人们的休闲娱乐需要自然而然形成了贸易空间和演艺空间构成张力的“街市”空间形态,同样不是从规划角度出发形成的。因此,天桥广场空间结构的形态是一个充分张扬自由活力,各种因素平等互动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广场文化中街道广场的代表性例子。
三、天桥广场的人群特征与演艺活动
与空间形态一样,广场上的活动也是广场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天桥广场空间时所指出的一样,对于一个脱离了规划的空间,常常是富有活力的广场活动营造成了富有活力的空间。我们前边已指出,北京天桥的广场活动可以分为贸易活动和演艺活动,而演艺活动又是促生前者活力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广场上的演艺活动。
活动的主体必然是广场的人群,北京传统天桥广场的人群层次性特别丰富。
第一个层次是城市市民阶层。天桥虽然长期处于北京外城,但因为内城严格的规划格局,浓厚的皇权气氛,一直以来对于市民的自由集会和交往是有所限禁的,明代时期,内城尚可以在积水潭湖畔、鼓楼地区自由买卖和娱乐,但在清初,朝廷颁布了“内城逼近城阙,例禁喧哗”的禁令,不准在内城设立会馆、戏院、妓院,于是这些体现着市民情趣的活动多设在在外城,其中天桥地区最为集中。加之天桥的确发达的贸易活动,在内城被重重限制的市民阶层自然对天桥充满了希望,纷至沓来,构成了天桥广场数量巨大、成分复杂的市民层次。第二个层次比较特殊,也至关重要,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城市闲人”。所谓“城市闲人”就是城市社会中的有闲阶级,他们经济上相对宽余,同时又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对于对象能够抱着超越现实的眼光去审视,他们在有目的的从事生活与无目的的欣赏生活的意义上构成了与城市市民的区分。自元至民国,旧北京天桥广场上的“城市闲人”基本上由三种人群组成,文人、游客以及清末民初的没落的八旗子弟。虽然在后世文人的表述中,天桥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是非之地,但从元到民国,文人的身影一直在天桥广场隐现。在元代,天桥地区就是文人寄托山林之思的所在。明、清、民国时期,随着天桥世界的越来越发达,久居京城身心疲惫的传统文人们更是在此处找到了和光同尘、解放身心的世间乐趣,此时他们大多聚集在天坛北墙外和金鱼池属于天桥路东一带,与路西纷纷扰扰的“街市”世界保持着欣赏但不参与的距离。天桥地处外地进京的交通要道,加之此处诸项方便,因此,这个地方也挽留住了一大批外地来京的游客,他们大多稍有资财,与卜居此地的文人们一样带有着欣赏的眼光混迹人群之中。到了民国时期,“城市闲人”的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没落的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在清代属于贵族阶层,在清廷稳固的时期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日以游艺为乐,因此养成了较高的艺术修养。辛亥革命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天桥地区的常客;辛亥革命后,八旗子弟沦落为城市的最底层,在别的地方没有生路,也只能在天桥地区为人帮衬,聊以为生,然而他们前此优越的生活所培养成的对于现实的敏锐感觉和欣赏态度却仍然保留下来,成了天桥市井中的隐士。
在此我们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对于天桥广场的演艺活动而言,如果说城市市民阶层提供了基本的观众群体的话,那么,“城市闲人”阶层的意义尤其重大。这些“城市闲人”因为他们与现实之间的超越关系,因此能以赏鉴的态度而非仅仅是功利的态度去评价天桥广场的演艺活动,只有这样的赏鉴态度才能使天桥的演艺活动不断提升自己,成为包含着创造性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尤其是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行将没落的八旗子弟因自身生活境遇所迫大量参与到天桥活动中去,对于此时天桥广场上演艺活动的兴盛起了极大的作用,也因此对于天桥世界在此时期走向它的巅峰状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连阔如在《云游丛谈》中就谈到了“城市闲人”对于天桥评书演艺活动的意义,他说:“近几年来,闲散阶级的人日日见少,听评书必须有闲工夫,闲人少了,说书的座儿亦受影响。那位说,北平的闲人有的是,我说那不是闲人,是失业的人,他们虽闲着,吃饭还困难哪,哪有钱去听评书;听评书的闲人,是有资格的闲散人物,不是没有钱的闲人。”[4](P271)这些有钱的闲散人物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保证了天桥演艺活动的正常进行,更重要的是为之树立了一个艺术的标准。
城市市民是观众,“城市闲人”是评论家,那么,那些到处流浪卖艺的艺人们就是天桥广场演艺活动的作者了。天桥的艺人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者不同: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者多是以仕进为业的士人,在生存条件、道德价值以及空间位置上都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他们的创造通常是“以文载道”式的高台宣讲,而天桥艺人则多是因为天灾人祸,或者是因为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而被迫背井离乡的流浪群体,是一群游牧的部落,正如现代作家钱丽川对他们的描述:“无论到块什么地方,拣着一块隙地,把双手一拱,同时说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开场白,也就可以做起生意来。”[5](PP.506-507)所以他们的艺术创造不是要宣扬什么,而是重在眼明手快,随机应变,与观众互动打成一片,营造一种民间狂欢的艺术景观。这决定了天桥艺人演出形式一开始就是从“撂地”摆摊开始,后来虽然逐步规范化,也有了舞台演出,但其自由交流、面向观众开放的艺术宗旨没有改变。
天桥广场上的演艺活动由市民、“城市闲人”以及艺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生产体系,营造了一种因为充分开放所以能够吸引众人参与的艺术形态,使天桥广场呈现出长此不歇的活力。即以演艺活动中的曲艺活动而论,天桥广场上的曲艺演出在文本上不讲深度,内容是人们熟知的街头故事,主题是人们日常践行的伦常大义,而使这一切化腐朽为神奇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则是曲艺独特的唱腔韵律。曲艺的唱腔要求“一要清楚,二要单纯,三要质朴”,节奏简洁,周而复始,有一种神秘的原始力量,能将观众深深卷入其中。就是那些没有唱腔的曲艺,比如相声、评书、快板、莲花落等,也都有一种独特的节奏①。曲艺正是凭借着这种简朴的节奏韵律,加之人人熟知的内容和极具召唤性的表演形式,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参与曲艺的同时,也从人人隔绝的功利性世界中升华出来,参与到他人世界中去,实现人与人的相互认同,使天桥广场世界自成一体。《江湖丛谈》中就多处记载了在曲艺表演现场城市民众积极参与的狂热②,那真是如火如荼,如痴如醉,体现了城市个体从城市统治逻辑中的解放。曲艺所引发的城市个体狂欢还体现在它使整个天桥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是演员同时也是观众的大舞台。
四、天桥广场的现代启示
旧北京天桥广场作为中国传统城市广场的代表性例子,一直是蕴涵着巨大活力的空间,但不能否认的是,北京天桥也是鱼龙混杂的广场空间,在这里不仅仅有人性的自由张扬,同样也是人性被物质贫困折磨而遭异化的展示舞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笔下,天桥世界就更多地被展示为一个又脏又乱的城市脏污集合之地,是应该避之不及的。我们说,这种对天桥的负面描写当然有客观的成分,但同时也遮掩了天桥广场最为动人之处,这就是在又脏又乱的表象之下所包含的人性参与的广场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现代中国城市广场所缺少的,在此意义上旧北京天桥广场凸显出巨大的现代启示意义。
这种启示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空间形态上,现代中国广场凸显了自上而下的仪式性内涵,而否定了广场自身人性空间的建构。天桥广场不论是在外部空间位置上还是在内部空间布局上都呈现出非规划的特征,张扬了广场主体对于广场空间的自我营构。而现代中国广场在外部空间位置上常常位于城市整体空间布局中的中心位置,比如多条交通路线的交汇处,市政中心之前等等;在内部空间上,往往喜好大尺度空间的建造,对称空间形式的营造以及设置面积惊人的绿地和与当地人的接受心理很难发生认同关系的广场小品雕塑,等等[6]。现代中国广场的此类空间形态所彰显的是一种仪式化的冲动,体现的是城市统治阶层的意愿,但却抑止了城市个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自我表达,人们在这样的广场空间中,只能观赏赞叹,却无法实现自我与空间的交流与互融。
第二,在广场活动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广场的活动极其缺乏活力,不能聚拢人气,这是造成今日城市广场不景气的直接原因。旧北京天桥广场由城市市民、“城市闲人”以及艺人构成了成熟的演艺体系,而且演艺活动的开放性能够吸引人们的参与。而在现代中国广场中,因为广场空间的仪式性内涵,人们在广场上的活动主要是无所参与的“观光”,人与人之间很难形成稳定、深入的交流,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广场活动的层次性和体系性,使得发生在广场上的活动只能是暂时性、表面性的,根本无法聚拢人气。另外,从功能上来说,旧北京天桥广场是多种功能的复合,政治、经济、休闲、交流各个功能搭配在一起,这也是天桥广场活动发达的重要原因,但在现代中国城市广场那里,广场功能贫乏单一,主要是作为城市的象征符号以及外来游客“观光”的景点,却很少提供人们展开娱乐休闲活动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商店、餐饮、电影院、茶馆、咖啡馆等功能设施,相反,收费颇昂的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设施倒是必不可少的设置,这肯定抑止了人们在广场上展开多种活动的可能性。
总之,与旧北京天桥广场相比,现代中国广场的不足之处总其要可以归结为凸显了仪式性内涵,而抑止了广场空间和活动中的人性参与,这是今日中国城市广场不景气的深刻原因,正如西方学者在批判中国现代城市时所说:“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到底缺少什么?是专家还是资金?是规划还是资源?什么都不缺,最缺的是强大有力的民主法制机制,最缺的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7](P4)现代中国城市广场归根结底缺的就是对于人的尊重。
注释:
①我们引一段传统评书《劫皇杠》中的“旗幡赞”以见其面貌:“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武。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龙旗紫雾盘旋,飞凤旗红云漫漫,飞虎旗腾空杀气,飞豹旗盖日遮天。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背旗。大将旗,坐纛旗,这个旗,那个旗,大旗小旗,半大旗。”
②比如,“奎胜城学有八手钩,故说伍殿章在小月屯大战康茂才时,比仿八手钩极为精彩。他叫座的魔力,较比乃师有过之无不及,自称为净街奎”,见连阔如(云游客):《江湖丛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