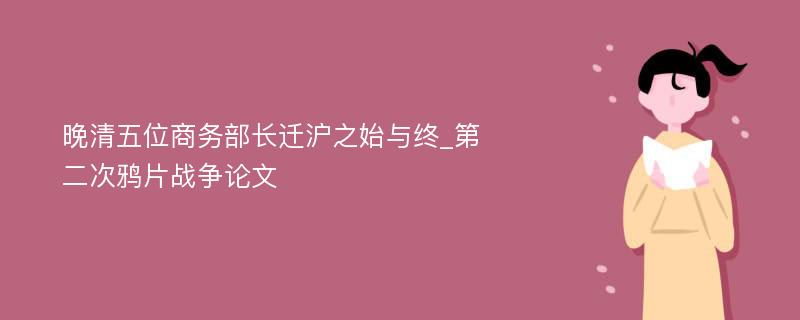
晚清五口通商大臣移设上海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始末论文,大臣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50年代末,常设广州几达15年之久的清朝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终于从那座与西方人已有上百年通商历史的海疆省会,移到了天朝的东南滨海县城上海。这在晚清的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上海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心口岸,上海,从此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它的份量。然而,这件事情的背景,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长期驻任南京,这段史实一般也不为上海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本文拟根据晚清旧档资料,对此作一阐述。
一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十三行专营外贸的特权被取消,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相继开放。为了应付头绪纷繁的通商交涉事宜,1842年10月,清廷任命曾代表中国与英方议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两江总督,兼筹一切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大臣之设由此发轫,史称“五口通商大臣”。1844年,耆英调任两广总督,并授命以钦差大臣办理各省通商善后事宜,于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也就成了两广总督例兼的职务,并被称为“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终未使中国社会从昏睡中惊醒,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大臣的设立,在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对咄咄进逼的西方人采取的一种“羁縻”手段。于是,在遥距京师的广州,奉命“驭夷”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很快与试图建立新的中外交往关系的西方人陷入了外交僵局。
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侨约有300人。 他们自朝贡时代起就被限制在城外沿江800英尺、面积约4英亩的十三行地区。〔1〕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些被久拒于城外的“夷人”终于提出了入城的要求,但遭到当地民众的坚决反对。
广州人恨西方人,固然是因为战争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痛苦,而且还使他们蒙受了因五口通商以后广州外贸垄断地位丧失而导致的重大经济损失,但其中,也不无来自传统夷夏之见的意气和成见。然而,无论是战争造成的怨恨,还是固有的夷夏成见,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正是它资以“驭夷”的“民气”。为此,清廷明确谕示:“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2〕
于是,答应西方人2年以后入城的耆英被召回了北京, 而被认为“办理海疆诸务,颇有定见”的徐广缙、叶名琛相继上任。〔3 〕面对找上门来的异族使臣,他们或虚与委蛇,或峻拒不见,使对方提出的新要求每每无法如愿。而在清廷的嘉许下,由当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广州民众拒绝外国人入城的斗争,则更使西方入侵者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进不了这座住有众多中国官吏和世家大族的省城。
为了摆脱上述这种困境,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急于在中国扩张侵略势力的西方人日益把外交的目光转向了北方的紫禁城。
1850年五六月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 )将本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为广州入城一事致清朝大学士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分别经上海、天津转递北京。照会称:“照得贵国粤省钦差大臣徐(指徐广缙——引者),因向取用词旨,设立方法,均似中有贻危两国和好之处。竟将体格字样皆失礼义之公文,欲札行驻粤领事官,其势我大英内阁各大臣,不得不转达贵国各大臣知照,深可痛恨!”照会表示:关于入城一事,“大英国家情愿简派大员,驰赴京都面议,商订其事。大清国家如果乐从,烦将是否妥合缘由见复,切所深幸也!”〔4〕
1853年4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也由粤抵沪,以国书难投为由,要求两江总督将其致清朝大学士的照会代呈进京。照会称:“自去年十二月至今,欲寻钦差(指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引者),未获面会,徒虚盼望。因在广东等候日久,乃照条约31款,已来上海,欲远交两江总督代呈,又值南京多事,未能转交。”照会认为,“其弗获将此书交钦差及别大臣者,由朝廷不欲外国大臣驻京,如此极难为本大臣矣。”要求清廷明确指示国书投递办法,并表示,希望能“得大皇帝准令进京陛见。”〔5〕
然而,西方人的这些外交努力,在只准常驻广州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一人办理夷务的天朝体制面前,最终都成了没有结果的事情。他们被告知:“中国抚驭外藩,惟年班及入贡诸国陪臣乃有请觐之例。该国远隔重洋,素敦礼义,中外体制,素所深知。但须恪守条约,照旧通商,正不必遣使入觐,始见诚悃也。”〔6〕
但是,西方人的贪求进取之势绝非是天朝的体制所能遏制得了的。1854年,《南京条约》签订满12年,西方人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有“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12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规定为词,〔7 〕向中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其中,派遣西方公使驻京成了首要的一条。当他们得知自己的要求最终被拒绝时,他们决心用西方的大炮来与天朝的体制对话。
二
1856年10月,在广州久争入城而不得的英国人借口“亚罗”号一事首先炮轰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12月,英法联军攻入城内,掳走了奉命“驭夷”的天朝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并将其解往印度,以“独惩其愆”。〔8〕1858年2月,英、美、法三国分别照会清朝大学士裕城,勒令清廷于3月31日前委派钦差大臣赴沪谈判, 遭到拒绝。同年5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攻陷大沽,兵临天津。6月,惊惶失措的清政府被迫与入侵者签订了包括公使驻京条款在内的《天津条约》,并同意派员前往上海与对方商定税则。
然而,清政府的签约原不过是“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的权宜之策,〔9〕至于条约中所拟定的公使驻京、内江通商、 内地游行及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等条款,在清廷的眼里“种种皆贻后患”,〔10〕是万难准允的。尤其是公使驻京这一条,“为患最巨,断难允行”。〔11〕因为天朝体制,凡外国人许其进京者,皆系朝贡陪臣,抵京后,“应先习跪拜之仪,然后奏请,定期令其随班引见”。〔12〕如果西方人进京不执此礼,中国帝王的颜面会在四夷面前丢尽,天朝的礼仪制度也会因此威信扫地。所以,为了维护天朝的体制,清廷决定,乘上海会议之机,重开谈判,不惜以“全免课税”为代价,挽回上述各款,以为“一劳永逸之计”。〔13〕
10月12日,税则会议在上海举行。为了确保既定的方针能在此次会议中得以贯彻,清廷拒绝了英方提出的由江苏巡抚赵德辙督同臬司兼署上海道薛焕会商税则的建议,特派经办《天津条约》的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以及亲信二品顶戴武备院卿明善、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等4人为钦差大臣,前往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主持此事, 并在给何桂清的密谕中再三叮嘱:“此次商定税则,系夷务一大转关,何桂清务须倍加慎密,不但严缉暗递消息之汉奸为要,即京员或有信函,尤不可稍为摇惑,议论多而实际少,惟静候内定办法,方能于大局有益也。”〔14〕
然而,会议开始以后,衔命赴会的清方代表迟迟未敢将改约的意图向对方明言,唯恐“与之明改章程,彼即指为背约”。〔15〕至于“全免课税”这一“内定办法”,他们更无意付诸实施。他们认为:“征收关税,谓之稽征者,稽查其出入之货是否违禁而征收其税也。若不征其出入口货税,则无所稽考,竟可任听该夷将我内地货物即在内地贸迁,胥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犹之人遭横逆,罄所有以与之,以求免累,仅存空房一所。彼果挈所有而远去,我尚可借空房为栖止,另图整顿。若不能遣去,势必得步进步,登堂入室,我衣食无资,童仆星散,其将何以御之?”〔16〕“所谓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其弊不可胜言,且不税于夷而税于商,更有许多窒碍。”〔17〕
清廷闻奏大怒:“此次桂良等前往上海与该夷会议,原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前经叠次谕令遵照内定办法,本月初七日复严切寄谕。桂良等接奉历次谕旨,自当激发天良,力图补救,若仍毫无把握,不过希图塞责,自问当得何罪?该夷条约,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4项,最为中国之害。桂良等能将此4项一概消弭,朕亦尚可曲从,若仅挽回一二件,其余不可行之事仍然贻患无穷,断难允准。何桂清受朕厚恩,亦当与桂良等筹议,计出万全,岂可专听属吏之言,自贻罪戾。”〔18〕
清廷的严谕,使在上海的清方代表跪聆之下,惶悚异常。无奈之中,他们不得不于10 月 22 日硬着头皮备文照会英国专使额尔金(James Bruce,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建议将上海作为办理各国事务之地,以挽回清廷最忌的公使驻京这一条款:“驻京一节,诸多未便,碍难照行,当时在天津匆匆议定,不及细述颠末,此时商办税则,正好将此不便之处详细商量,以期永敦和好。将来办理各国事务,改由上海商办。”〔19〕
其实,早在英法联军兵临天津胁迫清政府派出全权大臣前去谈判时,就有人提出过相似的建议:“伊意在津门立官,亦不过希冀遇事迅达之意。今如准其一切改在上海,而上海另立一专办夷务大员,如粤海关监督之类,随时有事,可以代其上达,伊即可将津门设官一层消歇矣。”〔20〕但这个建议当时并未引起清廷的注意。如今,面对“为患最巨”的公使驻京这一条,清廷不得不同意了桂良他们的办法,表示:“如果说定时,四事消弭,桂良等即可允其将钦差移至上海,专办通商事务,以后各国如有商办之事,即在上海商办,广东仍照旧通商。”〔21〕
但是,桂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额尔金的拒绝:“查天津所定条约各节,概为本大臣万不能更减,理合切实详言。至于此条(指中英《天津条约》第3款——引者)所载,大英特派大员,或入京长住, 或随时进京两端,应否如何,独归君主择定。……贵国向于外事,俱委离京远住之钦差大臣办理,以致历与各国大员每有不洽事故,适欲转陈伸曲,而朝廷仅据钦差大臣奏闻为信……今我国大员遇奉君主谕命入京长住理应遵行一节,既为条约已定之宜,贵大臣欲以画限,则本大臣一言一事,殊不能自允照行。曾已缕述容复布告外,缘顾此条,其志如何重大,亦难轻于奏请限除,盖其要旨,总由以本国大臣在京长住,实当贵国存诚守信,彼此修和之据。”〔22〕
额尔金的态度,使桂良等人感到“办理甚难著手”。于是,他们只得抓住该条款中“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这一“原属未定之词”,与之反复商议。〔23〕结果,说至再三,额尔金才表示:“如果当明年女王陛下政府大使在北京被有礼貌地加以接待来互换批准条约,而天津所订立的条约的所有其它细节又完全得以执行,这自然可以作为一种权宜的处置办法,女王陛下在中国的代表可以在北京以外其它地方驻节,定期对首都进行访问,或是仅仅由于公务紧急的需要不时地访问一下。”〔24〕
然而,清廷对此并不满意,上谕迭至,辞气严厉:“前次准将钦差移至上海,原为阻其进京及赴天津之计,若仍准其随时进京,则进京之后,如何驱遣,岂不与驻京无异,又何必改钦差于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总之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25〕
正当折冲甚苦之际,1859年1月, 传来了新任两广总督兼钦差五口通商大臣黄宗汉在广东继续与英人为难的消息。额尔金闻讯大怒,当即照会桂良等人表示抗议。
原来,早在1858年初,当广州失陷的奏报抵京后,清廷即授内阁学士兼署刑部侍郎黄宗汉为两广总督兼钦差五口通商大臣,驰粤赴任。由于当年广州绅民反对“夷人”入城的敌忾同仇之势给清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廷同时密谕在籍的户部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等:“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26〕,以便黄宗汉抵粤后,能“外示兵威,内借民力”,转圜事机。〔27〕以后,由于《天津条约》签订,广州的团练奉命约束、裁并,但其与城内英法联军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一心“想看到广州乡勇立即受到惩罚”的额尔金,遂决定利用上海税则谈判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去实现他用武力想达到的目的”。〔28〕
1858年10月7日,抵达上海的清方代表照会额尔金, 请其派人前来会议。 额尔金以黄宗汉仍在广州悬赏献英领巴夏利( Harry
Smith Parkes)首级为由,表示拒绝。 桂良等人于是不得不一面出示晓谕各地,俾知天津业已议和,中外民人应永敦和好,一面飞咨遥在广州的黄宗汉,嘱其毋再出示,并请知会罗惇衍等暂且停兵,俟上海税则商定。然而,额尔金对此并不满意,于10月9日照复, 非将黄宗汉去职,将罗、龙、苏三人特奉办理团练之权削去不可。奉命会议税则的清方代表顿感左右为难:“若不允其所请,不但他事不能商办,且恐立时决裂。”“若允其所请,又与国体攸关,亦不敢冒昧从事。”〔29〕不得已,于无可想法之中想出了一个“权宜救急之法”〔30〕,谎称“本大臣自出京以来,沿途访闻,两广督部堂黄办理一切,未能妥善,业于途次具折参奏,不久即可奉到谕旨,离任当不远矣”〔31〕。同时表示,愿奏请朝廷,撤去罗、龙、苏三人的团练大臣之权,“以示和好之至意”〔32〕。接到这一照会,额尔金才“心怀欣悦”,同意举行税则会议,并希望在上述两道谕旨降到之日,将谕旨转发阅看。〔33〕
然而,桂良等人的做法并不为清廷所赏识,认为:“若必尽遂该夷之欲,则是中国黜陟之权,外夷得而操之,尚复何所底止。”〔34〕但鉴于桂良等人已在额尔金面前撒了谎,并在事后补了一个参劾黄宗汉的奏折,清廷不得不顺其所为,另发谕旨,“使夷人闻之,知桂良等并非诳语,以安其心,而示之信”。〔35〕惟该谕旨并未将黄宗汉等人调任、革职,仅将其所办原委及现已停兵之处说明而已,桂良等人当然不敢将该谕旨向额尔金出示。于是,“权宜救急之法”因此成了滑头外交而终遭西方人的强烈抗议。
额尔金表示,不将黄宗汉及罗、龙、苏三人撤去,概不与议。急于挽回公使驻京等条款的清廷闻奏,马上在1859年1月29 日下谕:“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著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黄宗汉派员赍交何桂清祇领接办。”〔36〕于是,常设广州几达15年之久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终于移往上海。
三
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从广州移设上海,固然是清廷为阻止执意进京的西方人而不得已采取的又一“羁縻”手段,但它客观上也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末上海在中国对外贸关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据史料记载,当时上海的外侨已从开埠初期的25人增加到400多人, 超过了广州;〔37〕上海的外贸关税银收入也从开埠初期的17万两猛升至 180万两,跃居五口之首。〔38〕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不仅在黄浦滩头辟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租界,而且在广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日益把这座东南滨海县城视作他们与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因此, 1859年2月,奉命兼任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在《胪陈办理通商机宜折》中这样写道:
“上海为各夷聚集之所,应办事宜皆在上海,而夷性褊急,凡有照复事件,俱限以时刻。钦差大臣驻扎处所,若相离上海稍远,文报往还设有迟误,已多饶舌。而事未身亲目击,倘措置稍失其宜,即生枝节。故臣前有钦差大臣驻扎上海之议。”〔39〕
然而,也正鉴于此,这位主张将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移设上海的封疆大吏不避“饰词推诿”之嫌,反对由两江总督兼任此职,认为:
“两江总督驻扎江宁省城(即今南京——引者),今因城池未复,暂驻常州为后路策应,筹济饷需,弹压地方,一俟克复省城,即须前赴江宁办理善后,势不能时赴上海。设该夷酋借口有事,与钦差大臣面议,径来臣所驻之处,或遣夷官仆仆往来,骇人耳目,似多窒碍。且该夷近来蔑视督抚,倘因不能如其所请,仍欲进京与大学士尚书面议,巡抚系同官一省之人,虽出排解亦属无益。”〔40〕他主张:“将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由京简放,即在上海设立公寓,议给养廉,专司其事,以崇体制。倘有彼此龃龉之处,于督抚二人中酌量一人飞棹前往,为之设法排解,庶可日久相安。”〔41〕
然而,昧于大势的清廷旨趣全不在此,认为:“前因广东距京窎远,夷情不能遽达,致令借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钦差大臣于上海,并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两广总督之例,授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兹据奏请简派专员,驻扎上海,议给养廉,以崇体制。至总督距上海较远,事来亲身目击,恐措置失宜,并恐该夷遣人往来,似多窒碍等语。从前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遇有各国议事,先派员接见,原非事事与总督面议。叶名琛并不派员接见,相视太轻,而又不设备,故尔酿成此变。如果操纵得宜,亦不至蔑视督抚。况总督为地方大吏,足资弹压,若另设钦差,以京中大员任之,恐遇事呼应不灵。现在抚局尚未大定,所有应办各事宜,俟互换和约后,朕当再行详谕该督钦遵办理可也。”〔42〕于是,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一职终为两江总督所兼。
但是,清廷的一片苦心并未能阻止住西方人进京的决心。 1859年3月7日,当法国专使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 接到桂良等人照会,称嗣后各国通商事宜统归上海办理时,马上照复表示:“惟贵大臣未将归上海办理缘由声明。在本大臣尚未指实在何处所办理,何期贵大臣预为先定?其应在何处办理,惟本国与大英国方能准定,兹不具论,俟五月下旬本大臣赴京交换在天津议定章程,然后再议。”〔43〕于是,双方终于在公使入京问题上再次爆发武装冲突。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再度攻陷大沽,进占天津。同年10月, 联军兵临北京,迫使清政府无条件接受包括公使驻京条款在内的《天津条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长达4 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才宣告结束。但是,作为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五口通商大臣一职却从此移设上海,成了两江总督例兼的职务。
1861年1月,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多, 清政府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时,又分设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五口通商大臣遂成为办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虽仍用旧称,但实即“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洋大臣”,也称“上海钦差大臣”。〔44〕它列于总理衙门之下,但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按例皆由总理衙门承转。
注释:
〔1〕〔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0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1—12页。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21—222页。
〔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19—220页。
〔7〕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页。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56页。
〔9〕《钦差大学士桂良等奏英法条款要求太奢条约未能议妥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4页。
〔10〕《军机大臣寄钦差大学士桂良等著将内地通商及驻京等项窒碍之处向英法明白晓谕免遗后患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 ,第419页。
〔11〕《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应尽力阻止英法来京换约至驻京一节更断难允行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37页。
〔12〕《两江总督怡良奏在昆山接见美使并将所递国书呈览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页。
〔13〕《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在沪与英法会谈时应设法消弭派员驻京内江通商等四条之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44页。
〔14〕《军机大臣寄两江总督何桂清已派桂良等前往江苏会同妥议通商税则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469页。
〔15〕《钦差大臣桂良等奏税则议定大略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5页。
〔16〕《两江总督何桂清奏钦差大臣桂良等行过常州会同筹议税则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21页。
〔17〕《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洋务办理棘手及现在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35页。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166—1167页。
〔19〕《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连日与英会议税则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48页。
〔2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39页。
〔21〕《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从税则措手将使臣驻京等四事转圜其余即照天津及上海现定各款办理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3页。
〔22〕《附抄录英使额尔金为使臣驻京既为条约所已定断难更改照复》,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52页。
〔23〕《钦差大臣桂良等奏税则议定大略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5页。
〔24〕俄理范:《额尔金伯爵中国与日本之行纪事》,见《第二次鸦片战争》(6),第186页。
〔25〕《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使臣进京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76页。
〔26〕《军机大臣寄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著密传各乡团练将英军逐出广东省城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148页。
〔27〕《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黄宗汉著到粤后外示兵威内借民力期英法有所转圜并防俄美与之朋比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185页。
〔28〕俄理范:《额尔金伯爵中国与日本之行纪事》,见《第二次鸦片战争》(6),第179页。
〔29〕《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洋务办理棘手及现在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34—535页。
〔30〕同上引书,第535页。
〔31〕《抄录钦差大臣桂良等为告知两广总督黄宗汉已离任并撤去广东绅士办理团练之权事给英使照会》,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37页。
〔32〕同上。
〔33〕《附抄录英钦差额尔金为对黄宗汉离任并撤去罗惇衍等三绅士特权表示满意照复》,见《第二次鸦片战争》( 3 ), 第539页。
〔34〕《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务将内江通商内地游行等4 项要件全部挽回不得擅改内定办法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45页。
〔35〕同上引书,第546页。
〔36〕《内阁明发为英国抄送伪旨一道已著黄宗汉查拿伪造之人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603页。
〔37〕G.Lanning and S.Couling:The History of Shanghai,p.28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89页。
〔3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7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恒祺奏关税一年期满征收数目由》,见《第二次鸦片战争》(2),第192页;《劳崇光奏粤海大关一年期满征收数目由》,见《第二次鸦片战争》(2),第269页。
〔39〕《两江总督何桂清胪陈办理通商机宜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17页。
〔40〕《两江总督何桂清胪陈办理通商机宜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18—19页。
〔41〕同上引书,第17页。
〔42〕《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办理交涉事务要在操纵得宜并当与桂良等设法阻止英使进京等上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27页。
〔43〕《法使葛罗照复已悉简两江总督何为钦差大臣等事照会》,见《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24页。
〔44〕《钦差大臣奕訢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5),第343、344页。
标签:第二次鸦片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上海论文; 筹办夷务始末论文; 历史论文; 五口通商论文; 天津条约论文; 晚清论文; 额尔金论文; 黄宗汉论文; 何桂清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