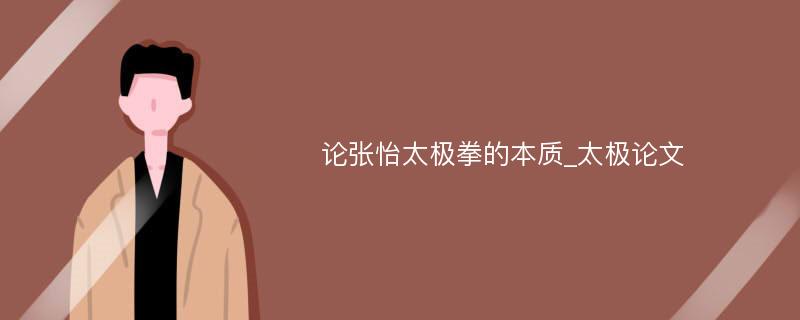
张栻太极体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极论文,体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4)01-0058-06 两宋之际的道学之传,重要的流派有二,一是道南学派,一是湖湘学派。这两派在道学发展过程中各有所侧重,道南一派强调静中体验,观未发气象;湖湘一派强调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涵养。道南至朱熹而大变,集全部道学之大成,湖湘至张栻亦有重要推进。道南与湖湘二派的具体思想主张虽有不同,但二者所承袭的道学重大主题、经典文献等却有一致之处。就作为思想来源与思想诠释基础的经典而言,除了传统儒学的基本经典即所谓“五经”及《论》《孟》之外,北宋道学如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西铭》,程颢《定性说》《识仁篇》等在南宋道学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样具有经典的地位。朱熹与张栻等道学家对此都有广泛深入的讨论或系统的诠释,从而推动了道学朝着更为宽广而又纵深的方向发展。就研究道学思想及其历史发展而言,对于朱熹和张栻等道学家关于北宋道学经典的诠释性著作及其讨论开展具体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仅就张栻对于周敦颐《太极图说》所作注解的有关问题作一讨论。张栻《太极图说解》不见于《南轩集》,而是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韩国学者苏铉盛教授曾整理《张栻太极解义》[1],可以参考。就张栻思想研究而言,其《太极图说解》是不可不十分注意的一个作品。因为其中确有独到的思想见解,而以往的研究由于文献查阅不便的原因而未能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一、注解《太极图说》 就思想来源而言,张栻与朱熹一样,都是由道学背景的家庭及师友授受而来。并且,二人早在隆兴二年甲申(1164)就曾有“三日夜倾谈”,而后乾道三年丁亥(1167)朱熹专程前往长沙会晤张栻,从容论学两月有余,朱熹通过张栻而受到湖湘先辈胡宏学说的较大影响,此后朱张持续往复论学十余年。朱熹几乎从二十几岁便表现出学术上的精进不已,层层更新,终于南宋一朝,几无人望其项背。当然这是后话。就本文所论主题而言,朱张大约在乾道六七年间已各自草成《太极图说解》,其时朱熹四十岁出头,张栻三十七八岁,都属于盛年时期。具体来说,朱熹草成《太极解义》当在乾道六年庚寅(1170),定稿当在九年壬辰。张栻的《太极图说解》则稍晚于朱熹完成。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其一,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太极图解》与《太极图说解》的合称)以后,随即展开讨论,并在讨论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关于《太极图说》的注解。我们知道,朱熹作成《太极解义》之后,与汪应辰、张栻、吕祖谦、蔡元定等有广泛的讨论。张栻与朱熹书曾说到: 《太极图解》析理精详,开发多矣。垂诲甚荷。向来偶因说话间妄为他人传写,想失本意多矣。要之,言学之难,诚不可容易耳。《图解》须仔细看,方求教。[2] 按,此书有“讲筵开在后月”一说。据《年谱》,张栻经筵开讲在乾道七年辛卯(1171)二月,可知此书作于是年正月。由此亦可知朱熹《太极解义》作于乾道六年庚寅。张栻这里所提及的《太极图解》或《图解》,即是指朱熹《太极解义》。而所谓“偶因说话间妄为他人传写”,则颇耐人寻味。对此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仅仅议论朱熹《太极图解》,一是因着议论而同时讲出了张栻本人关于《太极图说》的诠释性看法。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先请看张栻与友人吴翌书,中有云: 伯逢前在城中颇款,某所解《太极图》渠亦录去。但其意终疑“物虽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极之所以为极者,亦何有亏欠乎哉”之语。此正是渠紧要障碍处。[3] 虽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认定上面张栻所说的“妄为他人传写”的所谓他人就是胡伯逢(大原),但可以肯定的是,胡伯逢是积极传写张栻《太极图说解》的人之一。胡伯逢对于张栻注解中的“物虽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极之所以为极者,亦何有亏欠乎哉”一说,并不认同,以至其后张栻与伯逢书专门作了批斥和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张栻此说不见于现存《太极图说解》,是否《濂溪集》的编纂者作了删节,或是张栻本人后来作了修订。联系张栻与朱熹、吴翌(及胡伯逢)书来看,可以形成这样的判断,张栻在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书稿后,即与友人展开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张栻也初步讲述了他自己关于《太极图说》的诠释性看法,并很快为他人所传写。这种情形与张栻极为关注北宋道学前辈的著作及张栻在当时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完全吻合的。 其二,朱熹的有关说法,也足以说明张栻作有《太极图说解》。《答钦夫仁疑问》末尾附言: 刘子澄前日过此,说高安所刊《太极说》,见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见之者。不知尊兄以其书为如何?如有未安,恐须且收藏之,以俟考订而复出之也。言仁之书,恐亦当且住,即俟更讨论如何?[4] 同样意思的话,还见诸《答李伯谏》: 钦夫此数时常得书,论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极解》,盖屡劝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为然,不能深论也。[5] 以上所谓《太极说》、《太极解》,盖异名而同实,都是指张栻的《太极图说解》。据《年谱》,张栻于乾道七年六月出知袁州,实际从临安一路迁延至十二月径抵长沙。即使赴袁州任,恐怕也在八年初了。而此时刘子澄为高安县丞。张栻在袁州待的时间似乎很短,与刘子澄当属临郡为官。张栻如何于高安刻印其《太极图说解》,尚不得而知。但刘子澄知道实情,并告知朱熹,朱熹特为此事奉劝张栻暂时收板,待进一步商讨后再行刊印。②由此可知,张栻确实作有《太极图说解》。而此时朱熹《太极解义》尚在进一步修订之中,张栻的《太极图说解》则讨论并不怎么充分便匆匆刊印,无怪乎朱熹会表示明确的不同意见。朱熹之所以明确反对张栻刊印其《太极图说解》,除了张栻此书本身有待进一步“考订”以外,还与张栻此书中多次援引朱熹的注解有关,而朱熹并不认为他自己的注解已经很完备。事实上,现存张栻注解中所援引朱熹注解的两处文字,③皆与今传通行本《太极解义》有较大的出入,可见朱熹后来作了进一步的修订。 其三,从现存张栻《太极图说解》的文字来看,也可以看出张栻的注解是受到朱熹注解的启发或刺激而作成,尽管张栻注解中有其湖湘学派的思想主张在。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保存了张栻《太极图说解》(或亦称《太极解义》)的基本面貌,此本共有9段文字。如果联系朱熹《太极图说解》分为10章来看,张栻注解本似乎意味着分为9章。当然,并不排除这样的编排或许是《濂溪集》的编纂者有意为之。就这9章文字而言,有2章起首即是“新安朱熹曰”或“朱熹曰”,而后紧接着张栻的说法。这与上面所述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之后“偶因说话”,“所解《太极图》”云云,是恰恰吻合的,也足以表明,张栻的注解是在朱熹的注解之后完成。 综合上述,张栻当是在乾道六年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即与朱熹往复讨论,[6]并与门人朋友时有议论。乾道七年,张栻也作成了自己的《太极图说解》,随即为他人所传写。显然,张栻对于这个传写本有所保留,故向朱熹表示“想失本意多矣”。之后张栻当是有所修订,但似乎未臻完善,便于乾道八年刻印于高安。张栻在高安所刻印的《太极图说解》由于援引了朱熹注解,可是朱熹并不以其《太极解义》为定本,而张栻注解本也有待进一步修订完善,故而希望张栻收板止印。这大概是张栻《太极图说解》形成与刻印的基本情形。需要说明的是,朱熹于张栻去世后编订《南轩集》,未收录张栻《太极图说解》,幸而宋本《濂溪集》收录了张栻此书。而《濂溪集》得以收录此书,则当与张栻注解本“为他人传写”及“高安所刊”有一定的关系。职是之故,我们才有可能对张栻《太极图说解》及其思想作具体的讨论。此外,朱熹《太极解义》对于周敦颐的《太极图》与《太极图说》都有注解,而宋本《濂溪集》所录张栻注解,只有《太极图说解》,而无《太极图解》。是否张栻仅仅注解了《太极图说》,抑或张栻也对《太极图》作有注解而后来失传,尚不得而知。仅就现今可知者而言,张栻注解本称作《太极图说解》似较为合理,尽管宋本《濂溪集》卷三于夹注中有所谓“解义或本”一说,[7]但此所谓“解义或本”所指不详。 二、太极之体 张栻《太极图说解》云: 太极之体至静也,冲漠无朕而无不遍该焉。某所谓至静,盖本体贯乎已发与未发而无间者也。然太极不能不动,动极而静,静极复动。此静,对动者也。有动静则有形器,故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盖动则有静,而静所以有动也,非动之能生静,静之能生动也。动静者,两仪之性情,而阴阳者,两仪之质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矣。有一则有两,一立则两见矣。两故,所以为一之用也;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或几乎息矣。[8] 这段文字为张栻《太极图说解》第一段(或即第一章),其意思是说,太极之体是无对的,是一种绝对之体,其特性是“至静”。太极至静之体也即是冲漠无朕的理体,这是其纯粹形而上的一面。同时,太极之体又是“无不遍该”,也即是无所不在。这是体不离用,亦即道不离器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本体贯穿已发与未发的全部过程,未尝止息,未尝间断,也即至静的太极之体并非孤立独存的绝对静体,而是有动有静,静中有动,动中含静。所以说“太极不能不动”,此动即是至静的太极之体的自动。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动静互为其根,即动静互为变化的基点,而不是指动静能够相互生成。此意义的动静是太极发动之后的动静,是相互对待的,此即所谓“此静对动者也”。此动静又是两仪的内在特性,而阴阳则是两仪的形质表现。阴阳两仪的分立及其动静,与太极之体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有一则有两,一立则两见矣。”太极存在于阴阳动静的变化过程,即“无不遍该”,而阴阳在太极即冲漠无朕的至静之体的作用下展开其动静变化过程,离了太极之体,阴阳两仪便无从发生作用。张栻这里的两一关系说,应当是吸收了张载的说法。张载《正蒙》有云:“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9]但所谓两与一的所指,张栻与张载当有所不同。张载指的是气之一与阴阳之两的关系,张栻虽然未必否定张载的这个意思,但更根本的是指太极之一与阴阳动静之两的关系。 上段引文所谓“太极之体至静”,明确提出了“太极之体”的观念。太极之体是冲漠无朕的,其特点是“至静”,此“静”是无对的,也就是说太极之体以静为根本特性。同时,太极之体“不能不动”,也就是太极自身具有动静的功能,因而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静,静极复动。这实质上隐约透露出太极之体有一个静在先而动在后,也即由静入动的过程。这个思想与朱熹的太极论明显不同。朱熹反复思考之后认定太极之理自身无动静,体现在理气观上便是理无动静,气有动静,理是乘气而有动静。这大概也是朱熹反对张栻刊印其《太极图说解》的一个思想根源。就张栻来说,太极之体自身有动静,在宇宙论上有更多的说明。张栻说:“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也。极乃枢极之义,圣人于《易》特名太极二字,盖示人根柢,其义微矣。”[10]“易也者,生生之妙也。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11]太极为枢极根柢,又是“所以生生者”,“所以明动静之蕴也”,这是从阴阳动静和万物化生的根源来说明太极的意义。张栻说:“太极混论,化生之根,阖闢二气,枢纽群动。惟物由乎其间而莫之知,惟人则能知之矣。”[12]太极首先是万物化生之根,其动静阖闢而生出阴阳,又是各种运动变化的枢纽所在。正是由于太极自身的动静,阴阳二气及万物才得以化生。张栻说:“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13]张栻还从万物流行发育的意义上说明太极的意义。其《太极图解序》谓“《通书》之说大抵皆发明此(《太极图》)意”,认为太极可看作诚,作为万化的根源,太极有似于《通书》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即此可以“深明万化之一原”。而作为流行之体,太极之动有似于《通书》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即此可以体现“本体之流行发现者”。[14]因此,太极不仅是阴阳动静的根源,也是万物化生的根源,还是一个流行发育的“本体”。合而言之,阴阳五行,万物化生,“其本亦一太极而已”[15]。张栻所谓太极自动的论说,与朱熹所主张的太极自身不动有着重大的差异。而所谓太极为枢纽根柢,为所以明动静之蕴,则与朱熹所言太极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其意旨很是相近。 其实,朱熹在《太极解义》中也讲太极之体,不过区分得更为细致,有“太极本体”与“太极体用”两个观念。太极本体是绝对的万化根源,其自身也是冲漠无朕,无动静可言。太极体用则表现为因阴阳之气的静而为体,因阴阳之气的动而为用,“太极本体”通过“太极体用”的展开而化生万物。此体与用是太极的两种表现状态,但不可以动静的不同来判定太极有体与用的不同[16]。张栻则直接以太极之体自身有动静,从而太极之体的动静变化可以生出阴阳以及万物。这与朱熹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 三、太极之性 据前面的引文,张栻讲到太极“本体贯乎已发与未发而无间”,此说具有心性论的意义,而并不是仅仅针对太极自身动静与否的问题。张栻说:“太极,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动,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也。”[17]“太极,性也。惟圣人能尽其性,人极之所以立也。”[18]太极为性,实质是以理为性。张栻还进一步讲到,为什么需要有太极与性两个概念,而不是有性这个概念即可。他说:“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极,则只去未发上认之,不见功用。曰太极,则性之妙都见矣。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其太极之蕴欤。”[19]所谓曰性则只去未发上认之,实质反映的是湖湘学派性论的基本观念及其工夫导向。胡宏主张“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20]也就是性为未发,心为已发。胡宏又有“性,天下之大本也”[21],“性立天下之有”[22],“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物”[23]诸说。凡此,奠定并支配了湖湘学派关于心性的基本论调。张栻有这样的担心也就完全可以理解,而使用太极这个观念,则不仅可以表达“性”的含义,还可以表达“性之妙”,亦即“本体贯乎已发与未发而无间”的意蕴。故此,以性论太极,成为张栻特别喜好的一种思想观念,甚至被运用于诠释《孟子》。 张栻注解《孟子》告子“生之谓性”章,便是基于以性论太极的观念,阐发大段议论: 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发现,则人物所禀有万不同焉。盖何莫而不由于太极,亦何莫而不具于太极,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极,则有二气五行絪缊交感,其变不齐,故其发现于人物者,未尝不各具于其气禀之内。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异,知其流行之各异,而本之一者,初未尝不究也,而后可与论性矣。故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盖论性而不及气,则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极之用不行矣;论气而不及性,则迷失大本之一,而太极之体不立矣……故太极一而已矣,散为人物而有万殊,就其万殊之中而复有所不齐焉,而皆谓之性,性无乎不在也。[24] 这里,张栻从太极本体与太极之流行的关系来揭示性之本一与人物气禀之殊的关系。性之本一是从本原上说,性也即是太极,是万物之性的总根源,其流行发现便形成万物之性。万物之性无不源于太极,亦无不具备太极。这种关系,南轩认为,就是程伊川所说的性与气之间的关系,即性之本一,而其流行则各异,此即既论性又论气;万物之性各异,即太极流行各异的表现,而其本原则一,此即既论气又论性。如果割裂开来,或只看到其中一面,则要么只强调太极之性的本一,而不能认清人物之不同,从而太极只是一无用之体;要么只看到人物差异,而不能认定其性之本原为一,从而太极之体无从显立。值得注意的是,张栻论“性之本一”与“人物气禀万殊”的关系,不是静态地看二者的关系,而是动态地强调“流行发见”的作用,并由此而提出“物物各具太极”之说。他在《答胡伯逢》中说: 或曰:天命独人有之,而物不与焉。为是说者,但知万物气禀之有偏,而不知天命初无偏也;知太极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极也。故道与器离析,而天地万物不相管属,有害于仁之体矣。谓之识太极,可乎?不可不察也。[25] 按,张栻此说实质是针对胡伯逢始终怀疑他的《太极图说解》所谓“物虽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极之所以为极者,亦何有亏欠乎哉”一说所作的进一步申说,也含有批评胡氏的意思。在张栻看来,从流行发现的意义上看,则太极之一与万物气禀之殊可以得到统一,而道与器也是相即不离的关系。这里,尤其“物物各具太极”一说,与朱熹所谓“一物各具一太极”,极为相似。 由性气关系,张栻进一步讨论到未发与已发。其《太极图解后序》云: 先生(周濂溪)诚通诚复之论,其至矣乎!圣人与天地同用,通而复,复而通。《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同只是此理。人与天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得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尔。[26] 按,此段引文自“《中庸》”以下至末尾,出自《延平答问》李侗答朱熹问“太极动而生阳”一节,只是略有删节而已。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一亦收录张栻此序,于“《中庸》”以下至末尾的李侗答语无一字删节。以行文简洁顺畅及表达张栻本人的思想来看,当以《补遗》本为胜。在张栻看来,从纯粹的形而上,也即“天地之本源”的立场来看,太极本体只是理,是“至静”的。此太极及太极动而生阳,就人身上推寻,可以《中庸》喜怒哀乐已发未发言之。喜怒哀乐未发已发即是性之中,性之和,未发已发可以对应于太极之体的动静,因而可以说太极“本体贯乎已发与未发而无间”。张栻援引李侗的说法,并不是假借之说,而是实证之说,即从未发已发来体察太极之动静,从本原与分殊来体察性之本一(即太极)与人物之性各异的关系。而这也表明张栻吸收了道南学派的某些思想主张。 张栻以性论太极,无疑是受到胡宏性论的影响,而论性之本一与万物气禀之殊,则是采用程颐的说法。关于太极本体贯穿已发未发而无间的论说,则有李侗的影响在。所有这些,都在其《太极图说解》中有所体现。不论以太极为至静之体,还是以性论太极,张栻都强调太极“流行”的意义。这是张栻《太极图说解》的一大特色。朱熹《太极解义》则以理气关系为主导,建立起以理气论为基础的哲学架构。二者有诸多的不同,但以《太极图说》与《通书》相参互解,则是一致的。 总之,张栻《太极图说解》关于太极的诠释与论说有其独到之见。从纯粹形而上的理世界言之,太极之体至静。从流行发现言之,太极之动静生阴阳、五行、万物,此意义之太极贯穿动静,遍存于万物,而万物各有气禀,故太极与万物之间又有着性之本一与气禀万殊的关系。从心性论言之,太极本体(也即性之本体)的动静,可以从喜怒哀乐未发已发的角度来理解。张栻所谓太极之体与太极之性,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 注释: ①关于张栻《太极图说解》的研究,目前仅有苏铉盛《张栻的〈太极说〉》(陈来先生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第372-403页),苏氏此文是迄今关于张栻《太极图说解》较全面的研究论文。本文尤为关注张栻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及其思想意义。 ②朱熹的主张也得到吕祖谦的积极响应。《与朱侍讲》(十六)云:“《太极说》竢有高安便,当属子澄收其板。”(《东莱别集》卷七,《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237页上。) ③张栻注解援引朱熹注解的两处文字,一处为:“太极立则阳动阴静而两仪分,两仪分则阳变阴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乎天者也。”另一处为:“有是性则有阴阳五行,有阴阳五行则有人物生生而无穷焉。凡此,皆无极之真者也。(引者按,真,原作具。显误。)阴阳五行经纬错综,混融无间,其合妙矣。于是,阴阳又各以类凝结而成象焉。阳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布其气也;阴而顺者,母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质也。”(《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三,《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8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按,这两段文字分别对应于通行本朱熹《太极解义》第三章、第四章,然文字出入较大,当是朱熹后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