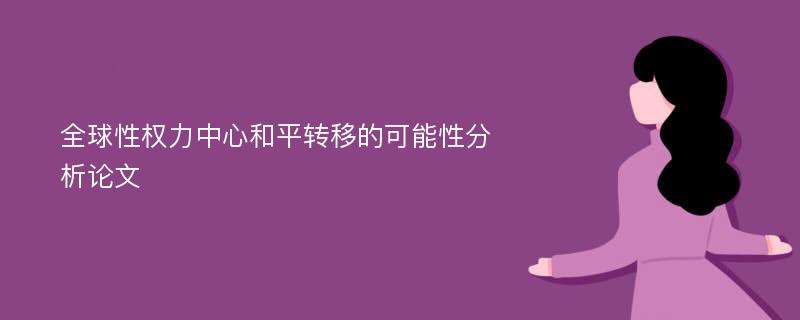
政治学研究
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分析
乔 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 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引发了国际权势对比格局的变动,进而导致权力中心的更迭转移。这一过程往往贯穿着新兴权力中心与既有权力中心之间的冲突、对抗。这一国际政治现象,为许多世界史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所关注。辨别区分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区域性权力中心的概念,明确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同其他层次权力中心转移的不同特点,就可以用超越既有理论范式的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上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一般性机理,以及转移过程中的竞争者与冲突战争等因素的特殊意义,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于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的原因与可能性的理解。伴随着世界历史上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数次转移,全球性权力中心自身变得更为复杂成熟,加之当今国际环境的变化,这种转移正日益趋向和平的方式,然而最终能否实现和平转移,还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外交水准和战略选择。
[关键词] 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竞争者;外交;战略
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兴衰,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中心的不断转移,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相关理论范式譬如奥根斯基等人的权力转移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吉尔平等人关于大国兴衰的论述,等等,都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基于西方视角的理论分析,大都存在几方面的问题:首先,目前大多数理论对于历史上权力中心转移的次数,特别是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同区域性权力中心转移之间的区别,没有足够的辨析意识,分析对象范围不同,定义标准相互矛盾混淆,难以得出一个实用结论。其次,这些理论一般都采取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和相关概念,虽有部分涉及了地缘政治,但是几乎都没有深入涉及国家的外交调控、战略操作这些重要方面,政治对策指导性不强。最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当今的国际体系环境也同以往大不相同,权力中心转移的特征和形式,也将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而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范式标准的这些理论,对于当今全球化时代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借鉴意义有限。因此,本文将厘清全球性权力中心同区域性权力中心之间的区别,并通过对历史上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一般机理的归纳分析,结合对国家外交、战略方面操作实施的分析,从基于非西方的视角范式角度,力求更好地探讨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的可行性。
一、全球性权力中心在历史上的两次转移
目前研究权力中心转移相关问题的学者,往往对历史上存在哪些权力中心,全球性权力中心究竟发生了多少次转移,存在论述不清或互相不一致的问题。现有理论大多是以广义上的欧美作为选取出发点,往往混淆和忽视了区域性权力中心和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区别。全球性权力中心不同于区域性权力中心,它的影响空间应当超越局部地理区域,乃至在全球层次上拥有影响力;它的能力既来源于强大的远洋海上力量,也来源于一定规模的陆地武装;它的实力要素综合而多面,对他国的影响手段和对世界的治理方式巧妙、高明而节约,并且拥有在文化、观念上的吸引力。当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时,就可以称其为全球性权力中心。不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权力中心,就只是一种区域性权力中心。世界历史上符合全球性权力中心条件的,有如下三个国家: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而葡萄牙、荷兰等案例,只是欧洲区域性权力中心。因此可以看到,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在历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两次,先是从西班牙转移到英国,而后又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一)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全球性权力中心
西班牙作为诞生于民族国家体系早期的一个“原初性”全球性权力中心,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后半段,不到百年内的急速崛起与衰落,他的国家事业巅峰是极为短暂的,这或许也是其全球性权力中心地位受到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西班牙经过了近半世纪的国内整合与海外扩张,在16世纪中叶的确建立了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法国、英国都在窥伺着它的海上霸主地位。在君主伊丽莎白一世的默许甚至鼓励下的海盗活动,劫掠西班牙往返美洲的金银船队,同时也利用新式造船工艺与工商业,对西班牙的海上优势发起强有力的竞争。属地葡萄牙与尼德兰也在不断反叛独立,烦扰牵扯着西班牙的精力,不断地在“让帝国流血”[1]40。同时在陆海两个方向面对分别来自英、法的竞争,西班牙帝国的权势技术基础,尤其是海上垄断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与损害。其最具象征意义的决定性一刻,就是无敌舰队征英的失败。由于战法落后和指挥不当,无敌舰队在海战中惨败于灵活而火力强大的英国舰队,西班牙损失了海军力量的主力,海上霸主的地位很快就被英国取代,加之随后陆地战场的失败,标志着其开始丧失全球性权力中心地位。
《分析试验室》1982年创刊,目前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分析化学专业刊物。影响遍及冶金、地质、石油化工、环保、药物、食品、农业、商品检验和海关等社会各行业及各学科领域。《分析试验室》以突出创新性和实用性为办刊宗旨,作者来自全国各行业的生产、科研第一线; 已被列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用期刊、美国“CA千种表”中我国化学化工类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国内外多家检索数据库、文摘收录,影响因子连续多年列化学类前列。
英国则不断地壮大自身的海上力量与经济实力,在国内解决了宗教纷争、苏格兰问题和改革阵痛,对外战略上利用欧陆均势、灵活外交和重商主义,逐渐从众多的竞争者(如奥地利、荷兰、法国等)中脱颖而出。通过两次挫败路易法国和波拿巴法国的企图,英国极大地巩固了自身优势,并通过工业革命,进一步确定了其领先地位。到19世纪中叶,尽管本土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2%,但英国的煤产量和棉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钢产量占53%,工业制造品与贸易量占世界近三分之一。伦敦作为当时全球金融无可置疑的中心,流通的对外投资达到世界总额的四分之三。[2]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的皇家海军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海军的总和,是全球各大洋上不容挑战的绝对性军事存在,拱卫着大不列颠的全球性帝国。世界上鲜有国家像英国(以及随后的美国)那样,在一个国家身上体现出工业、贸易、金融、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近乎全方位的综合性领先地位。
尽管英国在击败法国的两场重要战争中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然而就在两场战争期间,由于政策上的不当、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和战争造成的损耗,英国失去了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而历史终将证明,独立战争的失败对于英国来说,是最致命的失误。由于美国具备的潜在规模、资源和发展空间,都是其母国英国的放大与升级版,北美十三州的独立与巩固,实际在相当意义上就已经注定了日后英国的命运。随后的一百多年里,英国的全球性权力中心地位,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二)英美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历史
从美国独立之日算起,到二战结束,英美之间的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经历了好几个历史阶段。从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开始,一直到1815年根特条约的签订,两国处于大体敌对、冲突与对抗的阶段。期间由于较为亲英的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等人的外交斡旋,两国在1796到1806年间也曾有过不到十年的相对和平相处的“小和解”时期。但是在杰弗逊和麦迪逊任期内,先后出现了中立权地位纠纷、纽芬兰捕鱼权问题和“切萨皮克”号遇袭事件等冲突,英美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最后甚至在1812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连新首都华盛顿也被英军占领,白宫等政府建筑也被烧毁。最后由于两国外交上的谈判交涉,同时英国期望在拿破仑战败后能够迅速恢复和平局面,美国才勉强度过难关。
战败后的美国,严守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教诲,不再在加拿大等问题上激怒英国,集中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并且客观上利用英国海上优势力量的庇护,免于受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战争威胁。从1815年到1865年间,是英美表面上相安无事,经济上往来日益紧密,但是政治上仍然怀有冷淡敌意的阶段。美国利用这一段时间,将领土扩展至太平洋,同时通过内战解决了困扰自身多年的奴隶制和南北对立问题。虽然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自己的巅峰时刻,然而脱胎换骨后的美国,在治疗了战争创伤后,很快就将发展赶超英国。
2.5 儿童营养状况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分析方法,引入变量的检验水准为P=0.05,剔除变量的检验水准为P=0.10。以婴幼儿是否贫血、生长迟缓、低体质量(二分类资料)作为因变量,将性别、民族、婴幼儿月龄(原始数据)、母亲年龄及母亲职业等10个因素作为自变量,筛选影响婴幼儿贫血、生长迟缓及低体质量的主要因素为民族和婴幼儿月龄,见表2。
许多学者将1865—1914年,即英美不断从分歧走向和解,直至确立同盟关系的历史,称作“大和解”(The Great Rapprochement)时期。[3]随着美国的不断发展与英国优势地位的逐渐丧失,自治领加拿大又仿佛人质一般被美国威胁,英国发现自己同美国开战的风险越来越大,弊也愈来愈大于利。同时,大英帝国还要面对数个新兴大国对自身日益巨大的压迫,因而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和相对的孤立无援。对一个日益衰落中的英国来说,如果既要在欧陆遏制老对手法、俄,又要应付新近崛起的德、日,同时还要跨越大西洋同美国大打一仗,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因而英国对于美国的态度,是退让和争取为主。美国虽然在中南美洲有过一些冒失举动,但很快对英国的信号心领神会,在态度上也变得和缓与收敛。到了世纪之交,随着英国的进一步衰落和美国开始了对自身的军事武装,争取美国作为一个盟友而不是敌人,已经变成英国唯一较为现实的选择。这一阶段其实是英美全球性权力中心实现和平转移中尤为关键的阶段,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从1914年到1945年间的“新三十年战争”阶段,英美之间开始了西方学者所谓的“世界领导权”的传递。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并肩作战,不但强化了两国间的亲密关系,还通过战争拉大了彼此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虽然在1919年到1939年那充满危机的二十年中,由于美国重返孤立主义,英国又在表面上延续了自己“虚假”的全球性权力中心一段时日,但是这一不正常的幻景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英国再也难复往日荣光,甚至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后,逐渐沦为美国的跟班者。经过世界历史上全球性权力中心的两次转移,美国作为上一个全球性权力中心,到目前为止依然享受着相对较为优势的地位,然而随着全球性权力中心不断地向大洋彼岸转移,未来的全球性权力中心或许是不断发展上升的“印太”地区国家。
二、两次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一般性机理
历史上两次全球性权力中心的转移之间有很多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可被视作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所应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共性,审视这些特征,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因为后者只不过是前者在方式和表征上的一种具体的形式或方向。或许无法完整准确剥离出那些导向和平形式或方向的绝对因素,但英美之间实现和平转移的成功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蕴含和体现的一般性机理。
(一)国家间权势格局的变动
权力中心转移能够得以发生的最基本前提是国际体系中国家地区间权势对比格局的变动。在各种复杂原因的交织下,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的发展速率会很不一致,从而导致权势对比格局的变动。一个国家无法永久地拥有和保持自己的优势性地位,尤其是面对来自整个世界舞台的竞争时。全球性权力中心所凭借的领先世界的先进技术,或早或晚将扩散到其他地区,从而使其丧失了技术垄断优势,而对老旧的技术、制度的依赖与惯性,又使其无法像新兴地区那样及时顺畅地引进新的技术,因而总是易被具有“后发优势”的新兴国家地区所赶超。同时,随着全球性权力中心发展到鼎盛,往往面临着“过度伸张”的困境,这既包括成本、代价的日益高昂,以及经济发展势头的相对下降,[4]更突出的问题是,为了护持遍布全球的利益和秩序,往往背负着日益沉重的军事维护开支。当原有的全球性权力中心逐渐失去自己在经济技术上的优势之后,其领先地位也自然被更具优势的国家所取代,而后者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全球性权力中心。
(二)新老权力中心之间的互动方式
计算机信息化教育已经在我国初步发展起来,但仍远远不够。要想深化计算机信息化教育,我们的政府应该详细制定相关的政策并加强引导,支持建立专业计算机信息化教育机构;学校与企业之间应该加强合作;教师更应该转变现有的观念,加强计算机信息化学习,改变教学方式。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计算机信息化教育必将成为我国教育的主流模式,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使中国在世界科技之林中立于不败的位置。
之所以说它们之间实现了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是因为两者没有作为一场战争中的直接冲突双方或主要敌手。它们之间尽管有过冲突、对抗,甚至在局部战场的兵戎相见,比如英美之间的两次早期局部战争,但是在那些根本性决定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关键性战争中,它们一般只是作为阵营中的一员参与战争,战争的发起人和主要冲突方也往往是那些现有全球性权力中心的竞争者。未来的新全球性权力中心虽然也是竞争者之一,但是似乎都没有选择站在直接对抗的前列,它或者选择中立,利用战争机会扩大自己在经济或其他方面的优势,直至静待最后一刻突然发力;或者干脆选择作为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的盟友,共同对抗其他竞争者,将彼此间的分歧冲突向外投放发散,从而使两者间实现相对友好与缓和。而那些选择与全球性权力中心直接对抗的竞争者,通常不是惨遭围攻而遗憾失败,就是同前者两败俱伤,进而促成了隐藏在后列的“静悄悄的竞争者”成为新的全球性权力中心。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感受到前列竞争者相对更为明显的威胁,会优先选择遏制前列竞争者,与它们爆发冲突战争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大。
对照组-男、女占比各为29:21;年龄段在27岁至88岁之间,经计算后中位年龄为(57.98±1.64)岁。
冲突和战争往往带来三个结果,那就是大部分竞争者的失败,全球性权力中心权势的严重削弱,以及新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浮现。当一个较为成功的后列竞争者实现了获得优势性地位的目标后,它将面对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治理任务,通过成功挫败再度涌现的竞争者,可以提升自身威望与信用,巩固自身的全球性权力中心地位,同时还要制定有助于护持自身利益的制度与政策。然而这些制度与政策具有双刃效应,伴随着技术扩散与新科技的涌现,它们在维护全球性权力中心稳固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国家通过享用现有成果来发展自身,客观上培植了众多“搭便车”的潜在竞争者,从而造成优势的逐渐丧失和自身的相对衰落。同时在全球性权力中心的中晚期,还往往产生“过度伸张”的困境,即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和秩序,不得不选择进一步加强控制和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结果反而极大地损伤了自身的权威。选择“调控衰落”的全球性权力中心则一方面要处理权势处于衰落的危机现实,另一方面还要同时面对多个新兴力量的竞争与挑战。[5]由于自身日益衰落的权势,以及相对有限、分散的精力与资源,全球性权力中心经过权衡思考,决定遏制那些对于自身威胁更大的、态度更为刚愎的竞争者。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全球性权力中心能够成功挫败竞争者们,稍稍延长自身寿命。一旦国家间陷入冲突战争,就会导致权势都遭到极大的损伤与削弱,而那些损伤较小或明智地置身事外的国家,就能利用这一残局,成为新的全球性权力中心,从而开启新一轮的过程。
在英美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中,两国的外交水平与战略操作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汲取、研习它们带给我们的历史经验,能够给那些可能面临未来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国家外交和战略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有益的启发。
北区酒店布局较分散,地下2层酒店配套用房主要为酒店布草间、洗衣房及员工更衣室等,7层为酒店厨房及餐饮区,8~9层为酒店健身及室内游泳池等,11~24层为酒店客房。
(三) 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中的竞争者
我们发现,在上面总结出的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一般性机理中,都出现了一个名词——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在历次争夺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激烈竞争中,扮演了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多重角色。一方面,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通过挫败某个竞争者的图谋,不但解除了竞争与威胁,相反还往往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全球性权力中心地位,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自身的权力中心寿命;另一方面,当同时面对多个竞争者时,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往往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资源与精力上捉襟见肘,即便能勉强挫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竞争者,却也极大地损耗了自身的能力,从而导致权势地位的进一步衰落,甚至其全球性权力中心也被其他竞争者所渔获。全球性权力中心和竞争者之间互动的不同结局,既取决于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自身权势是正处于上升或衰落时期,也同竞争者自身的权势变动与数量有关。竞争者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同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的权势对比及策略选择。成功的竞争者往往能够成为新的全球性权力中心,失败的竞争者则为了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巩固,抑或为了新全球性权力中心的登场,扮演了自身悲壮而独特的角色。
新兴的未来准全球性权力中心,其实往往本身就是竞争者之一,而且是最终取得成功的竞争者。它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获得全球性权力中心地位,一般都多少采用了追随、搭车、不出头这三大战略。准全球性权力中心通常即便不是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的盟友,至少也在行为上展示出支持与顺从(或中立)的态度,避免同全球性权力中心进行直接的敌对和冲突。利用和享受全球性权力中心营造的和平环境、制度便利与技术扩散,来为自身的发展服务。成功的竞争者(或者说叫“静悄悄的竞争者”)总是力图避免过早引起戒心,招来遏制、对抗甚至战争。这需要在经济竞争、军事发展和外交决策上尽可能地隐藏锋芒,蛰伏在看似更咄咄逼人或更富攻击威胁性的其他竞争者之后,令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更加关注它们的崛起与挑战,从而有效地保护好自身的发展,可能的话还可以坐收渔利。
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都曾采用过上述这三大战略,尤其运用得最为巧妙与高明的是第三个。当西班牙忙于应付法国和其他势力的挑战时,英国抓住乱局起而得手,美国则一直利用英国的海军力量将自身隔绝在欧陆纷争之外,专心于自身的发展整合,同时享用英国的先进技术后来居上。即便在国力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越英国的“大和解”时期,美国也迟迟没有扩充自己的海军,战略上也保持相对低调,尽量避免同英国发生激烈冲突,藏身于其他国家之后静待时机。这就使得英国在面对挑战自身的俄国、德国、美国和日本时,优先选择了遏制德国、日本等国,并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同德、日等国两败俱伤。美国则从幕后冲上前台,抓住战争带来的机遇和英国权势大为衰落的事实,夺取了全球性权力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英美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激烈的对抗与争霸战争,实现了较为和平的转移过程,跟美国较为明智的外交战略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英美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有着地缘、文化等各种复杂的原因,然而美国的较为低调审慎的外交战略,显然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对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可能性的思考
(一)英美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是一个特例吗?
发生在英美之间的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究竟是一个特例,还是一项具有推广价值的模范案例?不得不说,由于在民族国家体系产生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史中,三个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只发生了两次转移,而其中和平转移也只大致是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英美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这一历史案例,有陷入研究孤证的可能与危险。但是,英美案例中所体现的那些促成和平转移的机理因素并不是孤案,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国际政治现象之中。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本能够,也本应该和平转移,只是由于当事国们外交与战略的不当,才走向了冲突战争的道路,使非和平转移成为了常态选择,和平转移反而成为了“特例”。英美“大和解”的案例是一个很具学习性与启发性的模范案例。
这些观点可能会跟人们一般熟知的结论大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而历史会给这一推断提供丰富的佐证。通过对历次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以及竞争者们所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知道,真正成功成为新全球性权力中心的竞争者,往往并没有同老全球性权力中心进行直接对抗。它们或者保持中立,置身事外,或者干脆成为老全球性权力中心的盟友,而不是敌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规避遏制、对抗与战争。这是因为一旦同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或战争,不但会极大地损伤自身的权势和发展机遇,更有可能会葬送自己奔向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前途。明智而富有远见的竞争者往往会选择低调行事,做一个“静悄悄的竞争者”,尽量不制订可能会与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发生核心利益冲突的战略,在非核心利益纠纷上则果断灵活地利用外交调控、协调。而恰恰是那些战略上冲动、短视、幼稚,外交上嚣张、僵硬、拙劣的竞争者们,总是试图直接挑战老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权威与权力中心秩序,最后被卷入孤注一掷的战争中,不但自身的挑战遭到挫败,丧失了问鼎全球性权力中心的资格,同时对老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权势也进行了极大地削弱,为“狡诈”地隐藏在自己身后的“静悄悄的竞争者”摘取果实铺开了悲壮的血路。历史上这样的所谓反面例证多如过江之鲫,因而也就一定意义上使我们摆脱了孤例、特例的危险。
(101)拟波氏羽苔Plagiochila pseudopoeltii Inoue,Bull.杨志平(2006)
通过对历史上三个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横向对比分析,全球性权力中心自身的形态特征经历了不断的发展演化,已经变得愈发地复杂与成熟,治理全球的方式也越发隐性、高明与节约,并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趋势。这部分地源于全球性权力中心本身的“进化”,导致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转移的特征也随之发生演变。此外,伴随着世界历史推进,全球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历次转移一次较比一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更复杂的图景,最为显著的就是随着时代发展,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所涉及的因素的演化。
站在将军身旁的医者“啧啧”连声:“你这伤当真是不简单,狼牙回锋箭,淬了唐门镇魂毒,发箭之人用的恐怕还是武当正宗的混元一气。搞不好,这人还练过影州密传的玄冰策,你的仇家这次可真是下足了血本啊。”
(二)当今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因素的演化
审视历史上出现过的这三个全球性权力中心,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可以发现三者在空间上的承接轨迹。它们各自的权势中心(即本土)展示出一个不断西移的过程,先是在伊比利亚半岛,随之西移到英伦三岛,最后跨越大西洋,到达北美大陆,而且在地理规模与地缘性状上,也发生了从半岛到群岛,再到洲际岛的扩大与转变。除却横向的比较外,全球性权力中心在历史纵向上也显露了某种程度上的演变或者说“进化”。新的全球性权力中心较之被它取代的旧有全球性权力中心,其自身发展更综合、全面且平衡,在空间维度上要更拓展稳固,在时间维度上要更稳定持久,治理手段与战略实施也更丰富、高效、经济、巧妙,各个地区更有凝聚力,技术工艺更为先进,产业规模更宏大,意识形态、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更富影响力。全球性权力中心在一次次的更迭之后,其形态不断发生着“进化”,不断走向成熟。随着全球性权力中心自身的愈加发展、成熟,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的转移也将随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并对转移的具体方式产生很多新的影响。
尽管新老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能够实现和平方式的转移,但是这不意味着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整个过程是没有竞争的。历次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历史,或多或少都伴随着国家间的分歧、冲突,甚至爆发战争,新老权力中心地区亦都曾被多次卷入其中。
全球性权力中心的转移是实质上发生在新老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的过程,而冲突战争是老全球性权力中心同失败竞争者两败俱伤的另一个过程,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正像英美之间尽管实现了和平转移,但没有人会否认转移期间发生了战争即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可能伴随着战争,但是战争并没有发生在新老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它们之间的转移是相对和平的。这其实也就是说,只要满足英美间导向和平转移的那些要素,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在相当程度上就可以再度出现,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依然取决于国家的外交与战略。全球性权力中心之所以没有实现和平转移,那一定是在某些环节(或者是外交,或者是战略,或者兼而有之)中发生了疏漏或失误。同时,随着当下全球环境的变化,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本身也在日益倾向于和平转移的方式。
西方理论范式某种程度上基于冲突对抗和周期循环的悲观视角,也不完全符合当今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国际政治现实,更难以适应今后世界政治发展的时代趋势。随着“印太”等新兴国家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兴起,西方对于话语权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和质疑。“西方方案”或者说“西方范式”,某种程度上可能无法代表和反映广大非西方新兴国家地区的历史传统、政治现实和文化模因。以G20、金砖国家为首的很多非西方国家地区,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世界政治和权力中心转移的认知理解和解决方案,譬如“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提法,就是对于局限欧美中心视角的旧有西方理论范式的超越。通过对非西方理论范式的解读和应用,可以发现权力中心的和平转移并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异常”特例,而是世界政治在今后应当奔向的合理时代趋势。
在早期的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中,譬如西班牙与英国之间,军事和地缘等传统因素曾起着极其重要的(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到了后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不但经济相互依赖、文化观念互动、国内制度舆论、大众民主政治等新的因素开始介入全球性权力中心的转移过程,而且其所占权重也在不断加大,日益显露出其重要性。军事、地缘因素比重大大缩减,优先序列下降,但依然发挥着极为关键的后备性作用。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成了新时代的主题和特征,国家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从竞争与对抗,转向合作与共赢,世界政治日益成为一个人们享有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其他新近出现的因素亦不可被完全忽视,譬如说各种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为国家间处理利益间的矛盾,实现合作共赢,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平台,对国家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施以更多的制约。核武器的问世和发展,使得战争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间特别是拥有核国之间的战争,将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所有这些新的时代因素,都一定程度上为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方式和特征提供了更多的制约和可能。随着全球性权力中心本身的日益复杂、高明与成熟,同时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这一过程本身愈发为多种综合性环境因素所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和平转移方式的实现的可能性,也将变得越来越大。
简论花山文化及其后申遗时期的研究策略 ………………………………………………………………… 王建平 陶志红(3/72)
(三)西方权力中心转移理论范式的超越
之所以英美在历史上的和平转移案例,看起来像一个不可思议的特例,恰恰是由于现有的权力中心转移理论或者范式,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局限性,需要对其适当地批判乃至超越,采取全新的不同视阈加以分析,才能够发掘出更多和平转移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现有的各路权力中心转移理论范式,基本都是基于欧洲中心或者说是欧美中心的视角,对于权力中心选择分类的标准,也是基于某种程度上的“西方标准”,因此在概念和案例上都存在混淆和偏颇,这种分析层次的偏差与错位,势必会影响相关一系列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众所周知,欧洲中心乃至西方中心的理论范式,对于当下国际政治研究,是一种带有严重主观偏见和理论局限的分析视阈。世界史近年来的崭新研究日益表明,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文明史,本来就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地位平等的文明中心,或者说影响力中心,仅仅选取欧洲历史经验案例,并试图推而广之,来解释多样并存的各种文明中心的理论尝试,注定是削足适履,并且也不利于对于其他地区权力中心的理解和研究。
其次,现有的权力中心转移理论范式都大致认为权力中心在转移的过程中,冲突与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发生的“常态”,即便新老权力中心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冲突对抗,历次权力中心转移也必然伴随着震荡整个国际体系。因此,在这种相对悲观的论调下,英美间实现和平转移的历史案例就会显得不合“常理”。然而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演化,未来权力中心之间的转移很有可能在同一个国际体系格局之内实现和平过渡,而不必然要推翻旧有的国际格局,建立新的格局,权力中心也很有可能不止局限于一个或者一种。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未来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日益显著,未来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兴大国关系”,甚至“人们命运共同体”,[6]这种崭新的国家间互动方式,使得一直强调国家间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西方主流范式理论,日益面临解释力的局限与苍白。
观察与比较两组心绞痛临床症状疗效及心电图疗效。(1)心绞痛疗效评定标准[3] 。治疗后心绞痛症状降低2级,Ⅰ~Ⅱ级者心绞痛消失,不用硝酸甘油,即显效;若心绞痛症状降低Ⅰ级,硝酸甘油减少幅度>50%,Ⅰ级者心绞痛消失,不用硝酸甘油,即改善;若硝酸甘油用量没有改变,症状没有改变,即无效。(2)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如果静息心电图已正常,在次级量运动试验方面,已经从阳性转变为阴性,或在具体的运动乃量上升高至Ⅱ级,即显效;若经次级量运动试验,得知心电图缺血性ST段有明显压低,治疗后升高>0.5 mv,但没有恢复正常,即有效;若相比治疗前,次级量运动试验心电图与之相同,即无效。
(四)对于国家外交与战略的思考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今天,全球性权力中心本身的日益复杂、高明与成熟,同时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这一过程本身愈发为多种综合性环境因素所作用,和平转移方式的实现变得越来越成为可行的方向和选择,这可以说是为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打开了另一扇新的大门。但选择是否通过此门,即全球性权力中心能否最终实现和平转移,还要取决于参与这一过程的各个相关国家地区外交调控的手段与水平,以及国家战略的制定与操作,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和平之钥仍然主要握于国家的外交策略、历史眼界和战略抉择。
在过去的“十二五”计划里,我国疾控机构的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仍然暴露出档案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和数量不足的问题。由于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在我国的进展比较晚,所以我国常用的档案整理电子办公设备、相关的档案数据库、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硬件和软件系统等等都比较缺乏,这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疾控机构档案管理的效率。
一是在在外交方面,英美外交一个非常明显的传统与特点,就是善于将分歧争端诉诸于仲裁调解,并可以根据、遵循已往成功的先例,将调解程序规律化,从而大大加速争端的解决。处理冲突与争端的具体外交途径,也尽量不采取军事解决的次佳方案,而是将其仿照民事司法争端的方法加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两国外交人员极具创造性的贡献。
要锻造优秀的外交团队和合理的外交政策,需要外交部门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以及较为专注的职权,从而尽可能地摆脱国内权谋斗争和官僚政治对外交的不利影响或损害。在当今民众普遍参与的大众政治背景下,则要设法引导大众舆论为外交所用,同时也要有敢于直面群氓压力的气度。优秀的外交要做大众舆论的主人,而不是反被后者牵着鼻子走。历史告诉我们,凡是任凭大众激情和民粹主义影响外交运作,一定会产生拙劣的外交和愚蠢的政策,而国家的命运也一定是凄惨而糟糕的。
外交官要明确外交目标的主次,优先解决最急迫的领域,避免将不相关的问题带入其中,给谈判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在外交的言辞、态度上一定要适切、慎重、富于理性。在外交谈判中,应当明确、厘清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在后一个领域要敢于和善于妥协,本着协调与和解的目的,在此大框架内为国家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外交队伍要始终牢记自身对国家前途所背负的重大责任,在言行举止上要不失机智、冷静与审慎。
不但在外交上要保持审慎的传统,国家在诸多领域的对外行为中,都应坚守这一宝贵特质:不是必须用国家前途来进行冒险的,尽量不诉诸冒险;可以不诉诸军事手段的,就不要急于使用军事手段,而是把它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在态度行为上没有必要采用高调强硬态势时,就不要自以为是地故作强硬。一个真正具有底蕴和魅力的国家,应当具备明智、审慎、低调、沉静的外交战略气质。
二是在在战略方面,对于国家战略的制定,首先要有明确、集中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较为清晰的方针与蓝图。在战略制定上要立足长远,具备宏大的眼界,预先为国家设定好未来长时段的战略方向,同时还要制定操作上现实可行的中短期目标。战略制定人员要较为准确地厘清国家战略目标的先后主次,摆正目标本身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战略的选择和操作,要始终以最有效地服务国家利益为衡量标准,也要同国家自身权势、资源、条件和能力相适应,并根据时局变化不断作出修正。
在战略的实际运行中,一定要注重策略,节约资源,避免陷入被动局面。真正巧妙、高超而明智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国家在充满变数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既要恪守既定的战略路线,又要时刻回顾已往的政策,不断作出反省、总结和调整,达到兼具笃定与灵活,从而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对战略细节与方向进行调控。
三是在外交与战略的良性契合。外交能够尽量做到在非核心利益上的妥协与协调,而在核心利益发生冲撞时,其能够回旋的余地则相对有限。为了避免发生国家间可能导致战争的核心利益冲突,应当不仅仅从外交上纵横捭阖,争取和解,更要在战略设计上,预先考虑到这些风险性因素,明确和限定好较为合理的核心利益范畴,不制定过于莽撞、冒进的国家总体战略,并为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时自身的外交斡旋保留有一定的余地。
外交是一个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决定着后者的质量和前途,而一个国家所制定的国家战略的素质,则可以从根本上极大地影响其外交调解的回旋空间。相较国际格局、地缘条件和历史环境等外在的给定因素,国家最能影响和掌握的就是自身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操作这些内在因素。一个正在兴起中的国家要获得最为顺畅的发展前景,把握好最为有利的历史机遇,一定要具备合理的外交政策和明智的国家战略。一个拥有明晰而理智的外交和战略的国家,确立目标冷静而务实,处理各项事务谨慎而细致,行事低调并留有余地,面对挫折变局极富耐心,善于等待把握历史时机。历史上历次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历史,尤其是英美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的案例启示我们,凡是注重培养这些素质的国家,往往能够逐步完成自身的发展累积,并最终实现自己的战略抱负。
四、结论
历史上各种西方理论范式对于权力中心的定义和划分,存在多种相互矛盾和混淆的地方,本文明确了权力中心应当分为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区域性权力中心,全球性权力中心在地理上是广域权力中心,在力量来源属性和权力中心特征上是复合权力中心,区域性权力中心则反之。历史上历次的权力中心转移,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在全球体系范围内的转移,也有区域性权力中心在地区范围内的转移,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有且只有两次,分别是从西班牙到英国,随后又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两次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相似,反映着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一般性机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性权力中心的转移往往发生在新老全球性权力中心之间,这种转移特别是英美之间的转移,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而冲突战争则发生在既有全球性权力中心同不明智的竞争者之间发生。[2]209
历史上全球性权力中心的历次转移,特别是发生在英美之间的和平转移,带给人们很多历史启示,而其中最为受用的,就是英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有着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大的国家战略设计图景,对于自身核心利益的定位也比较适当、准确与合理,同时有着坚定、长远的战略目标打算,并且在实施过程中认真、踏实,敢于反省总结自身失误,展现出能动、灵活、变通的战略操作。在这一基础上,英国和美国还注重外交上的谈判、斡旋与调解,在尽可能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如有必要,能够在非原则性问题上采取让步与和解的姿态,以规避冲突、战争,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创造出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两国也始终注重自身国家的发展和积累,从没有放松国内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军备的发展与建设。
国家总体宏观的大战略,要跟全球大环境相符合,顺应历史发展机遇,还要跟自身权势能力相契合,以免制定不合实际的战略目标,国家战略应清晰、集中、明确,要始终明了自己的任务、手段与目标,厘清不同目标的优先级与主次关系,坚守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并一以贯之地去笃行。无论是国家的兴起阶段,发展的鼎盛时期,还是相对的衰落过程中,都要始终拥有合理明确的国家战略,以及为之服务的具体策略,从而最有成效地争取国家权益。回顾历史上全球性权力中心转移的实际案例——英美和平“大和解”时期,或许可以得到实现未来可能的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较为关键的历史教益。
本组试验选取的数据为排水管壁试样直径d=100 mm条件下,3种土体分别在3种水力梯度下的试验结果(如图4所示)。图4显示:在试样面积、土体类型一致的条件下,与水力梯度i=6相比,水力梯度i=8时稳定梯度比Gr值增长了9%~15%,与水力梯度i=6相比,水力梯度i=10时稳定梯度比Gr值增长了24%~27%,稳定梯度比Gr值随着水力梯度的增大而增大。
[参 考 文 献]
[1] Modelski George.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M].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2] Temperley Howard.Britain and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M]. New York: Palgrave, 2002:60.
[3] Stephen R Rock. Why Peace Breaks Out: 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36-42.
[4]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1-160;161-188.
[5] Orde Anne.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Imperial Decline,1895—1956[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17.
[6] 戴长征.树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亚洲典范[EB/OL].(2019-06-18)[2019-03-10]http://www.cssn.cn/gjgxx/201906/t20190618_4919319.shtml.
[收稿日期] 2019-04-16
[基金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进教师科研项目“全球性权力中心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分析”(16QD11)
[作者简介] 乔亮(1987-),男,吉林长春人,讲师,博士,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9-0080-11
〔责任编辑:杜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