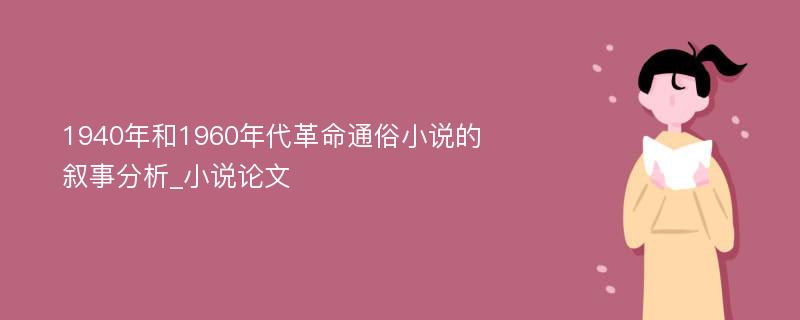
1940-1960年代革命通俗小说的叙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年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一起被视为创作数量最多、并且“达到的艺术水平”也最高的两类作品之一①。由于其在当代文学建构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因此50年代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有两个关键问题得到反复讨论,一是“革命历史”叙述与当代中国合法性建构的关系,另一即是这类小说大都采取的“通俗化”叙事形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历史内涵。 对于后一问题,许多研究或许过分关注其“意识形态”意味,而对“形式”本身的历史性构成分析不够。因此,常常笼统地将“革命历史小说”视为一个内在差异不大的整体性存在,较少勾勒其形成、变异与转化的历史轨迹。对“通俗化”形式本身,也缺乏足够的细致辨析,它常常是“民间”、“乡村伦理”、“传统”或“隐形结构”、“无意识”等的化身,而这一形式的内在差异,比如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比如英雄说部与武侠小说的分别等,及其如何被革命文学接纳,则较少展开历史分析。即便关于“革命历史”的具体指涉内涵,相关的理解也较为粗糙。比如很少有研究注意到,这类小说所讲述的“革命历史”,固然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不同时段,不过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尤有意味的是,除少数例外,那些被视为具有“传奇色彩”、“通俗化形式”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而那些“史诗性”的作品,则经常与国共内战的历史直接相关。 类似的问题经常被统摄于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中加以讨论,其关键在如何理解革命中国及其文学的性质,它是否“现代”,其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关系到底怎样?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将其指认为“古典文艺”或“封建文艺”,强调其前现代性②;1990年代后的“再解读”研究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凸显其现代内涵③,背后都涉及这一问题。本文将以革命通俗小说为媒介,力图更深入具体地重新探讨相关问题。 一 “革命历史”、“通俗化”叙述与“民族风格” 论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通俗化”问题时,评论家与研究者大致涉及如下作品: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1944)、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45)、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49)、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9)等。 将这些小说视为一种“类型”而展开的讨论,始于1957年《林海雪原》的出版。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很快便在《文学研究》《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出现了多篇评论文章④。侯金镜提出,新中国文坛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一种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上都获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品”,如《万水千山》《保卫延安》等;另一种则是“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但是因为它们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面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林海雪原》就属于这后一类作品⑤。何其芳也特别强调这部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革命斗争的“传奇色彩的情节”和这种“民族形式结合得好”,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⑥。王燎荧则判断《林海雪原》“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同时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⑦。 这些评论关注《林海雪原》的三个要点:一是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和资源,特别是如作者曲波提及的“三国”、“水浒”、“说岳全传”⑧等。由此导致其文本叙事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完整、人物特点突出、语言通俗易懂。这些特点往往被描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二是这种叙事特点,也造成了小说的缺点,即“思想性不深刻”,人物性格“单薄”、“不成熟”。所以,相对于“思想性”与“艺术性”更强的作品,它们无疑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当时的评论文章,一边为这部小说大声叫好,但同时也总会指出它在人物描写(如少剑波的个人主义)、情节构成(如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以及在表现“人民”方面的不足。三是这种小说的最大优点,在于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它“可以替代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⑨,“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⑩。 《林海雪原》之后,1958年出版了好几部类似的作品,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烈火金钢》(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敌后武工队》(11月)、作家出版社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2月)等。这些小说在讲述革命历史时,均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注重故事性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特别是《烈火金钢》出版后,引起了新一轮关于小说“民族形式”的颇为热烈的讨论。与《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比起来,《烈火金钢》的“民族风格”更直接地与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即新评书体联系在一起,这也使相关讨论能更深入到小说结构、叙述章法等层面去。这些评论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知识》等重要刊物上,因此可以将之视为与当时文学界有意识地发起关于《林海雪原》的讨论一样,是对文学普及问题与民族形式建构问题的进一步推进。 著名评论家侯金镜以“依而”为笔名发表的评论文章(11),首先从一份读者调查报告说起。如同曲波在创作谈中将文学作品分为两类并且褒贬鲜明(12),调查报告也提及读者更容易被“《水浒传》《三里湾》《林海雪原》”这类小说吸引,而对“《死魂灵》《子夜》《山乡巨变》《百炼成钢》”等则印象不深;进而概括出长篇小说创作的几条要求,诸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用行动来描写人物、语言通俗明快、叙述人的介入等等,其典范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的说部”,如“《水浒》、《三国》以及《说岳全传》”。侯金镜认为这份调查表提出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在创作实践当中的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与这一理论性问题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则是,“我们从五四以来虽然产生了许多好小说,但是在茶肆、曲艺厅、农村、厂矿里,讲述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书仍然始终不衰,甚至占有相当优势”。某种程度上,《烈火金钢》的成功也印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13)播讲的同名评书即在广播电台播出。有回忆文章这样写道:“1958年……不论大街小巷,或是穷乡僻壤,凡有收音机或大喇叭的地方,平头百姓都尖着耳朵听‘肖飞买药’。”(14) 在这样的评论视野中,有意味的问题不仅在小说的“民族形式”与五四式的新(西方)文艺传统之间的某种对立,更在一个特殊社会/文化群体的凸显,即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滋养的读者群,和他们在当代文学中所处的暧昧位置。一方面,他们代表着“人民群众”,“不积极地从民族风格方面去努力,就不能使新小说在劳动人民中大量普及并且生根”;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习惯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趣味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而使得在“普及”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既要“适合他们的欣赏口味”又“能够教育他们”。“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紧密地关联着这个暧昧的“人民群众”/“读者”群体。 蔡翔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提出,正因为“‘群众’这个概念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结构之中”,才导致了“当代文学的通俗化倾向”。但是,“群众”这一政治性概念和“读者”这一文学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读者’既来自政治的合法性支持,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某种传统”。蔡翔在这里引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某些传统文艺形式——这一形式包括古典文学、民间说书、曲艺、甚至口头故事,等等——的传播过程,已经构成了中国下层社会(乡村和城市)庞大的‘读者’群落,这一群落或许可以被称为某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安德森的理论正是指认出了这个“文化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15)不过,安德森虽然指出了现代民族认同与传统王朝国家、宗教共同体的瓦解及印刷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并没有具体讨论,在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构造的过程中,传统的“共同体”记忆如何发挥作用(16)。论及这一点,其实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区别于一般民族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西欧式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以前是农耕帝国后来却将它的政治凝聚性保持到了20世纪末的国家”(17),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有其独特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共同体经验与记忆,和现代国家认同之间,有着既连续又变异的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说,当代文学“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的暧昧处境,作为“读者”的文学趣味与作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身份之间的落差,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关联着帝国时代的文学传统和阅读经验,而“人民群众”无疑是一种现代构造。 中国古典小说资源及其塑造的文本叙事方式,经由无数已经内化并习惯这种文化趣味的“读者”/“人民群众”而延伸至当代中国的现实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是,这种传统美学形式和趣味固然可以被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不过仅仅有这样的形式与风格却不足以使文学成为“中国的”(特别不是“革命的”),因为这里所谓“中国”固然与古典中国文化记忆相关,但更是一项“现代的发明”。因此需要追问的是,古典中国的文化共同体记忆(文学形态及审美惯习、欣赏趣味),与革命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事实上,关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资源的位置,当代文学的主流建构者并非没有规划。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讨论并公布了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18),其中的三大构成部分分别是马恩列斯等“理论著作”、19世纪西欧与俄罗斯文学及苏联作品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作家需要吸纳的三种资源。与曲波及刘流等明确地倾向于“三国、水浒、说岳全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以求能接近“民族风格”不同,被认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更高”的《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则这样写道:“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19)显然,同样是叙述革命历史,为何《红旗谱》表现出比《林海雪原》等更高的“现代性”,或许关键便在文学资源的借鉴上,前者更多地吸纳西欧现代文学传统的缘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围绕通俗化、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问题,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肯定与倚重,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素养”问题,而涉及当代文学创作应当吸纳怎样的文学资源,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人民文学”这样的根本性理论问题了。 强调应当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凸显“民族风格”的小说观念,显然并不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等出现的1950年代后期才有的。当时,对这类小说的讨论,关联着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当代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理解,特别是与“大跃进”前后提出的新一轮文艺大众化路线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次讨论中,这种小说形态才得到了理论性的命名,并且以此为契机,这类小说在当代的历史流脉,也得到了明确指认。侯金镜、王燎荧在评论《林海雪原》时,已将之作为某种“类型”来看待;在评论《烈火金钢》时,侯金镜进一步认为相关的“有成效的努力”,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创作脉络。他提及的作品,赵树理之外,还有《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当这些于不同时间出现的作品被视为同一种“类型”时,“革命通俗小说”的命名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作品序列中,《铁道游击队》占有特殊的位置。这部作品出版的1954年,评论文章在肯定其“强烈的故事性”、“朴质的作风”(20)、“生活内容的‘新鲜别致’”与“惊险的战斗”(21)的同时,主要关注它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的真实性与历史意义,并对人物刻画的“简单化”和敌人描写的“漫画化”提出批评。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批评话语关注的重心是现实主义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这也使小说出版后的“畅销”与批评界的“冷淡”形成某种对比。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铁道游击队》在当代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话题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既是“滞后”的作品,也是“超前”的作品。说其“滞后”,是相对于1940年代出现的具有同类文本特征的作品,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说其“超前”,则是相对于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文本形态上,《铁道游击队》更接近于1950年代后期的作品:讲述对象为一支小型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性格鲜明,更具有“英雄传奇”的文体特点;而从创作过程来看,更接近1940年代的三部新章回体小说: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战斗英雄立传,相对更注重英雄人物的对敌斗争故事的全过程及其斗争经验。这两个时期的两种文本特色,被蔡翔概括为从“英雄”到“传奇”、从“真实”到“浪漫”、从“凡”到“奇”的变化(22)。事实上,1940年代三部以“英雄”为名的新章回体小说,与1950年代以“……队”为主体的传奇小说,还存在着许多差别,比如前者主要是从以“事件”为主体的英雄报道转化而来,并都曾在报刊上连载,因此其“章回体”形式与报刊传媒紧密相连;后者主要是以英雄群体人物为主、带有“回忆”和自传性质的写作,并且缺少报刊连载这一环节而直接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因素在影响作品的“真实”与“浪漫”、“凡”与“奇”的具体想象方式方面,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样时间上的变异过程,但两者仍旧有着更大的共同点,即借鉴古典文学资源以构造通俗形式和“民族风格”。如果说在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从1940年代的《吕梁英雄传》等到1950年代后期的《烈火金钢》等这样一个“革命通俗小说”的创作脉络,那么革命叙述与古典通俗小说因何、如何发生勾连的具体历史情境,就格外值得关注。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散布”着的诸种话语要素的耦合,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出现,而并非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便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方向,毋宁说,《讲话》恰恰是诸要素耦合而成的“新话语”出现的标志。历史研究的深入不是去追溯这一话语的“起源”,而是去探究“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如何“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23)。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去考察在何种历史情境中,古典小说传统与革命话语以何种方式发生了关联,耦合的诸要素发生了怎样具体的意义交涉。 二 “旧形式”与“民族形式”、“老中国”与“新中国” 在探讨革命通俗小说时,人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忽略,这里所谓的“通俗小说”并非现代的“通俗文学”,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旧小说”,即近代之前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作为革命中国“当代文学”构成部分的“革命历史小说”,其所借鉴的通俗小说传统并不是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而是前现代中国的小说传统。因此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下,革命历史的书写需要“调用”古典文学传统,或者说,古典传统如何进入到“当代文学”建构者的视野中? 洪子诚曾注意到,“言情、侠义、侦探等的通俗小说,是近代都市的文化产物。它们主要以城市中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为对象,在阅读上具有消遣、娱乐的‘消费性’”,但这种新型的通俗小说往往被五四新文学作家看作是“封建性和买办性文化的体现而受到排斥”。因此,他将“革命通俗小说”的出现,视为左翼文学大众化实践的一种“替代”性的产物。(24)李杨也提到,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中,通俗文学一直作为新文学的“他者”而存在。(25)不过,在五四时期,尽管存在如李杨提到的周作人对《西游记》《水浒传》《封神传》等作为“迷信的鬼神书类”的批判,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态度事实上并不统一。“白话文运动”的倡导中,一直存在着对传统文学“文白雅俗”的辨析,因而通俗的古典白话文学与现代的新文学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紧密关系,新文学的倡导者正是通过《白话文学史》(胡适,1928年)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年)这样的学术著作,而力图从传统中国历史中为新文学寻求合法性。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以“激进地反传统”而著称的新文学,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态度也并非一致。毋宁说,在打倒“野蛮的传统”与“再造文明”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事实上,比起现代性的晚清通俗文学,新文学与古典白话通俗文学的关系似更亲密,只是在“反封建”和吸取“民族文化精华”之间的分寸不好把握而已。比如,与周作人对《水浒传》等的激进否定态度不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事实上对其多有肯定。 自命为新文学运动继承人的左翼文学界,一方面如同新文学倡导者一样对现代通俗文学采取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对古典白话文学的态度则较为含糊。而值得探讨的是,直到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民族形式”大讨论中,左翼文坛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正面论述及基本评价方式才得以确立。 1939-1941年间发生于延安、重庆、香港、成都、桂林等地左翼知识界的“民族形式”论争,在塑造和构建当代革命中国与当代文学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汪晖所说,这场讨论中涉及的所有问题,都“围绕着‘抗战建国’和如何‘抗战建国’的‘民族’目标。文学及其形式在讨论中成为形成‘民族’认同和进行‘民族’动员的重要方式”(26)。其中,有五个关键概念成为讨论的焦点:其一是“民族形式”,讨论者都承认这是尚待创制的新形式,也是这次讨论的目标;而另四个则是藉以创制新形式的资源,分别为“旧形式”、“民间形式”、“地方形式”和五四新文艺。主要的争论发生在“民族形式”的创制应当是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向林冰等),还是应建立在“五四新文艺”的基础上或以五四新文艺为中心(胡风等)。最终的压倒性意见,则是陈伯达、周扬、茅盾、郭沫若、光未然等人提出的,在新文艺基础上吸收和利用“旧形式”而创制更高的民族形式。 在讨论过程中,“民间形式”与“旧形式”、“地方形式”的内涵与关系常常是含混不清的。所谓“旧形式”,常被认为是古典中国或正统或通俗的普遍性文艺形式,一方面与新文学之“新”相对,一方面与地方形式之“地方”相对;所谓“民间形式”则常指留存于民间的“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旧形式,与“正统”、“庙堂”相对。如茅盾认为,“民间形式”往往是指那些尚存活于民间社会的“旧形式”,因此,可以被包容到“旧形式”的范围内(27)。就其指涉的资源和对象而言,“地方形式”的涵义是相对清楚的,它指的是尚存活于某一特殊地域范围中的地方性文艺形态,与“全国性”相对,往往与“方言土语”、地方戏曲、地方通俗文化等直接关联。汪晖的文章《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正是从方言、语音中心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理论角度着手,探讨了论争过程中地方性的文艺与语言实践,如何仅仅是民族形式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如同西欧国家的方言民族主义那样,对普遍性的中国认同构成了挑战。但是,涉及“旧形式”、“民间形式”,问题就相对复杂,它们并不仅仅只在语言差异、地域差异、空间差异的维度上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发生关联。“创造文化同一性”特别是“创造超越并包容地方性和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同一性”(28),往往被视为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因为正是在将差异性“创造”为同一性的过程中,现代的民族认同才得以形成。但是,当“旧形式”与“民族形式”关联在一起时,涉及的并不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问题,毋宁说乃是“旧的文化同一性”与“新的文化同一性”,或“旧的全国性形式”与“新的全国性形式”的关系问题。这是远比“地方形式”更深地涉及中国历史独特性的问题。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厄内斯特·盖尔纳等人的民族主义理论中,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乃是一种彻底的“现代的发明”,它主要通过语音中心主义的方言运动而运作。在这种理论视野中,不存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同构的前现代共同体,而只存在文化与政治不一致的“帝国/王朝”或“宗教共同体”。但是,正如已有的许多理论研究指出的,这种民族国家理论乃是以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为模型的,它无法解释那些拥有漫长的“国家”历史和民族记忆的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欧式国家历史传统的中国。(29)因此,一种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民族认同更恰当的论述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既是一段历史悠久的文化建构过程,远早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时与西方势力交锋后的特殊产物。”(30)事实上,早在1987年的一次演讲中,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就将中华民族表述为“多元一体格局”,是“自在”与“自觉”的产物。(31)这也就意味着,考察20世纪现代中国认同,总是需要同时在两个面向上展开,一是与王朝国家的文化共同体记忆的关系维度,一是与现代西方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关系维度。探究这两者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到民族建构的历史方式,才是理解现代中国认同的关键。 具体到关于“民族形式”论争,需要意识到的是,正是在这次论争中,“旧形式”才得以作为“合法”的文化资源进入左翼知识界的视野,并确立了一套延续至50—70年代的话语体系。重新解读“民族形式”论争,需要意识到旧形式、民间形式、地方形式并非笼统的概念(如论争中大多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呈现出了不同的历史和理论向度,需要做具体的辨析。其中,特别是“旧形式”与“民族形式”建构的关系值得做更深入的讨论。这涉及中国共产党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建构民族认同,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地缘政治中寻求主体性时,如何与既有的帝国文化共同体记忆(特别是其现实性的负载者:广大内陆乡村社会和农民)建立协商关系,从而将自己确立为“历史的中国”的真正继承人(32)。这是比克服地域差异而构造新的共同体想象更重要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认同构成真正挑战的,并不是地方分裂主义或区域自治主义,而是如何与“历史的中国”建立真正的文化与政治关联。 关于“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都会提到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理论建构面向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向内,面向与同样自诩为“历史的中国”“继承人”的国民党,后者从1935年即展开“新生活运动”,以求诉诸“儒教中国”的民族传统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其二是向外,面向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内的亲苏教条主义者,他们仅仅将中国视为这一国际运动的区域性存在,而非民族—国家主体。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这种竞争性的政治主体关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背景下展开的。正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的,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构筑与成型,特别是民国以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方面,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学者柯博文(Parks M.Coble)认为,如何应对日本“巨大而无休止的压力”,对南京时代(1931-1937)的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促成了更加伟大的民族团结”。到1937年,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社会力量(33)。事实上,对于在抗日这一历史过程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并最终战胜国民党而取得中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民族主义是其内在的构成部分。毛泽东所说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意思。 从这样的历史格局再来看“民族形式”论争,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抗日战争中的民族主义、国际共产主义中的地缘政治、两种中国现代政治主体的角逐,以及人民战争的革命动员,是如何与文艺界关于民族文化认同的论争建立起关联的呢? 毛泽东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文艺界就试图将其转化成文艺问题的讨论,在一开始被作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式(34),或将其视为“旧形式”利用的基本原则(35),也有将其视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中国式转换(36)。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理论大师”的陈伯达,则以明确的方式对此做了统一的表述:“近来文艺上的所谓‘旧形式’问题,实质上,确切地说是民族形式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7)在这里,“旧形式”、“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虽然做了“无缝对接”,但事实上,真正关键的变化在于,这三种原本并非处于同一层次、场域的话语形态被置于“民族”构建这个共同话题之下。其中,改变最大的,莫过于“旧形式”话题。 “旧形式”的利用,是自抗战开始进行民众动员时就被广泛讨论的问题,不过这种讨论一直停留在较为实用主义的层面。所谓“旧瓶装新酒”,其中“旧瓶”的涵义是不清晰的,它假定旧形式如同“瓶子”一样是一种“空”而“固定”的形式,而忽视“瓶”与“酒”之间的一体性;同时也忽略了所谓“新酒”特别是抵抗的民族主义自身的构造性,而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产物。但“旧形式”作为问题的提出,又是如此重要,它是战争背景下现代中国社会结构性鸿沟的具体呈现。这种“结构性鸿沟”指的是都市与乡村、沿海区域与内陆农村、知识分子与农民、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巨大分裂。而导致这一分裂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下被迫展开的,主要沿东南沿海(江)的现代城市展开,而广大的内陆乡村则基本上仍旧延续着古老的帝国生存形态。这种分裂被王国斌描述为“两种类型的民族”的分裂:“一个属于崛起中的、受西方影响的城市精英文化,与属于仍然存在的大量农业人口的帝国文化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38)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的结果,便是将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从沿海城市驱赶至西北、华北、西南的内陆地区和乡村。当年周扬如此描述:“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的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39)因此,才有了新文艺工作者“认识老中国”、利用旧形式的诉求。 但是,将“旧形式”问题与“民族形式”直接挂钩,意味着讨论性质的飞跃,即:使有关“旧形式”的讨论,从实用主义的思路中摆脱出来,而纳入更高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规划中。“民族形式”这一理论问题源自一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视角,其立足点侧重于世界性、现代性的一面。问题不是从中国内部向外追求现代性(这是“启蒙”的视角),而是从现代世界格局向内来追求革命中国的民族性,即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世界文学,但却不能与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结合,于是生发出“民族形式”问题。因此,“两种类型的民族”的碰撞在这里导致的,就是如何融汇两种民族认同和文化共同体想象而创造更高的“民族形式”。 从“民族形式”论争到1942年《讲话》的提出,两者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说“民族形式”论争关注的是新国家的文化形式问题的话,那么《讲话》则提出了新国家的主体问题。“工农兵文艺”这一说法强调文艺的重心不再是城市/新文艺/知识分子,真正需要表现的对象是农村/旧形式或民间形式或地方形式/农民,而这种新的民族形式/文艺的创制者,则是“脱胎换骨”后的新文艺作家们。如果说《讲话》解决的是实践主体和表现对象的问题,那么“民族形式”解决的是民族文化认同方向问题,而新的国家政治构想方案,实际上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完成。从这样的历史关系来看,将“旧形式”讨论提升至“民族形式”这一理论层次,或在“民族形式”论争中引入“旧形式”问题,远远不仅是“形式”问题,而是在一种新的政治诉求和政治主体意识的推动下,包容并改造尚未从传统的帝国社会与生活秩序、古典文化共同体记忆中摆脱出来的乡土中国的过程。 三 “旧形式”与“当代文学”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一方面将“旧形式”明确地引入了左翼知识界的新中国文化政治构想中,同时也给定了它的话语等级地位。由于利用旧形式的目标必须是“新文艺运动的新发展”,因此它的位置始终是次等的、普及性的。在这场讨论之后,“人民性”、“阶级性”以及民族文化“精华”与“糟粕”的两分法等批评话语,开始从苏联批评界引入,从而为确立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序列和评价尺度提供了标准。这种重新评价传统文学的工作主要在两方面展开。一是在古典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如何用新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取代自五四时期开始,在“白话文运动”、“整理国故”、文学研究专业化过程中确立的“资本主义”学术话语(40)。到1950年代,一方面,《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已成经典而列入文学工作者的必读书目;另一方面,1953-1955年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便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主要实践活动。另一则是在文学创作领域,如何借鉴古典文学经典(作为有效资源之一)而形成当代文学的“民族风格”。 在如何利用“旧形式”以创造当代文学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实践路径。同样书写革命历史,梁斌追求的是“比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些”(41),也就是试图同时完成中西两面的融合与超越。不过,“革命通俗小说”代表的是另一种路向:它们试图更多地倚重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书写传统,在一种更为民族化的文化视野中来书写“革命”。这种实践的最早形态,便是《洋铁桶的故事》和《吕梁英雄传》。 《洋铁桶的故事》的作者柯蓝写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我刚刚开始向民间文艺、向我们古典文学学习的时候,也正是我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培养下,初入陕北农村,学习写作通俗文学作品的时候。”这就直接点明了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诉求。在具体的叙述形态上,小说主要借鉴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和讲故事的方法,力求学习“农民群众是怎样讲故事,是怎样有头有尾来讲述一件事情,又是怎样交错地来讲述同时发生的许多事情的”(42)。茅盾读到《洋铁桶的故事》后,曾将其与后来的《吕梁英雄传》《李家庄的变迁》并称,认为是新文学运用“旧形式”的“极有价值的‘实验’”(43)。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新章回体作品最初事实上并不被称为“小说”,而有一种特定的称呼即“通俗故事”。与小说所强调的“虚构性”不同,这种“通俗故事”更重视故事的纪实性和形式的通俗性。作品以1942-1945年间发生于山西的“沁源围困战”为原型,讲述外号“洋铁桶”的民兵吴贵,组织当地农民武装、协同八路军将日军赶出沁源县城的故事。虽然以“英雄”为书名,但是主人公的形象并不鲜明,人们除了记住他因“性情暴躁,说话声音粗重”而获得外号“洋铁桶”之外,几乎不能对其留下多少印象。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事件的展开过程,人物成为事件中的一个个功能性符号,缺乏生动细致的刻画。但是此后章回体革命通俗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在这部最初的尝试之作中都已具备。比如抗击日军的过程成为组织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英雄人物主要是作为这个叙事过程的行动者而非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人物行动带动情节发展叙述等;又比如抗日背景下小型武装力量的人物关系模式(包括作为主人公的英雄、八路军指导员、英雄同伴、日本鬼子、伪军、汉奸、地主、村民),和基本事件模式(如鬼子烧村、民兵袭击、除汉奸、收买伪军、威慑地主、组织新政权、拔除鬼子炮楼据点等);又比如口语化和通俗化的叙述语言。 到一年后发表的《吕梁英雄传》中,同样是讲述一个村庄组织民兵武装的抗日故事,叙事规模和人物刻画两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马烽、西戎在介绍写作经验时,强调了与通俗化报刊编辑工作关联在一起的民间文艺形态:“除了编报和下乡之外,陆续写了不少快板、故事、小秧歌等,同时还搜集整理一些民间故事。写这些东西完全是为了报纸的需要,为了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吕梁英雄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44)甚至《吕梁英雄传》的最初写作,就是想把民兵英雄的斗争事迹编成“连载故事”:“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本书,也没有预先拟出通盘的提纲,只是想把这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并且是登一段写一段,不是一气呵成……”(45)显然,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章回体的形式起到了十分便利的作用。茅盾读到这部小说后,赞美它“对白的纯用方言”,却批评了它“人物描写粗疏……未能恰如其分地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同时也提及并评价了小说所采取的章回体形式:“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与之相比,《吕梁英雄传》“在功力上自然比张先生略逊一筹”。(46) 虽然从当时批评界的评价上看,这两部小说都被认为存在缺陷,但是它们出版后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却表明这种写作形式在解放区农村乃至解放后的城市仍有着巨大的读者市场。《洋铁桶的故事》印成单行本出版后,1940年代在各解放区就有9个之多的版本流行(47)。关于《吕梁英雄传》,袁珂描述道:“它曾风行各地,翻印了若干版,畅销了若干部。去年单在天津一地,就印行了二万五千部,等于过去文人出了十四五版的集子(以二千部为一版计)”,因此如此评价这类作品:“也许在思想性、艺术性的成就上不能算是最好的一种,但在故事性和民族形式的通用上,却收获到了很大的成功,更为人民大众所喜见乐闻。”(48) 从延安文艺的整体格局可以看出,如何融汇新的政治诉求、五四新文艺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创制出新的“工农兵文艺”或“人民文艺”,存在着不同的实践路径,而且彼此之间并非不冲突。仅在叙事文学,就有赵树理对于民族形式的灵活制作,有丁玲、周立波、柳青等在西化新文艺形态中创制的“方言土语”,也有李季诗歌采取的“信天游”等地方形式。而《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的特点,则在明确借用了“旧形式”,即传统通俗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而且是其中的特殊类型: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混杂。值得分析的是,正是在最后这一类小说中,“思想性、艺术性”与“故事性和民族形式”发生了分裂。 茅盾在评价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时,也提及《吕梁英雄传》:“《李有才板话》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这和章回体的《吕梁英雄传》不同)然而这是大众化的作品。”(49)也就是说,《李有才板话》是“新形式”的,而《吕梁英雄传》仍是“旧形式”的。1946年晋察冀边区文联将赵树理树立为解放区文坛的“方向”作家时,如此解释他的“新形式”:“他的创作很明显的批判的接受了中国民间小说的优秀传统,然而他以今天群众的活的语言描绘了当前的斗争现实,经过自己的提炼,他创造了一种新形式。”(50)有意味的是,同样接受了“中国民间小说的优秀传统”,所谓“批判的”和“不批判的”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呢?赵树理的形式之“新”就在于,他的小说虽然保留了旧形式的一些要素,但通过重新组合和制作而成为“新形式”了。而《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之所以仍旧是“旧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留了章回体的外在结构形式,而且保留了一定的“英雄的说部”的类型元素/叙事程式。也许可以说,正是“类型”要素的存在,使这些章回小说的内容无论如何“新”,其总体却还是“旧”的。 事实上,在保留一定的类型化要素这一点上,不仅是延安时期的《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也不仅是40—50年代之交的《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包括50年代后期的《林海雪原》《烈火金钢》和《敌后武工队》,都是同样的。如果不仅关注其所借鉴的通俗文体,而且也关注其所借鉴的具体叙事类型与叙述内容,就会注意到,这类书写革命历史的现代通俗小说,其实一直未能摆脱延安时期开辟的叙述模式。这包括三个方面:一、借鉴的是旧章回小说的一个特定类型,即“英雄的说部”(英雄传奇)。虽然茅盾将《吕梁英雄传》的章回体与张恨水相提并论,不过张恨水是对章回体中的“世情小说”这一类型的发展和转化,而《吕梁英雄传》与其他革命通俗小说延续的则是英雄传奇类型。因此,值得去问的不仅是为何是“章回体”,更重要的还有为何是“英雄传奇”?第二个特点是其叙述内容都是革命战争题材。洪子诚曾提到:“这些长篇小说与《新儿女英雄传》一样,都是表现战争生活的。用‘通俗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生活,又是个未被试验的难题。”(51)而且特别的是,所表现的战争,又大都是抗日战争。在所列出的革命通俗小说中,除了《林海雪原》,几乎都是抗日战争题材。这与表现国共内战(解放战争)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均更注重“史诗性”这一特点,形成了某种参照。第三个特点是在叙述方法上都注重“说书人”这一叙述视角,注重故事性与语言的口头性。这使其“讲故事”的意味远大于“写小说”的意味。这三者的结合,毋宁说乃是革命通俗小说的最大特征。 这种文体形式并非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应该说充满了“意识形态”意味。这关系到的乃是革命中国与古典中国在文学形式上的具体交涉和选择,关系到“旧”的类型要素如何可以延续至现代革命的叙述中,又因为什么而最终不能被彻底转化为现代/革命的。 四 类型化的“知识”: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 革命通俗小说的“英雄传奇”类型和主要表现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叙述内容,这两个特点是特别值得深究的。它们背后共同关联着这一小说形态借以从“旧形式”转换到现代的“民族形式”的意识形态内涵表现在何处。 “英雄传奇”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如果说武侠小说的主题是“恩仇”的话,那么英雄传奇的主题则可说是“家国”。其中的关键差别在于,英雄传奇中的“英雄”并不是现代武侠小说中“不轨于正义”、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作为主体的个人,而更接近于古典通俗小说中家/国、神/人伦理阶序结构中的个体。 “英雄传奇”是中国古典长篇章回小说一种叙事类型的描述,这种描述出于“小说史家的概括”(52)。正如许多古典小说研究者都提到的,长篇通俗小说这一文体自其从元末明初成型开始,在题材上和文本形态上就表现出了鲜明的“类型化”特征(53)。一般将其描述为神魔、世情、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四种基本类型。不过,这种描述方法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分类描述的最早源头,被追溯到南宋时期的“说话”分类以及明代学者胡应麟等的研究(54)。晚清时期倡导“新小说”时,曾有人将章回小说概括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55)。当鲁迅开始“自觉建立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体系”时,他提出的分类法是三种,即“历史演义”(“讲史”)、“神异小说”(“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56),其中“英雄传奇”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看待。“英雄传奇”的说法最早见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并在郑振铎的研究中明确为一种小说类型概念,其最早被指认的典范作品是《水浒传》。到20世纪中期,将章回小说的类型描述为四种,即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小说、神魔小说,成为一种普遍的观点(57)。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的差别,被孙楷第概括为:前者“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及家人传者”,后者则“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或“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58)其(英雄传奇)代表性作品,除《水浒传》外,常提及的有《水浒传》续书(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及俞万春的《荡寇志》)、《杨家府演义》(及《说呼全传》《万花楼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说岳全传》与《飞龙全传》等。 可以看出,在基本的四分法中,“英雄传奇”是最晚得到命名的一种类型。此前它主要隶属于“历史演义”,因此与历史叙述关系密切。将“英雄”从“历史”中独立出来加以命名,一方面表明它与《醉翁谈录》(罗烨)、《都城纪胜》(耐得翁)等提及的“小说”分类,如公案、朴刀、杆棒、说铁骑儿等,在渊源关系上的内在发展,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提示了一种新的主体与历史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直到现代时期才得到命名,某种程度上表明“英雄”与相关的其他称谓,比如“侠”、“豪强”乃至“帝王将相”等,均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明初即已实存的类型化文本与近代的命名之间,存在着某种既连续又断裂的关系,表明“英雄传奇”这一叙事类型的独特性,可以说介乎现代与传统之间。这种暧昧的品性,正是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在当代中国得以延续的内在原因。 事实上,关于这种小说形态的命名,当代批评家的说法并不一致。《吕梁英雄传》曾被称为“英雄的史诗”,因为它写了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和英雄的“成长”(59);依而在评论相关文学时,称之为“英雄的说部”。王燎荧在评价《林海雪原》时,则从“现实性”与“传奇性”两个维度,将其称为“革命英雄传奇”(60)。这也成为人们后来使用“英雄传奇”来称呼这类小说的源头。这说明如何命名这类小说,是在与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理解中确立的,“英雄传奇”(或英雄说部)的说法并不简单是“英雄”与“传奇”(“说部”)的组合,而是在指称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小说类型。 考虑到问题的这一层面,就是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在叙事文体上的类型化、模式化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才培育出了欣赏口味、审美惯习相近的传统中国广大的读者群,并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延伸至现代中国。也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当代的革命文学创作者们,在组织其复杂的历史经验时,几乎是下意识地参照古代中国经典小说文本的类型模式而展开叙事。这也是人们考察“通俗”文学时经常会关注的内容。但是,常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与现代通俗文学基于现代性的文化传播机制不同,古典中国的通俗文学固然有其市场化诉求(印刷、传播、阅读等),但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体制,也就是那种仅仅把文学视为“消费”、“娱乐”、“休闲”等的观念,而是处在文学—生活—伦理—世界观等混溶的前现代状态。这也就意味着,文学的分类体制并非仅仅是“文学的”,而同时涉及藉以如此分类的生活、伦理与世界观。 张炼红在研究五六十年代中国戏曲改造运动时,曾提出传统戏曲分类与“民众生活世界”的紧密关系,认为戏曲中“人情戏、鬼魂戏和神话戏”的分类也是支撑起“传统文化基本脉络的人、鬼、神三界”。(61)事实上,在文艺并未从社会体制中“独立”出来的古典时期,不只是戏曲如此,可以说所有的文艺样态都包含了与“生活世界”的同一性,特别是后来被名之为“通俗”种类的文艺就更是如此。这也是赵树理在指出传统民间文艺的“自在性”时指涉的内涵(62)。因此,小说(也包括文艺)的分类知识,事实上也是指导社会伦理、生活秩序、世界想象的同一套知识。这就使我们在考察神魔、世情、历史、英雄等小说类型时,可以具有别样的思想与文化视野,探询连接文艺与社会的关联通道。 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关于明代四大小说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与一般侧重史料考证、文本与修辞分析的古典文学研究不同,浦安迪从思想史的角度,将明代四部小说的主题分别概括为“修齐治平”的反面实践,即《西游记》“不正其心不诚其意”、《金瓶梅》“不修其身不齐其家”、《水浒传》“不治其国”、《三国演义》“不平天下”。(63)这就颇有意味地将一般小说分类中的“神魔”、“世情”、“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分别与儒家文化(宋明理学)差序格局中士大夫的“身”、“家”、“国”、“天下”联系起来了。不过,由于浦安迪将四大小说视为“文人小说”的创作形态,因此,他基本上把“神魔”视为文人修身养性的内心修炼形态,而可能忽略了,在古典中国的世界观中,“神魔”或“鬼神”所占据的独特位置。“鬼戏”在当代戏曲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1960年代初期,关于“鬼戏”的争议成为了“文革”发生的前奏之一。但在现代文学中,很少能找到“鬼”的身影。不过,古典文学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特别是“神魔”书写,构成了古典小说的四大类型之一。“神魔”一说源自鲁迅的概括,这一小说形态出现于明万历年间,盛于明清,其成因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普遍社会潮流密切相关。而在神魔小说出现之前,书写“鬼”以及“精怪”的大量作品,则构成了“志怪”一类小说形态。(64)“神魔”的出现,很大程度地改写了“鬼”、“怪”的位置,将其置于更低阶序,同时,关于“人”的主体想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展开相关的讨论,显然需要更丰富的论证过程,这里仅通过与更为大众化的传统戏曲的参照,关注古典文学如何理解“人”。应意识到明清古典文学中,除了士大夫式的“身”、“家”、“国”、“天下”的横向差序格局外,还有更普遍的“人”、“鬼”、“神”纵向的三界,共同构造出一种独特的主体/文艺形态。 从这样的视野来重新考察“革命历史小说”与通俗化的“英雄传奇”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会变得格外有趣。这使我们不仅关注类型化叙事文本的结构、模式和修辞形态,也同样关注文本叙事据以类型化的生活、伦理、世界观内涵,从而打通文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通道,为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联形式提供更开阔的分析场域。 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一般可以区分为两种书写形态:一种以写“历史”为主,这指的是《红旗谱》《红日》《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更主流的、被认为“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采取的是更为现代的“史诗”叙事形态;一种以写“英雄”为主,这就是本文所主要讨论的“通俗小说”,其采取的是相对更通俗化的“英雄传奇”这一叙事形态。这两种叙事形态基本上接近于古典时期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的两种类型,即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孙楷第所说的“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的历史演义小说,多是编年体,其四个主要特点,一是讲述主体为某一朝代的王朝国家,一是事件与人物多据史实即“七实三虚”,一是其形态最早从宋代“说话”艺术中的“讲史”类发展而来,一是侧重正史、帝王将相与所谓重大题材。相应地,英雄传奇小说“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及家人传者”,多是纪传体,其同样具有的四个相应特征,一是讲述主体为英雄或其家族,一是多据传说故事因此“虚多实少”,一是由“说话”艺术中的“小说”发展而来,一是更为野史与市井庶民化。(65) 事实上,类似的特点在许多方面也适应于“革命历史小说”与“革命英雄传奇”之间的分别。比如讲述主体,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旗谱》《红日》等,虽也重视塑造“英雄”人物,但是“史诗性”的追求使其更关注长河式的历史图景和真实历史事件的展示;相应地,革命通俗小说中“历史”的书写是弱化的,而英雄或英雄群体(“……队”)则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由此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古典时期改朝换代的“王朝国家”与现代的掌握了中国政权的共产党“革命中国”之间,所谓“历史”想象的分野表现在哪里?相应地,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中,古典历史演义中的“帝王将相”与英雄传奇中的“英雄”有何分别,而现代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领袖”与革命通俗小说中的“英雄”又有何分别,以及现代与古典两者的历史分别又在哪里? 又比如历史叙述的“虚”与“实”问题。虽然革命历史小说与革命通俗小说都强调其真实性与纪实性的特点,不过,两者的性质还是有所不同。革命历史小说一般讲述的是有史实依据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它固然允许一定的虚构性存在,不过如何叙述这样的史实,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的事情,而更是“政治”事件,必须高度吻合“党史”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描述。比如《红旗谱》对高蠡暴动的书写,以及它在“文革”期间被指认是为“王明路线”翻案,比如《红日》对山东战场上的涟水战役、孟良崮战役等的叙述,以及它因“第一次在小说中书写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物”而在“文革”期间受到的批判等,都表明这种历史书写的高度规约性。相对来说,英雄传奇小说虽然都有一定的真实生活原型,但是从进入“故事”和“小说”的叙事形态开始,它们就不断地偏向“传奇性”的“虚构”叙事。如同知侠在回顾《铁道游击队》写作过程时明确表示的那样,“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两回事。艺术的真实更高,更集中”(66)。特别有意味的是,几乎所有这些英雄传奇小说的写作,都可以说是“延安道路”具体运作的产物,其创作动因都与1943-1944年前后,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树立“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新政治运动相关。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提到诸如1943年的山东军区“战斗英雄、模范大会”(《铁道游击队》)、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烈火金钢》)、1944年的“晋绥群英会”(《吕梁英雄传》),以及作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的沁源围困战(《洋铁桶的故事》)等。这也就是说,在小说叙事上,英雄传奇固然是“七虚三实”即在真实经验的基础上纳入了许多虚构的成分,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并非讲述者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主义中国运作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即通过“英雄”、“模范”的示范作用来教育广大“群众”这一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其实是催生英雄传奇小说的同样重要的现实媒介。因此,在“虚”与“实”关系上,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的高度政治性其实一如古典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成王败寇式的“胜利者的言说”,那么古典时期的“帝王将相”和改朝换代的“天下”之历史,与现代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创世纪式的“世界史”/“革命”之间,将个体经验提升为历史叙述的那一套背后的理论性知识,从古典到现代的延续性是如何构成的,最根本的分歧又是什么?相应地,如果说古典时期的“英雄”与当代时期的“英雄”实际上都保持着某种艺术与生活的“同构性”,那么两种“英雄”的异与同,以及造成这种异同的深层制约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同样,在偏重“讲史”与偏重“小说”之间,在偏重“主流”与偏重“民间”之间,革命历史小说与革命英雄传奇的分别,也一如“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 总体而言,从讲述主体、虚实关系、叙事形态、主流与民间的分野这样四个共有的层面来看,讲述当代革命的革命小说,与讲述古典王朝国家的古典小说,都具有引人注目的内在同构性,同时又具有现代的变异性。如果不能解释这种“内在同构性”因何和如何产生,那么可能会忽略革命中国与古典中国的延续关系如何呈现,或者颠倒过来,将革命中国仅仅视为古典中国的复现,而无法在更具体的层面来讨论两者的连续与变异关系,以及它们的发生机制。 五 主体的装置:英雄/“国”,“新人”/世界史 讨论的切入点,乃是小说叙事文本的类型化得以成型、文艺/生活同构的那一套“知识”即生活—伦理—世界观。如前文提到,古典小说中的神魔、世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这四种分类,提示的是人、鬼、神的等级序列与身、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其本质是古典特别是明清时期有关“人”的诸种知识。福柯曾称“人是一项现代的构思(更准确的翻译是‘发明’)”(67)。这也就是说,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启蒙思想,事实上与古典时期一样是一种“知识”的结果,从古典到现代时期的变化,并非从无“人”的神的时代向有“人”的世俗时代的转变,毋宁说乃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从这样的理论角度,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从长时段历史视野,将古典与当代置于同一考察平台之上,分析其小说叙事、文本类型与“人”的知识这三者的关联形态。 正如浦安迪相当有意味地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叙述的世界,区分为“天下”与“国”,实际上可以说,历史演义小说所讲述的乃是普遍性的“天下”,而英雄传奇所叙述的则是特殊性的“国”。最有意味的是,这里所谓的“国”在唐宋转型期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使其超越了囿于华夷之辨的“天下”之诸侯的“国”,而具备了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认同的雏形。与历史演义小说涉及各个时期的朝代不同,英雄传奇小说的故事基本上集中于宋,成书年代则在明清之间,情节都涉及抗击异族、立边功的内容。固然,英雄传奇也有《飞龙全传》这样的帝王发迹史,不过这里书写的仍旧是一个“宋代”的皇帝。与历史演义小说所涉朝代的广泛性相比,英雄传奇小说集中于“宋代”与抗击异族这两点绝非偶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们重新定义了历史的想象方式、作为主体的英雄,及二者的关系。这种变化可以从两个侧面来加以描述:其一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主体“英雄”,乃是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家国英雄,而非个人性或普遍性的“侠”或“帝王将相”。这使英雄传奇区别于武侠、侠义、公案等小说类型。其二是“英雄”与“国”的密切关系。正是在保护国家、争立边功的过程中,曾经的“匪”或“侠”才得以成为“英雄”。这里的“国”固然是华夷之辨中的“国”,因此有汉族的中国正统与异族的魑魅魍魉,但是这个“国”却是有清晰的边界的,超越这个国的界限(投敌)成为英雄绝不可能去做的事情。这就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涵义,其基本特征是清晰的边界,而帝国(天下)内部诸侯之“国”,其特征在于边境的模糊性和可变异性(68)。比如《三国演义》中,关羽对刘备的忠诚被解释为个人性的“义”,而在杨家将故事、说岳故事与《水浒传》中,类似的拒绝降敌行为则被解释为对国家的“忠”和最高的“大义”。显然在“天下”的视野中,一朝一代之“国”是可以超越的,因此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但是,在英雄传奇中的“国”,却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是英雄忠诚的最高对象。 “英雄”与“国”的同构性,特别是“国”的现代性,正是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既古典又现代的暧昧品性的来源。葛兆光在他的新著中提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意识凸显于宋代。由于宋代中国处在与辽、金对峙的紧张国家关系之中,汉民族主义和中国正统意识正是在这个时期才被发明出来。他因此认为,中国的近世民族主义,实际上并非仅仅形成于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侵略的反抗,以及民族救亡和文化启蒙一体两面的五四运动,而是宋代的“中国”意识本身就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远源”。他认为这正是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式民族主义的不同之处(69)。这种观点固然有进一步商榷之处,不过考虑到历史学界特别是思想史界关于“唐宋转型”的论述(70),宋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位置,特别是国家形态及其认同方式发生的变化,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从英雄传奇小说的叙事形态及其叙事内容的层面,这一变化也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印证。甚至可以认为,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它所书写的家国英雄、所讲述的抗击异族的情节、所表现的“中国”正统意识,都可以视为近世民族主义雏形的症候。——如果这样的结论可以成立的话,古典的英雄传奇小说类型在当代中国有意无意地被重新调用,也可以得到某种历史性的解释。 “英雄”与“国”的同构性及其暧昧的现代性,在当代中国复活的重要契机,乃是抗日战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如前文已提到,抗日战争的过程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普遍成型的时期。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现代的民族主义彻底地取代了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天下主义”的特点可以被称为“文化主义”,即只要皈依帝国的文明,野蛮的异族也可以“以文化之”,纳入我族(71),因此,华夷之间、他我之间的边界是不固定的。而“民族主义”强调的则是国族之间的明确边界与不可跨越性。另一方面,就中国完成现代化的过程来说,也就是从天下主义的“帝国”转向民族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可以说,晚清与五四时期的知识界变革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开端,但其普遍化并最终完成,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人民革命的民主主义与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合二为一,从而使现代民族与国家意识渗透到社会最底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古典英雄传奇的汉民族主义,几乎是“自然地”被调用到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认同之中。以“战斗英雄”“英模”为原型的当代英雄传奇小说,大都是以抗日战争作为叙事内容的,《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都是如此。在被称为“英雄传奇”类型的小说中,只有《林海雪原》是其例外。这一点并非偶然。正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过程中,古典时期处于“家”“国”之间的英雄,才能与现代的民族、民主主义诉求完成真正的“无缝对接”,“英雄”与“国”的同构性才能形成。其中,“英雄”因其报“国”的崇高性而得到认可,同时,“国”的合法性也因英雄的“正义性”而得到深化。 更有意味的是,英雄传奇小说在英雄与国的同构性上呈现出来的基本意义序列,也同样表现在古典与当代的小说中;同时,又在一个关键面向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也是古典与当代的分歧所在。 在古典的英雄传奇小说中,事实上存在着“鬼”—“人”—“神”三个纵向等级序列。《水浒传》中的108条好汉本是地洞里的鬼怪与妖魔,他们出世而为豪侠,但只有在立边功、报效朝廷之后才晋升为“神”。类似的由“鬼”升格为“人”进而成“神”的上升序列,在《水浒传》续书中重复。“鬼”的身份,表明他们曾经为“匪”为“盗”的不光彩出身,必须经历报国的赎罪,才能升入“神”界。在说岳、杨家将故事中,呈现的则是一个反向的序列:由“神”而“人”并复归为“神”。比如岳飞原本是天上神界的“大鹏鸟”,他作为民族英雄抗击金国的壮举,被解释为贬入凡间而与同由神界下凡为魔的金兀术斗法,并最终复归于神界。又如杨家将的故事中,有《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演义传》,表明杨家将和包公、狄青一样,本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与外在的异族(“魔”)和内在的奸臣(“鬼”)抗争而保护国家。这种简单化的分析力图呈现的,乃是古典时期的知识排列和分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伦理—世界观中,“英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才得以呈现。而有意味的是,如果没有“国”这一最高“大义”及其边界的存在,“鬼”与“魔”的非正义性都无法体现,“英雄”的天赋异禀也无从说起。但悖谬的是,正是象征“天下”的“神”界的存在,又使得“国”的正义性显现为无。当英雄升天、归入神界之后,英雄传奇在叙事中累积起来的强烈情绪(抗击异族、反击奸臣),突然表现为某种虚无。这大约是导致现代读者在阅读说岳、水浒故事结尾部分时的异样感受的原因。 在这些方面,当代的英雄传奇小说一方面延续了古典时期的内在等级结构,一边又在“神”界这一序格上做了根本性的改写。当代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普遍包含这样一个人物关系序列:日本鬼子(妖魔)—汉奸(鬼)—伪军、伪政权(非人非鬼、亦人亦鬼)—村民(凡人、“群众”)—英雄或英雄群体(半人半神,党员或以党员为核心)—共产党组织(神界)。与那些书写重大历史事件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革命英雄传奇一般叙述视点主要集中于日本鬼子与共产党组织之间的部分,即铲除汉奸、争取伪政权、发动群众,最终拔除日军据点,然后英雄(群)回归到共产党大部队中去。对“日本鬼子”和“汉奸”的修辞,高度类同于古典英雄传奇对金辽等异族、奸臣等内鬼等的书写方式。而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则显示出一个类似于“神界”的更高世界的存在。一方面,从凡人中超拔出来的“英雄”通过加入共产党而得到最后的命名;另一方面,也正是单个共产党的带头作用而使对凡人/群众的动员成为可能。 不过,在类似的鬼—人—神的意义序列中,其内在的结构方式被一种极为“现代”的方式改变了,从而使古典的等级序列转换为现代的革命/动员过程。这大概也可以被称为福柯所谓的现代治理术实施的过程。福柯在勾勒西欧社会的现代变迁时,曾如此描述:“基督教牧师或基督教教会发展了这种观念——我相信这是一种奇特的观念,与古代文化完全不同——即,每个个体,无论年龄和地位,从生到死,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受到某个人的支配,而且也必须让自己受支配,即是说,他必须在那个人的指引下走向拯救,他对那个人的服从是全面细致的。”由这种基督教神学发展出的现代社会治理术的三元结构,福柯称之为“与真理的三重关系”,即“被理解为教条的真理”、“对个体的特殊的、个别化的认知”和“反思的技巧”即“普遍规则、特殊知识、感知、检讨的方法、忏悔、交谈等等”。(72)从理论化的抽象层面而言,这种三元结构也正是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阐释的、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的人”与现代文学体制同构性的那种话语装置(73)。 在古典的英雄传奇小说中,“神界”的存在是一种意义的等级序列,可以简要地将其视为古典中国独特的社会理论“礼仪”的具体呈现。这种社会礼仪“反对将人当做基督教意义上的面对‘绝对他者’的个体,而将人社会化为有特定等级身份的团体,再将之‘嵌入’于一个作为整体的文明秩序中”(74)。从这样的人类学视野来看,鬼—人—神的三个等级序列实际上是区分人的社会身份的“礼仪”,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而非绝对性存在。因此,在“人界”(凡间)的格序中成为“民族英雄”,一旦回复到“神界”,其“国”族身份的绝对性就消失了。比如岳飞,一旦他死后归于神界,他就回复到“金翅鸟”的身份,宋金之间的民族冲突就成为凡人、人间的骚扰而远离了他。但是有意味的是,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并不存在英雄传奇小说中的“鬼”与“神”格序,而只有“人”的世界。比如《三国演义》,只讲“人力”不讲“鬼神”,而人力体现的乃是“天道”即所谓“历史”。但是,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不同的地方在于,古典时期的“天道”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空间性的等级身份关系,它的主体乃是“天下”。在这种更高的格序中,“国”不仅是可以被超越的,而且正是不同的“国”构成了“天下”。因此可以说,历史演义基于“天下”视野的“天道”超越了英雄传奇中的“国”,从而使与“国”同构的“英雄”成为一种暂时性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这种“天道”与现代的历史观最大的不同,乃在它是空间性的而非时间性的存在,因此超越“国”之“天下”的历史是循环的、借助于天启的神学式权威的,其呈现的历史景观便永远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与此相对,在福柯勾勒的现代治理术中,有一些根本的东西发生了改变。由于源自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治理术被作为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结构法则,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方式与古典中国的区别正发生在这里。与古典中国基于“礼仪”的差序格局最大的不同在于,现代社会治理的中心转移到了“内在的个体”。现代的个体在“与真理的三重关系”中,确立起了作为“绝对他者”的代理人角色。民族国家正是通过将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创造为“内在的人”(国民),而构造出自身的合法性与不可超越性。从现代民族主义的颠倒视野中,不是民族—国家创造了现代的国民,而是基于地缘与血缘共同体的国民创造了现代民族国家。原本存在于中国社会礼仪格序中的“天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中消失了(75)。同样重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学发展出来的现代社会治理术,也将一神论的世界观作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构成,并使神学式的末世论时间转化成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国族的主体被置于进化论的“长河式”历史景观中,从而与“天下”那种共时性的同心圆式(“圈”)图景大不相同。 不过,当代的“革命中国”不同于“现代中国”的地方,就在于通过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而构造出了一种新的超越了国族的“天下”视野,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世界想象,其主体是“人民”(工农兵)。但不同于“天下”的共时性,这种世界想象是在进化论的历史序列中展开的,黄子平所谓“作者和读者都深深意识到自己置身于滚滚抢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76)的历史图景,正是与这一新的超越性视野联系在一起。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占据古典小说中“神界”位置的共产党组织,既是民族英雄的命名者,也是其超越者。一方面,它与英雄构成了现代治理的关系,即参照共产党组织/新中国这个“绝对他者”而将自己创造为“内在的个人”,使自己从“群众”中超拔出来而“成长”为有着无产阶级觉悟的新人。在这个面向上,成为民族的英雄和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是同构的。但是,另一方面,“英雄”与“新人”又是有差别的。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的知识形态:“英雄”是一种等级性关系中的存在,他们是“非常人”,这就使其与古典的差序格局有着内在关联;而“新人”则是一种内在性的主体存在,他们是“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77),这就使其更是福柯意义上的现代治理术中的个体。两种人的知识装置同时交错地存在于革命通俗小说中,使其在叙事上存在着结构性的内在矛盾。革命英雄传奇一般将叙事的重心放在驱除异族和阶级敌人这一行为上,“凡人”(群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最终胜利而成为“英雄”。其作为“英雄”的分量是与其敌对力量的强度成正比的。正是在与“非人”的鬼、魔的对抗中,“英雄”才成为“超人”,这也是其“传奇性”所在。但是,由于叙事的重心被局限在这种“超人”的诉求中,所谓“平凡儿女”的面向就无法显现出来。比如,不同于“史诗性”的革命历史小说侧重书写“历史”的面向,革命英雄传奇总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神”(共产党)、“魔”(日本鬼子)之间的部分,它们书写的是在“鬼”、“神”参照之下的“人”的世界,而无法如史诗小说那样直接书写“人”的历史本身。实际上,使得超常的英雄再度回复到“平凡的儿女”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即无产阶级觉悟和世界革命的“世界史”视野。在那样的视野中,“英雄”将超越其国族而获得新的历史命名,即“新人”。那是一种“新”的“人”的世界,一个普遍的世界史的现代世界。 简要地说,英雄传奇类型小说中的“英雄”,在故事的宋代、书写的明清、被命名的现代和被挪用的当代之间,连续性的是对“国”的认知,一种类似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态。但实际上,古典中国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礼仪、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与话语装置上的不一致性。这使得英雄传奇因其相似性而作为一种叙事类型被调用,同时又因其话语装置上的不一致而无法超越古典,从而必然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上。 结语 现代、当代、古典与“当代文学” 革命通俗小说别具意味的地方,就在于它以一种独特方式串联起了古典、现代与当代的文学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为讨论古典、现代与革命“中国”的连续与断裂关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场域。在分析了这种小说形态的历史命名、发生的历史语境、类型化的知识形态、主体的书写装置等之后,一种历史地理学向度的阐释仍需在最后提及。这就是小说写作、阅读和传播的具体历史—地理空间场域。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无论就其故事发生的场域,还是写作与传播的场域,都与中国西北、华北等的内陆乡村关系极其密切。不关注这一地理空间的存在,就无法理解作为革命中国表征的“当代文学”的发生。洪子诚的研究提及,当代文学作家的地域构成与其活动区域,相对于现代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从重视学识、才情、文化传统、城市,向着重政治意识、现实政治和乡村的倾斜”,一是“文学创作中心(作家地域构成、题材地域性质、文学风格)的这种由东南沿海向西北的转移的情况,并不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作家又重新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集结而发生变化”(78)。显然,在“学识、才情、文化”与“政治”的对立描述中,包含着洪子诚对这种变化的某种价值判断,但是,当代文学(特别是40—70年代)与中国内陆乡村区域的关系,却正在这里的描述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地理/人文空间的转移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应当成为理解“当代文学”的入口。这意味着文学实践借以发生的场域、人群、文化环境、传播机制、接受视野与内在知识构成等,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王国斌所谓“两种类型的民族”正是要揭示出这背后关于现代中国的结构性鸿沟的存在。造成这种结构性鸿沟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一是中国被迫展开现代化的发生方式,一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切断了沿海与内陆的连接,一是冷战加固了这种内陆与沿海的区域分割等。革命中国正是在被迫深入到中国内陆乡村进而与之建立起复杂关系这一基本情境下发生的。这一地理空间的转移,也是导致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移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之一。 革命通俗小说的出现与写作实践,必须置于这样的历史—地理空间关系中加以考察。一方面,它是“革命的”又非主流的文学;另一方面,它也不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通俗文学;更重要的是,它透过内陆乡村民众的阅读记忆与文化习惯,以及与之伴生的生活—伦理—世界观,而与古典中国小说/社会传统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讨论这一文学形态涉及的问题时,有一些前提性的观念需要反省:其一是“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它通过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实践斥为暴力性或强制性的“政治”行为,而贬低其文学意义和被研究的意义;其一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它通过将一种启蒙主义的“现代”观绝对化,而拒绝在更丰富与灵活的意义上去理解传统的变异方式,特别是古典中国的复杂存在。本文对革命历史通俗小说的探讨,一方面希望将“政治”的力量、“文学”的实践,还包括非现代文学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实践,置于同一讨论的平台上,观察它们遭遇时的互动与意义交涉。另一方面,将古典、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都视为某种特殊性的、对等的形态,来考察文化与意义的变迁。这意味着在理解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发生的内在逻辑的同时,也将古典中国社会与文化视为一种有着内在完整性的形态,它如何遭遇“现代”,特别是遭遇作为现代之另类的“当代”,由此尝试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互为主体”的考察视角的可能性。 显然,探讨这样的问题,革命通俗小说仅仅是一个媒介,而且可能是一个力不胜任的媒介。不过,要相对深入地去理解革命中国及其“当代文学”在1940-1960年代出现与成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这却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媒介。 ①(24)(5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125、128,128页。 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③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作家出版社编辑部1958年7月将论文结集为《〈林海雪原〉评介》出版。 ⑤⑩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⑥⑨何其芳:《谈“林海雪原”》,《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⑦(60)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⑧曲波:《关于“林海雪原”》,《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11)依而:《小说的民族形式、评书和〈烈火金钢〉》,《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12)曲波在《关于“林海雪原”》一文中,把读过的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另一类是“三国”、“水浒”、“说岳全传”。前者是不能“讲”的,而后者则“像评词一样的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可以背诵”。 (13)袁阔成(1929- )在1950-1960年代播讲的十大评书分别为:《水浒外传》《东周列国—商鞅变法》《薛刚反唐》《林海雪原》《三国演义》《烈火金钢》《西楚霸王》《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封神演义》。 (14)参见王立道《烛照篇——黄伊和当代作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22)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196、168页。 (1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30)(38)[美]王国斌:《两种类型的民族,什么类型的政体?》,陈城等译,《民族的构成——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卜正民、施恩德编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29、130、139页。 (18)刊载于《文艺学习》1954年第5期。 (19)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文艺月报》1958年第5期。 (20)招明:《评〈铁道游击队〉》,《文艺月报》1954年5月。 (21)吕哲:《读〈铁道游击队〉》,《文艺月报》1954年第16号。 (23)[法]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汪民安、陈永国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25)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6)(28)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亚洲视野:中国历史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243页。 (27)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1940年9月25日。 (29)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韩毓海《天下——江山走笔》,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 (3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费孝通编著,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3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9页。其中说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33)[美]柯博文(Parks M.Coble):《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403页。 (34)柯仲平:《谈“中国气派”》,《新中华报》(延安)1939年2月7日。 (35)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文艺战线》第3期,1939年4月16日。 (36)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文艺突击》新1卷第2期,1939年6月25日。 (37)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文艺战线》第3期,1939年4月16日。 (39)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15日。 (40)参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9年版。 (41)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42)(47)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重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43)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香港)第1辑,1948年3月1日。 (44)马烽:《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文艺报》1952年第10期。 (45)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的写作经过》,《晋阳学刊》1980年创刊号。 (46)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中华论坛》第2卷第1期,1946年9月。 (48)袁珂:《读〈吕梁英雄传〉》,《川西日报》1950年7月3日。 (49)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 (50)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52)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53)参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刘勇强的《中国古代小说叙论》、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中的叙述。 (54)参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55)侠人:《小说小话》,《新小说》第13号,1905年。 (56)陈平原:《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 (57)参见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19页。 (58)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9)杜庸:《读〈吕梁英雄传〉》,《新华日报》(重庆),1947年1月30日。 (61)张炼红:《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62)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63)[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陈珏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另见《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浦安迪又译普安迪。 (64)参见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第五章《神魔小说》,第270~277页。 (65)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另见谭帆主编《明清小说分类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209页。 (66)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67)[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6页。 (68)[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69)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 (70)参见[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1期)等。 (71)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26页。另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2)[法]福柯:《福柯读本》,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73)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4)(75)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版,第446、472~478页。 (76)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77)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78)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7页。标签: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铁道游击队论文; 吕梁英雄传论文; 敌后武工队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新儿女英雄传论文; 林海雪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