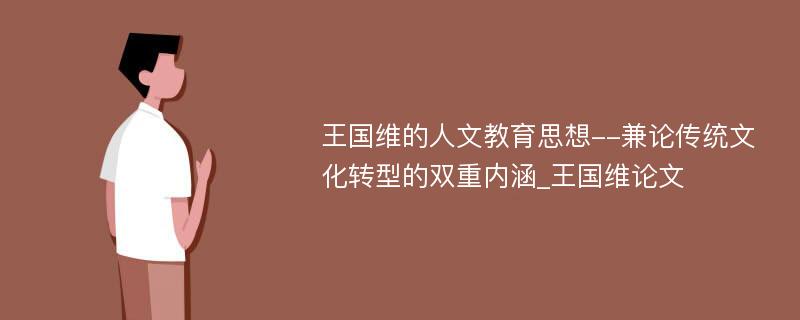
王国维的人文教育思想——兼论传统文化转型的二重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内涵论文,人文论文,王国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的人文教育思想,是本世纪初束缚在文化传统之上的神圣“道统”光环消褪之后,以理性智慧和人性之美重建精神家园的一次教育学尝试,是其学贯中西的人文学养在教育学上的一次厚积薄发的梳理和展示,是其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格在教育领域内的挥洒和彰显,也是他以生命深情地拥抱教育而结出的文化硕果。
一
传统价值失落之后,文化何以立足?这是青年王国维最为关注的问题。
1904年,满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等人起草的《奏定学堂章程》,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王国维敏锐地觉察到了文化只是这个章程的政治目的的附庸和工具。他针对这个章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在精神,及其浓郁的功利主义文化态度,在1905年至1907年的三年间,就人文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价值观体系。
“癸卯学制”在大学文科的课程设置中不设哲学课程,以“理学科”取代之,且“所谓理学者,仅指宋以后之学说,而其教授之范围亦限于此”(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554页。),王国维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政治功利性的“根本之谬误”(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642页。),它不仅表现在大学中对传统文化教授内容的政治性取舍,而且也表现在对西方人文学术及其文化的隔膜和无知,其症结在于“以哲学为无用之学”(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644页。),这样一种以现实的非文化功能来衡量、判断、剪裁文化的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
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之间具有高度的整合性(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265页。),受其浸润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就会从“世界观”、“方法论”即意识形态层面上来理解文化。本世纪初以来西学的大量引入,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其特点在于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都从属于自然的秩序并能通过科学方法来控制和认知,因为它们仅是简单的自然物质并按照确定的科学规律运动”(注:〔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这样一种独断论文化价值裁定。“唯科学主义”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以物理学、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现代形态知识来论证社会进化的合理性,替代了以天尊地卑、阴阳变化、中央四方的传统形态知识来论证封建制度永恒的合理性,其中的反封建的进步性质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为实际之国民”(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645页。),中国文化的“世间”、“乐天”、“实际”、“通俗”(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431页。)的实践理性精神特征,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生存压力下,对西方现代型知识的引进,总是急于寻找一种医治中国社会百病的总药方,很少有形上价值追求的理论旨趣,因而与“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的西方文化大异其趣:“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造成了“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的两种功利主义的学术态度。王国维以严复将"Evolution"译为“天演”为例,指出“天演”与“进化”相较,后者更切中其英文的本义。(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严复独创的“天演”,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译”:第一,他将赫胥黎仅仅在宇宙过程的方法和结果层面上使用的“进化”,夸大为物竞天择的“天演”,认为它是宇宙发展的根本机制;第二,严复有意略去了进化中必然出现的退化及周期性循环的内容,使“天演”成为一种“由简入繁,由微生著”的单向的时间之轴,是一种“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线性发展,强调过程的断裂性,否定过程的连续性,从而为“自强保种”提供一种社会进化论依据,这“是一种急于求成的实用倾向”。(注: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读书》1991年第12期。)王国维在1905年就敏感地觉察出这种不无片面的理论倾向的症结在于过分讲求文化的“
实用”价值,可谓独具只眼。
这种倾向于文化发展有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学理层次上的不利,由于缺乏抽象思辨和条分缕析“穷究之”的理性传统,使学术眼界局限于具体方面和实用层次,“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这是因为在抽象学理层面上和“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缺乏“抽象与分类”之科学理性的文化传统,造成“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30页。)的客观结果,使文化总也摆脱不了工具的命运。
其二为文化价值观念层面上的不利。学理上的实用倾向不仅表现在“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这样一种缺乏悲剧体验、难以从世俗功利中超越出来的“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8页。),塑造出世俗层面上的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而且形成了中国“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文人“无不欲兼为政治家”以求通达,否则“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化价值观及其与之相应的文化人格:
未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为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学术,尽管很快就完成了由传统型知识论基础向现代型知识论基础的转型,但是根深蒂固的功利性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仅没有得到扭转,文化学术中“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33页。)的实用倾向,反而因政局的动荡有所强化。王国维对实用型文化价值和依附型文化人格的批判,表明他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不仅理解为知识类型的进化,而且更将其基础定位于文化自身价值的独立和知识分子个性的自觉之上,在当时就显示出他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理解的过人之处。无独有偶,13年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也有同样的感触,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科技文化方面,而且也突出地体现为“哲学美术(学)”等人文学科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形成了一种“惟重实用,不究虚理”,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的狭隘治学态度,这种不明白“救世经国必以精深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反而“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的近代文化价值观,“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造成,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待于“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的出现。(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10页。)扭转功利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认为重新确立民族文化基础,冀求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建立文化自身的独立价值,学者独立的文化人格为前提,就成为王国维人文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
二
王国维的西学修养使其将哲学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可爱而不可信”的“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和“纯粹之美学”;另一类包括“可信而不可爱”的“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和“美学上之经验论”(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24页。)。后者主要是指在本世纪初就风行于中国学术界的以马赫、孔德为代表的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属于“概念的知识”,主要满足人的生存性的认知需要;前者则主要是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属于“直观的意识”(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11-612页。),主要满足人的形而上的精神性需要。二者具有根本不同的功能和价值。
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人类抽象知识起源于“生活之欲”:“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其间经历了一个由人与动物都具备的“悟性”到人所独具的“理性”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人们首先了解的是“我与物之关系”(悟性)的基本生存价值,随着知识的进化,人们开始逐渐了解与己无直接关联的“此物与彼物之关系”,并且“知愈大者其研究愈远焉”,研究事物“全体之关系而立一法则”的“理性”的自然科学由是而生。自然科学的诞生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趋利避害的能力,但也使人类的“生活之欲”“增进于无穷”。王国维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都建立在“生活之欲之上”(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362页。),产生于包括人在内的求生意志的需要,“知力者意志之奴隶也”(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17页。),而这一类的知识传授又是近代社会职业分工的产物(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18页。),“一切学问,一切职业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因而是功利的,有用的。包括科学在内的“抽象知识”教育,尽管“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培养出来的“教员、医生、政治家、法律家、工学家”,解决的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生存性需求,故而其社会效益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趋于一致(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389页。),但是如果把教育视为获取“实利”的手段而不把教育本身视为目的,就会使“抽象知识”本身丧失“独立之价值”,使学者“于学问固无固有之兴味”而“以筌蹄视之”。(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77页。)不幸的是,清朝政府的价值导向于此犹如火上浇油。
《奏定学堂章程总纲》即《学务纲要》中,有学堂教员“列为职官,确立任期”的“奖励”条例。王国维指出:“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在这种社会前提下,“以‘官’奖励职业,是旷废职业也;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今以‘官’予服务期满之师范生……无怪举天下不知有职业学问而惟‘官’之是知也。”(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24页。)
“官位”与“学问”,利禄与教育,实利与文化,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迄今为止一直是困扰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道挥之不去、欲罢不能的“围城”。王国维在90多年前所发的议论,尽管同当今的现实已不完全吻合,但联系当今莘莘学子和文人的种种表现,不能不引人深思:“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之意义则今日之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社会之趋势既已如此,就令政府以全力补救之,犹恐不及,况复益其薪而推其波乎?”(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80页。)
知识分子必须超越传统设置的文化“围城”,是民族文化由传统的意识形态性格走向现代的追问具体而有意义的理论性性格的必经途径。
三
王国维关于哲学范围的二元界分,使他把教育的知识传授相应地也分为两类。其一为教授书本上的“抽象知识”,其二为教授“美术人生上”的“完全之知识”。(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69页。)就教育本身而言,以上二者都有一个确立自身独立价值的问题。
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其与“工厂阛阓”的区别,在于“所授者非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82页。),因为抽象的科学知识虽然使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求生意志,“然人之知力之所由发达由于需要之增,与他动物固无以异也”(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83页。),因而人的主体性以及知识的独立价值不仅体现在适应环境、满足需求的科学知识方面,更体现在阐释人生意义、彰显生命价值的“完全之知识”上:“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哲学、美学的价值,“正以其超乎利用之范围”,而具有满足“形而上学的需要”的功能(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79页。)。
与概念化的科学知识不同,美学不指向现实的具体事物,“美术上之所表者则非概念,又非个象,而以个象代表其物之一种之全体”,艺术家“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于美术中”,因而美学“个象”中积淀了丰厚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故从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81页。);而哲学作为“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的理论性知识,“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所以同美学性质相同,只不过在“解释之方法”上,哲学是理性的和思考的,美学是直观的和顿悟的而已。二者都是对内在心灵的体悟,都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都充满了生命智慧的灵气,都具有使人“不惑于歧途”的人生体验的导向价值。(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82页。)
要进行探讨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人文教育,培养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人文旨趣,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重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张之洞等人从狭隘实用的政治眼界来剪裁传统文化,拟定文科大学课程,结果“周秦诸子之学皆在所摈弃,而宋儒之理学独限于其道德哲学之范围内研究之”,将其中具有形而上学价值和超越性文化意义的命题(如“太极”、“无极”、“主静”等等)不予理会,那么这种学问就只是一种“无根柢”的学问。为了建立文化的现代性根基,培育文化的独立性格,在传统价值失落之后的“研究自由之时代”,必须要有宽阔的文化视野,必须注意先秦儒家典籍与“周秦诸子”之间、宋代诸子之间及其学术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学术联系,切忌不可重犯“教权专制”、“罢斥百家”的文化专制主义错误;纠正宋以后“哲学渐与文学离”的文化偏见,既要把握传统文化“最粹之文学”的脉络,同时更要发掘蕴含其中的“纯粹之哲学”资源,完成民族文化由依附的传统性格向独立的现代性格的转型。(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13页。)
二是具备跨文化的学术胸襟。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创新的前提之一,是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型。在引入西方现代型科学知识,破除传统文化的知识论基础的同时,必须同时引入以形而上学眼光衡量文化意义的现代型文化价值取向,以打破功利型实用性的传统文化价值框架,民族文化独立性格才有坚实的价值论基础。职是之故,以探究宇宙人生根本意义见长的西方哲学是不可或缺的:
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45页。)
这是一个以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为本位,博采古今中外文化资源之所长,具有开放性、人类性、综合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现代人文教育价值体系,并且已经被当代教育实践所证实。
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把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分离,看作是“两次提升”,一次是“一般生产”把人类从动物本能活动中提升出来,一次是“社会关系”把自身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王国维关于教育传授的“概念知识”和“美术(学)知识”,就是人类“两次提升”的产物。其中关于人类可以借助美学哲学超越“生活之欲”的束缚,从而获得宇宙人生的根本性体认的人文教育思想,无疑深化了“两次提升”中固有的文化学内涵。从传统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这种内涵的深化,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其一,英国学者哈耶克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不确定”(“理性不及”)的社会发展过程,人类文化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机遇:促使个人的天赋和环境形成某种特别的组合,从而造就出某种新的工具或改进某一旧的工具:二是增进成功的可能:促使诸如此类的创新能够迅速地传播至那些能够利用它们的人士,并为他们所利用。”(注:〔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页。)前者主要是指制度性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恩格斯所谓的以“法律形式”促进的经济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也就是王国维所强调的建立在“生活之欲”基础上的“概念知识”的运用;后者则涉及到进行文化操作个体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和人生态度的净化。当代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王国维所强调的旨在净化生命情趣和提升人生境界的人文教育。
其二,王国维认为概念的科学知识与直观的美学知识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概念由直观抽象而来,“故其内容不能有直观以外之物”,“概念之愈普遍者,其离直观愈远,其生谬妄愈易”,理性及其知识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在本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酝酿期间,是难能可贵的清醒的文化意识,并且在对二者之间的联系方面的认识超过了二十年代的“科玄之争”:“书籍上之知识,抽象的知识也,死也;经验的知识,具体的知识也,则常有生气”,“真正之新知识必不可不由直观之知识即经验之知识中得之”,为了保证思想独立和人格自由,文化人格保持“直观之能力”及其带来的思维中“自然之光明”,不使“他人之思想”“压倒自己之思想”,就必须以“无概念杂乎其间”的“美术之知识”进行人文教育,梳理受教育者的美学修养,调适其文化价值取向,这是十分必要的。(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08页。)
其三,王国维在其人文教育思想中强调的文化自身和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价值,以及对实用型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批判,触及到本世纪初以来民族文化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的二重内涵:文化转型不仅仅是现代型知识取代传统型知识的知识学基础的替换,而且还是从形而下的工具理性向形而上的价值理性,这样一个更为深刻的文化态度和人生旨趣的全面转型过程。因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一个直线发展的“理性化”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多元的“理性不及”过程,文化转型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近百年来把文化功能等同于现实的政治革命,或者将其价值等同于经济效益,以及在此基础上滋生出来的把文化视为个人晋升之阶,这样一种“工具理性”的实用型文化价值观,是本世纪以来的文化转型迄今迟迟难以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就是王国维人文教育思想留给我们的启示。
标签:王国维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王国维遗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人文教育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美学论文; 二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