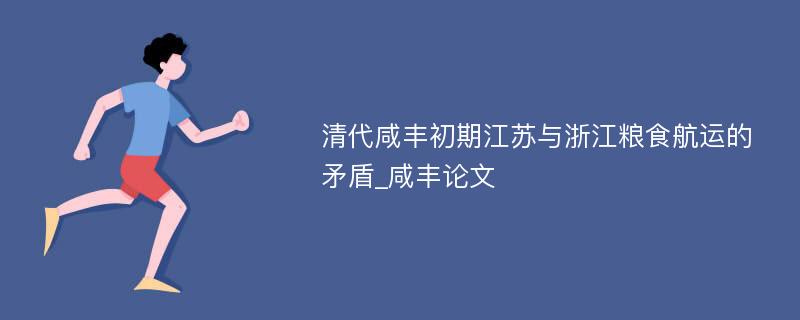
清代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咸丰论文,初年论文,清代论文,海运论文,江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1-0122-06
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要员逐步掌控并主导地方权力,形成中央与地方二级行政主体;而在此之前,则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有学者曾形容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各省之间的财政协调,“有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看作是一种艺术当是可以的”。① 本文则欲以咸丰初年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为例,来揭示在督抚权重之前,虽然还是归属于中央集权体制,但因为经费支出的纠葛、人事关系的复杂,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早已存在和势同水火。同时,正是由于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才为后来的督抚权重及各自为政格局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一、浙江第一次办理海运
浙江与江苏同为清代最重要的漕粮输出地,两者合计居全国份额的四分之三。但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为止的清代漕粮海运,均行之于江苏,“浙省不与焉”②。考虑到江苏海运行之有效,咸丰元年,御史张祥普要求浙江同办海运。③ 但这一提议遭到浙江巡抚常大淳的坚决反对。常大淳指出,浙江虽有乍浦、宁波等出海口,但均非理想,从上海放洋则沙船不敷,盘剥甚远,开支极巨,且呼应不灵。他还表示,浙江运丁水手素称疲累,旗丁衣不蔽体,食不充腹,若试行海运,水手虑及失业,“或借索帮欠逗留生事,或流为盗贼,扰害闾阎,尤不可不防其渐”。由于浙省反对海运的态度极为明确,咸丰帝只得朱批:“既属窒碍,著暂停试办。”④
但河漕的困难显而易见。成丰二年七月,黄宗汉出任浙江巡抚,当时浙江上年的杭、嘉两帮漕船,头船甫运出江,后者尚未离浙境,又因黄河丰工决口,河道淤塞,至十一月仍有浙漕在常州搁浅,江苏护漕负担随之加重,江苏对浙江的不满日益表露,天天以公文咨催责难。黄宗汉甚至对僚属抱怨:“江苏督抚一天来一件六百里公文,凡过往行人之阻滞,以及贡使之迟误,无一不归咎于浙漕。来文直是申斥,浙抚几至无可喘气,使弟不为椿公不休也。”⑤ 椿公即浙江布政使椿寿,因“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余万两”,“情急自缢”⑥。可见黄宗汉对江苏方面的恼怒。河漕难行,于是黄宗汉认为,补救之方莫如海运,浙漕如能改行海运,“全局从此可以转移,于公私全为两便”⑦。这一主张得到清廷同意,浙江的漕粮海运遂得以开展。
浙江海运的出海口选在上海,系跨省运作,又与江苏同时进行,必然存在一个如何协调的问题。黄宗汉将担忧上奏清廷,咸丰帝当即命两江总督陆建瀛和江苏巡抚杨文定等人妥筹章程。经过商议,江苏作出如下承诺:派雇沙船责成沪局委员,“倘有米无船,即将苏省经理委员查明参处;若有船无米,或有米而无水脚,即将浙省办漕各县揭参惩办。如此责有攸归,庶几海运可期迅速”⑧。
虽然江苏对船只做出了承诺,但浙江当局却并不当真,而是从头做起。他们认为,海运以雇船为最重要,宁波北运商船共有100余只,为顺利海运,“业已饬令该管道府先行尽数封雇”。考虑到还须添雇江苏沙船方可敷用,黄宗汉特飞咨两江当局,要求他们派委干员,会同浙省委员“预为封雇”⑨。即便如此,黄宗汉还是担心船只不敷,又向直隶、山东、奉天等处发咨文,要求这些省份先期将各船商预定货物运到出海口,以便船只能迅速装运后返航,参加二运。⑩ 黄宗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当浙江委员赶赴上海开验时,发现除浙江宁船外,仅有卫船4条、沙船1条,续报的也只有13条,而浙漕共需要沙船200条,可见江苏方面对浙江海运所需船只的态度。(11)
最终解决难题的,是直隶和山东大约200余号卫船的赶到。据北直船商陈典等禀称,他们情愿承运浙江漕粮,并请在大东门外开设天顺公记,凡卫船到上海,均由公记具保报局,听候查验。(12) 又据天津县知县谢子澄报告,他已经命当地卫船赴沪受雇,结果海船户长李廷荫等人禀报,已经招雇卫船义源茂等51船,愿意前往上海装载漕粮。在领到天津县颁发的票照后,这批船只也于三月初八日陆续出口,赶往上海。(13) 正是有了这两批船只的鼎力相助,才有了浙江漕粮海运的顺利进行。这也是后来黄宗汉再次上奏时,明确表示“船只无虞缺乏”(14) 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江苏省在派拨船只上对浙江的毫不关心,无疑在本来就不融洽的两省关系中打入了一个楔子。
根据事先的规划,江苏漕粮可于二月兑竣,浙江亦可于三月兑竣。但到咸丰三年二月底,两省起运米数仅及一半。更为奇怪的是,当黄宗汉奏称浙漕已经运到上海30余万石时,统筹负责江浙两省海运事宜的江苏布政使倪良耀却稀里糊涂地表示,浙米到沪者仅止6万石。咸丰帝看到这两份奏折时大为诧异:“倪良耀此次办理海运,实属迟延。”(15) 倪良耀表示要申严纪律,咸丰帝则曰:“不知该藩司何颜出诸口也!”(16) 通过以上公文,又至少可以看出,江苏布政使对于浙江漕粮动态的漠然。
无论如何,经过努力,浙漕最终还是与江漕相安无事地放洋了。但在放洋一事上,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奏称,此次漕粮海运出洋巡护,浙江船只“倘私自偷泊,恐江南水师难以约束”,必得浙省巡洋官兵“会同巡护”,才能有所保障。也就是说,江苏方面希望浙江也能分担两省海运的护漕工作。经闽浙总督怡良协商,浙江不得不决定由署定海镇印务右营游击周士法负责,经费则由浙省自行开支。(17)
如果说浙江的第一次漕粮海运,江浙两省的分歧还只是初步的,那么在随后咸丰四年的漕粮海运,双方的矛盾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二、浙江反客为主
咸丰三年六月,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刚结束,太平军就攻占镇江、扬州,切断运河通道,漕粮再由河运已不可能。七月初,户部决定江浙两省仍办海运,由上海放洋。其中浙漕70万石,苏漕则因战事,仅办白粮5万石。恰逢青浦县周立春因征漕问题率众起义,小刀会领袖刘丽川呼应,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八月,接连占领上海、南汇、青浦、宝山等厅县,并一度欲攻占太仓州。清廷急图克复,调兵遣将,激烈厮杀,虽夺回宝山,但上海一时无法攻下,海道未能打通。
海运由上海出运的计划无法指望,户部便五百里加急咨文浙抚,希望浙漕能改由乍浦或其他海口出运,“迅即妥筹具奏,不得借词军务,以致临时贻误。如上海即日克复,则江浙海运漕粮自可循照旧章办理”(18)。黄宗汉奏称,他已派粮道周起滨、嘉兴知县杨裕深前往乍浦调查。但乍浦海口有铁板沙,大船难以停泊。加之乍浦内河窄狭,装载麻袋及盘坝脚力,须增经费。且该处靠近上海,“更何敢以数十万银米,置诸危险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乍浦闽广人数众多,“猝然内应,防不胜防”。种种窒碍,必不能行。(19)
黄宗汉继续命属员探查,得知江苏宝山县蕰藻浜河面深阔,沙卫各船皆泊于此;太仓州所属浏河口,本系元代海运故道,因沙淤改途,近年沙淤渐开,沙船六七百石者皆可收泊,千石以上则可用小船过载,这两处均堪起运漕粮。(20) 黄宗汉于十月间飞函两江总督怡良及江苏藩司陈启迈,要求确查。同期,他还派署绍兴府知府缪梓、杨裕深等人前往复查。杨裕深首先是选派家丁随同绅董俞斌、张修睦等人前往,当他们行抵太仓州,正碰上太仓州牧蔡映斗也在此地,得知浏河口外约里许有拦沙门一道,现已逐渐消散,惟存阴沙一片。涨潮时即使是装载千余石大船也可出入无碍。此处人烟稠密,沙卫各船多由此进出,文员有州同衙门,武弁有都司衙门,足以弹压。而菹藻浜与吴淞口接近,河面甚宽,在此停泊沙卫各船约以千计,办理亦极顺手,但可惜离上海太近,不过五六十里,风险极大。经综合考虑,他们一致认为,浏河口较为稳当。(21) 两江总督怡良也转告黄宗汉,浏河口尚宽,出运便利,惟从太仓六渡桥至浏河旧闸镇二十四里,河面曲折,多有淤垫,应行挑挖。(22)接着,怡良、署江苏巡抚许乃钊和黄宗汉联衔上奏,表示四年海运将从浏河出海。(23) 户部很快议覆并批准。
浙江海运总局浏河口分局(简称“娄局”)委员杨裕深和江苏候补委员朱钧等人禀称,江苏须于四年正月十五日以前,将太仓河道深挑。浙江可先期借银1万两,分两批行走,此项拨借银两,江苏自应于经费稍敷之日,“即行移还浙省”(24)。不久,江苏有消息反馈回来:经蔡映斗、李翰文查勘,自小普陀起至石家塘止,工长6230丈,系驳船必由之路,亟需挑浚深通,酌挑面宽6丈,底宽2丈,平水面浚深7尺,估工202409.32方,每方折给钱240文,共48578237文。又需修筑东西两大坝,以及沿途河汊各小坝,估需工料钱5707627文,又车戽通河水工钱5400千文,总计估需钱59685864文。他们强调,此案挑工系为浙省驳运起见,“可否由浙省派委大员,驰往该处,会同该州县撙节复估筹款解发”?(25) 也就是说,江苏认为所有挑浚费用均应由浙江承担。但浙江则认为双方共同漕运,且挑河利在江苏,经费理应由江苏支付。双方就此展开多次书面交涉,最后江苏只是开出空头支票:此款系向浙江借领,他日若江苏经费充足,自当归还浙江。
太仓和镇洋地方没有驿站,只有铺递,浙漕娄局设立后,特雇用代马船4只,分段接递文案。(26) 考虑到浏河为交米、收米总汇,距上海不过百里,银米纷至,帆樯云集,沙船水手动以万计,运米驳船以及税行、斛手,群聚庞杂,难保无游手好闲之徒藉端滋事,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江苏添派干员,“巡查弹压”,但江苏方面并未回应。(27) 黄宗汉只得特派浙勇1000名,配足大炮、抬炮、鸟枪、火箭、长罐、长枪、大刀各武器,分作3批,驾船游巡,昼夜梭织,“如遇贼匪,即行迎剿”。如河面驳船拥挤争斗,亦派兵设法疏通,“倘有逞刁船户不遵,即行拏送该管地方官惩治”(28)。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太仓形势极不稳定。咸丰四年三月初九日,黄宗汉接到上海督勇攻剿之留浙补用知府石景芬禀报,江北大营于初七日被太平军焚烧,兵勇溃散。负责押粮的周起滨也称,从初七日起,眼见逃兵无数,沿途抢掠。因事情突然,黄宗汉“既虑贼匪或窜苏松,复料逃兵之必抢掠浙省银米,在途至为可虑”,加派兵勇300余名,坐船40余只,连夜行走,直抵太仓,防护驳船银米。浙江还另由绅董王庆勋等雇船6只,招募水勇100多人,运解大炮24门,配足火药铅弹,委候补县丞黄恩诏带赴佘山以南洋面防护。(29) 其中,王庆勋所募之船每月约需洋银七八百元,又需大炮40尊,劈山炮12尊,抬枪4枝,鸟枪24枝,亦由浙江当局配发。(30)
三、浙江对江苏的敌意
咸丰四年的漕粮海运,江苏仅出运白粮5万石,即便如此,它的兑运速度也极其缓慢,以致验米大臣责问:江苏仅运米5万,虽系时事艰难,何以浙省办运数十万石,现已“连樯而来”,该省米石不及1/10,尚未全数兑收?(31) 如此少的运漕量,即使是江苏本省官员也极为不满:江苏大吏但知彼此诿过,不能公忠体国,听其溃败决裂,不肯补救,“虽曰劫数,实由人事酿成,可浩叹也”。(32)
一方面,通过此次海运,浙江当局对江苏的敌意,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所掌握的材料都是站在浙江的立场上,资料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从这些带有明显立场的材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在浙江看来,江苏在漕粮海运中不尽如人意之处包括:
其一,江苏不办全漕,对浙江征漕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黄宗汉曾不无苦恼地指出,浙江通省民情,实无一人不打算完漕,“无如苏省败坏至此,浙之州县从而效尤,恨不得汉忽有暴病死了,全漕可以不去,官吏及吃漕规者得以分肥,故辄以苏为借口”。迟至四月,仍有未解银二十一万有余,而本年天津用款、仓场轻赍各款,俱要由海同时起运。一边不来,一连催用,“真令人急煞,亦只好办了就是”。他表示,说到人事,没良丧心之州县、漕书、迄揽、劣衿、顽梗匪辈,“生怕漕务办成,米俱出去,银须起解,多方阻挠,日日盼望贼来,可以不起解矣。谣言四起,怨讟滋生,而其根子则皆由于苏州之不办漕”。(33)
其二,浙江办理海运,江苏多有掣肘。黄宗汉认为,自始至终,江苏对浙江海运都极为不满,“深嫉浙江办此漕粮,以形其短”。首先是浏河出海,江苏不肯先说,经黄宗汉催促,“尚搁一月余不答,可见凡中不无尤我”。其次是封船,浙江海运所需沙船始终受到江苏方面,尤其是江苏巡抚许乃钊与苏松太道吴健彰的阻挠。“彼时钊犹以谓浙未必办成,俟其不成,乃益显苏之高见卓识,及早已议折价也”。迨三、四月间,许乃钊探听浙江漕务将成,“心嫉焉”,因沙船一节“其权在苏”,尽管江苏也曾封雇沙船二百号,但吴健彰公然听船户捐免,宝山县丞更是得赃卖放,把停泊各口之沙船全行捐免卖放。只是海运章程规定,“有银有米而无船,责在苏省”,倘浙江漕粮无船承运,则江苏当局吃不消。江苏海运局员朱钧“知吴王八之存心,许乃钊之中其计”,不得已亲自到省城,面见怡良禀报详情。怡良大发雷霆,将宝山县丞撤任,书吏枷示河干,将停泊的沙船一并封发浙局,“其船乃得敷用”。(34)
其三,经费开支,全部转嫁浙江。因浙江是漕运主体,故江苏一切事皆不管,自挑挖河道起,至护送出洋止,专委诸浙省。正月二十六日,黄宗汉特奏,要江苏派泊承升在佘山以南洋面防护浙漕。尽管多次催请,泊承升始终不到,“督(怡良)之意大有憾于抚(许乃钊),窥其口气,泊镇在沪,抚不叫之走,渠亦无法”。(35) 与此同时,许乃钊却向咸丰帝奏称:江苏得力船只大半调赴镇江,存营之船不敷防护,所以向上海道吴健彰借船4只,以护浙漕。(36) 因泊承升迟迟不动身,黄宗汉屡次八百里叠催,“数其罪而责之”,该镇不得已怒气而来,赶到浏河,已在四月初七。浙江头批、二批之米已过佘山,三批亦续发。泊承升情急之下却称,苏省并无一船交他,“用何剿贼”?借吴健彰拖罾船4只,实只给1只作为坐船。他还宣称,浙江水师有4只护送宁波商船到浏河口,可先行截留。黄宗汉得报后,不禁万分痛恨,“我浙已先有雇水勇炮船六只在彼防护,但得苏省派几只师船,交泊镇带往即万全”,乃迁延至四月初,漕粮已出洋,一得风便,八九天即可到津,“上纾圣廑,下慰民望”,江苏却因嫉妒,势必使得浙漕不被盗劫而心不休。(37)
在黄宗汉的多次咨催下,吴健彰的其余3船才赶赴浏河口,“王八[笔者注:吴健彰]乃复议船价”,每船每月须银800两,四船须3200两,火药、铅弹在外,亦不包括损坏修理费用,均由浙江给发。黄宗汉认为,即此一件,就可看出许乃钊全无天理:苏漕经过山东、直隶,“有带银子自己沿途挑河而行乎?有带水陆之兵自己防护乎”?浏河即使单办浙漕,也应由江苏派兵防护。如今挖河由浙备,陆兵、水兵由浙自带。但江苏也有白粮起运,所有水陆各兵,一并俱令浙江出,“浙之银非泥沙,岂有如此用法”?两江总督怡良有些看不过去,命江苏藩司筹银3000余两送到浏河,得知消息的许乃钊却勒令将银子归还藩司。黄宗汉不禁责问:“此有心乎,无心乎,有银乎,无银乎?”咸丰帝曾规定,江浙两省一并派委水师大员赴天津,以便在漕粮入口时稽查奸细,管收器械,苏省派游击1员,浙江派参将1员,派员各走各路,但江苏官兵口粮、使费一并咨浙发给,“满口总以防护浙漕四字为题目,其心非徒计较经费也”。(38)
因以上过节,黄宗汉曾多次责骂许乃钊:向来漕运事宜,浙省皆跟着苏省走。今年独异,必多方败坏浙事,“以为此等系外官做久良心丧尽者之所为,许七兄当不至此”,“今历历思之,乃知人言不诬也”。他又称,四月间有两事几乎大误,不能不痛恨于许老七,“初不料老七之丧尽天良固至此也。诛其心,满望浙漕办不成以分谤,生怕办成以相形也”。(39) 浙江在与江苏合作过程中,诸事皆不顺手,故除黄宗汉外,其他浙江官员也多次表达对许乃钊的强烈不满。在上海的石景芬写信给黄宗汉,“不称许中丞(许乃钊),而目之日逃帅(三月初七日逃了),不称之曰吴道(吴健彰),而目之曰吴贼。屡次禀词皆以逃帅为误国病民,以吴贼为养贼、济贼、通贼,痛哭流涕千万言,并责弟以不参之咎”。只是黄宗汉考虑到,如果奏参许乃钊,一则与江苏闹翻,以后海运更无法可想;二则会使太平军乘机下手;三则许乃钊系浙江钱塘巨家大室,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通省士农工商人众,阿其听好者多,一动众怒,恐以后绅民不与我协心齐力,官民稍隔矣”。(40)
虽然因资料方面的限制,笔者尚未找到江苏方面,尤其是许乃钊、吴健彰等当事人的想法及反驳意见,难以全面的梳理其中的是非恩怨、对错曲折,但双方矛盾的激化程度却是再明显不过的。
简言之,通过江浙两省在咸丰初年的漕粮海运实践活动可以看出,由于经费支出、人事关系的竞争及纠纷,两省的各自集团利益分野十分明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态得到充分体现。需要指出的是,江浙两省在漕粮海运上的矛盾,虽经长期的人事更迭,一直到清王朝灭亡,都没有出现和解的迹象。(41)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是中央集权体制,还是督抚权重格局,区域集团利益总是始终存在,并未随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全国上下一盘棋的“艺术”说法,似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而所谓的“督抚专权”,亦无非是随着局势的变化,区域集团利益在某些方面的放大而已。
注释:
① 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4)。
② 《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初编》,马新贻序,同治六年十月。
③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祥普请将本年江苏新漕援照前届海运成案推广常镇各属及浙江一体遵办》,见《海运续案》卷一《谕旨、章奏》。
④ 《浙江巡抚漕粮难以试行海运请仍循照旧章办理》,见《海运续案》卷一《谕旨、章奏》。当然,常大淳也是在听取了浙江粮道等人的禀报后决定的,他们的意见与常大淳上奏的内容基本相似,在此略之[《浙江粮道为筹议海运漕粮上常大淳禀稿(底稿)》,1851年7月8日,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112—114页]。
⑤ 《黄宗汉书》,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见《何桂清等书札》,第102—1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⑥ 《清史稿》卷三九四《黄宗汉传》。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咸丰二年十月初七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陆建瀛等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不过,对于这一点,浙江巡抚黄宗汉却认为,倪良耀因浙江办海运,“逆料浙之疲敝,断不能于四月以前全漕银米赶完,乃奏此章程以陷浙”,可见两省在办理海运方面的矛盾已经显露,见《何桂清等书札》,第135页。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二年十月二十日,浙江巡抚黄宗汉折。
⑩ 黄宗汉:《咨明浙漕商船抵奉即装货催令回南》,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初编》卷二《商船事宜》。
(11)(12) 晏端书等:《省局详请苏省赶备沙船二百号兑运》,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初编》卷二《商船事宜》。
(13) 黄宗汉:《浙抚行准直隶饬雇卫船驶雇装运》,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初编》卷二《商船事宜》。
(14)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浙江巡抚黄宗汉折。
(15)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咸丰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6)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咸丰三年三月初八日。
(17) 怡良:《闽督咨复饬定海镇统带舟师会同江省认真巡护》,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初编》卷五《放洋巡护事宜》。
(18)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19)(20)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浙江巡抚黄宗汉折。
(21) 缪梓等:《省局禀查勘浏河口堪以出运情形》,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一《省局事宜》。
(22) 怡良:《江督咨委员勘定浏河口设局兑运出洋》,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一《省局事宜》。
(23)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两江总督怡良等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4) 黄宗汉:《浙抚咨江苏督抚浏河口内河道及早兴挑并已解银万两》,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一《省局事宜》。
(25) 许乃钊:《苏抚咨兴挑浏河口内河道即委中防同知杨丞复勘》,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一《省局事宜》。据江苏报告,又有浏河自小普陀至黄泥浜西工尾上共计工长4050丈,估面宽6.5丈,底宽1.5丈,平水面浚深5尺,共估工79917.193方,内干土23362.7329方,每方库平银1钱,共2326.237两;淤土52617.3851方,每方库平银1.35钱,共7103.347两;瓦砾土4037.075方,每方库平银1.7钱,共686.33两,又估筑通工大小坝座料工库平银570.164两,以上实用库平银10686.87两。参见蔡映斗、李翰文呈文,《浙江海运全案续编》卷四,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26) 黄乐之等:《省局转详添雇代马船接递公文》,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一《省局事宜》。
(27) 黄宗汉:《浙抚咨行巡查弹压防护米船》,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一《省局事宜》。
(28) 黄宗汉:《浙抚札饬派兵勇千名分批在于内河梭巡防护》,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一《省局事宜》。
(29)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黄宗汉折。
(30) 韩椿等:《省局转详护漕勇船请酌拨枪炮药弹》,见《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续编》卷二《商船事宜》。关于此段时间的护漕,黄宗汉极为担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宗汉在信中称:“方苏兵溃散之初,我浙头批银米将赴浏河,适在昆、新一带有银十余万,一闻此信,我之魂魄随之,毫不怕贼,怕银为逃兵抢去。一两银,一点心血弄来,得自分毫,无才能可以报主知,拼命办此七十六万余石之米,聊表微诚。经费须六十余万银,加以仓场轻赍一款在外,须加十余万,共现银须七十万余两。自去冬至今,日则一点钟食早饭,夜则一点钟食晚饭。告示几万张,动兵五六次,札文上向各州县叩头乞救命,濡血濡涕等字样,千言万语,作威作福,摇尾乞怜,变幻百端,才弄此七十余万石。大致已十之七八,银甫得半,而打算各库不论甚么银,明日即抄家,今日亦先用,计算起来垫办得开矣。”见《何桂清等书札》,第125页。
(31) 《朱批奏折》咸丰四年五月初八日,钦差验米大臣端华等折。
(32) 《何士祁致吴煦函》,1854年2月26日(正月二十九日),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57页。
(33)(34) 《黄宗汉书》,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见《何桂清等书札》,第131—132、135页。
(35)(37) 《黄宗汉书》,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见《何桂清等书札》,第125—127、125—127页。
(36)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四年四月十一日,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报浏河兑运漕米情形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
(38)(39)(40) 《黄宗汉书》,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见《何桂清等书札》,第134、132、136、138—139页。
(41) 倪玉平:《招商局与晚清漕粮海运关系新说》,载《学术月刊》,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