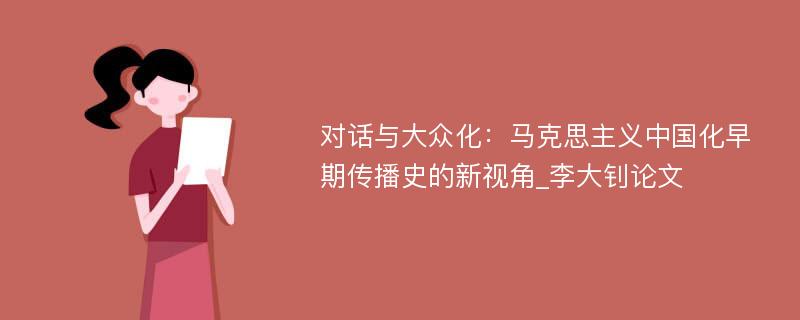
对话与大众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认识的一个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6-0043-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一日千里,国人趋新、趋西,传统文化遭遇寒潮,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主义广泛流布于中国社会。这是“主义”兴起的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一趋势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而愈益昂扬,“社会主义”即有几十种,以至于孙中山曾疑惑地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1]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也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哗众取宠,如北洋御用政客安福系王揖唐通过兜售“过激”社会主义来美化军阀统治。面对鱼龙混杂的“主义”冲击,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抽象理论不能取代实际问题,高谈主义不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要求大家“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2]胡适的立论受到学界关注并遭到回击。最早是蓝公武的驳斥,之后引来李大钊辩难,再之后又有诸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很快形成一场有意义的思想争辩。这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不久,关于这次争辩的起因、性质、规模及其影响就成了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尤其是胡适的立论和李大钊的辩难是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决裂,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等等。本文不愿意卷入这些争辩之后的再次争论,而试图另辟蹊径,从学理的角度谈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溢出学理范围的学理对话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究竟如何界定,长期以来是“百家争鸣”,互不相让。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曾一度被政治因素所干扰,被意识形态因素所左右。即使略去新中国成立初期批判胡适思想时所认定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论断外,很长时间以来,这一论争仍被一些学者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3](P249、258)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论,也是新文化领域同人分道扬镳的一次决裂①。其争辩“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由暗而明的争辩其实是“改良”与“革命”的对立。[4]
近年来,学术界对上述判断的商榷开始增多。更多学者认为这一争辩固然有政争的意味,但更应该说成是学理的争辩:“很难说当年的论争就是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5]这场争辩使人们能对“主义”建立起必要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应该成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6]甚至有学者以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仍是好朋友,甚至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认为他们之间当初的争辩范围是有限的、平静的、学术的,甚至当时双方还是同盟者②。
的确,“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陈独秀还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③。李大钊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宣传研究更多的还是一种学术层面的认同,没有上升到具体的革命实践领域。争辩的双方既不反对“主义”,也不反对“问题”,只是各有侧重。在胡适看来,“主义”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否则它便失去了意义;在李大钊等人看来,没有“主义”的指导就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显然,当年双方的争辩表现于学理的歧见超越了政治的分野。更何况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时,虽然李大钊等从事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介绍,但谈论社会主义的主要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进步党人和社会党人。[7]胡适最初言辞所向亦旨在谴责王揖唐等政客利用好听的“社会主义”来蛊惑民心④。
由于新中国建立后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使原本的学理争辩很快变了味道。包括胡适本人晚年也持如此看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8](P193)并把这场争辩看成是他“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⑤。显然,胡适刻意渲染了当初双方论争的政治意义。
历史发展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回过头来,对历史的认识和分析又掺杂了后人太多的政治意识的过度诠释,使这一争辩超越了学理范围,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领域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之后,中共党内知识分子不仅根据政治思想立场和革命时代的需要来阐释‘问题与主义’的原始发生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对‘问题与主义’作了追加性的评判”。这一评判“适应了不同阶段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充分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昭示了剧烈的时代变迁,也折射着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9]
“问题与主义”这一学理争辩被后人及当事人后来做政治化渲染的背后,乃是一种历史潜流的显现,也即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寻找新思想”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努力和激情⑥。这一冲动推动着当初学理争辩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理想进行社会实践,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裂痕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产生了巨大分裂,当年的学理性研究发生了政治性的严肃意义。此后,胡适虽以独立知识分子自居,但和政治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关系;陈独秀、李大钊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中国开始了革命的实践,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们不仅创立了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最终他们的后继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埋葬了国民党政府。毛泽东曾对这一分化有深刻的分析:“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10](P832)“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理歧见,演变成了政治思想的歧路,进而转变成了政治行动的分野,并使“主义”一方完成了从书生到革命家的蜕变。
二、矢志不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正面推进
“问题与主义”之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参与的人也不算多,但这次争辩却从多方面直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首先,“主义”派吸收了“问题”派的许多有益观点,促进了自身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成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践。“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时,“主义”派还没有进入到具体的革命实践阶段,但通过这次争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从“问题”派方面吸取了许多优点,从实际问题着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进程,以及对中国革命事业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实践。有学者就曾指出,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年后的反应来看,在最初的争辩后,双方都曾向对方表示善意,而马克思主义者一方似更明显;胡适的主张不时得到呼应,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人。[11]
此后,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倾向于关注中国实际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和大众化工作进行了最初的探索。李大钊认为,任何“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2]
陈独秀根据胡适的某些观点,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工作。陈独秀认为,“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13]这和胡适的实验主义观点有某些契合。其后,陈独秀在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时,开始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14]
应该说,这次规模不大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出路时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其争辩的结果,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在实践上更加积极。并且努力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以此推动实践的进程。
其次,“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主义”派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准备了最早一批理论家和践行者。作为争辩的一方,李大钊虽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介绍稍早,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却是在胡适的文章刊发后才明确表示出来的。[15]经过这次争辩,李大钊的思想更加成熟。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谈到:“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12]这一论述说明李大钊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开始尝试用它来解释中国的社会问题。
李大钊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早期的宣传骨干和组织力量,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争辩之后,李大钊更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章,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更加深入和宽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进一步的学理思考和创作灵感源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此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已经迈入实践领域,“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12]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面包运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妨害治安》、《出卖官吏——蹂躏人格》、《被裁的兵士》、《“用民主义”》、《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五一劳动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这些文章的发表和问题的提出,表现了李大钊务实的态度和积极参与讨论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的趋向,并期望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应用于实际,从而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广泛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主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推介马克思主义。
正是基于李大钊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迅速扩大。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在西方舆论的诱导和北洋政府的压制下,中国国内报刊普遍以“暴烈党”、“激烈党”、“过激派”等字眼形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至于布尔什维克究竟是什么样的主义,“十个人之中恐没有一个能够明白”,[16]这一状况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成果乃是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时,陈因身陷囹圄而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他当时的立场显然是“中立偏胡”的。[17]只是在陈独秀出狱之后,经过重新思考,他很快转变了态度。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陈独秀对“主义”的重要性进行解说,算是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做了一个总结。陈指出,研究问题固然重要,宣传主义更是必需,仅“把主义挂在口上”尚不算数,重要的是凭藉一个主义去“努力”进行。该文还特别批评了“一班妄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制度”的谬论。[18]这无疑是对“问题”派治标而不治本的改良主义主张的一个批判性回应。其后,陈独秀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社会主义批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答区声白的信》等,都显示出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陈以其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和科学的理论观点给了迷茫中的青年以切实的思想指导,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1923年,陈独秀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介入到“科玄论战”之中,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此后,陈独秀很快从理论宣传层面,转入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的实践中,开始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陈独秀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巨大成果。
再次,“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双方揭露冒牌“主义”,直接宣扬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胡适在挑起争辩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首先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2]胡适旨在揭露冒牌“主义”的言辞,无疑将反衬出科学主义的价值。同样,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也用了相当篇幅指责王揖唐等冒牌的“主义”,“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需要真正的“主义”来抵制冒牌的“主义”。他说:“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12]
论争双方对冒牌“主义”的批判,无疑唤醒了人们对真正“主义”的关注。那么,李大钊选择和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呢?他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12]李大钊的“自白”,显然有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的意味。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在中国传播不久,多数民众还不清晰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时代,李大钊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问题”派的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亦多次提到“马克斯”、“马克斯主义”,并部分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马克斯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竞争学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19]尽管胡适从反面立论,但他对世界范围内都相当吃香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拒斥,甚至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20]争论双方的论辩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论争双方通过批判种种冒牌‘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众多的‘主义’之中脱颖而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入了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引来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关注,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奠定了基础。”[21]
最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双方将争辩放在学理范畴之内,并通过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形式“百家争鸣”,将救国拯民变成了多数人的事情,将“主义”的传播变成社会各界的自由、自愿选择,这从根本上加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一种思想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就不能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说,必须让社会不同阶层参与讨论,然后推而广之。这就是李大钊在政治策略上的正确选择。在李大钊看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中国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12]于是,作为《新青年》第六卷主编的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七篇介绍马克思的文章,而其作者则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如顾孟余属于孙中山一派人物,黄凌霜则是无政府主义者,陈溥贤是改良派所办的《晨报》的重要撰稿人,刘秉林也是改良主义者,还有李大钊本人。
李大钊敢于将不同派别和观点的人物的思想拿出来共同讨论,足见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获得认可的信心,也反映出李大钊希望将马克思主义放到整个中国知识界去讨论,去引起关注的策略。瞿秋白即谓:“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对象。”[22](P294)有学者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几乎同时谈论马克思主义或对之感兴趣,当然不能看成是一种巧合,甚至也不能看成主编者李大钊的功劳,它反映了一种客观的趋势,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就是以这种特殊的形式拉开帷幕的”。[23](P36-37)这种特殊的形式,就是社会广泛参与、互相包容的共同讨论,这种自由、平等的讨论氛围,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可以说,“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是不同政治取向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也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双方所坚持的立场。这一立场成为五四时期一大批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最终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价值动力。
三、种豆得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种途径
作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一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正面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为争论的另一方——胡适及其所代表的“问题”派也客观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当中的传播。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20世纪20年代,许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进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却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活动,而是倾向于从事考据之类的学术工作。[24](P311)曾深受胡适影响,而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就是代表。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毛泽东受“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于“问题”派。毛泽东与同人在1919年9月1日于长沙创立问题研究会,制订《问题研究会章程》,着手对包括经济、文化、政权、教育、外交、实业等71个大类,大小共140多个问题的研究,毛泽东深受胡适实验主义思想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恰如其本人所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25](P139)毛泽东直陈自己在思想方面的追求即是“实验主义”。只是,随着毛泽东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及其实践的碰壁,其思想和胡适的实验主义发生了分离,并最终完成了超越。
毛泽东虽曾提出过需要解决的140多个具体问题,但和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他更倾向于通过引进“主义”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点滴的改良。“问题之研究,需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需为各种主义之研究”。[26]毛泽东开始在政治上重视信仰和旗帜,认定先有主义才能更彻底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在几次“改良主义”之实践碰壁,特别是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便很快与之彻底决裂。1920年11月25日,毛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之一法。”[27](P584)并且他还强调:“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25](P146-147)这种历经实践失败之后的认识,不仅深化了毛泽东对胡适“问题观”与改良思想的反思和歧见,也最终推进其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革命观的接受。此后,毛泽东将他的理想应用于实际。从1920年起,毛在长沙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致力于研究和宣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与蔡和森等一起组织对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南的建立和发展清除了障碍,而且为湖南中共人物群体的形成和成长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努力下,湖南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影响最大、马克思主义者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也曾深受胡适“问题观”及其实验主义的影响。他一度认为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环境,而实验主义哲学“刚刚能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28]整个世界思想文化进化史恰好经历了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当前的实验(主义)哲学时代。[29]显然,瞿秋白不仅认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流布是一种必然现象,而且将它作为一种新权威式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符号来加以推介。同样,经历了思想急剧变化的过渡阶段,尤其是在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和实践中,瞿秋白很快抛弃了以往他那“孤寂的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并指责“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定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而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28]从而开始接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实验主义的思考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渡。此后,瞿更是大力歌颂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只有革命,方能缩短“‘社会主义婴儿’诞生时间而减少其痛苦”。[30]
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受批判的胡适,也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渐已明确其身份认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不少人,多少分享着胡适的观念。[15]毛泽东、瞿秋白就是这方面的卓越代表,这也是这场争论之意义的最大限度发挥;另一方面,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揭橥或作为争辩的结果而彰显的诸如解放思想、不迷信、不盲从,经过实践来求证等道理,历经时间的检验亦显得弥足珍贵。以至于余英时认为:“中国大陆上今天喊得最响亮的两个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至少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31](P200)周策纵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告诫中得益最多的,实际上却是共产党人。”[5]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超过了当年胡适的想象,也超越了胡适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初衷。
四、小结:学理对话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2](P11)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主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空前关注,成了一个时髦的用语。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将“主义”理解为引导人们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旗帜”,[25]甚至激进的国民党人戴季陶也视“主义”为擎起革命的大旗和继续革命的号召。[32]“主义”之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问题与主义”之争适逢其会,将之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促使作为众多“主义”中科学性强而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持久而有效的传播。梁启超曾感慨:“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34](P45)
其间,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主义旗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理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争辩。争辩发生之时,双方都没有政治利益集团的背景,没有党派的意气成见,而且还是如切如磋的文化同盟者,开诚布公的政见协商者⑦,心态开放而交流自由。双方的争辩在很大程度上有“真理愈辩愈明色彩”,这即是李大钊所谓“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共同的认可”。[35](P413)在这种较高学理涵养论争背后,是各种思想碰撞的火花,以及“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立场的坚守和为自己信奉“主义”奉献的决心。各种“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充分的争辩和实践的检验而被历史选择或者遗弃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大众化是这一争辩的成果,也是这一争辩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2-02-10
注释:
①小田、季进:《胡适传》,第14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桑逢康:《胡适在北大》,第3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有趣的是,按照胡适的表述,这一次分道扬镳不是胡适和新文化阵营其他干将的分道扬镳,乃是陈独秀与“北大同人分道扬镳”。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1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美国学者格里德曾指出:“与第一个宣布他对马克思主义忠诚的李大钊,胡适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富有感情的友谊,直到1927年李被处死。”参见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第2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胡绳也指出这一争辩更多的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争论,都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争论。参见“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③胡适曾说1919年的陈独秀“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193页。确实,陈独秀在回答一名读者对社会主义的询问信中就言简意赅地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可见,1917年的陈独秀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参见陈独秀:《答褚葆衡》,《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④罗志田就指出:“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辑唐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仔细阅读胡适那几篇文章,可以发现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安福系。”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26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⑤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189页。三年后,胡适曾回顾说当时挑起这个讨论,一方面是安福部极盛、国内政局混乱,另一方面乃是新知识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参见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刊》第7号(1922年6月18日)。
⑥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195页。美国学者史华兹、唐德刚等有这样的观点:“纵是五四时期有名的‘守旧派’,也不是完全生活在传统中国里的人,或是预备以传统来做他们防御武器的。”换言之,纵是最守旧的反对派,对旧传统也不是无条件地去“守”了,那时的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主张提倡或多或少的新思想,来代替被所谓“儒家”所滥用的旧思想。
⑦胡适第一次写政论文章——《我们的主张》时,因想将此作为一个公开的宣言,于是“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此时的李大钊已是共产党人,可见此时双方关系仍然非常亲密。参见《胡适日记全编》(3),第66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标签:李大钊论文; 陈独秀论文; 胡适论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再论问题与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