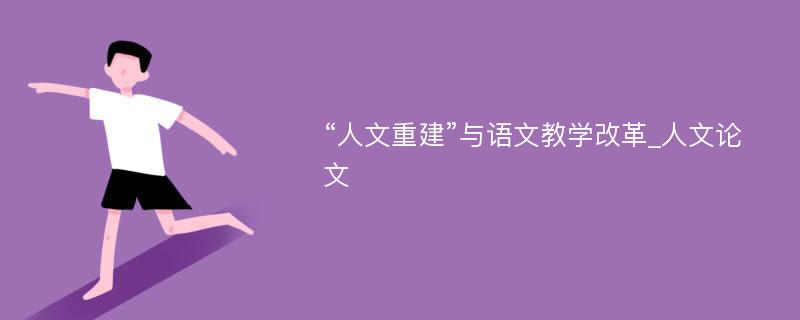
“重建人文”与语文教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改论文,语文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学术界关于“重建人文”、“重建道德”的讨论十分热烈。这场大讨论,针对社会风气逐渐远离传统、教育失误、价值观“物化”的种种负作用,针砭时弊,目的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恢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复兴我中华。
这场大讨论中,理论家们对于“重建”的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都在“重建人文”上。那么,什么是“人文”?为什么要“重建人文”?“重建人文”与普通中小学的语文教改又有什么联系?这是普通的语文教师不得不关心的大问题。
什么是“人文”?智仁相见。古文献《易》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即是“人文”。最具权威的国学泰斗钱穆先生解释说:“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他又说:“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须一身具诸德。……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1]这是以“仁”为核心,由人之一的观点,直演进到天下之一的观点。这是强调教化、修养和精神,使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它要求人们做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交,止于信。”[2]这是几经历史变迁,却不改初衷的观点,即“肯定人性的价值,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肯定人是目的,维护和弘扬人的主体性”。[3]
可是,长时期以来,我国忽视“人文”建设,到“文革”期间,竟毁灭文明,那时哪来“人文”,有的只是宗教蒙昧主义的“神文”。近十几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教育失误”,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而新的价值系统又没有建立起来,“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建设”,所以“人们的心灵无所归依,行为失范,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空前地衰落了”![4]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衰落的人文精神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广大的青少年,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对此采取了对策,但是在治“本”上还要花大气力。中、小学语文依据本学科特点,在对学生的“人生修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上,应该大有可为,但是,努力远远不够。
实现“四化”,复兴民族的希望在21世纪,在今天的青少年。所以“重建人文”对现今的青少年学生,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必须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标准,不在其地位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少,而在于是否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是否有高的“人文”素质,是否德、智、体等诸方面全面发展,否则难以承担“四化”重任,能以对自己、家庭、社会乃至天下实现“自我价值”。我国的“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物”的“现代化”,更重要取决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尤其需要具有“人文”的高素质。
“重建人文”不仅是中国的必须,也是全世界的必要。七十年代以来,东亚崛起,这是“工业文明”与中国儒教的“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西方专家因此称之为“后儒家社会”。这震惊世界,值得我们借鉴。现在,在日本、美国、西欧和世界上许多地方,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南朝鲜,则强调以儒学治国;在新加坡,对中学专门开设儒经伦理课,让学生一方面学习“经典”,一方面学习汉语言。七年前,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曾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同属于全人类所共同有的。五年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我国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对未来人才要求提出了相适应的伦理规范,这就是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的八个“关心”,充满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西方发达国家,重物轻人,以力横决天下,人们心为物役,重利轻义,不少人做人丧失原则,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际关系冷漠,现在他们中的有识之士,转向东方,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中国的儒教和“人文”,寻觅中国古老的“东方智慧”,以期获得济世良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走势。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抓紧教育,重建人文。
近十几年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拨乱反正,肃清极“左”。如中学语文大纲对过去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文学课”、“政文课”做法,提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要“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是给“语文”作了科学的定性定位。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依纲据本,在语文的德育渗透、在开发学生智力,发展其听、说、读、写能力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上作出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语文教法的艺术性探讨、语文学法的艺术性探讨,以及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和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方面的研讨等等,使语文教改进一步深化,这都应给予充分地肯定和高度地评价。但是整个中、小学语文还存在一些问题,致使不少语文专家们惊呼“速度效率偏低”、“实用性不强”,这原因究竟在何处?
依笔者浅见,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上“重理轻文”、商品经济的负面作用影响学生学习等等,除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些值得研究,如:在强调语文的科学性同时,没有鲜明提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修养”的培养。我国的“语文教育”在世界上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具有“中国特色”,它的知识综合性极强,是一种文化教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教育,同时也是进行学习汉语语言教育。这一点,从春秋战国时的《学记》到清代的《学海津梁》等众多的语文教育论著所论述的便是明证。到近代废科举、兴学堂之后,“语文”逐渐被“科学化”,但也逐渐淡化了“人文”。现在强调了“学习语言”,是一种进步,但没有鲜明提出“人文”问题,而缺少“人文”,远离传统,语文在其指导思想上,在教材内容上,甚至在教学方法上,就缺少了“生命”的源头活水,它的“舞台天地”太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适应不了“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应借鉴古人,重树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语文教育观。
正如现今的语文教材,缺少展示中华民族“元典精神”的“经典”。没有这些“经典”,学生就不能直接接触优秀传统文化,也就谈不弘扬它,也就不可能具备“人文精神”。
近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在普及知识教育上,在传播新思想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对以“经典”为代表的旧文化的清算上,缺乏冷静分析的理智,只凭强烈的爱国热情,全盘否定了“经典”。兹后,独专白话文,而废除了我们祖先的珍贵的典籍,并不断地批判了先哲们的不朽的思想。其实“经典”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可以“重建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们重估《学衡》是正确的了。也许有人会问:“三纲五常”也正确吗?回答应是:“三纲”不正确,是负面的,它不符合孔孟儒家传统精神,但它是从汉朝开始起被后人异化的,至于“五常”或“五伦”是可以作现代化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当然要分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再如在教学方法上,现在重分析、重理解,受西方影响很深。美国杜威博士的理论“教育即生活”、“理解为教育前提”;前苏联不少教育家的理论,他们强调科学,科学讲求的是知识的系统性,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这对于自然科学的教育行得通,但对于中国传统的语文,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是广义的文化教育,它所突出的是人文教育、文化素养的培养。所以在方法上,注重“时雨春风”的陶冶,讲究“熟读而精思”的读书法,提倡“长善救失”的原则,在教授过程中还强调“身正而行”的为师之道。在语言上,汉语言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点,因此倘用西方分析语言的方法分析汉语语言,其效果有时甚至味同嚼蜡。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说:“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是朦胧、模糊,它的涵盖面几乎无边无际,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而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分明。”接触一下古代经典,读起来赏心悦目,不少语言极具结构美、音乐美、词语凝练美,包括象庄子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作品,读起来竞感到诗意盎然。我国古代这些经典作家,他们都是一些最好的语言大师,读经典又可以学习祖国的母语,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经典”上语义,绝不是靠西方“科学方法”分析出来的。
“重建人文”与当今中、小学“语文教改”是这样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指导下的部分实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部分结果。这不正是“大语文观”吗?
注释:
[1]钱穆《民族与文化》第32页—33页
[2]《大学》
[3]郁建兴、王小章《马克思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4]李宗桂《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新华文摘》、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