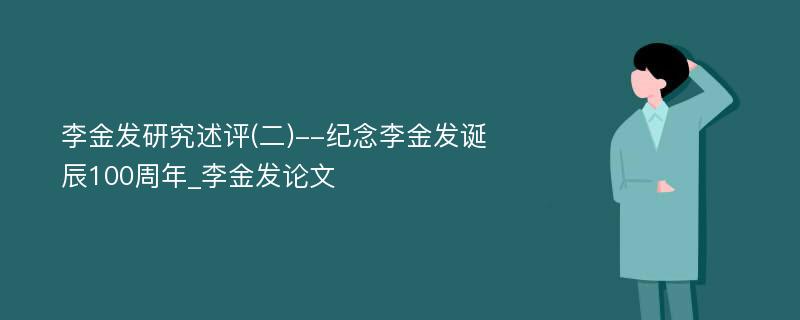
李金发研究述评(之二)——纪念李金发诞辰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诞辰论文,之二论文,周年论文,李金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独尊现实主义语境下的李金发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本文个别地方涉及海外)的李金发研究可以198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李金发几乎被人遗忘。这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因为从30年代中后期起,李金发就从诗界文坛淡出,对诗歌创作几乎不再有什么热情,偶尔动笔写点东西,也是小说、散文或游记、时评之类居多,诗作很少。担任国民党政府驻两伊外交官员之后,虽也保留了一点文人的风雅之趣,时有文章发表,但已不能产生什么影响。1951年全家移居美国后,更是深居简出,不事张扬,李金发就更加不为世人所知了。其次,共和国成立后,在独尊现实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延安窑洞里出产的“工农兵文艺”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强行进入文艺批评领域,社会、历史、政治的批评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唯一合法的批评话语。抗日救亡历史背景下生成的战争文化审美规范统摄了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切艺术领域,带着浓郁的“异国熏香”的李金发与其所代表的象征派诗,要么无法进入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被认真对待,深入研究,要么就被当做反面教材,贴上“反动”、“逆流”一类的政治标签,恨不得满门抄斩,一网打尽。前者如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厚厚的两大册,是同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但他们就是只字不提李金发和象征诗派,似乎新文学史上压根儿就没有李金发、象征派诗歌之类。后者则可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他们认为,李金发及其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代表着中国新诗创作中没落颓废的倾向,其消极厌世,悲观绝望的情绪,恰恰是其“内容浅陋”的最好说明,“畸形怪异”毫无章法可言的诗形,是其“病态人格”的折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和他所代表的象征诗派,“是新诗发展途中的一股逆流”(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94页。),其“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注: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55页。)。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臧克家说“李金发留学法国,巴黎的那种霉烂生活,使他沉浸在官感的享受里,形成了他的颓废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奇怪了(注: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见《中国新诗选(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相比较而言,谢冕的批评就算是温和的了,他说李金发的“诗根本无法读懂,实在是对祖国语言的一种侮辱……他的诗没有一点中国味儿”(注:转引自[苏]契尔卡斯基:《论中国象征派》,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第361页。)。这种或视而不见或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政治大批判式,全盘否定一概抹煞的做法,一直维持到1980年。
七、浮出历史地表的李金发
1980年以后,随着现代中国新一轮启蒙思潮的到来,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显得格外活跃,因“朦胧诗”论争而起的关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和讨论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界的热点。李金发和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一样,像刚出土的文物似的被人热烈地谈论着。但是,这时李金发早已在大洋彼岸作了古人。研究者首先碰到的难题是他谜一般的生平、身世。像他的诗歌一样,李金发的生平也是扑朔迷离、捉摸不透。许多人错把他在《语丝》杂志上发表第一首诗作《弃妇》时所用的笔名“李淑良”当成原名,而且后来一直被人广泛使用,被写进各种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和新诗研究专著(注:冯光廉、刘增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84页。
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5页。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第206页。
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出版,第143页。
钟友循、汪东发:《中国新诗二十四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出版,第541页。), 一些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工具书也宗此说(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有研究者将李金发的别名“遇安”误认为原名的(注: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48页。), 或者干脆把因为一个梦而随意取的笔名“李金发”(注:李金发:《我名字的来源》,见《异国情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第37—40页。),当做诗人的原名,还说是因为在南洋经商的父亲“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经商发财,因此给儿子”起了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等等(注:丘立才:《李金发生平及其创作》,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第147页。),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毋庸置疑的定论。一位自称认识李金发的文学前辈,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一次现代文学讨论会上还说李金发“是华侨,在南洋群岛生活,中国话不大会说,不大会表达”,他“原来学美术,在德国学的,法文不大行”(注:卞之琳:《新诗和西方诗》,见《诗探索》1981年第4期,第40页。此文原是卞之琳先生在1981年 4 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文中所引是卞之琳发言时孙席珍的插话。)。言之凿凿的发言姿态,俨然一个知根知底的知情人。其实,这些都是误会。这种是非莫辨、各执一词的现象恰恰表明问题的复杂,意味着我们的研究须得从头做起。所幸的是,这一阶段有了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海内外文化学术的交流日益活跃,许多以前视为禁区或无法深入的问题现在有了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 期发表了丘立才的《李金发生平及其创作》,他们都对李金发的生平、身世、经历等做了认真梳理。前者虽然不属个案研究,但重点是在李金发。在这些研究中,有些细节虽不够准确、翔实,但总体轮廓是清晰的,朦胧的面影不再神秘。在此基础上,1986年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李金发评传》(杨允达著)和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陈厚诚著),在李金发家世、生平的研究上又取得了新的成果,他们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廓清了原来存疑的某些细节问题,两书后面都编有李金发年谱,他们纠正了此前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譬如说,李金发在欧洲娶的洋小姐的国籍问题,杨允达和陈厚诚都由传主的亲属或后裔获得证据,确证李金发娶的是一位德国姑娘,纠正了以前“法国小姐”一说(注:杨允达:《李金发评传》,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出版,第64—65页。
陈厚诚:《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69页。)。
陈厚诚的《李金发传》对李氏一生的经历做了全方位的展示,生动地再现了诗人生活、创作、艺术等各个方面,为研究李金发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八、囿于成说的“冒牌论”
这一阶段关于李诗的评价,虽然不再流于肤浅的简单否定,但是,要作出一个真正使人信服的结论也很难。
艾青、卞之琳、周良沛、李旦初等人囿于历史定见,对李诗仍持激烈否定的态度,停留在原来的“难懂”、“逆流”之类的认识上,称“‘象征派’是新诗中的一股逆流”(注:李旦初:《“五四”新诗流派初探》,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第130页。),说李金发的诗“好像是外国人写的”,“完全离开了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把人引向不可理解的迷雾中去”,“比中国古诗更难懂”,这样的诗“在人世里很难找到知音”(注: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代序)》,见《现代百家诗》,北京:宝文堂书店1984年出版。),并以“糊涂体”讥之,说他“对于本国语言几乎没有一点感觉力,对于白话如此,对于文言也如此,而对于法文连一些基本语法都不懂,偏要译些法国象征派诗,写许多所谓法国式的象征派诗,结果有过一个时期,国内读者竟以为象征派诗就是如此,法国象征派诗就是如此。也有过一些人竟学写这样的‘糊涂体’”(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卞之琳:《新诗与西方诗》,见《诗探索》1981年第4 期第40页。)。说得最绝的是孙席珍,他说“要说引进象征派,李金发是第一个”,但是,他的诗既不是白话,又不像文言,“杂七杂八,语言的纯洁性就没有了”。“引进象征派,他有功,败坏语言,他是罪魁祸首”(注:卞之琳:《新诗与西方诗》,见《诗探索》1981年第4 期第40页。)。著名诗人、诗评家周良沛认为,李金发“‘引进’的不是象征主义,只是李金发主义。‘引进’的既有一部分人对于了解西诗,丰富诗艺的渴求,也有既知其‘难以卒读’,又需要象征主义做旗帜的希望,于是,不是他有魔力,人家就已入魔,是他首先被冒认,然后才成冒牌的象征主义者,由此,也就引进了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自嘲,成了诗坛愚人节上演的一出迟迟无法闭幕的闹剧”。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不是“因诗而传”而是以“诗人的名字如此而传,这也是‘诗怪’传下的怪事”(注:周良沛:《谈“诗怪”李金发的怪诗》,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4期第110页。)!作者因此叹道:“这是李金发之幸或不幸呢?这是历史的误会,还是我们误会了历史呢”(注:周良沛:《“诗怪”李金发序〈李金发诗集〉》,见《李金发诗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前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青年诗人带回国的并不是原生状态的法国象征主义,而是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法国象征主义”,他说,“李金发那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诗”,“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法国式的,它没有民族面目”(注:[苏]契尔卡斯基:《论中国象征派》,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第359—361页。)。这显然是说,这些不伦不类的玩艺儿,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既没有社会价值,也不具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类似倾向的评价还有不少,恕此不赘。
九、广阔学术背景上的重新观照
所喜的是,8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更多的是将李诗置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下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一批新诗研究者,引入新的理论资源,用新的批评方法,如哲学、创作心理学、人类文化学、形式批评、语言哲学等,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上对李诗作出新的阐释和具体的历史评价,譬如新诗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孙玉石、谢冕、蓝棣之、陆耀东等,对李诗均有精辟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既有偏向于史的发展、流变和文学渊源的梳理,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或者是具体的诗作本文的解读。
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李诗具体的思想意蕴、主题倾向、诗美诗艺、表现技巧等特征的研究;二是李金发在中国诗坛出现的历史原因、文化背景的探讨;三是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以及与新月派、现代派等的关系;四是李诗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关系;五是李诗怪异神秘、难解晦涩之谜的研究;六是李诗创作的缺失。
(一)李金发诗歌的思想内容
孙玉石认为,“歌唱女性和爱情”,描写自然风物,抒发爱国思乡之情是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他大胆地将“丑恶,死亡和梦幻”等颓废意象纳入“艺术表现的视野”,大大地扩展了中国新诗的表现领域(注: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也有研究者说,李金发的诗“是一个失路的灵魂唱出的奇异的哀歌”(注:金钦俊:《新诗二十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04页。), “表现的是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空虚”,“绝望厌世的思想情调”,充斥其间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对死亡的颤栗与讴歌,病态的呻吟与欢乐,寂灭的感叹与祈求”等等,乃是“世纪末”的“‘现代’情绪的典型反映”(注:龙泉明:《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论》, 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第88—100 页。),是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产物。他的诗还留下了诗人身处异域备受压抑和歧视的痛苦记忆,大部分诗作中的抒情主人公正是一个孤苦可怜,茕茕孑立的“弃妇”形象。他的诗,又可以说是一个天涯孤客唱出的漂泊之歌、流浪之歌。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知识分子在“面临自身独立的人生选择”和独立人格的精神建构时,因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进退失据,去从无着而产生彷徨感、悬浮感的结果(注:李怡:《李金发片论》,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8年第4期,第183—194页。)。
陆耀东、宋永毅、杜学忠等还认为,除了以上几点外,诅咒、抨击物欲横流的社会丑态,表现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展现异城的风物人情,山光水色,欧陆情调等也是李诗的一个鲜明特点(注:陆耀东:《论李金发的诗》,见《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70—310页。)(注:宋永毅:《李金发:历史毁誉中的存在》,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82—408页。)(注:杜学忠、穆怀英、邱文治:《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第39—66页。)。
总之,“从《微雨》到《异国情调》,李金发诗大体是涉及人生的体验,以及他所经历的值得回忆的一切”(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11页。)。
(二)李金发诗歌的流派特征、创作方法、表现技巧
多数研究者对李金发在中国传播与实践象征主义诗艺是首肯的,普遍认为,李诗是典型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孙玉石在他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就明确写道:“李金发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西方象征派引进中国新诗国土的诗人”,吴中杰也说:“将法国象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当推李金发”(注: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5年出版,第二名3页。)。在李金发之前尽管早已有人在中国译介象征主义的诗学文献和文学作品,但仅止于理论的倡导和作品的译介,而李金发却是“首次将法国象征主义移植到中国”的一位诗人,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实践者和尝试者”(注:陈思和:《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见《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45页。)。 陆耀东说,李诗“是中国新诗中最典型的象征派作品”,“他的诗是典型的象征派诗,完备的象征派诗”(注:陆耀东:《论李金发的诗》,见《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70—310页。)。蓝棣之在他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从象征派、现代派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典型特征是象征主义”(注: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出版,第261页、200页、257页。), 龙泉明也说李金发是“典型的中国象征主义诗人”(注:龙泉明:《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论》,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第88—100页。)。此外,金钦俊的《新诗三十年》,谭楚良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张同道的《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钟友循、江东发的《中国新诗二十四品》等,对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风都持不争的态度。吴晓东则说得更干脆,他说:“以李金发、穆木天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诗人,在哲学观的层面上是深得象征主义思潮的个中三味的”(注:吴晓东:《“契合论”与中国现代诗歌》,见《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可见,研究者对李诗的象征主义诗学特征是普遍认可的。
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没有不同看法。此前所述周良沛和契尔卡斯基就认为李金发引进的不是法国的象征主义,而顶多只能说是冒牌的象征主义。另一位新诗研究者李怡则说,他在李金发诗歌中看到的不是象征主义的颓废和绝望,而是“微笑中的自信自持,颇具浪漫派风采”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上”俨然一位“暂时受挫的孤胆英雄”,“不断寻找理想又不断失望”,始终不改的是“一颗孤高的心”。因此,李怡认为,李金发是怀抱“浪漫主义诗人的情愫”的“漂泊者”和“游猎者”,诗风与浪漫主义诗人更加接近(注:李怡:《李金发片论》, 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8年第4期, 第183—194页。)。另外,台湾学者杨允达则认为李金发的诗“很富阿波莱尔(通译阿波里奈尔——引者)的颓废之风”(注:杨允达:《李金发评传》,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出版。)。
在创作方法、艺术表现技巧上,李诗的主要特点,孙玉石把它概括为:第一,运用象征性的形象和意境,表现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第二,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第三,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第四,是观念联络的奇特(注: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谢冕说:“这类诗弃绝对于生活场面的直接描写,也不试图以直抒胸臆的办法对他所感受的一切进行抒情。他借助象征的形象的展现和组合,隐秘地、曲折地、甚至是怪诞地表达主观感受和丰富复杂的内在情感。直接性的描写和抒情不见了,人们得通过这些呈现去探寻他的象征意味(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7页。)。
另外一些研究者,如龙泉明、宋永毅、张同道等,他们认为李金发的诗艺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诗的思维术;二是诗的逻辑学;三是语言陌生化的尝试;四是雕塑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技巧的影响和借鉴。
具体地说,就是大量使用象征、暗示、省略、跳跃、通感等表现技巧,不固守文法,打破语言常规,改变原有的搭配习惯,将不相属的观念、认识联络在一起,于常人看来不相同的事物之间看出同来,发挥超常的想象,创造出新鲜奇特的诗歌意象;不重题材,偏重形式,表现的是些微妙朦胧的情调、情绪、幻觉或内心感受,在具体写法上则有意割断诗句与诗句之间的联系,抛开传统诗歌作法的起承转合等套路,东一笔西一画,完全是感情的涂鸦。“契合论”是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它直接影响了象征派诗人的世界观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注:吴晓东:《“契合论”与中国现代诗歌》,见《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故李金发诗艺的一大特点就是“契合”。
(三)“李金发现象”产生的文化背景、历史原因
李金发出现在20年代的中国诗坛,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具有十分深刻、丰富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的文学史现象,它是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和中国新诗自身发展规律交互作用的结果。孙玉石把李诗出现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是,时代的气候对青年精神的影响”;“其次是,异域文学营养吸取结出的精神果实”;“第三是,新诗本身艺术发展规律的需求”。蓝棣之则将李金发和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置于全球性的现代艺术潮流中加以考察,在世界文学格局的广阔背景和中国新诗自身发展运动的轨迹上来理解李金发所开启的一代诗风。他认为,象征派诗是为了“补救写实主义之弊”,“对抗”和“反叛”浪漫主义的“坦白直说”、大喊大叫,而出现在中国诗坛的一种文学史现象。他说,“从中国新诗的发展看,新诗是从浪漫主义,经过新月派而发展到象征主义的。象征派诗人们跨越了巴那斯阶段,新月派诗人们却在巴那斯阶段停留下来探索建树,然后转向象征主义。”在蓝棣之看来,“周作人肯定和提携李金发,施蛰存捧出戴望舒,都是因为李、戴诗风在中国是异军突起,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反叛”(注: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出版,第261页、200页、257页。)。谢冕的分析是:“李金发在中国倡导象征诗, 一方面是由于他在法国对这一诗潮有直接的了解与接触”,“使他能够把握当日风靡世界的象征主义的氛围”,“诗人置身于那个环境又继承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感知,很快地与世界潮流产生共鸣,这便是李金发及其所代表的象征派诗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另一方面,就创作主体而言,“他的诗歌实践是五四初潮之后对于忽视诗艺自身而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纠正倾斜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当时新月派的整体争取相一致,他也致力于纠正五四初期那种对诗艺切磋的轻忽和冷淡”(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10页。 )。龙泉明的观点和蓝棣之有相似之处,他认为,象征派诗的出现是因为“中国象征派诗人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那里找到了对抗‘坦白直说’、过分的感情宣泄和缺乏深沉含蓄的艺术缺陷的出路”,新月派和象征派对“新诗流弊的修正和超越”走的分别是两条不同的路:“一重形式,一重表现,两者在艺术上都是富有创新意义的建构,都是对整体的新诗的一种推进和拓展”。他们对“新诗坦白奔放、直露肤浅倾向的反叛”对西方现代诗意象繁复、诗意朦胧、晦涩多义的风格的崇尚与追求,可以看做是中国白话诗的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它有效地遏制了“新诗太实、太白、太直、太露,缺少诗味的艺术弱点”的继续发展(注:龙泉明:《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论》,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 1期第88—100页。)。
(四)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孙玉石认为,“李金发始写于1920年而公开发表于1925年的诗作,是新诗中象征主义由萌芽走向真正诞生的标志”。他说,“从创作实践上,为新诗最早引进西方象征派的艺术潮流,并用大量的作品显示中国象征派新诗的实绩,从而引起了中国诗歌中一个新的艺术流派的兴起,这不能不说是青年诗人李金发的贡献”(注: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蓝棣之认为,“象征派、现代派真正突破了胡适的诗的‘明白清楚’主义的藩篱,超越了胡适语言和诗体革命的目标,而带来了以意象暗示内心意绪的朦胧诗风。”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更接近于诗的本质”。而且,李金发的诗歌活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现代派,他以为,现代派的“戴望舒注意到了李金发的新路向”,但同时又“不满意李诗的神秘和看不懂”,觉得李诗“没有体现出法国象征派魏尔伦诗风中”的优秀品质,所以直接读了法国象征派的作品,一跃而为现代派诗的领袖(注: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出版,第261页、200页、257页。)。另外,王泽龙、凡尼等也认为, “在现代派的创作中明显地反映出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注:王泽龙:《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位置刍议》,见《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31—36页。),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所代表的是“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从幼稚到成熟的历程”(注:凡尼:《从李金发到戴望舒》,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 期,第44—51页。)。谢冕给李金发的评价很高,他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李氏在诗坛所进行的“大胆的试验”是“纠正当时新诗创作的随意散漫的倾向”的自觉努力,李诗的出现说明,“当浪漫主义的潮流流行中国之时,象征诗就以先锋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诗坛”,“其意义在于它证实中国新诗现代主义初潮”已经到来,中国新诗“继新月对纯粹诗美和形式化的追求之后,象征派诗的出现,它的反叛传统和挑战品格,事实上极大地拓宽了当日诗坛的视野”,“象征诗作为中国新诗现代初潮的涌现,开启了新的奇异的诗风。李金发在他当日和身后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怀疑和责难,但他依然有着倡导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气以及播下象征诗种子的功绩。”(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1页。 )李金发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先驱”(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6页。)。谢冕还说, 李金发的“也许更为突出的贡献,却是公开的、勇敢的把西方情调和异域的艺术方式引进刚刚自立的中国新诗中来。他也是东西方诗风交流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工作与五四前后那些向着西方盗火者的业绩一起,记载在中国新诗史上面,不会也不该被遗忘”(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15页。), “从艺术观念的引进和实践的角度看”,象征主义诗歌和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为艺术的浪漫主义,“都是对于世界曾有过的艺术实践追踪式的补偿”(注:谢冕:《新世纪的太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11页。)。 龙泉明的意见是,“象征诗派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主要不在于提供了多么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情感内容,而是提供了与以前新诗完全不同的新的表现技能,赋予诗歌一些新的变化和革新,推动了自由诗的发展,开创了新的诗风”(注:龙泉明:《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论》,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第88—100页。)。
所以有人说,当日的中国诗坛,即便“没有李金发后来也会有李金发式的诗人出现”(注:陆文綪:《李金发与戴望舒:超步与超越》,见《求索》1994年第 1期。)。长期遭人诟病的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巨大的历史贡献,得到充分肯定,它再次表明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不是可以轻易翻过去的一页。
(五)李金发与中外文学、艺术传统的关系
李金发曾一再声称魏尔伦、波德莱尔是“我的名誉老师”,说自己是受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影响才开始写诗的,这在李金发研究中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李金发只宗一家一派。事实是,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从他不多的诗论看,影响李金发的艺术因素是多元的,仅就诗歌领域而言,李金发“读过、译过并受到影响的西方诗人”就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单,如古希腊的荷马、碧丽蒂,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歌德、席勒,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拉马丁、缪塞、戈蒂耶,前象征主义的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兰波,后象征主义的瓦雷里等等(注:宋永毅:《李金发:历史毁誉中的存在》,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82—408页。)。李金发还曾经特别强调说“我还是喜欢读拉马丁、缪塞、 沙庞(Aehert Samain)等的诗, 这也许因为与我的性格合适些”(注:李金发:《诗问答》,见《文艺画报》1935年第1卷第3期。)。李怡在《李金发片论》中也曾敏锐地指出李金发诗中的浪漫主义倾向,这在前面的评述中已经谈到,恕此不赘。
李金发原本习雕塑,为学好雕塑,他又学绘画,而且,他又恰好处在艺术风云变幻无定,艺术流派多姿多彩的艺术之都巴黎,印象派、现代派、立体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画风无不对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宋永毅说,“印象派重视光、色组合及其音乐效果的手法,对李金发诗歌的影响是明显的”(注:宋永毅:《李金发:历史毁誉中的存在》,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82—408页。)。象征主义与印象派绘画的关系早有研究者论及,《林风眠传》的作者郑重就说:“象征诗人与印象派画家,有着心灵上的相通”(注:郑重:《林风眠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作为一个雕塑艺术家,雕塑艺术不会不对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唐弢说,李金发将“雕塑的艺术引入诗中,别有一种浑成的感觉”(注:唐弢:《唐弢书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出版。)。宋永毅认为,李金发最欣赏的三位世界著名雕塑家吕德、罗丹、米开朗基罗,“无一不带一定的感伤色彩”。既然如此,李诗带有浓重的悲观厌世情绪就在情理之中,其“灰色”“晦暗”的诗风与雕塑艺术使用青铜、花岗岩等材料的颜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宋永毅还认为,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地影响了李金发的诗歌创作(注:宋永毅:《李金发:历史毁誉中的存在》,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82—408页。)。
李金发的诗,初看洋味十足,但是细加咀嚼就可以辨出其中有很重的古典味,蓝棣之一再指出,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晚唐六朝温庭筠,李商隐一类诗词”有着“惊人的相似”(注: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出版,第261页、200页、257页。),中国的象征派、现代派“都从西方象征主义和中国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诗风汲取一些共同的东西”(注: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出版,第261页、200页、 257页。)。宋永毅也认为李诗的“伤感”是“中西合流的”。“温李那一路的诗句”是李金发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注:宋永毅:《李金发:历史毁誉中的存在》,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82—408页。)。
标签:李金发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