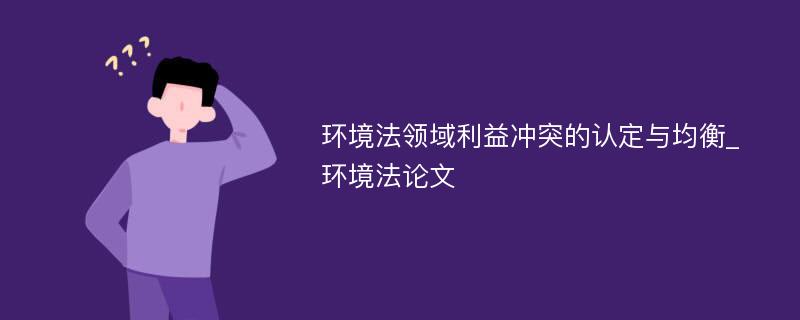
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冲突论文,领域论文,环境法论文,衡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15/j.cnki.fxpl.2015.06.015 一、环境领域内的利益需求和冲突 (一)环境法领域的利益需求 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涉及利益的识别和衡平。这里,利益指人的需求及其需求的满足。需求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个体的和集体的、正当的和非正当的。满足指面向和实现正当需求诉愿的正当的条件和方式,包括法律的和非法律的。由于利益的多元、多样、多层次的存在,利益之间存在着多元、多样、多层次的冲突,注定利益的识别和衡平须采多元、多样、多层次的理念和方式。此为利益的本质属性之一。 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识别和衡平)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环境法的研究当应以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为主要任务。权利、权力与义务是利益的法学核心表达、阐述和展开。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权利就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律首要的任务是调整因每个人根据其价值而获得待遇的不平等之利益关系。罗斯科·庞德指出法律秩序所保护的是利益而不是法律权利,法律是一种获得利益的手段或是社会关系的保护。①由此,笔者认为,法律是获取或减损利益的方式,是利益认可、给予、限制、剥夺或致损的正当、正式、规范、合法、最终的方式和手段。在一般意义上,法律关系即指利益关系。所谓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制裁实际是围绕利益展开。法律权利可以认为是利益获取或扩张的方式。法律义务是利益的限制或让渡方式。法律制裁是利益的限制、剥夺或负值(负利益)方式。调整法律关系,实为识别和衡平利益关系。这说明法律关系的调整即利益的识别和衡平是动态的过程、渐进的过程、进化的过程。② 环境法无疑存在着利益和利益需求。人们的环境利益不限于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生活,诸如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等,包括生活质量和生活能力,即应包括“人之为人”的全部要素和条件。在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直接表现可以简略表达为持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及其满足能力之间的冲突。就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法学认识而言,应当注入人文关怀,认识到环境问题与其说是经济行为的副产品,不如说是经济社会科技进步利益与环境利益不良衡平的结果,或曰未得合理衡平的结果。当下中国弘扬和建设的生态文明,在环境法领域的引领作用和实证功能可以解释为,它是环境立法依托的规范理念和伦理文化,它指引和支持环境法的目的和功能,促进合理地识别环境利益和衡平环境领域的利益冲突,形成和维持有利于人与环境和谐的社会秩序,持续提升人的生存质量。在理解生态文明的含义和解析要素时,不可以采取“见物不见人”的分析态度,仍应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康德指出:人的最高价值应被阐释为绝对目的,即要把人的价值——成为人——作为目的第一位和首要的法则。③这种法则从形式上说具有普适性。 有两个与环境法领域利益需求和识别的相关学说,应引起格外注意。第一个是美国的社会学家马洛斯的六大需求学说,即需求层次论。④这一理论说明了利益的多元、多样、多层次性,揭示了利益的类型化、客观化、真实化和时空可变化的规律;它尤其要求人们在进行利益识别和权衡时在方法论上应遵循类型化分析和时空有限性运用。第二个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的论说。“四大自由”是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⑤这一理念提醒人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不只是环境的生态功能的恶化或丧失,不只是对生态条件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威胁和损害,是一种权利的被剥夺状况,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剥夺。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环境法领域的利益需求的内核与外延均显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性需求即持续的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人对生活质量有着多样多重的要求,笔者认为它至少应包括:第一,生活的方便度;第二,生活的舒适度;第三,体面和尊严;第四,吁求、争取、保障基本生活质量并持续的提升生活质量的自由权利或为此所开辟的通道。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所阐述的:这种发展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和关注文化价值的社会新发展。⑥美国学者德尼·古莱认为:当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实”而不是“更加充裕”时,社会才更加人道或更加发达。⑦发展的主要标准并不是生产或物质福利的增加,而是人们生活质量的充实。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已经说明,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变得比单纯的经济指标更为重要和紧迫。由此,可认为,人的利益需求在环境法领域已经进一步地发展和深化,它已并非一般的生存要求,而是更高层次的生存、生活质量的要求,是越过基本生存要求的生活质量的更高层次、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要求,是在衣食满足后更高的生活需求——可称为发展要求。人的发展需求的实质是对自由的吁求,不只是物质性的增长和充裕,也是为了扩展人的实质自由。自由是人的发展需求的最终目的,亦是发展的重要手段。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著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很多启示。他认为:发展就是扩展人们的真实“自由”,即人们拥有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⑧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原则1申明: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从国家角度来看,保护自然和维护自然的正义是国家的一项基本义务,也成为环境法的基本目的并要求其成为环境法的基本功能。《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确认: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对于人的福利和基本人权,都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发展,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各国政府应尽的责任。 (二)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蛙跳式”跃进,人们的生活条件已有了明显可感知的改善,生活质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透过提升生活质量的强烈要求而表现出愈来愈多样和广泛环境利益需求,民众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和发散。这种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变化自然会在环境和环境法领域反应和展现。当今中国社会进入了环境敏感时期。近一些年来,公众对环境权益的表达和维护往往转变成利益冲突,即在正常途径不能疏通致使民意的合理表达和上传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环境维权催发成由环保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抗议。这种大规模的行动,通常是缺乏理性的,甚至在部分场合滋生暴戾之气而出现场面失控,演变成法国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和美国的伊罗生在《群氓之族》中所描述的令人失望、沮丧、唏嘘和扼腕的现象,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产生社会性的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形成美国汉娜·阿伦特所称之为“平庸的邪恶”(或译为“平凡之恶。”),“作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大奸大恶之徒,普通者亦可能在丧失理智、盲目服从时所为”。⑨美国的米尔顿·迈耶在《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一书中也有酣畅淋漓的解析。尤为令人颤怵的是,在这种情景里,政府和某些专家跌入了“塔斯陀陷阱”,这就是,当政府部门失去民众信任即失去公信力,无论你是在说真话还是假话,你在做好事还是坏事,民众都认为你是在说谎和做坏事。这是可悲可怖的局面。有研究者指出:根据核心诉求的不同,可将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类:“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性事件”。这三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驱动力量分别是:经济利益,不满情绪和政治权利。⑩这些现象同时也凸显了对国家治理的体制的合理性和能力的可行性的质疑。有研究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长期存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演变并激化为“人民紧迫需要的公平的生存、生活及生产发展的环境与相对落后的国家治理体制之间的矛盾”。(11) 环境法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确认、保障环境权益,合理衡平在环境领域中发生的利益冲突,排除对环境权益的威胁和损害。对环境权益的威胁和损害,有着诸多因素,其中发展与贫困的因素是基本的和关键的因素。发展不足尤其是贫困,威胁和损害人的生存质量,威胁和损害人民的基本福祉,限制和剥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炫耀性消费为表象的过度发达,其过度消费和损害了生态的供给和消纳功能,同时也对人的生存质量产生威胁和损害,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产生威胁和损害。由此,从法学角度理解,环境问题可以划分为两类:因发达引起的环境问题和因发展不足所致贫穷引起的环境问题。《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确认:在发展中国家,多数的环境问题是发展迟缓引起的。因此,它们首先要致力于发展,同时也要顾到保护和改善环境。在工业发达国家,环境问题一般是由工业和技术发展产生的。在具体应对环境问题时,应当认识到:生存需求永久的拥有绝对优先权。所以,环境问题永远让位于生存问题,任何理由都不能够凌驾于人类摆脱贫困的要求之上。有些环境问题是因贫穷导致,但无论如何,人们不应该因环境保护而导致贫穷。环境法关注的应是基于提升生活质量的发展的需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二、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的实质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环境法领域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的直接表现可以简略表述为:持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之间的冲突,也即发展与保护的冲突。 (一)利益要求的同源同质性 经济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即发展的需求,其宗旨在于维持、改善生存条件,提升生活质量,这是正当性需求。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的宗旨同样是维持、改善生存条件,提升生活质量,这也是正当性需求。因此,这两种需求在动力源泉和本质属性方面是一致的,都涉及如何拥有和实现安全、充足和尊严的生活的条件,即对提升生活质量的选择的自由。 (二)利益冲突是选择自由的权利冲突 当主张保护环境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会在客观上对某些发展需求形成限制。由于自由首先是选择权利(选择和不选择的权利),权利的多少和实现条件是自由度的大小即选择能力的约束或促进。这种发展与保护之间的选择权利可以理解为在发展与保护之间的选择的自由和自由度。发展的权利要求和保护的权利要求均为正当性、合理性的利益基本要求和基本权利要求,均为应当维护并促进实现的基本需求。这两类正当性、合理性的利益基本要求和基本权利要求的确认和实现(即选择权利的运行),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通常难以同步并行,便产生了选择的踌躇和冲突,即形成实质是选择自由的矛盾的利益冲突。 (三)利益冲突的非对抗性 发展的利益要求及权利和保护的利益及权利均为法律应当刻意和竭力保护的正当利益和权利。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本质上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性质属于非对抗性的利益冲突,不是非此即彼的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可以判定,环境法涉及的是两个正当利益的非对抗性的冲突。对此类利益冲突,法律应当持同等的保护立场,不可为了保护一个正当利益而否定或侵犯另外一个正当利益,不管有多么冠冕的理由。依据德国著名法学家阿列克西所阐释的理论(“阿列克西命题”,价值权衡理论),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利益所储存的价值发生了冲突。对于价值不能用排除的方法来解决,只能用“权衡”的方法来解决。(12)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是非对抗性的当利益之间的冲突,便为冲突的协调(利益衡平)提供了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同时也为在利益衡平过程中的达成共识、公众参与提供了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条件。 三、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衡平原则 自然权利还是人为利益?环境权是国家确认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环境权不是自然权,是后天的,需要认可的,环境权的内容以国家确认为准,环境权的权利确认和幅度也依赖于国家认可。因此,环境权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权利。环境权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刻意追求独立的权利形态而是立足于利益诉求及其多样性的实现。 环境法涉及到的是两个正当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实质是两个正当利益如何实现的选择自由的冲突,是两个正当利益优位性选择的问题,表现形式是基于可行条件和问题的紧迫性的时空优先顺序的安排,并非对抗性的淘汰式选择。选择既然是时空顺序的优先安排,即位次安排,并不涉及性质对抗,其利益衡平的宗旨应当奉行“统筹”、“兼顾”和“双赢”的衡平理念。利益选择的顺序安排可以考虑以下这些有意义的原则。 (一)一体化原则 在衡平发展利益和保护利益时,不应当刻意强调并追求所谓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的机械的“优先”安排,应当推崇将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的“一体化”原则,避免发生二者之间相互割裂、相互封闭的状况。但是,当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对环境产生或可能产生严重不良或不利影响时,则应毫不踌躇地实行环境保护优先。 (二)社会可承担性原则 在衡平发展利益和保护利益时,应当顾虑到协调成本,使社会主体感觉到所采取的方式、措施、手段在“成本效益”和“可适用”的考量下,是允许并乐意接受的,且是可负担的。 就社会可接受性和社会可承担性而言,有几个关键性条件应考虑:使用可靠,价格合理,经济上可行,社会可接受,改进与替代,环保可接受性,清洁使用。与此相关联的整合性问题,即环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整体性和分散性治理。此外,积极性社会治理的倡导和实践同样具有意义。 (三)紧缺利益优先保护原则 紧缺这个词本身具有时空性的含义,具有时空的阶段性和位序性,也包括利益供给的可提供性和可获得性。紧缺包括自然紧缺和人为紧缺。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利益紧缺,无论是自然紧缺还是人为紧缺,均是对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严重的致命的损害,都是必须采取紧急和严格措施予以填补的。循着阿马蒂亚·森的贫困、饥荒与权利剥夺理论的思路,(13)我们在认识、分析和理解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利益紧缺时,应当将这种利益紧缺与权利紧密相连,可以认为这种紧缺不单纯是利益供给不足,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利益的稀缺性不是绝对的。某种利益是否稀缺的关键在于差异性,要差异性地理解和区别对待。紧缺实际上就是差异性原则,差异先于同一,多样先于单一。 (四)协商原则 环境法本质是公法,环境属公共利益,环境污染属于公害,环境保护属公益行为。环境法规制的是集体的行为造成的集体危害,激励的是保护环境的公益行为。按照德国学者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解释,环境问题属于“集体的不负责行为”。环境问题的出现正是集体行为造成的集体危害。 环境、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均具有公共性的特征。这类事务可以列入具有公共决策、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公共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采行公众参与、运作沟通和协商是民主的现代发展。孟德斯鸠曾说过:“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14)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研究结论指出:只要参与者充分发表观点,沟通顺畅,那么,公众治理公地的效率高过政府管制与公司拥有。(15) 在环境法领域,公众参与、沟通和协商的意义在于促成利益识别和衡平功能的公共性,具体而言,可以包括:将环境法领域的利益独享、分享转化为共享;将利益的独惠、特惠转化为普惠;将环境责任由独担转化为共同承担;将利益的竞争转化为利益的竞合。沟通和协商是个过程,需要时间、耐心和不间断的努力。沟通和协商是为了创造协商、对话的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和协商过程的意义可能胜于沟通和协商的结果。因此,重视沟通和协商过程的合理性要优于对结果的重视。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沟通和协商或沟通和协商达成什么结果,重要的意义在于沟通和协商什么?又怎样进行沟通和协商? 沟通和协商需要包容,即妥协、让步、宽容、兼容。沟通和协商不只是允许和维护他人的诉求表达,还应包括不强求形成认同或达成共识。孔子曾倡导“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可以斗胆添附“己之所欲,亦勿施于人”。沟通和协商并非为了争夺、控制或垄断话语权。拥有话语权,并不是就当然拥有道理或真理。后者更难于前者。若沟通和协商是以拥有话语权为目的,最终会成为党同伐异的对真理的“霸凌”并进而导致对民主的嘲弄和践踏。沟通和协商本应是平等的和睦相待,不是恩赐或施舍。1989年的冬天,瓦茨拉夫·哈维尔(一译哈韦尔)等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了8条《对话守则》。内容是:(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16) 沟通和协商应当采行“有效参与”原则。沟通和协商既是个有没有的问题,也是个多或少的问题。“有效性”是公开公平的实际步骤和策越选择。沟通和协商的有效性,至少应包括这些要求和条件:(1)保证和实现有效平等的沟通和协商,是政府不可推诿、不可懈怠的义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2)制定沟通和协商的明确规则在先。(3)充分的知情。(4)平等的表达。(5)资格的宽松。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均应当有适当的机会和方式参与对严重影响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活动及其论证、决策过程。(6)公开的辩论。(7)对政府就环境生态状态、已经或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活动及论证、决策的质疑,并有得到及时、明确、详细的答复。质疑是科学最可宝贵的品质和基本精神。答复是政府责任履行和公信力的显现。若质疑能够得到合理回复,自然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正所谓:“空谷足音,跫然色喜”。(8)在沟通和协商过程中,应竭力避免以牺牲其他当事人的合理要求和合法权益,牺牲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性,牺牲政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作为求得不靠谱的缺乏可信度的“共识”的代价。(9)公众的意见能够对相关论证和决策产生实际影响。参与的公众需受到尊重,不应当是在他人导演的戏剧中充当着配角。(10)在论证或决策过程中认真、谨慎的考虑所有参与者的意见。决策者应当为可能出现的潜在的受影响者的参与提供方便,预留通道。(11)经沟通和协商达成的共识不得像“黑巫术”那样,转移灾祸或危害他人。 沟通和协商应是政府、企业、受影响居民、受益公众等诸多利益相关方的充分沟通,理性协商,以促成在包容的基础上达致各方虽不甚满意却尚可接受的妥协方案。理性协商应采非暴力沟通方式来进行公开平等的公共讨论,避免协商功能和实际效果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避免形成本不应形成的彼此对抗、难以消融的窘困局面。古训言:“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与乱同道,莫于测也,后嗣可观。”国外历史上的圣雄甘地以及受其影响的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先哲的实践值得我们效仿。对此,美国的马歇尔·卢森堡发现了神奇而平和的非暴力沟通方式,其所著《非暴力沟通》一书会给我们有益的启发。(17) (五)类型化原则:统一基点上的利益识别和衡平的多样性与类型化 环境法领域的利益识别和衡平,应当着眼考虑既应对现实的具有确定性的损害、威胁、危机,亦应顾及可能面临的10年、20年、30年甚或更长远的长期挑战和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引入“谨慎”、“安全应对危机”、“风险规制”、“减缓恐惧”等理念和机制。 四、环境法的理念选择:利益最大化与损失最小化 环境权、环境法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利益诉求,包括个体利益诉求和集体利益诉求,其核心依然是财富(或公共福祉)和自由,这实际上涉及价值。环境法的利益的识别功能可以理解为确认庞德所阐释的“评价有关利益或主张或预期的标准”。环境法的利益的衡平功能则可以理解为实践“经由法律实现的正义的标准,即价值衡量”。(18) 环境法的利益识别和衡平功能的实现过程会发生公法与私法的竞合。庞德认为,“公法”与“私法”已不是罗马法意义上的探讨,而是诉诸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交换(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19)在实在法中,“交换正义”是“等同法”,指用补偿或类似的方式保障利益的法律。“分配正义”是“排序法”,指按照对其价值的权衡而优先保障某些人利益的法律。依此,私法被认为是等同法,公法被认为是排序法。有趣的是,这两类法律均适用于环境法的利益识别和衡平功能。 环境法领域的公法与私法的竞合,引发了在环境法领域如何认识和理解环境法和民商法之间的区别的思考。环境法和民商法之间的区别在哪?按照约翰·罗尔斯的思想脉络分析,环境法和民商法之间有一个很主要的区别。民商法强调物尽其用,这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实际是获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功利主义的效率原则的选择。民商法是“两利相较取其重”,强调利益最大化的,于其是正当合理的,是必然必要的。环境法则相反,是“两害相比取其轻”,是强调损失最小化。“损失最小化”应包含有两个要素。一是确实受到损失,而且这个损失是必须付出的;二是损失是他人的所得,利益的获得者必须支付对价。利益的取得必须支付对价,这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共同原理。对价是给予受损者的补偿。损失最小化至少应包括两个要求。一是“最大的最小损失”原则,这是最小损害原则。另一是“最小的最大补偿”原则,这是最大补偿原则。 补偿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也是最低层次,实行“适当”原则,即适当补偿。这是不对等的欠额补偿。基点是“有胜于无”,聊补困窘和匮乏。第二层次,是实行“合理”原则,即合理补偿。这是对等的等额补偿。比“适当”充足,也有进步。第三层次,是实行“充分”原则,即充分补偿。这是超额补偿。例如,在欧美,污染肇事者除对污染受害者给予同污染的实际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损失,现实的和预期的等)相等额的补偿或赔偿,还要支付数额不菲的惩罚性赔偿。这后一部分已超过了可计量的实际损失,可理解为超额的补偿。补偿的具体方式应当呈现为多样化形态。具体方式的设计和施行原则是“实际有效”。实现“实际有效”,应当在共同参与、共享普惠的基础上实行特定的类型化,允许补偿的实际差异的存在,同时要为潜在的受偿者的未来的可能的诉求提供便利。 五、结语:利益冲突的平衡是生态文明的实践智慧 环境法的升华与递进,即环境法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化与扩张,可以称为是在多变复杂的世界里找寻新智慧,是可持续的实践智慧。巴里·施瓦茨认为:“人们通常认为对付制度缺陷的办法就是制定更多的规则或提供‘更管用’的物质激励。不管是规则还是激励,都无法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实践智慧”——做正确之事”。(20)他界定的“实践智慧”,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针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庞德曾批判只从法律自身出发看待法律和构建法律制度,主张将法律视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和手段,一种系统运用政治组织的强力调整关系和规制行为的手段,通过承认、界分和保障利益来维护法律秩序,最终达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目的。 环境法作为一种衡平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社会工具,其表现形式是基于可行条件和问题的紧迫性的时空优先顺序的安排,展现出一种利益衡量的“实践智慧”。当下中国弘扬和建设的生态文明,正是环境立法依托的规范理念和伦理文化,它指引和支持环境法的目的和功能,促进合理地识别环境利益和衡平环境领域的利益冲突。这种制度与智慧的统一,使得多层次、多元、多样的利益协调成为可能,也使得人与环境和谐的社会秩序协调成为可能。 ①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林、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34页。 ②参见李启家:《论环境法功能的拓发展——兼议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前景》,载《上海法治报》2009年3月11日第B05版。 ③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立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9页。 ④参见[美]亚伯汗·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9页。 ⑤参见关在汉:《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 ⑥参见[法]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⑦参见[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温平、李继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⑧参见[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⑨沈栖:《当年的红卫兵的人性回归》,载《新一代》2011年第3期。 ⑩参见王赐江:《群体性事件类型化及发展趋向》,载《长江论坛》2010年第4期。 (11)江濡山:《治国未必需要高超的智慧和伟大的理论》,新浪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8e96920101kvk8.html,访问时间:2015年7月19日。 (12)参见王旭:《论权衡方法在行政法适用中的展开》,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3)参见[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1-70页。 (14)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3页。 (15)参见[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3-278页。 (16)参见[捷]哈维尔等:《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http://www.docin.com/p-320708767.html,访问时间:2015年7月19日。 (17)参见[美]马歇尔·卢森堡:《非暴力沟通》,阮胤华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18)同前注①,[美]罗斯科·庞德书,第112-125页。 (19)参见前注①,[美]罗斯科·庞德书,第92-100页。 (20)参见[美]巴里·施瓦茨:《遗失的智慧:除了抱怨制度,我们还能做什么?》,杜伟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Ⅸ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