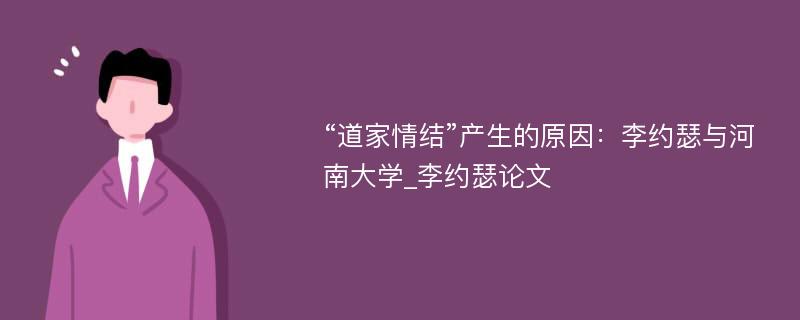
“道教情结”缘于此——李约瑟与河南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情结论文,河南大学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约瑟,这个在科学文化界人人熟知的名字,因穷其毕生精力写下了七卷本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成为著名的科学史家,因提出“用对大自然有机体的较深理解来修改牛顿的机械宇宙观”,[1]成为有机论哲学家。卷帙浩繁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极为推崇道家和道家思想,认为道家思想是整个科学的基础,并从道家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出发,提出了有机论哲学。知识界把李约瑟对中国道家和道家思想的赞许,称为李约瑟的“道教情结”。李约瑟的“道教情结”是如何形成的,这不仅与他遍访中国抗战后方的道观、搜集道家的著述有关,也与他访问河南大学、初识《道藏》有缘。[2]
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就以对胚胎化学的卓越贡献使他饮誉全球。1931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1932年又出版了《胚胎学史》,这些成果的问世使他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家。
1937年,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三位年轻人为求学来到了剑桥。这三个人,特别是鲁桂珍,对李约瑟产生探索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想法影响最大。鲁桂珍(1904—1991)祖籍湖北蕲春,其父鲁茂庭(字仕国)是南京药商。鲁桂珍曾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抗战初期,其未婚夫为国捐驱。鲁桂珍遭此巨痛,遂断绝婚念,在父亲鲁茂庭的支持下,来到剑桥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李约瑟的夫人多罗茜·莫耳(Dorothy Moyle)。
李约瑟是在1939年产生探求中国古代科学和文明的强烈冲动的。在此之前,李约瑟对古代中国所产生的足可以和古希腊、罗马相媲美的文明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一个偶然的机会,鲁桂珍向他谈起古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使李约瑟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全部科学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3]从此,李约瑟倾其毕业精力,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李约瑟在回忆这种转移时写道:“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而来。”[4]鲁桂珍终生陪伴李约瑟探求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并于1989年成婚。和中国文化本来并无任何渊源的李约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皈依,此因起源于他与鲁桂珍相遇。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Ho Peng Yoke)曾经对此发表了看法,假若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而只有在生物化学领域的Joseph Needham。也有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桂珍年轻貌美,是女性的魅力吸引了他。
1942年,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李约瑟以粗通中文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个合作馆是抗战期间中英的合作项目之一,它由英国承担经费,中国国防科学促进会(行政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参与的中英科学合作机构。李约瑟和这个馆的使命,是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提供物资援助和信息交流。李约瑟来到中国后,使他可以直接考察中国文化,寻找中国文明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他乘飞机经印度抵达昆明,在云、贵、川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后又亲自驾车、踏遍抗战后方的十余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并至敦煌千佛洞。1944年,李约瑟的夫人多罗茜·莫耳也来到中国,夫妇二人共同为中英的科学交流做出了贡献。李约瑟遍访了处于抗战大后方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对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的中国科学事业和科学家以倾力支持,赢得了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信任和尊重。1942—1946年李约瑟在中国的见闻和旅行,反映在夫妇二人合写的《科学前哨》一书中。江泽民同志曾为他题词:“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他的高度评价。
在中国考察期间,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从而形成了他终生不渝的“道教情结”,这种情结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重庆时,他以“丹耀”为号,作为自己对道家思想的向往。后又以“胜冗子”、“十宿道人”为号,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向。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他发现自己的名字约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译音是“十宿”,以“十宿”谐“约瑟”,并把自己中文名字的姓取为“李”,以与老子李聃同姓为荣。夫人也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李大菲,表达夫妇二人有着共同的志向。1972年8月,他访问中国时,递给别人名片的下角就印有“十宿道人”的字样,由此可见他对道家思想的向往。
二
1945年8月,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的曹天钦博士,作为秘书、翻译同李约瑟夫妇一起,进行了西上秦、陇的考察。1944年8月曹天钦燕京大学毕业,由黄兴宗介绍并接替黄到李约瑟身边工作。由于李约瑟对道教经典著作有着浓厚兴趣,终南山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察对象。
位于西安市南的终南山,是传道的圣地,相传道教全真道北五祖中的吕洞宾、刘海蟾修道于此,北宋初期著名道家陈传在此隐居。1945年8月,李约瑟一行深入此地,到楼观台访道,与七十岁高龄的鹤真监院(摹佛道人)谈《道德经》,并登炼丹楼。不过,在楼观台所搜集的资料不多,因为楼观台的道观属于长春真人邱处机建立的龙门派,道士们修的是内丹,不是外丹,炼丹楼是道士们修身养性的地方,不进行化学试验。尽管如此,楼观台道长和他的谈话,他却记得非常清楚:“道教的学者至今还能给你说出一种很好的古老传统的悖论。楼观台的主持,一位谈笑风生的可敬的长者,曾对我说:‘世人以为他们是在前进,而我们道家是在后退,但实际正好相反,我们是在前进,而他们是在后退’。”[11]为了收集更多资料,他们深入秦岭腹地,考察了位于庙台子的张良庙——一个三教合一的道观,这里供奉的主要是功成身退的张良。通过考察,他们了解到,这里的“道士们不炼丹,却是能用山中的褐铁矿石和树枝炼出灰口铁的巧匠。他们制做的铁锅,行销远近,颇负盛名”,[5]这个发现证明道士们掌握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在这次西行中,李约瑟巧遇河南大学。从而与道教经典《道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河南贡院是河南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位于开封城东北隅,清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曾在这里举行。河南知识界的有识之士于1912年,在贡院的遗址上,创办了河南大学。她先后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为校名,她选取《礼记·大学》中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校训,旨在泽惠中原。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避战火,辗转搬迁数地,在敌后坚持办学。先是迁往信阳鸡公山,后又迁至南阳镇平。1939年,又迁至位于洛阳南的河南嵩县潭头。1942年3月,流亡于潭头的河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综合评估,评为全国国立大学第6名[6]。1944年1月,豫西一些县城相继沦陷,5月15日,日寇向潭头发起进攻,河南大学师生仓促躲避,造成了河南大学历史上的“5·15”惨案。这次惨案,使河大师生有16名遇难,25名失踪。出逃的河大师生西出荆紫关,翻越秦岭,于1945年4月抵达西安。又奉教育部令,西迁宝鸡,以石羊庙、武城寺等处为址暂时安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教学活动。西行考察的李约瑟与为避战火西迁的河南大学相遇,李约瑟借此机会访问了河南大学。这次访问,目前还没有查到官方与校方相互通函的资料,也没有查到具体的访问时间,所以把它称为“相遇访问”。对这次相遇访问,李约瑟是这样记载的:“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铁路去五证寺,这是当时河南大学最后的疏散校址。河南大学利用一所很精美的旧道观作为它的一个校舍,(李约瑟是非常注意道观的,笔者注)这个道观座落在一个黄土岗上,大致在汘水从北面流入渭河的地方,隔着渭河(中国文明的摇篮)向南可以看到秦岭山脉”。[3]曹天钦院士是这样回忆的:“我也不能忘记在宝鸡东郊的卧龙寺和石羊庙的一段经历。那时日本侵略军侵扰河南,河南大学的部分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迁到宝鸡,借宿破庙,坚持上课”。[8]
1945年10月,李约瑟偕夫人及曹天饮等随行人员来到河南大学。为避战火,河南大学抗战8年内处于流亡办学状态,与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极为困难,因此校方十分重视这次来访,认为是一次难得的与国际学术界学习交流的机会,希望借此向国外展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办学精神,并沟通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为欢迎李约瑟的到来,经校长会议研究,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河南大学的全体师生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席地而坐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学校领导致欢迎词后,李约瑟作了《科学与民主》的演讲报告。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他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挥笔写下的《纳粹势力对科学的摧残》一文的内容,在这个报告中,他阐述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并论述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和俄国科学的发展。他“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君专制者之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而近二十年来俄国对于土壤、地质及胚胎学均有显著进步,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9]李约瑟的报告不仅鼓舞了在战乱中坚持教学、科研的河南大学师生,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学术信息。
在河南大学访问期间,校方还组织了由教授们参加的座谈会,同李约瑟交流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座谈会只能在破庙中进行。没有沙发,也没有圆桌,更谈不上贵宾室,只能抵膝而坐,对面相谈。当时在场的曹天钦院士回忆说:“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李约瑟同化学系的教授们促膝长谈。他们讨论的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5]在河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李俊甫(字相杰)陪同下,李约瑟还参观了战乱中不断搬运的河南大学图书馆,当他看到道家经典《道藏》时大加赞赏,惊叹不己。《道藏》是道教经典的总称,它由道经汇辑而成,故曰道藏。道径的汇集,始于六朝。宋有《万寿道藏》,金有《玄都道藏》,明有《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明代的《道藏》内容庞杂,除有道教经书之外,还收集了诸子百家文集,是现今流行的通行本。河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道藏》,是民国十二至十五年(1923—1926)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版本影印的。目前存1096册、127函。李相杰教授向他介绍了《道藏》中的古代炼金术以及中国化学史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取得的成果。[6]李约瑟的这次河大之行,使他有缘目睹《道藏》,了解全部《道藏》的基本内容,因而使他的“道教情结”更浓。对此,何丙郁说:“大约60年前,李约瑟博士在四川的时候,已经从中国学者那里获知《道藏》对中国化学史研究的重要性”。[8]何丙郁所说的中国学者,也应当包括河南大学的李相杰教授。看到河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道藏》,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印象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给予了追述:“我花一个下午和李相杰教授一起看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来有很多藏书,可是连续几次疏散使图书馆受到很大的损失。图书目录已经找不到了,书籍堆在那里,许多还成捆地放在古老的神像脚下,就像刚由汗流浃背的搬运工从扁担上卸下来似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李相杰向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介绍说,在《道藏》(历代道家的经典)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他们饶有兴味,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史家所完全不知道的。李相杰对我所作的这番介绍,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3]
三
李约瑟对河南大学的访问,对河南大学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对国外的宣传起了重要作用。抗战前后的10余年,是河南大学历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多位校长的领导下,辗转搬迁、流亡数地,在抗战的腹地,坚持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经过全体师生的努力,由一所一般性地方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立大学,形成了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抗战后期,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综合评估,排名名列前茅,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这一时期,著名专家学者云集,在学术上取得了大量的引人注目的成果。李约瑟向国外介绍了河南大学的学术水平,使河南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得到扩大。
李约瑟还在重庆中英科学馆工作时,联合国在巴黎成立了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是李约瑟的老朋友,英国生物学家尤里安·赫克斯利。李约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尤里安·赫克斯利写信,认为这个组织还应担负科学交流和共同开发的任务,建议这个组织的名称还应加一个字母“S”,即英文“科学”的第一个字母。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于是,便有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其英文缩写是UNESCO。1946年3月,李约瑟应尤里安·赫克斯利之邀,前往巴黎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的科学处长之职。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李约瑟还同河南大学保持联系,“经常给河大寄书刊资料,热情支持河大的科研工作,”[9]使河南大学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在联合国“备案”的大学之一。
李约瑟同河南大学的联系一直持续到他逝世之前。1987年,当年作为学生曾在宝鸡聆听了李约瑟演讲的河南大学李丙寅教授,因到英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拜访了李约瑟。“当我电话预约时,他立即说工作忙而拒绝,但当我告诉他,我在四十多年前作为河大学生曾在宝鸡听过他演讲时,他就兴奋地说记得那次河大之行,并安排了20分钟的会见”。[15]这次会见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并用茶水和饼干招待李丙寅。二人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当问及何时再到河南大学访问时,李约瑟表示等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即访问中国,再访问河大。李丙寅向李约瑟赠送了带有熊猫图案的手帕(工艺品)和河南大学校园明信片,接受纪念品后,李约瑟立即提笔,写下了“最热烈地向中国人民致敬”的题词赠给李丙寅。1990年,经李约瑟评审,李丙寅的论文“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入选在剑桥召开的“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并邀请李丙寅参加。李丙寅因故没有成行,这次交流未能如愿。后来,二人经常书信联系,一直到李约瑟逝世。
李约瑟对河南大学的访问,极大地鼓舞了河南大学师生在流亡中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是,陇海线尚不畅通,返汴困难重重。为了保证1946年春季按时在汴复课,学校决定提前结束本学期课程,学生自行编组返校。1945年12月底,河南大学由宝鸡迁回开封,结束了流亡8年的办学生涯。
四
李约瑟对河南大学的访问,对他来说,就是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搜集了资料,作了必要的准备。《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就是十分推崇道家和道家的思想。李约瑟自号“胜冗子”、“十宿道人”,足可见他对道家学说之倾心。知识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李约瑟的“道教情结”。[10]这里姑且不论是否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最大,但是道教对中国炼丹术的贡献最大应当没有争论。李约瑟作为生化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最先注意的是化学史,所以,他一定会注重搜集道家的经典,并注意道家的思想,这就是“道家情结”的缘由。在访问河南大学之前,李约瑟就已经对道教发生了兴趣。“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关于艰深而重要的道教的阐释。在老关台观主曾永寿身上,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传统道教的化身。”[3]访问河南大学看到《道藏》后,使他进一步看到道家经典的博大和精深,使他对道教经典有了系统认识,使他的“道教情结”更浓、更深。
在河南大学李约瑟初识《道藏》后,他对道家经典《道藏》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化学史和科技史的考察方面,而是通过对道家思想的深入考察,确认在《道藏》中存在着有机论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李约瑟明确预言了科学整体化时代的到来。1951年,李约瑟在法国里昂大学就作了“具有有机哲学思想的中国哲学”的演讲,表达了他的看法,1956年,他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科学的基础。”[10]并指出,道家思想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中国普遍流行的思想潮流,道家思想是现代科学的先驱。到60年代,李约瑟又把这一思想上升到新的高度,明确指出:“所有存在物的和谐协调并非出于它们之外的某一更高权威的命令,而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它们都是等级分明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整体等级构成一幅广大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它们服从自身的内在自配。”[12]这就是中国思想家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李约瑟通过对中国的考察,通过对《道藏》的研究,不仅使他成为著名的科技史家,而且成为20世纪著名的有机论哲学家,这就是李约瑟“道教情结”的缘由所在,也是他从中国、从河南大学所带走的。“道教情结”缘于此,这就是李约瑟与河南大学长期保持联系并念念不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