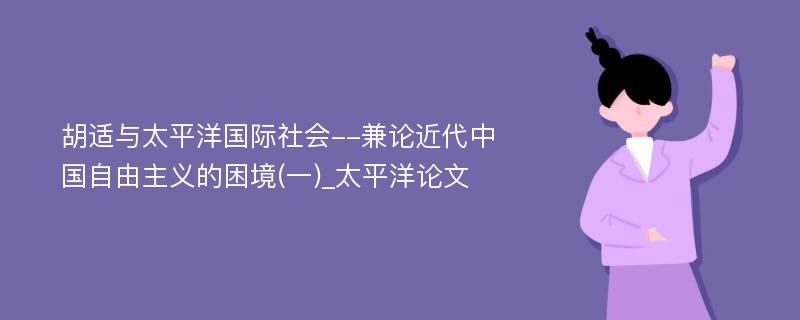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太平洋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处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洋国际学会(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英文名称为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日本称之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但中文名称则繁多。在1920年代主要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30年代以后则有多种称呼,如“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太平洋国际协会”、“泛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会议”等等。其中“太平洋国际学会”是1931年以后中国分会对这一机构的正式称呼。)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主要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设有14个分会。1947年以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断受到有关“亲共”的指控,1952年又被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指控为应对“丢失中国”负责。学会也因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只好于1960年宣布解散,前后共存在了35年(注: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史与活动,可参见John N.Thomas,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4;John K.Fairbank,William L.Holland and the IP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acific Affairs,Vol.52,No.4,1979;Paul F.Hooper,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Pacific Affairs,Vol.61,No.1,1988.)。
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从1925年加入到1950年宣布退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共存在了25年。在这期间,胡适曾于1931-1938,1946-1950年间两度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还担任过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理事会副主席、学会程序委员会主席。虽然胡适没有参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工作,但是他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一个松散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也是他亲自宣布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解散。可以说,自1931年以后,胡适就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的言论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前后的思想动向。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事实上,胡适的日记、书信和演讲中都有许多涉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内容,只是未曾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把太平洋国际学会放到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动中去考察,对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的言论和活动作一初步的分析,解释其所以如是的原因,并进而揭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艰难处境。
一、太平洋国际学会之源起、理念与演变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和社会思潮变动的产物。其最初的源动力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热点逐渐由近东移到了远东,世界的舞台也逐渐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源于一种新眼光的世界潮流也兴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层面的国际关系通常由政府垄断,而经济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则由私人或企业进行。但是战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经济和文化事务,同样私人也开始进入以前神秘的政治领域(注:A.J.Toynbee,World sovereignty and world culture,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ince the war,Pacific Affairs,Vol.4,No.9,Sept.1931.)。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也确立了,比如公开外交、自决、多数人的智力、公理等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决定发起一次会议,讨论太平洋国际间各种问题,以期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并求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此议由檀香山商、学界领袖提出,在与美、中、日等国家的名宿磋商之后联合发起。后来因为种种关系,有许多当事人,不愿意以宗教来限制本会的性质,就渐渐地把会议的范围放大,由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一变而为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之会议,再变而为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国民会议,并于1925年7月在檀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把该会原定的名称“太平洋国民会议”改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并设立永久机构,总部设在檀香山,各国设立分会,每两年集会一次(注:参见陈立廷:《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东方杂志》第22卷第19号,1925年10月。又见陈衡哲:《太平洋国交会议记略》,《现代评论》第6卷第142期,1927年8月27日。)。这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由来。
最早参与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有夏威夷、美国、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9个国家或地区,也即是在上述地区设有分会(注:开始时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分会以Nation为单位,其意义重在民族,不重在政治,所以朝鲜、菲律宾、夏威夷都可以独立组团参加学会。1929年学会修改章程,规定分会以State为单位。而所谓State又被解释为两种,一为独立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一为自治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朝鲜、夏威夷、菲律宾都无权独立组团参加学会,只能作为日本或美国代表团的一部分与会。后来由于朝鲜方面的反对,得以允许朝鲜和夏威夷、菲律宾都可以独立组团参加学会,但无权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只有独立或自治国家才可以在理事会上推选代表。参见前溪:《太平洋讨论会特记》,《国闻周报》第6卷第44期,1929年11月10日;前溪:《太平洋讨论会特记》(续),《国闻周报》第6卷第46期,1929年11月24日。)。之后规模不断扩大。1928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表示愿意以太平洋国际学会英国分会的名义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活动(注:News Bulletin,I.P.R.Mar.1928。英国本身并不是太平洋地区国家,但英国在太平洋地区有许多殖民地,它是英联邦的领导者,在太平洋地区有广泛的利益。在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感到,没有英国的参与和表态,太平洋地区任何问题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Memorandum on the relation of the British Comnmnwealth to the Pacific problems,Prepared for I.P.R.by J.B.Condiflle,News Bulletin,I.P.R.Oct.16,1926.)为此,加拿大分会干事尼尔松(John Nelson)向大英政府建议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1926年10月,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式向皇家国际事务协会发出邀请,建议它承担起向1927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派遣代表的任务,而它可以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分会。皇家国际事务协会接受了这一邀请,同意派代表与会,但不愿意以太平洋国际学会分会的名义。(Great Britain Joins the Institute,News Bulletin,I.P.R.January 1927.)到1928年,皇家国际事务协会在其内部正式成立一个机构,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之英国分会。)。荷兰和法国也都成立了分会。1931年苏联也正式成立一个小组并被承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之苏联分会(注:Institute notes,Soviet membership,Pacific Affairs,Vol.4,No.12,Dec.1931.苏联之与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27年在檀香山的会议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总干事梅勒(Merle Davis)就开始寻求苏联与会的可能性。1927年12月16日,梅勒在日内瓦宣布,他计划前往苏联。他说:“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相信,没有俄国的参与,有关太平洋事务的真正讨论都是不可能的。我计划邀请莫斯科当局派代表参加1929年的会议。我希望俄国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永久会员。”(News Bulletin,I.P.R.Jan.1928.)但苏联方面对此反应冷淡,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原则与红色国际之间存在矛盾,并且很难调解。”(J.Mede Davis,Europe meets the Institute,Pacific Affairs,Vol.1,No.1,May 1928.)但学会一直努力争取苏联的参加,1931年初苏联终于成立了一个太平洋研究小组,不久即被承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之苏联分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分会,如荷属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尽管如此,太平洋国际学会仍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南美洲的太平洋地区并未参与。在太平洋学会那里,“太平洋”一词并非指地理意义上的太平洋地区,它有特定的含义,在含义上与“远东”一词并没有多少区别(注:John K.Failbank,William L.Holland and the I.P.R.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acific Affairs,Vol.52,No.4,1979.)。因此所谓太平洋问题也即是远东问题,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的问题大多与中国和日本有关。
按照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的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它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注:《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永久组织”委员会纪录》,《青年进步》第86册,1925年10月。)为了表明学会的独立性质,在学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会议”(conference)一词有意避免使用,而代之以“集会”(assembly)。同样“代表”(representatives)和“代表团”(delegates)也避免使用,所有的会员都以私人身份与会(注:Stanley K.Hornbeck,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mion,August 27,1925,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Ⅸ,1925.)。同时,为了保证学会的独立性质,学会的讨论也集中在文化和经济问题上,尽量避免涉及政治问题。
在最初的两年里,学会尚能维持其独立的非政治的理念。从第三年开始,学会内部关于学会的原则和宗旨开始发生分歧。多数的分歧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学会是应该维持其最初的性质,也就是作为一个低姿态的论坛,还是变成一个讨论亚太地区国际国内问题的组织?在1927年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美国代表克里(Carrie Chapman Catt)呼吁学会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学术研究的安全领域,应该勇敢面对这个世界的基本问题。他说:“国际间的猜疑增加了世界不可数的不安定问题,只有改变国际关系准则和体系,才能得以解决。这些措施都是政治性的,充满争议。但是勇敢的人们为什么不愿意表态呢?”(注:Carrie Chapman Catt,Ideas and aspi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Chairman,Address given before the general session of July 17,1927,News Bulletin,I.P.R.Sept.1927.)克里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东部地区会员的基本主张。当时美国分会内部存在争议,夏威夷和太平洋沿岸的会员主张维持学会独立的非政治性质,而东部地区的会员则主张改变。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夏威夷的安瑟顿(Frank C.Atheflon)是前一主张的领导人,而美国分会领导人卡特(Edward C.Carter)则代表后一种主张。1929年,学会总干事梅勒(Merle Davis)因不愿意看到学会从关注文化和经济问题转而关注远东政治冲突问题而辞职(注:John N.Thomas,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sia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4,P5-7.)。1933年,卡特当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次年学会总部也从檀香山迁到了纽约(注:安瑟顿对这一结果非常不满,并力图把学会总部迁回檀香山。为此胡适劝安瑟顿放弃此种努力,承认纽约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新都,而不可强求挽救。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页。)。这标志着太平洋国际学会政治化时代的来临。
尽管学会将其关注的重心转向政治,甚至对于当时“最严重之争执问题,亦复不畏讨论”(注:《太平洋学会开幕》(格林氏之演词),《申报》1931年10月22日。),学会还是试图尽量维持其超派别的理念。有关政治的讨论仍是“诊断的”而非“治疗的”(注:J.B.Condliffe,An experiment in diagnosis,Pacific Affairs,Vol.2,No.3,Mar.1929.)。学会从未对任何一个讨论多年的问题以“决议”、“声明”或其它方式表达过正式的看法。与之相应的是,学会特别强调会员要保持一种无私的立场,在讨论问题时以理智代替感情。不过,随着中日冲突的不断升级和其它国家的卷入,超派别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与会的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前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在会上提交的议题和看法。会后要向政府汇报会谈的情况。与会者都把会场当作代表各自政府进行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地方(注:Charles F.Loomis,Light from three conferences:an exploration into their technique,Pacific Affairs,Vol.3, No.1,Jan.1930.)。许多国家的分会采取了与政府一致的立场,学会的所谓学术、会议也变成了“太平洋关系各国正式会议的试探”(注:纪:《太平洋问题之全面展开》,《申报》1936年8月30日。)。学会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主编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明显地感觉到一些国家的理事会试图把《太平洋事务》当作表达实际上是“官方路线”的“私人观点”(注:Owen Lattimore,Preface,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collected papers,1928-1958,Paris Mouton & CO La Haye,1962.P17-18.)。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别无选择地强化了与政府的关系,整个学会卷入了反法西斯事业。美国分会的领导人韦尔伯(Ray Lyman Wilbur)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学会的官员和职员都相信,战争的形势赋予学会的研究和对局势的讨论一种新的重要性。这些活动是为民主而战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民迫切的任务就是彻底进行战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其它轴心列强。他们的失败是远东和其它地方和平的前提。太平洋国际学会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承诺‘中立’。相反军事侵略无视其他人们的权利,与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的一切相背离。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美国分会承诺尽其所能。……学会经过多年的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知识团体和培养一批对远东有广泛理解的人,现在是做出贡献的时候了。”(注:IPR in Wartime: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转引自Paul F.Hooper: A brief history of I.P.R.)
为了更好地与政府保持联系,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和美国分会理事会于1942年联合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与盟国政府接触。同时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加入学会,一些重要的学会官员则直接参加到与战争相关的活动中。学会与政府间的这种紧密关系给学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给学会的生存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尽管战争使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分会处于混乱状态,但战后许多人还是对学会的前途非常乐观,人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太平洋秩序即将出现,学会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鼓励下,学会的领导层一致决定恢复学会传统的运作模式。1946年初,霍兰德(William Holland)接替卡特担任学会总干事。他采取鼓励、支持和访问的方式帮助许多在战争期间中断了的分会恢复活动,同时又使学会的会议及研究出版工作继续进行。然而,战后的世界毕竟不同于战前了,学会再也无法创造出以前的那种氛围。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导致了大量对与学会有关的个人及学会本身的指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指控拉铁摩尔为苏联间谍。为此美参议院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太平洋学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应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负责(注:John N.Thomas,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sia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4,P93.)。尽管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反共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大多相信了这些指控。对学会的支持减少了,原来支持学会的洛克菲勒基金和卡内基基金都撤走了,一些国家的分会宣布脱离或解散。这样继续努力维持学会已经毫无意义了。1960年12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正式宣布解散学会,2个月后,美国分会也宣布解散,太平洋国际学会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二、胡适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转型
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最初参与其事的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立于1915年,首任总干事为美国人巴乐满(Fletcher S.Brockman),副总干事为王正廷。巴乐满返关后由王正廷接任。1917年余日章接替王正廷担任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成立时,即采取不参预政治的立场。但到192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五四以来科学精神对宗教的挑战,也面临着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下种种反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能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必须有所改变。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丽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注:参见王成勉:《余日章与青年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3年出版。)。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注:余日章:《中国在国际间之地位》,《青年进步》第73册,1924年5月。)因此,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他们是:余日章(主任)、赵晋卿(副主任)、黄任之(副主任)、方椒伯(司库)、许建屏(书记)、唐俞庆棠和朱经农。到5月底,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7月便派代表出席了在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立大会,也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第一次会议,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注:陈立廷:《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经过之颠末》,《青年进步》第86册,1925年10月。)。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后,立即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的支持和帮助。1926年6月,学会总干事梅勒访问了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他会见了中国分会的会员和20多位中国各界的领袖级人物。在北京他会见了大批中国名人,其中有范源濂、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这是胡适第一次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接触。同时梅勒还广泛接触了中国最好的学术机构,访问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并与这些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注:Second report letter from China,June20,1926,News Bulletin,August 24,1926.)。梅勒此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分会的发展,许多名人纷纷加入学会。1928年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会改组,分设高级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高级委员会的成员是:余日章(主席)、赵晋卿、方椒伯、徐新六、王云五、刘鸿生、陈立廷、朱经农、刘大钧、俞庆棠。全国委员会由20人组成,他们是:唐绍仪、蔡廷干、梁启超、熊希龄、周作民、宋庆龄、孔祥熙、曹云祥、伍朝枢、陈光甫、刘鸿生、宋汉章、温世珍、张伯苓,颜惠庆、严范孙、蔡元培、黄炎培、孙仲英、徐庆云(注:Council Interest,Pacific Afairs,Issue 1,May 1928.)。不过这份名单中有许多人只是名义上委员,并不实际参加学会的活动。
随着大批名人的加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渐渐扩大,因而也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宗教的色彩越来越淡。在1929年的京都会议上,学会的政治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而193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使中国分会彻底摆脱了过去的宗教化时代而进入一个政治化的发展时期。这次会议从筹备到召开经过了一段曲折。先是1931年2月2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宣布杭州为会议地点,其理由是杭州“远离政治中心,但又很方便”,而且杭州“具有历史魅力和现代精神”(注:Institute notes,Pacific Affairs,Vol.4,No.3,Mar.1931.)。不料,到5月下旬的时候,北京、南京、杭州等地都出现了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言论。有人甚至宣称,若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在杭州开会,将有“忠实党员及高丽革命青年,组织铁血团,携手枪炸弹赴大会助兴”(注:《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大会》,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出版,第1页。)。为了确保会议/顷利进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请王儒堂以个人资格监视大会一切行动(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记录》(1931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2页。)。此外,蒋介石于1931年9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批评了那种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论调。他说,“太平洋国际协会,系由各国国民自动的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实非各国政府之机关,其目的也在以国民资格,集合研究国际间各种矛盾问题,进而提出适当之方法,以期相互谅解,联络各国国民间之感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又说,“太平洋国际协会此次在华开会,其发动固多出于青年会中人,惟正式邀约,则系出之政府。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决无宗教意味存于其间。”(注:蒋中正:《太平洋国际协会之性质——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在中央纪念周演讲》,《中央周报》第172期,1931年9月21日。)此后,反对之声渐息。不料就在蒋介石发表演讲4天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会议再次面临流产的危险。为此,胡适与颜惠庆、陶孟和等人代表中国分会致电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要求会议延期举行(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156-157、158页。)。同时日本分会也要求会议延期并改在中立国家(如菲律宾)举行,并且表示如果在中国开会,日本会员将不出席;如大会不顾日本会员出席与否照常开会,日本分会将退出学会。经过中日代表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几度磋商,最终都同意按照原计划如期开会。不过为了减少中日冲突起见,会议地点由杭州改为上海。会议的议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后的议程为: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关系;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关系;食品和人口问题;太平洋地区的附属地和土著;文化和社会关系;移民和种族问题;劳工和生活水平问题(注:Institute notes,Pacific Affairs,Vol.4,NO.11,Nov.1931.)。
也就在会议召开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7月,余日章因“心脏病复发”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注:Dr.David Yui Resigns,Pacific Affairs,Vol.4,No.8,Aug.1931.)。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纪录》(1931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871页。)。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学会年会主席。在会前的筹备会议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式颁布了学会的章程。章程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英文名称是CHINA INSTT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本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1931年),刘驭万主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231页。)会址设在上海敏体尼荫路123号。此外,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改组了领导机构,设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共15人,他们是:徐新六、余日章、周诒春、陶孟和、刘湛恩、胡适、丁文江、吴鼎昌、刘大钧、何廉、张伯苓、陈光甫、刘鸿生、吴贻芳、陈立廷。另设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8人,他们是:胡适(委员长)、吴鼎昌(常务委员)、刘鸿生(书记兼司库)、陈立廷(主任干事)、徐新六(副委员长)、刘湛恩(常务委员)、何廉(研究主任)、刘驭万(副主任干事)(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题名》,刘驭万主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233-234页。)。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权已经从青年会手中转移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领导职务后,极力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在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时,他说,“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注:《申报》1931年10月22日。)到1933年,胡适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并用它来解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在1933年召开的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胡适没有对中日冲突发表评论,而是大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国际学会开会时,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它国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决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和发言。国家的观点只有在充实材料使整个问题的图像构成之时才是有意义的。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这些后果负责(注:Hu Shih,On an I.P.R.philosophic code,Pacific Affairs,Vol.6,Conference supplement,Oct.1933.胡适的这一演讲曾被翻译成《太平洋学会的规律》刊登在1933年9月25、26日的天津《大公报》上。)。胡适的这一主张,既与学会的理念相通,又与他惯有的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作一个“诤友”的心态是一致的(注: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4月8日),《胡适书信集》上册,第589页。)。
胡适主持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期间,吸引了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加到学会中来。1934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改选,胡适再次当选为委员长(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877页。)。胡适本人也对学会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1934年春,新任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卡特访问中国,胡适召集在北平的会员20余人宴请卡特一行(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378页。)。在随后的二、三年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达到了她的鼎盛时期。
三、当自由主义遭遇民族主义:胡适的主张与学会的反应
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在上海召开之时,适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对此作出了“低调”反应。作为大会主席,胡适在会议开幕词中说,虽然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公开的战争,但这两个国家,在太平洋的西岸,确已处在战争的状态中,全中国的人都被一种强烈的耻辱和怨恨的反感燃着了。不过胡适并未就此谴责日本,而是话锋一转,谈起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理念。他说:“我们在此,不是来哭,也不是来笑,只是来明白一切。我们在此,不是来教导,只是来互相交换意见。只要我们有谦和的精神,去求真理,然后如有小小的成功,可以达到。”(注:《申报》1931年10月22日。)在会场外,有记者问胡适,值此国难当头之际,胡适主张学术救国,是不是太过迂腐?胡适回答说,“此说似迂腐,其实是最切实的道理。”“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决不[是]口号标语的工作。我们需要的[是]无数的巴士德和爱迪生。”(注:《民国日报》1931年10月25日。巴士德即Pasteur,法国科学家。)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这是胡适的基本主张。胡适认为战争是一件大事,作为民众领袖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否则就不能算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责任。而作为民众则应冷静地考虑替代战争的其它方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注: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蒋廷黻选集》第6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0页。)。
胡适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另一主要人物丁文江在对日问题上也是极端的“唱低调”。他主张中国应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来缓和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它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胡适称丁文江王张的妥协是一种“有计划”、“有条件”的“妥协”(注: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7),第508页。)。胡适本人也是主张“有计划有条件地对日妥协”。1932年9月,胡适在给当时的外长罗文干的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和日本拼死活?如真有此决心作拼命到底的计划,那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谋最后的总算账。如果我们无此自信力,如果我们不能悬知那‘总算账’究竟有多大把握,那么我们不能不早打算一个挽救目前僵局的计划。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的方式应该是,如果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达到(1)取消满洲国;(2)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之目的,则我们应该”毅然决然开始直接交涉。”(注:胡适:《致罗文干》(1932年9月15日),《胡适书信集》上册,第579页。)
胡适、丁文江在对日问题上“有计划的妥协”的主张,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支持政府做对日作战的准备,而不是现在就与日开战。其前提就是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175页。)。这意味着要拥护国民党政府,容忍蒋介石的独裁。会上,中国会员坦言“在外侮凌逼之际”,中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势,并且“为谋中国人民幸福起见,为谋各友邦在华利益起见,舍此莫由。”(注:刘驭万主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35页。)胡、丁都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社会上也以自由主义者目之,对于他们主张拥护政府甚至主张独裁,社会舆论多有不解。对此,丁文江解释说,“国民党是以一党专政为号召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当然不能赞成它‘专政’。但是我们是主张‘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他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他。”(注: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在外患危急的时候”,这是胡适、丁文江等人在解释其立场时反复强调的。的确,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一种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外来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须支持政府,共御外侮;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放弃其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放弃其批评政府的立场。事实上,自巴黎和会以来,欧美列强常常批评中国政局不定,没有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有效力的政府。日本正是利用欧美此种观念,在国际上极力宣传,攻击中国政治紊乱,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并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理由。所以当时中国感到十分紧迫的,就是充实中央,组织强固政府,造成政治重心,一致对外,以正国际视听(注:《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能“自由”的余地也就不多。换言之,当自由主义者遭遇民族危机的挑战时,自由主义只能是其次的选择。胡适说,“我们要抵抗外侮,要救国,要复兴中华民族,这都不是在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上所能做到的事。我们的敌人公开讥笑我们是一个没有现代组织的国家,我们听了一定很生气。但是生气有什么用处?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所以缺乏现代国家的组织,是不是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曾建立起我们的社会重心?”(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