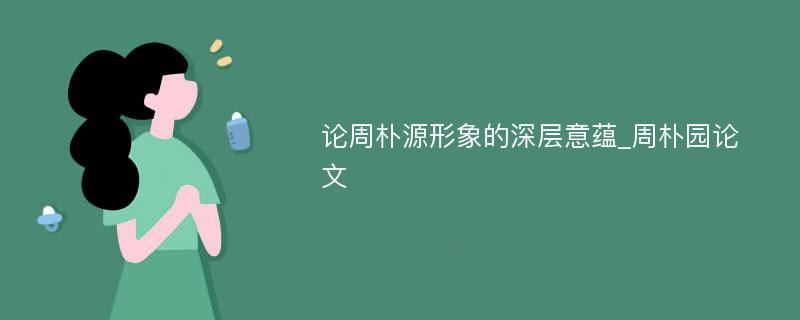
论周朴园形象的深层寓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形象论文,论周朴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我常常禁不住要问自己:这个作品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写?阅读《雷雨》,当我又一次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对曹禺在批判周朴园这样的恶人时为何笔端显得特别沉重,为何在“憎”中还夹杂着那么多复杂的感情,产出了浓厚的兴趣。
大凡熟读《雷雨》的人都知道周朴园是以恶者的形象出现在《雷雨》戏剧舞台上的。他那血腥的发家史,镇压工人的凶残、阴险,对侍萍的背信弃义,令人窒息的家长专制,倘若把他置于法律和道德的审判台前,无论人们对他进行怎样的指责、惩罚都不为过。然而,稍加留意,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雷雨》剧中,每一次伴随着对周朴园人性恶的无情揭露,鞭挞,我们便可以看到曹禺对周朴园的另一笔描写——对深藏在罪恶者背后的十分痛苦的真正的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并且这一情节贯穿着剧本的始终。
三十年前,周朴园抛弃了为他生养过两个孩子的侍萍,可剧本并没有对此大加渲染,反而多次借繁漪、四凤之口或由周朴园本人直接告诉读者他虽然多次搬家,但侍萍喜欢的家具,侍萍年轻时候的照片,侍萍产后受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都被他保留着,连位置也没有改变,他爱穿侍萍绣过的衣服,每年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他都要给侍萍做生日。这一切无疑暗示读者背弃侍萍后的周朴园虽然功成名就,成了社会上的体面人物,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宁静。他在事实上遗弃了侍萍,但在情感上又无时不在怀念侍萍。
三十年后的一天,周朴园意外地与侍萍相遇,带着多年来尔虞我诈的人生经验,周朴园断然决定“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这一次赶走侍萍,周朴园的罪恶严重到了极点,但他的灵魂也沉重到了极点。侍萍答应永不再见周家的人,周朴园的“威胁”已经解除,他本该感到舒心才对。然而恰恰相反,幻灭的情绪盘踞了周朴园的整个心灵,他的精神再度陷入孤独苦闷之中。剧本写道:深夜两点,周朴园独自呆在客厅,“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照片,拿起,戴上眼睛看。”此后,虽有仆人和周冲两次打断,但他们一走,他又拿起照片端详,以至被刚从杏花巷回来的蘩漪发现,奚落一番。不但如此,周朴园的内心还升起了从来没有过的无限恐惧,禁不住先后两次对周冲和周萍说:“(寂寞地)今天——呃,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觉得恶兆来了似的)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畏缩地,不,不,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太冒险。太——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如释重负)今天大概是过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后——不该,再有什么风波)。(不寒而栗地)不,不该!”
为了进一步展示周朴园内心的痛苦,作者在序幕和尾声中甚至让周朴园以皈依宗教的孤独老人出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周朴园作恶多端,他的种种劣迹造成了无数人的精神创痛。可曹禺为什么不把他塑造成一个唯利是图、阴险凶残的资本家典型?或是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一个玩弄女性的轻薄的花花公子?就周朴园的所作所为而言,他不是不具备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曹禺难道不怕读者指责他宽宥坏人吗?凡是读过《雷雨》戏剧文本的接受者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评论界。有论者曾藉此对曹禺提出严厉的批评。八十年代以后,评论界在谈及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否真实时有了一致的看法,大家肯定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之所以怀念侍萍是因为人生路上的许多不如意。然而,至于曹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周朴园?曹禺塑造周朴园这个典型的深刻寓意何在?评论界似乎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我的思考正是从这里开始。
曹禺是一个忠实于生活,有着独特艺术思维的戏剧家。他写戏追求的是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研究、去表现,通过写人去诠释历史、诠释人生。因此在塑造人物尤其是在涉及恶人时,他从不简单地把罪孽归结于某一道德个体,而是更多的思考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动因。周朴园这个形象的塑造正是基于这一深沉的艺术思考。周朴园的所作所为的确给无数人带来了悲剧,他的种种恶迹表明他是个吃人者,他理应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裁。然而作为悲剧制造者的周朴园,他在吃人之际并没有摆脱在更大范围内被人吃的悲剧命运。
剧本为我们提供了老年周朴园的形象,其实从剧本的多处暗示中我们完全可以在想象中复活出年青时代周朴园的形象。剧本第二幕周朴园在斥责周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自命比你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从时间上推算,周朴园留学欧洲大约在本世纪之初,当时的中国,科举应试仍是“正途”,出国留学,那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可周朴园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正试,远涉重洋来到了资本主义的德国。我们暂且不管他的具体动机如何,这种举动在当时也是颇为惊世骇俗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把周朴园看作是中国最早觉醒的资产阶级启蒙者的同路人一点也不过分。剧本多次提到侍萍从前念过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些有钱人家都不大愿意送女子读书。更何况侍萍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女子哪有条件读书写字。那么侍萍又是如何获得这种权利的?很显然,这个帮助侍萍念书的人只有周朴园,不会是别人。我们暂且不管周朴园让侍萍念书的目的何在,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贵族少年,竟然主动帮助一个婢女读书,可见年轻时代的周朴园也是有过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剧本还告诉读者,侍萍曾为周朴园生养过两个孩子,她在周家有自己喜爱的家具,有给孩子取名的权利。从这一情节来看,周朴园与侍萍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太短,大约有三年之久,而且他们的同居是完全公开的,侍萍虽然没有明媒正娶,但她的生活是优越的、幸福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少爷喜欢上聪明、美貌的侍女,那是常有的事。但喜欢归喜欢,偷偷摸摸干出一些荒唐事,这也不足为奇。倘若从地下转为公开,那是为封建礼教的虚伪道德观所不容的。可周朴园竟然与一个侍女在大家庭里公开同居。我们暂且不管周朴园今后是否抛弃侍萍,他的这种作法在当时的封建大家庭里无疑有点离经叛道。
一个人物的具体动作和思想是具有连贯性的,舞台上正面展开的某一段情节与这个人物过去的生活不可能完全剥离,所以探讨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我们不仅要具体分析人物在大幕拉开以后的生活,而且应该走出作品,潜入造成这一形象的历史尘封中,了解人物心灵的历史缘由。追溯周朴园在大幕拉开以前的这一段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年轻时代的周朴园也曾追求过社会的新思潮,在他身上并不乏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甚至还闪耀过反封建的思想之花。他本可以成为新旧交替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代新人,因为在他身上不是没有导致他背叛本阶级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肩扛起黑暗的闸门,当他抛弃侍萍时又回到了本阶级的阵营,与传统的封建力量达成了和解。当然,这其中不能排斥周朴园个人品质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剧本通过蘩漪冷嘲热讽周萍“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哼,都是些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暗示读者外表威严、冷酷、专制的周朴园也有性格懦弱的一面。但更大范围说这也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封建闭关锁国的状态虽然被打破,但中国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形态。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周朴园,虽然为爱情作过一番挣扎,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弱。客观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周朴园放纵自己的生命激情,剧本借侍萍向周朴园诉说自己当年被迫离开周家时不用“你”而说“你们”、“你们老太太”暗示读者周朴园背弃侍萍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于他自己,而是那个代表着封建传统规范的母亲。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周朴园本人也是封建传统文化的被杀害者。
了解周朴园早年的这些经历,对于我们破译曹禺为什么在无情揭露周朴园冷酷、专横、凶残的面目时总不忘记对周朴园怀念侍萍、内心孤独的另一笔描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于周朴园来说,他有权有势又有钱,只要他愿意,他很容易找到渲泄情感的方式。巴金笔下的封建家长高老太爷(注:高老太爷是巴金的名著《家》中的一个封建专制家长,他表面上一本正经,其实道德败坏。年轻时同妓女交往频繁,人老了还跟唱小旦的戏子往来。),矛盾笔下的资本家吴荪甫、赵伯韬(注:这两个人物都是出自茅盾的小说《子夜》。吴荪甫是一个精明能干、有雄心、心狠手辣的民族资本家,身处逆境时,他就变得内心空虚,甚至奸污女佣人以渲泄自己的苦闷。赵伯韬是一个买办资本家,生活上极端糜烂,他在扒进各式各样的公债时,也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不都有着荒淫的一面。可周朴园与“荒淫”二字似乎很难有联系。他不象一般的有钱人,家有三妻四妾,还要到外面寻花问柳,他在肉欲上对自己近乎残酷,剧本借四凤之口告诉读者周朴园念经吃素,并且“一向讨厌女人家的。”周朴园为什么要如此禁锢自己,不肯放纵自己的欲望,而唯独对那个已经“死去”的侍萍念念不忘?如果不了解他早年的那些经历,那么这一系列的情节就不会令人信服。至此,我终于明白曹禺为什么不单单描写周朴园人性的恶,而要反复陈述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忏悔以及内心的孤独。原来这一情节在作品中的频繁出现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在暗示读者周朴园不只是个吃人者,同时也是个被吃者。今天的周朴园动辄以建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来毁比他年轻的人,殊不知昨天的周朴园正是毁于这种所谓的“家庭秩序”。周朴园从一个天真、有理想、有一定叛逆精神的青年堕落成一个世故、专横、冷酷、无情的封建家长,这个过程本身就有点意味深长。
《雷雨》剧中,曹禺如果一味描写周朴园的人性恶,那么我们憎恨的只是周朴园个人,而现在曹禺强化描写周朴园皈依封建规范秩序之后的精神创痛,把他塑造成一个既是吃人者又是被吃者,既毁于秩序又异化为秩序来毁比他年轻的人的双重身份的人,这就把读者的憎恨情绪从周朴园这一道德个体上升到了对整个封建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逼问。由此可见,曹禺没有把周朴园处理为一个十恶不赦、毫无一点人性的大坏蛋有他深层的艺术思考,那就是他不希望读者对周朴园们进行个体的法律和道德层面的简单谴责,他要读者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去思考某种社会必然,从而达到对罪恶根源的理性追问。
在《雷雨》戏剧舞台上,我们可以从许多人物的不幸中体味出封建力量吃人的本质。蘩漪、侍萍、四凤,哪一个能逃脱封建势力的魔掌,她们的悲剧正是对封建传统文化吃人的有力控诉。但是笔者认为,周朴园这个形象所包孕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现实批判力量比《雷雨》中比其他任何人物的悲剧性处理所产生的控诉力量都要深刻和有力。因为从情感的贴近来看,蘩漪、侍萍、四凤自始至终都站在封建力量的对立面,她们的遭遇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情,作者通过她们的不幸来谴责、追究环境,那是很自然的。然而周朴园是以恶者的形象出现的,他本人就是一个专横、冷酷的封建家长,曹禺要从这样一个令人憎恨的人物身上体察出封建意识和文化吃人的本质,首先必须克服感情的障碍。曹禺真不愧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在审度一个有种种劣迹、作恶多端的反面形象时,他并没有忘记生活的全部真实。
关于周朴园,评论界曾一再申明,曹禺描写周朴园的冷酷、专横、自私、伪善,其目的是为了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而描写他对侍萍的怀念,他的孤独,只是为了遵循“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的美学要求。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并不能说明《雷雨》何以超越同时代的同类作品,曹禺的独特艺术发现何在。显然,曹禺的用意并不希望停留在对周朴园进行一般性的揭露,因为这样的描写在曹禺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过许多;他也不单纯为了打破“叙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的肤浅的“性格单一论”。曹禺的艺术眼光旨在通过撕开周朴园这个专制家长曾经受创的精神伤痛,告诉人们周朴园强行把封建的“家庭秩序”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是这个“家庭秩序”的更早的牺牲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鲁迅以来的许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的宗法家长。但曹禺在揭露宗法家长吃人之际,描写他们在更大范围内避免不了被人吃的命运,这就告诉人们,当时社会广泛存在的悲剧并不是几个恶人所能承担。倘若曹禺将憎恨的情绪仅仅指向周朴园个人,岂不是放过了真正的凶手!
一个人物形象的艺术生命,不仅仅在于这个形象本身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而且这些性格特征能够“把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内蕴揭示出来”(注:阿·托尔斯泰《给一个初学作者的信》,见《论文学》第261页。)。 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使得曹禺在塑造周朴园这一形象时不仅写出了人和人性的无比丰富,同时达到了显现形象“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内蕴”的审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