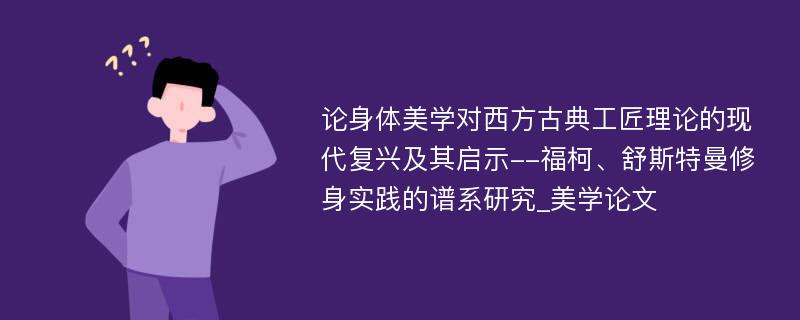
论身体美学对西方古典工夫论的现代复兴及其启示——阿多、福柯和舒斯特曼之修身实践的谱系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斯特论文,美学论文,工夫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6-0011-07 法国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研究表明,古典希腊时期的哲学首先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行为;不是一个思想体系,而是追求智慧的预备训练活动,即一种生活方式。阿多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哲学论述(discourse)和哲学本身之间的差别。自中世纪以降,哲学已经成为一种哲学论述,一种纯粹的理论和抽象行为,而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状态一直沿袭至今。比如,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哲学教育更多的是在讲授哲学论述,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无甚关联。因而阿多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是那些哲学教授的生活方式”以外,哲学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在现代性话语背景中,哲学话语(discourse)已经完全压倒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古典的哲学为人们规划了一种生活的艺术;而现代哲学则成为一种留给专家们的专业语言的构造”[1]199。 阿多古典哲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试图重建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个思路直接启发了福柯和舒斯特曼各自的研究,他们都是在回应阿多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主张。在阿多看来,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在古典时期的首要内容就是精神性训练(spiritual exercises)。精神性训练主要勃兴于希腊化时期。斯多葛派哲学明确提到,哲学乃是一种训练,它不在于传授某种抽象理论,而毋宁说是倡导一种哲学化生活的方式。哲学行为不只是限定在认知层面,而是包括认识自身及其存在。从现存保留在亚历山大的菲洛(Philo Judeaus)著作中关于古典精神性训练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对古典哲学的精神性训练管窥一二,其内容大致包括研究、调查、阅读、倾听、关注、沉思、治疗激情、牢记善的事物、自我管理和完成责任等等[2]84。所以哈多说,物理学研究在希腊化时期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性修习的方式。因为,物理和宇宙研究以及所有的精神性修习的目的,都是把我们从人的局限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让我们产生一种宇宙意识和普遍意识,把我们置身于宇宙整体性的视角和立场中,我们可以从“上面”鸟瞰世间万物,使我们获得思想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从而使自我的精神境界得到转变和提升。在古典时期,不同哲学流派的精神训练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无论其哲学流派之间有何差异,究其精神训练的目标而言都是相同的,即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自我提高(self-improvement)和自我转变(self-transformation)。福柯的好友思想史家保罗·韦恩(Paul Veyne)曾说,福柯晚年深深着迷于古希腊—罗马思想,一如他的精神导师尼采。晚期福柯久久驻足古典思想和古典修身工夫实践的关键人物便是阿多。两人的学术交往颇有渊源,福柯对阿多的古典哲学史研究也颇为欣赏,并于1980年推荐阿多加入法兰西学院,执掌“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思想史”教席近十年之久。同时,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明确提到阿多的研究对自己的巨大影响,福柯对古代性行为的研究深受阿多精神性训练观念的引导和设定。 舒斯特曼认为,阿多通过研究希腊化时期的精神性修习实践,尝试重新复兴一种古典时期就已存在但却被后世遗忘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晚期福柯受此影响,通过与阿多的对话提出了一种作为生活艺术的伦理学,探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真理的关系。而舒斯特曼的身体哲学和身体美学则通过修正和拓展身体经验的范围[3]61,批判、继承、发展和整合了福柯和阿多所提倡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并将其推进到一种实践的身体美学的范畴。舒斯特曼试图通过批判而逃离阿多和福柯的论述,建构起自己的现代身体美学实践。然而在笔者看来,身体美学在对阿多和福柯思想的整合中,除却缺少了古典修习特有的神性维度外,表现出共同的精神性训练主旨,即引导人们改变自身,达到一种智慧追求方式、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转变[1]195。同时,三人的思路都体现出不重视理论建构而重视生活实践活动的方法论特质,因而从本质上说,身体美学与古典哲学化生活和精神性训练具有同构关系,于是在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逃离阿多和福柯的古典修身工夫论阐释的同时,恰恰构成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超越式回归,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以最大的可能性在当代复兴了一种古典的修身工夫论,即一种身体美学实践外表下的古典精神表达。 在现代哲学语境中,阿多和福柯对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之研究可谓筚路蓝缕,接着又有当代学者P.布朗(Peter Brown)、M.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A.戴维森(Arnold Davidson)紧随其后,于是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现代研究和实践终于蔚为大观[4]7。在古典精神性训练的现代诠释中,福柯的影响如日中天,几乎掩盖了阿多的实质性存在,笔者在此特别提出这个隐藏在幕后的关键人物,试图从哲学化生活的宗旨、作用和特性三个方面来考察阿多、福柯和舒斯特曼三人思想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类似辩证法式“正-反-合”的内在逻辑结构,以作为舒斯特曼对古典修身论的逃离努力和超越性回归的基础地平。 (一)哲学化生活的宗旨:超越“整体性”和“个体化”的自我转变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阿多对希腊化时期精神性训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强调,得到了福柯和舒斯特曼的一致肯定。阿多认为,通过具体的精神性训练,个体把自身提升到宇宙意识的境界,即在一种整体性(wholeness)的视角中看待自我和世界,超越自我的个体性局限,从而达到一种天地精神的永恒状态,我们的整个生命从而能够向上提升。精神性训练使得个体从一种无意识的非本真状态中奋起,转向一种本真的状态,在那里他会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对整个世界的正确看法以及内心的平静和自由[2]83。 晚期福柯理论的出发点也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但是福柯的精神性训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个人主义解决方案。他曾将自己的所有研究概括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l' 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èmes),因为福柯的宗旨是试图重建我们自身,即使我们自身真正恢复成为当下实在的我们自己。福柯继承的是启蒙哲学的传统,把普遍性问题转化为个体性的伦理选择,要求认识我们自己的当下现实,并超越我们的当下现实。这是一种持续的“当下本体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它建立在一种通过“自我技术”而达到的哲学化生活方式上。福柯所侧重的是自我关于自身的关系,自我如何构建自身,自我如何建构和达到真理。福柯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个体性。然而,阿多对福柯的“自我的形成”观点有所保留,他认为福柯过于强调个人和自身构成的“自我”,强调个体性在精神性训练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阿多认为古典哲学中所关心的那个真正的“自我”,是精神性训练所要达到的具备了普遍性的自我。比如说,斯多葛派的精神修习的目标就是把“自我”提升到与“宇宙理性/普遍理性”融合为一的思想和行为中[5]615。在他看来,实现自我的个体性到普遍性的升华才是古典哲学精神性训练的首要目的。 通过强调身体(soma)在个体性精神训练中的中介作用,舒斯特曼整合了福柯和阿多的差异,并站在福柯的个人主义一边。舒斯特曼认为,由于阿多哲学的目的是通过转变个体自我达到宇宙意识的客观性立场,致使其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中过多地强调了精神的普遍性维度,忽视了精神性训练中的身体维度。显然,福柯比阿多更为敏锐地意识到身体在哲学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无论如何,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和阿多所说的“精神性修习”都必须以身体为其自我转变的场域。正是在这一点上,舒斯特曼补充了身体在自我修习中的作用,正如苏格拉底通过规律的舞蹈训练来锻炼他的身体,身体对所有人类的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健康,因为即使是在最少需要身体协调的思维活动中,严重的错误往往发生在人们疾病缠身的时候[6]30-31。此外,调息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通常我们并不注意自己的呼吸,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奏和深度改变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所以调息乃是古代东西方修身工夫论中最常用的方法。可以说,舒斯特曼的哲学化生活的目标就是我们的身体本身,身体作为一个具体的场所,在身体美学中既是整体化的又是个体化的。 (二)哲学化生活的作用:治疗功能和美学功能的合流 哲学化生活和精神性训练所针对的共同对象都是源自古希腊时期的激情。古典哲学时期,所有的哲学流派都认为激情是导致人类苦难和无序的根源,无规范的欲望阻碍了人类朝向真正的生活。因而所有的哲学首先都旨在治疗激情。各派的方法虽异,但认为哲学所具有的治疗功能则同,即治疗激情,促成个体的转变(self-transformation)。 舒斯特曼认为,自柏拉图以降直到希腊化时期,古希腊哲学被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健康为目的的医学模式,另一种是关于艺术的美学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哲学的治疗功能,哲学家和医生有很多相似,医生治疗身体的疾病,而哲学家治疗心灵疾病。但是哲学家必然高于医生,因为人生难免一死,肉体必然消亡,所以医生的失败是被死亡所预先注定的。可是哲学家通过把身体和心灵区分开来,基于心灵的不朽而超越了死亡的限制,使得哲学事业必然朝向永恒的胜利,即心灵的健康必然能够实现[4]24。阿多认同古典哲学的治疗功能,反对福柯的美学模式。他梳理了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早期基督教对哲学作为一种“死亡训练”描述,认为其治疗功能表现在通过死亡的限定性,迫使人们返回到唯一能够把握的当下,从而超越了对过去和未来的恐惧,在对当下自我的关注中,人们规训和管理自己的欲望。 福柯和舒斯特曼都明确倡导哲学的自我提升的美学功能。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高度赞扬了哲学家对美的爱欲(eros),认为这就是哲学的源头。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式生活就是对更高的美的不断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对更高的美的占有,毋宁说是在追求美的爱欲的启迪下,创造和孕育出“美的东西”,而且哲学家更以对美本身的完美形式的遵循为达到德性和完美知识的不二法门[4]25。这一古典哲学的思路得到了尼采、波德莱尔的发展,并在晚期福柯思想中发扬光大。自我把自身创造为一件艺术品的思路,正是晚期福柯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核心。舒斯特曼的身体哲学强调一种与现代主义相关联的美学模式。他认为哲学模式和美学模式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和重叠的。这种互补关系由来已久,在马可·奥勒留和普罗提诺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哲学和美学模式合流的情况。最显著的莫过于普罗提诺关于雕刻自己身体德性的例子。在普罗提诺看来,作为精神性修习之终极目标的自我实现就好像是雕塑家雕刻琢磨雕像的过程。与绘画的添加不同,雕像是一门删削的艺术,那个如同雕像造型的真我原本就预先存在于大理石里面,通过削凿掉多余部分,把所有细节打磨的温润光滑之后,其本体才得以呈现出来[2]100。当阿多反对福柯的美学模式,把福柯的美学模式简单地等同于浪荡子主义和人为的矫揉造作的时候,舒斯特曼恰恰是要通过雕刻的例子说明,治疗功能和美学功能可以是同时具备的。美学并不能局限和等同于乖奇和人造的,美学也可以是平淡、简约和修习的。普罗提诺关于自我雕刻的意向,正是在表达这种纯粹修习工夫的美[4]202。 (三)哲学化生活的特征:作为“自我创造”的自我发现 台湾学者何乏笔认为,阿多和福柯探讨精神性训练的不同,代表了欧洲修养工夫论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即追求自我发现的修养工夫和追求自我创造的修养工夫[7]48。阿多侧重的是一种以“心灵”为中心的修养模式,而福柯侧重的是以“创造性”为中心修养模式。以上述普罗提诺自我雕刻为例,自我发现意味着,我们的本真自我本身就包含在我们之内,“你必须去除掉所有的冗余之物,弯者使直,暗者使明,直到你使要发现的东西熠熠生辉”[2]100。因而只需要作减法,去掉不属于我们的无用东西,使原本晦暗的东西澄明起来,我们就能在自身之内发现真正的自己,紧接着涵养而扩大,最终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自我发现预设了一种传统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等级,也就是柏拉图式的欲望和灵魂的等级。个体所要做的就是发现真正的自我,因为发现的过程就是提升自我的过程。 而自我创造则意味着变换了主角。首先,自我成为雕像过程的中心,创造自我的过程就是自我形成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从被动性到主动性的转变,从客体性到主体性的转变,从普遍性到个体性的转变。福柯和舒斯特曼都更为强调这个意向中的创造性维度。这是一种启蒙哲学的常态语言,人超脱了“模仿者”的角色(模仿被创造的世界)而成为“创造者”[7]56。自我正是在不断的雕琢(即“创造性的越界”)中不断地臻于完美,止于至善。其次,自我创造的主动性扭转了自我和真理的关系。在福柯和舒斯特曼的思路中,他们更强调哲学化生活中的主动性和个体性要素,是自我在自我与真理的关系中构建了我自身、我的真理以及我的存在,也即自我创造了美,而不是美创制了自我,因为我们只是发现它。再次,自我创造意味着不断地创新和超越,因此福柯提倡一种越界的体验,即尝试和超越我们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创造性的越界”不仅仅是对波德莱尔式现代主义美学的追随,而且也深受康德启蒙思想对知识局限的批判和超越的启发。虽然舒斯特曼深受福柯自我创造的美学思路的影响,但是却不能认同福柯在创造性的越界中走向极端。这一点也受到阿多的批评,作为一名思想史家,阿多认为福柯所探讨的古代史料难以支持他如此激进的见解。 从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差异,可以引申出一种对立的态度:倡言发现者往往回望历史;倡言创造者总是眼光朝向未来。虽然舒斯特曼认为哲学化生活的探讨,应该更多地聚焦于由福柯和阿多初创的古典哲学时期,但是舒斯特曼也认为古典思想太过久远,无法切合我们当代对哲学式生活的追求。福柯也意识到,他研究古典的目的不是为了回归古典时代,也无法回归。在这个意义上,舒斯特曼继承了福柯的当下眼光,并不认可阿多的复兴古典哲学式生活的思路。在此,舒斯特曼试图调和阿多的修养论和福柯的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即把阿多的古典精神性训练的修养论放置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中,因为当代的问题只能由当代人来面对和解决;同时把福柯的自我创造模式限定在身体美学的实用主义范畴中。 作为一种倡导力行的“行动指南”,舒斯特曼无意于建构一个宏大理论体系,因为这与其实践立场相悖,也与身体维度相左。在某种意义上,舒斯特曼的思想倒是颇有孟子“距杨墨,放淫辞,正人心,息邪说”(《孟子·滕文公下》)的味道,他是在对历代思想流派的批评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起其必要的理论,在各种情境和场合下提撕现代人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自身,进而真正关心自身,故而其重心依然落实在如何作为“行动指南”力行的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哈多-福柯-舒斯特曼的思想所形成的“正-反-合”结构,恰恰显示出古典修身工夫论在西方思想中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以及身体美学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这种超越式回归并非对古典修身论的原样复制拷贝,而是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溢出了古典修身论的范围。 (一)舒斯特曼敏锐地意识到,作为一种精神性训练,过度内在化的自我检省是有问题的。完全内在化的自我分析和自我关注都具有片面性或者是基于某种文化或历史的偏见。而且,过于陷入沉思的自我分析对心理健康与健全也是无益的。尼采说:“人们如何能够知道自身?如此掩藏自己并沿着最近的道路强行下落自己本质的井穴,这是一种痛苦和危险的开始。他在此如此轻易地伤害自己,以至于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愈他。”[8]因此,福柯在尼采思想的基础上认为,一个建设性的自我关心比一个极端的自我认识更重要,所以哲学化生活和自我的精神性训练的目标都应该是如何达到自我转变,其目的是为了逃离当下状态的内在性和有限性,而不是如阿多所迷恋的要使自我一成不变地寓于其中。舒斯特曼说,歌德也曾批判传统的自我检省的内在化观念,他认为一个更健全和更可靠的自我认识不仅依赖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且特别在于通过其他人的见证来认识我们自己[9]49。无疑,歌德反对孤独的凝神于自身,他认为通过认识外部世界转而认识到的自我更有益处,即孤独的内省所达到的自我认识未必是充分的。通过把我们的生活和别人的加以对比,我们获得了比之于孤立的内省而言更为客观和差异更为细微的自我知识[9]44。 (二)舒斯特曼曾说,在身体美学的三个分支(即分析的身体美学、实效的身体美学和力行的身体美学)中,福柯都堪称典范[6]48。但是,晚期福柯用吸毒刺激产生剧烈快感,并通过同性恋和虐恋超越身体限制追求极端体验进而试图到达自我转变[10],以及他以波德莱尔的浪荡子主义的标榜来追求当下的短暂瞬间的英雄化[11],都削弱了哲学化生活的身体实践所内含的精神价值。舒斯特曼认为,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修身论对美学模式的理解太过激进和单一了,因为“简单的通过增强感觉的强度并不能增强快感。当感觉遭受剧烈冲击时,感觉欣赏反而会变得迟钝”[6]59。福柯的思路,与阿多所描述的古希腊修习训练(比如体操),特别是与东方文化中特有的通过“虚静恬淡”来实现自我精神境界提升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照。比如,瑜伽行者反倒是通过排空当下所有欲望,调息止气,专注于一,进而达到身体和心灵的充实。舒斯特曼用自己非常欣赏的东方式的虚静来补充福柯对美学模式理解的片面性和简单化,这个思路对西方修身工夫要么苦行禁欲要么纵欲无穷、动辄走向极端的态势给予了针砭和纠偏。 (三)舒斯特曼认为身体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我们是一个身体,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身体[6]14。我们是一个身体意味着我们能够自我创造,我们有一个身体则意味着我们能够自我发现。古典时期的修身论不谈创造性,因为自我处在柏拉图设置的金字塔等级中,遵守规训的要求足以使自我发现自身而提升境界,在古典人看来创造属于神性的维度。福柯对古典哲学式生活的研究引入了自我创造,因为他着眼于考察主体创造自身的过程。对福柯来说,身体一方面通过建立尚未被社会规训的快感而构建出独立自治的自我,从而达到自我的精神转变,另一方面,在舒斯特曼看来,无论什么样的自我建构过程本身都是一个不断被社会权力规训的过程。即便是福柯的“创造性超越”的美学诉求也必须以一种身体的修习训练为前提。因而,舒斯特曼对福柯把身体的规训和无规训的试验相结合持保留意见,就像晚期福柯思想把艺术和激进的新思潮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一样[4]36。舒斯特曼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可自我发现的。而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自我发现并不是一种对自我反思的认同。舒斯特曼坚定地认为,身体美学所要发现的那个真实的自我绝对不是通过意识的自我反思获得的,反思总是添加了不是自身的东西。因而,那毋宁说是一种超意识的自我发现[12]7,作为一种“自我创造”的自我发现。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上说明了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在西方的古典修身工夫论的现代话语中所处的位置。阿多、福柯和舒斯特曼对古典修身论的发展以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结构得到表现,舒斯特曼整合了阿多和福柯的精神修习的言说,通过恢复了身体作为体验和实践之场所的重要地位,实现了对古典修身工夫论的现代复兴。同时,在这种生活美学的接引下,我们也发现西方古典修身工夫论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修身传统具有颇多亲缘性:二者都强调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倡导通过一系列的修身训练的实践活动,而实现自我的精神状态的转变。因而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说教,而是一种实践的行动指南。在这个意义上,舒斯特曼的身体哲学成为东西方传统修身工夫论对话的一个桥梁。如今,国内学界基本已经认同了舒斯特曼身体美学具有“知行合一”、“身心合一”、“身体表现”和“生活美学”的特点[13]69-70,其身体思维与东亚思想的亲缘性也带给东亚思想诸多借鉴。 (一)舒斯特曼对东方式“淡雅的美学”颇有好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它不同于阿多笔下古典希腊世界的写实的逼真,也不同于福柯式的对极限体验之强度的无限追求。当西方思想史可以化约为“极端的身体体验”和“哲学推理研究”相互补充[4]33,以期跃出经验和语言的限制的时候,舒斯特曼引介东方式的恬淡宁静,对身体哲学给予多维的补充。舒斯特曼从日本“能剧”的身体表演,宋元山水画中的修身风格,禅宗的身体实践,中国的房中术、瑜伽与太极,费尔登克拉斯技法以及现代建筑和摄影等等角度,切入具体的日常生活。东方式的淡雅与中道是一种在生活之中的身体体验,它不走极端、深入生活,这一点在舒斯特曼身体哲学中产生了共鸣。无独有偶,晚近对中国文化极为仰慕的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也从同样的角度赞赏东方式厚度体验,认为东方强调的“暗调”价值观,与西方文明对“亮调”的喜悦形成鲜明对比[14]。这是一种“中道”的美,一种东方式追求充满时间厚度的、朴素原生的、历久弥香的恒久美感,与福柯所代表的那种瞬间的、人为的、强烈的美感完全不同。同时,舒斯特曼的思路得到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的回应。于连集中讨论了表现在中国绘画、饮食、音乐、诗歌中的淡而无味,甚至把“淡雅的美”上升到中庸的本体论高度。“平淡是人意识中一种全面性的经验,它以最根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在世存在”[15]。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舒斯特曼身体美学在复兴古典修身工夫的过程中,与东亚哲学和美学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化生活相遇,并深为其吸引并视为同道。它对身体体验之深度和厚度的强调,更是对福柯推崇的身体体验之强度和烈度的矫正和补充。作为一种精神性训练的现代模式,身体哲学对东亚淡雅美学的推重,使传统中道之美在西方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二)中国传统哲学向来被视为不重理论思辨而重修身实践,这恰恰与阿多研究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希腊哲学颇有汇通之处。然而,舒斯特曼发现,在古希腊时期,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self-knowledge)的首要功能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避免傲慢地挑战诸神的权威,因而自我关心(epimeleia)和自我知识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健康的。可是,当后来自我知识完全来自对自我及其特性的严格剖析的时候,自我知识和自我关心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过度的自我分析的沉思和玄想早已与自我关心的本旨大异其趣。同理,在中国古典修身工夫论中,虽然孟子提到要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但后来王艮的以“身”为“天地万物之本,天地万物之末”(《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心斋语录》)及“以己正物”的思路同样与先秦儒家本旨相去甚远。宋明理学以降,向内收敛的心学使中国知识人放弃了社会和宇宙,自我封闭于道德主体的修习之中。于是,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一方面认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性训练的古典修身哲学的历史价值(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的修身工夫论),另一方面又对其彻底内在化的趋势表示遗憾。因而,通过继承尼采、歌德、詹姆士和杜威的思想,舒斯特曼毋宁说主张通过我们在世界中的活动来实现自我的转变,而非通过内向的专注于我们的私人意识来达到自我的转变[9]51。精神性训练如何通过“在世界中的活动”来达到,如何像福柯一样逃离当下状态的内在性和有限性?这正是舒斯特曼的身体哲学所关心的——即实践中的完美主义和对生活的批判[3]59。舒斯特曼强调身体修身实践在个人和社会中所产生的实际效用,比如社会改革、民主伦理、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批判等等。所以,从实现自我转变的目的讲,身体美学既与古典修身功夫同源同构,又有其超越性,即它不是一种内在性的对意识活动的反思,而是一种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拓展了身体经验的至善论。 (三)舒斯特曼提出的一种作为“自我创造”的自我发现,试图重新勾连起康德以降就被割裂开的道德伦理与艺术美学。道德修习和艺术美学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强项。且不说《论语》“风乎舞雩咏而归”,和《乐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的圣贤之路,单就舒斯特曼举到的中国书法之例[16],就完全能够作为身体美学实践表现的最佳的象征。虽然阿多也提到古典希腊时期的美指的是形式的完美、灵魂的安宁、自我的满足和宇宙的意识等等,获得幸福生活的途径正是修习工夫和死亡训练[1]197,但是西方哲学固有的形而上思路往往使美学诉求倒向了纯形式的超越性和彼岸的神学维度。福柯晚期思想的核心是个体通过自己的伦理选择而把自己的生活构造成一件艺术品的生存美学[17]。这种伦理和艺术的世间化程度并不充分。所以在世界中寻找道德与艺术的结合的范例,使舒斯特曼再一次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传统中的修身工夫论——中国书法。与中国画的纯艺术美学不同,中国书法完全是一种越界的美学[18]105-109。它既是记录,又是修习;既是实用性的生活工具,又是创造性的美学追求。书法本身就是一种法度严谨、需要长期训练、技近乎道的修身工夫。首先,书法是一种生活化“日用即道”的修身方式,它不是朝向某个超越维度的禁欲表达。其次,它是建立在自我认识基础上的自我创造,任何人经过训练都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个性与情绪表达。东亚思想善于在日用修得中表现美学,以中国书法为代表的一种精神性训练思路,即一种作为“自我创造”的自我发现,完全实现了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诉求,成为一个东亚式道德修习与艺术美学相结合的实例,中国传统的修身工夫论反倒给西方现代修身工夫的复兴以启发。 总之,阿多对古典修身工夫论的研究和福柯对身体维度的强调,使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复兴一种古典修身工夫论成为可能。哲学化生活和精神性训练可以既是普遍化的又是个体化的,既是哲学的又是美学的,既严格修身又自由创造。福柯因为反对阿多修身工夫论的古典色彩而逃离走向伦理自我,舒斯特曼因为福柯自我的不彻底性而逃离走向身心合一的身体,但是这种否定之否定的逃离,恰恰构成了舒斯特曼身体美学对古典修身功夫论的超越式回归。阿多曾说:“在二十世纪末,福柯、我自己,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人,我们以完全不同的进路,却将相遇在这个鲜活的重新发现的古典之经验中。”[2]233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之理论构成的非体系化、修习工夫的实践表现和精神性训练之目的的生活美学诉求,都最能代表古典修身工夫的实质,所以身体美学的现代外表下流动的恰恰是古典精神的血液,正是这种从现代回到古典的品质,使它为东西方修身功夫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平台。 收稿日期:201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