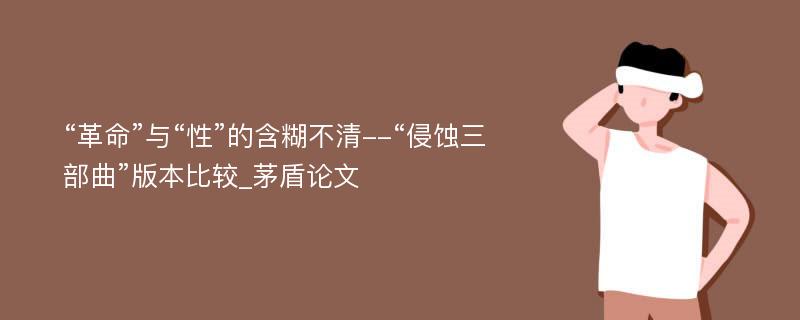
“革命”与“性”的意义滑变——《蚀》三部曲的版本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版本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茅盾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三部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从1927年下半年的第九号第十八卷起到1928年上半年的第九号第十九卷止。这是这三部小说的初刊本。1930年5月,茅盾应开明书店之约,将三部合为一部出版,总题为《蚀》,是为初版本。此后,开明书店将《蚀》多次再版,其间作者没有作什么修改。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这个三部曲时,建议作者“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1] (第427页),茅盾便作了一番大的删改。这便是《蚀》的定本。1958年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一卷和1984年出版的《茅盾全集》第一卷所收录的都是这个版本。在《蚀》的版本变迁过程中,只有1954年的修改才是真正的修改。这次修改涉及多方面,但主要是“革命”与“性”的内容。当置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中心的茅盾,以新政权文化要人和文学权威的身分来修改20年前的这部旧作时,无疑会使这些重要内容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滑变。
一
“革命”这个20世纪的流行词汇,在《蚀》三部曲中具有一种宽泛的语义。不同人物以不同的理解和行动来诠释这个大的时代词汇。对于静女士来说,逃避包办婚姻并附带增长见闻,获取新知便是她对“革命”的理解;而慧女士显然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看穿这世界后游戏人生的姿态。对于方罗兰来说,“革命”意味着在左右摇摆地为党国卖力的同时开导保守的妻子,从而使自己获得在工作、家庭(妻子)和红颜知己(孙舞阳)之间的转圜。对于史循,“革命”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和无尽的挫折感、失败感;而于章秋柳,“革命”便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热情来激活业已消沉的革命者史循,从而使自己的梦想得以借这个曾经强壮的身体来实现。这些人物尽管不曾大谈“革命”二字,但他们的行动无一不在印证着革命具体化出来的种种情态。而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革命”至少具备两层语义:一是政治地位和身分上的平等和自由;二是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改造和解放。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革命”一词,茅盾更偏向后一层语义。在《幻灭》中,他借李克训诫静女士的口吻说:“也许你不赞成我们的做派,但是革命单靠枪尖子就能成么?社会运动的力量,要到三年五年以后,才显出来,然而革命也不是一年半载打几个胜仗就可以成功的。”[2] (第75页)这种重视“启蒙”的革命观,虽不否认革命所具有的军事斗争的一面,但更重视它唤起觉醒,改造精神的另一面。在茅盾早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都提到“革命”及与之相关的“改造”、“解放”、“自由”、“平等”等系列词语。事实上,“革命”一词已内化成茅盾的基本词汇,对其语义需反复阐释和扩充,目的是让它能跟上现实政治发展的步伐,从而获得更为完整、系统和精确的意义。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这场革命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有所作为,而不至于被时代大潮抛弃。这种对革命的理解显然远比将其单纯理解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斗争的看法要宽泛得多;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定位,茅盾们的自我默认当然就是精神导师,这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一种天生的自我优越感,其中既不乏中国式的“为帝王师”的文人理想,也暗合了他们谙熟的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者之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革命模式。但事实总比理论更具说服力,在真正的革命开始后,一个罗伯斯庇尔远比一打伏尔泰或卢梭更有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启蒙更具备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茅盾们所颇为自得而不时刷新的革命定义还是赶不上也把握不住现实的发展,甚至不时沦为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阵营的笑柄,而他们急切地想投身革命阵营发挥自己才能的行动又总被涂上一层“小资产阶级”的色彩而屡遭批判。
知识分子投身革命遭遇的尴尬,乍一看是他们没怎么弄清“革命”的实质就匆忙上阵。仔细考察才会发现:其投身革命的动机本身就值得怀疑,其中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往往要多于为理想而献身的成分。此外,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唤起革命的往往是一两个先觉者,但它一旦成为时代大潮后,就会演化成为群体性的冲动而将先前个人独立判断的成分淹没。不管承认与否,后来的知识分子侧身其间更多的是出于不愿被时代所弃的功利想法。茅盾本人的投身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革命阵营的外围写下大量革命性的文字之后,终于忍不住一试“革命者”的身分。但跻身于革命行列并不能抹去这些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天性——怀疑和反思引发出的个人独立判断,而正是这种判断往往会导致他们质疑眼前这场革命大合唱。显然,这种理性判断已在悄然中与他们当初投身革命的动机发生了深刻矛盾。所以,置身于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普通民众,在更容易对革命产生狂热依恋情绪的同时,也更容易对革命发生怀疑而陷入悲观和颓废。茅盾小说中的人物及他本人都以自己的行为印证了这点。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将革命乌托邦变成了一种具体可感的政权和制度,此时茅盾们回首曾经走过的路,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才发现他们当初对革命的理解哪里为正确、哪里又有偏差或者错误,以及自己在这场革命中及革命后的定位。而他们此刻要做的就是及时地调整和学习。当然,这不过是在以一种既定成型的制度作标准来纠正从前的理解并尽量向这种制度靠近,以期实现曾经“为革命奋斗过”的经历和身分体认,而并非是曾经对“革命”的理解和憧憬了。因此,当作者发现自己早年对革命的理解已无法跟上新时代对它的定义时,对旧作中革命定义的刷新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初版中作者所犯的最大失误可能是:一、对革命的方向认识不清。几十年后再回头可以很容易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政治和军事斗争。而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将热情和努力用错了方向,而且眼光狭小局促,缺乏必要的胆识和魄力,基本上是一群软弱无力的“文人型”革命空谈家;且往往沉湎于一己之解脱,并将这也看做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慧女士的性开放,方罗兰的家国兼顾念头和行为,章秋柳的企图唤醒早已行尸走肉般的史循的生命欲望和革命热情等。这种带有明显“五四”个性解放和精神启蒙色彩的“革命”举动从政治和军事层面来讲,基本上是无用的。在“破”字当头的年代,需要的是认清方向后的猛烈进攻,而一切具有建设性的东西是要退居第二位的。二、没有发现革命的主体。“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而整本《蚀》中的所有主要人物居然都没有认识到人民身上蕴藏的无穷的革命力量。就算偶尔出现的像孙舞阳和方罗兰等对诸如南乡农民的行为一定程度上的默许和赞同,也不过是好奇大于理解。不仅如此,甚至在初版中还有不少蔑视普通民众的描写,比如对南乡农民的“公妻”场面的渲染。这些失误在1954年修改时尽管已不可能完全改变,但局部的订正还是可以做到的。经过修改,作者有意从文本所营造的真实环境中抽身出来,站在更高角度上俯视主人公们的盲动,揭示一种必然失败的“教训”,而不是引发读者产生与自己当年相似的困惑感和幻灭感,从而取消了初版中作者与读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代之以指导者的口吻。在此转换中作者也巧妙地实现了自己对“革命”定义理解的刷新和提升,即:他承认新政权所倡导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式的“革命”更高明,并对这种“革命”所带来的改天换地的变化表示了心悦诚服的欣赏和追随。作者正是通过修改旧作中相关内容来彻底改造自己过去的“革命”理解,并全盘接受了新政权的革命观。而至于某些地方的修改可能带来的历史失真就不再是作者所愿从容斟酌的了。此外,初版本中可能引发读者偏离“革命”正题,向耽于爱情或者丑化人民群众方向发展的词句和线索也被修改或截断,民众的形象得到了改善。不过,对于营造艺术真实的考虑及其它一些原因,也使作者在修改时保留了大量此类描写。如此一来,小说尽管离后来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红色话语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对于早年追求“实地观察”、“客观描写”等自然主义写法的茅盾来说,这种转变已经是巨大而深刻的了,作者本人的形象也在这种修改中悄悄实现了升级。
二
女性解放问题一直是茅盾写作的中心话题之一。在其早期的社会评论中,很大一部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相对于经济独立和政治权利的获得,“性”的自主或曰对自己身体的支配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更迫切也更容易付诸实施的“革命”。茅盾曾说:“我信妇女问题不必定要从经济独立做起——西洋的往迹虽是如此,那是病的状态,不是正当的途径,……我所主张的,且信的,是妇女问题该从改造伦理,改造两性关系入手……”[3] (第138页)。基于这种观点,再加之年轻激进的心态,就使茅盾在他的小说中着手实现这个“革命”中极重要的方面。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这类女子尽管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已频频出现,但如此大胆而正面地描写她们的“性”,作者还是第一人。大概是为了肯定性地凸显她们的“解放”姿态,表明“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4] (第524页),作者不惜笔墨,甚至以过度的“性”描写方式来渲染她们。其中或许有向保守的旧式道德和文学观念宣战的姿态,或是受了自然主义描写观念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在应和时代大潮,创造一种新的时代女性形象和道德观念。这些描写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不乏引人注目之处,难免招来非议和批评,但毕竟在时代主题之内。
初版本中往往有意凸显女性性别身分,其意在让女性认清自己不同于男性的性别特征,并表明这种性别差异恰恰有可能是女性获得自身解放的一个突破口,女性不应将自己的身体保持在那种不敢诉诸欲求的状态,而应释放自己的情和热,追求和男人一样的幸福、平等和自由。像慧女士那样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也应受到一些道德上的非难,但仍不失为一种“解放”的姿态,实际总比旧式女子沦为男子发泄工具要觉悟得多,而孙舞阳则甚至获得了男性中的佼佼者方罗兰的青睐和追求。章秋柳对于革命者史循来说,简直就是可以赐予他力量的“女神”。她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革命性”举动,用《动摇》中史俊评价孙舞阳的话来说,就是“不做点破天荒给他们看看,是打不破顽固的堡垒的”[1] (第170页)。在经济独立,政治平等暂时还无望的情况下,这种奇特而大胆的方式自然就成了茅盾所认为的妇女解放的“捷径”,也是符合他所强调的通过“改造伦理,改造两性关系”来解放妇女的主张的。尽管这相对于真正的妇女解放来说,还只停留在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条件去和男权社会讨价还价的阶段,但它毕竟比封建伦理中要求妇女无条件向男权屈服强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在宪法中已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而且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翻了身。恋爱婚姻自由、经济独立、政治权利的获得等已成为现实。一直关心妇女解放问题的茅盾不能不对他早年的观点有新的扩充。过去他所提倡的那种与性别身分紧密联系的妇女解放在今天已不够格称为“解放”了,而与之相关的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则已不成其为问题,如果还在小说中以这种凸显妇女性别特征和性别差异的方式来阐释妇女解放的话,显然就有贬低妇女的嫌疑了。因为,新社会恰恰是以抹去妇女性别身分特殊性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妇女解放及其地位的。
因此,小说中显得不合时宜的地方就需要大作删改了。初版本中有意凸显女性性别身分,大量存在引发性联想的词句以及诸如将钱素贞一类女子人格贬低的描写。到了定本中,则尽量减少或弱化女性的性别身分,删去可能引发性联想的词句和情节,并抬高妇女地位和人格。修改后,小说中的女性如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无一不是内涵丰富,敢作敢为且光彩照人,就连懦弱的静女士、传统的陆慕云和温柔内向的方夫人也都不乏开放和进取之态,尤为重要的是,她们更多的是以自己的人格和性格而不是身体来取得了与男人的平等。比如,《幻灭》的结尾部分重点描写静女士开导强连长的部分基本没动,而他们在庐山热恋的部分就被删去或简省了;在定本《动摇》中,孙舞阳让方罗兰拜倒的地方不再仅仅是身体,更是她的谈吐、见识和为人处事之处;而定本《追求》中,史循和章秋柳之间带着狂乱和死亡气息的“刹那的肉感的狂欢”完全被删去,目的也在淡化章秋柳以身体激活史循时所带有的强烈的女性性别色彩,而保留并加重了前者对后者精神上进行开导和指引等内容,前后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一些直接与性描写相关的内容,如《动摇》中陆慕勾引钱素贞的一大段,《追求》中章秋柳与史循的性爱场面等,被大面积删改;甚至一些描写女性身体部位如胸脯、屁股、腰肢、皮肤、曲线等的词句,也被删改。比如初版本中,作者在描写慧女士和孙舞阳等人时,总爱对特定部位进行不厌其烦地刻画,在定本中大部分都删去或更改了;甚至连那些只是间接反映性别特征或与之有关的描写和渲染都不能幸免,如眼神、暧昧色彩的话语、口鼻的气息、身上的香味、衣服的样式、走路的姿态,乃至房间的陈设和环境等等。某些地方的删改的确起到了去芜除繁并使叙述更趋紧凑流畅的效果,但更多的却是带来了减弱阅读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度的负面影响。当然,通过这些修改,作者当初所提倡的妇女解放方式和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也就发生了变化,妇女以“改造伦理,改造两性关系”求得自身解放的内容的删改和与之相对的争取与男子同等政治经济地位内容的保留,都使女性形象向新型的妇女解放观靠拢。
三
女性的解放不是孤立的,总是与男性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男性在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茅盾自认为:“提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使和男子一般高,使成促进社会进化的一员,那便是我们对于女子解放的理想的大标帜。”[3] (第98页)在《蚀》三部曲中,方罗兰的身上集中展现了当时革命者典型的“双重任务”:革命+恋爱。革命者们在忙于火热的革命工作的同时,也将高涨的革命激情分出相当一部分投入到爱情中。另外一类则是将爱而不得中被压抑下来的爱欲冲动转化为革命或社会活动的热情,静女士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在恋爱场中失败的人儿,现在转移了视线,满心想在‘社会服务’上得到应得的安慰,享受应享受的生活乐趣了。”[2] (第78页)还有一类是由于内在或者外在原因导致革命欲望无法满足,便寻找恋爱来替代。“例如同事们举动之粗野幼稚,不拘小节,以及近乎疯狂的见了单身女人就要恋爱。”[2] (第153页)王德威评论说:“小说家更标举革命与爱情,并赋之以改革现实的使命。用陈清乔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爱情(love)看成一种情感驱动力,内化了社会改革的冲劲;那么爱欲(eros)或可视为一种生命能量,足以推动终极的革命之轮’。”[5] (第54页)恋爱与革命并行不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恋爱本身也是革命的推动力或形式的一种。当然,对于二者奇妙的结合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革命与恋爱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革命使人斗志昂扬而恋爱使人容光焕发。而革命的开放性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需承担起使命,其目的指向全体利益的实现,但它在宣称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其实无法满足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所以,这项伟大事业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并且不可能完美。恋爱的排他性意味着只需对一个人负责,其目的指向个人身体和精神的愉悦感的获得,它的完成有可能缩短到一刹那,并让人体验到完美的成功感与满足感。不管是基于一种什么考虑,茅盾以及他后来的大批同道者和追随者都选择了“革命+恋爱”这种奇妙的方式来实现他们革命化叙事的欲望。其实这种方式也真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革命者因此而变得有血有肉,鲜活可感,向一切读懂他们的人散发着自己身上无尽的情和热、光和能。相对于几十年后红色话语体系下涌现出的“革命者”来说,他们身上保留了不少“人之初”的真诚感和真实感。当然,这种由青春情绪、爱欲冲动激发并绑定的“革命”向往,实在与另一种由工农翻身欲望激发的“革命”需要大相异趣,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了工农革命胜利后前者必须实现全面“整改翻新”以向后者看齐的伏笔,而对这种“革命”进行描述的小说自然脱不了干系。
新中国的成立让一切对革命模糊而狂热的憧憬都变成现实,“革命”坐实为实在的政权和制度后,新的风尚、规范和禁忌便随之出笼。在新社会,“性”问题遭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阻力,爱情也在“不便多说”的范围之列。“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翻了身’,也许翻过来的身体应是‘无性的身体’?革命的成功也许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新的社会全景中‘性’所占的比例缩小到近乎无有?”[6] (第63,64页)革命与恋爱之间不再是二三十年代的并行不悖、一体两面,而是互相替代、互相排斥的关系,甚至变成了大家与小家、大我与小我、进步与落后的代名词。追求前者只能牺牲后者。而且,新社会正圣贤化和理想化革命者群体,并崇高化历史记载中的相关革命片段,以激励民族、教化人民。在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下,革命者形象如果还不能“与时俱进”,势必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严重的可能会背上抹黑革命和革命者的罪名。所以,定本通过对初版本中相关地方的“洁化”,基本上符合了新社会的要求。这里不妨简要举证一二。
《幻灭》中的强连长是一个带有“未来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他最终在继续爱情与重返部队之间选择了后者。这种行为在初版本中,读者往往是站在静女士的角度理解成她个人追求的“幻灭”。作者的初衷也很可能是想凸现这点,表明强连长的离开是厌弃了再也不能带给他新鲜刺激的静女士。但在定本中,同样的行为,读者却很可能是站在“革命者”强连长的角度,把它理解成冲出生活的小天地,走向革命的大舞台。这里面尽管有时代背景变化的因素存在,但作品在修改后“革命”语义的潜移却是导致这一变化的更主要原因。需补充的是:静女士的性别身分在修改后被明显减弱,甚至出现了反过去开导强连长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加强了读者从强连长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减弱了她带给读者的被抛弃印象。在淡化了个人生活和情感追求后,强连长与静女士都不自觉地向“革命”的方向靠拢了。《动摇》中的方罗兰,定本在大量删改了初版本中关于他的性和爱情的描写后,他身上肩负的家庭与革命的“双重任务”中,家庭(或者说个人情感需要)的一面减弱,而重心则滑向了“革命”的一面。而对于孙舞阳,在初版本中,作者总是努力想把她塑造成为一个身体和灵魂“双重解放”的女性,结果是“解放”总被“性感”取代,灵魂的吸引力被身体的诱惑性所稀释。定本则通过对大量围绕在她身上的涉性句段的删改,使孙舞阳在大大减弱了性别色彩的同时,其内涵和革命性得到了加强。正如方罗兰对孙舞阳的总体评价由初版本“……她的活泼和肉感”变成了定本“她的豪放不羁,机警而又妩媚,她的永远乐观,旺盛的生命力”一样,孙舞阳总体上由“性”魅力变成了“性格”魅力,真正像一个女革命者了。
四
茅盾曾说,他对《蚀》三部曲只在“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1] (第427页)。其实,这种说法不确切。至少“革命”和“性”这类重要内容是作了很大修改的,并直接导致了意义的滑变。在初版本《蚀》中,茅盾证明了性描写的合法性,呈现了性与革命的紧密关联;定本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这种合法性的质疑和对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的认同。初版本写出了革命的含混性和复杂性,定本则张扬了政治维度的革命,明显使革命的意义单纯化。仅从对“革命”和“性”的修改来看,《蚀》的新旧版本就体现了不同的版(文)本本性。茅盾在修改《蚀》三部曲时曾担心,“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1] (第426页)。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事实。实际上,在新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修改《蚀》,必然会受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的约束。不仅如此,这种修改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中国文学“洁化叙事”规范的建立。而“革命”这一20世纪的重要词汇的语义滑变,也无疑会为观念史学或语义学的研究提供绝好的例证。
不过,一个有趣而重要的方面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在新社会,《蚀》中的革命者至多只能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者”。所以,尚还被容许身上有诸多“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认不清革命方向,犹疑不决,沉湎于个人主义,追求爱情享受和精神刺激等等——作为反面事例存在,以教育人民。茅盾有一段向人民真诚剖露心迹的话也似乎证实了这点:“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1] (第425页)但恰恰是这层“小资产阶级”定性的保护色,给茅盾在1954年对初版本的修改留下了相当大的回旋空间,他可以而且理所当然地保留涉“性”(和爱情)句段、主人公并不怎么革命的言行举动,以及对“人民群众”不太客气的描写等。所以,在笔者对校初版本和定本时,发现一些在20世纪50年代完全称得上是犯忌的地方居然基本保留。如对农民的描写,南乡农民的“公妻”举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共产共妻”的味道,而共产党对敌人“共产共妻”的污蔑一向是极度愤怒的;王卓凡的“耕者有其田”外“多者分其妻”的口号也是极大地与后来新政权提倡的“一夫一妻”、恋爱婚姻自主自由相违背的。在后来的红色话语体系中也从未出现过描写农民如此违背共产党政策的地方。这些内容,在《蚀》中虽然作了很大修改,但居然有许多保留,不能不算是保护色创造的一个奇迹。
总之,从初版本到定本的变迁中,作者对多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而“革命”与“性”两方面则是重心所在。由此而形成的定本实现了对文本的全面翻新,并让读者读出了许多不同于初版本的新意来。当然,在修改中作者也尽可能地尊重并保留了作品中自己旧有的思想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