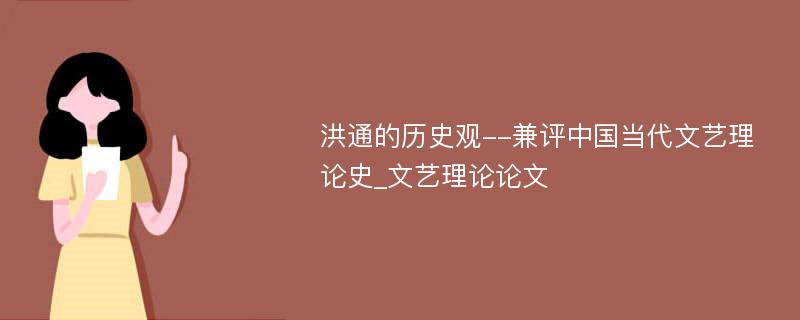
宏通之史识 卓然之史观——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卓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世纪之交的文艺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建立一种具有时代独创性并能够满足当代中国人审美需要的新形态的文艺理论。总结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经验,认真审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误区,正确设计文艺理论的未来走向,就成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南京大学包忠文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版),便是当代文艺理论界对建国以来文艺理论发展的一次深刻总结。该书追溯了自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到1996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六次文代会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并结合史的线索,对许多困扰着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问题作了深入探索,充分昭示出著述者宏通之史识,卓然之史观,是一部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力作。
一、整合历史、创为新说。
写史有什么用?这是每个著史者经常面临的诘难,但其答案也同样是不容究诘的。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如何科学、理性地对待过去,更应有助于人们认识现实观照未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正是在整合历史中创为新说,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理论色彩。具体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使该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深刻性方面有新的拓展。历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这种研究能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它完整、全面地追溯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47年的坎坷历程,系统准确地记录了各种文艺思潮的衍生嬗变、重要文艺观念的兴盛衰败,以翔实的史实,从正反两方面全面分析了这些思潮、观念、现象的是非、得失,深入剖析了导致其挫折、失误的原因,处处显示出著述者将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将有益的历史认识付之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与文艺创造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又在史的勾勒中重点反思了四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坚持和发展、文艺理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文艺理论模式探索,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当代文艺理论所走过的47年,既是在“左”的文艺思潮下遭受重创的时期,同时也是不断走向重大发展的时期。这就从本质上廓清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只看到失误,看不到前进;只看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力量,看不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创造作用;只知道否定,不知道继承的思想误区,将历史的反思提高到怎样建立开放的富有中国特色马克思文艺学的理论基点上。作者认为:从建国以来文艺理论发展看,一个带根本性的经验教训是如何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问题。史著认真地清理了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局限,指出其在接受的片面性、研究的注释性上所犯的错误,深刻地剖析了庸俗社会学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经院化、神圣化,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脱离了现实社会与当代文艺实践,最终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和创造品格的教训。作者继而针对当前文艺理论研讨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持怀疑、否定乃至敌对态度的趋向,指出:不能把当代文艺理论在接受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上的偏差、失误、挫折,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本身的失败;也不能一讲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否认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今的文艺理论建设中不仅不能削弱与取消,相反还应该强化,她应当也必然会在批判地吸收各种各样文艺美学的内核中,立足中国的当代实践求得更加全面深入的发展。由于占有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作全面的对比分析,史著的总结是有说服力的,也说明了著述者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证判,在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
其二,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使该书建立新文艺理论体系的构想更具科学性。史著在研究思路上坚持两点:立足现状,立足新时期文艺及其理论的发展,坚持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总方向;运用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美学方法,承认历史事实,并对建国以来文艺理论的历史,作出切合我们时代发展的阐释。所谓民族化,是指从“古今中外”化的角度来建立文艺理论研究的独立品格。它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继承、借鉴古今中外文艺传统与经验,按时代的要求对它们加以改造、革新、创造;二是将文艺理论研讨向中国文化和思想覆盖,深入到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建构上,从审美意义角度揭示出我们的民族特性。所谓科学化,是指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特殊性。一方面,要确定文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文化中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区别其不同于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意识形态的独立意义;一方面要确立文艺研究方法自身的特点,寻找其不同于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采用的独特方法。正是凭着对文艺理论“民族化”、“现代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凭着将“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美学方法,史著撇开政治的漩涡,揭开历史的尘封,对众多的文艺理论著作、文艺理论家、文艺思潮作出了中肯的历史评价,清晰而又科学地勾勒出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总体脉络,并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诸如文学艺术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文艺的本质和规律、“左”的文艺思潮与传统文化、文艺理论体系的科学化和民族化,当代审美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历史运动,当代诸种文学观及其局限、新时期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与反思、当代文学史观的发展、历史和历史剧问题、周扬现象和胡风现象、“历史合力论”与当代文艺美学研究等作了专题探讨。此中,不论是对一些基本理论概念与范畴,如文艺的“艺术认识本性”说,“艺术审美本性”说,“艺术——情感”说,“艺术——人学”说的重新审视与评判,还是对文学艺术的“依存性”和“独立性”、文艺与政治、文艺的外部和内部关系、文艺思维与科学思维、文艺与社会、文化、生命、语言和审美的关系的探讨,抑或文艺理论建构中所涉及的中外古今文艺思潮、方法论问题,其思维向度都能尽弃琐碎而入远大。力摒狭隘而见宏阔,远弃曲说而得大道,最终创造性地提出文艺理论建设的未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为基础,以艺术规律为本位,对中西文论传统以及某些自然科学成果全面融汇,创造整合而成“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新思潮,内之仍弗失(中国)固有之血脉”,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历史感又具创造性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些提法都是独具史家慧眼的前瞻,也是符合当前文艺理论具体实践的科学创见。
二、纵横交错、史论结合。
关于历史,贝克尔是这样表述的:历史总是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经验而变化。就史观而言,贝克尔的观点自然有相当的局限,却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对何谓历史的不同理解常常会导致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史方法:要么是精益求精地考据,校勘、注释、搜集、辨析史实以编年纪事,以陈述历史为重;要么是以流行的价值判断为旨归去整理历史,以解说历史为主。《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的治史方法与之不同。全书构架分为三块:《绪论》系总论,重点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以及文艺理论的民族化、现代化等问题;《当代文论史概观》,共三章,就“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新时期二十年三个历史阶段文艺理论的发展态势,作概要的描述;当代文论史专题共十二章,就贯穿当代文论史整个过程的十二个基本问题作多方位多层次的透视。这样,全书实则是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这一有机整体分解为历史整合、历史过程、历史现象三大板块,形成了以纵向追踪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基本脉络为经,以横向剖析重要文艺思潮、文艺现象、文艺理论概念、范畴为纬,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高屋建瓴的理论阐释为纲的体例构架。既在“博古而通今”中标举史实,真实、完整、系统地作出史的追踪整理,又在为“通今而博古”中构筑史观,准确、独特、科学地解读出文艺理论史的当代性。史与论可谓双臻齐美。
纵横交错,史论结合的论证方式,同样也鲜明地呈现在各个章节的具体叙述之中。譬如在纵向勾勒1977至1996年文艺理论的发展态势时,史著对围绕方法论、主体论展开的文艺论争就没有停留在编年意义上的史实考辨上。它旁搜远绍,沿叶寻根,将此中指涉的两大主题放在20世纪国际文化背景下去思考,以此求证出它们与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渊源关系。又如在对新民主义理论格局下的现代文学史观作专题探讨时,史著的着力点却放在考证《〈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蒋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的传承关系上,从而以史实的慎思明辩推导出新的结论:“无论是30年代起始的文艺政治化观念,还是50年代出现的文学史观的政治化现象,都并不是政治性的主动要求和行政高压所致,而是文学家和文学史家自动地、自发地进行理论建设和观念开创的结果。”这样,史著就将史料考证的精审博洽与学术眼光的洞幽烛微融为一体,其思维方法与论证框架丝毫不落跑马占地和划地为牢的研究窠臼,其史料的留存又完全迥异于“文抄公”般仅仅辑录他人材料与誉说他人观点,处处让人耳目一新。
三、比较研究、方法多样。
史著体例构架的另一层含义是:它不把当代文艺理论史作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体,而是试图将之置于广阔的背景下去考察其“合力”因素。在作者看来,当代文艺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而且也与我国传统的哲学、政治、社会、伦理、艺术、审美等种种思想观念有着无法分割的复杂联系,因此,它有着对内的纵的开放性。同时,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又是在诸多外国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的影响移植中成长壮大的,它浸淫着东西方文化的充足养分,必然兼具向外的横的开放性。基于此,史著虽然把当代文学理论的时段划分界定为1949至1996,但是,无论是在总论、概说还是史的专题研究中,其论述就不再是简单地从政治性的时限规定出发,而是从当代文艺理论对古代文论的继承革新,对东西方文论的借鉴引进的座标系去作史的勾勒,其拓展面覆盖了古今中外文化的众多层面。譬如,关于中国“左”的文艺思潮的起源,学术界早有“其深受苏联、日本左倾文艺思潮影响”的定论,但是史著却从中国左倾文艺思潮与苏联、日本左倾文艺思潮的差异性入手,以儒学文艺思维模式与经学思维模式的因袭来加以解释,令人豁然开朗。又如关于审美文化中“意义”的美学阐释与历史阐释,其它专著少有提及,本书给以较为浓厚的笔墨。这些研究视野的拓展一方面说明著述者对于古今中外文化发展、文艺思潮演变、文艺方法论更新态势的稔熟,一方面也说明了比较研究的宗旨已深潜研究者心底。在此基础上,著述者还博采各家各派文论有价值的成分,广泛吸收系统论、接受美学、信息论、社会民俗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论的合理内核,深入分析了当代文艺理论与其它学科的联系与互补,通联与碰撞,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人性和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表现理性”、“文化与文化传播”等,其命题就已经显示跨学科比较研究的应有之义。又如史著打破社会学批评局限,应用神话——原型的文化学研究方法去分析寻根文学思潮,充分显示了多学科多方法探讨的巨大潜力与优势。可以说,史著本身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合力论”的积极成果。综合分析比较的方法也真正使这部当代文艺理论史成为了主调鲜明而又色彩斑斓的立体雕塑,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理性启迪与感性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