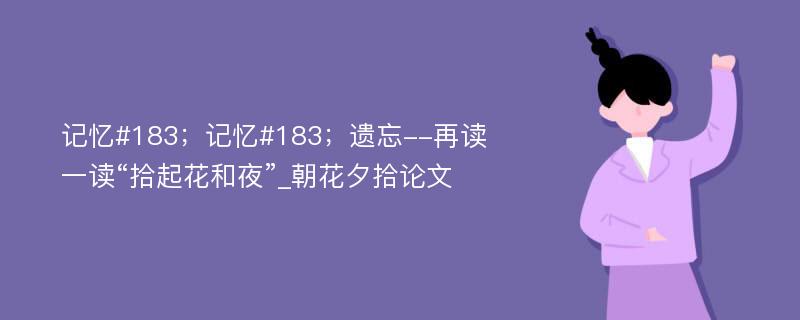
回忆#183;记忆#183;遗忘——再读《朝花夕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花夕拾论文,再读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4-0042-04
“刺激—回应”之间
“五四”落潮后鲁迅备受外界各种“纷扰”的刺激,直到1926年,这些刺激都远未成为“过眼烟云”,“华盖运”、“碰钉子”、“碰壁”是他对彼时境遇最经常的形容。从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提及他在创作这个文本过程中遭遇的时空和人事的曲折流转,也可想见他这一时期的嘈杂情绪,因此鲁迅说“带露折花”固然好,但在他是做不到的。那么,面对“刺激”鲁迅是如何“回应”的呢?
1924至1926年间鲁迅创作之丰富形成了其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多体裁、大密度、高质量的创作现象在鲁迅一生中是独一无二的。以这些创作观之,当诗人用语言文字去表达思想感情,在“刺激—回应”的两端审时度势时,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分裂”的:一方面他对现实的“纷扰”作出猛烈而愤慨的回击,骂军阀,骂文人学士,骂正人君子,无所顾忌,坚持“精神界战士”的刚毅形象,几乎跌至有意纠缠、意气用事的边缘(见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另一方面则对自己进行冷静而酷烈的“抉心自食”式的自剖,销骨铄金般的沉潜于自我生命“哲学”的提炼(见散文诗集《野草》)。在这犬牙嶙峋的矛盾两端,巨大的分裂地带横亘其间,但是在这分裂地带的上空,鲁迅那清醒的理性意识作着鹰隼般的盘旋,他在试图寻找机会消弭裂痕。他想提醒别人,也想说服自己:不管是那个坚持社会批判的“我”,还是这个“抉心自食”的“我”,都是同一个“我”。于是他开始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重构自我人格生成历史,这就产生了《朝花夕拾》。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人格并不只属于生物的个人,它产生于环境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是“自我”不断调节“本我”和“超我”的过程。正如鲁迅所说的“地火”在运行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释放喷发,《朝花夕拾》就是“地火”喷发后留下的“地囱”。《野草》以它的拒读性沉入鲁迅意识的潜层,而《朝花夕拾》则以易读性(鲁迅曾将此书当作了解中国社会的入门读物介绍给日本青年增田涉)浮出鲁迅意识的表层,但不能因此忽略《朝花夕拾》乃是化装后的“白日梦”的心理文本。从这一角度看,回忆性文本《朝花夕拾》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鲁迅矛盾心理机制调配下的产物,可以说,它是作为矛盾的对抗物出现的,同时又成了矛盾的反身象征物。“分裂地带”并非真空,“回忆”的置入使其成了尖锐矛盾的缓冲地带,诗人在其中得以安身立命。鲁迅曾坦言《朝花夕拾》的创作目的是“欲从纷扰中寻出宁静”,“因为不愿想到目前,于是记忆便在心中出土了”。可见,“记忆”是“目前”最有效的遮蔽物。于是,当我们重读《朝花夕拾》时,我们能很容易地感觉到“回忆”从第二篇《阿长与山海经》起便浮出了文本的表层并占据了中心地位。从创作心理上看,鲁迅在创作第二篇文章时就进入了写作的“高峰体验”,他受到了回忆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快感”能量的牵引、制导。正如玛德莱娜点心之于普鲁斯特一样,回忆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1]
回忆·记忆·遗忘
当我们将目光聚集于《朝花夕拾》文本的“回忆”时,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所指涉的“回忆”,还需要厘清几个概念。首先是记忆与回忆。在心理学概念范畴中,回忆和记忆原可通用,但它们所指涉的同一内涵却有两个层面:一指我们回忆过去的能力,代表一种大脑的功能,另一指本身被回忆的某种东西——一个更抽象的概念。记忆的这两方面似乎不同,但它们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从词源学上看,“记忆”更着重于“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回忆”更倾向于“忆”,是为了当前有关的事而回想到过去经验。在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是缪斯女神之母,她在传统中被刻画为一个身披绿色常青柏的年轻女性,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本书和一支笔。[2]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这两个概念之间形象的区别。在后来的文学领域中,诗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对记忆和回忆进行相应指称和定义。君特·格拉斯在自传式小说《剥洋葱》中对回忆和记忆的理解就是一例。他认为回忆总是趋向于美化往昔,抹去让人不快的事实,所以对从前的回忆并非事实的真实再现,而是经过回忆过滤筛选之后所忆事实的“一个版本”,回忆还常常会提供若干个相似、相差甚至相悖的“版本”。而记忆则与之相悖,它竭力再现过去事件和行为的细节,它总是表现得近乎迂腐的认真并较劲地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格拉斯选择“琥珀”这一意象来形容记忆,琥珀似的记忆封存的是事物的原样,不允许主观记忆的随意篡改或扭曲。由此《剥洋葱》中引进了一组对立的核心范畴——(喜美言的)回忆与(求事实的)记忆。[3]
如果把《朝花夕拾》中鲁迅的回忆看作是“喜美言”的回忆,而把鲁迅的亲友对他的回忆当作是“求事实”的记忆的话,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其中多有出入:例如《五猖会》中父亲临时叫儿子背书一节,据周作人的判断伯宜公是不会这么不通情理的,就是说存在杜撰的嫌疑;[4]再如《父亲的病》中结尾部分指使童年的“我”拼命叫唤临终的父亲的是衍太太,据周建人回忆应该是长妈妈,后来发现的鲁迅作于1918年的最早一组散文诗《自言自语》中的《我的父亲》说是“我的老乳母”,看来周建人一说更可信;[5]再如《藤野先生》中鲁迅说收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事实上并未见,藤野先生也对此事完全不记得了,因此日本许多研究者认为该文是一篇小说,日本小说家太宰治还专门据此写成小说《惜别》。更奇的是在《范爱农》一篇中,据周作人回忆实际上鲁迅和范爱农的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给清政府当局拍电报是没用的。但在文章中鲁迅却让自己站在了范爱农的对立面,主张发电报给政府当局。[6]如果从记忆的科学研究角度来说,《朝花夕拾》完全可以被举证为一个“记忆”症候式文本。对此鲁迅或许早有意识,他在《小引》中自辩道:这几篇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可能有错。如果说真是因为时隔已久出现记忆差错,当然情有可原。但在读者的眼中,上述一些“错误”却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此列。科学研究最终将记忆的缺陷归结为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而文学研究则倾向于将记忆的缺陷与人类心灵的创伤联系起来。准确的记忆要求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重新打开创伤,而这种方式无法靠人们自己来完成,因此他重述事件,构造人物,甚至不惜篡改因果联系,寻找借口托辞。我将这种有意歪曲理解为一种“遗忘”机制的作用。
“遗忘”原是心理学研究记忆的过程中涉及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可指记忆功能的障碍,也可指需要被记忆的某种东西的缺失。在此,我倾向于认同哲学家伽达默尔将“遗忘”上升为“人类的历史法则”加以把握的看法。[7]在1924年至1926年期间,鲁迅对遗忘的体验无疑已经上升到历史原则的认识水平上。“忘却”是鲁迅思想言说中的一个重要语汇,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对于历史遗忘的强大力量,早有清醒的意识:“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而个体生命“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与此同时,鲁迅对个体遗忘的体验却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活着就有必要“记住”,如《坟》中的“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摄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又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批判道:“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这些是鲁迅在国民性批判视野下的对中国人“健忘”心理的剖析;另一方面又认为活着却有必要“忘却”:“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对待“遗忘”的矛盾态度正体现了过渡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这种沉滞纠结的思维方式与鲁迅身上怀疑主义者气质相契合。“在寓言的触动下,个人从历史的无时间状态中苏醒;记忆在这种晦暗的时间中把自己揭示为一个遗忘的巨大空间。由此,个人随着历史的运动而出现,而寓言自身则成为一份遗忘的谱系。”[8]254从这个层面理解鲁迅所体验的“遗忘”,无疑为《朝花夕拾》中的“回忆”洞开了一扇全新的视窗。通过这一视窗,我们看到的文本建构过程便是一个“记忆”通过“遗忘”机制“过滤”留下“回忆”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就像一台天平,遗忘相当于一个制衡的砝码,在平衡与失衡之间实际上体现的是现代个体与传统集体之间的矛盾:当遗忘靠近回忆时,遗忘的“过滤”功能被充分激发,回忆的选择性和建构性被明显加强,为现代理性批判精神创造了宽裕的生长空间;当遗忘靠近记忆时,遗忘的“过滤”阀门松脱,记忆不加选择地流泻出来,理性精神的生长空间被压缩,现代个体就陷入传统影响的深度焦虑中。
“回忆”之为“镜像”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构筑了一座“回忆之屋”,试图栖身其中,寻找闲静。“然而委实不容易”,最终未能如愿。“回忆之屋”终成“空中楼阁”,正像“带露折花”变为“朝花夕拾”。在这里“回忆”实际上成了一种“镜像”。“镜像”是借用自著名心理学家拉康的提法,其核心范畴是指人的自我主体心理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主体分化的“镜像阶段”。[9]但本文具体指的是,当记忆中的无意识因素支配了回忆者的建构能力,回忆便丧失了它的治疗慰藉作用,回忆者贯彻始终的启蒙批判立场便被悬置,从而形成“镜像”。
日本文论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通过对“风景”的考察,反思在文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把“流”当成“源”的错位颠倒。尤其对于标榜理性,高扬个性的现代个体而言更存在这样的认识盲区。[10]1“五四”一代启蒙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疾呼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确立了彻底反封建反传统的理性批判立场。就在他们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横扫旧传统的同时,也扫除了与一切可借鉴资源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一个简单的“现代”概念时强加给自己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内在丰富性以桎梏。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许多已被认可的观念会被颠倒过来理解,从而使看似“不言自明”的地方反而成了重新思考的出发地。“五四”落潮期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断裂地带”,[11]处身其中的鲁迅体验到了深切的孤独和绝望,他天生的怀疑主义者气质和敏感具体的思维方式,使他通过反顾自身来对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反思:当他在《野草》中完成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后,他的目光落回到生命的来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于是便有了《朝花夕拾》。这个文本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天启:回忆只是借镜,目的在于察本清源。当他回到生命源头,他发现了历史和生命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因为此后的种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而被遮蔽、抛弃。如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通过否定自我而获得透彻的历史意识,[12]那么鲁迅的《朝花夕拾》则是通过肯定自我来洞见历史的本相。
当性灵漂泊成了诗人的基本生存体验,精神返乡便是他追寻的首要价值。那片笼罩灵光的故土绝不亚于朝圣者心中的圣地麦加。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他还强调唯有离开家乡历尽沧桑后重返故乡的诗人才能真正领悟故乡的意义。[13]不幸的是,中国的启蒙者从未在精神返乡中获得那种宗教般的救赎和慰藉,鲁迅的《故乡》便是很好的例子。少年闰土在一片美丽的故乡风景中出现后很快消失了,然后还原为萧条、严寒的现实图景。这意味着鲁迅从《新生》时代开始的“希望理论”破产了,故土成了梦魇之地。在鲁迅小说的影响下形成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中都无例外地出现一个从外部观察乡村的叙述者,他为乡土上裸露的种种非人的残酷、愚昧和麻木,感到震惊不已,痛心疾首,“这位自我流放中的儿子再也认不出童年记忆中的自己……这种习俗强调的是乡村和城市、童年和成年之间的中断。”[14]77但是鲁迅对于故乡的情感是复杂的。如《野草》中《好的故事》那段关于山阴道上的美丽风景的描绘,是诗人对故土的热爱的流露。到了晚年,鲁迅曾抒发怀乡之情:“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15]此中坎坷心曲令人心酸,而对故土深切情意堪与屈子媲美。而这种认同感和亲和力,绝不同于海德格尔那形而上式的现代性审美体验。1914年,鲁迅收集自己故乡绍兴府会稽的先人著作逸文八部,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在其序中写的“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或“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等等,这里的描写与鲁迅对其所喜爱的诗人裴多菲的故乡普斯多的描写可引为同调。可见,鲁迅对乡土持的是一种地缘与血缘相勾连的态度,即源于乡土对伟大人物孕育方面的肯定。乡土历史通过祖母、保姆等古老记忆的保存者的反复诉说得以流传下去,乡土社会被认为是共时社会,鲁迅的乡土记忆无法避免共时社会中惰性的历史力量,因此,他的乡土言说必然超出“愚昧—启蒙”的话语维度。
对于天真良善的儿童时代的回归也是处于疲倦漂泊状态的现代成人的美好理想。在儿童的世界里快乐原则占据首要地位,他受本能驱使,直接追求着生命欲望不受压抑的完全满足。但儿童这种无拘束的天然快乐不得不在文明进程中接受现实原则的限制。[16]12建构一个以儿童趣味为导向的审美世界,一方面唤回了对往日幸福体验的依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忆者追随儿童的审美趣味,将“快乐原则”奉为至上,字里行间流露出自然童真的无忧无虑,全然超越了书塾生活枯燥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一种现在正在受到禁忌的批评标准,如《五猖会》、《父亲的死》、《范爱农》等篇章中对至亲友朋痛苦的压抑性回忆。这就使我们有了这种联想:回忆再现的情境是回忆者处身的现实的投射。这种颠倒过来发现问题的思路所具有的力量最终将冲破产生和限制它们的那个现存框架。鲁迅很早就注意到“儿童”,他在早期的论文《破恶声论》中提出推崇“白心”思想,认为它是看破社会矛盾与虚伪的力量,它更多的与《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思想相联系,这是一种从根底上发出的、具有扫除一切思想蒙蔽的反叛力量。[17]
现代文化一道最坚固的意识形态防线:即自主个体观。1935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五四”文学的成就进行检视时提出一个著名观点:“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借此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得以确立。但在鲁迅回顾视镜中个体从未获得完满的发展,是有缺陷的个体,如年少失父,青年离家,异国受辱,回国遭弃等,而个体要直面自身的缺陷,治愈创痛,就要学会如何直面自己的过去和传统。现代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学本身便是集体心理学,我们是历史的存在,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一定的“成见”之中。[16]13鲁迅说他从旧垒来,情形看得更分明,反戈一击,一定更能击中要害。这可以成为正命题,说明鲁迅有着强大的反封建的战斗力;这也可以成为反命题,说明鲁迅始终无法逃脱旧传统的影响。社会学家希尔斯发现传统中所内含的“卡里斯玛”特质使其有了自己的造血功能。[18]有学者指出,鲁迅的反传统实际上是接受了传统中的反传统养分。鲁迅以自己独特深刻的体验方式也间接达到了这种认识程度:接受传统中的反传统与发现“卡里斯玛”特质异曲同工。这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鲁迅与传统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问题,但传统在鲁迅那里仍是避不开的话题。
严家炎先生很早就指出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最早可追溯到鲁迅那里,鲁迅的早期论著中就有对“物欲”遮蔽“性灵”的阐述。而在1926这种思考无疑是更进一步了。在本雅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那种“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中的时间,是一种被同化了的“同质的、空无的时间”。[8]254他用另一种时间感来同这种时间相对抗,那便是回忆的时间。鲁迅在这一时期体验到了历史时间的停滞,即“历史循环感”,他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回忆的时间。回忆作为一种审美能力,这种能力的发现始于卢梭的《忏悔录》,浪漫主义艺术把异化的外部世界加以内在化,使之变为风景,人们开始发现回忆的审美能力。[19]卢梭之后,乡土田园、天真儿童、自主个体成了现代文学经常流连忘返的“名胜”。[10]32在《朝花夕拾》中这些风景是以换喻的方式被引入启蒙语境里,它们与启蒙话语处于一种接近或相继的连接轴上。这正如我们构造一个句子时,必须把主语和谓语联系在一起,必须将代名词、名词、副词、连接词等放在句子中正确的语法位置上,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系列,这种组合的过程表现在“邻近性”,它的方式是换喻。这种连接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效果,正如有一个观点所表达的那样:“信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聪明并没有防止现代世界满怀深切的遗憾去回忆更不文明的年代。……现时代越是坚持强调其自己的智慧、经验和成熟,回顾起那些简朴而单纯的时期似乎就越发吸引人。进步暗示着怀旧成了它的镜像。”[14]77
收稿日期:2011-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