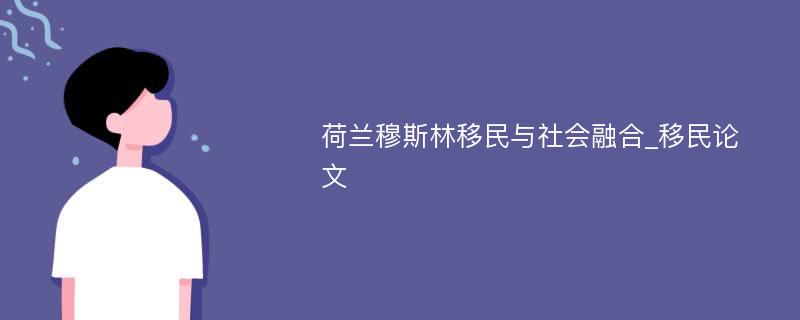
荷兰穆斯林移民与社会融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荷兰论文,移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穆斯林移民不断涌入、穆斯林人口持续飙升,西欧由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元并存的异质性社会。“穆斯林问题”亦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和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西欧各国在处理穆斯林事务上各有差异,但在政策上采取同化策略已成为广泛共识和普遍趋势。①值得关注的是,以崇尚宽容精神、讲究自由放任而著称于世、一度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荷兰,近年也表现出明显的移民范式转换。也就是说,摈弃包容并蓄、善待差异的多元文化政策,转而实施严苛限制的同化政策。本文拟探究荷兰穆斯林移民问题产生与流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反思穆斯林融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 穆斯林移民的存在与边缘化
穆斯林在荷兰的足迹可追溯至1879年,源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穆斯林定居海牙,直到二战爆发,其穆斯林人口不过几百人。其大幅增长肇始于战后不断涌入的移民浪潮。当时,穆斯林移民可分为“后殖民移民”(post-colonial immigration)、客工(guest worker)、家庭团聚(family reunification)、强迫移民(forced immigrant)四大类。“后殖民移民”始于1949年印尼及1975年苏里南独立,一批与殖民母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穆斯林移居殖民宗主国。客工移民起因于战后荷兰经济繁荣需要从事繁重工作的廉价劳工。1963年、1969年荷兰政府分别与土耳其、摩洛哥签署劳工招募协议。受石油危机、经济衰退影响,1974年荷兰终止客工计划并鼓励客工返回原籍,此举成效不彰反而刺激移民的滞留。随后实施的“家庭团聚”更使客工家眷蜂拥而至。“家庭团聚”政策标志着穆斯林与西欧国家关系性质的重要变化,客工由单身男性为主、暂时性的外来劳工骤变为以家庭为单元、永久性的移民;移民通过家庭的存在与社会发生广泛的接触与联系,不仅体现在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方面,还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磨合与调适。②80年代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催生大批难民、政治避难者等“强迫移民”及非法移民的纷至沓来。在上述移民中,客工及家庭移民占据主体,其余两类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少。
移民运动一旦开始,就不可避免成为一股自行持续、路径依赖的社会潮流。③在四股移民浪潮的推动下,荷兰穆斯林人口大幅飙升、急速膨胀,由1971年约5.4万人陡升至1975年10.8万人、1980年达到22.5万人、1997年为57.32万人。据2006年荷兰国家统计局(CBS)数据显示,穆斯林人口已达85万,占总人口的5%,其中土耳其裔32.5万、占穆斯林总人口的38%,摩洛哥裔26万、占穆斯林总人口的31%。④2011年皮尤中心估算,荷兰的穆斯林人口已达到91.4万,占总人口的5.5%。鉴于穆斯林较高的出生率和不断涌入的移民,预计到2030年,穆斯林人口将增至136万,占总人口的7.8%。⑤尽管这些穆斯林移民已永久定居荷兰,构成荷兰社会的一部分,但迄今为止仍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究其原因,首先是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低下。第一代土裔、摩裔客工主要来自传统乡村,其教育、技能、语言等先天不足,大多从事肮脏、危险和不体面的工作,易受经济波动影响。因此,穆斯林失业率要比本地人高出2-3倍。2006年,本地人失业率为9%,而土、摩裔分别高达21%、27%。穆斯林妇女劳动参与率低,高度依赖社会福利。在社会福利依赖者中,移民占47%(1998年数据),其中主要为穆斯林。穆斯林移民后代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多数仍未摆脱贫穷的命运。土、摩裔高中生辍学率分别高达35%、39%,监狱犯人中,移民占32%。比例偏高的失业率、社会福利依赖率、辍学率、犯罪率等社会问题严重妨碍穆斯林的社会融入;⑥其次,集中居住与社会隔离。穆斯林移民的先期抵达者往往扮演桥头堡的角色,继而亲朋好友鱼贯而至,构成以亲缘、地缘为特征的“链条移民”(chain migration),形成了互助团结的人脉网络;移民习惯定居在大城市的少数族裔聚居区,集中居住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四个大都市,其中阿姆斯特丹半数人口为穆斯林,是全欧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语言或能力的不足,一些穆斯林习惯于自我隔离与边缘化,既没有和本地人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也没有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生活的隔都化(ghettoization)阻碍了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和交流;再次,穆斯林社群的碎片化。穆斯林远非一个同质性整体,它因循族群、语言、教派或政治倾向的断层线而四分五裂。在高度组织化的西欧社会,穆斯林的碎片化阻碍了穆斯林创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群组织,也妨碍了穆斯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对话,或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更遑论协同合作、选举政治代表、影响公共政策;⑦最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比库·派瑞克把穆斯林移民喻为“原型陌生者”(archetypal stranger),意指穆斯林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与西欧主流社会存在巨大落差。⑧本土民众对穆斯林父权家庭、性别歧视、买卖婚姻、内婚制、割礼、头巾面纱等传统习俗难以认同并严词抨击;保守的穆斯林对荷兰社会的妇女解放、同性恋、性开放等现代风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价值观冲突和文化障碍使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形成一条泾渭分明、清晰可见的心理和情感边界,这无益于双方正常的接触交往与互谅互让。⑨
需要指出的是,穆斯林移民在某些方面日渐进步: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掌握了荷兰语;更多的穆斯林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第二代穆斯林进入中高阶层和学术领域的比例和人数正在增加;穆斯林妇女生育年龄正缓慢延迟。⑩然而,穆斯林面临的最大挑战却是荷兰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排斥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穆斯林作为“他者”、“外来者”、“异邦人”(allochtons)的刻板印象,“黝黑皮肤、喧嚣粗俗、劳工下层、图谋不轨”的负面标签已然根深蒂固、难以消弭,即使土生土长的第二、三代穆斯林亦备受歧视和排挤。2006年欧盟“种族主义与排外监控中心”研究报告表明,从住房、就业机会、教育到文化习俗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穆斯林皆受到严重歧视。(11)阿亚汉·卡亚认为,伊斯兰平行社会在西欧内部的凸显,不是穆斯林保守落后的产物,而是对结构性排斥机制的反抗。(12)困难重重的社会流动、无法逾越的族群鸿沟、难以克服的社会歧视等问题进一步激发与强化了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身份认同。许多穆斯林在《古兰经》寻觅慰藉,在清真寺找到归属,重新皈依为“再生穆斯林”(born-again Muslim),并想象建构出一个全球化的、去疆域化的、超越族群和文化藩篱的“新乌玛”(neo-Ummah,伊斯兰社群)。新生代穆斯林更擅长利用伊斯兰话语和身份认同,使之成为争取认同和群体权利、激励政治动员的载体与动能。(13)据荷兰社会研究所(SCP)的调查,第二代穆斯林在宗教上变得日益虔诚,1998-2011年间参加清真寺礼拜的人数,摩裔从9%增至33%,土裔从23%升至35%,而经常参加礼拜的第二代穆斯林对“过去母国”的认同超过荷兰的国家认同;这些人更可能囿于其族群的小圈子,在对待妇女和同性恋等问题上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14)不言而喻,穆斯林“平行社会”的存在和伊斯兰认同彰显对荷兰国家认同、价值观及社会凝聚构成了严重挑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荷兰社会融入政策的失败。
二 从多元文化政策到同化政策
斯蒂芬·卡斯特斯和马克·米勒指出,一个完整的国际移民过程不仅包括移民迁徙的原因、过程和模式,而且亦涵盖移民以何种方式融入接受国(host country)及其社会。关键问题是如何使移民及其后裔成为接受国和社会的一部分,国家和公民社会如何能够加速这个融入进程。(15)按照欧盟2004年《移民融入政策的共同基本原则》定义,所谓“融入”(integration)亦译为“整合”或“融合”,系指所有移民与接受国民众之间动态的、相互调适的双向过程。(16)不同国家在对待移民和少数族群事务上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既深受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历影响,也取决于具体时空脉络下的国家吸纳策略。吸纳(incorporation)一般建立在特定的观念之上,具体而言,国家把移民作为个体加以融合,不考虑其文化差异或群体归属,如法国共和同化模式;抑或将其视为社群,维持其特有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如英国多元文化模式。在对待穆斯林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上,荷兰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由放任(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多元文化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以及同化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17)
如前所述,荷兰招募客工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暂时性:穆斯林外来劳工数量有限、定期轮换,不会长久滞留;作为前殖民地的子民,许多穆斯林残存自卑感,深知自己身份地位低下,明了“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的道理;客工基本由单身男性构成,他们只身闯荡异国他乡,意在积攒钱财、荣归故里。鉴于此,荷兰也就顺理成章地把穆斯林客工视为匆匆过客,他们与其母国的关系和身份认同理应维护。用西方政治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亦即政府以无力或不该介入为由,对少数族群的存在装聋作哑,采取规避策略。在实际执行中,对于穆斯林的基本宗教信仰和功修,荷兰政府以“外包”(outsourcing)的方式来处理,即允许土耳其、摩洛哥等官方机构或跨国非政府组织,介入荷兰穆斯林事务,由外部为穆斯林提供宗教服务、清真寺建造、语言文化学习等事宜。国外行为体介入穆斯林事务,一则控制离散者,政治上为己所用;二则谋求汇款、投资等经济益处。由此,所谓“大使馆伊斯兰”(embassy Islam)或非政府组织的伊斯兰跨国主义(Islamic transnationalism)应运而生。这些跨国网络和认同进一步确认和强化了移民与母国的脐带关系,导致“跨国意识”(transnational consciousness)或“分裂忠诚”(divided loyalties),自然成为穆斯林与接受国的接触互动与融入进程的障碍。(18)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行为体正从权力、取向、认同和网络等各方面穿透和侵蚀主权国家的治权。(19)然则,“在文化上直到上世纪70年末、在政治上直至80年代末,穆斯林都是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因此“穆斯林问题”在西欧各国并未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政治社会议题。(20)
到70年代末,荷兰政府察觉穆斯林“返回故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因此有必要检视愈演愈烈的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1979年,荷兰智库——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WRR)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报告》,建言政府采取协调行动、吸纳移民。1980年,政府公开承认客工永久定居的事实,并采纳了《少数族裔报告》的观点。诚如汉恩·恩泽格尔所言:“直至80年代初,荷兰政府才制定了较为连贯一致的政策,希冀促进移民融合。”1983年,政府正式出台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主义色彩的“少数族裔政策”(Ethnic Minorities Policy)。该政策指出,移民已使荷兰成为一个多族群社会,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应相互尊重、和睦共处、机会平等,公共权威有责任为此创造必要条件;承认少数族裔的文化差异和宗教差异的权利,主张“保留认同之融合”;强调“宣传多元文化之事例、训练文化认同之自觉”,支持少数族裔组建各式各样的社群组织。该政策主要有以下特点:移民按其群体成员而非个人加以对待,这与多数欧洲国家显著不同;承认文化差异,赋予特殊文化权利,反对文化歧视;多元文化主义制度化,保护少数族裔认同;文化解放(cultural emancipation)是改善社会经济、融入主流社会的关键。(21)
在法律政治领域,荷兰强化了反歧视立法;1985年赋予非公民的移民地方选举的投票权;移民归化入籍更为宽松;与移民的协商机构陆续建立,移民得到更多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引入针对少数族裔的劳动市场规划、特殊培训课程和教育计划,帮助移民签署自愿协议、寻求就业途径。在文化、语言和宗教领域,政府慷慨动用公共资金,资助建立各式各样的族群基础设施,诸如创建传授移民“母语”的穆斯林学校,开设具有文化特色的专门课程,支持组建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于是,大量的清真寺、文化中心、伊斯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1970年,荷兰全国仅有8座清真寺,到2009年拥有500多座清真寺、40多所伊斯兰学校、一家穆斯林广播电台,以及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同业公会。(22)与法国同化模式、德国排斥政策相比,荷兰为穆斯林移民提供了较为宽容友善的空间,允许其在公共领域里表达自身特殊认同;认为移民存在不是累赘,反能丰富本国的文化多样性,能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实现解放。(23)这个被誉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荷兰模式”(Dutch model),被广泛视为处理不同文化、宗教、族裔之间各美其美(respect)、美人之美(tolerance)、美美与共(cooperation)的典范。但也有学者贬之为“放纵的多元文化主义”(permissive multiculturalism)或“多元文化主义的极端版本”。
荷兰之所以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政策),除了众所周知的多元宽容的历史渊源外,与其特有的“柱化”(pillarization,verzuiling)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传统上,荷兰社会结构由新教、天主教、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四大社群所构成。(24)每个社群皆有权组成一套自成一体、平行存在的制度体系,形成一套各行其是、独立自主的学校、医院、媒体、政党等自治设施。政府透过社群代表间的折冲樽俎、协商共识,维持公共政策正常运转。不过,当穆斯林移民潮到来之际,整个社会的世俗化、个人化及社会流动已使柱化结构日渐崩塌,但宪政原则仍遗留传统,故而相沿成习鼓励穆斯林建立一套自身的宗教、教育和文化社群体系,冀望形成一个新的“伊斯兰支柱”(Islamic pillar),此设想也与穆斯林希望保留宗教传统、生活方式的愿望不谋而合。此外,许多荷兰人对于二战中境内犹太人惨遭空前的杀戮深怀负罪感,亦对先前残暴的殖民统治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加之当时“普世人权”话语的广泛传播,国际和国内法律机构将先前仅赋予本国公民的权利扩展至领土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即由公民权(citizenship)向居民权(denizenship)让渡,对其有无公民权身份几乎忽略不计。(25)“在此背景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就等同于缺乏人道关怀,抵制针对弱势少数族裔的偏见既是履行道德义务也是至高荣耀的象征”(26)。正因如此,为迎合多元文化的浪漫憧憬,为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荷兰各界对多元文化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置若罔闻。
1989年的拉什迪事件是西欧国家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自此西欧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从开放转为排斥、从正面到负面急遽改变。荷兰智库——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WRR)对少数族裔政策提出质疑,批评其过于关注“文化道德”领域,要求关注社会经济领域、激励移民独立自主、减少其对国家的过分依赖。1991年,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党魁弗里兹·博尔克斯泰因(Frits Bolkestein)声称,“伊斯兰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不相容”,抨击现行政策与本土价值观背道而驰,呼吁当局向移民施压,迫使后者接纳社会价值规范。上述质疑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遭到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和围剿,另一方面却在民众之中产生广泛共鸣,许多人早就厌倦多元主义的陈词滥调,出于多重顾虑不便公然反对。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移民融入政策开始转向,倡导“好公民”和“公民融入”成为关键性的政策概念。鉴于多数新移民对荷兰语言及文化缺乏了解,无法有效进入就业市场,政府认为需要对新移民实施“强制性的公民融入课程”。1997年,荷兰议会批准了《新移民公民融入法案》(Law on Civic Integration for Newcomers),翌年9月正式生效。该法案规定:来自非欧盟的新移民必须参加强制性的600小时“公民融入”课程,其中500小时为荷兰语学习、100小时为公民教育和劳动市场准备培训,所有费用均由政府支付,上述措施旨在督促新移民尽快熟悉荷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据统计,1999年有超过1.9万名新移民参与公民融入课程。(27)荷兰移民融入举措很快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并纷纷效法实施。以上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期,荷兰开始从多元文化政策领域撤离,到2000年完全弃之一旁,转而实施公民融入政策。
归纳起来,荷兰各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和批判,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族群认同和群体差异以及赋予特殊文化权利过度强调,助长内部穆斯林“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y)、“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和“隔离主义”(segregationism)的滋生蔓延。(28)对文化多元性和族群特殊性的过度彰显非但无助于实现社会整合,反而加深了社会分裂。伊恩·布鲁玛指出,问题根源在于二战后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天真的包容与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毫无原则和立场的姑息、屈从、放任自流,致使内部价值紊乱、融入失败,终究酿成“多元文化主义的悲剧”;(29)第二,多元文化政策并未缓解穆斯林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反而养成其对社会福利制度的过分依赖,滋生其“不负责任”的心态和习气,进一步加深其社会经济的边缘化。与毗邻的德、英等国相比,荷兰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给予移民慷慨的社会福利权益,却产生南辕北辙的消极负面效果。正如维基解密(WikiLeaks)所透露的,美国驻荷兰大使馆称:“荷兰穆斯林是全欧洲最缺乏整合、最疏离的社群之一”;(30)第三,穆斯林抵抗世俗主义和现代性,不愿主动接纳和适应荷兰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反而一味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当清真食物要求满足后,他们又要求工作场所的祷告;当后者被满足,又要求禁止宗教亵渎书籍;当那一要求满足或平息后,又要求承认多重婚姻;之后,他们要求实施无息贷款,建立伊斯兰银行、金融和保险公司,其最终目的就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生活于此”(31)。这一连串的特殊要求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招致主流社会的怀疑和抨击,甚至那些多元文化主义者也感到穆斯林的要求难以招架、欲壑难填;第四,穆斯林问题造成本国社会的分裂和极化。荷兰穆斯林融入失败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生,更刺激国内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反移民、反穆斯林为政治诉求的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皮姆·佛图恩党(Lijst Pim Fortuyn,LPF)和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PVV)不断抨击多元主义政策,强烈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移民和穆斯林的肆意蔓延,结果造成了移民和少数族裔事务的高度政治化。(32)至此,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宣告失败,应结束“多元文化主义的闹剧”(multicultural drama),改弦易辙、另起炉灶。(32)
三“9·11”事件后的社会融入举措
荷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转向同化政策,但“9·11”事件后,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论在荷兰社会迅速蔓延。2003年1月,时任欧盟官员、前自由民主人民党领袖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的“鹿特丹演讲”,被视为荷兰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死亡判决书”,预示着政府将采取强硬措施应对“穆斯林问题”。博尔克斯泰因指出,荷兰必须彻底摒弃“价值相对论”,明确支持“共同规范”,此前允许两套标准并存的情形不复存在;现存法律制度完备无缺、无须更改,荷兰政府和社会“全无过失,皆是移民自身的问题;穆斯林必须自我调整,“若移民想成为荷兰人,就会是荷兰人”;不仅荷兰将采取同化政策,整个欧盟国家亦然如此。(34)
2004年马德里“3·11”爆炸案、提奥·梵高谋杀事件、2005年伦敦“7·7”爆炸案等恐怖事件,使整个欧洲的反穆斯林、反移民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和排外情绪大行其道、无以复加。在许多欧洲民众眼中,穆斯林不仅是文化和价值观的隐患,更是政治和安全的威胁。阿雅·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等极右翼人士竭力诋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肆意煽动狭隘排外的民粹情绪。他们一方面打着捍卫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理性”的旗号,另一方面却歇斯底里地喧嚷严控和打压穆斯林。威尔德斯叫嚣严禁穆斯林移民,驱逐非法移民,控制穆斯林人口膨胀,禁止发行《古兰经》,严禁穆斯林妇女穿戴布卡(burka)、希贾布(hijab),强制实行“头巾税”(head rag tax),彻底遏制荷兰社会的“伊斯兰化”。(35)极右翼人士把穆斯林“污名”为包藏祸心、伺机颠覆的“第五纵队”,执意摧毁西方文化和自由民主制度。这些攻击和丑化穆斯林的语言暴力和言辞渲染,颇为迎合保守人士、中产阶级及基督教信徒的恐惧心理,颇具民意支持和社会基础,也造成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社群之间关系的空前紧张,加剧整个社会思潮的集体右转。据2005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荷兰民众对穆斯林抱持最负面的评价。(36)凭借民粹主义的煽动与穆斯林问题的情绪化和操控国内政治议程,极右翼政党在相当程度上绑架了对穆斯林问题的理性探讨,使之高度政治化,继而捞取政治资本、从中渔利。2010年全国选举中,威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PVV)一举赢得15.5%选票,跃居国内第三大政党。极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反映出荷兰社会对穆斯林人口不断增长的担忧,对暴力恐怖主义所带来威胁的恐惧,对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日渐削弱的焦虑。这时,彻底摒弃多元文化主义、实施严苛强硬的同化政策已成为跨党派、跨阶层的基本共识,一系列限制移民和强化整合的措施纷纷出台。
第一,增强民族国家认同,致力于公民参与和自助。荷兰政府宣布放弃“多元社会”观念,“荷兰社会虽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不断变迁,但它依然保持自身固有特点,这是无法替代的”,执行融入政策须优先考虑荷兰主流社会及其价值观。司法大臣帕亚特·唐纳(Piet Hein Donner)在2012年提交议会的“新融入议案”中称,“公众对于多元文化社会模式的不满情绪,政府感同身受并着手调整,以‘荷兰价值观’(Dutch values)为优先考量。荷兰社会价值观在新融入体系下尤为重要,政府已摒弃多元文化社会模式”;“一个强迫性的融入措施实属必要,否则社会将土崩瓦解,每人亦最终无法感受家庭般的温暖,融入政策并非针对特定群体量身定做,而是对每个群体一视同仁”。为了应对失业、缀学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移民必须肩负起公民融入的责任,生活在荷兰的每个人均应致力于积极的公民权、参与和自助。政府不再依循群体的属性和渊源来制定融入政策,政策规则适用于所有人。(37)公民融入更强调个人的自主自助精神,移民有责任自觉融入接受国社会,政府不再为其承担高额的融入成本,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就业和住房等政策已提供充分的融入机会,要求移民自己支付公民融入所有的费用。
第二,强化移民控制,实施准入管理。荷兰政府一改过去未加限制的移民政策,陆续出台一连串移民收紧政策。2000年,荷兰颁布《外国人入境法案》,有效减少政治庇护者的准入,从2002年的1.8388万人剧减为2003年的8262人,随后大约每年3000人。2000年12月通过《国籍法》(2003年4月生效),要求对归化申请者进行考试,考核其语言能力和国家知识;政府拒绝透露考试的任何内容,不提供任何准备资料,因为“任何人不可能学习成为荷兰人,他必须感觉是荷兰人”。归化考试的实施使得归化申请者大幅下降,由2003年3.7万人减至2004年1.93万人,仅有不到半数的申请人通过考试。2011年,荷兰宣布移民必须在三年内通过融入考试,否则取消其居留权。
2005年,荷兰首创“国外融入”(integration-from-abroad)这一强制性的新政策,以期强化对外来移民的控制,尤其针对以土裔、摩裔穆斯林为主的家庭组成移民(family-forming migration,国外配偶)和家庭团聚移民,而欧美或高技术移民不在限制之列。(38)2005年的《公民融入国外法案》(Civic Integration Abroad Act,2006年3月生效)规定,外来移民须具备荷兰语和荷兰社会的基本知识,才有资格申请暂时居留许可(MVV),也就是说,须先通过“公民融入国外考试”方有资格入境。申请人须参加荷大使馆举办的荷兰语测试(TFN)和荷兰社会知识测试(KNS),观看隐含社会道德取向的荷兰影片,使申请人尽早了解“荷兰价值观”。(39)倘若考试失败,他或她将无法进入荷兰;申请者可无限制申请考试,但须支付每次350欧元的考试费用;政府不提供任何有关考试的辅导材料。借助花样不断翻新的公民融入设计,荷兰公民权的内在逻辑已彻底改变,名义上的移民融入政策已然成为移民控制的工具。(40)
第三,采取严格安全措施,遏制暴力极端主义。在严格限制移民的同时,荷兰强化了安全与反恐法律,回应恐怖极端主义的挑战。随着穆斯林问题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欧洲各国政府日渐把伊斯兰视为“生存威胁”,危及本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规范,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加以遏制。据此,“法律赋予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更严厉手段处置穆斯林公民或移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41)。“9·11”事件后,荷兰通过了一系列的反恐立法或修正案,并设立了全国反恐协调员(NCTb)这一官职。2004年11月梵高谋杀事件后,政府迅速提议剥夺拥有双重国籍极端分子的荷兰国籍,关闭原教旨主义清真寺,驱逐极端伊斯兰教士。2005年,移民局驱逐了宣扬极端思想的四位伊玛目(imam)。(42)据2004年荷兰情报机构(AIVD)估计,社会融入政策的失败造成穆斯林移民严重的疏离感,这为极端主义思潮的蔓延提供了沃土。2008年内政部研究报告估计,荷兰国内有2500-3000名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反抗西方的生活方式、颠覆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地位,而荷兰尚未做好抗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准备。(43)
第四,强化国家对伊斯兰事务控制,培育本土化的伊斯兰机制。荷兰政府试图重夺(reclaim)、驯化(domesticate)和规制(regulate)伊斯兰教,建立一个具有本土色彩的伊斯兰教,将其纳入国家监督与控制之下。2004年,荷兰成立全国性的伊斯兰委员会(Contactorgaan Moslims en Overheid,CMO),旨在扶持一个充当穆斯林社群与政府的“桥梁”的对话者,意在减少跨国网络及外部宗教势力对本国穆斯林事务的渗透、干预和影响,培育熟悉本国文化传统的土生土长的伊斯兰宗教人士,发展荷兰式的“温和中立”的伊斯兰力量,缓解穆斯林社群与主流社会的敌对情绪。政府与伊玛目签订“合作协议”,鼓励伊斯兰宗教领袖与执法机构合作,甄别辖区内的极端分子,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义,共同防范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种自我监督机制已成为协助政府部门、加强监控计划的有益补充。(44)时任移民部长的丽塔·维尔东克(Rita Verdonk)提议,要求所有伊玛目必须完成荷兰语训练、本国法律制度、人文风俗等文化涵化课程。借此,2005年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专门开设培养伊斯兰牧师资格(Islamic Chaplaincy)的课程。乔纳森·劳伦斯指出:“在过去20年间,欧洲组织化的伊斯兰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从过去无规制、无法辨别、资金不足,逐步走向国家监控、接受与此相连的收益与约束的伊斯兰。”(45)
上述举措无不表明,在不断高涨的反伊斯兰、反穆斯林情绪鼓噪下,穆斯林问题业已高度政治化与安全化,荷兰社会陷入集体焦虑和道德恐慌之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抑制“伊斯兰威胁”。如今,荷兰已彻底抛弃多元文化主义转而实施“管理式多元性”(managed diversity)的同化政策。据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的分析,荷兰的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分值从1980年的2.5分、2000年的5.5分下降到2010年的2分,这一态势表明荷兰已从多元文化主义大幅撤退。(46)随着荷兰融入哲学和政策的剧烈转变,其政策举措与法国倡导的公民同化主义(civic assimilationism)、德国主张的“管理式融入”(managed integration),无论内涵抑或风格可谓大同小异、如出一辙。(47)简言之,面临融入危机的西欧各国整合政策,更趋于去民族化和政策趋同,即以非自由手段追求自由的目标,日益带有“抑制的自由主义”(repressive liberalism)特征。(48)
四 荷兰穆斯林融入的反思与展望
事实上,包括荷兰在内的西欧“穆斯林问题”之产生是当代全球移民运动的产物。作为全球化重要构成要素之一的移民,在20世纪后期的主要特点就是由南向北的人口迁移。历史上,西欧一直是向外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但二战后却戏剧性地成为外来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在短暂的时间跨度里,西欧从拥有微乎其微的穆斯林发展到穆斯林人口显著增长。对于穆斯林移民持续涌入及其多重意涵,西欧各国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政策上皆估计不足、缺乏准备。穆斯林移民涌入改变了人口结构,加剧了社会异质性,引发不同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碰撞,诱发社会排外情绪与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导致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和穆斯林问题的政治化。总之,穆斯林问题对西欧各国的主权、国家认同、政治文化、公民权、福利制度等形成重大冲击。(49)荷兰一改过去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浪漫情调与天真遐想,取而代之于对穆斯林的集体焦虑和恐惧感。社会舆论认为,穆斯林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发展,反而诋毁国家认同、削弱社会凝聚力、加重社会福利负担、制造安全威胁。因此,如何整合穆斯林已成为荷兰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
其实,穆斯林问题既非哈贝马斯等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所宣扬的“后民族主义”之书斋呓语,也非亨廷顿等东方主义者所鼓噪的“文明冲突论”式的危言耸听。绝大多数西欧穆斯林移民追求美好生活、期盼安身立命、分享繁荣成果;多数穆斯林持有世俗观念、支持自由民主价值观,远非如主观臆想、等齐划一的原教旨主义者或圣战分子,同时也需要对宗教保守主义者与“圣战主义者”进行区别对待。(50)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穆斯林整合进程与其他移民曾历经的融入过程大同小异,或者成为穆斯林这个事实使之构成了某种特殊态势?何塞·卡萨诺瓦指出,十九世纪美国天主教徒也曾被视为“无法接纳”民主规范的“另类”,但此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天主教徒悄然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类似的犹太人、黑人问题的缓解也是如此。理论上,并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非历史的本质属性,使某一社会群体全然无法变迁、与时俱进。今天的欧洲穆斯林与当时的天主教徒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只要西欧国家应对得当,穆斯林移民完全可能实现融入目标。(51)
如前所述,整合融入是一个相互尊重、共同努力、彼此调适的双向过程。穆斯林移民应努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融入荷兰社会,为国家福祉和发展做出贡献;效忠国家基本制度,恪守自由民主理念,增强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证明“穆斯林是值得信赖的公民”;弥合传统价值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落差,摒弃阻碍现代生活方式的陈规陋俗。毕竟,任何社会要有规范共识,倘若社会成员间无法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社会难以为继。欧洲伊斯兰思想家塔里格·拉玛丹指出,对于那些出生在西方或是西方国家公民的穆斯林而言,“已不再是‘定居’或‘整合’的问题,而是‘参与’和‘贡献’”的后整合(post-integration)话语时代。(52)乔纳森·劳伦斯亦认为,必须借助赋权行动,透过不断扩大的参与和草根民主,鼓励穆斯林参与基层决策和管理,建立沟通与回馈机制;唯有成为肩负起融入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穆斯林才能成功地加入西方社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53)与此同时,荷兰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责无旁贷地帮助穆斯林摆脱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弱势族群提供合理的社会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并深入理解和学习其他族群文化与价值的优点。正如欧盟融入原则所主张的:“接受国必须为移民创造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参与的机会。”(54)不管本地人喜欢与否,穆斯林已是荷兰社会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宗教,所以荷兰人必须学会同穆斯林及伊斯兰教和平共处,需要抛弃“伊斯兰恐惧症”、摒弃“伊斯兰安全化”的立场来对待穆斯林,尽可能地鼓励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55)双方只有建立一种和谐、共存与友善的接触和对话关系,才能增进彼此了解、相互体谅、共同合作,才能实现自由民主和伊斯兰教的对接和兼容。
实现社会融入是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甚至几代人的时问跨度,才能充分展示整合融入趋势的程度。因此,穆斯林融入将是一个循序渐进、漫长持久、“润物细无声”的转变过程。期间呈现的将是一个坎坷不平、起伏不定的发展历程,有时会向整合融入迈进几步,有时又往冲突对抗退几步。不管怎样,只要荷兰政府和社会愿意直面现实,以宽爱之心善待穆斯林同胞,而穆斯林移民也愿意加入这个大家庭并引以为荣,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迸发出强大的社会力量,就能逐步破解相互怨恨和彼此敌视的对立僵局。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渐改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穆斯林的存在便能为整个社会所熟知和接纳,只有在族群和谐的氛围中,荷兰穆斯林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融入。
注释:
①Christian Joppke,“Beyond National Models:Civic Integration Policies for Im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es,Vol.30,No.1,2007,pp.1-22.
②Jocelyne Cesari,When Islam and Democracy Meet:Muslims in Europ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3.
③Stephen Castles,“Why Migration Policies Fail”,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7,No.2,2004,pp.209-210.
④Statistics Netherlands,“More than 850 Thousand Muslims in the Netherlands”,25 October 2007,http://www.cbs.nl/en-GB/menu/themas/bevolking/publicaties/artikelen/archief/2007/2007-2278-win.htm,last accessed on 17 April 2013.
⑤Pew Center,“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Projections for 2010-2030”,January27,2011,http://www.pewforum.org/The-Future-of-the-Global-Muslim-Population.aspx,last accessed on 28 March 2013.
⑥Christian Joppke,“Beyond National Models:Civic Integration Policies for Im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0,No.1,2007,p.6.
⑦Jytte Klausen,The Islamic Challenge: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81.
⑧Bhikhu Parekh,“Multicultural Society and Convergence of Identities”,in John Erik Fossum et al.eds.,The Tie That Bind:Accommodating Diversity i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Brussels:European Interuniversity Press,2009,pp.33-54.
⑨Paul M.Sniderman and Louk Hagendoorn,When Ways of Life Collide:Multicultu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he Netherlan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20-42.
⑩Jaco Dagevos and Merove Gijsberts,Integration in Ten Trends,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Hague,January 2010.
(11)European Union Monitoring Centre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Muslim in the European Union:Discrimination and Islamophobia,Austria,EUMC Report,2006.
(12)Ayhan Kaya,Isla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The Age of Securitization,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9,p.85.
(13)Olivier Roy,Globalised Islam: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London:Hurst & Company,2004,p.20.
(14)“Dutch Muslims Are Becoming More Religious”,Dutch News,15 March 2013,http://www.dutchnews,nl/news/archives/2012/11/dutch_muslims_are_becoming_mor.php,last accessed on 28 April2013.
(15)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Miller,The Age of Migration (Fourth Edit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20,245.
(16)European Union,The Common Basic Principles for Im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Brussels,2004,p.19.
(17)Peter Scholten,Framing Immigration Integration:Dutch Research-Policy Dialog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1,pp.16-17.
(18)Jonathan Laurence,The Emancipation of Europe's Muslims:The State's Role in Minority Integ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p.30-38.土耳其官方宗教事务局(Diyanet)有1300多名宗教人士在欧洲从事伊斯兰教的宣教活动,瓦哈比教派、穆斯林兄弟会等跨国宗教运动也纷纷在欧洲各国建立各种宗教设施(religious infrastructure),意欲影响当地的穆斯林社群。
(19)Ulrich Beck,“Cosmopolitan Manifesto: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 Conference”,Helsinki,2000,p.11.
(20)Bhikhu Parekh,A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Politic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99.
(21)Han Entzinger,“The Rise and Fall of Multiculturalism: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in Christian Joppke and Ewa Morawska eds.,Toward Assimilation and Citizenship:Immigrants in Liberal Nation-Stat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p.61-63.
(22)Marcel Maussen,“Constructing Mosques:The Governance of Islam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PhD Thesis,Amsterdam:University of Amsterdam,2009.
(23)Ahmet Yükleyen,Localizing Islam in Europe:Turkish Islamic Communitie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4-15.
(24)Arend Lijphart,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25)Yasemin Soysal,Limits of Citizenship,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26)Paul M.Sniderman and Louk Hagendoorn,When Ways of Life Collide:Multicultu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he Netherlan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2.
(27)Han Entzinger,“The Rise and Fall of Multiculturalism: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in Christian Joppke and Ewa Morawska eds.,Toward Assimilation and Citizenship:Immigrants in Liberal Nation-Stat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p.75-77.
(28)Ruud Koopmans et al,Contested Citizenship: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p.11.
(29)Ian Buruma,Murder in Amsterdam: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New York:Penguin Press,2006,p.11.
(30)See Frank De Zwart,“Pitfalls of Top-down Identity Designation:Ethno-Stat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Vol.10,No.3,2012,pp.301-302.
(31)Bhikhu Parekh,A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Politic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99.
(32)Sarah L.de Lange and David Art,“Fortuyn versus Wilders:An Agency-Based Approach to Radical Right Party Building”,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4,No.6,2011,p.1229.
(33)Paul Scheffer,“Her Multiculturele Drama”,NRC Handelsblad,29 January 2000.
(34)Jytte Klausen,The Islamic Challenge: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69.
(35)Spiegel Interview with Geert Wilders,“Was the Head Rag Tax Just A Bad Joke?”,Spiege,November 9,2010,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spiegel-interview-with-geert-wilders-merkelis-afraid-a-727978-3.html,last accessed on 11 April 2013.
(36)“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Spring 2005,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05/07/248- Topline.pdf,last accessed on 11 April 2013.
(37)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Integration Policy”,http://www.government.nl/issues/ integration/integration-policy,last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3.
(38)Sara Wallace Goodman,“Controlling Immigration through Language and Country Knowledge Requirements”,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4,No.2,2011,pp.235-255.
(39)BBC News,“Drug Trials,Song Spats and More”,15 March 2006.
(40)Christian Joppke,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Cambridge,UK:Polity,2010,pp.54-56.
(41)“安全化”是指在威胁政治共同体生存的紧急情况下,国家有必要采取法治外的一些特殊措施和程序。一个成功的安全化依赖安全化行为体(Securitizing actors,尤指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文化和传媒行为体)“叙事安全”(speak security)的能力,将指涉对象(referent object)呈现为一个挑战政治共同体安全的生存威胁,并能使“重要受众”(significant audience)产生共鸣。传统的安全化分析侧重于话语与公共辩论,而新近研究较注重制度与政策制定。see Jocelyne Cesari,“Securitization of Islam in Europe”,Die Welt des Islams,V01.52,Issue 3-4,2012,pp.432-433.
(42)“伊玛目”是伊斯兰教教职称谓。阿拉伯语,意为领袖、楷模、师表、表率等。伊斯兰教集体礼拜时,伊玛目在众人前面率领众礼拜者。
(43)Dutch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From Dawa to Jihad:The Various Threats from Radical Islam to the Democratic Legal Order,The Hague:AIVD,2004.
(44)Yvonne Yazbeck Haddad and Michael J.Balz,“Taming the Imams:European Governments and Islamic Preachers Since 9/11”,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Vol.19,No.2,2008,pp.221-222.
(45)Jonathan Laurence,The Emancipation of Europe's Muslims:The State's Role in Minority Integ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11.
(46)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ism:Success,Failure,and the Future,Washington,D.C.: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2012,p.26.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指标(immigrant multiculturalism policy scores, IMPS)的总分为8分,从宪政立法、教育、媒体、公民权、平权行动等八个方面对西方各国的多元文化主义现状进行评估和比较。
(47)德国长期奉行公民资格的“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不承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采取“宽容排斥”政策(exclusion with toleration)对待移民,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国籍法的修改,其移民整合政策调整为“管理式融入”(managed integration)。相反,法国始终秉承公民共和原则和“出生地主义”(jus soli)的传统。英国则从过去的自由多元文化主义转变为现今的管理式多元性。上述观点是作者与约尔根·尼尔森教授研讨的总结。
(48)Christian Joppke,“Beyond National Models:Civic Integration Policies for Im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0,No.1,2007,pp.1-22.
(49)Eytan Meyers,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Policy: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99.
(50)Jytte Klausen,The Islamic Challenge: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5.
(51)Jose Casanova,“Immigration and the New Religious Pluralism:A European Unio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in Geoffrey Brahm Levey and Tariq Modood eds.,Secularism,Religion and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39-163.
(52)Tariq Ramadan,What I Belie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5-6.
(53)Jonathan Laurence,The Emancipation of Europe's Mnslims:The State's Role in Minority Integ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5012,p.269.
(54)European Union,The Common Basic Principles for Im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Brussels,2004,p.19.
(55)Jocelyne Cesari,“Securitization of Islam in Europe”,in Jocelyn Cesari ed.,Muslims in the West after 9/11:Religion,Politics,and Law,New York:Routledge,2010,pp.9-25.
标签:移民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穆斯林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