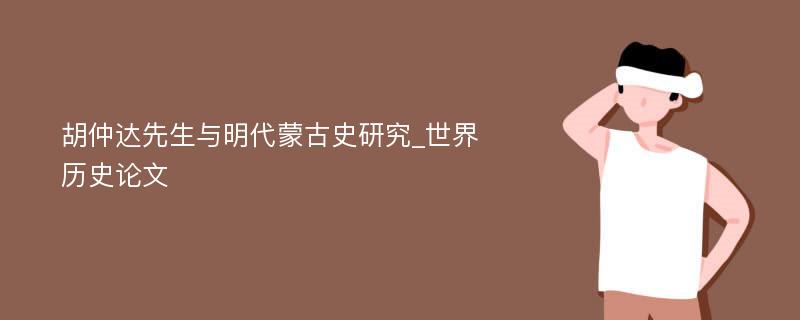
胡钟达先生与明代蒙古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明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生与论文,胡钟达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钟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古代史专家,生前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会长。他在世界古代史、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学界所公认的。他还曾涉足时代蒙古史研究,尽管发表的论著数量有限,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胡钟达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们讨论他在明代蒙古史领域的建树,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所论或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一
胡钟达先生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 1948年应聘至北京大学,历任历史系助教、讲员、讲师,1956年晋升为副教授,同时兼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在北大期间,他于1956、1957年先后在《光明日报·史学》和《历史教学》发表《关于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目问题》和《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两篇论文,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学术胆识和功力。他所编写的《世界古代史讲义》也被高教部审定为全国普通高校的教学参考书。这一切显示,他在世界古代史领域如日初升,前景辉煌。
1957年奉调来内蒙古,是胡先生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出于对教育、对学术的强烈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他倾全力筹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积极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时1958年的“史学革命”尚在进行,权衡利弊,选定《呼和浩特史话》作为集体研究项目,他本人也毅然中止已经初露头角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一个大转弯,进入尚是一片荒芜的明代蒙古史园地,承担起归化城建城历史的写作。1959年9月成《呼和浩特旧城 (归化)建城年代初探》,长16000字,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创刊号。两个月以后又成《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27000字,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胡先生于 1958年春节过后来到内蒙古大学,至此不过一年有余,除去筹建历史系,以及正常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实际读书研究的时间少之又少,而他已经完成了从世界古代史到明代蒙古史的大跨度的“转岗”,并且在没有前人成果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写出了长达四万余字很见功力的两篇论文,先生杰出的史学素养和勤奋,于此可见。
1962年6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上,先生以《十三世纪蒙古族社会性质》为题作了长篇发言。此后由于左的倾向愈演愈烈,他再无新作。
文革结束以后,胡先生重回世界古代史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论著,但仍不忘明代蒙古,1984年又发表了蒙古史学界公认的力作《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胡钟达先生作为著名的世界古代史专家,他有关明代蒙古史的论著虽然只有三篇,但都是精品,在我国明代蒙古研究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二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明代蒙古史研究,虽有李文田、沈曾植、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为《蒙古源流》作笺注,作考证,但涉及有限,从总体上看基本是一块荆棘丛生、未经开垦的处女地。50年代仍旧寂寞冷落,研究者和学术成果非常稀见。
胡钟达先生负责撰写《呼和浩特史话》归化城建城一章。归化城建城年代本有多种说法,出于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开宗明义,必须首先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代。于是写下《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这篇纯考证性文字。
关于归化城建城流行的说法是嘉靖或隆庆年间,根据作者的归纳,其实皆源于《明史》以及沿袭《明史》的《大清一统志》、《归绥县志》等志书。另一种万历十四年说,则是对《明史纪事本末》的误解。作者广泛征引当时呼和浩特和北京地区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如《明实录》、《国榷》、《万历武功录》、《全边略记》、《石匮书后集》等,予以排比考订,一指出诸说的谬误之处,的确起到了廓清旧说作用。文章关于《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料价值的分析,关于《万历武功录》及其版本的评述等等,所体现出来的史学素养和功力,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初涉明史不过一年的年轻学人的手笔。
由于缺乏关键性的直接证据,胡先生在考订过程中过分相信《明史纪事本末》和《全边略记》关于归化城的记载,误入歧途,因而认定归化城建于万历九年。对于这一结论,作者并不自信。他反复声明:这“只是我们初步探索的一个成果”,“对这个问题要做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关资料和文献”,同时恳切地希望有人“能提出更多的论证,来肯定我们这个初步的结论或修正我们这个初步的结论”。其实作者已经从张居正文集所收给宣大总督郑洛和大同巡抚贾应元的信件中,查找到俺达筑城的记载,但是他说“可惜郑洛和贾应元都无专集行世,我们不可能从他们写给张居正的原信中多了解一些俺达筑城的情况了”。事实上,25年以后薄音湖先生正是因为找到了郑洛的信件,才纠正了胡先生的错误,最终解决了归化城的建城时间问题。
这里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到,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考据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备受声讨挞伐。1959年其余波尚在荡漾,作此类考证文字,需要学术胆识。据后来胡先生告诉我,当时内大确有人要求进行批判,幸亏学校领导主持公道,给予保护,才躲过一劫。
《呼和浩特史话》是历史普及性读物。因此《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文字明显有别于枯燥的学术论文,平易流畅,许多地方还带有故事性,而内容都完全是学术性的。关于明代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清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地方志书曾有所描述,大抵皆片言只语。以新体例作详述的首推荣祥先生于1957年写成并油印分发内部征求意见的《呼和浩特沿革纪要》。此书涉及呼和浩特明代建制沿革和各族迁徙居住,取材仅及《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会典》等寥寥数种,内容极为简略。胡先生此文比之《沿革纪要》等等,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是资料丰富。除了荣先生所引诸书外,胡先生首次将《明实录》引入呼和浩特地方史的研究,成为主要的史料渊薮。与此同时《国榷》、《明通鉴》、《罪惟录》、《四夷考》、《万历武功录》、《译语》、《夷俗记》、《三云筹俎考》、《全边略记》、《口北三厅志》、《云中降虏传》、《款塞始末》、《伏戎纪事》、《通贡传》、《两朝平攘录》、《涌幢小品》、《五杂俎》、《北狄顺义王俺答等贡表文》、《蒙古源流》以及《明经世文编》、《张居正文集》、《大隐楼集》等等,都成为采摘对象。以上文献自先生首先引用,至今仍是研究明代呼和浩特历史的基本史料依据。
文章分七节叙述。一,从明初开始,全面铺叙俺答开发丰州滩的背景;二,俺答开发丰州滩、构筑大板升的过程;三,板升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四,把汉那吉降明和俺答封贡;五,归化城的建立;六,俺答去世和三娘子的功绩;七,封贡以后丰州滩地区的和平景象与社会经济发展。由于作者掌握了空前丰富的历史资料,《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第一次完整、系统,在某些环节上还相当精细地勾画了明代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所论嘉靖中丰州半农半牧业的发展,板升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发展,俺答封贡的实现,归化城的修筑和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娘子和俺答后裔的劳绩等等,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本文所构建的明代呼和浩特地区历史的框架,至今依旧是该课题的研究基础。
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嘉靖以后丰州滩地区历史的论著日多,较之胡先生此文,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的进展,但此文所开掘的基本文献,奠定的基本框架,至今仍具生命力,其开创之功不可泯灭。
自60年代中明代蒙古史研究中断20年以后,1984年胡先生在内蒙古大学的一个报告会上就明与北元——蒙古的关系作了演讲,事后加以整理,以《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为题,著文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与前两篇文章不一样,这是一篇宏观驾驭近 270多年明与蒙古关系的力作,在当时就非常引人注目。
明代蒙古的归属原先国内外的有关著述大体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蒙古是独立于当时中国以外的一个国家,另一种则完全相反,否认蒙古有自己的政治实体,认为仅仅是明朝的臣属。1981年我本人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2-3期合刊发表《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就题记中屡屡出现的“南朝”“北朝”字样,稽钩史料,作考订、分析,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明朝与蒙古是当时中国土地上的两个对峙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南北朝。这第三种观点,完全有别于前两种。文章写成以后,请胡先生审阅,他很赞赏我的观点,认为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主编,亲自审定签发,在《内蒙古大学学报》发表。不过拙作对此大体上仍止于历史事实的考订,未及展开专文论述,因而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1984年的当时,我正遭受无妄之灾,处境非常困难,他做报告,撰论文,在更深的层面上系统论证中国境内明朝与蒙古两个政权发生、发展和重归一统的全过程,并分析引起这种矛盾运动的内在原因,这是对我道义上的支持,更是在学术上的执著追求。
文章的第一部分,论蒙古与明朝同是那个时代中国土地上的两个并立政权。作者首先强调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元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古代封建正统王朝序列中的重要一环;元王朝的版图就是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中国的版图。以这一基本史实为出发点,作者高屋建瓴,淋漓酣畅地展开了论证:“北元——蒙古是14世纪至17世纪建立在元代中国领土上的一个国家;它同明朝一样,是元朝遗留下来的中国领土上并存的两个政权。”因而也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权。这种顺理成章的论断,显示了很强的逻辑力量。
任何经得住推敲的结论都是逻辑和实证的统一。作者随后征引大量原始资料,包括檄文、诏敕以及一些典章制度等权威性的记录,分别从蒙古、明、清三方面进行论述:蒙古诸汗是成吉思汗、元顺帝皇统的延续,蒙古承袭了元朝的国号、礼制,并且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元朝的合法继承者。对于这一点,与之对峙,以奉天承运自居的明朝,以及重新实现大一统的清朝,或者被迫,或者乐于公开予以承认。全部议论,始终紧紧地扣在元朝是中国古代的正统王朝这样一块坚固的基石之上,其构思、说理别具匠心,令人悦服。
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列举种种文献、碑刻、题记资料,证实当时明蒙双方朝野,上自皇帝、大汗,下至蒙汉各族村夫牧民,几乎无例外地称明为南朝,蒙古为北朝,据此论定明与蒙古的对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南北朝。
在随后的第三部分,作者总结历史,指出一个规律性现象:三次南北朝都是暂时的,“因为这种政治局面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符合我国广大各族人民的要求。”站在这样的高度,深入研究明与蒙古对峙二百余年的历史风云,高度评价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草原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指出,元朝“政治上的统一推动南北经济的发展和联系,蒙古草原在经济上与内地成为一体。 1368年以后,两个政权并立,人为地切断了这种经济一体,结果使蒙古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单一游牧经济时代”。经济的倒退,给蒙古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弥补单一游牧经济的不足,上至大汗贵族,下及牧民群众都迫切要求从中原地区获得手工业和农产品。“人们的这种经济要求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在明朝与北元——蒙古之间,开辟着交往的渠道。而当它受到明朝一方的阻挠而不能实现的时候,往往以战争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战争则又使双方两败俱伤不得不坐下来探求新的和平途径。”最后由清完成了重新统一的使命。文章正是从这种经济联系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明与蒙古复归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样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论点,显示了相当的认识深度,且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平等团结,从理论上作出了贡献,达到了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和战斗性的统一。
《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征引文献达 30余种。作者还善于从人们所习见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不寻常的价值。如朱元璋的《北伐檄》,人们皆津津乐道其“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云云,作者则从该檄文中发现,他承认元朝是受天命,得正统的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序列中的一环,并且肯定元朝的治绩,声称自己是元朝正统的承受者。因而,令人感到史料丰富,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功力深厚。
自胡先生此文出,明与蒙古对峙,构成中国古代第三次南北朝的观点,日益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
三
评论胡钟达先生在明代蒙古史领域的贡献,不应该忘了他的论著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我本人的学术志趣本来是在魏晋南北朝。大约1964年初,系领导要我转入明代蒙古史,争取两三年内先开出这门课。当时,我对此除了土木之变、庚戌之变一类的常识以外,一无所知。接受了任务,首先去了解国内的研究现状,发现基本上是一块未开垦的莽原,论著极其稀少,而这极少的著述中,胡钟达先生关于归化建城的两篇文章非常引人注目。找来认真读了几遍,收获极大。不仅增加了许多知识,知道了明代丰州地区的历史概况,他在考订、论证中所显示的严密的逻辑力量,也使我深深钦佩。最大的获益还是通过先生的论文,掌握了有关明代蒙古史的第一份相对完备的史料目录。于是开始按图索骥,逐一找来见面。同时以《明实录》和《明经世文编》为重点,认真阅读和摘抄我认为有用的史料,积累了上千张卡片,就这样一步步走进这一块新的学习和研究的园地。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重拾明代蒙古史研究。为参加1980年在海拉尔举行的中国蒙古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我以《阿拉坦汗和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为题提交了论文。此文专题探讨俺答开发丰州川的背景、条件、过程和板升内部的阶级关系等等。当然,后来者居上,比60年代胡先生的作品是大大深入了一步。但所论实际上仍是在他所提出的框架之内的深入开掘。资料,由于呼市地区藏书的限制,亦大体是他所运用的那些,我的工作是扩大和深入发掘这些文献,主要是《明实录》、《明经世文编》中所蕴涵的有价值的史料。
学术总是在继承的前提下才有发展。后来者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是在前人辛勤铺垫的基础上,或者说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回顾40年来自己在明代蒙古史领域的跋涉,我深深感激胡钟达先生论文的引路作用。
一个有趣并值得深思的现象出现在中国蒙古史第二届年会上。原来会上提出的关于俺答汗的论文并不止我的一篇。本次讨论会所提交的以汉文写作的论文总共58篇,其中明代蒙古的6篇,6篇之中有五篇不约而同皆为研究俺答之作。其中除了珠荣嘎先生的《从〈俺答汗传〉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因蒙文《俺答汗传》而发,关系不大。其余杨绍猷先生的《论俺答汗》,杨建新先生的《蒙古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阿勒坦汗》和荣丽珍先生的《略论阿勒坦汗》,虽各有特点和侧重,内容也比胡先生的两篇更丰富、更深入,但大体都是在他的框架内向前探索,所用文献也大体相同。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俺答,从俺答入手走进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大门,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而胡先生论文的指引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研究,至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从事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学人。
还有一件事,值得作为史坛掌故一叙。
前文已经提到,在写作《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考》时胡钟达先生已经深感所论存在缺憾,并且隐约意识到可能出现新史料的地方。1/4世纪以后,内蒙古大学的年轻学者薄音湖先生终于从外地图书馆中发现《名臣宁攘要编》一书,其中收有郑洛的《抚夷纪略》。不出胡先生所料,确有关于呼和浩特建城情况的史料数则。薄音湖先生根据这些新史料,撰成《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重考》一文,论定万历九年筑城之举,是扩建外城约二十里;而归化城的建城与赐名应在万历三年,当时已经具备相当规模。
胡钟达先生作为学报主编,迅速将这篇论文发表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并在文后署名加注了一段“阅稿附记”。“阅稿附记”说:读薄音湖同志此文“极为快慰”,25年来的“种种疑团几乎一一冰释,呼和浩特城始建于隆庆六年,建成于万历三年,扩建于万历九年,已经可以视为定论。”“阅稿附记”最后说:“薄音湖同志近年着力搜求明代有关蒙古典籍,发现了郑洛的《抚夷纪略》,并据此对这一相当复杂的问题,作了合理的分析,订正了我在《初探》中的错误,我应该在此向作者表示谢意。”
面对一位年轻学者公开纠正自己研究中的失误,胡先生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对批评者表示感谢,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学人对学术的极端负责的精神和虚怀若谷的风范。在浮躁之风甚嚣尘上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
收稿日期:2005-09-12
注释:
①我本人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以姜叔晶笔名发表《读〈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初探〉》予以评论。本节所论多引自该文,不再出注。
②明初大元国号尚存,史称北元,永乐间废大元国号,径称蒙古,所以胡先生称明代蒙古270多年的政权为北元——蒙古。本文为简明起见,径称蒙古。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内蒙古大学学报论文; 明朝论文; 明史纪事本末论文; 万历武功录论文; 明经世文编论文; 汉朝论文; 经济学论文; 呼和浩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