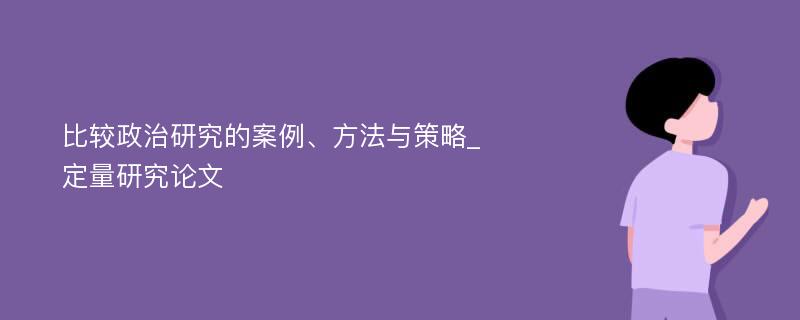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案例论文,政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估、检验和发展理论是经验性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因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比较政治学因其在方法论(比较方法)方面的重要特性,这一过程更是一个在不同案例、方法和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比较政治研究中案例、方法与策略的选择,本质上还是一个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有关的重要问题,同时也受到与研究者相关的诸多因素(如知识储备和积累,特别是对经验案例的掌握情况、理论素养以及研究兴趣)、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目的(包括方法论目的)以及不同的思考和推理逻辑等诸多方面问题的限制,不同案例、方法和研究策略的选择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规范的学术研究要求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而正视并接受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限度的方法论理性同样不可或缺。
一、案例选择与选择偏差
案例选择是比较研究的重要起点。在研究过程中,选择怎样的案例(经验材料)以及选择多少案例,只是确定不同研究类型的一个维度,而如何运用所选案例进行研究,或以怎样的方式在经验材料(证据)与理论(观念、假设)之间建立起符合逻辑的联系来,以实现理论(观念、假设)与经验材料(证据)之间的有效对话,则涉及与研究相关的几乎所有方面。在这种意义上,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的诸多问题都与案例及其选择有关。案例的选择影响着研究的走向和结果。“糟糕的案例选择甚至可能在后来的研究阶段摧毁作出可靠的因果推论的最具天才的努力。”①在这种意义上,随机抽取样本似乎是比较研究中一个理想的案例选择方法,但在小样本研究中则并不普遍适用。于是,样本的非随机选择就为各种各样的案例选择偏差开启了大门。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是在特定研究背景中产生的系统错误②,在研究过程中具体表现为选择那些能够支持研究者希望得到的研究结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组合的案例。由于大多数定性研究中的案例选择标准并不明确,选择过程也常常缺乏研究者评估潜在偏差的自觉努力,各种选择偏差被带入案例选择过程的机会因而就大大增加了。
在比较研究中,案例一般表现为具体的国家或某种经验观察。案例选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案例的可比性,即选择可比案例。虽然比较方法更有助于次国家案例的比较③,但国家的比较更常见于比较政治研究。不同国家在地理上的接近是可比性的重要基础,但却不是可比性的必然基础。事实上,可比性并不是内在于所有给定对象的一个特征,而是由观察者的视角所赋予的一种特征。④因此,比较研究中的案例选择不仅应遵循和符合一般思考和研究逻辑,还应体现比较的逻辑,甚至在比较思考中发现和创造比较的基础,以确定进行比较的案例。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研究假设或初始理论的提出往往基于某些经验观察或案例。因此,用于检验假设和初始理论的案例的选择,应避免重复使用从中产生了研究假设和初始理论的案例。这可以看作案例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案例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在研究者所要检验的初始理论的适用范围内,应当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这两个标准实际上就是案例选择的一般逻辑。
案例选择是在“无知之幕”后进行的。如何在各种各样的经验观察的混沌和迷雾中选择案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由理论来引导案例的选择就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救赎之路”。⑤理论不仅影响着研究路径的选择,也指导着案例的选择。理论选择或研究路径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哪些案例(国家)或观察可作为研究案例。因此,理论本身就是指导案例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则。
理论对于案例选择的影响,可能体现于不同方面,或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首先是理论的适用问题。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作为分析基本单元的案例常常就是指国家。对理论的准确理解和对经验现象的深入而系统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选择哪些国家或观察作为研究案例提供直接和具体的引导。譬如,如果确定了将法团主义现象作为所要研究的问题,法团主义的相关理论就是最适合的理论和研究路径选择。在这一研究中,具有法团主义传统的国家(如伊比利亚国家、奥地利、拉美国家等)以及一般被认为没有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构成了法团主义研究的良好案例,其中具有法团主义传统的国家更成为这一研究的最佳案例。在最消极的意义上,理论和研究路径的确定已经将一些国家(如英国⑥、美国)排除在案例选择范围之外了。
由理论所识别和引导的概念和变量的确定及其不同关系构成了类型分析的不同维度,并使研究者获得有关潜在的案例总体的一个清晰印象。确立多维分类体系或类型(multi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scheme or typologies)是案例选择的一个有用的出发点。由理论所引导的类型一旦确立,研究者即可选择有望能最好地回答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案例。⑦仍以法团主义研究为例。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与社会法团主义( societal corporatism)是施密特(PhilippeSchmitter)基于法团主义的制度基础而提出的法团主义的两种重要类型。⑧其中,国家法团主义指表现出由上而下或威权主义组织特征的政权或制度。这种国家法团主义主要见于南欧和拉美国家;社会法团主义也可称为新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则代表了一种较为民主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安排。北欧国家以及奥地利、德国、瑞士等欧洲民主国家的法团主义制度就体现了典型的社会法团主义特征。
研究假设或初始假设的内容实际上决定了案例的选择范围,或者说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就是案例的选择范围。譬如,有关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的研究假设或理论的检验,就可以从所有民主转型国家这一样本总体中抽取样本以检验假设或理论。根据因变量选择研究案例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一种常见方法,并已在研究实践中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这种研究无法检验自身提出的理论并可能损害研究的推理逻辑。
选择“硬”案例(“hard”cases)是避免案例选择偏差的一个重要途径。“硬”案例就是可以为理论提供严格检验的案例。如果一个理论得到了硬案例的检验,它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也是成立的。通过硬案例检验理论的逻辑也被称为“纽约推理”(New York inference),即“如果我在那里(纽约)能够成功,那么我在哪里都会成功”。硬案例也被称为“更加确定的案例”(“a fortiori”cases):如果一个理论能够在特别困难的环境中击败各种与其形成竞争的理论,那么它在有利的环境中更容易得到检验。⑨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案例选择并没有统一的规则。如果说有的话,这个统一规则就是在检验研究假设和初始理论时,以不损害推理逻辑即不损害推理质量的方式选择案例,避免案例选择偏差。
二、不同的研究逻辑,不同的研究类型
在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中,似乎案例和观察“越多越好”。对于定性研究而言,“多少观察足够”是定性研究中的一个定量问题。案例选择的多少,与推论的可靠性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试图得到的因果推论。此外,变量特征特别是未被作为控制变量的变量特征,对于研究所需要的案例和观察的数量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因变量的变异性(variability)越大,就需要越多的案例以获得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者对推论确定性水平的要求也影响着选择案例的数量。如果可以容忍某种不确定性,研究者只需要较少的案例;在一些人们所知甚少的领域,任何新知识的获得都非常重要,对确定性的要求也会相对低一些,而在人们已经积累了较多知识的领域,增进知识所要求的较高的确定性则提出了需要较多案例的要求;原因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水平和共线性(collinearity)越高,就越可能浪费案例和观察。原因解释变量赋值方差(variance)越大,研究者只需要越少的观察以达到特定确定性水平的因果推论。
尽管在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中,案例和观察对于获得可靠的研究推论似乎“多多益善”,但考虑到不同研究设计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研究中涉及的具体变量的不同特性,以及获取案例和观察方面的诸多问题(如时间、资金及其他问题),有时更多的案例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甚至是一种浪费。原因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存在较高共线性时尤其如此。理论评估的逻辑强调“使杠杆作用最大化”(maximizing leverage),即“以尽可能少的案例作出尽可能多的解释”。这也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目标或标准。⑩
依据所选择案例或观察的多少这一数量特征,可将不同研究类型简单区分为大样本研究和小样本研究。对较多国家和案例的研究称为大样本(large-n)研究;与之相对应,对较少国家和案例的研究称为小样本(small-n)研究。其中,n代表所要研究的国家和观察的数目。
大样本研究一般指研究者通过充分且具有差异性的案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其中涉及的变量就是不同案例之间存在差异的维度。因此,大样本研究也是“变量取向的”(variables-oriented)研究。大样本研究试图通过增加案例和观察以获得和提升因果推论的可靠性,非常接近于科学的实验方法。
大样本研究在今天通常被称为统计学研究。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同事们对1950年-1990年间世界范围内不同类型国家(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和转型国家)所做的统计学研究,是较为晚近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大样本研究,并且获得了超越“仅仅掌握事实”的比较研究结论,即在处于经济发展任何阶段上的国家都可能引入民主。(11)
小样本研究是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中更常见的一种研究类型。其中除了研究技术、资金及时间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外,一些方法论方面的目的(如为了更好地把握因果关系过程或机制)也促使研究者选择小样本研究。(12)小样本研究通过对特定案例内以及为数不多的案例的比较来检验假设提出的因果关系过程并作出推论,也被称为“案例取向的”(case-oriented)研究。在比较研究中,研究的焦点往往在于国家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变量之间的分析关系。对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意在揭示每个国家的共同点,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结果。小样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数量有限的案例和增加因果过程观察的数量来增进因果推论的可靠性。
小样本研究可以使研究者深入案例内部,发现其特殊性,从而对可能的因果关系的每个环节进行检验,进而更可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对于一些现实社会中相对较少的现象(如革命),则更需要就每个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也只有选择较少的案例才可能使研究富有成果。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1979)就是对革命现象所做的小样本研究。政治学领域许多有影响的研究都产生于小样本研究。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1963)、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的《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又译《市场与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学》,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1981)等都是小样本研究的经典。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小样本研究倾向于被定位于对必要和充分的因果条件的分析,并至少隐晦地蕴含着对因果关系的某种决定论(和非线性的)观点。大样本研究(也包括某些小样本研究)则对因果关系采取了一种或然性观点。政治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事实上使得小样本研究内在的决定论逻辑偏离了现实,特别是在识别所谓“反常”国家(“deviant”countries)或离群现象(outliers)方面,大样本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13)
更好的数据收集方法比更好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可取,被认为是在大样本研究与小样本研究之间作出选择的基本原则,因而也使大样本研究与小样本研究之间的平衡似乎偏向了大样本研究一边。当充分量化的可比信息能够获得时,大样本研究设计就会被采纳。但是,案例和观察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免费午餐”:新增案例与原有案例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概念在为数众多的案例间“穿行的问题”(the travelling problem)(14),所使用的指标是否适用于新的案例等问题,都可能使大样本研究变得不可取、不可能。
在研究结论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小样本研究反映了深度优先的研究逻辑,而大样本研究则将广度放在第一位。因此,小样本研究可能会以牺牲普遍性为代价追求解释的准确性和详细的因果过程描述;而大样本研究常常以使具体个案隐形的方式,甚至是以无法解释任何单一个案为代价,以强化人们对普遍性和因果效应强度的信心。
大样本研究和小样本研究的互补性已被广为认识。大样本研究与小样本研究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使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这两种不同研究类型之间的界线模糊了。
三、研究策略的选择与运用
在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15)是一种传统的二元类型认识。传统上,研究者倾向于将大样本研究与定量研究相对应,而将小样本研究与定性研究联系起来。这种传统认识事实上只是一种部分正确的认识。具体而言,大样本研究与小样本研究之间的差异一般与抽样总体、抽样以及统计的变化倾向有关,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差异则是围绕概念的构建和测量。无论在研究逻辑上,还是如研究实践所表明的,小样本研究常常是定性的,但并不必然是定性的,而大样本研究也有可能是定性研究。(16)
如何运用所选案例进行研究,或以怎样的方式在经验材料(证据)与理论之间建立起符合逻辑的联系,实现理论与证据之间的对话,代表着趋近证据的不同路径,即不同的研究策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以及不同的比较研究策略。
定量研究主要运用数字和统计方法,以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现象的数字测量为基础,并强调从对特定案例的抽象中寻求一般概括或检验因果假设,而相关测量和分析可由其他研究者重复进行。定量分析的出发点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通过许多案例所进行的模式的考察和分析是理解基本模式和关系的最佳途径。研究者通过考察许多案例可以从中概括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从而提供有关社会政治现象的“全景式观点”,而对任何单一案例或较少案例的研究,则只可能获得有关社会生活的一个扭曲的图像。(17)一般地,也是在上述意义上,定量研究常常与大样本研究相联系。
定量研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常常建立在对许多案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并通过表明许多案例间两个或更多特征(变量)的共变关系来构建所研究问题或现象的概念。其中,变量是定量研究者构建其概念的关键要素,定量研究常常使用相关性一词来描述两个可测量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模式。定量研究因其通过浓缩许多案例以获得有关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图像而具有非常明显的普遍性特征;同时,因案例较多而不可能考察较多的变量,还使定量研究具有同样明显的简约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使定量研究契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基本目标,如发现一般模式和关系、检验理论并作出预测。相对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还具有适宜理论检验的特点。由研究者的理论观念或所要检验的理论转化而产生的分析框架,可以明确与理论相关的案例并描述其主要特征,使研究者发展对于相关变量的测量,采集数据,评估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理论或假设进行检验——支持或否定。
在定量研究的诸多环节中,分析框架的确定对于后续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在不以理论检验为目的的定量研究中,分析框架仍然主导着诸如确定案例和变量、采集数据、测量变量、检验相关关系等工作。这些不同环节基本构成了定量研究的一个完整过程。定量研究在研究中所展示的多方面特点,使其与其他研究策略相比似乎更为“科学”。在一些定量研究者看来,定量研究所进行的系统的统计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
定性研究实际上是多种不依赖于数字测量的方法和路径的集合。定性研究一般集中于为数不多的案例,通过深度访谈或对历史资料的深度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推论的特性。宏观历史研究、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及被称为阐释主义解释学和“厚描法”(interpretivism hermeneutics,and“thick description”)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政治研究常用的三种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试图识别和理解研究对象的属性、特征与性质,因而也必然要求只对数量较少的国家予以关注。(18)基于这样的研究取向,定性研究一般与小样本研究联系在一起。
定量研究在提供有关社会政治现象的“全景式观点”的同时,却可能对某个(某些)特定案例所知甚少。因此,定性研究者认为,只有通过对特定案例的深度考察才可能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恰当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定性研究更重视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系统认识,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及定量研究方法“科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社会科学中的大部分专门知识都产生于定性研究。(19)
定性研究很少以检验理论为目标,解释具有重要历史或文化意义的现象并推动理论发展是其主要目的。定性研究的步骤或研究环节大致可表述为,在初步的或模糊构建的分析框架中明确案例范围,确定案例和概念,厘清所使用的概念和类型,进行因果关系评估,并在研究过程中完善或重构分析框架,对假设进行验证,或提出新的解释。
在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及其差异,以及两种方法之间孰优孰劣的长期争论,还使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以不同研究方法为核心的两个分支:定量的系统概括性分支(quantitative-systematic-generalizing-branch)和定性的人文主义推论性分支(qualitative-humanistic-discursive-branch)(20)。不仅如此,定量研究因其更“科学”而日益受到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而定性研究也被认为应遵循与定量研究同样的逻辑;另一种情形则被称为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即坚持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很难对话和交流,也无从相互学习和借鉴。(21)
事实上,大多数研究都不能精确、严格地归类为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中的某一种类型而不具有另一种研究类型的某些成分。定量研究常常离不开一些定性的概括和归纳,而在定性研究中往往也可以看到定量研究被当作一种辅助手段,与定性研究结合在一起。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遵循共同的推理逻辑,两者之间的差异只是研究形式的不同,在方法论和实质上并不重要。(22)
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是实实在在的,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也被称为牵强的“和解方案”。(23)在研究中选择哪一种方法或策略,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社会、政治或经济行为的模式与变化趋势较适于量化分析,而有些问题并不能够以量化数据通过假设检验而得到阐释,从而在根本上排除了将量化研究作为一个选项。
选择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还常常与大样本研究或小样本研究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系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一些研究也的确打破了方法论类型的刻板模式。譬如,一些研究虽是大样本研究,但却表现出定性研究的特点;也有研究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是小样本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前者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欧洲革命:1492-1992》(European Revolutions,1492-1992,1993)中就涉及了数以百计的案例;后者如一些以预测美国总统及国会选举为目的的研究常常只选取十多个样本来进行统计分析。詹姆斯·坎贝尔(James E.Campbell)的《美国竞选:美国总统竞选与全国投票》(The American Campaign:U.S.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the National Vote,2000)就是此类研究的典型。
样本量的大小虽然不直接影响研究策略的选择,即选择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但样本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研究策略的选择。定性研究通常运用厚分析或深度分析(thick analysis)的方法。定性研究者往往沉浸于案例的具体细节中,从中构建其概念、变量以及基于知识的因果关系理解,排除具有竞争性的其他解释并确立经得起检验的解释。定性研究所要求的丰富的信息层次和对具体案例的深入了解,使得大样本研究非常困难。相反,定量研究所要求的对假设的统计检验又常常是小样本难以支持的。统计检验是定量研究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定性研究的力量则源于厚重的分析。当然,有时厚分析也在定量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24)
大样本研究与小样本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有关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研究策略与类型的两个不同维度,不仅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两种不同研究策略的选择可能受到样本量的影响,而所要选择的样本总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间不同选择的影响。
“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s”design,MSSD)和“最不同体系”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s”design,MDSD),是普热沃斯基和特纳(Henry Teune)在其被奉为比较社会科学研究圣经的关于比较研究价值的分析中所讨论的两种一般性研究方法,也被看作两种比较研究策略。在他们看来,大多数比较分析者都相信,“在尽可能多的特征方面尽可能相似的体系构成了比较研究的最优案例”。最相似体系设计特别适合于专注于区域研究的研究者。(25)这种比较策略以约翰·密尔(John Mill)的差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为基础,试图识别相似国家中可以解释观察到的政治结果的关键的差异性特征。研究者在研究中大多选取相似的政治体系,然后分析其差异,并观察这些差异对其他政治或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最不同体系设计以约翰·密尔的契合法(method of agreement)为基础,旨在找出不同国家的共同特征以解释特定的结果。这种研究策略允许研究者选择两个或更多在本质上具有差异性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研究集中于寻找这些国家的相似之处。最不同体系设计尤其适用于找出一个需要解释的特定结果的比较研究。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最相似体系设计是更常被使用的研究策略,其原因就是为了控制尽可能多的变量。这一点既是最相似体系设计的优越性,也使这一研究策略面临风险,即由于具有相似性的国家数量毕竟有限,要控制所有可能的解释变量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很容易使研究遭遇“许多变量,很少案例”(many variables,small number of cases)的问题。为了弥补最相似体系设计的缺陷,普热沃斯基和特纳提出最不同体系设计作为替代策略。就两种比较策略的运用而言,当研究者关注于体系层面的变量(variables at a systemic level)时,最相似体系设计尤其有用;当研究者关注次体系层级的变量(variables at a sub-systemic level)时,最不同体系设计更适用,并使“许多变量,很少案例”的问题在次体系背景中得以补救。(26)在研究实践中,还可以看到将两种不同比较研究策略结合使用的混合设计。胡安·林兹(Juan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1996)中,先是运用最相似体系设计来比较南美、南欧和东欧等不同区域内的民主巩固经验,又运用最不同体系设计来对这三个区域进行比较。
无论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还是最相似体系设计与最不同体系设计,案例选择的多少在不同程度上对研究策略的选择以及研究结果都可能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多少样本/案例的研究适于采取某种研究策略的问题,在研究实践中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实际上,用尽可能少的案例获得尽可能可靠的推论,始终是研究者选择研究策略的重要思考。
大样本研究常常涉及50个以上的案例,有的调查数据涉及数以千计的样本;小样本研究一般是对一个或为数不多的几个案例或观察的研究。数量范围不同的案例都有其相应的研究策略选择。譬如,比较方法主要运用于对适当数量的案例的考察,几个案例到50个左右的案例被认为是这一方法运用的适当范围;10-20个之间的某一点应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界点;等等。(27)那么对于10-50个之间的案例和观察而言,应使用关注于深度分析的小样本研究还是倾向于广泛概括的大样本研究,却并不明确。譬如,少于15个案例/样本的选举预测模型仍然可以使用大样本统计常用的统计方法。学者拉金(Charles C.Ragin)提出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和模糊集合(聚类)(fuzzy-set analysis)分析,不仅为介于小样本与大样本之间的中等数量(规模)样本(intermediate-n或moderate-n)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方法和分析工具,也在很大程度上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架设起了桥梁,从而有助于观点与证据之间更加富有成果的对话。
定性比较分析运用布尔代数(布尔逻辑)来实践定性研究者的比较原则,逻辑比较的布尔方法将每个案例看作原因和结果的一种组合。这种研究技术通过使定性分析的逻辑形式化,将定性研究的逻辑和实证强度与包括更多案例的研究结合起来,而后一种情形通常需要运用变量取向的定量研究方法。(28)被认为将会带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革命的模糊集合(聚类)分析,是定性比较分析的改进和发展。其中,对模糊集合(聚类)的理解常常需要借助于与其相对应的明确集合(crisp set)的概念。明确集合指一个案例属于或不属于某一集合,只涉及两种明确的情形——属于还是不属于。明确集合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集合的一种常规认识。与此不同,模糊集合(聚类)则是在属于或不属于某一集合之间设定了从0到1的一个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0和1两个性质不同(属于和不属于某一集合)的两极之间形成了具有程度差异的案例序列。这种方法可以使研究者抛弃有关案例和原因的“同质化假设”,从而提供了理论与数据分析之间的强有力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可适应不断变化的理论概念。
比较研究策略的确定,远不是在诸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最相似体系设计与最不同体系设计等一系列二元选项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需要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目的在由不同研究策略所构筑的选择空间制定灵活和务实的研究方案,其中不同研究策略的融合也是一种常见的选择。
四、有限度的选择与反完美主义的立场
在比较研究中,围绕所要研究的主题,与案例相关的诸多问题,如选择怎样的案例,选择哪一种研究类型(如大样本研究或小样本研究,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等等),以及确定怎样的比较研究策略(如最相似体系设计或最不同体系设计),都与案例的选择密切相关并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案,而不同的研究方案则代表着经验材料(证据)与相关理论(观念、假设)间对话的不同形式。
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对话中,案例的选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影响。其中,案例的选择早已超越了选择哪个(哪些)国家或观察作为研究对象和基础的单一问题,而与更为广泛的研究目标和思考逻辑联系在一起。比较研究中的大样本研究或小样本研究、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等选择,看似不同维度上的不同研究类型,实际上却存在着由一般推导逻辑所决定的内在关联。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这两种比较策略则较为明显地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推导逻辑和研究抱负。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政治学在吸收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开放性的特征。同时,在使政治学趋向科学化的努力中,比较政治学因其方法以及建立在方法基础上的经验研究特征而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比较政治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其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最终仍必须服从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逻辑和规律,而不可能因袭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
有限的信息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特征。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研究过程中案例、研究方法及策略的选择等诸多环节,都是在有限的信息环境中甚至在“无知之幕”后进行的。因此,比较政治学所适用的研究方法与策略常常会受到诸多限制,研究所获得的结论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其适用范围更常常是有限的。这种状况应理解为比较政治学学科研究的一个常态。
重视方法、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将会有助于研究者成为有意识的思考者(conscious thinkers)。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从不同案例的选择,到不同研究方案的选择和确定,都需要研究者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methodological awareness),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贯彻并及时调整和修正研究设计所确定的研究方案,则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和提升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但是,要避免成为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说的以源于自然的、“范式性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原则为标准的“意识过度的思考者”(overconscious thinkers),除了重视方法之外,还必须接受研究方法的局限性。(29)充分认识和重视比较政治学领域研究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种种问题,将使学习者和研究者理性认识这一学科——它的特性以及由其特性所决定的各种限度,从而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思考者,而不是一个意识过度的思考者。
在比较研究中,研究者既要有方法论意识,还应有方法论理性,对学科研究在不同维度上的限度保持清醒的认识,包括对方法作出必要的改进。选择怎样的案例,选择大样本研究或是小样本研究,定性研究或是定量研究等,是比较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同研究方法和策略各有优点,相对于所研究的具体问题也表现出各自的劣势。于是,探索不同方法和策略间的结合就成为改进方法论的重要突破口。譬如,研究者为了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建立联系已经进行了不懈努力,其中既包括试图将定量研究的逻辑运用于定性研究以使定性研究的结论更为有效的尝试,也有将案例研究与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30)等。在这种意义上,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法论观点被认为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取得进展的最大希望所在。(31)
规范、科学的研究离不开有关方法运用的明确意识,但比较政治学是一门充满或然性的科学,在这一学科领域追求完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完美运用,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一个有意识的思考者也应是一个清醒的反完美主义者。
注释:
①参见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第三章,陈子格、刘骥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D.Collier and J.M ahoney,“Insights and Pitfalls:Selection Bi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49(1)1996:56-91.
③Arend Lijphart,“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8,1975:158-177.
④Dankwart A.Rustow,“Modernizatio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Prospects in Research and Theory”,Comparative Politics,1(1)1968:37-51.
⑤See Dirk Leuffen,“Cas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Bias in Small-n Research”,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eds.,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45-160.
⑥事实上,英国在一段时间内也曾存在类似的现象。塞缪尔·H.比尔(Samuel H.Beer)对可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类似现象的研究,与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对意大利的研究、斯坦·罗肯(Stein Rokkan)对挪威的研究等,一起被看作法团主义早期研究中欧洲阵营(the European Camp)的重要组成部分。See Paul S.Adams,“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s There a New Century of Corporatism?”,in Howard J.Wiarda,ed.,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3[rd] ed.),Boulder,CO:Westview,2002,PP17-44.
⑦See Dirk Leuffen,“Cas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Bias in Small-n Research”,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eds.,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45-160.
⑧Philippe 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in Philippe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eds.,Trends Towards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9.
⑨See Dirk Leuffen,“Cas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Bias in Small-n Research”,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eds.,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45-160.
⑩See Gary King,Robert O.Keohane,and Sidney Verba,“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2(2)1995:475-481;Gary King,Robert O.Keohane,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29-31.
(11)See Adam Przeworski,Michael E.Alvarez,Jose Antonio Cheibub,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Gabriel A.Almond,Russell J.Dalton,G.Bingham Powell,Jr.,and Kaare Strom,eds.,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a world view,(8th ed.),New York:Pearson,2006,PP33-34.普热沃斯基与其合作者所使用的数据截止到1990年,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被纳入其研究,如有着极为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大约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均收入与民主化之间实际上存在相关性,但在其特定背景下,民主化的最好指标似乎是经济改革。Valerie Bunce,“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33(6/7)(2000):703-734.
(12)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宁骚、欧阳景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1页。
(13)See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Introduction:Designing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A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and Data”,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eds.,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18;Todd Landman,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n introduction(2[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27.
(14)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IV(4)1970:1033-1053.
(15)定性研究近年似乎越来越多地被称作质性研究,尽管也有研究者在二者间作了一些区别,但大多数研究者仍坚持质性研究就是定性研究。这里仍使用“定性研究”这一术语,以与中国政治学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习惯使用的定性研究概念保持一致。
(16)See Henry E.Brady,“Doing Good and Doing Better:How Far Does the Quantitative Template Get Us?”in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P53-67.
(17)See Charles C.Ragin,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method,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 Press,1994,P81,P131.
(18)Todd Landman,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n introduction(2[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19.
(19)Larry M.Bartels,“Some Unfulfilled Promises of Quantitative Imperialism”,in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P69-74.
(20)Gary King,Robert O.Keohane,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4.
(21)See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Introduction:Designing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A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and Data”,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uhimmelfennig,eds.,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18.
(22)Gary King,Robert O.Keohane,Sidney Verba,“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9(2)1995:475-481.
(23)See James A.Caporaso,“Research Design,Falsification,and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ivi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9(2)1995:457-460.
(24)David Collier,Henry E.Brady,and Jason Seawright,“Sources of Leverage in Causal Inference:Toward an Alternative View of Methodology”,in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P229-266.
(25)See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New York:Wiley,1970,PP32-33.
(26)Arend Lijphart,“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5(3)1971:682-693;Carsten Anckar,“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 and the Most Different Systems Desig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11(5)2008:389-401.
(27)Charles C.Ragin,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method,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 Press,1994,P105;David Collier,Henry E.Brady,and Jason Seawright,“Sources of Leverage in Causal Inference:Toward an Alternative View of Methodology”,in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P229-266.
(28)See Charles C.Ragin,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Charles C.Ragin,Fuzzy-Set Social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Charles C.Ragin,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29)See 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IV(4)1970:1033-1053.
(30)Even S.Lieberman,“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9(3)2005:435-452.
(31)See David Collier,Henry E.Brady,and Jason Seaweight,“Sources of Leverage in Causal Inference:Toward an Alternative View of Methodology”,in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P229-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