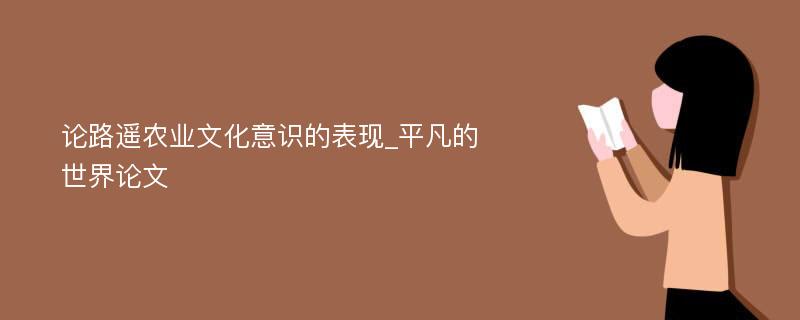
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路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1999)05—0066—05
路遥,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洞察、深邃的主题、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不少感人至深的作品,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那浓浓的儒家农本文化意识更是其创作的精髓,更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永久的魅力。
一、家庭本位:人性善的本源及体现
路遥的生活阅历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作为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民之子,他不能不受深固的亲情与乡土文化的牵制和影响,因此,他最乐于也最善于描写农村生活,描写本土或来自乡间的人们的心灵和遭遇。而在这片土地之上较为浓郁的儒家文化的传播,使作家深深地烙上了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印痕。
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着温暖的人情味,是路遥作品的共性。而透视这种人情,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农村的生活方式、精神内核的洞见与理解,那就是对家庭伦理思想的关注,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里体现得最明显。孙玉厚一家的生活正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传统家庭生活的缩影。孙玉厚赡养母亲、供养弟弟、为儿子操心,无不体现了孝、悌、仁、慈的伦理规范。而懂事较早的少安,虽有别样的人生理想,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又是传统伦理感情和人生义务的承担者。一心追求生命价值的孙少平,无论是在县城求学,还是在黄原打工,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家”。在他们的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怀、体贴、以及建立在尊老爱幼基础上的平等已经成为他们人生感情的重要支柱。这种家庭本位思想,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包含着窒息人性(如压抑个性)的封建毒素,但对农村父老的爱和理解、同情,却使作者宁愿给予另一种诠释:人情。
路遥还表现了家族之外的人们之间的关怀与体贴。他们之间亲情无处不在,关怀体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如美丽善良的刘巧珍,当自己的爱情理想破灭之后,仍然对欲羞辱加林的姐姐巧英说:“要是墙倒众人推,他往后可怎样活下去呀?……”(注:路遥:《人生》,《路遥文集》(1),第192、40、15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并极力恳求高明楼为高加林找一条生路。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爱和宽容!在《平凡的世界》里作者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刘巧珍式的人物——李向前。他痴爱着田润叶,却没有回报,作家借润生之口写到:“两年来,他跟着姐夫学开车,姐夫不理姐姐如何对他不好,却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他。姐夫真是忠厚人,不仅对他家,就是对世人都有副好心肠。……他常对人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多做点好事,做了好事,自己才能活得心安……”(注: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4),308页。)孙少安千辛万苦办了砖窑场之后,雇用了村里许多人,对此,少安是这样想的:“政策是政策,人情还是人情,作为同村邻居,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注: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5),4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则使人性美得以升华。
在对现实关系中多式多样的人的理解上,作者表现出一种包容万物的人生哲理。这种人生哲理的价值,就在于他对农村世态的真切理解。农民以血缘而居,血缘造成了他们的地缘关系,家以家为本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注: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农村基本上没有极端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十恶不赦的恶人,大多是一些既为自己又为他人的人。作家没有在人格的意义上否定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按照惯常的模式将任何一个人置于道德的极端。从乡土政治家田福堂、高明楼、游手好闲的王满银、善于看风使舵的马占胜、孙玉亭,甚至包括傻瓜田二的身上都直接或曲折地闪现出人性的光彩。他们可能有致命的性格、品质上的弱点及生理上的缺陷,但这不仅不妨碍他们成为审美意义上的人,也不妨碍他们成为人格意义上的人,体现出较为深刻的普通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和人生哲学。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52章,作者借少平的感觉表达这样的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注: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3),447,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眷恋、热爱着这片土地。田福堂是中国畸型发达的政治行为的产物,作者对他的针贬显而易见,但当考虑到他只是一个文化程度和职务都很低的农民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超人的智慧和才能。活动的天地、面对的对象和挑战没有使田福堂成为伟大的人物,但他的才智却可以让许多平庸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人生》中的高明楼,他的不道德行为是通过刘巧珍的骂表现出来的:“高明楼心眼子真坏,什么强事都敢做……”(注:路遥:《人生》,《路遥文集》(1),第192、40、15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这是一个有着自私自利缺点的基层干部,但他在处理恋爱事件、漂白粉事件时却也闪现出了人性的美质。
对人性美的阐释,对于路遥来说,则是必然。它不仅是客观现实的产物,也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体悟与认识:“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注:《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第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月第1版。)
二、交叉地带:两种文化的互动
农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美好之处,但对于接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来说,农村毕竟是闭塞、狭小的,外面的世界好大、好有诱惑力。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注:《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第 55 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所以,走出农村,奔向城市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冲动。
17年作家也大量涉及这个问题,如《春种秋收》、《创业史》、《韩梅梅》等,但作家处理时往往采用一边倒的倾向:知青回乡务农是热爱劳动、热爱家乡,而向往城市、奔赴城市是好逸恶劳、忘本叛家的表现。这种模式是农本思想的体现,也是17年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造成的。而到了新时期,路遥率先以《人生》松动了17年的惯常思维。
在《人生》中,作家肯定了高加林向往城市的冲动,并揭示了农村青年到城市后也能大有作为的现实,表明了青年应该到最能发挥才干的地方去。这与17年截然不同。正因为如此,小说敏锐地提出了青年人的“人生”问题,引起了争论,也触及到了当时的敏感神经以及处于思想解放初期的矛盾心理。但这部作品也体现了作家的矛盾:尽管高加林更应该到城市去,但最后还是回归土地;同时,作为高加林离弃乡里的对比与参照,作家又树起了德顺爷爷这个丰碑,又象征了高加林的不该。作家刚刚触及到这个问题,显得惶惑与不安。刚从17年走过,背叛17年那种人生归宿,就显得忧疑与不坚定。但从此之后,也奠定了作家的创作特色,那就是在城乡交叉地带塑造青年人,反映青年人的人生追求。“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发,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注: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文集》(2),第40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在交叉地带的人如何生活与生存,作家起初是困惑的,但随着生活和创作的发展,追求什么、如何追求逐渐走向清晰和坚定。
《平凡的世界》中,作家的矛盾已得以缓释:不管在何处,青年人只要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即可。因此,孙少平、金波、田润生、孙兰香、金秀等均义无反顾地奔赴城市,在城市里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英雄有用武之地,志得意满。这一点与河南人所表现出来的“城市潇洒”中难得潇洒不同。(注:参见拙文:《恋土:一个纠缠着河南作家的情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 2期。)在这里,农村人到都市后并没有堕落下去,而是以农村的美德去生活。如少平对于惠英嫂、金波对于藏族姑娘、润生对于郝红梅、润叶对于李向前甚至包括金秀对于少平也是情真意切,以善良争取爱情,以爱情印证善良,这与有些作家反映农村青年一到城市便堕落相反。农民的善良在城市大放光彩!
随着创作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作家的农本意识在逐渐变化。不再是那种“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4·19》)的守土精神, 也不再是故土难离。乡土精神由物性的粘着于土地转变为灵性的乡土情怀、乡土美质的闪光。与土地的关系由肉体的皈依转为精神的向往,起初土地是裁决人物行为的一种尺度,到后来成为对现实缺憾的一种弥补,成为人性美的标志与向往。“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还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注:《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第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城乡在社会发展、伦理道德、人性人格上有着不同的价值尺度与表现。在城乡关系的把握上,显示出了作家的辩证思维:张扬农民的美质,扬弃农民的缺点;城乡应互补互渗,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就是友谊与婚姻的最佳结构也是城乡结合型,如高加林与黄亚萍、马健强与吴亚玲、孙少平与田晓霞等。这种结合表面是一种友谊与婚姻关系,但在潜意识中却表现出了城乡的差别与互渗:当城市姑娘向农村小伙子表白感情时,小伙子总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而姑娘爱小伙儿,是因为他们勤奋、努力、拼搏,不向命运低头等。小伙子以自己的品质赢得了爱情,姑娘慧眼识英才,爱之所爱,除掉了门第、势力等世俗之见。城乡美质在碰撞中发出耀眼的光彩。
三、男女青年:命运的搏击者
早年家庭的贫困,注定作家的童年生活充满着辛酸。但同时也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与向困难抗争的精神,正是经过努力拼搏自己才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注:《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第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只有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注:《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第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注:《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第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注:《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第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可见, 他对逆境不是恐惧,而是崇拜。
在成长过程中,路遥所感受并接受的是儒墨的“入世”精神,而非道佛的“悟空”、“出世”思想。这不仅使他以后的思想和行为都带有儒家文化的基因,而且也使他的创作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对塑造他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他的笔下,凡是积极奋进、不屈不挠的人物及其行为,总是得到他的赞美。儒家强调“知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14·38》)、“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8·7》),这些思想在路遥的人物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塑造了一系列“落榜或辍学的生活强者”的形象,其中给人印象较突出的有:想走出黄土地成就一番事业的高加林;想依靠自己完成学业的卢若琴;身陷囹圄而不忘学习的冯玉琴,依靠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孙少平;不向困难低头,敢于面对现实,在现实中自强不息的孙少安;不安于现状,勇于追求的田晓霞等等。作者在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描写的同时,赞美的笔触也几乎相映成趣地跃然于纸上。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2章作者写到:“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注: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4),355页。)这是作家的思想的具体表现,同时又是对孙少安创业精神的由衷赞美。第43章里,作家又借少平的口,对积极进取和向上的精神进行了热烈的赞美:“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注: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4),365页。)“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14·35》),尽管少平的追求是盲目的,但作家并没有批评他的盲目性,而对其进取向上的苦行僧式的精神大加赞美。
在这些不向挫折低头、勇于奋斗进取的拼搏型人物身上,明显地寄托并表达了作家积极入世的儒化的人格理想。有时作家格外突出人物可爱的执拗与可杀不可辱的硬汉品格。如孙少平因为憎恶包工头胡永州对在工地上打工的小女孩小翠的污辱与恐吓,就不顾同乡的情面,辞去收入较高的工作,重新加入揽工汉的行列之中;马健强为了自尊而拒绝接受别人的帮助;马延雄为了良心和正义不屑在红总、红指面前低头;以及特写《病危中的柳青》中的“柳青”、作家自己带有象征性的名字“路遥”等等,都显豁地表现出儒家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风范。正是由于这些青年人的努力拼搏,往往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与敬慕,直至爱情。作家笔下的农村小伙子往往都有一位城市知音。这虽有着传统的“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才子佳人的旧模式,但也体现了人人平等的仁义观以及对奋发向上人的赞扬与肯定。
钱穆曾指出:“人生本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使人能成圣人。换言之,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注:钱穆:《中国知识分子》,《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下),第445—4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种将平等主义思想与修身致圣理想相结合的人生理想,可以说正与路遥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相一致,于是也产生了一系列与此相一致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也正是民族性格的继承者和受益者:“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众,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东西。”(注: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在路遥笔下,我们很容易看到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身心上烙有的“礼教”印记,儒家的崇尚道德完善的倾向支配着或约束着路遥笔下的众多人物的言行,妇女往往成为了传统美德的化身。刘巧珍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具有中国传统妇女所有的美德:勤劳、朴实、善良、纯真、忠厚、大胆,对爱情矢志不移并愿为爱情献身,同时,她还有别的农村姑娘难以企及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很不平常的精神追求,为生活在那一方土地上的可亲可敬的女性立下了一块丰碑。《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兰花,也是一位贤淑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对丈夫王满银这样一个四处游荡、不务正业的流浪汉总是极尽妇道,毫无怨言,即使亲眼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另外的女人同床共枕,竟也能容忍,真是贤慧之极?!杜丽丽这位敢尝禁果的现代女性,也时常被痛苦折磨得一塌糊涂,最终落个与丈夫离婚的结局。即使是田晓霞、吴月琴、吴亚玲这样的颇有现代女性品味的女学生、女知青,行为仍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这表明作家在努力将传统与现代做某种程度的结合,我们从作家展示的一些性际关系的描写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这种“交叉”型的心态。
在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中两性关系往往更加复杂,更为牵动人心。路遥虽然反感于儒教的男女之大防、“授受不亲”等许多清规戒律,但对广泛而复杂的性际关系,还是慎重地给以区别对待的。如《生活咏叹调》中,便将男女之间那种“广义”的朋友关系(尽管有时有辈份之差,有朦胧恋情)视为相当珍贵的性际关系,这里显示了作家的敏感以及些微的“柏拉图”色彩。对卢若琴之于高广厚、吴亚玲之于马健强、孙少平之于惠英嫂的关系处理,也是这样,着重从助人、善良等道德范围着眼。但对那些较远地游离了传统女性规范的人物,如黄亚萍、贺敏皆被置于第三者的位置上,连同他们的穿戴、爱好和谈吐也往往给予了否定性的描写,有时甚至明显地带有讽刺和嘲笑。
很多描写表明,路遥对现代文化的态度,在经济生活的改革方面比较大胆,在道德观念的更新方面显得比较谨慎。对于田润叶不接受李向前、孙少平不接受金秀、杜丽丽既爱丈夫武忠良又与古风铃关系暧昧等,作家显得顾虑重重,有时甚至走向了极端。在《平凡的世界》中的婚姻往往是非常态的。田润叶之于李向前(起初不爱,当向前截肢后才同居)、田润生之于郝红梅、孙少平之于惠英嫂(寡妇虽无可厚非,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是非常态的女性)、孙兰花之于王满银(有爱情,但更多一些从一而终的贤淑)。这些婚姻产生的基础很难说是爱情,往往缘之于同情,由同情而生怜悯之情。而常态婚姻往往要夭折:杜丽丽与武国良(离婚)、孙少平与田晓霞(晓霞因救人而牺牲)、孙少安与贺秀莲(秀莲得了肺癌)。这种婚姻结构显示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对非常态婚姻的认同反映了青年人的善良与对命运的抗争;常态婚姻的夭折给人提供了修炼自己的契机,使人更臻完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9·28》),但未免过于凑巧和概念化。 从现代爱情观看来,同情并不等于爱情,虽然农村的婚姻乃至中国的婚姻事实往往是“先结婚后恋爱”,但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完全认同更不能赞同这种事实,过于良善而委曲了人性的健康、茁壮发展。如果说路遥的妇女观基本上是传统的,带有明显的保守性,这并非虚言。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注:傅立叶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马克思也同意此观点。)而路遥笔下流露出来的传统文化的男性中心倾向,恰好证明了他至少在道德领域的许多方面,仍处在儒家的妇女观的影响下,有时甚至流露出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的倾向。历史上儒家思想浸入人们心灵的这种积淀,对于作家,对于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沉重的,这未免使文明的发展更艰难。
收稿日期:1999-06-15
标签:平凡的世界论文; 路遥文集论文; 文化论文; 路遥论文; 陕西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人生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孙少平论文; 高加林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