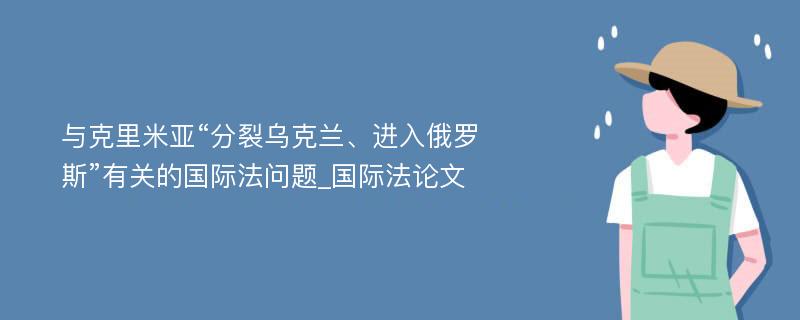
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里米亚论文,国际法论文,事件论文,脱乌入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乌入俄”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家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还随即履行了国内相关的批准程序。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则表示强烈反对,不仅不予以承认还启动了对俄的一系列外交和经济制裁措施。2014年3月27日,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等国起草的一份题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00个国家投赞成票,俄罗斯、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等11个国家投票反对,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乌兹别克斯坦等58个国家弃权。①虽然决议获得简单多数通过,但仍有近70个国家投了反对票或弃权,另有20多个国家没有参加投票。可见各国对于克里米亚公投所持的立场存在很大的分歧。 撇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因素,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不可避免地涉及一连串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问题:民族自决能否为克里米亚公投提供国际法依据?民族自决原则适用的具体情形是什么?一个现有主权国家内的部分地区或民族是否享有自决权?如何处理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与民族自决的关系;当二者发生抵触时,何者优先?2010年科索沃独立是否可以作为克里米亚仿效的先例,甚至是其他国家特定地区或民族仿效的先例?什么样的公投才是合法和有效的民族自决方式?下文笔者试图从实然国际法及其实践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阐述和回应。 一 民族自决原则适用的范围问题 民族自决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民族自决成为苏联的一项民族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间,民族自决原则曾促使奥匈帝国的瓦解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独立。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中曾包含了民族自决原则,但是丘吉尔将其解释为只适用于欧洲国家及纳粹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政府,不适用于殖民地。②《联合国宪章》首次以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章程的双重法律形式确立民族自决原则,第1(2)条明确规定,“发展国家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并将民族自决的含义主要限定为“自治政府”并作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目标。但是,宪章并没有对各国就民族自决施加具体而又严格的法律义务。③此外,《联合国宪章》第73条规定,“促进非自治领土及其人民自治,并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渐发展”;第76条规定,“增进联合国托管领土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 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宣言促使民族自决从一项法律原则迅速地演变为一项具体的权利,④尤其是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首次明确规定殖民地人民享有独立的权利,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去殖民化运动。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以下简称为《国际法原则宣言》)再次宣告,“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而且“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自决权之方式”。但是这里的民族是何含义?是特指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和殖民地人民还是泛指任何意义的民族?这些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一再确认自决权概念,但是并没有规定清楚的定义、厘定严格的权利和义务界限。 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开启了通过人权条约确立民族自决及其适用范围的新时代。该两公约的共同第1条规定: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二、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三、本公约缔约各国,包括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应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决权的实现, 并尊重这种权利。” 上述第1条规定的民族自决权是一种“持续性权利”(continuing right),并不是由公约所创设的。⑤最初第1条的条文草案的措辞是“所有人民应有自决权”。最终的文本将“应”(shall)字删除。显然,这一修改旨在强调民族自决权是一项固有的和持久的权利。根据上述第1条的规定,民族自决权在国际法上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基本含义: 第一,各国人民享有不受外部干涉自由地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及政治机构的权利,人民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决策。此即“对内自决”(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因此,两公约禁止一缔约国以严重违反另一缔约国“自由确定其政治地位和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方式干涉另一缔约国的内部事务。这实质上进一步强调各国相互尊重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一习惯国际法原则,并且禁止缔约国以剥夺其他缔约国人民自决权的方式侵略和占领其他缔约国领土。 第二,各国人民享有表达大众意愿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言论自由(第19条)、和平集会的权利(第21条)、结社自由(第22条)等等。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上述具体权利与民族自决权相关,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权利也是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是特定的法律概念。 第三,各国人民享有控制其本国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并从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行使自决权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物质基础。当然,人民控制自然资源和享受资源财富的权利也要受到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约。例如,本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应妨碍旨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国际条约或协定的实施或与之相抵触,并不得违反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第四,附属国或附属地人民享有自由决定其国际地位的权利。显然,这里规定的附属国或附属地是特指殖民地或尚未获得独立的非自治地区或置于托管的领土。对这类领土或地区的人民而言,其自决权包括自由选择成立独立国家或并入一个现有的主权国家的权利。值得强调的是,自民族自决原则确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一大批殖民地或附属地人民先后选择成立独立国家,大大地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殖民主义制度瓦解的步伐,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基本秩序和结构。现在,殖民地已基本不复存在,民族自决原则这一层含义的现实意义已经十分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两个基本人权公约,或是联大通过的有关决议,都没有就自决的“民族”(Peoples)作出明确的定义。那么,到底什么民族或何种类型的民族享有自决权呢?一般说来,每一项涉及民族自决的国际法律文件对其适用的民族都有特定的范围。例如,区域性人权条约中所指的民族限于该区域内的民族,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的民族限于尚未获得独立或非自治领土区域的民族。就《联合国宪章》和两个基本国际人权公约而言,其所指的民族的范围是广义的,主要包括:(1)生活在一个独立国家的全体人口;(2)尚须取得独立之领土上的全体人口;(3)生活在外国军事占领下的人口。⑥ 那么,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是否适用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少数民族或族群呢?比如,如何理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该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该条文的含义非常明确:第一,该条所规定的权利是针对作为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人,而不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第二,该条没有包含少数民族整体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自决权利,其列举的权利仅限于文化、宗教和语言的自由,即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保持其民族身份或特质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是个人权利,并非民族自决权的范畴。这一断定在该公约起草过程的有关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为参与该公约谈判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如果授予一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权,势必造成现有主权国家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⑦ 冷战结束后,民族自决原则的适用范围或情势呈现出新的情形。典型的实例就是科索沃的独立与国际社会较广泛的承认。众所周知,科索沃原本是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解体后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其居民绝大多数为阿尔巴尼亚族人。该少数族群声称并有证据表明在前南内战期间遭受了塞族军队的种族清洗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因而主张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国民大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成立科索沃共和国。虽然科索沃的独立立即获得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承认,但同时也遭到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同年10月,联大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问题发表咨询意见。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就此发表意见,但是回避了包括自决权在内的诸多实质问题,只是认为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并独立建国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⑧因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不构成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先例。 二 国家领土完整与民族自决的关系问题 正如国际法院在科索沃咨询意见中所确认的,“领土完整原则是国际法律秩序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联合国宪章》第2(4)条中赋予神圣的地位”,“领土完整原则的范围限定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⑨领土完整概念的核心就是国家拥有和有效统治的领土不可侵犯。在国际法上,领土完整概念从一开始就与主权概念密不可分,这是因为领土是国家的基本要素,甚至是第一要素。此外,领土完整与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紧密相连,因为依据现代国际法,除非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自卫,其他国家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破坏或损害一国的领土完整。⑩ 除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的判例之外,领土完整原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联大通过的有关决议中多次得到重申。例如,1960年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称,“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以使他们能和平地、自由地行使他们实现完全独立的权利;尊重他们国家领土的完整。”“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更是开宗明义地确认,“国家领土不得作为违背宪章规定使用所造成之军事占领之对象。国家领土不得成为他国以使用威胁或武力而取得之对象。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并在正文多处重申“各国负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上应避免为侵害任何国家政治独立或领土完整之目的”,“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目的之企图,均与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197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不使用武力剥夺他国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或破坏其领土完整”,并重申“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即构成“侵略”。 可见,国家领土完整在国际法上具有神圣地位,除非国际法允许的特殊例外,各国都应予以尊重,不得破坏或侵犯。然而,随着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和民族自决原则的确立,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家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兴起,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国家“领土完整原则过时”的论调。认为领土完整应让位于民族自决原则和尊重人权原则。(11)尽管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占据少数,但是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如不予以澄清和驳斥,势必误导社会和公众。 如上所述,国家领土完整是近代国际法早已确立的原则,具有习惯法和条约法的双重法律基础。经过全球最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章程的确立和一列重要决议的进一步重申以及国际法院的确认,领土完整原则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国际法上确立的民族自决原则要比领土完整原则晚近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自决原则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如领土完整原则,反之亦然。应该说,二者在国际法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上述有关的联大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均同时宣告或重申二者的国际法律地位。即使在确立民族自决原则和权利的情况下,国际法仍然赋予领土完整以中心地位。例如,在非殖民化时代,殖民地人民在运用民族自决原则实现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同样应尊重领土完整原则。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今天非洲联盟的前身)在支持非洲民族政治独立的同时,充分顾及到维持原殖民地边界对于各个新独立国家领土和边界稳定的重要性。(12)诚如克劳福德(James Grawford)教授所论述的,“现有国家的民族以符合维持这些国家领土完整的方式行使自决权”。(13) 领土完整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存在性质上的不同或法律阶位的区别,二者都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并具有强行法性质。二者的区别在于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领土完整是国家及其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行使有效统治和管辖的法定空间。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才能保证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正常的交往与合作。正是由于领土完整对于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至关重要性,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国家不高度重视国家的领土完整。在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中,领土安全无疑处于首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建立和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始终如一地坚持各国领土完整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地位。 在国际人权法的语境中,民族自决权着重体现国际法的人本价值,从集体人权的角度强调现代国际法除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之外,同时还应维护人民或民族的根本权利。这个根本权利就是各国人民或民族自由选择独立或并入其他国家或其他政治地位的权利,以及保持民族特色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自主的权利。可见,民族自决权适用的主体和情形,一般是指现有主权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殖民地人民和民族的“对外自决”和“对内自决”。 那么,民族自决原则的适用是否必然影响国家的领土完整呢?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对内自决权”不会对一国的领土完整构成影响,因为它不会改变现有国家的版图或统治范围。相比之下,一个民族的“对外自决权”会对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殖民地人民独立建国势必导致原宗主国领土的减少。再如,一个国家特定区域或民族独立建国或从原属国中分离且并入另一个国家,也会发生领土变更,即其原属国的领土范围必然随之缩小。一般说来,殖民地独立对原宗主国领土造成的影响是现代国际法所认可的。撇开政治因素,单纯从法律角度来判断,凡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民族自决而产生的领土变更,无可非议,并应予以承认;凡是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民族自决而引起的领土变更(如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甚至制裁,并不予以承认。 三 公民投票的国际监督问题 美欧指责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克里米亚公投缺乏乌克兰全民参与和国际组织的监督,从而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克里米亚则宣称,它曾口头邀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观察员监督公投,但遭到后者的拒绝。欧安组织认为,欧安组织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克里米亚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国,无权请求派遣观察员。尽管如此,仍然有来自23个国家的135名观察员、1200多名当地观察员和来自169家国际媒体的600多名记者现场观摩了公投。(14)那么,在国际法上,何种公投方式是合法有效的呢?公投是否必须有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的参与才能合法有效?国际组织的监督是否为公投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必备条件? (一)必须指出的是,公民投票或全民公决自近代以来不仅成为一些国家决定本国重大事项(如领土归属、国家分离或合并、缔结重要条约、加入重要国际组织等)的一种民主方式,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组织为确定有争议领土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常用途径。公民投票作为一种民主决定的形式,有的国家通过宪法予以明确规定,有的则通过立法机构的决定作出。(15)因此,凡是符合一个国家宪法或法律规定的公投,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毋庸置疑,存在争议的通常是缺乏宪法或法律依据的公投。 (二)国际法并没有就公民投票或全民公决作出一般性或专门性的具体规定。在实践中,通常由国际组织的有关机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形通过决议的方式作出举行公民投票的决定或建议。例如国际联盟的行政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多次通过这种形式建议有关有争议地区就其政治地位举行公投。 (三)尽管国际法上并未规定公投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具体标准,长期的国际实践还是形成了一些普遍遵行的原则。(16)首先,公投应具有参与的普遍性或广泛性,即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有关地区公民或民族普遍参与的行动,而不是部分甚至是少数公民参与的行动。其次,公投应以和平方式举行,不应有任何外部力量干涉或干预,尤其是禁止武力干涉或武力威胁。最后,公投应以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方式进行。 (四)有关非自治领土(殖民地、国联委任统治领土、联合国托管领土)政治地位的公投,只需当地居民的参与,而无需原殖民国家或宗主国的参与。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除了符合上述(三)中阐述的诸项原则之外,还必须在有关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下举行,这已成为自国联以来普遍一致的国际实践。 (五)涉及既有国家的特定地区或民族政治地位的公投,如果是该国家公民的整体参与,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只有当地居民的参与,而且缺乏明确的国内宪法或法律的规定,所属国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其合法性通常引起争议,这就是克里米亚公投受到一些国家质疑的关键所在。 (六)关于公投的国际监督,国际法也没有作出一般性的规定,而是视具体情形而定。如上述(四)所述,有关殖民地独立、非自治领土和有争议地区政治地位的公投,通常是在国际组织派遣的观察员监督下进行的。缺乏国际组织的监督,有关公投的公平性、公正性和透明度自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至于现有国家部分地区公民投票举办方自行邀请其他国家、国内民间社团、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现场观摩或监督,是否可以作为国际组织监督的替代,在缺乏实然国际法和先例的情况下,其有效性引起争议就不足为奇了。 四 国际组织介入的涉及民族自决的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先后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介入下的一些涉及民族自决的典型案例,不仅为确定一些长期存在争议的地区或民族的政治地位、从而维护有关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促进了关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法理论的不断完善。 (一)国际联盟介入的涉及民族自决的案例 在国联时期,有两件涉及民族自决的案例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一是阿兰群岛案,二是萨尔区案。 1.阿兰群岛案 历史上,阿兰群岛在瑞典和芬兰联盟时期属于芬兰管辖,芬兰取得独立后,两个国家都对该群岛主张享有领土主权,并提到自决的法律问题。1920年,在常设国际法院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国联行政院将这一问题提请一个临时任命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和审议认为,自决概念在当时并不能被认为是实证国际法所确立的一部分,至少在通常情况下法律的“必要根基”是主权,然而缺乏稳定的主权的情形下,法律情势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一模棱两可的情况是“由事实转变为法律,从事实情形转变为正常的法律情形……在此类情况下,自决原则是可以适用的”。根据这一咨询意见,国联建议阿兰群岛依旧属于芬兰的主权之下,但同时也要求芬兰必须提高对该群岛自治的保证。最终芬兰和瑞典都接受了国联的建议。(17)2004年,在芬兰加入欧洲联盟时,阿兰群岛的高度自治地位再次得到确认。 2.萨尔区的公民投票 一战之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萨尔区委托给法国和英国占领和管理。1934年6月4日,国联行政院批准了阿洛伊西委员会(the Aloisi's Committee)提出的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建议,并成立了一个组织公民投票的委员会。在国联行政院授权的一支国际部队的监督下,该区公民投票的结果是:90%的选民投票赞成回归德国。国联理事会据此通过决议,萨尔区于1935年3月1日并入德国。(18) (二)联合国介入的涉及民族自决的案例 1.厄立特里亚的独立 厄立特里亚原本是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宣布放弃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1950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自治体同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1962年,埃塞俄比亚强制取消联邦制,将厄立特里亚合并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导致厄立特里亚人民长期为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1993年4月23-25日,在联合国的斡旋与监督之下,厄立特里亚举行全民公决,以绝对多数赞成厄立特里亚独立。同年5月24日,厄立特里亚正式宣告独立。(19) 2.北塞浦路斯独立问题 塞浦路斯于1960年8月16日宣布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由南部的希腊族和北部的土耳其族组成联合政府,并于1961年3月加入英联邦。此后,两大族群之间武装冲突连绵不断。1983年11月15日,北部的土耳其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而塞政府坚决反对土族独立,欧盟和美国等国也明确宣布不予承认,唯一给予承认的国家是土耳其。从1975年起,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斡旋。2004年,塞浦路斯就联合国提出的统一方案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该方案未能获得通过。虽然北部土耳其族人多数赞成该方案,但希腊族占主导地位的南部投了反对票,从而宣告了联合国斡旋的失败。(20)2004年5月1日,受到国际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南部希腊族控制)正式加入欧盟。 (三)国际法院裁决(或发表咨询意见)的涉及民族自决的案例 1.西撒哈拉独立案 西撒哈拉原为西班牙殖民地。1973年5月“西撒人民阵线”决定通过武装斗争争取西撒哈拉独立。与此同时,其邻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也反对西班牙对西撒哈拉的统治。1976年2月27日,“西撒人民阵线”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此后,摩、毛军队与“西撒人民阵线”的武装力量不断发生冲突。1979年8月,毛里塔尼亚放弃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退出西撒战争,摩洛哥则乘机占领了毛里塔尼亚退出的地区,从此摩洛哥与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负责监督双方停火状况,并组织让西撒哈拉人民决定该地区未来地位的公民投票。但是,由于冲突双方在确定选民资格等重要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公投一直没有举行。在此过程中,联合国大会曾于1974年通过第3292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西撒哈拉是否为无主地以及该地区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之间法律联系的性质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法院在其意见中首先指出,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大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决议来解决。法院进一步指出,宪章第1(2)条确立了国家间关系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并通过1960年联大通过的第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这些条款和文件为非殖民化运动提供了法律基础。法院确认,根据民族自决原则,非独立领土可以自由选择三种法律地位中的任何一种:(1)形成为主权国家;(2)与现行独立国家自由组合;(3)与现行独立国家合并。(21) 2.布基纳法索诉马里边界争端案 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在独立前同属于法属西非殖民地,1960年两国先后获得独立。独立后,两国很快就设立了双边机构以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并顺利划定大约三分之二的边界,但在东部仍有约300公里的边界未能达成一致,并曾因此引起武装冲突。1983年9月16日,两国签订特别协定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在该案中,虽然国际法院分庭的使命是裁决两个当事国之间的边界,但是裁决书中对于民族自决权要素的界定和对殖民地边界不可改变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法院裁定,表面看来殖民地边界不可侵犯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之间必有抵触,然而,实际上维持非洲领土现状通常被视为最明智的行动方向,从而维护各民族为其独立而斗争所获得的成果,并避免对于经巨大牺牲而获得的大陆之干扰。为了殖民地民族的生存、发展并逐步在其所有领土上巩固其独立,稳定这一必不可少的要求促使各非洲国家明智地同意遵守殖民地边界并将在解释民族自决原则中予以考虑。(22)本案的裁决再次表明,领土完整原则在实施民族自决过程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要求。 3.东帝汶案 东帝汶原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960年被联大宣布为非自治领土,由葡萄牙管理。1975年,印度尼西亚武装入侵并控制东帝汶,葡萄牙被迫撤离。1989年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签署联合勘探开发帝汶海大陆架资源的条约。葡萄牙认为澳大利亚此举侵犯了东帝汶非自治领土的地位和葡萄牙作为管理者的权利,并在国际法院起诉澳大利亚。虽然印尼对于案件的主题事项具有直接的关联,但它拒绝作为案件的第三方参与审理。尽管国际法院以此为由拒绝对案件的实质事项作出判决,但是法院有关民族自决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法院确认,民族自决是“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进一步将其归于“对一切的义务”,(23)从而具有强行法性质。这就意味着国际法院认定民族自决权构成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从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国际法院的判例表明,民族自决权不仅与有关的领土相联系,而且还包括自由选择其认定为合适的治理方式。 4.科索沃独立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索沃独立咨询案中,国际法院对于国际法是否赋予一个现行国家内的部分人口享有自决权或者所谓“救济性分离权”的敏感问题,巧妙地予以回避,认为没有必要回答,理由是联合国大会请求咨询的问题中并没有提及这些问题。国际法院的做法是,分析和阐释科索沃局势的形成过程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通过考察从近代到当代有关新独立国家及其国际承认的实践,得出一般国际法并不禁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结论。法院认定,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有大量宣布独立而遭到被分离国反对的事件,其结果是,有的导致新国家的产生,有的则不曾如愿,但实践表明国际法并没有产生禁止宣布独立的新规则,因此法院认为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不违反国际法。(24) 五 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概括性的认识: (一)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从确立到演进与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它作为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由《联合国宪章》首次确立;作为一项国际法权利,先后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联大一系列重要决议予以确认,但是其适用范围仍然有争议。 (二)民族自决比较确定的适用包括以下情形:(1)现有国家的人民自由选择其政治地位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2)殖民地人民、被外国占领和统治下的人民自由选择独立、并入一个现有的独立国家或其他政治地位的权利。 (三)在国际法上,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领土完整原则有着密切关联。二者都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组成部分,同属国际强行法性质。但是,二者在不同的国际法语境下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国家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概念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且是第一要素,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物质基础;民族自决在形成和演进过程中侧重于国际法的人本化价值取向。“对内自决权”的行使对国家领土完整不构成影响,而行使“对外自决权”则一般会带来变更现有国家领土的结果。 (四)长期以来,民族自决在实践中引起争议最大的当属现有国家的少数民族或某些地区的“对外自决”问题,这直接影响到现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一方面,虽然国际实践不尽一致,但从现有国际法来看,不构成人民的现有国家的部分区域人口或少数民族并不享有国际法上的自决权。他们只有在遭受国内政权长期地一贯地大规模地粗暴地侵犯人权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形下,并且在没有任何外来武力干涉、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并且在国际组织的有效监督下,通过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公民投票方式作出的关于他们自己政治地位的决定,才有可能获得国际上的广泛承认。 (五)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折射出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在现实中矛盾的一面。在这一事件中,俄罗斯阵营和美欧阵营之间出现的分歧甚至对立,不仅仅涉及合法性问题,更牵涉到双方的价值取向和重大战略与核心利益的冲突。在缺乏获得普遍承认的国际先例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对于这一事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实属正常。如果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就克里米亚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扔给这个国际司法机构的势必是一个“烫手山芋”:它或者作出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相同的意见,即现行国际法并不禁止克里米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和并入俄罗斯;或以克里米亚不存在类似当年科索沃存在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认定其公投损害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不符合国际法。归根结底,克里米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借助国际法,但关键还取决于有关各方的政治智慧。 注释: ①General Assembly,General Assembly Adopts Resolution Calling upon States Not to Recognize Changes in Status of Crimea Region,GA/11493,March 27,2014,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14/ga11493.doc.htm/(last visited March 31,2014). ②《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7-338页。 ③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65. ④Patricia Carley,"Self-Determination,Sovereignty,Territorial Integrity,and the Right to Secession",Report from A Roundtable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s Policy Planning Staff,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Summary,Peaceworks No.7,March 1996. ⑤See Comment made by the Chairman of the Working Party of the Third Committee when presenting the draft to the Third Committee,UN Doc.,A/C.3/SR.668.,para.3. ⑥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p.59 and pp.61-62. ⑦参见[奥]曼弗雷德·诺瓦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第2版),孙世彦、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62-665页。 ⑧According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kosovo,I.C.J.Advisory Opinion of 22 July 2010,para.121. ⑨According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kosovo,I.C.J.Advisory Opinion of 22 July 2010,para.80. ⑩Michael Wood,"Territorial Integrity",in Princeton Encycoldedia of Self-Determination,http://pesd.princeton.edu/? q=node/271/(last visited March 31,2014). (11)Michael Wood,"Territorial Integrity". (12)Michael Wood,"Territorial Integrity". (13)See James Crawford,"State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Relation to Secession",(1998) 69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85,p.85. (14)"Crimea Referendum:Voters 'Back Russia Union'",in BBC News,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606097/(last visited March 31,2014). (15)Yves Beigbeder,"Referendum",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Article last updated:June 2011,http://opil.ouplaw.com/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088? rskey=3j7BpG&result=1&prd= EPIL/(last visited March 31,2014). (16)Yves Beigbeder,"Referendum". (17)See Norman J.Padelford and K.Costa A.Andersson,"The Aaland Islands Question",(1939) 33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65. (18)Yves Beigbeder,"Referendum". (19)Yves Beigbeder,"Referendum". (20)Yves Beigbeder,"Referendum". (21)Western Sahara,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5,Summary. (22)Frontier Dispute(Burkina Faso v.Mali),Judgment,I .C.J.Reports 1986,p.554,para.567. (23)Case Concerning East Timor(Portugal v.Australia) Merits,Judgment,I.C.J.Reports 1995,p.102,para.29. (24)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2010,Summary,paras.79-84.标签:国际法论文; 克里米亚论文; 法国殖民地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联合国宪章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