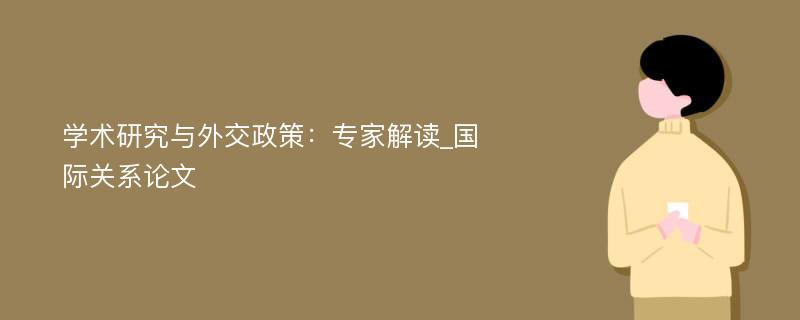
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专家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学术研究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质量的研究不必在意直接政策效果 周弘
在全世界的欧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两种研究风格,一种是进行纯理论研究,一种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
但是必须注意到一点:理论发展和方法论研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讲,如果想在学术上有所发现,必须做实证研究。而所有的实证研究都会涉及政策问题,我们不可能脱离政策问题而做实证。即使不是为了给政府出谋划策,学术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政策。学术和政策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桥梁就是实证研究。
我自己一直在做一些实证研究,例如社会政策、对外援助等。这种研究是学术研究,但很自然地会有政策影响力。同时,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会有某种理论视角,理论就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有效工具。
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逻辑。有一种政策研究是就事论事的,与任何理论、流派都无关。但是这种研究效率不高,只能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无法直接产生出可积累的优质知识。更好的政策研究还是需要有一定学术性,它不一定能够直接指导政策,但有利于产生好的战略。
至于学术研究是不是应该影响外交政策,如果年轻时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会说,谁做研究不想影响政策?但是现在我已经50多岁,影响与不影响已经不重要了,能够积累和生产出新的知识就可以了。
影响政策需要很多因素,例如知识和理论要在合适的时候提出来。我20年前就在呼吁社会政策,但是没有回应;现在却水到渠成,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关注我的研究成果或前来进行咨询。学者做研究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不必过于在意是否在当下就能产生直接的政策效果。
不同的制度背景制约着学术与政策的关系
[比利时]斯坦利·克罗希克著
范勇鹏译
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学者都在对外交政策事务进行深刻的思考,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文献。这是必要的,有利于我们提高对外交事务的认识,提高对外交决策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背景的理解。然而,学院式的研究对外交政策制定的直接影响在不同的情境下却是效果迥异。
学术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是难以衡量的,然而却并非不可估测。在中国,多数智库和学术研究机构都是党政系统的一部分,决策者可以经常而方便地借重于这些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有充分的经费,且与政府之间保持着良好而及时的沟通互动。很自然,中国的理论学术研究显然直接有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
在美国,智库和学术机构不是政府部门,但是有两个因素决定了它们会对政策发生影响。其一,由于美国政治的任期制。每过4年或8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决策人士在“庙堂”和“江湖”之间上上下下。一项新的任命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而一旦被任命,官员的政治任期却并不长。其二,美国的“旋转门”使很多学者进入政界。优秀智库和重要政府部门的领导几乎都出自同一群人。这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得到了智库的充分支持。
欧盟的情况或许是个特例。研究欧盟的智库和学术机构总体看来资源有限,而且欧洲的学者有一种学院化倾向,他们更强调增加社会的知识生产,不太重视公共政策问题。因而,他们与欧盟的政策制定之间互动较少,不如中、美两国研究界与政策决策之间的关系紧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欧盟的外交政策决策主要还是在成员国层面上完成,而欧盟层面上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很难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它们的学术研究因而也就更难以对欧洲外交政策发生大的影响。
(范勇鹏/译)
学术与政策之间,需要理顺三对关系苏长和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能够发达到政府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将其成果信手拈来、转瞬即用的地步。要理顺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摆正三对关系:
其一,“上”学与“下”学。最好的策论研究总是与坚实的基础理论分不开的。好的理论能够加深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给我们反直觉的知识或者推翻流行的常识性知识。社会科学自有其形而上的成分,有其不为凡人熟悉的逻辑与原理。但是,这些学科每一次理论范式的超越与突破,都与时代变迁共生。最好的形而上的知识,是能够顺应历史和时代之潮流的,学者和政治家由此可以顺势而为。学术和政治的完美结合,往往会造就伟大的思想家和国务活动家,中外历史,概莫能外。
其二,“实”学与“时”学。“实”学讲究客观的调查、真实的数据与确证的逻辑,不可以“毛估估”与“差不多”就完事;“时”学则强调研究必须跟上时代变迁,发挥科学研究的政策服务和社会服务功能。理论之“实”学与政策之“时”学应该紧密相关,“时”学一定要建立在牢靠的“实”学基础上。
其三,“慢”学与“快”学。政策研究是“快”学,有的时候甚至是应急之学,哪里起火了首先得把火灭了,灭火的时候还在讲理论,那是迂腐。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要是一味被“应急赶快”所牵制,就会少了冷静的判断。因此,政学各有分工,不能相互取代,这是良好的政学生态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需要比慢,要有“三年不窥园,十年成一赋”的慢功。政府的课题支持倾向于功用,合情合理,但是也需要支持看上去似乎没有用的基础性研究。有了基础性研究的积累和支撑,政策的应急之学就会不失宏谋远虑,不为事态变化而摇摆,学术和政策之间就可以做到相互滋补、相得益彰。我注意到,近几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际问题研究类的课题指南更多地以政策研究为主,对学科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的基础研究类课题似乎有减少的趋势,这一点需要扭转。
关键是要跳出西方理论,说“中国话” 王义桅
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美国也许是老生常谈了,学界一直纠缠于“理论指导实践,还是实践产生理论”这种“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在中国,问题就简单多了:两者泾渭分明。究其根源,可作三方面假设:
假设一,没有外交理论,只有外交实践。如果命题成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便很简单,便是有和无的问题,只有等将来外交实践提炼出理论来,才能谈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情形,说中国没有外交理论,恐怕是不公平的。这种假设并不成立。
假设二,理论是普世的,而实践是国别的。如果命题成立,只有外交理论指导实践的份儿,充其量不过是如何将西方普世性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践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外交理论指导不了中国外交实践。因此,这种假设也不成立。
假设三,理论是灰色的,外交实践常新。如果命题成立,只能得出“外交理论滞后于外交实践”的结论。另一个可能结论就是中国外交是有特色的,外交理论也具有中国特色,随着外交实践而与时俱进。实际情形似乎印证了前一结论,但后一结论则不然。中国外交实践丰富多彩,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却并未出现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总体上看,这种假设难以描述中国情形。
既然这三种假设都不大成立,问题就出自假设本身。中国的问题,并非纠缠于理论与实践的上述三种假设。根本原因是,中国并非民族国家,也不处于西方外交理论所依赖的线性进化的特定阶段。这就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难以用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衡量。中国外交自始至终都是内政的延伸,只不过最近30年来贯穿“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时代线索而已。
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和外交操作的三位一体,体现出外交文化、外交机制和外交艺术的辩证统一。换言之,外交政策是打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实现前景是学术政策化和政策学术化。
所谓学术政策化,特指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外交理论的政策取向,即从理念上包装、从逻辑上阐释好外交政策,使之合理、合法。所谓政策学术化,特指外交政策既要坚持又要超越中国特色,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沟通,感染和说服国际社会。
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而是不敢追求自己的理论,在无休止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乐此不疲地去研究人家的理论;或有一定的自我认识,但不了解中国的外交实践与机制,难以真正参与政策研究,有效地将理论、理念转化为外交生产力。从外交政策方面而言,也有经验性等制约,致使理论与政策成了“两张皮”。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有两条:一是做真正的学术,提出“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系统学说,阐明“世界的中国”;二是发展真正的政策,把握时代脉搏,服务中国崛起,规划“中国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有可为,关键是学术研究要说中国话、体现中国思维、折射中国情结。
三类知识有助于政策制定于铁军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知识类型。宏观体系理论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必然距离现实世界较远,距离对外政策的制定也较远。我认为有三类知识与政策制定更加相关:其一,历史案例。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历史类比的方法。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历史知识大多(除了丘吉尔和毛泽东等少数外)都不及格。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者的作用便很重要。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刚刚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他既是美国最好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也有效地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F.H.Hinslev。其二,中型理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Alexander George一直在提倡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索中型理论在对外政策中的应用。这种类型的理论可以为政策提供四个方面的指导,即诊断情况、预测发展、“开药方”和事后评估。其三,地区和国别知识。理论能够提供共性,但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常要遇到关于某个国家和某个地区的知识。“临上轿现包脚”是来不及的,这就需要有长期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圈的一些重要智囊型人物,不少都是专门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例如研究中国问题的白鲁恂、奥克森博格和李侃如,研究日本问题的赖肖尔和格林,以及研究俄罗斯问题的MaCfaul等。
真正做好研究才能更好影响政策 孙学峰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大规模引进科学方法。此后,政治学的专业门槛逐渐提高,其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对立性也日益显现。国际关系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关系和解决之道的探讨一直未曾间断,其主流观点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越来越深奥,方法越来越复杂,但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却日益衰微。因此,学术界应当作出改变,强调学术研究要满足现实需求。在设定职称晋升、期刊录用等标准时,充分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历来较为重视研究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并不一样。美国的问题是学科专业化程度强,学术门槛高,但不重视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而中国则是学科的专业化水平还较低,学术研究的质量仍有待提高,研究成果难以满足政策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越重视研究的现实意义,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对立就越突出,主要原因在于过分突出研究的现实意义,会阻碍国际关系研究专业化水平的实质性进步,加剧低水平重复现象,而学术研究质量的停滞反过来会降低学术研究在政策界的声誉,加剧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对立。
因此,要缓解当前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对立,首要任务是切实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研究质量,推动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具体的努力方向包括:一是推动实证理论研究。其核心目标是发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经验困惑,提供理论解释,并运用经验事实和相应的方法对理论解释进行可靠的检验。这类研究能够提供分析国际关系现象的基本原理和逻辑,促进知识积累,提高专业化程度。二是推动国际关系历史过程的研究。其核心目标是展现国际关系领域中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提供历史细节,并运用可靠的史料加以支撑。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这类研究能够提供历史细节和经验,拓宽当代学者的分析视野。对于实证理论研究而言,扎实可靠的历史过程和细节研究会大大提高理论研究的效率和质量。
可以想见,随着学术研究质量的深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专业化水平会逐步提高,学者面对政策咨询和相关需求时,既能提供分析原理,又能介绍历史细节,国际关系专业会因此赢得应有的声誉和尊严,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矛盾也会得到缓解。当然,我们强调提高学术研究质量是首要任务,并不意味着要刻意回避研究的现实意义,否则又要重蹈美国学界的覆辙。
美国理论与政策隔阂的原因何在? 宋伟
学术界政策影响力虚弱的问题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虽然类似,但原因可能大不相同。从美国的情况来看:首先,一些理论较为宏观抽象,而外交政策问题过于细致具体。沃尔兹认为理论肯定会远离现实,解释力的获得是通过与“现实”拉开距离来实现的,“一个完整的描述最缺乏解释力”。因而对于许多具体的政策研究者来说,自然会觉得理论往往过于抽象甚至偏颇。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说,学者“有充分信息和大量时间”,而外交政策制定者通常既没有时间,信息也很有限。
其次,政治家和学者对理论的不了解或误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辩论不断的过程,即使在同一个理论阵营内部,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论分支。因此,要准确把握某个理论的“硬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一些学者把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确定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这就是一个彻底的误解。小布什政府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和单边主义色彩的新保守主义(或者称为“进攻性理想主义”)与米尔斯海默的强调国际体系制约、伺机而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要用理论来分析外交政策,首先就要真正理解理论。
最后,国际关系学者希望保持价值中立,不热心政策。应该说,这一点正在改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不仅开始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外交政策理论,他们的研究也紧紧联系现实,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包括法里德·扎卡里亚的《从财富到权力》、杰克·斯奈德的《帝国的迷思》、斯蒂芬·沃尔特的《联盟的起源》、柯庆生的《有用的敌手》等等。
如果想要把国际关系理论较好地运用于实践,那么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澄清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明白深入地剖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和结构;其次是完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政策理论,使之能更好、更顺畅地运用于政策的分析和制定。
国际关系学科需要“功能革命” 王文
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90周年。对于过去的90年,我们通常只关注学科的理论演变史,却很少注意到学科功能的变化。我认为,大体看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为了政策”、“为了学术”及“为了社会”三次功能革命。“为了社会”,即做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也不是为了影响政策,而是为了影响社会。这个第三次功能革命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近年来蔓延至中国,并在中国出现了去政治化、非学院化和泛娱乐化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关系学内部,这种转向可能还没有产生对研究框架的冲击,但是,对于整个学科共同体来说,它却改变了国际关系学在社会话语结构中的生态状况。
从积极面看,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出现了公共问题化的研究转向,学者功能也出现了一些分层,知识垄断也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都受鼓励参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从消极面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与世界同行类似的学术危机,即学者的社会影响力下降、学界的社会话语权旁落,以及学术知识的社会贬值等现象。
由此看,中国学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学术内部的“主体革命”,还要进行一场思想观念上的“功能革命”,即允许、鼓励甚至奖励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影响社会”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去。这就需要学者在语言沟通、问题意识、知识捕捉能力上进一步强化自我。只有这样,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跟上中国崛起的步伐。
“去历史化”倾向需要纠正 王栋
外交政策当然需要来自理论研究的智力支持,对于理论研究如何走出与政策脱节的困境,我认为有如下路径:首先,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区分“政策相关性理论”与“非政策相关性理论”,前者以政策为导向,后者以知识为导向。其次,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少谈些主义当然不是不谈主义,而是应当超越“译介”式、“书评”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式,真正回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提出好的问题,并且以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办法去提出假设、收集数据并进行验证。再次,回到国际关系研究的两大支柱——历史和哲学。尤其要重建和复兴历史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去历史化”的现象需要纠正。最后,要重视对下一代决策者的培养。研究者们致力于培养出具有扎实学术底子、有思辨能力、有理论修养的下一代决策者将是理论学术研究对政策制定的最大贡献。
不应用“两分法”看待学术与政策的关系达巍
我赞成用政府政策、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三分法”,而非学术和政策的“两分法”,来审视学术与政策的关系问题。理想状态下的政府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三者应该有密切的互动;好的理论研究应该有较强的现实相关性,并为政策研究和政府政策提供基础;而政策研究在理论研究与政策之间则应该发挥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两个圈子彼此轻视的现象严重,人员交流不多。在政府长期任职或在智库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没有机会跨越学术“门槛”,再进入大学。大学里的学者也鲜有愿意进入智库工作的。与之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水平与美国同行相比差距极大。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内部,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并无特别深的鸿沟。一些学者同时兼做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两类研究学者的互动交流也比较自然,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圈子。这或许是因为理论研究不够发达所致,但是客观上也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政策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通过以下路径:其一,既要避免仅仅停留在对现行政策进行诠释的层次,也要顶住民意和媒体的压力,更要排除利益的左右;其二,要强化方法论意识,重视实证研究;其三,强调研究的专业化,同时加强专业间的协作;其四,增强官、学、商、媒之间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