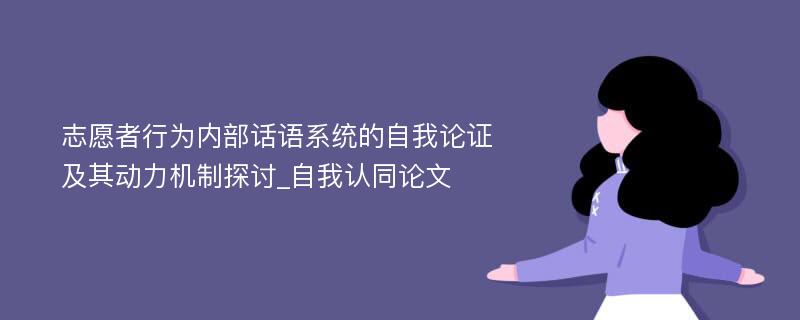
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的自我论证———项关于其动力机制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于其论文,志愿者论文,话语论文,机制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3)02-0105-06
一、问题提出
通过前期探索,笔者发现,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从事志愿服务”,很多志愿者的回答是“好玩”、“新鲜”、“好奇”。但通常,对志愿者动力机制的研究是将一些政治和学术力量建构的外在话语体系强加给志愿者——如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无偿性、自愿性、组织性、公益性,用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从事志愿服务。也就是说,现有对志愿者行为动力的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解释经验现象。综览现有文献,关于志愿者行为动力机制的研究汗牛充栋。为了便于分类与研究,我们将其归纳为“精神法”范式和“利己—利他”范式。
“精神法”范式研究主要是从精神、道德、价值、体验、意识形态、自我实现等思想情感层面来探索促成志愿者行为的动力[1]。为了方便表述,我们将其命名为“精神法”。首先,无论“精神”的内涵是志愿精神、志愿道德、政治动员(意识形态)还是自我实现,它都可以归类于思想层面的内容。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都缺少历史的连贯性。处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志愿者行为可以由不同的“精神”来激发。其次,这种范式的潜在假设是,“精神”的存在与志愿者行为的产生具有等号效应。问题随之而来,“精神法”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认同和持有志愿精神的人没有从事志愿者行为?而那些主要受非志愿精神激发的志愿者行为是否没有志愿精神的激发效应?这种研究范式正好应和了后功能主义的代表美国人杰夫里·亚历山大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实际上,“精神法”范式的各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都忽视了个体对具有强烈社会特性的“精神”所发挥的能动性,从而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建构“精神”、强化“精神”的内化就一定能够促成志愿者行为的产生和普及。
另一种则是“利己—利他”范式。Stenzel和Feeney在这一范式下,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分为三大类:利己;利他;社会责任[2]。在中国学者中,刘珊[3]、吴鲁平①、谭建光[4]从各自角度展开研究。这一范式谈及利他倾向时,更多地从宏大叙事的角度谈“利”。无法让志愿者行为回归个体本身所能获得的进步。在谈及利己倾向时,倾向于从精神层面谈“利”。虽然个人精神满足也的确是志愿者行为可以给予志愿者的一个回报,甚至是重要回报。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同样可以或明或暗地因为有形利益去从事志愿者行为。在这方面,相关研究较为少见。
除此之外,沈杰的研究融合了以上两大范式[5]。朱健刚则对自下而上发起的志愿者行为的实践逻辑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类行动具有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双重框架[6]。任剑涛从一般意义的志愿者行为角度提出。志愿者行为有两种推动力量:个人道德理想与组织推动力量[7]。这项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引入了行动组织化程度高低的变量。这实际上是对精神、心理层面的要素与志愿者行为之间天然的等同关系的否定。
中国众多大型活动对于志愿服务的巨大需求是可以预见的。因此,志愿服务的组织和开展也是一个必将面对的问题。在需求面前,我们如何鼓励中国人参与到大型活动志愿服务中来?参与动机是什么?当上述两种范式的效力受到质疑之后,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做出尝试性地回答,即,志愿者行为的动力机制是其内在话语体系的自我论证过程。
志愿者行为话语体系分为内在话语体系和外在话语体系。后者是一种由学术和政治力量主导建构的话语体系。本文将以具有自上而下特性的大型活动为例,着重对内在话语体系进行研究。所谓自我论证,即一个微观个体从事的对志愿者行为话语体系建构及合法性赋予的过程。首先,自我论证是合法性获致的前提。其次,自我论证过程不是以群体为主体的,它是以常人个体为主体的。第三,自我论证是一个反复行进的过程。最后,所谓“自我”,这种论证过程所仰仗的依据是其本身。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依据调查获得的经验材料,本文为了方便论证,假定将“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的构成部分限定为爱好、过程标准化、品牌化、责任等四个维度。这仅仅是出于展开论证的需要。实际上,每个个体的内在话语体系构成部分都是独特的。
二、作为动力机制的内在话语体系自我论证过程
(一)生成
1.互动生成
个体一旦进入到志愿者行为,都会碰到外在话语体系失效的局面。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外在话语体系对于志愿者行为的激发和维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更多承载的是学者或者政治力量赋予它的内涵,脱离了个体的具体特性以及不同志愿者行为的内在特征。外在话语体系与志愿者行为不匹配的情况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的发生使得外在话语体系在志愿者行为中只具有象征性的作用,无法产生实质动力意义。
外在话语体系合法性的丧失使得志愿者必须寻求新的话语体系来支撑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进入研究视野。本文认为,每一个志愿者行为被一套内在话语体系所环绕,并且,这套话语体系是由志愿者个体间互动生成的。互动生成也是自我论证过程的开始。任何志愿者在进入到志愿者行为之前,他都不可能持有、更不可能认同志愿者行为的内在话语体系。内在话语体系的生成是志愿者在特定志愿者行为过程中互动的产物,而不是互动的前提。我们必须区分清楚志愿者行为和内在话语体系的先后关系:“志愿者行为”在先,内在话语体系的生成在后②。
2.正负极挑战
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在初步建立之后,它会经受多种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是正负极挑战。所谓正负极挑战,就是对内在话语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或者多个构成部分加以否定。当志愿者在构建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的时候,实质上是对每个构成部分的正极加以肯定。笔者在访谈中设计了正负极实验对这一过程加以展现。
在对一位汶川地震灾后心理辅导志愿者的初次访谈中,她告诉笔者:“对于社会工作,我确实很喜欢。这次去四川,我就是喜欢社会工作才去的。”对这段访谈进行编码就能够发现,这位志愿者强调她是因为喜欢从事社工,才加入到志愿者行为中来的,“爱好”是她的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她极大地对“爱好”在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肯定,从正极对其加以论证。
为了对“爱好”的正极进行挑战,笔者对这位志愿者进行了二次访谈,并就“爱好”对其进行了质问:“你真的觉得你从事志愿者行为是因为喜欢?”被访者显然感受到了来自于笔者从负极对“爱好”的挑战。她很肯定地回答笔者:“当然。我过去一直在想,有没有哪次机会能让我去亲身感受一下。学了这么多年社工,热情还是在的,没热情就学不到今天了。”为了使她的反应更为明显和剧烈,对她的回答,笔者仅仅投之以微笑。她显然感受到了笔者对之持续的挑战,又继续说:“我们很多去四川的同学都是因为喜欢才去的。去四川这种灾区做志愿者,肯定会被晒黑的,我们都是很喜欢的。”
到此,在对构成部分的挑战中,志愿者行为的符号地位并未受到挑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该志愿者对内在话语体系的自我论证,或许“爱好”无法成为内在话语体系的构成部分。但志愿者行为的符号地位不会丧失,它仍旧可能由其他构成部分来维持。所以说,日常生活中的正负极挑战只是对内在话语体系的一个局部性挑战,它不会危及到整个志愿者行为的符号地位。这种挑战仅仅局限于一种所谓“量变”的视野之中。就此而言,任何对正负极挑战的回应,即自我论证的过程也都是一种局部性的自我论证。这种自我论证无法超越各个构成部分的范围。也就是说,每个自我论证的过程都只是对一个或者多个特定构成部分的论证。它不是从志愿者行为的整体特性入手进行论证,而是在局部展开对话。
3.破坏性挑战
加芬克尔发明了破坏性实验[8]。他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人与人的互动中,存在着基本的共同规则。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共同规则的认同是有界限的。它可能仅仅存在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群体当中。笔者发现,一旦这种共同规则受到破坏性挑战,那么自我论证就会进入启动程序。为了展现这一过程,笔者选取了一位上海世博会志愿者进行二次访谈。首先呈现的是访谈的关键进程。
笔者:你这些天去世博会做什么?
志愿者:我是去当志愿者的。
笔者:当志愿者需要做哪些事?
志愿者:就是每天到了那边以后,要在入口的地方引导大家有序地排队。
笔者:你们做这个志愿者工作有什么要求吗?
志愿者:就是要有责任感,不能说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③……而且我们的日常用语、手势还有表情都是有统一要求的④……反正当世博会志愿者挺光荣的,现在我家里的亲戚都知道我在世博会当志愿者⑤。
笔者:你觉得你是在从事志愿者行为吗?
志愿者:当然是啊,怎么了?
笔者:你可以用另一个词语来形容你每天所做的事吗?
志愿者:(思考了很久)我不知道啊。
笔者:如果我说你每天去世博会是“探索未知世界”,你同意吗?
志愿者:当然不同意。
笔者:为什么不同意?你每天在世博会能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人和事啊。
志愿者: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就像我和你说的,我们从事的是志愿者行为。
在这种“破坏性挑战”中,互动双方之间最基本的共同规则已经被打破,也就是说,互动双方并没有就“志愿者行为”这个基本框架达成一致。笔者是对志愿者行为本身进行的挑战,并用另一个符号来取代“志愿者行为”,这就是“探索未知世界”。它试图彻底打破“志愿者行为”及环绕在其周围的整个内在话语体系。
面对笔者的这种破坏性挑战,志愿者就“志愿者行为”这个基本框架展开自我论证,这种回应是全局性的。他首先坚持了志愿者行为的符号地位,断然否决了笔者提出的“探索未知世界”。他用“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的强烈反问句把笔者的提议否定了。接下来,“我们连文明用语都是规定好的”指代的是内在话语体系的“程序标准化”;“我来做志愿者,我爸妈都告诉亲戚朋友的,他们好像也挺高兴的。”这句话指代的是内在话语体系的“品牌化”,以父母亲的认同来暗指世博会志愿者的高度品牌特性。
在对话语体系构成部分的自我论证中,他所运用的论据仍旧是内在话语体系自身。这和对志愿者行为构成部分的自我论证是同样的逻辑。这些对其它符号排他性地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对自身所持符号的论证过程。这种论证过程背后所指的依据并不是其他,而是这种符号自身。与其说,个体运用这种符号依据否定的是其他符号,还不如说,这种否定意味着运用一种符号对自身的不断论证和强化认同。
4.行动准则的生产与执行
生成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的最后一步是生产与执行一套与话语体系相对应的行动准则。志愿者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套有序的行动,所以其内在话语体系的构建其实也是为了这套行动的执行。因此,内在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无论如何不能将行动准则遗漏的。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所有的志愿者在谈到内在话语体系的时候都会极其明确地向笔者指出与之相对应的行动准则。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将行动与内在话语体系人为地割裂,那么任何内在的话语体系都是一个未完工的“烂尾楼”。人们甚至无法理解这套内在话语体系的具体含义,缺少行动的话语体系只会是一个缺乏实际参照物的空洞概念。这个概念一定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所以,行动准则的生产是建构内在话语体系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
同时,行动准则的执行也属于这一过程。正如霍布斯鲍姆对“传统的发明”界定一样,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所对应的行动也是“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9]如果说前面自我论证的进程都是位于言语层面,那么这个阶段的自我论证则是位于行动层面。相同的是,这些论证所运用的论据都是话语体系及其衍生物自身。区别仅仅在于,前面几步自我论证的论据抽象性较为强烈,而对于行动执行,对其的感觉是可触摸、可感知。也就是说,行动准则通过微观个体的实践,自我论证过程才得以完整。
(二)强化
在经历了四个步骤的生成过程之后,完整的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自我论证过程还包括强化。
1.内在话语体系认同个体数量的增加
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合法性强化的表现之一是对其认同的个体数量的增加。内在话语体系认同度在人群中的传播并不是由外在话语体系那样的社会化效应产生的。每一个个体对内在话语体系的认同都是来源于完整的自我论证过程。所以,合法性的强化不能被看做是产品本身的扩散。我们必须从自我论证的过程中去探索,其关键点在于论据的社会性。
在局部性自我论证和全局性自我论证中,个体都是用初步建构的话语体系及其构成部分来对自身进行论证。在互动生成中,内在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是一个具有社会特征的过程,个体与个体在互动生成中形成了相似的话语体系。在局部性与全局性的自我论证中,我们不能将初步建构的内在话语体系在个体之间的传播视为一个最终的结果。相反,内在话语体系是作为一种论据在个体间进行传播。这就是说,志愿者在进行自我论证的时候,运用了社会性的论据。
在行动准则的生成与执行中,志愿者为了保持与群体同样的前进方向,依照初步构建的内在话语体系,会生产具有社会性的一致的行动方向。前文已述,行动在生成之后反过来又会作为内在话语体系自我论证的重要论据。所以,达致合法性的这一阶段同样可能形成对类似内在话语体系的群体认同。
需要澄清的是,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合法性的个体认同数量的增加与外在话语体系合法性获得是有显著区别的。尽管他们都表现为合法性认同的个体数量的增加,但内在话语体系的合法性获得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虽然不同个体所认同的内在话语体系具有相似性,甚至是相同的,但个体与个体都分别独立地经历了生成过程的四个阶段。在个体间各自的自我论证过程中,志愿者们都选取和运用了相似的论据进行自我论证。这是致使志愿者们形成类似乃至相同的内在话语体系的关键。
2.内在话语体系构成的扩展
第二个表现是内在话语体系构成的扩展。内在话语体系的自我论证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尽管不具有绝对性,但它具有将不同的构成部分纳入到内在话语体系中来的极大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某一时间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为内在话语体系寻找到一个边界,但它始终处在动态的进程中,它始终在吸纳新的构成部分。由于我们无法找到特定志愿者行为的终点,所以我们也无法找到这种构成部分的最终界限。但我们相信特定构成部分的自我论证是具有清晰的界限的。不同构成部分的自我论证的前后相连形成了一个合法性不断强化与巩固的局面。
社会学从理论上强调其动态性,这给予我们对内在话语体系合法性强化的研究极大的启示。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志愿者行为永远是一个需要面对突发情况和未知情境的事业。对于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而言,新的情境就是自我论证的起点。所以说,内在话语体系构成部分的扩展对于志愿者行为而言是一个必然要面对的过程。因此,它的合法性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相反,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始终是志愿者应对不同的复杂局面从而进行自我论证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内在话语体系的构成部分在原有基础上的添加。
3.内在话语体系和大众媒体
最后一种表现是大众媒体的反映。无论内在话语体系具有何种特性,一旦获得志愿者的认同,它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反之,它就不能获得合法性。消费时代中,大众媒体在制造传媒内容的时候,竭力迎合包括志愿者在内的个体,如果没有个体消费大众媒体所制造的产品,那么大众媒体就将面临被边缘化或者破产。所以,内在话语体系是否获得合法性,只要稍加检视大众媒体和话语体系的关系便可得知。当然,这种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话语体系是否进入到了大众媒体,由于中国大众媒体特殊的宣传作用,我们还有必要检视,如果话语体系进入到了大众媒体,那么,是否得到了个体的认可。
笔者在对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进行研究的时候,选取了众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对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的广播专访。在这些专访中,尽管未曾言明,但志愿者们详细介绍了他们构建的众多内在话语体系,包括“品牌化”、“程序标准化”、“责任”、“爱好”等各个构成部分。选取这些内在话语体系作为广播节目内容的主题,大众媒体必然是考虑过个体对其的认同度的。因为认同与否直接决定着收听率,而收听率对于大众媒体而言就是生命。并且,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些接受采访的志愿者个个都能较为熟练地应对媒体采访。简单的事实清晰地显露了,志愿者行为的内在话语体系能够较为容易地进入到大众媒体当中。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标化方法多少会受到质疑,但大众媒体是否报道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以及报道被个体认同的程度仍旧是当前一个衡量其合法性的非常有用且便于获得的指标。或许个体通常很难获取特定节目的收视率报表,但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上,我们对其是否引入内在话语体系的报道的检视,还是能够较为便捷地窥探出某种内在话语体系是否被个体所认同。
三、结论
本文较之现有研究的突破在于,志愿者行为的动力是内在话语体系的自我论证过程。“内在”,就是说,建构的主体既不是学术力量,也不是政治力量,而是志愿者自身。任何离开了志愿者自身建构尝试的话语体系都不能被称为“内在”。“过程”,包含生成与强化的双重阶段。生成,经历了互动生成、局部性自我论证、全局性自我论证以及行动准则的生产与执行四个过程。强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认同个体数量的增加;二是内在话语体系构成部分的扩展;三是大众媒体的反映。
应该说,这一结论将作为言语的话语体系与作为行动的志愿者行为有效地结合起来了。自我论证的过程赋予了内在话语体系合法性,它强调的是个体在志愿者行为中应对具体问题时的行动方案,是一个结合了行动的过程。在自我论证的过程中,志愿者行为在话语体系和行动方式上得到双重发展。由于它内在地含有了行动的方案,所以,只要是自我论证的完成,也就是行动的生成。总的来说,将“行动”融入志愿者行为内在话语体系的自我论证是这项研究的一个必要视角。
收稿日期:2012-09-05
注:
①参见吴鲁平《志愿者的参与动机:类型、结构》,刊于《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少数从动态视角来观察志愿者行为动机的学者。他认为,志愿行动的发展进程也意味着动机的发展。并月,他运用过程化分析对其加以关注。具体而言,这分为“初始参与动机”和“持续参与动机”。但他对此的分析显得较为简单粗糙。
②当然,如果到目前为止就用“志愿者行为”这四个字来指代个体从事的这种行为的话,显然是不精确的。因为,任何的符号如果缺少了话语体系的环绕,就等于缺少了内涵,那么它就不是它了。但为了不引起更多的论述上的混乱,笔者权且用“志愿者行为”做临时性的指代。
③笔者注:责任。
④笔者注:标准化。
⑤笔者注:品牌化。
标签:自我认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