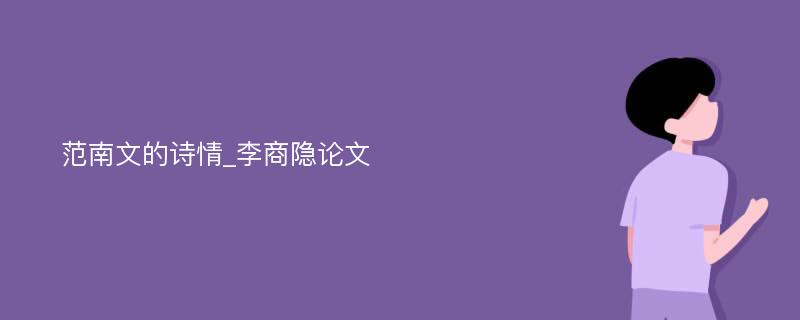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诗论文,的诗论文,樊南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玉谿诗与樊南文,是李商隐倾其毕生精力与心血铸成的艺术珍品。自钱钟书先生提出“樊南四六与玉谿诗消息相通”(引自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前言》)之说以来,先有周振甫先生对“商隐以骈文为诗”这一面作过精切的阐发[1],继有董乃斌先生在其所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浓缩的符号——典故”、“非诗之诗”等有关章节中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周、董两位先生的阐论,大抵侧重于商隐骈文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但玉谿诗与樊南文的关系,还有另一重要侧面,即玉谿诗对樊南文的渗透与影响,或可称之为“以诗为骈文”。作为一个在诗歌创作上卓有成就、极富个性特色的大家,他的骈体文不可能不受到其诗歌创作或明显或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樊南文中的诗语、诗情、诗境等诸多方面,而又集中表现为樊南文所特有的诗心——李商隐的诗人心灵与个性。钱先生所说的“樊南四六与玉谿诗消息相通”,当兼该“以骈文为诗”与“以诗为骈文”这两个方面。优秀的玉谿诗和富于诗情诗境的樊南文正是同一心源所生的珍奇硕果。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主要是樊南文中富于抒情色彩(特别是个人抒情色彩)的文艺性文章。商隐一生,辗转寄幕,为幕主或他人撰拟了大量表状书启及其它应用文。这些文章尽管在隶事用典、敷采摛藻、声切对偶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堪称“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二),但从整体上看,仍属应用文而非文艺性文章。樊南文中,真正具有文艺性的,是哀祭诔奠之文和一部分抒情书启。这部分文章尽管只占现存樊南文的三分之一左右,却是最能代表樊南文的特色与文学成就的。由于玉谿诗对樊南文的渗透,有时一些非文艺性文章中也会出现文艺性的段落或句子,论述中也间或旁及这类文章。
樊南文中的诗语
在中国古代各种文章体裁中,骈体文是形式上最考究的一种美文。它以隶事用典、追求华藻、讲究声律为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诗歌语言的精炼含蓄、富于音乐美、色彩美密切相关,有的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诗歌语言的特点而形成的,特别是初唐四杰的骈文,其平仄的更加谐调,属对的更加精切,就与当时近体诗的发展定型有明显关系。但是,并非具有上述特点的语言就能成为诗语。作为诗语,还必须有诗歌语言特具的形象性与韵味,像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典型的例证。樊南文中的诗语,大体上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在前代诗文隽语基础上融铸而成的,如《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中的一段文字:
皋壤摇落,老大伤悲……心惊于急弦劲矢,目断于高足要津。而又永念敝庐,空余乔木。山中桂树,远愧于幽人;日暮柴车,莫追于傲吏。捋须理鬓,霜雪呈姿;吊影飏音,烟霞绝想。
这是代长期寄幕、落拓不偶的文士张周封向当朝宰相杨嗣复陈情告哀、祈求荐引的书信。节引的这一段融化了谢朓、古乐府、陆机、《古诗十九首》、《楚辞·招隐士》、江淹、陶潜、曹植等一系列清新俊逸、富于形象感、画面美而又诗味隽永的清词丽句。作者以“老大伤悲”的不遇之感为中心,将它们累累如贯珠似地串连成一个整体,不仅表现了张周封进不能仕、退不能隐的悲苦处境,而且活现出一个须鬓霜雪、形影相吊的失意沉沦之士的凄苦形象。由于这一连串诗语的巧妙组织与配合,便酿造出了非常浓郁的诗味。这种集合诗文隽语的方式,并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在吸纳原诗语内涵、意味、色调的基础上,经作者的妙手点染,产生新的诗味。“心惊”一联,化用陆机诗句“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及古诗“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而分别冠以“心惊”“目断”,就在强烈的对照中,更加突出了面对急弦劲矢般逝去的时光和自身仕宦无路的处境时那种既焦切惊心又无望无奈的心情。因要津之渺茫难即而益感时光流逝之迅疾,又因时光流逝,头颅老大而益感仕途之无望。这种集合式的诗语,在樊南文中随处可见,如:
今春华以煦,时服初成,竹洞松冈,兰塘蕙苑,聚星卜会,望月舒吟。羊侃接宾,共其醒醉;谢安诸子,例有风流。(《上李舍人状五》)
久乘亭障,长奉鼓鼙。猿臂渐衰,燕颔相误。弊庐仍在,白首未归。(《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
某始在弱龄,志惟绝俗。每北窗风至,东皋幕归,彭泽无弦,不从繁手;汉阴抱瓮,宁取机心?岩桂长寒,岭去镇在,誓将适此,实欲终焉。(《上李尚书状》)
有时,用一两个典故也能融铸成情味隽永、形象鲜明的诗语,如《上河东公启》:
某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
分用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写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以“梧桐半死”喻丧偶,不仅形象地显示了与妻子王氏同根共体的亲密关系,而且将自己遭到这场变故后形毁骨立、生意凋丧的情状描摹得鲜明如画,其内心的创痛亦不言而喻。以“灵光独存”喻己身独存,其孑然孤立,形影相吊之状固如在目前,且于言外透露出一种人世沧桑之慨。
另一种类型是不用任何典故、藻饰,自出机杼铸成的诗语。如:
清秋一鹗,碧海孤峰。(《为濮阳公与度支周侍郎状》)
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上易定李尚书状》)
万里衔诚,一身奉役。湖岭重复,骨肉支离。(《上度支卢侍郎状》)
白露初凝,朱门渐远。(《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去岁陪游,颇淹樽俎;今兹违奉,实间山川。曲水冰开,章台柳动。(《上李舍人状五》)
今者冰消雪薄,江丽山春。(《为荥阳公与浙东杨大夫启》)
除首例是用秋鹗、孤峰象喻对方的品格风神外,其余诸例均为抒情写景的句子。或写对前辈知遇的感念,或抒亲故零落的悲痛,或叙羁旅漂泊的苦辛,或状两地相隔的怀想,无不清词丽句,诗味浓郁。末例遥想会稽春天风物,纯用白描,而名山胜景春日的盎然生机与明丽色彩宛然在目。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商隐并非纯以獭祭数典取胜,而是同样擅长白描。没有典故的骈句,照样可以成为清新俊逸的诗语,关键在于其中所蕴含的对所写人事景物的诗意感受。从另一方面说,它们之成为诗语,也并非由于其语言比较通俗,不用藻饰典故。陆贽的奏议也很少用典,语言朴质明快,但它们仍是标准的文章语而绝非诗语,关键亦在于作者对所论的内容并没有诗的感受而纯出于理性的思考与剖析。这里已涉及诗语所蕴含的诗情问题。实际上,诗语与诗情是互为表里的,很难截然分开。
樊南文中的诗情
李商隐是一位主情型的诗人,其诗以“深情绵邈”著称。这一本质特点也同样体现在樊南文中,特别是抒情色彩比较浓的文章中。樊南文中的诗情,最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怆,对亲朋故旧的感念及不幸遭际的伤悼。并以此为基点,辐射到其他人事上。
感伤身世,原是玉谿诗中一个贯串始终、弥漫于各种题材的基本主题。可以看出李商隐作为一个诗人,这方面的体验特别深刻,情感也特别浓挚。这种沉凝郁积的诗情,在他一系列陈情告哀或感念知己的书启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如大中三年十月他应武宁节度使卢弘止之辟后所写一封谢启中这样写道:
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踰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恩旧凋零,路歧凄怆。荐祢衡之表,空出人间;嘲扬子之书,仅盈天下。去年远从桂海,来返玉京,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隘傭蜗舍,危托燕巢。春畹将游,则蕙兰绝径;秋庭欲扫,则霜露沾衣。勉调天官,获升甸壤。归唯却扫,出则卑趋。仰燕路以长怀,望梁园而结虑。
李商隐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四年释褐任秘书省校书郎,旋调补弘农尉。到大中三年,“获升甸壤”,仍然是一个畿县的县尉。其间经历了恩知令狐楚、王茂元的去世,老母的亡故,府主郑亚的被贬,以及自己展转寄幕、南北驱驰漂泊的生活。十三年中,绕了一个大圈,最后仍然回到原来的起点。明乎此,才能感受到这段倾诉十余年来坎坷经历的文字所蕴含的感伤身世之情的浓度,才能感受到诸如“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恩旧凋零,路歧凄怆”,“归唯却归,出则卑趋”一类句子所包含的痛切人生体验和“仰燕路以长怀,望梁园而结虑”中所流露的急切期盼和感念。将此启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对读,当会更明显感受到其中所凝结的诗情。与此类似的,还有《上李尚书状》、《献舍人彭城公启》、《献相国京兆公启》、《献河东公启二首》(其一)、《上河东公启》等。这些启状所投献的对象,与商隐的关系虽有较亲较疏之别,但作者在抒写自己流离困顿的身世时,都毫无例外地充溢着感伤的诗的情愫。在诗歌中,他往往通过咏物、咏史甚至歌咏爱情的方式寄寓身世之感,表现得比较曲折深隐,在文中则表现得相当明显直接,甚至淋漓尽致。这当然与这些书信有明显的投献目的,不如此不足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同情密切相关,但也可见其身世之悲蕴积之深。《上河东公启》是大中五年到东川幕后不久,辞谢柳仲郢赠歌妓张懿仙而作,是一篇工于言情的诗体式书信。启中自述妻亡子幼一段,写得最为哀恻动人:
某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每嗟漂泊。
悼伤之情方浓,又复抛下年幼的儿女,只身远幕东川。一路写来,似乎只是在渲染丧妻后自己的孤凄衰病和骨肉分离、无暇提携的痛苦歉疚,实则处处都在暗示:自己既深念亡妻,更怜念子女,根本不可能移情他顾。虽未明言,对方自能从这充满哀感的自述中揣知商隐因丧妻别子衰病而风怀已淡的隐衷。虽用了一连串典故,却挟情韵以行,如同信手拈来,曲折如意,表现出驾驭骈文这种形式的高超工夫。
商隐祭奠之文,写得最富诗情的是祭奠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恩旧戚属的文章。令狐楚是他正式踏入社会以后对他有指点提携之恩的第一位显宦,他的骈文章奏技巧和登进士第的荣耀,都与楚的拂拭照顾密切相关。开成三年,他在《奠相国令狐公文》中这样写道:
呜呼!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送公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誉公怜,人谮公骂……愚调京下,公病梁山,绝崖飞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镌辞墓门。临绝于宁,托尔而存……故山峨峨,玉谿在中。送公而归,一世蒿蓬!
从大和三年初谒令狐于洛阳,得其垂拂,到开成二年令狐临终托其代草遗表撰写墓志,前后将近十年,可叙之事本多。但这篇祭文却撇开许多具体情事,以抒情的诗笔集中写令狐的知遇。十年的交契始末,只用“昔梦”十六字高度概括,一生一死,一始一终,略去中间无数情事,亦包蕴无数情事。这种浓缩虚括的诗笔,最宜于表达浓郁深挚难以用具体情事表达的诗情。“天平”四句,似涉叙事,实为抒情,从“将军樽旁,一人衣白”正可见自己以白衣未仕之身受到令狐的特殊恩遇。包括下面的“临绝丁宁,托尔而存”,亦均从知遇之恩着笔,说明令狐直到生命终结之日,所信任倚重的仍是自己这样一个尚未正式入仕的小人物。结尾因令狐之逝而发“一世蒿蓬”的悲慨,其时义山已经登第,这种“预言”初读似有过情之嫌,但只要联系义山的身世境遇,便不难发现这实在是他的真情流露。令狐楚是他在“内无强近,外乏因依”,“沦贱艰虞”的处境中首先予以有力援助的知己,因此对楚的去世,不但倍感悲痛,而且有一种“一世蒿蓬”的不祥预感。而这种预感竟不幸而言中。冯浩说:“楚爵高望重,义山受知最深,铺叙恐难见工,故抛弃一切,出以短章,情味乃无涯矣。是极惨淡经营之作。”所言诚是。
从《奠相国令狐公文》可以看出,商隐这类吊祭恩知亲戚之文之所以哀恻动人,富于诗情,是和其中融入了身世沦贱之感密切相关的。现存商隐祭奠文中,《祭外舅赠司徒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祭徐氏姊文》、《祭处士房叔父文》、《祭小姪女寄寄文》无不具有这一突出特点。在这些祭文中,对恩知戚属的感念哀悼和对自身遭际的伤感往往水乳交融:
呜乎!往在泾川,始受殊遇。绸缪之遇,岂无他人?樽空花朝,灯尽夜室,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语皇王致理之文,考圣哲行藏之旨,每有论次,必蒙褒称。
祷祠无冀,奄忽相违……此际兄弟,尚皆乳抱。空惊啼于不见,未识会于沉冤。浙水东西,半纪漂泊。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衬故丘,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
前者写在泾原时所受于王茂元的“殊遇”。在对当时情景充满诗情的追忆中所流露的正是茂元以尊显之位对他这样一个出身寒素的年青人“忘名器”“去形迹”的厚谊。后者写仲姊死后自己随父漂泊异乡,继又因父亲去世孤儿寡母扶柩回乡的情景,透露出商隐一家当时几乎跌落到社会下层的穷困处境。其中所蕴含的感情既深挚强烈,语言亦精炼而富于含蕴,具有诗的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商隐有些代人写作的这类文章,也无形中渗透了作者由自身不幸遭遇形成的人生体验,如《为司徒濮阳公祭忠武都押衙张士隐文》:
举无遗算,仕匪遭时。何兹皓首,不识丹墀!剑折而空留玉匣,马死而犹挂金羁……泉惊夜壑,草变寒原,荒陌是永归之里,老松无重启之门。
《为荥阳公祭吕商州文》:
参差觏闵,萋斐成冤。汉庭毁谊,楚国谗原……书断三湘,哀闻五岭。天涯地末,高秋落景。重叠忧端,纵横泪绠。
或因怀才不遇而白首不识丹墀,或因党局反覆而遭谗外贬。这种遭遇触动商隐自身的沉沦之悲,形成共振,故笔端饱含诗情。相反,对有些生平经历并无明显悲忧情事的祭奠对象,则笔下每较平淡。商隐胸中郁积的深沉强烈的身世之悲,可以说是其诗、文创作一个极其重要的动力源,也是其骈文诗情的泉源。
樊南文中的诗境
这里所说的诗境,是指一篇文章或文中某一相对独立的段落,由诗语、诗情或诗景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具有诗的意蕴的境界。一般习惯于用意境之有无高下评诗,而较少以之衡文。但樊南文中一些出色的抒情文是具有诗的境界的,这正是它高出一般文章的地方。大中二年春他在桂林为郑亚代拟的几封书启,就在似不经意中渲染出一片诗境。《为荥阳公与浙东杨大夫启》:
不审近日诸趣何如?越水稽峰,乃天下之胜概;桂林孔穴,成梦中之旧游。遐想风姿,无不畅惬。一分襟袖,三变寒暄。虽思逸少之兰亭,敢厌桓公之竹马。况去思遗爱,遐布歌谣;酒兴诗情,深留景物。庾楼吟望,谢墅游娱,方知继组之难,不止颁条之事。今者冰消雪薄,江丽山春,访古迹于暨罗,探异书于禹穴,不知两乐,何者为先?幸谢故人,勉自遵摄,未期展豁,惟望音符。其他并附乔可方口述。
这封仅一百五十字的短简,撇开一切浮文俗套,入手便问“诸趣何如”。以下便从杨汉公曾任官的桂林和现居官的越州分别落笔,写两地风物之胜与对方风姿之畅,写两地相隔的思念和汉公观察桂管留下的“去思遗爱”“酒兴诗情”。于“方知”二句作一小束后,转又写遥想中会稽的春日丽景与汉公的寻春访古之趣,回应开篇。全篇以如诗似画之笔,行云流水之势,渲染出一片由明丽自然的诗语诗景、萧散自得的诗情诗趣构成的优美诗境。作于同时的《为荥阳公上宣州裴尚书书》与此可谓异曲同工:
待诏汉廷,但成老大;留欢湘浦,暂复清狂。思如昨辰,又已改岁。以公美之才之望,固合早还廊庙,速泰寰区。而辜负明时,优游外地,岂是徐公多风亭月观之好?为复孟守专生天成佛之求?幸当审君子之行藏,同丈夫之忧乐,乃故人之深望也。
裴休字公美,穆宗长庆中登进士第,历五朝尚居外郡,故云“待诏汉廷,但成老大”。时郑亚亦以给事中出为桂管观察使,处境堪忧,故于裴之屈居外郡,实有同命相怜之感。但文中并不直言屈居外郡之牢骚,而是用“待诏”二语微露消息,不满之意,寓于言外。以下转笔回忆去年“留欢湘浦”的情景,亦于“暂复”二字中略透本意。随即再转写时光流逝之迅疾,其中既寓思念,亦寓感慨。且将裴休“辜负明时,优游外地”的原因归结为“多风亭月观之好”,“专生天成佛之求”,语带谐谑,意含牢骚。表现上的轻松风趣与内里的不满牢愁形成对照,蕴含了耐人寻味的诗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在相反相成中构成了诗的意境。
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人间词话》)此论实可移之评义山抒情文。《祭小姪女寄寄文》便是一篇写真感情而具有优美境界的文章。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的名作,商隐此文完全可与之方驾,而写作的难度却比《祭十二郎文》要大得多。因为韩文所祭的姪子老成,年岁与韩愈相近,自幼一起生活,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包括生活琐事作为叙事抒情的凭藉,而商隐所祭的小姪女,却是生下后就寄养于外姓,四岁方归本族,旋即夭折的幼女,跟作者接触很少,缺乏具体的生活情事作为抒写的材料。同时,骈文这种形式,比较板滞,不像散文那样可以自由舒展地叙事抒情。但文体与材料的限制却没有难住李商隐。相反还对传统的骈文多用典、重藻饰的特点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抒写真感情的有效形式。全篇纯用白描,纯以情胜,清空如话,在回环往复的抒情中不断将感情推向高潮。文章在抒写生未尽鞠育之恩的悲伤后,紧接着是一段抒写死未能及时迁葬之痛的文字:
时吾赴调京下,移家关中。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寄瘗尔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我有罪矣!
自寄寄夭伤到迁葬这五年中,商隐经历了移家、入幕、试判、秘省任职、丧母家居一系列事情与变故。作者化叙事为抒情,化实为虚,以“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八字概括许多难以尽言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感慨。“白草”四句,纯用白描,将一个幼小的灵魂置身于异乡荒郊古陌的孤单凄凉渲染得十分动人,具有诗的意境与情韵。“尔之栖栖,我有罪矣”,仿佛是过情之语,但正如商隐所说:“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这篇祭文所抒写的,正是“发乎情”而不大考虑是否“过礼”的至情。下面一段,又换另一副笔墨:
自尔殁后,姪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
以丽景衬哀情,以姪辈的天真嬉戏反托寄寄精诚不知所之的哀感与凄凉,同样写得极富诗情与诗境,“堂前”二句,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这是骈文。
呜呼!荥水之上,坛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汝来往于此,勿怖忽惊。华彩衣裳,甘香饮食,汝来受此,无少无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写到这里,不但完全撤去了幽明的界限,而且撤去了尊卑长幼的界限,一片深挚的柔情,溢出于字里行间。骈俪之文,运用得如此纯熟自如,不假雕饰,确实令人惊叹。全篇在反复抒情中所展示的,正是由至情至性所构成的诗境,是作者的心灵世界。
樊南文的诗心
樊南文中的诗语、诗情、诗境,从根本说,皆源于商隐特有的“诗心”。这种“诗心”,主要表现为互有关联的两个方面。
一是对人生悲剧特有的关注和深刻体验。商隐骈文中最具抒情色彩和浓郁诗意的,除个别篇章外(如前举《为荥阳公与浙东杨大夫启》),几乎都是抒悲写痛、陈情告哀之作;即使代人撰拟的书启,写得最富诗情的也多为与人生坎坷经历、悲剧遭遇有关的内容(如《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这说明商隐具有异于一般作者的感受人生悲剧的诗心与个性。张采田说:“义山诗境,长于哀感,短于闲适,此亦性情境遇使然,非尽关才藻也”(《李义山诗辨正·〈喜雪〉评》)。其文境亦然。诗、文俱长于哀感之境,正缘其同出一诗心。前已论及,义山一生的悲剧身世境遇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悲剧性人生体验,乃是他诗文创作最重要的动力源。创作中只要一遇到这类题材或内容,其敏感的诗心便会引起强烈共振而发为悲吟。像《为裴懿无私祭薛郎中衮文》中的薛衮,与商隐未必有很深的交情,只因他的死带有悲剧性(其兄弟薛茂卿系泽潞叛镇大将,因此忧惧而死),故义山在AI写作祭文时感情投注,写出极富哀感的文字。
一是义山独具的感伤气质与个性。对于人生悲剧的关注与体验,在义山心中凝成的主要不是愤激,而是深刻的感伤。由于悲剧性的身世之感、人生体验深入性灵,致使这种感伤情绪已内化为一种气质个性。发而为诗为文,则特具一种感伤的诗美。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义山却是绚中有素。”此论完全可移之评樊南抒情文。上举诸文之所以哀挚动人,具有“沁人心脾”之诗境,关键在于其中蕴含了对人生悲剧的深刻体验,在于作者的感伤气质与个性是深入骨髓的而不是浮浅表面甚至虚矫做作的。
中国古代骈文的发展,与诗歌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为用,是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现象。诗之骈化与骈之诗化差不多是同步进行的。六朝和初唐骈文中,都有颇富诗意的篇章,特别是像庾信的《思旧铭》、《哀江南赋序》,王绩的《答刺史杜之松书》,骆宾王的《与博昌父老书》、王勃的《滕王阁序》等,都有浓郁的诗情。但统观唐代,诗歌号称极盛,骈文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朝着越来越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很少出现具有诗情诗境的名文。直到李商隐,才以其特有的诗心诗才,在一部分骈文中恢复并发展了抒情和诗化的传统。由于商隐骈文的诗化,是在经历了唐诗的高度繁荣,包括作为传统五七言诗诗艺的总结者李商隐自己的创作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诗化的程度较前更有所提高,艺术上也更加纯熟。这是李商隐对骈文发展的一种贡献。与此同时,他对骈文多用典、重藻饰的传统形式也作了改造的成功尝试,这就是像《祭小姪女寄寄文》那样,在抒情化、诗化的基础上使骈文语言通俗化。初唐魏征、中唐陆贽的表疏奏议也很少用典,语言比较朴质通俗,这也是对骈文的一种改造,但这是在突出其实用性基础上的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使骈文更切实用,其结果是使骈文离文学、离抒情、离诗愈远。这和商隐的骈文通俗化尝试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尽管现存商隐骈文中,像《祭小姪女寄寄文》这种诗化、通俗化的文章数量很少,只能看作一种未必自觉的试验。但这个成功的试验本身却说明:传统的骈文,是可以改造成既具对仗声律之美,诗情诗境之美,又无堆砌典故辞藻之弊的美文的。只是由于商隐并没有将这种试验的范围扩大到形成一种明显的趋向与风格,因而后代的骈文家也未注意到这一偶发的成功尝试,以致对后代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其间原因自然很多,但人们对骈文的传统观念(认为骈文必须大量用典铺藻)和思维定势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何焯《义门读书记·李商隐〈镜槛〉诗评》云:“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庚子山笔法。”此实即最早提出商隐以骈文为诗之说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