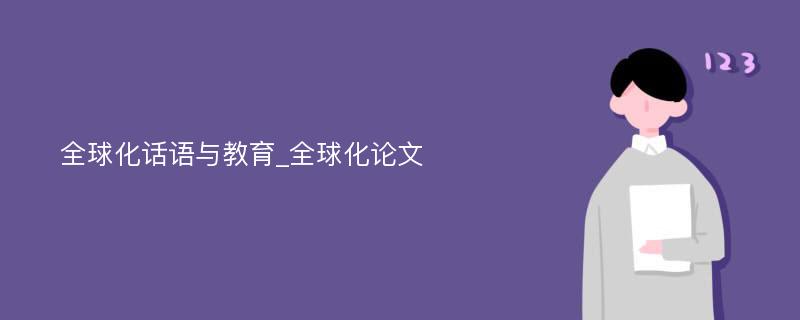
全球化话语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4-0086-15
中国台湾地区《天下杂志》曾对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努力程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台湾地区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成长经济条件较佳、高等教育机会供应充足、整体社会或校园国际化程度不足,使得年轻人较不具广阔的国际观,企图心也不够旺盛。[1] 当然这份报道的取样和归因都有待商榷,但此处我们关切的重点是:《天下杂志》原是一份以探讨财经现象为主调的著名刊物,这份财经期刊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怀和探讨、对于台湾地区社会各层面变化的积极分析,背后其实都是以“追求台湾地区长远竞争力”为诉求。①《天下杂志》的专题报道凸显资本主义国际竞争的压力,尤其在晚近资本主义标榜“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② 的体制中,积极“超限”与“越界”的企图和行动。上述关于台湾地区大学生的报道,既是财经话语,也是经济化的教育话语。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过去二十年来使用频率极高但其指涉现象和具体内涵却相当模糊多变的语词之一。促使全球化话语快速生产、传播的相关联的语词和意象包括“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y society)、“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等。此外,“全球化”一词常与“全球性”、“国际化”、“美国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等语词互相置换、混用,用以说明国际政局的密切关联和某些超级强权的影响。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局势、大量不断涌现的全球化话语和相关文献、不断被激发、辩论和改变的各国教育改革,本文无法也无意囊括所有文献的讨论,只是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考线索。
对某些国家、地区和群体的人们而言,全球化象征着开放疆界和经济活力的新时代想象(例如美国、中国某些地区),但对其他国家、地区和群体的人们而言,全球化却象征着压迫剥削的新帝国主义势力或愈益异化与疏离的世界(例如亚非的第三世界国家)。究竟全球化提供怎样的社会想象和提示?全球化是“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抑或“空泛却霸气的定义名词”?全球化的话语有哪些论辩的重点?全球化的话语所描述的因素和变化,对于理解教育现象或变迁提供怎样的参照概念?
一、全球化的内涵和论辩:扩散现象和问题反思
根据赫德、麦格鲁、高登布雷特和裴若顿(Held,McGrew,Goldblatt & Perraton)等学者的看法,全球化有不同的类型③,大体可归纳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2] 经济全球化的层面强调资本、生产、交易的跨国流动;政治全球化的层面强调民族国家的疆界、权力与控制力受到更多外来的影响、区域或全球性政治组织日益增多,且逐渐增加其影响力;文化全球化层面则涉及本土与外来文化互动的可能过程和结果,涉及文化冲突、文化混杂(hybridization)、意识和认同的问题。此外,全球化也涉及人口移动、通讯、生态危机、环保、人权和社会问题等诸多面貌和复杂议题。
由于全球化仍是个“被结构化与结构中”(structured and structuring)的历程,相关的辩论也持续进行。全球化是一个单因现象还是多元决定现象?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看法。法国经济学家阿达(Jacques Adda)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3] 但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者,则反驳经济全球化有过度化的偏失。例如赫斯特·汤普森(Hirst Thompson)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许多质疑[4],凯特·纳什(Kate Nash)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涉及政治制度、权力、社会运动和文化政治的复杂历程,而不只是资本主义的扩散发展过程。[5] 英国学者杰索普(Bob Jessop)在《全球化的反思及其非逻辑》(Reflections on Globalisation and its illogics)一文中,强调全球化并不是一组因果机制,而是在特定的结构脉络(structure contexts)中,由多边、多元、多中心的历程序列所产生的复杂、混乱、多元决定结果;全球化是一种包含的结构脉络,提供一个“行动的地平线”(an horizon of action),让当代的人在行动上是本土的,但思维却可能是国际化的,从中开展其累积的策略和经济计划的引导方向。[6]
因此,“本土的”(local)概念仍是全球化概念中相对重要且更具实质意义的。从多元文化或空间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全球和在地的辩证关系(global-local dialectics)是指全球和在地并不是一组二元对立或绝对分化的概念或现象,在地是全球化现象具体发生的真实基础和可能脉络,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强调“全球本土性”(glocality)就是从本土的空间脉络去检视全球化的产生过程。[7] 不同社会往往会有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关联的方式,参与构成制度关联方式的明显或隐藏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或了解全球化之时,本土的具体理解和因素关联解释其实是关键基础。
哈维认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巨大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的转变,这种历史断裂构成了后现代思想存在的基础。但他强调,在变化背后,资本主义积累的潜在逻辑仍继续运作,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连续性。[8]
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析,到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意像以至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社会连带的基础不断松动,人们的社会分工和交换越来越专精、复杂,在不同时空的进出和流动频繁更加快速,传统社会阶级或家庭的图像不断改变,社会或家庭的功能也持续分化(外包)。现代生活的拼贴和颠覆,例如陌生/熟悉、外来/本土、时髦/传统、虚拟/真实、前进/退缩、迎合/抗拒等概念或现象的并陈,都呈现社会系统中杂糅又矛盾的特质。全球化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特质,因此我们也被迫改变我们与世界遭逢的方式。透过全球资本主义、跨国媒体和科技,全球的政治、经济、消费和文化呈现某种相似性;但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多本土的特质、不同声音和文化差异性也被激发和看见。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区分了“全球主义”、“全球性”和“全球化”三个不同层次现象和概念(参见表一,笔者整理)。[9] 贝克以全球资本主义作为全球化的根本基础,全球主义涉及经济层面、全球性涉及文化层面而全球化涉及政治层面。
表一 贝克对于“全球主义”、“全球性”和“全球化”的区分
定义和内涵特征和表现
1.世界市场宰制的意识形态或新自
1.世界市场对政治行动的排挤或
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取代
2.经济帝国主义
2.政治与经济的区别被消除
全球主义 3.不同立场
3.一切事务均以经济思维为主(单项
(1)肯定的全球主义 因果关系、经济主义运作、社会多
(2)否定的全球主义(包括黑色、 面向性简化为经济面向)
绿色和红色保护主义者④)
1.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 1.在他者的影响和对照下,我们如何
中(世界是指差异性和多样性,而 在彼此的区辨中认知自己?
社会是指非整合性) 2.世界社会的自我认知将在何种程
全球性2.全球性是不可逆转的、多中心的、度上与行为相关?
因事而异的、政治的
3.世界社会是可以被认知和具有反
身性的社会
1.跨国行动者及其权力机会取向认
1.跨国空间、事件、问题、冲突、生涯
同和网络的运作史的强化
全球化2.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受到打压和穿
2.对全球/地方的辩证关系,应该透
透的过程 过时空事件的差异加以理解、探询
其不同的程度、密度和规模
贝克以“二次现代”的概念取代“后现代”,第一现代强调文化认同、民族国家的世界图像,第二现代则强调全球化时代的解构和去中心化特质,以及全球性的不可逆转。全球性是否不可逆转?这其实仍是有争议的,所谓全面的、真实的全球化是否真正发生了?还是我们其实只是将“国际化”加以夸张?而全球化仍是话语和预测的成分居多?全球化对于各国的教育或不同社会位置的教育参与者而言,究竟是怎样的趋势?是正面的利益还是负面的冲击?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对上述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二、全球化话语与教育:“竞争求胜”或“社会正义”?
(一)四种全球化教育话语
针对当前全球化与教育的许多论述,陈-提伯肯恩(Jennifer Chan-Tiberghien)归纳出四种主要研究取向、研究焦点和途径(参见表二)[10],其中教育重建(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和(部分)教育制度主义(educational institutionalism)与贝克所提的全球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部分)教育制度主义和教育多边主义(educational multilateralism)则是对“全球性”、“全球化”的响应;全球社会正义(global educational justice)则强调对上述多重现象的批判并提出可能的对抗策略。
表二 教育全球化的四种研究取向及其研究焦点和途径
教育全球化的研究取向 研究焦点途径
教育重建经济别无选择(TINA)
教育制度主义文化异种同型(同晶体现象)(Isomor-
phism)
教育多边主义政治协力合作(Cooperation)
全球教育正义对抗霸权(counter-hegemony) 追求多元性的多元人群(DPD)
*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 DPD:diverse people for diversity
(资料出处:Chan-Tiberghien 2004:194)
“教育重建”的话语基本上是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为基础,基于全球竞争和国家竞争优势的考量,强调国家教育改革。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为基础,英、美、新、澳等国于1980年代开始公共部门的改革,企图以自由市场取代国家管制,以自主管理取代传统行政。改革的主要趋势是小政府、大市场、去中央化、松绑、教育私有化、竞争等,中小学和师资培育的改革,高等教育的去中央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学校课程的重构等。[11~13] 乔佰和莫(Chubb & Moe)的话语可作为此思想的代表,他们以美国私立中等学校的制度层面和人们如何选择的个人层面交叉搜集相关数据,研究发现私立学校的制度在响应市场需求时最为有效,因此极力鼓吹公立学校进行制度改革,以吸引学生,提高组织效率。[14]
“教育制度主义”是指不同国家追求相似的教育文化,例如大众教育的扩充、国家教育科层组织、国家课程、妇女就学率的提高、社会科学的课程。唐和西米诺恩(Daun & Siminou)指出,过去二十年来,欧洲国家在教育政策上似乎有某种世界模式(world models),以瑞典、法国、德国和捷克四国为例,去中心化、去规则化、选择机会的扩增、增加私人兴学的资助,以及在管理模式中注入许多新要素。[15] 马丁·卡诺依(Martin Carnoy)也指出,全球化对教育的冲击主要在三个方面:在财政方面,大多数政府意图降低公共教育支出的财政压力,谋求其他的财政支持以支撑教育扩充;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政府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期许,促使政府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因此扩增大学的就学机会,也相对提供给女性更多高等教育就学机会;在国家教育质量方面,因国际的比较而带来了国家教育素质的提升,尤其是数学和科学方面。[16]
“教育多边主义”则是基于左派的观点,对经济或文化全球化的话语进行批判,尤其质疑国际组织(例如OECD、World Bank、WTO等)对于提供普世的人道主义或民主教育的贡献。因为上述组织往往受到强权国家的操纵,无法让不同地区国家的权力获致平衡。戴尔和罗伯森(Dale & Robertson)强调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其具体实践是透过政府机构或个别行动参与者所进行的诠释和行动。[17,18] 对于所谓“共同的世界教育文化”(a common world educational culture,CWEC)的名词加以解构,分析目前其内在实质是“全球建构的教育议程”(globally structured educational agenda,GSAE),后者实是强权国家的主导建构,并非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进程。
“全球教育正义”的话语主要是基于对上述三种研究路径的总批判和尝试超越。陈-提伯肯恩认为,虽然教育多边主义尝试批判全球化的缺失,但上述三种途径其实都未能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⑤。因此她尝试结合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认知正义(cognitive justice)和去殖民化的方法论(decolonizing methodology),开创第四种全球化与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路径,也试图颠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意识形态的霸权。其研究途径和对抗策略,基本上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策略联盟,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社会运动,有后结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对于认可(recognition)和发声的强调。这其中涉及分配正义,也涉及认可正义。
综观教育重建论和教育制度主义,两者的动机大抵是寻求改变的参照架构和永续竞争力,改变的驱动者或主体可能包括国家、社会组织或个别行动者,改变的具体策略是寻求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借用或移植、教育资源的相互流通,以此造成国际教育议题的相互影响(全球教育话语的形成)、国际文化或知识内涵的相互影响和涵化,逐渐产生镶嵌的制度和政策。因此全球教育改革或变迁往往有“趋同”(convergence)的趋势,趋同并不是一致性,而是一种密切的关联,类似因素的聚合或外在形式的模仿;但源于各地或不同行动者的特殊条件和特性,例如历史、社会脉络、经济、文化和价值取向等,仍会造成各地方教育的差异和特色。
但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的角色如何?在全球化的概念和冲击现象中,民族国家的权能似乎受到许多国际竞争话语和国际组织规约的冲击和牵制,因此对于各国教育具有相当的影响。但若认为民族国家就此失去其教育的自主性则未免言之过早。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是使民族国家瓦解或失去其统治权能,因为自主性的部分丧失并不就等同于统治权的丧失,民族国家的权力其实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转换到跨国组织或地方组织的层次上继续运作其影响力,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统治权力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
全球社会正义的批判涉及对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麦克拉伦和法拉曼普尔(McLaren & Farahmandpur)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脱掉手套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that takes the gloves off)或“护卫富人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or the rich)。[19] 不同阶级在标榜自由选择的市场中,往往受益程度不尽相同。例如英美教育改革中强调父母的教育选择权,市场表面看似自由,但只有中产阶级父母才能在所谓的自由市场中拥有足够的消费信息和教育购买力。美国学者阿普尔(Michael Apple)也以“谁的市场?谁的知识?”质疑新右改革中标榜的自由根本是有权力者的自由(包括政府、宗教领袖和新中产阶级的家长们)。[20]
(二)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批判教育学观点
从全球社会正义的角度而言,全球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尤其是指当前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所展现的军事和外贸扩张野心、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掠夺和文化侵略等,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明显象征和恶劣罪行。全球资本主义不单纯只是商品的标准化或全球销售,它还通过商业的利益入侵教育场域⑥,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逻辑和分工社会关系的全球辐射,以及“商品化”或极端“物化”思维的全球扩散。上述后果涉及复杂的因素:包括国家追求整体资本的累积和国际竞争力,对自由市场持过度乐观的想法(因此强调删减公共预算、一切民营化),对高利润、低价格的追求和资本的累积(因此强调减少贸易税、低廉工资、弹性工时等),对于少数族群公民权的漠视(对移民法的高度把关、社会歧视或差别待遇)以及资本家或中产阶级对剥削、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不义的社会事实采取麻木或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全球资本主义透过各种方式推销“消费”的人生观和“人人都是消费者”的意识形态,上述的意识转移或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可能观察和敏感度。以哈耶克(Hayek)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经济效率和自由为基础,主张削减政府的不当管制和市场介入。但市场总有失灵⑦[21] 的时候,教育事务的公共性和外部效果使得教育很难以完全市场化的逻辑运作。
奥曼(Allman)强调,必须体会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辩证的精神,对资本主义进行“辩证的阅读”(dialectical reading)。[22]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的运动和发展,其实是人类生产其物质世界和意识的结果,唯有体会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开放的精神(而非必然的因果解释),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劳动异化的问题加以剖析,并进一步进行革命性的社会转化。奥曼强调批判教育学应该更坚持革命的实践,主张批判的革命教育学(critical revolutionary pedagogy),坚持阶级分析、了解资本主义的根本运作逻辑是批判教育学的首要任务。根据批判教育学者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图像的描述和批评,笔者归纳其要点呈现于表三。
表三 批判教育学者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图像的描述和批评
全球资本主义
核心价值追求最大利润、经济扩张以求取资本累积
支配性的逻辑
运作逻辑1.积极建立合乎核心目标实现的相关社会事务和制度
2.扫除一切阻碍其核心目标实现的相关事务和制度
3.透过政治、商业、军事等多方面进行强制性的资源掠夺
权力主导者 跨国资本家以及与资本家合谋的政府
生产方式阶级分工、剥削
社会关系支配和被支配
教育场域符应经济之发展需求;教育商品化;绩效管理
产生问题民族国家的疆界和认同问题、在地产业或文化的危机所得差距扩大、贫富
不均、失业率提高、工人、妇女或被压迫阶级劳动的异化、生态问题
政治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抨击,大多针对全球资本主义根本上取代了政府应有的公共权力和社会责任。英国学者赫兹(Hertz)在其《当企业购并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之死》一书中指出,当前许多跨国大企业,在第三世界全力投资和设厂并财援人民的行为,表面看似慈善,但严格检视其背后的动机,仍与商业扩张和文化侵略有关。她指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对于大企业的敬重和依赖,已悄悄地让大企业接收或取代政府应有的决策视野和公平判断,政府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和积极寻求者的身份已然变质。[23] 英国学者约翰·格瑞(John Gray)认为资本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充满危机的,因为其中夹杂着经济泡沫化的不安和巨大的不稳定性,所以全球资本主义无法长久,只是一种“虚幻曙光”(false dawn)。[24] 左派人士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并成立相关的跨国公民组织,包括:反G8高峰会(anti-G8 summit)、反WTO论坛(anti-WTO forum)、世界社会论坛⑧(World social forum)等。
正如荷兰学者温特(Went)所言,上述抗争是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坚持与改变可能性的期待:
这样一种正面的另类出路,需要的是去质疑全球化、自由贸易以及市场专制。以往从不曾像现在这样,在可能与实际之间有如此大的鸿沟。彻底地将工具、资源与结构重新分配并加以民主化,仍然是我们要奋斗的世界图像。主流的看法虽认为社会将不可能被改变,但左翼组织、工会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必须找到出路,以重拾希望,并重建一个可信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的另类出路。这并不简单,但绝对必要。[25]
问题是除了对资本主义或全球资本主义极端抗争或拥护,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乐观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感以及创造性毁灭,反而使之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调整能力。香港地区学者许宝强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地域似乎更应强调对市场、私产、会计和发展等概念的再思考,即重新争取有关自由、个人利益、理性与美好生活的文化统识。[26]
有些地区或许可以抗拒全球资本主义(尤其当全球资本主义被等同于美国主义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影响的化外之民,但台湾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区域政治、军事关系以及经济活动和劳动条件的历史积累等问题,使之无法自外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或成为天真的全球化反对者。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置于全球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中理解,以下即以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绩效管理的问题为例,了解其与上述生存策略的内在关联。
三、新自由主义下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绩效管理的迷思
(一)高等教育变迁与新自由主义的绩效管理模式
以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而言,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大众高等教育的逐渐形成,基本上是响应经济成长的需求以及民众受教育权诉求的结果。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目标、运作特性以及知识生产和传递特质面临重大转变,大学的目的不再只是少数精英的培养以及神圣知识的传承与创造,而是逐渐转向对世俗世界的积极回应(尤其商学院或理工学院的发展);而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英美国家为主的新右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经营管理、绩效等经济领域的概念不断被强调,并跨界成为政治集体行动的准则,影响所及,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口号也被强力放送和积极运作。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影响下,高等教育市场化或管理绩效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有些学者以全球化作为分析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核心概念[27],但笔者个人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现象或问题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层面。一方面,全球化作为一种多因现象,其根本原因应与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有关;另一方面,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因素应是高等教育本身迅速扩张,并非全球化的直接影响⑨;此外,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其具体实践仍必须通过政府机构或个别行动参与者的诠释和行动。此外,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讨论不应只是描述其过程和现况,也应展现解构和建构的思维,例如对市场化意识形态和迷思的批判以及对公民社会如何形成的思考。[28]
回溯近代历史,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外在名称不变,但其内在支配话语却是从文化的话语一路转向宗教的、政治的乃至经济的话语。支配话语的转变,强烈影响在此场域所有参与者内在的认同、价值意识以及行动取向。大学话语和实质的内在转变,深究其原因,在于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大学之超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或政治力量作为保护(保护是一种赋予相对自主性的关系,与控制不同),才能与社会保持某种距离,才能观察和批判社会、孕生思考和创造的文化。而近代以来,不论中外,大学的保护伞不断地被移开,政府希望大学能自力更生而缩减补助,大学被迫直接与社会接触,甚至必须从社会中获得其经营费用以维持运作。此外,随着世俗化的影响,大学越来越多,资源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在庞大的财务压力下,社会的资源和支持成为必需,商业的、现实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如同浮士德以自己的灵魂和魔鬼交换)。[29] 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以自己切身的学术行政经验,分析大学为何会一直走向商业化的原因、危机和解决之道。[30] 为了筹募经费,美国大学不论是校际球队、科学研究、教学课程(包括各种进修推广班和函授教育)都朝“如何赚钱”的思维前进。大学的理想在这样的空间中被挤压或遗忘。
纽曼、康特瑞和斯卡瑞(Newman、Couturier & Scurry)在其《高等教育的未来——修辞、事实与市场的危机》一书中,分析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31] 他们提出,一般大众和企业人士倾向于世俗的实用价值,政府官员关注国家竞争力和财政效率,而大学校长则关注经费的短缺和竞争的压力,以及大学学术理想和教学品质的衰微。有关大学“修辞”(理想)和“真实”(实际情况)的巨大落差,应该被正视和解决,这些落差由来已久,且日渐严重。例如,理想上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要教导学生如何学习,但学生却被要求背负主要的学习责任,并为自己的学习失败负责;理想上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要献身于教学,但事实上在大多数四年制学院里,大多数老师的时间、精力和创造力都花在研究、出版和外界的咨询上;理想上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要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但事实上政府财政支持方案的提供越来越多强调某些优点(merit-based),而不是针对学校的真实需求(need-based),因此学校也就越来越注意招揽那些最优秀和家境最富裕的学生;理想上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要服务社会,但事实上学校却越来越注意如何在知名媒体(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提高排名;理想上高等教育机构宣称应提供基础和值得信赖的学术以服务社会,但事实上,上述理想已经衰微,因为企业对于研究的控制日益增加,学院内部利益冲突也逐渐扩大。上述博克和纽曼等人描述的问题,在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这涉及高等教育在社会变迁中认同的危机和问题。
高等教育的认同除了社会变迁的因素外,政府的管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来看,不断进行资本累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在资本无限增值的内在冲动下,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朝两个方向扩张。在国内,资本通过侵入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涵和范围,把越来越多的其他劳动者置于资本的剥削之下;在国外,资本主义通过侵入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置于资本的国际统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所组成,高等教育正是与劳动力市场最密切相关的领域之一。
(二)以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学术评鉴的问题为例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量和质的转变,可视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环,也与社会文化变迁有关。包括高等教育院校的快速扩充(回应人力资本论、大众受教权和私人财团的办学)、政府高教经费的缩减、高教学费的提高(基于使用者付费的概念)、高教资源的分配(政府根据权力精英的建议规划出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高教机构的学术品质监控和高教机构的生产力如何提高等。这些议题和发展不能都以“市场化”一词加以概括和解释,因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从解严前政府强力管制时的“教育部”大学到现今较为松绑的自主发展空间,其实与美国高等教育学府一向所享有的自主性并不相同。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其实仍在政府某些有形或无形的监控和管理中,尤其公立大学,从招生规则、系所增设或整并、评鉴、人事聘任、经费补助和使用等,其实“教育部”仍有许多监控的权力。更何况,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是一个内在讯息并不透明化的市场,再加上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其实“等级化”的现象比市场化更为明显。
2003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不当的评鉴后,爆发许多争议和问题,尔后台湾地区人文与社会领域的一些学者即极力呼吁“教育部”不应以美国的、自然科学的、量化的学术标准盲目套用在人文社会学科的评鉴之上。2003年底,许多学术社团串联,通过一个研讨会⑩ 和网站发声,对于台湾地区“教育部”和“国科会”以SCI、SSCI、TSSCI作为学术评鉴指标,人文和社会学者疾言控诉其乃不当之举,并揭露其中许多意识形态和权力操作的问题,其中重要的批评有三点:(1)上述评鉴指标的呈现,透露出主其事者有“美国化”等于“国际化”、等于“全球化”此种褊狭的学术意识形态;(2)以SSCI、TSSCI作为大学学术品质评鉴标准既不公平,也不等于国际化,只是彰显了计量经济学的学术权力;(3)国际竞争力并不等于学术的全美语化和对美国的全面认同。[32]
上述第一、三点其实与台湾地区的学术殖民情境有密切相关,也有历史脉络可循。二战后,与美国关系的密切和留美学生人数居高不下,造就了台湾地区学术界以美国为学术宗主国的历史现象。叶启政在1991年前就曾从“文化优势的扩散”与“中心—边陲”的对偶关系分析其中的认同和成因:“科技的统治是结合商品化之市场经济模式来展现的。它如何展现就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特质有密切的关联”。[33] 对于“中心国”(或称“上国”)文化符号的拥抱,其实就因为它是一种市场高利润商品的象征,其衍生的附加价值不只是实质利益,也包括社会地位,这可由目前政府或各校的学术奖励办法和聘任、转任或升迁的考虑条件中获得清楚例证。
学者批评,以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而言,台湾地区学界如果只是盲目仿效美国学术界的引用指标,是严重扭曲台湾地区学术的主体性,既缺乏反省的主体意识,也轻视了中文作为学术表达和社会沟通的重要性,同时忽略了台湾地区的地缘认同;台湾地区学者如果只一味以跻身欧美著名外文期刊为荣,却未能以自己所学找出本土的研究题材和特色,未能提供重大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实是未善尽学者的社会责任,也忽略了台湾地区学术在国际场域中的比较立足点。
从国民党时期党国独大的思想控制,到现今科技官僚以主流量化经济学为圭臬的大学评鉴,都是对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的严重伤害。依生产力的高低(而所谓生产力的标准和定义是由上述政府认定的权力精英决定),高等教育机构被分级并依不同的级数给予经费补助(这同时也是一种市场价格的定位和社会地位的认定),依学科学术性的高低和发表产出量,给予不同的评价和奖赏。通过政治权力和专业意识形态(真理政权)的合谋操弄,在现代社会中不被看好的冷门人文学科,往往在上述的标准中,成为高教场域中受到贬低和忽视的一群。事实上,所谓“绩效”的定义,不应只是由政府和所谓技术专家所订定的外在标准,组织内部成员由下而上发展出来的真实觉知和文化共识也应被重视,这是一种内在绩效的概念[34],而这种概念应是建立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而非检查和监控的权力关系。
生产场域受到大学许多研究成果和话语的影响,但大学场域中的学术或教学也受到生产场域极大的影响。我们可将之称为“外在的内在化”(outside in)和“内在的外在化”(inside out)。[35] 前者是将市场化、商业的法则注入教育机构,重新改造教育组织;后者是指教育机构如何将自己的教育产品商品化,并且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知识经济”的前提下,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著作点数”的规则下,学术劳动的价值都是可以被量化换算和指标化的。上述大学与生产场域的密切关系,促使我们在理解全球化话语时,必须有所觉察。例如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有关知识经济的相关研讨会(11)、科系或课程在大学纷纷设立,目前已有大学设立“知识经济学系”(12)、“文化产业管理与经营学系”、“风险管理学系”。台湾地区“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基金会”(13) 于2005年5月成立,并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开始运作,正对台湾地区的大学展开评鉴。事实上,除了高等教育评鉴外,中小学信息教育、数字学习的强调、全民学习英文的狂热,也都可以看出全球资本主义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影响。
四、结语:变幻的文明图像与各种可能性的积极理解和响应
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到今日互联网时代,我们当前所体验感受的时代变化,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有迹可寻。国际的互动交流、国际化的开始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久长、幽远。全球化的话语是提醒或说明(虽然有时甚为夸张)其强度和界面的特殊性。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生产、传输和获取方式已经与之前纸张、印刷的时代大不相同。虽然有人认为网络上大多只是零碎(甚至不正确的、价值偏颇的)讯息而非完整或深入的知识体系,但网络使得信息快速被搜寻、浏览、汇聚和整理,似乎也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更广博的可能的学习空间和基础,也将为学习赋予不同的面貌和动力。
教育学术话语或教育实践领域往往具有极强的“再脉络化”和“被动塑造”的特性。再脉络化是指教育的话语几乎都是其他社会或学术场域的话语冲击、借用或推移;被动塑造是指民族国家或市场作为教育体系的主要资本资助者,民族国家或市场所遭逢的经济冲击和全球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不同时期教育变革的基调。作为国家生产力常备军的重要训练基地,教育的话语或实践必须是“顺势而为”的,如果资本主义是许多影响教育趋势的深层结构因素,那么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转折、关键因素、矛盾等各方面都应该都更深刻了解、反思批判和谨慎响应。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也应该超越单一绝对的意识形态,在“竞争求胜”和“社会正义”之间求取可能的平衡。
如果全球化是一个充满权力和欲望的历程,如何不要别人强加的全球化?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如何觉察人的价值、意识、生活和行动受到全球资本主义或隐或显的影响?这些都是必须深思的问题。如果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那么问题是:这个进程究竟是开放参与的,还是垄断的历程?是一个只能被动接受的,还是一个可以积极对应和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中心放射,还是一个可以容许不同文明相互对话,呈现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过程?有关教育与全球化话语的探究和思索,其实隐含着世人在不同层次上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探询,探究的过程和结果不只与个别国家的命运兴衰有关,也与个人生命或全人类过去和未来的文明图像息息相关。
注释:
①从1996年开始,《天下杂志》陆续制作了“海阔天空”教育系列影片和每年的教育专刊;2004年针对台湾地区外籍通婚与外来新移民现象,出版《新台湾之子》专书。参阅天下杂志网站http://www.cw.com.tw/。
②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89)所谓晚近资本主义弹性积累体制(a regime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现象,是指由资本高度流动性和弹性造成原有的产业生产及劳动过程渐趋分散化、个别化和多样化。一方面通过时间压缩效应以消除资本累积的空间障碍,另一方面藉由加速资本回路的流动性,使资本能够在此弹性发展中迅速再结构,这种弹性调整以因应动态变迁的做法成为目前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
③戴维·赫德(David Held,1999)等人提出一个分析全球化的架构,其中包含四个维度——全球网络广度、全球相互联系强度、全球流动速度、全球相互联系影响,再搭配四种维度——基础设施、制度化、分层化、交往方式等,归纳出全球化的类型,包括密集、分散、扩张、稀疏等四种全球化类型。
④反对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团体是基于不同的关怀而有不同的反对立场:黑色主义保护者是指传统价值和民族意识拥护者;绿色主义保护者是指重视环保和生态的拥护者;红色主义保护者是指左派的拥护者,通常是正统马克思信徒(Beck著、孙治本译,1999:13)。
⑤针对Chan-Tiberghien认为多边主义的学者还是在新右意识型态框架下分析,Roger Dale和Susan Robertson可能不甚同意。因为在他们主编的期刊Globalization,Societies and Education中的文章或访谈非常强调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
⑥麦克拉伦和法拉曼普尔在《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教学》一书中,描述了美国中小学教育如何受到财团商业活动的入侵。例如米尔肯(Michael Milken)原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投资客,后来转向教育市场,成立“知识宇宙”(knowledge universe)专门生产教材和所谓益智玩具,获利非常可观;全美至少有234商业机构以提供教材名义进入公立学校,包括提供影片、教科书或计算机软件等;因接受厂商赞助的视听器材,学校中的教学频道(Channel One)以播放厂商相关商业广告影片作为回馈等(pp.166-168)。
⑦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在某些外在因素影响下,使得市场在自由运作下无法达到最有效率的结果。造成市场失灵的可能原因包括:竞争失灵——如产业的经济规模达到自然垄断的地步、产品具有公共财性质,私人无法提供、商品之生产或消费具有外部性、不完全市场、市场信息不完全、失业通货膨胀与总体失衡、政府基于效率之外的考虑介入等(Stiglitz 1986,转引自瞿宛文2003:235)。
⑧参见世界社会论坛在印度网址http://www.wsfindia.org/index.php以及Glasius、Kaldor、Anheier和Holland等人合编的Global Civil Society 2005/6(London,California and New Delhi:Sage,2006)。此书为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SE)全球统治研究中心与公民社会中心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民社会中心所合编出版。
⑨参见林本炫《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载台湾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主编《市场、国家与教育——教育社会学的分析》,2003年版,第135-164页。
⑩“反思台湾地区的(人文及社会)高教学术评鉴研讨会”,2003年9月25~26日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研讨会网址:http://www.hss.nthu.edu.tw/~apcs/pages/act/kao.htm。会后根据学者之意见,整理出十点主张和说明,见http://www.hss.nthu.edu.tw/~apcs/pages/auucement.htm。
(11)例如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主办“知识经济与教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12月14~17日,中国台湾:台北。
(12)台湾私立南台科技大学与台湾私立真理大学都设有“知识经济学系”。
(13)http://www.heeact.org.tw/.
标签: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