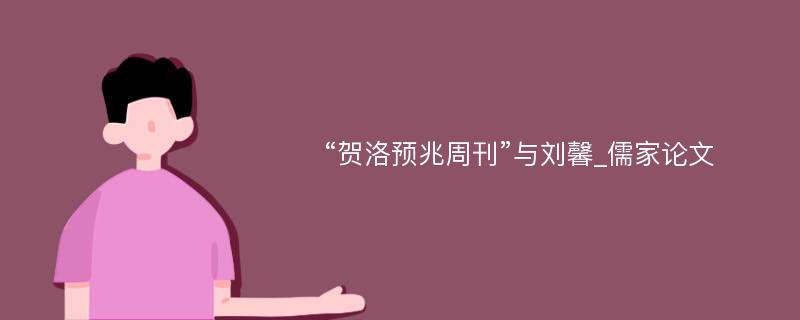
河洛谶纬与刘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谶纬论文,河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河图、洛书乃是汉代谶纬之学兴盛的思想传说根源。从文献记载考察,至少自春秋战国以来它已在流衍传播之中,但对其意义内涵的确切阐释却只能追溯及刘歆。以刘歆的这个阐释为核心,汉儒将当下及前代流传下的相关资料汇为一炉,并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主干,整合融汇出汉代的谶纬思想体系。因此,刘歆的阐释成为汉代谶纬之学的知识生发点。以此生发点为据去探求谶纬之学的体系内容和发展脉络,才能真正把握住谶纬的内在意义理路。如从现代的学术观点审视,刘歆谓伏羲画卦等于界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其意义是空前的,绝不比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推黄帝为中华始祖的意义小。但近来的谶纬研究者虽然不少,却恰恰于此注意多有不及。如有学者总结有关谶纬起源之十二说,唯独未注意到刘歆之说的意义,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①。本文拟由此入手,分析谶纬形成的原因、影响和流变,冀就正于同仁。
一、衰世预言与谶纬
历来谶纬浑言无别,但其间也有学者指出二者的内涵性质有异,提出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此说以《四库全书总目》言之最辨,其《易》类六《易纬坤灵图》案语谓:“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又指出,纬多出儒者推阐,虽“渐杂以术数之言”,“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但纬书终究“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②。此从内涵与性质之异对谶、纬二者严加辨析。是后有较多学者附同其说。但另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不同看法,如陈槃在《谶纬释名》中指出,谶、纬二者异名同实③。是后有学者循此思路研究指出,不论从汉魏人对谶纬的理解来说,或者就谶纬的实质来看,谶与纬只是异名同实。只是追索到谶与纬的产生时代,自然谶先于纬。因为在经学兴起之前,已有谶语流传,在经学定于一尊之后,谶于是依傍经术而形成纬书,于是有“经谶”、“经纬”、“谶纬”等名号。谶依附于经的最大特征就是导致孔子的神化,这对汉代推尊孔子极有裨益,后来郑玄相信谶纬与此有关。汉代今文经学衰微,于是魏晋以后谶纬屡遭禁绝,纬书残佚,纬学不绝如缕,但谶语则历代广泛流传,所以谶与纬比,可谓源远流长④。按照思想意识的发生顺序看,确实应该谶先于纬,谶在纬先。
谶本指预言性谶语,谶语往往与卜筮占验相联系,因此有所谓谶书,如《后汉书·张衡传》:“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汉书·贾谊传》:“发书占之,谶言其度。”说明至少西汉初已有谶书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谶言其度”的“谶”字,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策言其度”。《史记·赵世家》:“秦谶于是出”,同样文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谶”作“策”。策又指蓍策,《战国策,秦策一》:“数策占兆”,《庄子·外物》:“七十二钻而无遗策”,皆策用作卜筮占验之证,是谶之义的互证。
从文献记载上看,谶的出现要以《史记·赵世家》“秦谶于是出”为最早,当秦穆公时代。但从谶作为占验性预言的本质,及人们预知未来的希望看,谶的出现必定很早。人们出于对自身和社会命运的关怀,尤其需要预知未来,而且越是世衰或社会危机时代,人们对预言的关注愈是急切,这是预言性谶语出现的社会心理基础。以周代为例,西周末年的王朝危机,已在迫使一些政治家密切关注未来天下形势的变化。郑桓公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向史伯请教。史伯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认为王室骚乱,周室必败,必要出现“姜、赢、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国语·郑语》)的局面,断言秦、晋、齐、楚作为未来大国将相继兴起,告诉郑桓公应避地济、洛、河、颍之间。其中史伯又提到宣王时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其实这就是一个谶语,其后应在褒姒,这是西周末社会政治危机时代的产物。《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按辛有预言非专为秦、晋迁陆浑戎于伊川而发,而是预言周室衰敝,导致戎狄强大,并陆续入居中原而侵凌诸夏,是接着史伯“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讲的。总之,西周的衰败,引致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于是生出上引那种消极性的未来预言。《左传》一书好借占梦卜筮作各种预言,反映出古代相信巫卜占验的神秘思维习惯,其中颇有与谶语相近者。如僖公五年预言虢亡的童谣,昭公二十五年预言昭公出奔的童谣,由于都采用了韵语的谣谚形式,与后世的谶语尤为相类。这类关系家国兴亡的政治预言,最易引起人们关注,也最易传播保存,在谶言中占的数量比例也最多。《管子·侈靡》亦曾托于齐桓公、管仲之口记载了一个预言,其曰:“问:‘运之合满安臧?’‘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律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对此预言,学者多有说解⑤。应予指出的是,既托于齐桓公、管仲之口,必是立于齐国的立场设言。细味其义,所言应与周政将移、齐国将变有关。郭沫若据“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认为所言乃西汉初惠帝在位吕后专政之事,并为此专作考辨⑥。其说不妥。其所作预言,除一般泛说之外,必应与齐国有关。故《管子集校》引章炳麟曰:“此管子所定之谶,托桓公问以明之也。”似为有理。如认为“妇人为政”乃吕后专政,倒不如说是王建在位时君王后主齐政更为相近⑦。其大背景则与春秋战国时代周室既衰,天下行将有变相关,尤其应与秦国强大行将统一六国有关。如“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人君声服变”、“国之称号亦更”等,读之都令人有上述之感觉。又战国政治变常,“妇人为政”除齐国外,秦昭王母宣太后亦曾擅秦国之政,宣太后又有秽乱宫闱之事,此殆《荀子·强国》所记对齐相言“女主乱之宫”的背景。秦宣太后稍早于齐君王后,同为战国后期妇女干政的现象,并为世人所瞩目。齐国之士有鉴于此,于是托为此谶载入《管子》。谶语是世衰或社会危机时代的意识反映,是以秦代有“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等不吉告凶类谶语。秦以后每朝末世都必有此类谶语。
与此类消极谶语相对,还应有积极性预言,即能满足人们对未来希望的那种预言,希望能有圣人王者出而收拾残局,还天下以太平、安宁与繁荣。因此,就谶语本身的内容而言,它可能是荒谬的,但由于它担负着满足人们某种心理预期的社会现实功能,因而它是必需的。至于谶在谶纬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可举一事明之。《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因见“图纬虚妄”,遂上书请予禁绝;然其通篇内容,或言“谶”、“谶书”、“图谶”,而绝不及“纬”之一字,谶在谶纬体系中的代表意义,由此可知。
二、河洛受命传说与谶纬
由谶纬的话题必然要引出与之紧密相关的河洛受命传说,它在先秦迄汉代是传播较广又备受人们关注的传说主题。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西周末直至秦汉之际的衰乱积弊,应是河图、洛书传说产生传衍的社会根源。从春秋战国直至汉代,河图、洛书作为一较有影响的传说长期行世,后发展为汉代关于圣王河洛受命的新天命说模式。它具有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重要影响意义,在汉代的学术思想中备受关注。为便于分析,现仅据截至汉初的文献记载所见,搜寻其例于下: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⑧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管子·小匡》)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图,洛出书。(《文子·道德》)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殷灭,周人受之,河出圆图也。(《随巢子》)⑨
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吕氏春秋·观表》)
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椰……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
圣人有国……洛出服(符),河出图。(《大戴礼记·诰志》)
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新语·慎微》)
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淮南子·俶真》)
大哉关雎之道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韩诗外传》卷五)
臣闻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汉书·晁错传》)在先秦及汉初的记载中,能较多见到“河出图,洛出书”这类陈述,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但若联系其上下文,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圣人明王、至德盛世或诸种祥瑞灵异之物相关,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它是圣王或至德盛世降临前后的一种征兆瑞应。此后大约在西汉中后期,河图洛书传说引起汉儒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宋蔡元定指出:“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⑩他指出河图、洛书与伏羲、大禹的关系,乃由汉孔安国等人最初明确指示。按:
河图,八卦是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11)
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尚书·顾命》孔传)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尚书·洪范》孔传)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所言不知何据,但这却是汉儒关于河图洛书的明确看法。汉儒又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上》:“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今文学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歆父子推演灾异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诸人所不及,可见刘歆本为今文学者(12)。虽然刘歆本为今文经学家,但后来因表彰研治古文诸经而在学术上有所转变,乃至在学术史上主要被视为古文经学家。按《汉书·五行志》所言,汉儒关于河图洛书内涵的阐释,主要由刘歆作出,因而刘歆对汉代今文阴阳五行体系的构筑,其功实为董仲舒之后第一人。他利用先秦以来“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并通过自己的诠释,使蕴蓄于河图洛书内的天人感应式受命理论被发扬出来,由是汉儒融合《周易》阴阳、《洪范》五行及《春秋》灾异为一炉,构筑起今文阴阳五行化的所谓天人之学。同样受其启发,谶纬河洛之学转而大盛。河图洛书本是圣人受命的天降瑞应,它同时必然包含天下太平、世道清明的内涵,这原本是长期以来衰世之中人们的期盼。经刘歆之徒的推阐,不仅使河图洛书具有明确的意义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为谶纬之中的圣王受命提供了模式化的基本依据。此外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跻身河洛圣王受命的行列,这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河洛受命说既是春秋战国以来广为传播的一则神话,又是期盼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则原始预言。同时,它也为丰富汉代的经学思想内容,提供了可资取用的材料。
关于谶纬文献的形成演变,陈槃早就指出,《河图》、《洛书》之出在先,由《河图》、《洛书》更滋生《易》、《书》、《诗》、《礼》、《春秋》等纬书。后有学者沿此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洛》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13)。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反映了谶纬文献形成的先后次第,值得参考。还应指出的是,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直接与刘歆对河图、洛书意义内涵的明确阐发相关,是刘歆的启发极大地推动了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如果再追溯其源,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广为流传的河洛受命神话,充分反映了衰世之中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的一种期盼,那么,从此角度而言,河洛受命传说乃是为满足人们期盼而被世人制造出来的一个预言,而这正是所谓的“谶”。因此,若溯及汉代谶纬的起源原因,理应考察其前较早流传的相关谶语预言形式。
三、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
与谶纬的兴起及其思想内容相关,还有两个话题必须涉及,这就是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两个话题。其实此二者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在酝酿播衍之中。
前文的论述指出,在河洛受命传说中,本来包含着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期望。其实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河洛受命传说之外,其他形式的预言中也出现过有关圣王与太平的主题。《史记·周本纪》载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在当时应是一个较有名的预言,是以在《秦本纪》、《封禅书》及《老子传》中又先后出现过,所言年数小有出入,如“十七岁”又作“七十七岁”、“七十岁”等稍异,但五百年大数都相同。这应该反映出人们期望有霸王者出世,结束诸侯纷争的乱局,使天下太平。稍后《孟子·公孙丑下》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所言已由圣王代替了太史儋所言霸王,自是儒家本色。考太史儋年世应略早于孟子,又为周室太史,其影响必大于孟子,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当承自太史儋。此预言影响及于后世,《大戴礼记·礼察》:“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岁而不失”,是以五百岁为历史运行盛衰的一个周期大数。故司马迁绍述之以自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预言五百年的圣人大数又影响及于谶纬之内,如《尚书考灵曜》:“五百载,圣纪符,四千五百六十岁,精及天数,握命人起,河出图,圣受思。”(14)而且谶纬中进一步总结出圣人受命之“期”,或曰“期运”,如《论语撰考》:“河图将来,告帝以期。”(15)《春秋说题辞》:“《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16)这实际上是使圣人受命之期的预言抽象化为一般的律则,于是有此“期”或“期运”之说。
除孟子关于圣人五百年兴起的预言外,战国末邹衍则进一步抽象出五德终始循环论,即帝王之兴按五行相克的循环周期相代。值得注意的是,五德终始说中的帝王相代,必伴随有符应,所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如周文王时得火德,故“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吕氏春秋·应同》),按此帝王将兴伴有的祥瑞,与河图、洛书作为圣人受命祥瑞,其性质相当,而且文王赤乌丹书之祥亦见于纬书《尚书帝命验》、《尚书中侯》、《尚书中侯我应》等。
河洛受命圣王乃谶纬的一个主题,如从谶纬体系的性质结构而言,加上汉武尊儒的原因,又以孔子的圣人受命传说最为重要。儒家推尊孔子,如果从记载上追溯,记载列国大事的《左传》一书中,于昭公七年、哀公十四年及十六年,分别记载了孔子为圣人之后、西狩获麟及孔子卒三事,这是在史传经典上儒家开始对孔子尊奉有加。孔子圣人之后说在《论语》、《孟子》中发展为直称孔子本身为圣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明谓获麟乃孔子圣人的瑞应,孔子亦由此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顺着《公羊传》的道路,进一步肯定获麟乃孔子圣瑞,并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说成孔子获麟之叹,孔子为此作《春秋》自见于后世。谶纬以这些记载为根据,再加以推衍,于是使孔子跻身河洛受命圣王之列,并且成为谶纬的制作者、阐释者及为汉帝制法的玄圣素王。
汉代谶纬中被神化的孔子圣人形象,其实在汉初以来的儒家著作中已可见其端绪。如《新语·明诫》:“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哀)风化之失,以匡衰盛,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世之类。”察其所引《易》文字同今本有异,最大差异乃“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系辞上》作:“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引《易》乃配合整段文字表达对圣人的期盼推崇。这里的圣人不仅可以“平四海”、“一风俗”、“纪物定世”,而且还可以占图纬星历,知阴阳变化,“推演万事之类”,故如此圣人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久已期盼的受命圣人,而且又接近于谶纬中被神化的受命圣人形象。《新语·本行》则谓孔子“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王利器解曰:“图录谓谶纬,然则谶纬之道,汉初人即谓其托始于孔子。”(17)即孔子已被视为谶纬的制作者与阐释者。继陆贾之后,董仲舒极称孔子,推之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认识都被谶纬所吸纳,并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发展,即谶纬发挥儒家尊孔之义,侪孔子于古今帝王受命之列,并视孔子为古今圣王受命之集大成性代表,这是谶纬为推尊儒学而神化孔子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究其由来,乃儒家利用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又相继加以推阐、引导,使长期以来有关圣王、太平的理想与祟儒尊孔之义结合起来,并在谶纬体系中发挥完成,亦从而为河洛传说作出最终总结。
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理想,反映了人们摆脱世乱和期望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渴求。查太平说在公羊家的思想理论中最有影响。《公羊传》有所谓“三世”,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何休则分《春秋》十二公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是传文见“乱世”之明文,何休《解诂》所谓衰乱、升平、太平之说并非出《公羊传》本文,殆出于京房太平、升平、霸世所谓三世说(18)。查“太平”确为公羊家旧说,不始于何休,董仲舒已言,《春秋繁露·王道》:“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19)又如《汉书·儒林传》中公孙弘亦谓武帝已致“太平之原”。公羊家之外,汉代经师亦多言太平,如《诗·小雅·南有嘉鱼序》言“太平君子至诚”,《诗·小雅·南山有台序》言“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刘歆、郑玄为表彰《周官》,俱说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20)。如从汉代经师再往前溯,战国以来诸子多言太平者,如《尸子·仁意》:“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于玉烛,息于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是太平之世有诸种祥瑞。《庄子,天道》谓:“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是乃道家对太平的极度推崇。《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此相当于儒家治致太平乃制礼作乐之说。儒家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所以太平不仅仅为公羊家旧说,《大学》已结合道德修为修齐治平之说,把天下平视为儒者向往的最高境界,《孟子·尽心下》则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应是儒家理想对世道追求的一种回应。其他如《淮南子》的《俶真》、《泰族》等亦论及太平。太平理想在汉人中议论最多,如《论衡》的《是应》载儒者论太平瑞应,《自然》亦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明确把“河出图,洛出书”说为太平之世的瑞应。“致太平”则成为《太平经》一书的思想出发点(21)。综之,自战国迄汉代,太平理想在诸家思想中传衍颇广,其中较早且又较系统予太平境界以推阐者,可举《韩诗外传》,其书卷三曰: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平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
据此所言,太平之世乃是天人合和,政治清明,百姓众庶各安其生的和平富庶之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关于天地瑞应讲得相对较少,而是注重讲政治人事上的合理举措及其带给社会民生的安宁富足,因此这里所说乃是一幅现实具体的太平盛世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众庶百姓的理想期盼。考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说,有儒家与阴阳家之别。儒家太平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方案,人事举措,目标在政通人和。阴阳家太平主要是由天地瑞应与四时和气编织而成的天人感应图景,强调的是阴阳和合。后来纬书中所言太平在很大程度上富有阴阳家色彩。上引《韩诗外传》所言显然以儒家为主而吸收了阴阳家思想,并反映了众庶百姓的政治期盼与社会理想。秦汉国家也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目标,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会稽刻石:“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汉武帝时也招致儒术之士,“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汉书·田蚡传》)。总之,太平至少应是战国以来人们要求摆脱乱世、获得安宁富足生活的理想渴求,也曾作为预言传世,并为谶纬所吸纳,如《易纬通卦验》曾言“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22),此类用例甚多,不一一列举。
以上论述说明,从春秋战国以来,与河图、洛书预言相伴流行的,还有其他关于圣人受命、太平降临等形式的预言。这些提供了谶纬形成的社会思潮基础,也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料。而从刘歆赋予河图、洛书以明确的内涵阐释之后,谶纬之形成应该由此正式启动。此前长期流行的以河图、洛书预言为核心,包括相关如圣人受命、太平盛世等形式的理想、预言,也作为附和因素汇聚在共同的思想体系之内,结胎成型。这是在探讨秦汉之际《河图》、《洛书》早期谶纬形成过程时,应从社会思想及学术文化自身发展方面,特别给予关注的焦点。
四、刘歆与河洛谶纬及其影响
河图、洛书乃是象征圣人受命和太平理想的典型预言形式。这些预言、传说的积累,启发诱导秦汉之际早期谶纬河洛之学的产生。对具有预言性的河洛传说的总结整理,不仅是为记忆和重现那段历史,更主要的是为对目下的社会政治有所借鉴,尤其是对汉代摈弃秦代暴政、直承三代文化传统,意义极大。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谶纬河洛体系的形成,也是春秋战国以来以河洛传说为代表的社会思潮长期传衍的一种延续,并从思想资料上丰富了今文经学的知识内容。历来只注意到刘歆作为古文家的一面,忽略了刘歆所学最初本为今文学的事实。因为根据《汉书·五行志》,刘歆堪称西汉阴阳五行灾异之学的大家。刘歆后因发现古文诸经,为传播弘扬之而致力于古文诸经的研究表彰,于是在学术上发生转向,并从此跻身古文学家的行列。但若追溯今文谶纬河洛之学的形成,刘歆的开启之功不可没。因为他对河图、洛书内涵意义的明确阐释,为谶纬之学提供了进一步生发推演的知识理论基础。刘歆所言伏羲八卦和大禹洛书,系从圣王传统和天启文明的角度,构筑起河洛受命说的基本框架,此后汉代河洛说的推演变化大要不出其既定框架。郑玄的古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绍述刘歆而来,这在《周官》的反映上最为明显。既然刘歆与今文谶纬的关系如此,那么,郑玄注经兼取今文、崇信谶纬的学术取向亦不足为奇。现在的问题是,《汉书·五行志》仅用“刘歆以为”道明河图、洛书的内涵意义乃由刘歆作出,却未说明刘歆的根据何在,这仍为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今本《尚书》孔传也对河图、洛书意义作出解释,所言与刘歆相同。但要注意的是,第一,《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仅“河图,八卦是也”一句简单的话,至《尚书》孔传乃详言伏羲得《河图》、大禹得《洛书》之事,因此,孔传所言是否就是孔安国所言,尚难断言;第二,孔传与孔安国的关系至今尚无法考明,因此很难说是刘歆完全承自孔安国之说;第三,因为《汉书·五行志》已明言“刘歆以为”,那么至少班固认为这种河图、洛书的解释出自刘歆,至于刘歆之前的渊源何在,班固也不清楚,问题至此再无法前溯。
近年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出土(23),似为人们认识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提供了考古实物上的可能性参照。出土时玉版夹在玉龟的腹甲与背甲之间,它为纬书中“元龟衔符”、“元龟负书”之说,提供了可供理解的参证。玉版上刻有图,从而使纬书中“河图玉版”之说似有端倪可寻。玉版边缘上刻有不同数目的圆孔,其数的排列顺序依次为4、5、9、5,研究者认为数的排列顺序合于“太一下行八卦九宫,每四乃还于中央”的说法,并推测含山所出玉龟和玉片有可能是远古洛书和八卦(24)。其实河图与洛书二者按《汉书·五行志》之说,本应有别,即河图乃八卦,洛书为九畴,内涵上相互有异,在宋儒则有九图十书与十图九书之辨(25)。因此对含山玉龟与玉版究竟为河图洛书中何者,应有较清楚的界定。如果玉版刻图确如论者所言乃原始八卦(26),则玉龟所衔并非洛书九畴,而是河图八卦。当然,纬书中也有“大龟负图”之类的说法,但一般而言,纬书中图、书还是有别的,如《尚书帝命验》:“河龙图出,洛龟书威”(27),《孝经左契》:“天龙负图,地龟出书”(28),都与《五行志》之说相合。有的研究者又指出,所谓河图、洛书表现的只是两个不同的布数过程,二者分别代表五、十图数的两幅图,玉版中心的八角把二者融为一体,并断言这两幅五、十图书应统统归为“洛书”,至于真正的“河图”乃是“太极图”,与这类五位九宫图无关(29)。按刘歆对图、书的解释,应该有其根据,很可能是其时较为流行的看法,只不过由刘歆正式提出。此外,含山玉龟、玉版的出土也可能对我们理解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有某种启发,只是这一切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为至今还没有可以为人完全信从的解释。
在《汉书·五行志》所载河图八卦与洛书九畴的说解中,关于河图八卦,在早期记载中几若无可质证,而洛书九畴则可见若干记载上的线索。如:
禹锡玄珪,告厥成功。(《尚书·禹贡》)
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
按《尚书》所言应为禹赐洛书说的传说原型。玄珪者,禹治水成功天所赐玉版,纬书中即如此记,如《尚书璇玑钤》:“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30)《河图挺佐辅》:“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宝文大字锡禹。”(31)按天赐禹玄珪应是赐禹洛书九畴的异闻,“宝文大字”或即《五行志》所谓“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化出。又《庄子·天运》:“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按“六极五常”乃《洪范》九畴之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九洛之事”应即洛书九畴(32)。又“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即《洪范》之“彝伦攸叙”、“彝伦攸斁”。《天运》所述即承《洪范》而来。另,“此谓上皇”,疑“上皇”即伏羲,如郑玄《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孔疏:“上皇,谓伏羲。”上皇之称又见于《楚辞·九歌》,王逸注谓东皇太一;五臣注曰:“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伏羲在《月令》为东方之帝,在方位上与东皇太一合(33)。那么,伏羲上皇之称似可追溯及战国之世,与《庄子·天运》的时代相近。这样,《天运》所述以洛书九畴传说为主,隐微之间又可见伏羲河图之事的端倪,或者说伏羲河图传说附于洛书九畴之下流传。以上据《尚书》与《庄子》所言,可以考见刘歆所述河图、洛书之义当前有所承,只不过在传衍过程中有某些不确定的因素,至刘歆时基本成型,故其后汉人说河图、洛书皆如刘歆所言。
综之,刘歆原本今文造诣深厚,又于古文诸经的表彰发明之功甚巨。因此,其在各方面的影响应该注意,特别是历来几乎为人忽略的、其对今文谶纬河洛之学的开启之功,尤有必要特予提出加以关注。因为其事不仅是汉代谶纬及经学发展上的枢机关键,而且对研究理解相关的经学现象极具启发意义。要解读郑玄兼取今文、崇信谶纬的学术取向,刘歆与谶纬河洛之学的关系就是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注释:
①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26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
③陈槃:《谶纬释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
④钟肇鹏:《谶纬论略》,第8-9页、第11页。
⑤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3-396页。
⑥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8-201页。
⑦胡家聪:《侈靡著作时代质疑》,《管子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91-299页。
⑧《古论语》作:“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载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0年,1575页。又《史记·孔子世家》作:“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⑨这两条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后附《随巢子》佚文,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490页。
⑩转引自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208页。
(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0页。
(12)边家珍:《汉代经学发展史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25-128页。
(13)参阅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20页。
(14)[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5页。
(15)[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第1068页。
(16)[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第856页。
(17)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页。
(18)参阅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7页。
(19)又见《春秋繁露》之《考功名》、《通国身》、《天地之行》诸篇。
(20)参阅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36页。
(21)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
(22)[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第207页。
(2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24)陈久金:《陈久金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25)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8页。
(26)有学者通过考古实物的比较,论定玉版与原始八卦相比,乃是比较复杂的八卦图,见宋兆麟、冯莉;《中国远古文化》,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年,第402页。
(27)[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第373页。
(28)[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第997页。
(2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2页。
(30)[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第376页。
(31)[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下册,第1109页。
(32)沙少海:《庄子集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6页。《河图始开图》:“帝命伯禹曰:‘告汝九术五胜之常,可以克之,汝能从之,汝师徒将兴。’”(《纬书集成》下册,第1105页,又见《河图握矩记》)此“九术五胜之常”或与《洪范》之九畴五行相当,应是随河图洛书之说的传布而出现的讹变。
(33)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毁弃》章见“上皇”一词,有学者引《楚辞》与《庄子》解之,似非。见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85页。按《日书》上皇乃民间信仰中的神祇,与《楚辞》、《庄子》上皇不能相比。
标签:儒家论文; 河图论文; 春秋战国论文; 春秋论文; 公羊传论文; 读书论文; 洪范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 汉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