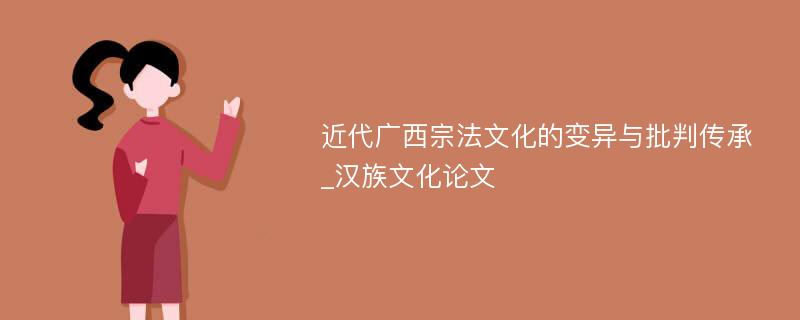
试论近代广西宗法文化的变异性表现及其批判继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异性论文,宗法论文,广西论文,近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广西近代社会宗法文化的变异性主要表现在族长由传统继承转变为选举产生,族权行使由个人专制转变为集体执行,族产由世袭的地产转化为能生息的资本,族谱族规由维护封建伦常转化为产生了民主和商品意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占有了较突出的地位。这些变异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和规律,正确认识宗法文化及其变异性有利于当今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
关键词 广西;宗法文化;变异性;批判继承
宗法制度及其思想习俗所形成的宗法文化,在我国几千年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宗法文化,对当前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试对前人未曾探讨过的近现代广西以汉族地区为主的社会宗法文化的若干变异性表现进行研究,并探索在当代批判继承以求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借鉴的途径。
一、族长由传统继承转变为选举产生
宗法制下的继承制度分为族长继承、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即血统继承,即宗族血脉传承不能中断。族长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五个特征之一,族长的继承实即族权的继承,而族权的继承又与财产的继承不可分割。长子继承、幼子继承、兄弟继承、传贤不传子,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上都存在过,只要为族人认可,能巩固宗族族权和血统的承传而不发生矛盾,这些继承制度同样能巩固宗法制家族。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广西汉族地区,特别是桂东南、桂东北地区,却产生了族长继承的选举制度。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前期,我国宗法制下的族长一般均是世袭继承的,形成了世族制度;唐宋以后,虽然掌握宗族权力的族长一般都在不任官职的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家族中产生,但族长的职务仍是传统世袭继承者为多,所以近代广西社会族长由传统继承逐渐转为在族中通过公举产生,实为近代社会条件下宗法制度出现的一种变异形态。关于族长的选举,本文下几节都会论到,这里先引证宣统三年(1911)编辑出版的《广西民事习惯报告书》的材料作说明。近代广西族长之性质、出任的条件和选举办法如下:
“族长者,为族众所推举,以主持合族之事务者也。”
“族长之选任,除依行辈年齿递推外,要皆以声望素孚者为合格;设有数人之行辈年齿声望俱尊者,则以抽签法定之,然亦有不论行辈年齿而以年力强壮能理事之人充当族长者,且因族众繁多或推选三四人者,柳州属之罗城有此习;有因家产殷实藉子弟之势力强充族长者,桂林属之中渡有此习;更有因功名显达例选任为族长者,泗城属之凌云有此习。”
“族长之限制约有三种,一同姓不宗之人不得代任为族长,一抚养异姓之子不得选为族长,一曾受国法之处分者,不得充当族长,此普遍习惯也,但事实上亦有区别。如声望素孚之人,非其罪而受刑罚,在各属中仍得被选为族长者居多数,至对于抚养异姓之子,则以族规为区别,如其族素严异姓乱宗之禁,固不得选为族长;若族规无明文而所养之子才能出众、富有家产为族众所推服者,亦得被选为族长,桂林属之灌阳、兴安、中渡、平乐属之贺县、昭平均有此习。” 关于族长之责职,《报告书》规定:
“族中公务之执行,族长有督饬之责;关于族众之赏罚,族长有主持之责;族中若有公事会议,族长有事先召集之权;临事有裁决之权,或有仓猝之事发生,虽可由族众自行集会,亦必通知族长;族中若与他族争讼,首以族长出名,或族长年高步履不便,始另议一人代之;族人若有争讼,由族长秉公剖析,俟调处不谐,始向官府控诉是非,各属中公同之习例。”
“族长多以尊卑充当其经理公务,恒给以相当之报酬,罕预订罚规者,或有侵蚀公款等弊,由族中临时酌议,除革退族长外,大都仅负赔款之责,惟桂林属之临桂,有终身不许族中事务之罚则,庆远属之宜山,有加赔偿之罚则,是为特例。”[①]
清末编定的《广西民事习惯报告书》,是清代后期广西民间社会习俗的一个总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入近代以来虽然广西各地的族长继承制上有各种形式,但均非由族长家族成员继承,而是由宗族成员公举产生,则为共同的规律。当然“公举”、“推选”是有条件的,第一,有等级地位上的限制,即“行辈年齿声望俱尊者”或“家产殷实藉子弟之势力强充族长”、“功名显达例选任为族长”等等。这些条件总的来说,就是必须由宗族内有钱有势有声望有文化而且辈份较高之人担任,这就排除了贫苦的族人担任族长的可能。所以族长虽由公推、选举产生,但其范围则限定在属于地主贵族等富裕阶层的小圈子内。第二,宗法和国法均禁止同姓不宗之人及受到国法处刑的人担任族长。这是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广西同一姓氏之人极多,在任何一个地方同姓而不同宗者均占极大多数,所以单是同姓一般来讲不是本族成员。明清时期,地方宗法势力与国家的封建统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宗族要依靠封建国法加强对族人的控制,国家也需要依靠族权来巩固对族人的奴役,当然国家不允许违反国法受过刑之人担任族长。
由此可见,近代广西一些地区的族长继承虽然已经废除了传统的世袭继承而转变为公举推选,但族长仍由地位尊贵、财产充裕、声望素著的名门家族中产生的实质未变,族长均为统治阶级中人担任的阶级性未变,族权成为政权的辅助统治工具的作用未变。
二、族权的行使由个人专制转变为集体执行
随着族长的继承由一家世袭转变为一定条件下的族人公选,对族权的行使也逐渐由族长个人专断转变为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的集体执行制。根据我们对近代广西汉族族谱的研究,族权由集体的形式来行使已较为普遍。例如近代玉林陈氏的宗祠组织就非常严密。陈氏组织了宗族的集体管理机构——陈龙章祠家族委员会。家族委员会以族长为首,负责召集开会及处理、调解族内纠纷事宜;宗族的日常具体事务,则由家族委员会推举的执行委员6人、当然委员5人、监察委员5人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并监督所处理的事宜,可以说玉林陈龙章祠所组成的家族委员会成为集体型的族权的执行者。[②]临桂县李氏宗族对族权的行使亦实行集体型,宗族成立了族长领导的评议会,议决和行使族中的重大事务,主管祠内集会、祭祀及经费使用;评议会建立了常设机构,有总经理1人,名誉经理1人,会计1人,具体执行评议会的决议,保管宗祠公产,征收钱粮,召集族人等,可以说评议会和常设的总经理等执行人员集体行使了族权。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族权的执行者居然冠上了“总经理”、“副经理”等带有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商业色彩的名称。[③]灌阳王氏宗族族权的行使亦为集体型,宗族设经管十人,主管宗祠大小事宜,经管中又设总理2人,总理和宗祠下的各级房长具体负责钱粮的征收,文册和钥匙的保管,各房公粮的管理。[④]灵川蒋氏宗族的族权采取由各房房长轮流行使的方法,主要管理宗祠的经济事宜,另外又设立理事1人、司库数人,负责主管宗族内的专项教育费用,不涉及其他族务。[⑤]以上几种类型均为族权行使的集体型形式。此外还有个人型,如桂林张氏宗族推举祠总1人,具体行使保管帐目,办理祭祀,处置族人等宗族的权力;祠总下又设立祠正5人、祠副5人,行使征收钱粮,通知召集族众,办理祭祀的具体工作。[⑥]北流陈氏宗族与此相似,宗族建立了议事会决定宗族大会的召开,由议事会公举1人掌握祠堂和蒸尝田产,宗族的具体事项则每年由各房轮值,负责收取蒸尝田租、办理祭务等事。[⑦]以上几种类型都反映了近代社会在广西的汉族宗族中,族权的行使已非为族长一人所垄断执掌,而由宗族公选产生的集体主管来执行了。
当然,只要存在宗族,族长总是有的,但与古代社会比,辛亥革命后广西汉族宗族的族长的权力有了很大的限制。一种情况是族权由族长和祠总(或祠长)共同掌管,族长只管族内事务,而祠长成为行使更大权力的宗祠事务的专管;另一种情况是族长外还有评议会、家族委员会、议事会等集体决策机构,这种集体决策机构能反映和集中宗支更多的意见,更为族人所接受。所以族长的权力比之古代社会来讲是大大削弱了,出现了几种形态:其一是名誉型,即族长是齿德俱尊的宗族内长者,在宗族内有一定威信,能参与族权的行使,但决策大权完全掌握在祠长或议事会等的手中。如桂林张氏宗族规定:凡族人违犯族规,如不孝不悌者,由“祠长祠正令其到祠,于神位前跪听教责”;关于族人后代继承之事,亦先由族人“族议,然后通知族长,择吉入祠告拜。”[⑧]可见族长变成了无实权的荣誉性的职务。其二是分管型,族长仍在宗族内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但仅限于一般族务。宗族的重大活动,如祭祀先祖,祠产管理,均由祠总、祠长或评议会、议事会管理,除以上所举各例外,灵川苏氏宗族亦是一个典型。苏氏的族长主要职责只是“处理族人纠纷,召集各房首事议事”,祠中一概事务由各房轮管,祭祀大事亦由各房推选首事管理,各房首事的作用相当于祠长或祠总,主管族内祭祀事务,可见宗族事务已由各房首事和族长分管了。[⑨]其三是执行型,即族长对宗族大事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必须由宗族集体领导机构作出,族长的任务是负责具体执行,如上述临桂李氏的族长就是“总经理”,总经理以及协助其工作的副经理只是“执行评议会议决各事项。”[⑩]由各房房长组成的评议会,对族中大事有决策的大权,“但遇有急要之事务,用费在三百元以下者,不及开评议会议决时,总经理得先裁决施行,即行通报各房评议员”。[(11)]可见族长的权力仅在执行。其四是决策型,即族长仍对宗族大事有决策权,如灌阳王氏,当宗族内的议事机构产生意见分歧时,由族长最后决断;在宗族的最重大活动——祭祀中,规定“宗子(族长)主祭,毋得僭越”。[(12)]然而就在王氏宗族中,族长之外毕竟成立了由经管十人组成的议事机构,宗族的重大事务要先由议事机构讨论,这对族长的权力毕竟是一种限制和削弱。
三、族产由世袭的地产转化为能生息的资本
族产,是宗族的共同财产。只要存在能行使宗法权力的宗族组织,总会存在族产,因为族产是宗族得到凝聚和进行宗族活动的必备经济条件;没有族产,宗族就会瓦解。在我国古代以及世界古代多数国家和地区,族产一般均为地产。我国封建社会至近代,宗族的族产土地有族田、祠田、蒸尝田、祭田、宗庙田、粽粑田等多种称呼,广西汉族和少数民族宗族的族产也是这几种称呼。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广西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族产却从地产转变成能从事开发投资的货币(资本),表现了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尤其在汉族客家人的宗族族产中表现最为明显。以藤县客家李氏宗族的祠产为例:“溷逻祖祠蒸尝:1.三碑洲田租谷一千二百斤;2.都芳垧田租谷五百斤;3.占集益公司十八分之一约值银五百余元;4.占土益公司十分之一约值银一千六百余元;5.当租约一千七百斤;6.良蒙三界岭松山一所;7.祖祠后背山场一所;8.占平南粮税三元一角五分。”[(13)]这8项被称为“蒸尝”的族产中,有二处是宗族的公共山场;三处是宗族土地,由出租收取租谷作为宗族的公产;二处是将公产转化为资本,与他人合作开设合资公司,收取利润,供宗族公用;还有一处数量最少的是粮税银的一部分。这种祠田、祭田与投资于企业的资本共存的族产存在形式,是到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藤县李氏族谱》修成于1934年,族产转化为资本的情况出现于清末以后,在清代中期前修成的族谱中我们还未发现此种情况。根据该族谱的记载,藤县李氏宗族鉴于春秋二祭无资,于清光绪十五年由族人召集全族90余人,“捐签开田,出息积聚,……由是昭穆明而祀事有资。”[(14)]李氏的族产在清代是以族田开始的,所以族田的田租收入占据了祠产的绝大部分。订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临桂李氏族谱中,亦记载了当时临桂李氏的族产已基本上不是地产,而是以税收方式向族人征收现金。这种以征税方式征收的现金共有六种:财产捐、丁口捐、立主捐、所得捐、特别捐、租赁金。[(15)]族产由地产转变为向族人征收货币性质的捐税,而捐税的多少又与每户族人的经济条件、资金多少联系起来(如财产捐、所得捐明显是以各户财产收入多寡为标准征收的),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的产物,反映李氏宗族内各户的主要财产已不是土地财产,而是工商业财产,所以宗族的共财只能建立在收财产税的形式之上了。当然就近代广西各民族宗族共财的总况来看,各种形式的祠田、祭田、义田、蒸尝田、族田还是主要的,但在靠近桂林、梧州等经济较发展地区出现了族产转化为资本、按各户经济力量征收的变异现象,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对传统封建宗法制度的冲击和影响。
四、族谱族规由维护封建伦常转化为产生了民主和商品意识
族谱是关于宗族血脉的谱系记载,是明确族人的宗亲辈份关系、维系宗族成员联系、实行宗族统治的工具。在我国汉族地区,凡是存在宗族的地方均有族谱,有些地方至今还在修族谱。一本族谱中份量最大的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对族内任过官宦的名人还常有专门介绍;其次是刊载宗族的祠堂、茔田、族田等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祠田序、墓志铭、各种文契等,目的是留于后世作为宗族财产的文字依据;第三是宗族的历史演变和先祖的事迹考略,是对族人进行宗族传统教育的教材;第四部分是宗训、族规以及宗族艺文等,是宗族内进行宗法教育、宗法统治的文字条例,在族谱中占有主要地位。族规包含在族谱之中,但一般意义上的族规是指宗族法规,族谱是指宗族谱牒和历史,两者含义是不同的。
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宗族中,族谱族规所宣传和维护的是封建伦常道德,在广西近代汉族的族谱族规中,也是把尊祖宗、孝父母、纳国课、正男女、严尊卑、敦诗书、治匪盗等条文作为宗族教育的主要条规,凡违犯者则予以严惩。[(16)]但是,由于受近代时代潮流的影响,在族谱和族规中有了变异性的新思想因素的出现。其一是从维护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意识到产生商品意识。如编定于民国年间的《筹备广西李氏宗祠章程》的族规中明确规定:“凡租赁宗祠宴会者按照左例数目纳捐:(一)花园,日捐银二元,夜捐银四元;(二)戏台,日捐银五元,夜捐银十元”;“各项收入达五百元以上即行存放银行或妥实银号生息;达五千元以上即行购置或建筑不动产;达三万元以上即行经营实业或为营业之借出。”[(17)]足见在宗族成员很多弃农就商的条件下,宗族也与社会商品经济领域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商品意识和保守的农耕意识在族谱族规中已同时并存。其二是某些族谱族规产生于辛亥革命以后,在封建宗法伦理受到冲击时,在族谱族规中也反映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对两千年来传统的宗族封建专制主义的旧礼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如“昔公宴限于男丁,近十年来妇女亦得参与,自较合理。”“元旦团拜,元旦之晨整肃衣冠,齐集祠中,燃香烛,供清茶,不设祭品,行谒祖礼。”[(18)]上述临桂李氏等族谱改族长之名为“总经理”,将宗族的行政、司法、监察人员职责分开,互相监督,也透露出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的信息。其三是有的族规中明确规定把从商作为宗族的重要职业,如近代广西很多族规都有“士农工商任尔子孙为,切不可游手好闲全无事业”这样的话。古代“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传统风气在近代广西的族谱、族规中也有所改变了。
五、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占有了较突出的地位
半个多世纪前,广西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曾说:“广西文化,由妇女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有一极大特色,这就是女性主义。”[(19)]妇女在几千年的宗法社会中一向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和奴役,但在近代的广西社会,很多族谱族规确实反映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了较突出的地位。这在外省是较少看到的,是近代广西宗法文化中的一种变异性表现。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妇女既普遍参加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家庭副业的劳动,又操持家务,养老扶幼,在生产、家庭中占有较突出的地位。这在广西各民族中均有表现,以汉族的客家人而言,素有“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之说。其实,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等等广西各族妇女,都是很勤劳的。北方各省多平原旱地,农业劳动远不及广西那样艰苦,而广西地形复杂,多高山密林,耕地相对来讲较少,这些自然条件决定了在广西要发展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要付出特别艰巨的劳动,只有妇女既从事生儿育女养老扶幼的家内劳动,又从事农、林、副、渔、工商等生产活动,才能使一族一家能生存发展下去。
第二,在族谱和族规上反映了近代广西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女子受翁(公公)姑(婆婆)虐待时,在某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族谱族规中允许其离婚,如《广西民事习惯报告书》中记载着:“不堪夫及翁姑之凌虐时,女子当此与其受虐而死,不如求出而生,故习惯上有主张离婚者。然在贤淑之女子只自怨自艾,甘受从一而终之义;在柔弱之女子,有母家出头理论,代请离婚之习。桂林属之临桂,女子于请求离婚后,有只能离俗(出家作尼),不可嫁人之习。”离婚是违背“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宗法的“三从”之义的,但到了清代末年如遇翁姑、丈夫虐待女性时,宗族在习惯上出现了让其离婚,“与其受虐而死,不如求出而生”的习俗,而且“离婚者属大多数”,不能不说是对封建宗法传统的一种变异性的否定。[(20)]2.强调夫妇之间互敬互重,出现了夫妇平等的观念。如1927年编成的全县(今全州县)《刘氏族谱》记载:“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此夫妇之伦也,上承祖祧,下衍儿孙,夫不轻其妇,妇不违其夫,情同比目之鱼,义皆雍鸣之雁,夫妇相敬如宾,岂有反目鸳鸯,妇内夫外,夫倡妇随,此宜然也。”[(21)]3.某些族规明确规定禁止溺杀女婴:“古者缇萦上书而救父,卢氏冒刃而卫姑,这等孝女大有异乎男子耳?何言生女无用哉。且人生之道,一男一女,如仅有男无女,己身何出?遂亦绝矣!女可溺乎也屿哉?……吾等各教妻妾,莫作此孽而可哉!”[(22)]尽管族规对“禁溺女”的出发点仍是从人类繁衍后代、宗族传承香火的前提出发的,但其宣传男女同样重要,无女便无男的思想是进步的和科学的。
第三,寡妇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广西客家社会中,由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劳动中起了较多的作用,使男子能安心地外出仕宦、经商或从事其他实业活动,因此她们受到族人尊重,即使寡妇也不例外。在来宾县良江乡的客家人中,“守寡很被人尊重,欺负寡妇婆的事很少发生,兄弟自然在农忙季节帮助寡妇人家。”[(23)]寡妇以外的妇女亦有较高地位,据我们的调查,北流县新圩的客家妇女,在解放前在夫家祭祖宗完毕的次日,可以返回娘家入祭祖宗。
第四,在少数民族中,婚姻形态受汉族传统的封建宗法伦常思想影响较少。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上较为随便和自由,这些情况在壮、瑶、苗、侗等族的婚姻形态上都有一定的表现。虽然这些婚姻形态最后仍摆脱不了族权父权夫权的控制,但毕竟反映了女性还保留了原始婚俗中的某些性爱选择的自由。
近代广西女性在家庭、生产和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保留了一些原始习俗,受汉族封建宗法伦常影响较少,第二,生存的需要,广西不仅离汉族中心地区较远,而且多山少地,地形复杂,生产活动需要妇女发挥特殊的作用;客家人中男性又常外出经商从政,需要女性在家操持家务。但这些情况绝不意味着妇女的解放和男女平等,能否提广西有“女性主义”值得商榷。从总的来讲女性仍从属于男性,妇女仍成为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统治下生男育女的工具。据1933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编印的《广西各县概况》记载,果德县“女子之地位:农业操作,多有女子参与,惟读书识字者少,仍依赖男子,于社会上未占何种地位。”思乐县“女子之地位,多依赖男子,无何种地位可言。”总之广西妇女在建国前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除了广西西部北部少数民族山区受汉族封建伦常影响较少的原因外,主要是对她们在男子经常外出后为维护家族香火和从事生产活动的肯定,有利于在宗法上男性血统地位的继承和家族的兴旺,本质上还是宗法性的表现,所以妇女参与政治活动,担任官职和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职务者是极少的,女性从根本上讲,仍是没有得到解放的。
六、对变异的规律性探讨及在当代社会的批判继承
综上所述,近代广西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法制度和文化形态相比,产生了变异的特殊形态。对其变异形态的产生发展规律及在当代社会批判继承的途径方法,试作分析如下:
(一)生产力提高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使传统的宗法文化产生变异的根本力量。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属于不同氏族血缘宗法组织的人们之间为了商品经营的目的,而处于不断的流动、迁移、交错杂居的状态,从而成为瓦解传统的世代守土守宗的宗法组织的根本力量。商品生产下人们为追求利润、金钱的目的进行扩大生产和销售的努力,也成为冲破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因素。但是,商品生产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古代奴隶社会有奴隶制商品经济,当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古典希腊和古典罗马,由于奴隶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已使宗法组织瓦解,这是熟悉世界史的人都知道的。我国近代虽然出现民族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广西尤为如此,所以在宗法制的表现形态族长、族产、族谱、族规中,虽多方面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影响,使千年以来以土地为基础、以守土守宗为特征的宗法文化产生了变异,但它仍成为宗法文化的一个部分。由此可见,要使封建宗法得到彻底的改造,除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取代封建宗法思想外,在生产力提高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是十分必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仅是冲击和瓦解封建宗法的力量,而且可以使传统宗法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得到批判继承,为发展经济服务。
(二)社会制度和统治思想的变化,是使宗法文化产生变异的基本原因。广西近代族长由世袭继承演变为选举产生和集体执掌的、带有一定民主性倾向的集体执行型的宗族管理机构,使原有族长的权力大大削弱,这反映了19世纪晚期以后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及思想对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公选产生的集体执行的族权行使,虽然不同于古代个人专制世袭承继的族长权,但这种权力仍是包含阶级性的族权、父权、夫权、神权的宗法统治的特殊形态。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建立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但仍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剥削制度,人民群众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而以父权和族权为特征的,反映了阶级对抗内容的宗族家族制度,可以存在于任何经济不甚发展的阶级社会,可以为任何剥削阶级所利用;宗法的存在形态可因历史条件而变化,而宗法制度的阶级性往往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上述集体型的族长制中,其族产有的由土地变为经营性资本,正反映了宗法的阶级性由封建性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要真正取消宗法的阶级性,必须是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后,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阶级压迫剥削制度及其思想的影响,是当代改造宗法文化的关键。
(三)推翻剥削制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国家管理,是女性获得真正解放的前提条件。广西近代女性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是由特殊的社会和自然条件决定的,但从根本上讲她们仍未能摆脱受族权、父权、夫权统治的地位。她们在生产和家庭中的作用正是宗法家族的管理、承续、兴旺所必要的;她们毕生辛劳,但其思想深处仍是宗法下的已嫁从夫、生育后代、家门兴旺的传统观念。在旧社会,妇女能受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的机会很少,更缺乏参加国家管理和高层次社会工作的基本条件。由此可知,首先必须彻底推翻剥削制度,取消封建宗法存在的阶级基础,同时在全社会必须形成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风气,女性必须自信、自尊、自强,努力学习和掌握文化科学管理知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样,妇女的解放才能真正达到。
(四)打破闭塞保守,在批判继承原则下广泛接受一切外来的新的思想、科学和文化,是使传统宗法文化得到改造的重要途径。广西近代宗法文化的变异性的产生,很明显是受到了19世纪晚期以来新的政治思想、经济学说、价值观念、科学文化影响的结果,使封建社会的宗法文化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宗法文化。这种变异形态的宗法在束缚和统治族人中起了消极作用,同时又在推动族人接受新事物、传播新知识、促进宗族发展上产生积极影响。当代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宗法制度存在的阶级基础已被取缔,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又为我们批判继承一切民族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条件。剔除和摒弃传统的封建宗法文化中封建迷信、守族排外、任人唯亲、重男轻女、多生多育、宗族械斗等带有阶级社会烙印的消极因素,弘扬和光大宗法文化中团结凝聚、互助合作、爱家爱乡、技术传授等积极成份,完全具备了条件,也是当前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宗法制度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既然在解放前的广西近代社会已经产生了商品意识和民主化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利用其血缘性的特点,继续清除其阶级性的影响,是可以去掉宗法性,加强民主性,去掉保守性,加强开放性,去掉闭塞性,加强商品性,是可以转化利用其为当前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
注释:
① 《广西民事习惯报告书》第一编第一类《宗族》,广西官书局清宣统三年(1911)编印。
② 《玉林陈氏族谱》(1985年复印本)。
③ ⑩ (11) (15) (17) 《筹备广西李氏宗祠章程》(民国)。
④ (12) 《灌阳王氏族谱》(1870)。
⑤ (18) 《灵川蒋氏宗谱》(1948)
⑥ ⑧ 《桂林张氏族谱》(1933)。
⑦ 《北流鸭垠陈氏族谱》(1935)。
⑨ 《灵川苏氏宗谱》(1934)。
(13) (14) 《藤县李氏族谱》(1934)。
(16) 这些族规内容除见上引诸族谱外,还见于《修仁三诰蒋氏族谱》,《全县刘氏族谱》,《北流联石罗氏家谱》、《灌阳唐氏族谱》、《贺县朱氏家谱》等。
(19) 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52页。
(20) 《广西民事习惯报告书·婚俗》。
(21) (22) 《全县刘氏族谱·家规》(1927)。
(23) 韦富强:《来宾良家乡客家人情况调查报告》,见徐杰舜、覃乃昌主编:《广西汉族考查》,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8年5月编印。
(24)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