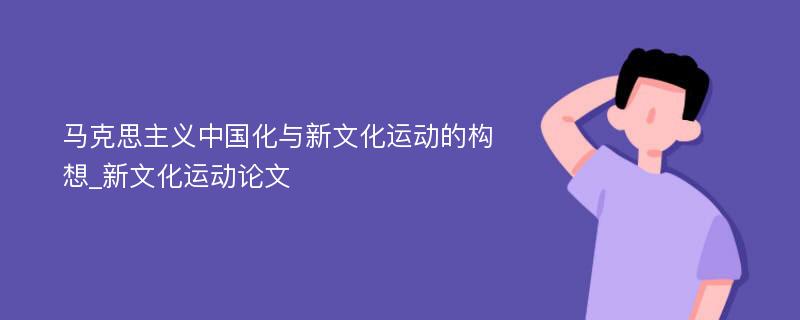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先后形成了两大科学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被列为国家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子学科。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论文、著作大量涌现。但笔者以为,许多论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内涵的理解上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只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相结合,而忽视或很少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这种理解上的偏颇又直接影响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忽视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忽视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①这种造成理解上偏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必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必然。长期以来,一般研究者主要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视角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而忽视了它的文化运动的背景。最近两三年,有的研究者虽然对此有所阐述,但仅限于新启蒙运动,未能顾及五四以来的整个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延安的新文化运动。本文拟从五四以来的整个新文化运动视角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由来,力图提供若干为人忽视的重要史料,以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文化背景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概念、命题是认识成果的结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时就开始了,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则有一个过程。它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初就能提出,而只能在传入之后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取得重大成果之时才能形成。因此,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时着重论述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背景(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和对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理论背景(由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到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这是十分正确的。学术界、理论界对它的阐述已很多,本文不再赘述。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要求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毛泽东把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作为全党学习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研究历史的重视。在此讲话中,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既不是在论述研究理论的部分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在论述研究现状时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在论述研究历史部分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他明确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割断历史,要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很明显,毛泽东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除了中国革命运动实践背景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背景外还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这一点正是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者所忽视的。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对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总结,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文化和人才条件,任何否定、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功绩的言论都是错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历史局限性。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只看到思想文化的时代性、变革性,忽视思想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只看到新旧文化的对立,没有认识到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取,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形式主义的简单否定态度。这种错误的认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仍然存在。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虽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文化,但他没有能摆脱五四时代简单否定的思维方式。他强调的是思想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忽视了它的民族性、继承性。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堆“粪秽”,称“东方文化之圣徒”研究国学,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②陈独秀精通国学,但他的上述认识使他不可能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说,只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忽视对它的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弘扬,是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存在的倾向。
思想文化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联。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亡,国难当头。随着民族危机日深,民族意识高涨,文化的民族性也日益凸显。少数思想敏锐的进步知识分子自觉地认识到,国家与文化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要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创造综合中西哲学之长的新哲学。他们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罗素的解析方法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综合为新的唯物论。张岱年明确指出:“一种哲学必与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建立本国哲学不顾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1](p.205)张氏兄弟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阵线,但他俩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人民的抗日爱国热忱进一步高涨。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文化人发起了新启蒙运动,以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心,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新启蒙运动在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精神的同时还提出:文化的民族性,尊重民族文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纠正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的错误。作为新启蒙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张申府指出,五四时代是两大口号,“打倒孔家店”和“德赛两先生”;现在要改一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和“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2](p.190)他还指出:“新启蒙运动应是综合的。”“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文化;当然更不应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因此,“新文化不只是大众的,还应带些民族性。”“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是今日中国所需要。”“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2](p.192)张申府主张中西文化综合和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思想是鲜明的、正确的。
总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在不断增强,思想文化中的民族性得到张显。“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p.161)毛泽东在1935年底讲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心声,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者。
新启蒙运动时间甚短,只有1936-1937年两年左右的时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文化背景仅限于新启蒙运动是很不够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同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有更为直接的关联。这一点只要去读一读在延安出版的1937年至1938年的《解放》周刊上有关文化工作、文化运动的文章即可明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新时期。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包括知识分子、文化人在内的中国先进分子向往的圣地。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工作,他明确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4](p.461)为了加强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党中央组织上海、北京等地党的思想理论骨干、作家和文化人到延安。1937年10月,周扬、李初梨、艾思奇等由上海到达延安。随着文化人的不断到来,延安的文化工作亦随之不断展开、加强。正确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现状,是开展新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
1937年11月,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署名为“从贤”(这似乎是一个笔名,真实姓名待考证)的《现阶段的文化工作》长篇文章。该文对“抗战对文化的影响”、“现阶段的文化运动的任务”和“目前文化运动的内容”三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文章正确提出,现在的文化应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大众的。在阐述民族的内容时,从贤说:民族的文化是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成果,要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把它发展光大,要启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他尖锐地指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的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要使文化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从外国文化中接受过来的,然而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把它种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③文章正确指出,文化运动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就必须中国化,中国化是大众化的深入所要求的。
紧接着,初到延安的李初梨,在《解放》上发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他在总结过去十年(1927年至1937年)文化运动时提出了“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他正确地把马列主义的具体化、通俗化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他首先肯定,在过去的几年里,马列主义的具体化是进步了,通俗化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成绩。同时他也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通俗化仍然不够”是一个缺点。他提出的现阶段文化运动的第四项任务为:提高文化水准,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④这是笔者迄今为止见到的明确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命题最早的一篇文章。当然,李初梨还只是把“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看作是文化工作诸多任务中的一项,而不是把它看作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方针。他对“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内涵和如何进行具体化中国化也没有论述。尽管如此,“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现在诸多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形成的文章、著作很少提到李初梨的这篇文章,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遗漏。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化、民族化的背景下,艾思奇明确提出了开展“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他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根据哲学的现状和时代对哲学的要求,艾思奇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在延安,他与毛泽东及其他文化人有所交往,关系密切。他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是否与毛泽东及其他文化人讨论过,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延安后,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更加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在这时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的任务决不是偶然的,同他的这种经历密切相关。从20世纪30年代前期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必然。艾思奇对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内涵做了初步阐述。他指出: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不是书斋堂课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要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在文章末尾,他发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号召。[5](p.387、388)艾思奇作为一个青年哲学家所强调的重点是哲学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要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以丰富发展哲学理论,再用发展了的哲学理论,指导现实的运动。这是十分深刻的,确实是中国化的最基本的要求。不足之处,他的哲学中国化内涵里没有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艾思奇提出的“哲学中国化”运动在学术界引起了注意。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前记”中谈到对“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他认为,“哲学中国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理论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二是“用现实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6](p.162)通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全书,胡绳的工作仍属通俗化的范畴。他对中国化的理解有比艾思奇前进的地方,涉及要联系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但也有不如艾思奇的方面,他所理解的中国化比较粗浅,主要是指在阐述哲学原理时联系中国具体事例,而不是指导中国现实运动和对现实运动经验进行哲学总结。
笔者在查阅《解放》周刊时发现:“新文化的中国化”,在1938年春的延安文化界已成为一种共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1938年5月4日)指出:文化运动应注意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特点,“疏忽自己民族的历史,疏忽自己民族的特点,或者不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弱点,这是错误的。”“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须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意见》还论述了文化的新内容和文化旧形式的结合问题、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关系问题,指出:“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在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而非现实的。”⑤这表明,中国化的实质是民族化,真正的大众化离不开中国化。
总之,在1938年10月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在反思和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文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方针,无疑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它的阐释和提倡。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7](p.425)。毛泽东在这样的重要会议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党的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因而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许多共产党员,包括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轻视研究历史,只懂得外国,不懂得中国,对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讲了学习问题,号召全党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他精辟地论述了研究历史的意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尖锐地批判教条主义、洋八股。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因研究者对这一经典论述都很熟悉,故在此不再引证),无疑吸取了当时文化界的思想;同样无疑的是,他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他以往的经验、思想和学养的升华,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做了创造性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具有经典性。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那样经历、思想和学养的人,是讲不出那些精辟的话的。
毛泽东是革命家、理论家、党的领导人,又是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具有渊博知识的学问家。还在学生时代,他虽然推崇陈独秀,但不赞成陈独秀对东西文化简单绝然对立的态度,主张中西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他重视历史的研究,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8](p.7)他博古通今,经史子集、笔记小说,无所不读。1936年,斯诺在访问毛泽东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9](p.65)毛泽东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古为今用。他在1926年就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⑥这些话表明,他已自觉地认识到外来的思想文化必须本国化,具有中国的气派,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他在1937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从思想到文采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他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昭告全党和世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10](p.42)他在一些讲话、谈话中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复古主义。但他承认“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10](p.43)他在文章、讲话中时常引用孔子的话,批判地吸取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他在论述调查研究的意义时就指出:“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3](p.110)毛泽东不赞成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但十分肯定孔子是教育家,肯定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在抗大的多次讲话中论及孔子。针对有的教员不安心当教师的思想,他说: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该是当教员到死吧。我们要学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⑦毛泽东不仅注重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十分注重对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在这方面,他讲得最多的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高度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孙中山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10](p.111、112)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真正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精神。可见,毛泽东讲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这样的话,决不仅仅是受了当时文化界的影响,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底蕴,是他以往思想的总结。毛泽东的上述言论和思想对全党,尤其是对延安的文化界无疑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延安文化界提出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一切最优秀的学说”等思想和提法是否与毛泽东的言论、思想有联系,这也是可以讨论的。毛泽东与延安文化界在思想上存在互动,这是需要注意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全面而深刻,包含丰富的内容。他虽然是在论述研究历史时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却不能仅仅限于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上,而是必须对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三者做统一的全面理解,必须联系党的历史、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去理解,必须联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去理解。毛泽东的精辟论述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实现的基本途径。毛泽东本人是这三者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地地道道中国的,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实现的基本途径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现实的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这三者的结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点、适合指导中国实际运动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赞同。张闻天在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组织工作要中国化。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11](pp.225-226)
毛泽东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在公开发表(刊于《解放》周刊第57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专刊,1938年11月25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广大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所肯定和赞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刊物上曾有“学术中国化”的公开讨论。张申府专门撰写了《论中国化》(1939年2月10日)一文对毛泽东的讲话加以响应和阐发。当时就有文章指出,“学术中国化”成了1939年中国文化界的基本口号。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经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阐述和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此而言,人们习惯地称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者,这不无道理。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是重要的话语。为纪念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三周年,青年哲学家、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撰写了题为《新哲学的新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延安《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1941年8月)的长篇论文。在文中,他系统地论述了新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中国化的含义、中国化的途径等问题。他还指出,毛泽东在1937年抗大的哲学讲座,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道路”。毛泽东本人也再次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教条主义时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10](p.373、374)还须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所规定必读的18个文件(后又补充四个文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18个文件的第17件为《宣传指南小册子》,其中有《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辑录了《论新阶段》“学习”一节中从“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至“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克服的”)”的文字。由此看来,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教育的。
最后还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明通俗的表述”,后者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有的研究者进而认为,今后要少用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两者之间的内涵在最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毛泽东本人对两种表述也不作严格区分,他更多地使用后者。但若从学理上说,“两者含义上完全一致”,则难以苟同。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语言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更加简洁,但内涵却比后者丰富。它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一个方面外,还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两者含义上完全一致”的见解势必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理解。再者,如果说两种表述的含义真的完全一致,那么苏共在20世纪60年代就大可不必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大可不必指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两种表述都是正确的,不存在一个比另一个更为精确或更为通俗化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化”、“东方化”、“西方化”、“本土化”、“民族化”一类名词,都是学者、文化人最初使用的,很难说得上是通俗的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实简洁明了,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两者在含义上有差别,因而在使用时可依据不同的情况、语境选择恰当的一种,少用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主张并不可取。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毛泽东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在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已经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化民族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问题,已经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代表。经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阐述和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对思想理论建设、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和久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坚持的理论方向。
注释:
①参见许全兴:《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②参见陈独秀:《国学》(1924年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4页。
③参见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第23期,1937年11月13日。
④参见李初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⑤参见《解放》第39期,1938年5月22日。
⑥参见毛泽东:《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6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冯文江听课笔记。
⑦参见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解放论文; 毛泽东论文; 艾思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