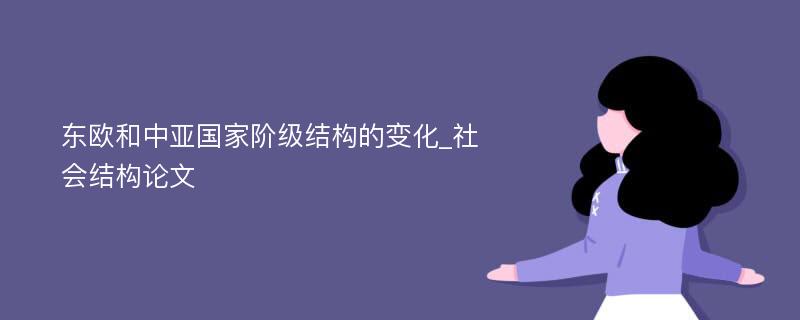
东欧中亚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东欧论文,阶级论文,结构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给东欧中亚地区的社会面貌造成了急遽、深刻和全方位的改变。这其中也包括阶级结构的嬗变。尽管截止到目前,这种演变尚未最终到位,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但它的基本轮廓业已凸现出来。
(一)
笔者以为,在推动东欧中亚地区的阶级结构变迁的众多因素中,以下三方面为直接原因:
其一,苏东国家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往近看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往远看是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论是斯大林模式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皆以“一元化”为基本特征而迥异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原生的、内在的历史传统的作用,决定了即便全力效法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今天的东欧中亚国家实际上也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只能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形态。东欧中亚诸国所独有的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的产生和活跃,就是这一特色在阶级结构方面的鲜明表现。
其二,苏东演变所确立的目标模式。尽管存在一些不同,但苏东国家在社会演变的方向上,都选择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模仿对象。虽然一时做不到全盘西化,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少东西,的确已经被移植到了东欧中亚地区。东欧中亚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两极分化的趋势、雇佣劳动阶级的产生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等等,都应当归因于此。
其三,剧变以来所实行的政策和具体操作方式。以东欧中亚各国普遍推行的私有化为例。就速度而言,东欧国家着手实行私有化的时间最早、推进得最快;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次之;中亚诸国又次之。与此相应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东欧诸国诞生得最早;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次之;在中亚地区又次之。从深度和广度着眼,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比较彻底,除了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维持国有制外,余者一律实行私有;俄罗斯等国的私有经济的范围则相对狭小些,它不仅被排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之外,而且在农业部门中所占的份额也有限;中亚国家更退一步,除了中小企业实行私有化外,大企业和土地全部维持国有制。由此导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东欧国家的根基最牢、规模最大,在俄罗斯等国次之,在中亚诸国又次之。匈牙利在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结果导致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匈牙利的强盛;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主要凭借行政手段去搞私有化的做法,则助长了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概括而言,今天东欧中亚国家的阶级结构的面貌可以表述为:两大基本板块、四个主要阶级。所谓“两大基本板块”,是指经过这些年的演变,原来的社会分层模式已经瓦解,今天的东欧中亚国家业已初步形成了“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泾渭分明、两极对峙的格局。其中,“上流社会”主要由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三个社会集团构成;而雇佣劳动阶级,则是支撑“下层社会”的主体。
下面,笔者依据所掌握到的材料,对上述四个阶级一一展开评述,以期对它们的基本特征做出大致的描述。
(二)
官僚以阶级的形态存在,这是东欧中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社会的一个具体国情或典型特征。官僚阶级,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阶级。马克思在对覆盖俄罗斯等东方国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时指出,该生产方式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其社会稳定地保持着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大一统”结构,从而使得以帝王为首的贵族阶级长期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这个贵族阶级,也就是官僚阶级的原始存在形态。
在剧变前的几十年间,苏东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它赋予干部以一般公民根本无法企及的地位、特权和利益,从而将它造就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这个干部集团,是官僚阶级的直接前身。关于官僚阶级对干部集团的继承性,单从官僚阶级和干部集团在人员构成方面的同一性,便足以得到印证。例如在俄罗斯,尽管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剧变和剧变之后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但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干部队伍一直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据199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总统班子中所占的比重为75%,在政府各部门中所占的比重为74%,在地方政权机关中所占的比重更是高达80%。在其他独联体国家中,目前坐在国家元首宝座上的,除了亚美尼亚外,多数都是苏联时期的官僚。其中有半数的最高领导人,干脆就是原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第一书记。
其次,它拥有全面支配社会的权力。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斯大林模式,其本质都是政治社会,即政治权力异常强悍,它不仅运作政治事务,而且统辖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正因为如此,政治地位的高低,是界定社会集团的决定性依据;掌握政治权力最多的集团,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显赫的阶级。尽管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在今日的东欧中亚地区,尤其是在独联体国家中,对政治权力进行压缩与制约的机制尚未最终生成,政治权力主导社会的状况依然如故。与此成因果,官僚也不似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是一个职业门类,而仍然维持着阶级的内涵。在今天的东欧中亚诸国,尽管从纵向化,官僚阶级的权势已不及昔日的干部集团;从横向看,各国的情况也存在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官僚阶级的手中都不仅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而直接管理经济事务;此外,官僚阶级还掌握着可观的舆论工具,这使得它能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呼风唤雨。
最后,官僚阶级具有不少转型社会独有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权力寻租”为主要形式的腐败现象的泛滥。在剧变之前,集权体制外加合法的干部特权,使得“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很有限;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健全的制约机制对“权力寻租”造成了有效的抑制。恰恰在今天的东欧中亚诸国,独立的经济正在生成而制约权力的机制尚不完备,于是“权力寻租”大行其道。以俄罗斯为例,其官僚腐败已经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表现之一,是腐败的范围广。据传媒揭露,目前俄罗斯官员的收入中,有1/3来自受贿,而其中的一半很可能还与黑手党有关。表现之二,是腐败的层次高,即卷入腐败的包括一大批位尊爵显的要员。例如,1997年就爆出了第一副总理丘拜斯的“稿费丑闻”和有几十亿卢布的灰色收入的传闻。另外,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首领也被指控与黑社会勾结,侵吞了数百万美元。
(三)
官僚资产阶级,是当前东欧中亚地区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集团。这个阶级在俄罗斯最为发达,也最具有典型性。关于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的规模,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可靠的统计数字。据有的俄罗斯专家估计,这个阶级的人数大约占到俄罗斯总人口的6%~7%,但他们手中控制着全国70%的银行资产和50%的工业产值,势力的确不同凡响。其中众人注目的金融寡头,正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一身兼具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属性,它有以下具体表现:
首先,从人员组成来看。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大都来源于“官僚圈”,即他要么是官僚阶级的“关系户”,要么干脆就是官僚出身。以在俄罗斯社会中叱咤纵横、风光无限的所谓“七大金融集团”的头头为例:五人在前苏联时期有为官的经历,其中波塔宁甚至是父子同在苏联外贸部任职;余下的两人——别列佐夫斯基、弗里德曼,头上虽无乌纱帽,但身旁却多官宦友。
其次,从发财方式看。这些人致富,主要不是靠生产、经营,而是凭分配、瓜分;不是借经济才能,而是用政治本领。具体而言,官僚资产阶级暴富的法门,一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二是利用外贸垄断体制及其所形成的商品国内外市场的巨额差价,进行国际贸易,获取暴利;三是凭借“全权委托银行”的地位,坐地分钱。这三板斧,尽管路数各异,但它们皆脱不了“以权谋钱”的窠臼。
再次,从行为方式看。他们对公共权力有强烈的兴趣。如前所述,官僚资产阶级是凭借政治权力发达起来的,所以,它自然就很在意维护这个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官僚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干预和操纵,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进行:(1)培植代理人。在当今俄罗斯政坛比较活跃、比较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后面,几乎都有官僚资本的影子在闪动;并且,它们的远近亲疏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政治势力的地位。(2)影响甚至左右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国家的不少大政方针,如1995年所推出的“抵押拍卖”政策以及1998年初的政府改组,都是官僚资本干政的“杰作”。(3)自己走到前台,直接参政。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1996年,金融寡头波塔宁、别列佐夫斯基分别出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和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要职。
最后,从发展前景看。官僚资产阶级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向。在用不名誉的手段聚敛了财富、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官僚资产阶级本身还在继续变动。有些官僚资产阶级将比较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的活动当中,通过促进经济的发展,使自己的财富进一步增殖。按照这样一条路线走下去,这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最终可望演变成比较标准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另一些人,自恃财富来得比较容易,加上本身素质的局限,他们把手中的钱财不是投到生产中,而是用到消费上,终日纸醉金迷、挥霍无度,最后只能成为消极、腐朽的食利者集团。
(四)
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是构成东欧中亚地区的又一个社会集团。从一般意义上讲,尽管有不少共性,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在今天的东欧中亚地区,由于社会转型方兴未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处在形成的初始阶段(或者叫做胚胎阶段),所以它们相互间的分化还不充分、差别也不明显,故而可以将它归结为一个社会集团。考察这个社会集团,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它主要是小私有化的产物。所谓小私有化,简而言之,就是政府通过出售、拍卖、租赁、退还等形式,将土地和小企业等规模较小的经济单位转交给私人的行为。而这些私人,就被培育为资产者。在俄罗斯,小私有化从1992年开始到1994年底大体完成。所以,到1995年,俄罗斯城市中建立的私人小企业约有90万家,农村中的个体农户经济达到28万户。在捷克,政府将过去没收的产业如土地、作坊、小企业、商店、饭店、旅店一律退还原所有者或其继承人,它们的价值约有220亿~250亿美元。此外,政府还通过拍卖、出售等方式,将10万余家、价值达300亿美元的国有小产业交到私人手中。所以,到小私有化基本完成的1992年底,捷克城市的个体经营者达到了120万人;同期,农村也出现了2万个体农民,这还不包括数千个私营农业合作社。当然,小私有化是催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但它不是惟一的力量。一些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了机遇而白手起家的人,也跻身于这一集团。
其次,它的发展不稳定,起伏性大。所谓“起”,是指私营中小企业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在俄罗斯,1993年底,各种小企业只有6万余家;但仅仅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即到1995年,俄罗斯的小企业数达到90万个。所谓“伏”,是指私营中小企业的淘汰率高。还是以俄罗斯为例,1997年,莫斯科市共有正式注册的中小企业40多万家,但经营状况好的只有24万家。其中莫斯科东北区登记注册的3400家中小企业,只有1500家在维持正常运行。在农业领域,由于经营困难,农户经济解体的数字已连续几年呈现上升的态势。1991年解体的农户为5000个,1992年为1.4万个,1993年为2.6万个,1994年为4.6万个,1995年达到了6.5万个。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东欧中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显然,这种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高淘汰率并存的局面,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处于大进大出、剧烈分化组合的动荡之中。
最后,它的阶级属性不够单纯,具有复合的色彩。在俄罗斯,目前私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就业人口为9.5人。在1996年的波兰,个人所有制单位平均雇佣的人数只有1.6个;合伙性质的单位平均雇佣人数仅为3个。同年,在全部私营中小经济中,74%的劳动力是所有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这些数字,不仅直接表明这些企业的规模确实比较小,而且也间接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今天苏东地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除了具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凭借资本获得收益外,恐怕还具有劳动者的身份,靠劳动谋生。
(五)
雇佣劳动阶级是构成东欧中亚地区“下层社会”的主体。这一阶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它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大体占全部社会成员的50%以上,堪称是社会金字塔的塔基部分。如果进一步细分,雇佣劳动阶级大体包括了三个阶层。一个是正在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集团。这些人拥有劳动力,并且能够被他人雇佣,以此获得收入来维持生存。他们既是雇佣劳动阶级的主体部分,也是其正常的存在形态。另一个阶层是拥有劳动能力,但欲出售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表现形态,就是所谓的失业大军。还有一个阶层是无劳动力可出卖的集团。它的成员包括退休人员、残疾人等弱势人群。
其次,它的处境最糟糕。这有多方面的表现,诸如政治地位的低下、精神状态的抑郁以及身体健康的恶化和寿命的大幅度减少等等。单就物质生活的贫困而言,就不仅有相对贫困,而且有绝对贫困。自社会剧变以来,俄罗斯最贫穷的10%的居民所得的收入在居民全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逐年下降;而最富裕的10%的居民所得的收入在居民全部收入所占的份额却逐年增加。这二者之间的差距,1990年为1:4,到1996年上半年发展到1:13,另外,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东欧中亚地区的人民生活状况普遍滑坡。例如在俄罗斯,到1998年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累计下降了30%左右。在保加利亚,从1993年至1997年,居民的贫困程度加深了10倍,许多家庭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塔吉克斯坦的情况最差,民众的生活水平已经倒退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水平,即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
最后,它具有若干时代和国情的特点。换言之,这个阶级,既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传统无产阶级,也与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有所区别。例如,它还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时期的好处。在俄罗斯,从80年代起,按人头平均分配,城市居民的每个家庭在郊区都可分得一块土地。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笔可观的不动产。俄罗斯人不仅可以在上面盖别墅,更可以将它用于耕种。只要利用休息日去打理一下,从这块土地上所收获土豆、黄瓜、西红柿,就足够他们全年享用。也就是说,单凭这块地,俄罗斯人就可以维持生存。又如,它的不少成员有多重角色。不少雇佣劳动阶级的成员,可能白天给老板打工,晚上或休息日则自己当老板;公开的身份是雇员,但非正式的还有别的职业。换言之,他们是打上了其他阶级烙印的新型的雇佣劳动阶级的分子。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关于四大阶级的论断,是将东欧中亚诸国看做是一个整体而得出的。具体到某一个国家,有的可能四者俱全,如俄罗斯;有的则可能只有其中的两三个,如大多数东欧国家。另外,今天东欧中亚地区有的国家中,还存在着上述四大阶级以外的社会集团。譬如,黑社会就是俄罗斯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外国资产阶级,在今天的匈牙利就很风光。但总起来看,类似这些社会集团,一来只存在于个别国家中,不具有普遍性;二来能否稳定地生存下去,尚需进一步观察,所以,它们暂时还无法与上述四大阶级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