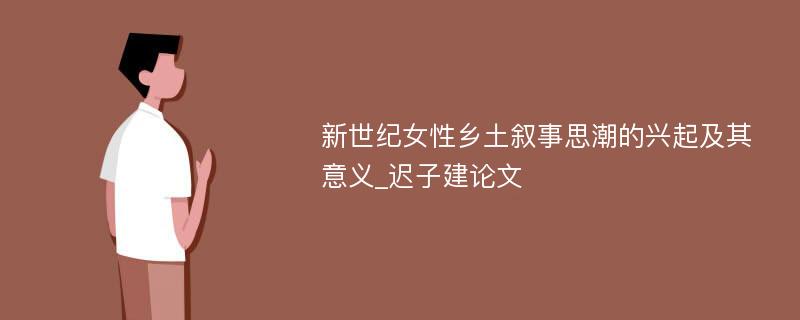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乡土论文,潮流论文,意义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80、90年代,除了迟子建、铁凝等少数几个女作家外,乡村几乎是女性写作的盲点。但90年代末直至新世纪这一状况渐渐得到改变。愈来愈多的女作家开始介入一向由男作家主宰的乡土叙事①领域。其中较具影响的作品②数量就相当可观。首先是迟子建、孙惠芬、葛水平等专事乡土叙事作家的诸多作品,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花牤子的春天》,孙惠芬《民工》、《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吉宽的马车》、《上塘书》,葛水平《喊山》、《甩鞭》、《地气》、《黑口》,邵丽《明慧的圣诞》等;而以往并非专事乡土叙事的女作家们也纷纷推出她们的乡土力作,如王安忆《天仙配》、《喜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发廊情话》,铁凝《笨花》,林白《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方方《奔跑的火光》,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谁家有女初长成》,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城乡简史》,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盛可以《北妹》,王建琳《风骚的唐白河》……显然,女性乡土叙事不仅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的重镇,甚至也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作为一股崭露头角又有独特而积极文化诉求的新生创作潮流,迫切需要评论界、研究界的介入,为其命名、评介,宣告其存在,关注其动向,与创作界一同谋求其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提升。
一、乡土经验的女性形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现,“乡村”也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热点。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以阎连科、刘醒龙、尤凤伟、李佩甫、李锐、周大新、关仁山、何申、张宇等为代表的新乡土叙事潮流,这股潮流进入新世纪,加入底层文学的大潮中,在新世纪的头十年更是蔚为大观。它传达了80、90年代文学语境中多少被忽略的、转型期本土经验中一个重要部分,即乡土/底层的经验。但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乡土/底层经验,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性别身份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色彩。事实上,从20、30年代的乡土文学到40年代至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再到新时期以来的新乡土文学,近百年主流乡土文学所传达的看似中性的乡土经验,实际上是男性的乡土经验(底层文学的情形也类似);同样的,看似中性化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农民形象。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女性经验,女性经验也会因为民族、空间、阶层等等多重身份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尽管对经验主体的性别差异性的关注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立根基础,但这一话语自身却忽视了由性别之外其他社会身份的差异而带来的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因此,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大面积地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一脉一直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的乡土经验,从而提示乡村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村/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从而呈现女性经验的多元复数形态。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既是女性的,又是乡土的,但二者并非简单相加,而是在互动中构筑了女性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既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转向,又标志着新世纪乡土文学不容忽视的新特质。对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意义。但是,这股文学创作潮流却一直处于学界与批评界的盲点中,个中缘由大致如下:
众所周知,主流文学研究、批评界对现当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历来非常充分,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年语境中甚至达到一个高潮,但极少见到专门针对女性乡土文学(主要是乡土叙事)的研究。虽然不同时代的女性乡土叙事都会以个体面目吸引批评、研究的目光,如学界对萧红、丁玲、铁凝、迟子建等人的乡土叙事的持续关注,但很少有研究者意识到女性乡土叙事彼此之间存在着的历时性或共时性互文关系,及其所包含的重要文化意义。因此,尽管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蔚为大观,并一再以个体面目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甚至成为一时的热点(如本文开头我们提到的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文本频繁得奖就是有力的明证),但却从未被作为一个具有新特质的文学潮流、创作倾向来看待。已有的研究存在以下偏颇:在研究格局上,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一直在新世纪乡土小说整体格局中被提及(如新世纪头十年有关孙惠芬、葛水平创作的评论),这样的研究格局当然有意义,但也容易淹没女性乡土叙事的异质性;同时由于在新世纪头十年乡土小说格局中,女作家的创作相对处于边缘,因此,获得关注度必然也有限,常常处于被附带提及的位置。
而女性主义学界对这股创作潮流也始终处于盲视状态。这还得从这股创作潮流的滥觞说起。任何一股文学潮流的产生,都始于涓涓细流终至蔓衍成潮。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也如此,除了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的催生外,实际上有其自身内在的必然逻辑,其滥觞早已出现。
尽管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最初发端于知识女性对自身经验与境遇的切肤之痛,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批女性文本,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洁《方舟》、《祖母绿》等③,但随着这一写作立场的深入,一些眼光敏锐的作家开始从反思乡土生活、乡村女性的经验、境遇中来展开性别的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铁凝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三垛”④。“三垛”不仅是对造成乡村女性悲剧宿命的乡村传统文化,乃至20世纪各种名目的现代文化中男权机制的审视、反思,也是对女性文化谱系的溯源、寻根、自审。“垛”的意象已然是女性乳房的隐喻,是孕育生命、包容万物、藏污纳垢的母性文化的原型,同时这一来自乡野的意象俨然又是一个母体性的乡村形象。20世纪90年代初徐坤的《女娲》、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同属这一路径,仍然是将性别议题承载于对20世纪中国乡村女性独特的生存方式、性别境遇的反思与批判中。当然,反思与批判的姿态远要比铁凝“三垛”尖锐。这一叙事路径实际上在性别视角下延续且超越了“五四”启蒙文学将国民性问题与对乡村女性的叙述挂钩的思路,延续且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以乡土作为文化溯源以及作为自审的最主要场域的思路。而铁凝在90年代推出的一组短篇小说《小黄米的故事》、《秀色》、《孕妇和牛》则转向以一种悲悯、包容甚至认同的姿态去面对乡村女性的性别生存经验,但与此同时,在对都市、知识女性的生存经验表达中,铁凝则展开对男权文化以及在男权文化阴影下女性生存自身的尖锐解构与批判的性别立场,如《玫瑰门》、《对面》、《无雨之城》、《永远有多远》等。铁凝的两种姿态实际上表明她开始在意特殊的空间与阶层的身份是如何影响了乡村/都市女性不同性别经验、主体位置的建构。
在这方面特别应当提到迟子建的创作。迟子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创作绝大多数涉及乡村生活,尤其是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同铁凝一样,她也非常注意乡村女性的独特性别位置。如短篇小说《逝川》,乡村男权文化传统造成漂亮能干的吉喜一辈子孑然一身的悲剧,但她平静豁达地在日出日落间劳作,在对自然和生命的大爱、对命运的承受与包容中,吉喜超越了男性、超越了苦难,成就一份乡村女性生命的尊严与高贵,这其中包含了对男性的宽容与温情。事实上迟子建的乡土叙事总是充满温情,《亲亲土豆》、《日落碗窑》、《白银那》都表现了在艰难生活中夫妻之间、亲人之间、乡亲邻里之间的温情。他们互相以自己卑微而韧性的生命支持着对方,点点滴滴共同求取生存之光。但迟子建更多将这种温情归于人性本身的高贵,而不是归于乡村传统伦理。20世纪90年代以男作家为首的乡土叙事中有一种美化乡村传统伦理(包括父权秩序)的文化守成倾向,迟子建的写作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于这一倾向,实际上她的很多作品呈现了乡村传统伦理文化对自然生命(特别是对女性和孩子)的压抑、宰制。由此可见,铁凝与迟子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些乡土叙事文本实际上标志着女性主义叙事本土化的苗头。
这样的梳理让我们惊奇地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女性写作中,乡土叙事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其脉络却一直没有中断,性别立场对乡土叙事的渗透也一直存在。但这样的写作脉络却处于无名、自在的状态,得不到应有的辨识、梳理与命名。尽管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持续不断地倡导女性主义的本土化,但对身边一直存在着的女性乡土叙事细流却始终熟视无睹。90年代被认为最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写作是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表达都市知识女性经验的写作,所有女性主义批评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这一脉女性叙事潮流上。甚至到了新世纪头十年,女性乡土叙事已经蔓延成潮,但依然没有引起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注意。
主流学界与女性主义学界的上述盲视其实可以归咎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方法论、知识论,实际上很难向包括乡土文学在内的其他研究领域渗透,因此无法与其他话语建立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一再被拒绝的女性主义话语也只能满足于自说自话。这就造成在乡土/底层文学研究视野中,女性乡土叙事在乡土/底层层面上被阐释,其性别视角带来的独特内涵被忽略;而在女性文学研究视野中,女性乡土叙事又仅限于性别层面上被阐释,其更丰富的内涵被忽略。在前一个视角下,女性乡土叙事被归入乡土叙事潮流;在后一个视角下,女性乡土叙事又被归入女性写作潮流,而忽略了探寻性别视角与乡土视角之间的互动及其给女作家的乡村表述带来的新质,更未曾意识到女性乡土叙事在对20世纪的乡土文学传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传统的继承、融合与超越中可能成长为一种新的叙事倾向。
二、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以知识女性的青春、爱情、自我为书写内容的“五四”女性文学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渐渐衰落,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庐隐的创作或中止或停滞。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事实上是女作家的乡村叙事在延续着女性文学的血脉⑤,如冰心的《冬儿姑娘》、《张嫂》、《分》,罗淑的《生人妻》、《桔子》、《刘嫂》、《井工》等,白薇的三幕话剧《打出幽灵塔》,丁玲的《阿毛姑娘》、《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包括她转型后创作的《田家冲》、《水》、《奔》、《东村事件》,更不用说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牛车上》等。女性乡土叙事并没有放弃“五四”女性的性别立场,只是作了转换,将女性性别意识带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这在萧红的全部创作以及丁玲40年代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等作品中更有突出的表现。历史时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类似的文学史逻辑同样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女性文学的发展逻辑中。
我们知道,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女性主义写作潮流到90年代上半叶达到高潮,被视为高潮标志的是林白、陈染、徐坤、徐小斌、海男以及诗歌领域的翟永明、伊蕾等人的作品,表达都市知识女性经验,写作以个人、自我、身体为中心。这一高潮在90年代后期渐渐消歇,尽管仍有一些颇具分量的新作问世,如世纪之交铁凝的《大浴女》、张抗抗的《作女》,但作为创作潮流已渐渐失去先前群体性的整齐阵容、迅猛的发展势头和新锐的精神锋芒。即便像《大浴女》、《作女》这样的佳作也没有开辟出女性主义写作新的话语场地、呈现更丰富的叙事可能性。这里似乎还应该提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的所谓70年代出生“都市新人类”女作家们的写作⑥:从表面上看这一群体的创作似乎延续女性主义写作的路径(当时的批评界也不乏这样的期待甚至论断),成为女性主义写作潮流的后续力量。同样是类自传色彩的女性生活场景、散漫情绪化叙事方式,但主人公已由抑闭孤独的知识女性变成隶属“都市新人类”的狂野的“坏女孩”,叙事空间已由幽闭的“自己的房间”转换为酒吧、迪厅,女主人公们已不再作痛楚的精神漫游,而是沉湎于酒精、爵士乐、性甚至大麻的疯狂刺激中。这一创作群体虽然竭力要表明这种“另类”生存方式的反叛意义,但“另类”和反叛在这个群体的语境中更多的是自我作态的时尚化表演,一种以反媚俗的姿态出现的隐蔽媚俗,并不具有先前的女性主义写作特有的性别精神立场。这一群体的写作可以看成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这一脉女性主义写作潮流在资源日益枯竭背景下的下滑与陷落。
于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陷入沉寂、停滞且处于困境等断言纷至沓来。恰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女性主义写作的转机悄然来临。世纪之交,底层文学潮流兴盛一时,女作家也加入这一潮流中,王安忆的《富萍》(2000)、《上种红菱下种藕》(2002),方方《奔跑的火光》(2001),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2002),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2002)、《民工》(2002)等作品相继问世,并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出于本文第一部分论述的原因,这些作品理所当然地首先在底层文学/乡土文学的语境中被接受、解读。当然,它们也会在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下被解读,但从没有人以乡土与性别相兼容的双重视角来看待这批文本,因而也就很难意识到这批文本之于中国女性主义写作转型的意义。直到2004年林白推出被称为“最胆大包天尝试”的另类乡土叙事文本《妇女闲聊录》,评论界联系她此前的《枕黄记》(2001)、《万物花开》(2003)才震惊于林白的转型⑦。“从一个崇尚个人的女性主义作家转向对中国民间大地的热烈关注”⑧这样的评价,在对《妇女闲聊录》的众多评价中颇具代表性。林白创作的新变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姑且将林白创作的新变以及评论界对此的反应称之为“林白事件”。
“林白事件”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为什么选择林白创作的新变作为女性主义写作转型的标志?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林白一直被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标志性人物,在人们的意识中,所谓“女性主义写作”就是指林白式的以个人、自我、躯体为中心的写作。而这就涉及到我们对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潮流的理解。事实上,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潮流是多元共生的,陈染、林白的创作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如果说,林白、陈染这一脉以女性的个人、自我、躯体为中心的特立独行的文本实践构成这个潮流的浪尖潮头,那么,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方方、池莉等人具有更广阔社会生活内涵的创作,则以沉厚的面貌构成这一潮流广阔而坚实的腹地风景。作为一种文学潮流,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于前者,后者似乎并不特别张扬女性主义的叙事立场,但不等于就没有这一立场,而是将这一立场带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从而使这一立场变得隐蔽却更显坚定而沉着。甚至在她们的一些超越性别议题的作品中,性别的立场也昭然若揭。如王安忆90年代初的《叔叔的故事》,以男性叙事人的口吻讲述一个父辈(叔叔)与子辈(“我们”以及“叔叔”的儿子)的故事,小说最终结束于这样的追问:一个“将儿子打败的父亲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而一个被父亲打败的儿子的前景就更可想而知了。叙事从而不动声色地宣告了以权力为中心的父子秩序的颓圮⑨。这已然是一个坚硬无比的性别立场,却鲜被识别。在如何界定一个作家、一个文本、抑或一种写作潮流是否具有女性主义立场问题上,似乎不能看写了什么,而要看怎么写。伍尔夫曾经说过,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区别并不在于男人描写战争而女人描写生孩子,而在于两个性别都表现自身。超越性别来书写性别才是女性主义写作的最高境界。正是这种超越性别又书写性别的文本实践才启示着女性主义写作广阔的话语前景,为这一写作潮流提供了个人、自我、躯体之外的叙事可能性,并最终酿成新世纪的转型。其实,具有文学史意味的转型发生在林白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同样被看作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标志性人物的陈染身上,个中原因也莫不如此。比较林白、陈染两人在90年代的创作,不难发现林白的性别化叙事并非如评论者(甚至包括林白自己)所认定的那样极端封闭、自恋,而是不乏个人、自我、躯体之外的内容,如故乡亚热带边陲小镇(沙街)上的各色人情风土、乡野的诡异传奇、底层民间的悲凉经验。而在陈染的作品中却很难见到这些。因此,林白创作的转型契机实际上早已孕育于她在90年代的写作中。
“林白事件”另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形形色色欢呼林白转型的话语实际上都不言而喻地包含这样的论断:那就是转型后的林白已经放弃先前女性主义的个人化立场,回归主流叙事。这实际上也是主流文学界对以林白为代表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转型的期待⑩。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样的转型就意味着性别精神立场的后撤,意味着女性主义写作血脉的中断以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终结。但事实上,无论是林白本人的创作,还是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都没有放弃女性立场,而只是作了转换,将女性性别意识带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正如我们上面一再提到的,超越以个人、自我、躯体为中心的写作并不等于就放弃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女性写作的乡土转向,是否定之否定后的提升,而不是简单的后撤、回归。
三、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
与以往女性文学相比,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最大的不同点是超越女性/性别的议题,将性别视阈引向更广阔的乡村生活。《笨花》、《额尔古纳河右岸》、《第九个寡妇》、《赤脚医生万泉河》、《妇女闲聊录》、《上塘书》等新世纪头十年最重要女性乡土长篇小说,除了《第九个寡妇》较多展开乡村背景下的女性/性别议题外,其他作品的叙事域都面向更广阔乡村的历史与现实,甚至有的作品最重要的主人公都不是女性人物。性别视角有意无意的介入,使得这批作品对乡村的历史与现状的叙述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中性化(实际上是男性化的)乡土叙事的崭新特质。这样的特质首先表现在对乡村日常性的还原上。当然,日常性并不是新鲜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中也不乏乡村的日常性,甚至新世纪男作家的乡土叙事也刻意凸现乡村的日常性,以此来呈现总体性终结后的乡村面貌,颇具代表性的是贾平凹的《秦腔》。那么,性别视角的介入又使得女性乡土叙事对乡村日常性的表述呈现怎样独特内涵?《秦腔》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来剖析这个问题。
尽管《秦腔》作者贾平凹一再声称自己所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评论界也一致认为《秦腔》呈现的是总体性终结之后的碎片化的乡村,但在文本叙事层面《秦腔》实际上潜藏一种重返总体性的努力。这集中表现为叙事对象征、隐喻的热衷。首先,小说总体叙事框架极富象征意味:叙事以疯子引生对白雪的痴恋开端,最后终结于引生亲眼目睹白雪在七里沟崖崩的轰鸣声中倒地。在白雪倒地前的一刹那,引生看到她身后佛光万丈,“如同墙上画着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白雪作为诗意化、纯洁化的传统乡村的化身,她的倒下暗示着传统乡村的香消玉殒。除了白雪,其他的人物也都有象征意味:执迷秦腔的乡绅型人物夏天智和执迷占卜的巫师型人物中星爹,两人象征着包含宗法伦理、民间戏曲、鬼神信仰在内的一整套乡村传统文化谱系,两人先后死去意味着整个乡村文化传统的终结;而老村长夏天义的死则代表着20世纪中叶乡村政治传统的终结。夏天智、中星爹寿终正寝,是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的自然宿命,夏天义却死于一场意外的崖崩,而这场崖崩与夏天义不顾自然规律和社会人心,近乎偏执地在七里沟淤地不无干系。从这样的情节设置中不难看出作品所包含的对20世纪后半叶乡村政治历史的隐喻。不仅如此,甚至那些鸡零狗碎的“泼烦细节”也充满象征隐喻色彩,如白雪和夏风的女儿牡丹生下来就没屁眼,暗示着传统乡村文明无法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获得自新的动力,纳新却不能吐故。夏天智四兄弟名字分别为“仁义礼智”,而作为下一辈的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却分别名为金、玉、满、堂和瞎瞎,这毫无疑问象征着原本散佚乡野的儒家传统的消亡,以及乡村迅速的功利化、世俗化(11)。类似这样例子还有许多。由此可见,《秦腔》并没有真正回归自在、本真的日常生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小说的叙事姿态。虽然小说第三人称叙事人呈现价值立场中立,但小说并不缺乏价值判断,这个判断由另一个叙事人——自我阉割的疯子引生来完成的。引生生理上的去势并没有导向叙事姿态的放低,除了痴恋白雪时陷入一种癫狂状态外,疯子引生在其他时候基本上思路清晰,价值判断明确,引生其实是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乡村代言人(作者自己)的化身。
与《秦腔》相较,同样描写当下乡村中的日常性,《妇女闲聊录》则完全不同。在这部作品中,乡村的日常生活与其说是被表述不如说是被呈现。小说以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乡村妇女木珍滔滔不绝的闲聊,来呈现她的家乡王榨村庞杂的日常生活景观。作者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不是表述者,从而最大限度地祛除了表述(话语)中所隐含的权力机制。木珍的叙述没有精心设置的叙事框架、象征隐喻,甚至价值立场含混,王榨村的鸡零狗碎就是鸡零狗碎,没头没尾、无始无终,但就是这样看起来支离破碎暧昧含混的鸡零狗碎,其实恰是日常生活最原初的状态、最完整的面貌,让人从中得以窥见长期以来乡村一直被各式各样的话语遮蔽的自在面貌。
林白《妇女闲聊录》选择呈现而拒绝表述,孙惠芬的《上塘书》却不拒绝表述,“上塘书”意味着要为上塘做书立传,这俨然是传统宏大叙事的姿态。再看小说的章节,似乎也是按照方志、村史编撰方法,以政治、地理、交通、教育、贸易、历史、文化等等分类来表述上塘村。作者并不抵抗宏大叙事逻格斯化的命名与分类方式,而是承认这套分类、命名方式,同时又赋予它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上塘的交通”一节为例:从上塘到歇马镇上的山道、甸道,到镇上唯一的柏油马路,到村里通往坟地的道路,再到上塘男女身体的交通,最后到上塘人心灵之间的交通;从赶集的女人们在甸道上的叽叽喳喳,到瘫在炕上多年被叫作燕子的老婆婆50年后第一次由儿子推着从村道上回娘家,再到上塘男女在僻静村道上偷情寻欢……这一切都被命名为“交通”。原来鸡零狗碎、飞短流长也可以被堂皇地命名为“交通”?这是和“交通”、和历史、和逻格斯开了一个玩笑,就在这玩笑中文本叙事“拯救”了上塘,使它不至于被政治、地理、交通、教育、贸易、历史、文化这些僵硬无情的分类框框割裂得支离破碎、无血无肉,从而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上塘,这是日常生活的原初状态,也是上塘的原初状态。
无论是《妇女闲聊录》还是《上塘书》,在叙事的姿态上,无疑都拒绝代言,非常低调,并由此造就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
与林白的断然拒绝、孙惠芬的“阳奉阴违”相比,铁凝的《笨花》似乎最接近人们熟悉的宏大叙事式的乡村史诗,但却只是“在宏大叙事和家常日子之间找到一种叙述的缝隙,并展现了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12),这种东西正是铁凝所理解的“笨花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精神;同样,笨花村的秩序就是日常生活的秩序。这样的秩序兼容了“笨”(沉重)与“花”(轻盈),宏大叙事与鸡零狗碎,风云与风月,前者不能覆盖后者,后者也不能拆解前者。笨花村的历史就是日常生活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没有中断只有绵延,没有突变只有渐变,不是除旧布新,而是以旧纳新。《笨花》叙事并非以鸡零狗碎来颠覆宏大历史,像以往的女性主义小说、新历史小说那样,而是让两者纷然并置,甚至消弭两者之间的界限,回归日常生活最原初的兼容并包状态,呈现乡村混沌、包容的母体特征,这就是铁凝所心仪的“笨花精神”。
无论是《妇女闲聊录》中的王榨还是《上塘书》中的上塘,实际上都具有这种“笨花精神”:一种从原初的日常生活中升腾而起的自足的乡村精神,这也是一脉女性版的乡村精神、一片女性的乡土。而这恰是传统乡土文学中少见的。
四、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女性主义写作作为一股新锐的创作潮流已经不复存在,却衍化为一种更具普泛性的创作视角,被更多的女作家所接受。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开始作为一种知识谱系参与了女作家们的多重叙事视角的营构,进入更加广阔的叙事领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崛起,它超越性别但依然书写着性别。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乡土中国的文化自觉与重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乡土文学依然可能是中国文学的重镇,那么,女性主义向乡土叙事领域的渗透,其意义将是不容小视的,它不仅意味着女性文学的新动向,同时意味着乡土文学的新动向。
注释:
①“乡土叙事”是从“乡土文学”中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乡土小说。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应该在一个宽泛意义上来理解“乡土文学/叙事/小说”,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它应该包括“底层叙事”中以进城农民工生存状况为表现内容的作品,这部分作品应该看作乡土叙事的特殊变体。换句话说,“乡土文学”是个大概念,而新世纪的“底层叙事”以及20世纪50-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都是乡土文学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
②“较具影响”指引起社会反响,如引起读者、评论界广泛关注、获得各种大奖项、进入权威小说选本、排行榜等。部分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作品获各种大奖的情况如下:《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发廊情话》、《大老郑的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一届“仰韶杯”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笨花》获第三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2006)最佳奖”,《城乡简史》、《明慧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喊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2005年“人民文学奖”,《地气》获《黄河》2004年“雁门杯”优秀小说奖,《妇女闲聊录》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奔跑的火光》获第一届“仰韶杯”优秀小说奖,《花牤子的春天》获广东佛山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
③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收获》1980年第5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张洁:《祖母绿》,《花城》1984年第3期。
④“三垛”包括《麦秸垛》(1986)、《棉花垛》(1988)和《青草垛》(1995)。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王安忆1989年具有强烈女性主义立场的《岗上的世纪》,作品以知青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探寻女性的身体和性所具有的超越性的精神向度。
⑤参见乐铄:《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及其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⑥自1998年7月《作家》推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始,短短的两三年间,70年代出生女作家已然形成一个不小的群落,这一群落包括卫慧、棉棉、周洁如、魏微、戴来等。卫慧的《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象卫慧一样疯狂》等作品基本上代表着这一群体创作的大致面貌。
⑦评论界对林白转型反映强烈,参见张新颖:《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下降”的艺术》(《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贺绍俊:《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读林白〈妇女闲聊录〉》(《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1期)、施战军:《让他者的声音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林白〈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陈思和:《“后”革命时期的精神漫游——略谈林白的两部长篇新作》(《西部文学》2007年第10期)等文章。
⑧陈思和:《“后”革命时期的精神漫游——略谈林白的两部长篇新作》,《西部文学》2007年第10期。
⑨参见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94-196页。
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10月5日的《北京晨报》甚至以“林白,不再做女性主义斗士”为题来推介林白的另一长篇《致一九七五》。
(11)这些细节的象征意味在多名学者针对《秦腔》评论中已被反复提及、论析。
(12)铁凝、王干:《花非花、人是人、小说是小说——关于笨花的对话》,《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标签:迟子建论文; 林白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乡土论文; 文学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铁凝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笨花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