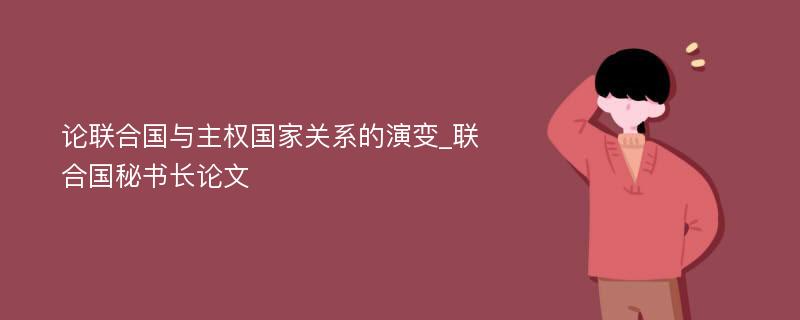
试论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主权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它与“世界政府”或“超国家组织”最大的不同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冷战后这种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科索沃危机促使人们对联合国的作用,尤其是对主权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联合国与其成员国的关系如何变化、如何定位,关系到未来联合国的性质,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的变化趋势作出分析。
一 从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看联合国
从宪章看,联合国属于国际组织,因此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性质规定了联合国的性质。尽管主权国家千差万别,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作为国家,它们具有人们经常提到的国家的“三要素”:领土、统治权和国民。(注:关于国家的“三要素”可参见[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作为主权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主权。布丹、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著名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主权,尽管它们的主权理论有所不同,但它们几乎都论证了主权是一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权力。抛开那些围绕主权概念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意味着国家“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权力”。(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第67页。)最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在其自身的主权获得承认的同时,也须承认其他国家具有独立的主权领域”。(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0页。)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础。
主权国家在处理与其他主权国家关系的过程中,构成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国际法。那么,加入一个国际组织对国家至高无上的主权意味着什么?
显然,主权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后其主权必然要受到一定制约。首先,必须遵守组织规章和有关国际法原则。其次,必须承担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再次,如果违反组织规定或有关法律会受到制裁。但没有国家认为参与国际组织意味着对国家主权的放弃,或国际组织有权任意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第一,国际组织不同于世界政府,不是国家主权之上的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主权国家间的合作。第二,国际组织是主权国家成立的,它的权力是主权国家授予的,也是由各国政府的代表来行使的。接受或附加何种条件,何时退出组织,这些权力均由主权决定。第三,加入国际组织并不意味着将国家主权转让给组织机构,不管加入组织后要签订多少条约,承担多少法律上的义务,都“不会因其数量多少本身影响该国主权”,“只要这些法律约束不影响其最高的立法权和执法权的性质。”(注:[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页。)
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国际组织的发展表明,主权国家缺乏行使和保护完全主权的必要能力,而且愿意并逐步将其部分权力交给跨国的非领土内组织机构。(注:ImmanuelWallerstein, "The New World Disorder:If the States Collapse, Can the Nations beUnited?" Albert J.Paolini ed.,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lobalGovernance:The United Nations,the states and Civil Society,Macmillan Press LTD,1998,p.171.)国际组织不只是具有合作的职能,而是走向一体化、走向世界政府的开始,可以接管并行使成员国管辖范围内的职能。(注:饶戈平主编:《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对主权国家的干涉问题一直是个具有极大争论性的问题。一种观点反对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内政任何形式的干涉,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组织可以对主权国家进行“依据权利的干涉”和“人道主义干涉”。根据组织原则,一些国际组织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超国家性。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看,如果安理会通过决议,联合国就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从法律上看,这应该属于正常合法的干预范围,争论点在于如何解释有关强制干预的条款。在实际中,判断干涉的合法性更取决于国际组织中大国的意志,因此造成国际组织中不公正的干涉现象,即大国对弱小国家主权的干涉,或国际组织屈从于大国的意志,违反国际法和组织章程,对主权国家进行干涉。
国际组织对其主权成员国管辖范围内事务执行强制干预,甚至武力干预,这属于极为特殊的现象。不能因为联合国具有某种超国家性,就认定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具有普遍的、强制性的干涉权,甚至将联合国划归“超国家组织”。不管理论上如何错综复杂、争论不休,主权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一般情况下,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没有普遍的、强制性干预权力,这是国际组织区别于超国家组织或世界政府的形式。如果若干国家自愿将其最高立法或执法权交给一个机构,这就不是国际组织,而是国家的合并或联邦国家。如果一个组织的职能不仅是促进政府间合作,而是制定法律以直接适用于成员国领土,对其成员国主权具有普遍的、较强的干预能力,这个组织也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是“超国家组织”。(注:饶戈平:《国际组织法》,第17页。)今天的欧盟可以说具有超国家组织的性质,但联合国不是超国家组织。
联合国的成立是国际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设计上看,联合国比以前所有国际组织更广泛、更有效、更具全球性。由于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组织,是一个具有某种强制权力的组织,从最初设计和宪章看,尽管具有某些超政府性和全球性特征,但它既不是超国家组织,也不是世界政府,联合国仍然是一个国际组织,关于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联合国。
从宪章看,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联合国是大国利益平衡的结果,是当时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是大国享有某种特权的组织。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的态度。
第二,联合国是主权国家建立的、以维护主权国家独立、平等、不受侵犯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组织。宪章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保证“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等原则。
第三,它是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对主权国家具有某种超国家权力的组织。联合国有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强制制裁行动的权力。但这种超国家权力只是在“国际和平及安全”受到威胁时,或在主权国家受到侵犯时才适用。不能因为这一点认为联合国是超国家组织,因而具有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普遍权力。
第四,联合国是主要以谈判、调查、斡旋等和平手段解决主权国家间争端的组织。
第五,联合国是具有全球性、综合性的国际组织,肩负着管理全球性事务的责任。从联合国的设置和宪章看,联合国不仅关注国家间关系,也关注人类命运,关注普遍的人权;不仅关注狭义的传统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如战争和平问题),也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宪章中处处可见“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全体人类”、“全球人民”等字样,反映出宪章“理想主义”、“全球主义”的色彩。
联合国是一个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受主权国家制约的组织,但同时又具有从事一些超越主权、干预主权国家事务的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似乎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国际政治大师摩根索对这一矛盾关系有过论述:“这一冲突就是主权国家和有效国际组织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调和的。国际组织要有效,就必然损害它的成员的行动自由;成员国要是强调它们的行动自由,就必然损害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宪章》本身说明了这一解决不了的冲突,它一方面强调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另一方面给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权地位,这种地位相当于一个小型世界政府。”(注: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591页。)这就是说, 宪章赋予联合国某种超国家的权力,赋予它管理全球性事务的责任,同时,作为联合国主体和权力授予者的国家,其主权得到保护,其内政不可干涉。这意味着联合国的权限与主权国家的权限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冲突关系。
从以上联合国的几个特征看,联合国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结合的产物。所有矛盾在创建时已经埋伏,有的因为被冷战所掩盖才没有显露。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与主权国家间存在的许多矛盾日益尖锐,如果不对这些矛盾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重新定义,联合国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 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
从成立到今天,联合国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点。冷战时期,联合国基本遵循了维护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其全球主义、世界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那一面没有凸显出来。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联合国和主权国家都面临越来越多过去不曾遇到和想到的新问题、新挑战。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许多传统的观念被认为已经过时,一些新的概念和原则正在逐步被各国接受。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世界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自由化、市场化风行全球。通讯、媒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冲击着世界每个角落。发达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更希望看到世界各国的开放,看到主权的动摇以及符合其利益的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形成,这也是西方国家弱化主权概念的目的。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经济、政治上的干预。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利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通过联合国进行协调、干预的要求也逐步增多。许多政府感到,面对毒品犯罪、恐怖主义活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现象的国际化、全球化,它们需要联合国在全球范围采取强硬态度打击各种跨国犯罪。
冷战结束后,全球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国民的安全观念以及国家的安全重点也在变化,主权国家内的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日益突出。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人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综合安全问题,对安全概念进行了广义的解释。早在199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哈克博士在欧洲议员会议上阐述了他的“人类安全新概念”,认为这种新的安全概念自冷战结束后便逐渐形成。他的新安全概念包括四个内容:不仅是国土的安全,而且是人民的安全;不仅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安全,而且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安全;不仅是国家的安全,而且是个人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上的安全;不仅是防御国家间冲突,而且是防御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注:联合国新闻部发行:《联合国纪事》(中文版),1993年12月,第4期,第42页。)这种安全概念是何等宽泛,完全超出了传统的、狭义的安全概念。因此有人提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应该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建议联合国派遣“绿色维和部队”。(注:见孙林主编:《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反映在主权问题上,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原则”受到冲击。谈论“后主权国家时代”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已极为盛行。从近些年联合国的实践看,人道主义干预已经被接受。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不否认主权的同时又说,“那种绝对的、排他性的主权已不复存在”。(注:加利:《和平纲领》(中文版),纽约,联合国新闻部发行,1992年,第9页。)安南秘书长将“善政、 人权和民主化”视为和平与发展的“基石”,将其作为联合国的首要工作来推动。科索沃危机后,安南又一再阐述他的“新主权观”,提出不容许以主权为借口践踏自己国家公民的权利,主权不能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障碍。(注:可见安南:《在转变中自我更新》及 Preventing
War
anddisaster。纽约联合国新闻部1997及1999年。)
这种变化对联合国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主权过时论”挑战主权国家组织——联合国,另一个影响是“人权高于主权”挑战联合国“不干涉原则”。这就导致冷战后联合国作用“边缘化”和“扩大化”同时出现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但实际上这是一致的,这一逻辑是:主权不再是至高无上、不容干涉的,所以联合国应该能超越主权界限,应该实施人道主义干预,否则就不能发挥作用,就应该被其他组织替代。
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联合国干预活动“扩大化”的趋势:联合国从干预“国家间”事务走向干预“国家内”事务,甚至起着类似临时政府的作用;从中立、不干涉内政、非强制等维持和平行动走向不经主权国家同意的“强制维和”或“超越维和”;(注:加利:《和平纲领》。)从干预原本针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狭义安全”问题走向干预包括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健康安全等在内的“广义安全”问题;从干涉国家行为体走向干涉“个人安全”和“普遍人权”。安南甚至用“个人主权(individual sovereignty)”来解释主权在民,呼吁联合国“要保护每一个人, 但不包括那些破坏人权的人。 ”(注: Kofi Annan,"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The Economist,Sept.18[th],1999.)这意味着联合国不仅要管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还要对人类社会中不分主权、不分国籍的所有个人的安全、健康以及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负责。
但另一方面,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陷入要么扩大对主权国家的干预和要么被“边缘化”的困境。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军事力量等方面均占优势。它们借助强大的舆论工具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力图操纵世界局势,操纵联合国。科索沃事件中,西方国家不断扬言,如果联合国今后不能有效干预,民主国家将组成新的国际组织替代联合国。可见,如果联合国不服从西方大国的意志,就将面临被抛弃的可能。区域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更加剧了联合国“边缘化”的处境。
促使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主权国家内部的需要,但这种内部需要的变化离不开整个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离不开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主权国家与其他非主权国家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霸权主义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竭力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推动联合国走向“新干涉主义”。今后,联合国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具有超国家权力?对“人道主义干预”应该采取怎样的原则?这可能是21世纪联合国与主权国家面临的难题。
三 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面临的选择和前景
未来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如何定位?人们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超越传统的主权界限,扩大联合国对主权国家的干预作用,甚至提出将联合国改造成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另一种则反对联合国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联合国扩大权力和实施强制性维和。这里对三种比较典型的设想作些分析,未来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发展可能不会是其中任何一种,但很可能兼有这三种设想的某些特征。
第一种,关于“超国家组织”或“世界政府”的设想。持这种主张的人相信,国际社会因为没有政府,所以是混乱的、无秩序的。只有建立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如同治理国内秩序一样来治理国际社会或全球社会,才能摆脱主权国家的利益局限,更有效地对付全球性危机,实现全球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和一体化、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人权主义者更是积极倡议建立世界政府,以解决日益突出的全球威胁。“要想在全球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法律和有效的政策,必须创立一个全球政府并培养一个全球领袖,后者的职责将是拯救‘地球联邦’”。(注:[美]西奥多.A.哥伦比斯著,白希译:《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88 年版,第379页。)
尽管世界政府的理论今天仍然不是主流,但关于使联合国具有更强超国家权力的设想和主张的确越来越多。例如主张加强法律的全球化,认为全球社会需要一个相当于国家宪法效力的“世界法”、“全球法”或“人类法”,提出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必须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呼吁建立国际警察和国际部队等。那些要求将联合国建成“超强国际组织”的人,希望联合国在未来解决全球问题、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种观点对今后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以及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将有极大的影响。
第二种,在对联合国的未来进行的各种各样的预测或设想中,目前比较流行的提法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人们普遍希望联合国在未来的全球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管理”或“治理”(Governance)与政府(Government)不同。政府是一种组织机构,而管理是指一种组织形式。它是“对不同集团关心的共同事务作出集体选择”。(注: Christian Reus- Smit,"Changing Patterns
of Governance",Albert J.Paolini ed.,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p.5.)传统的全球治理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政府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参加治理,联合国体系是实行全球治理的综合组织机构,而新的“全球治理论”大多主张打破传统的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全球管理形式,建立“超国家全球治理”(Suprastate Global Governance)。 (注: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1997,p.23.)
如果说“世界政府论”主张对主权国家进行强而深的干预,“全球管理说”则主张在全球范围协调包括主权国家在内的各种关系,全球管理机构的权力是“广而浅”的。(注: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in Global Governanc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5,p.200.)在这种设想中,虽然没有世界政府那种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力机构,但对主权国家的干预是广泛的。按照这种理论,联合国不仅代表主权国家,还是其他非政府组织以至个人的代表,全球所有力量共同管理传统上由主权国家管理的事务。将联合国主权国家的全球管理形式变为多行为体的全球管理形式。
夏威夷大学教授约翰·盖尔藤(Johan Galtung )提出了他的模式,描述了如何将联合国改造成“民主的全球管理机构”。他设想联合国代表四类权力的分配,即上面提到的主权国家、跨国集团、市民社会和人民,这四者同属“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在联合国中,“主权国家”由现在的联合国大会代表,改为“联合国政府大会(UN Governments' Assembly)”,安理会是最高机构。 “人民”由“联合国人民大会(UN People's Assembly)”代表,是联合国的“第二议会(the Second Chamber)”。“跨国集团”由“联合国集团大会( UN Corporate Assembly)”代表,作为联合国的“第三议会(the Third Assembly)”。这三种力量互相协调、平衡,共同进行全球管理。 (注:Johan Galtung,"Global Governance for and by Global Democracy",Issues in Global Governance,PP.197~215.)
这种设想很有代表性,如果联合国真的是这样改革,或朝这种方向迈进,对主权国家的影响在于:主权国家地位降低,主权国家内的社会集团或个人也成为联合国的主体,可以直接与联合国联系,而不必通过国家政府代表。主权国家将受到更多的制约、监督和干预。非政府行为体和个人可以对国家决策施加更多的影响。联合国可能对主权国家内部包括个人在内的方方面面进行干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行为体介入联合国与主权国家之间,将更直接影响联合国的决策和干预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正如前面所说,在这种全球管理制度中,主权国家受到的干预和限制当然与世界政府不同,对主权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仍然没有出现一个凌驾于主权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三种,与前面两种观点有所不同,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詹姆斯·罗斯诺(James N.Rosenau)提出联合国应该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他认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而是向两个方向发展,出现了两个分枝(Bifurcation ):一个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世界”,另一个是多行为体的“多中心世界”。所以,联合国正在成为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罗斯诺认为,今后,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中仍然可以像过去一样,可以继续维护其主权,继续实施集体安全措施,五大国可以继续保留否决权。但并不妨碍它同时进入两个世界。他认为,今后联合国可能不只是服从其中一个世界的指令,联合国将成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它将把非政府组织引入主权国家世界,同时把主权国家引入一个多中心的世界。(注:有关Rosenau 的观点可见Rosenau,"The United Nations in a Turbulent World",Albert J.Paolini ed.,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PP.252~274.)
不难看出,有人在为联合国权力不够大而担心,有人则为联合国对国家主权的干预和侵蚀担心。今后联合国同主权国家关系应该如何调整、定位才合理、合法,这取决于不同人、不同国家不同的哲学观念、不同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利益背景,难以一一描述和归纳。这里只是对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可能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些判断:
主权国家的主导地位不会被替代,联合国不会成为超国家组织或世界政府。主权国家是联合国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主权国家在某些方面的作用可能下降,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能加强。因此,不用说世界政府,即便是将联合国改造成多行为体并存、相互制约的“世界议会”的设想也是难以实现的。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会继续加强,它们在联合国中的作用的确在不断上升,对各国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在加强,但它们将继续处于边缘地位,起辅助作用,而不可能替代主权国家的职能,或在联合国中与主权国家处于平等地位。不能想像,大国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会受非政府组织的左右。
向远看,建立世界政府的条件远未成熟。从近处看,尽管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大谈“后主权国家”时代,但各国政府在维护其主权方面的态度是坚决的。他们不喜欢世界政府,认为不需要世界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因为全球化而否认主权,主权没有过时。所谓“市民社会”也只是发达国家或富有者的事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摆脱贫困,更谈不上全球网络文化、人权文化或生态文化,远未出现市民社会或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所谓“人道主义干预”主要是大国对小国干涉的特权。发展中国家呼吁维护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因为主权是发展中国家“抵御这个不平等世界行事规则的最后一道防线”。(注:顾震球:《联合国任重道远》,载《光明日报》1999年12月26日。)
前面我们看到,与冷战时期相比,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今后还会根据形势而不断变化,不变也是不可能的。
前面分析过《联合国宪章》的包容性、可解释性。在未来,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将更复杂。联合国也将比过去更具有多重性,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为此在分析它与主权国家关系时,最好将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问题分开看。例如:我们也许会看到,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联合国可能更趋向超国家性,更多采取强制行动。在环境保护、难民救济、残疾人问题、妇女儿童问题、艾滋病防治等领域,联合国可能更像一个“全球管理机构”或“全球论坛”。在维和行动上,其形式将更加多样化,传统维和与第七章规定的强制军事措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区分。在一些情况下,联合国可能继续遵循传统的维和原则,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联合国可能试图发挥“准世界政府”的作用。
未来的联合国可能更具有双重性,它将代表人们的两种愿望:第一,维护主权国家的利益;第二,超越主权,管理全球性事务。如果冷战时期联合国在第一点上比较突出,今后在第二点上将更突出。有些时候、在有些问题上,以第一种特征为主,有时则以第二种特征为主。由于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联合国在维护一些国家的主权的同时,可能干预或损害另一些国家的主权。例如,联合国可能在扶持一些民族成为主权国家的同时破坏了另一些国家的领土完整,或导致一些国家的解体;可能在维护一部分人的人权时又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国际社会总的来说是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的,但联合国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主权国家的合作、协商与较量。联合国的性质决定了它没有能力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奇是国家主权激烈的抨击者,但他还是很现实的。他说:“在当前仍然以主权国家体制为组织形式的时期内,人类的事情还得继续受到各国的控制”,“暂时还不能触犯‘民族国家’这个世界政治结构的关键”。(注:[意]奥利欧·佩奇著,王肖平译:《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7页。)
因此,应该强调的是,尽管联合国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过去表现出更多、更强的超国家性,尽管今后会有更多区域性或专业性组织可能发展为“超国家组织”,但联合国不可能成为这种对主权国家具有普遍干预能力的“超国家组织”。联合国与主权国家关系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的性质也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