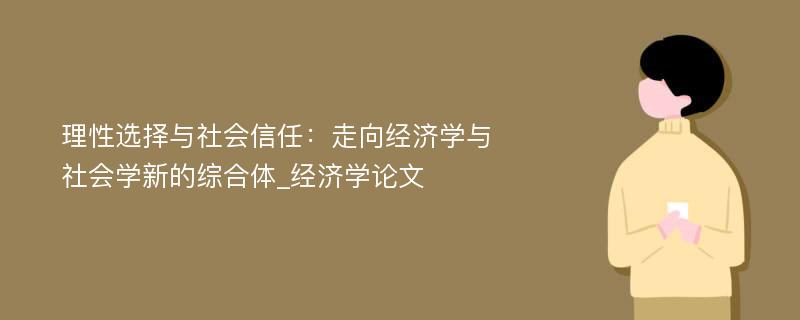
理性选择与社会信任:迈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存在绝对的学科分野。社会学将经济行动视为社会行动的一种类型;而经济学家也将社会因素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认为经济生活不能脱离风俗、习惯和道德(Smith,1979:232-233)。30-60年代,伴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兴起,社会学和经济学日益成为两个分立的学科。经济学家重点关注经济领域和理性行为,并借助数学方法和一系列简化的基本假设,致力于建构有效的经济模型,以排斥社会学家涉足经济领域;与此同时,社会学在帕森斯等的领导下,一方面力图构建巨型的社会理论,强调制度、符号、结构等对个体行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将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相剥离,把目光集中到非经济领域中。以至于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会依据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去区分经济学和社会学”(Samuelson,1947:90)。更有学者风趣地说:“经济学家讨论的是人如何做决定的,而社会学家讨论的是人如何不能做决定的”(Duesenberry,1960:233)。
分离后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下颇有进展,然而,经济学家很快在传统经济学的贫困中清醒过来。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挑战使热衷于数理模型的经济学受到了怀疑,经济学家不得不进行反思,以维持学科的中心地位。此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以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秉承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坚持理性计算和效用最大化追求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并以萨缪尔森(Samuelson)建立的最大化效益和最小化成本模型为经济分析的不二法则,力图将理性选择理论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理性选择理论被一再宣称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加里·贝克尔,1993),“经济学帝国主义”由此形成。此外,7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形成并日渐繁荣,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抛弃主流经济学的简化特征与计量法则,吸纳了“有限理性”假设,用微观经济学解释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调整与修改不仅维持了经济学长久以来的中心地位,也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对社会系统的过分关注,使社会学逐渐陷入了宏大理论的泥沼。由于过度强调符号、价值、规范等对个人的影响和限制,个体与个体行为的能动性在强大的“社会”概念下显得微不足道,微观与宏观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断裂,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包围又使得社会学的危机雪上加霜。在“包围”与“突围”的对抗中,新制度经济学助燃了社会学对经济领域的研究热情,使社会学家们运用经济学的“启发”去进行一种区别于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经济行为分析。最终,通过信任这一共同研究主题,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沟通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工具,推动着两学科迈向新综合。
一、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尚未分离之前,信任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综合力量”(西美尔,2002)和“普遍道德”(Smith,1776、1979)为两个学科所共同关注;进入30-60年代,经济学与社会学分离后,信任被归入非理性领域,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当时的社会学力图构建宏大的社会理论,也没有什么社会学家专心于此,信任研究在这一阶段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后,有关“欺诈”的研究增多,信任因其和秩序的关系再次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之中。
当代经济学对“秩序如何可能”这一问题作出了两种迥异的回答:第一类是以阿罗(K.Arrow)和赫希曼(Hirschman)为代表的类似于“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他们强调信任感在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充当着润滑剂的角色。阿罗指出,“社会在其进化历程中逐渐发展出某些潜在的约定——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到他人,这种约定对于社会的生存及其运行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rrow,1974:26)。赫希曼则认为,竞争的压力使得行动者倾向于放弃暴力和欺诈行为(Hirschman,1977)。这些回答无疑沿用了亚当·斯密的“普遍道德”观念,视经济行动者依从普遍道德从事经济活动。第二类回答则是从“低度社会化”的角度出发的。这一观点从托马斯·霍布斯(1985)的《利维坦》开始便成为经济学的一个传统。它强调理性的个人可能采取欺诈或破坏性行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必须依赖经济秩序来保证市场中经济行动的正常运行。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家们力图运用权威、契约等手段创造市场中的秩序,发展到现在,制度已经被看作一种重要的秩序来源。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威廉姆森吸收了西蒙(Herbert Simon)“有限理性”的人性假定,提出了人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1975:255)。“有限理性”使行动者不能拥有全部的市场信息,也未必能在各种待选方案中作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这种前提下,市场中的经济行动者很有可能利用对方的信息不完全或制裁措施的缺乏,采用诈骗等非温和的方式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共同作用,使经济行动者面临着被欺诈的可能。为了规避这种市场风险,人们需要收集信息、制定契约、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而这些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交易成本。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成为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的首要问题。在降低交易成本的路径选择中,威廉姆森用层级制整合组织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代替“信任”作为规范经济秩序的关键。
尽管同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威廉姆森也承认市场中信任的存在,且它作为经济生活的润滑剂,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但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中的信任是基于理性的计算性信任,在人的自利本性面前,它是十分脆弱的。甚至,这种信任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单方的信任恰恰让机会主义行为无后顾之忧而大行其道,使信任的一方付出更大的代价。由此可见,选择信任来降低交易成本就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一边是将来可能的更大损失,一边是即时付出的交易成本,经济行动者需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为了走出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威廉姆森在《市场与层级制》一书中提出:应该将市场的一部分功能转移到科层组织内部,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那些结果不确定、频繁发生并且要求大量投资的经济行为,最有可能通过企业内部的层级制方式组织起来,以规避机会主义的风险(Williamson,1975)。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秉承理性选择原则的当代经济学家们不再回避市场中的信任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将问题的关键转化为:选择信任是否是理性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理性行动者基于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倾向于选择不信任。然而,这种解释模式并不能完全为现代社会学家所接受。由此,围绕信任问题,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话,并对两个学科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学的拒斥与认同
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
最先通过信任研究开启经济学和社会学对话的是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作为一位关注经济学的社会学家,他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存在着“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倾向:一方面,社会学对符号、价值、规范等的强调,使“社会系统”、“共同价值”等成为一种“大而无当的语汇及臆测”(格兰诺维特,2007:序言),行动者机械地将社会系统的影响完全内化并依此行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延续功利主义的传统,行动者被认为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规避其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经济学家运用契约、制度等外部强制性手段规范经济行动,并认为行动者能够遵守这种规范。但这恰恰使现代经济学从一个低度社会化的极端走向了过度社会化,即过度依赖制度手段来确保秩序。由此,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学和社会学都错误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格兰诺维特,2007:6)。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个人利益的褊狭追求还是对社会规范的过度内化,行动者都被“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格兰诺维特,2007:6)。但事实上,行动者既非完全不受限制,也不是机械地臣服,他的经济行动既不完全依赖于社会情境,也并不独立于社会情境之外,真实的状态恰恰介于两者之间:行动者深陷于互动之中,立足于自己的关系网络进行理性行动。在这里,格兰诺维特发展了经济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1944)的“嵌入”概念,用以指涉这种现象,即个人嵌入于关系网络之中,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而他对这一观点的阐释集中体现在信任研究中。
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关于市场中秩序和信任的观点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他指出市场中存在着最基本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由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提供的,而并不像威廉姆森认为的那样——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不能保证市场中的秩序。那么为什么理性的经济行动者会在市场活动中选择信任呢?格兰诺维特用“嵌入”的观点对信任的普遍存在进行了解释。“嵌入”是介于“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一种中间状态,“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称‘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每个人都喜欢和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这说明大家并不满意于普通道德和制度设计的防弊功能”(格兰诺维特,2007:11)。也就是说,即使是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限制”中进行行动选择的,这种情境限制就是“关系网络”或者称为“社会结构”。经济世界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只有制度、契约、成本或效益计算的世界,我们乐意与某人进行交易,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通过互动产生的信任感,即通过互动产生的关系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对方的基本信息和建立交易关系的原动力,即互动确定了行动者是谁和社会关系的性质,网络表征了社会关系的互惠性,促成了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一句话:关系网络是行动者信任对方的一个必要条件,个人在这种关系网络的“情境限制”下,能动地进行理性选择。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仅被用于研究孤立个体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这与其所论证的“嵌入”观是格格不入的,应当受到质疑。但是理性选择“是一个不该被轻易放弃的假说”,因为“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定,尤其是把嵌入问题考虑进去,仍然可能是有意义的”(格兰诺维特,2007:30)。也就是说,理性选择理论对解释情境限制条件下的个人如何理性地作出行动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不过在经济学中,社会结构的“情境限制”作用被忽视了。此外,格兰诺维特还指出理性选择理论不应该仅仅将研究目标限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性行动中,还应该包括“社交、认同与权力的目的”等“目的性行动”(格兰诺维特,2007:30-31)。总之,格兰诺维特通过信任研究,说明了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同时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提供了一个背景——社会结构的情境限制。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个人才可能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且,理性追逐的这种利益不仅包括工具性行动所追求的经济利益,还包括目的性行动所能实现的许多社会性收益。对社会学而言,格兰诺维特希望,通过信任研究,社会学能回归到“韦伯传统”,即将经济行动视为社会行动的一种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格兰诺维特开启了“社会分析与自利动机、理性选择为前提的经济分析的对话”(格兰诺维特,2007:序言)。
科尔曼:信任研究是理性选择学说的关键
在格兰诺维特开启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后,两者原先严格的学科边界出现了松动。经济学家重新开始关注曾经为他们所忽视的社会结构对经济行动的影响,而社会学也更多地介入了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分析。但是,在社会学研究内部,肯定并愿意采用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方法的仍然占少数,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位关注经济学的社会学家,科尔曼受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他认为,经济学虽然关注个人行动,并且存在很多假设上的局限性,但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对个人的行动作出解释和预测,理性选择就是一个良好的解释工具。科尔曼指出:社会科学应该将社会系统的行为作为解释的重点,社会科学应该以个人的社会行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这也引出了社会学与经济学都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即如何使微观和宏观相连接。科尔曼主张应将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作为研究社会系统行为的出发点,以沟通微观和宏观。而对于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而言,理性是行动的基础,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将是行动者的目的。①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应该成为解释人们目的性社会行动的有效工具(科尔曼,1992)。
在将理性选择理论吸收到社会学之后,科尔曼认为,信任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可以用理性选择进行解释。他指出同其他社会行动一样,“信任”行为中存在着行动者、资源和利益。但因为信任意味着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所以这三种要素在信任行为中被细分为资源、资源委托人、资源代理人,以及由于控制权的转让而对委托人和代理人所分别产生的利益。在单方面的信任关系中,对代理人而言,他接受委托者资源的控制权就意味着获得利益,他所要决定的是守信还是违背诺言。对委托人来说,他将资源的控制权让渡出去就面临着损失的可能性,因此委托人需要决定是否信任代理人。那么委托人根据什么决定是否信任代理人呢?科尔曼认为,委托人会对资源控制权转让后可能的收益(G)以及可能的损失(L)进行估计,同时评估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期望进行行为活动的概率(P),只有在计算出GP>L(1-P)的情况下,委托人才会信任代理人,否则,委托人将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不信任代理人(科尔曼,1992:108)。
科尔曼指出信任是理性选择学说的关键,并认为尽管根据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单次博弈中的信任是非理性的行为,但是如果将收益范围扩大,仍然能够将信任看成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科尔曼列举了很多信任的例子:银行负责人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条件下对经济困境中的船主表示信任;农夫将农具借给素不相识的邻居;女孩让不熟悉的男生送自己回家并同意走偏僻小路。这些都是经济学无法用理性选择去解释的,但如果我们将互动看成是持续的,而非单次的过程,并将经济利益之外的一些情感性、文化的、社会性利益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就能用理性选择去解释以上行为。也就是说,对上述例子而言,银行家想在以后和船主多点经济来往以获得更多利益;农夫想在以后获得邻居的帮助,或者获得其感激和友谊;女孩想获得男孩的友谊。这些利益都不是一次性兑现的,也不完全是经济利益。科尔曼还指出,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利益和对利益大小的评价也完全依据行动者自身的感受。科尔曼关于理性选择的补充和重新定义,使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得到扩展(科尔曼,1992)。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科尔曼对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引入,形成了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或曰理性行动理论,从而为社会学分析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工具,终结了“社会学家讨论的是人如何不能做决定”的尴尬。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科尔曼为宏观社会系统行为的微观解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微观与宏观间的沟通。从他以后,社会学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理性选择理论,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同时,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的发展也迫使经济学不得不作出修正:将实质性经济利益之外的,包括友谊、认同、感激等在内的利益考虑进来,变利益的一次性兑现为长期的、持续的实现过程。这些变化都使得经济学和社会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重新融合,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共同点,两个学科综合的趋势更加明显。
福山:文化不是理性选择
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在信任领域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经济学和社会学从严格分离,到经济分析被纳入社会学分析框架,再到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分析的道路。如果说格兰诺维特是为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情境限制的背景,科尔曼则将理性选择理论扩展到社会学分析之中,还有一位学者则在宏观层面上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提出了挑战,该学者跳出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通过研究信任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找到了解释经济现象的一条替代性的路线,这就是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福山看来,经济学虽然将人们功利追求的利益范围继续在快乐和金钱以外的动机中扩展,但理性选择的一个根本的前提——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没有改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是理性的、自私的,这个学说的80%是正确的,剩下的20%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只能给出拙劣的解释”(福山,1998:16)。也就是说,在福山看来,理性选择理论并不能解释一切人类行为,且经济学家如果不理解不能被很好解释的那一部分,理性选择本身也就成为了无本之木。以信任为例,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看来,“信任”是非理性行为,不符合经济人的行动模式,但这在福山看来,社会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信任度与经济繁荣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决定信任的习俗等文化现象往往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福山认为,一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和该社会的经济规模之间呈现相关关系。在高信任度的社会中,企业规模比较大且通常有较长的历史;而低信任度社会中的企业多是小规模的家族企业,并且其经营通常在三代以后就难以维持。究其原因,高信任度社会的企业通常采用现代的企业管理模式,经营者不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却拥有良好的经营才能,同时高信任度也使得企业内部的员工能够相互合作、提高效率,经营者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企业的繁荣和永续经营;而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企业所有者往往也是企业的经营者,并且在两三代后,企业继承者往往不是最适合经营企业的人才,导致企业经营不利。同时,由于家族企业继承者之间的内耗,企业经历不断分割,最后通常不得不消失。因此,高信任度社会,企业永续扩大经营;低信任社会,企业则不断地出生和死亡。信任度和经济繁荣之间呈现正相关,而文化中的自发社交性产生信任。福山认为,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传统、习惯、习俗等文化因素,如日本家族企业中的长子继承制、终生雇佣制、收养制、招婿婚,中国的财产家族均分制、收养机制。这些文化有着不同的自发社交性,这种社交性促进了群体的形成,而群体成员因共享某种价值观而相互信任。由此,用理性选择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其效果将是十分拙劣的(福山,1998)。
福山在用理性选择理论去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之外,找到了一条从文化出发的解释道路。这一解释路径的产生,使得经济学不得不重视理性之外的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福山已不是单纯地为理性选择理论做补充或者扩展,而是为其指出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力图警醒经济学家重新关注曾为其所忽略的传统、习俗、道德等文化因素对人们的经济行动的影响,以避免经济学的盲目自信。在这个意义上,福山为经济学和社会学迈向新综合所作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三、走向新综合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能够看到:围绕信任这个共同话题,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理性选择”上展开了对话,使得两个学科经历严格分野后又重新回到了对话与融合。经济学家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认为信任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社会学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信任源于关系网络并在市场中大量存在;科尔曼在格兰诺维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理性选择的方法引入社会学,认为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行动,信任本身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而福山则在理性选择之外看到了文化的作用,找到了一条用文化解释经济的崭新路径。格兰诺维特、科尔曼和福山的学说分别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补充、扩展和批判,可以分别用背景路向、扩展路向和替代路向表示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关系②。这三条路向逐层深入,促使理性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重新沟通的桥梁,推动两个学科不断迈向新的综合。
在此以后,沿着以上三条道路,陆续出现了许多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其中,受格兰诺维特影响,对个人关系网络与经济活动关系的研究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如经济学家鲍威尔(Walter Powell)、舒瓦茨(Michael Schwartz)等。沿袭福山的传统,有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探讨也在增多,社会学家泽利泽尔(Viviana Zelizer)和迪马侨(Paul Dimaggio)就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此外,理性选择理论继续被经济学家用于分析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而社会学的批判也为经济学家所吸收并相应对理性选择理论作出了调整,“效用”的种类和范围都在扩大和变化。另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也再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它也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接受,用以研究个人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并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不再拘泥于自身的学科界限,而是根据实际研究的领域和具体问题选择最适合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些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经济学和社会学经过长时间的对话,已不再根据理性与非理性划分研究对象。正如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体现的那样,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不适用于解释全部经济现象;同样,社会学也不能完全脱离理性或者目的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相互借鉴,表现出新的综合趋势。但是,这种综合的趋势并不表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界彻底消失,它们在综合的同时,仍继续保留了该学科专属的研究范围,两学科在迈向综合的过程中,不断取长补短,以期更好地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经济学和社会学正在迈向一种新的综合,这种综合集中体现在两个学科关于社会信任问题的探讨中。在这一过程中,理性选择理论成为两个学科沟通、综合的重要桥梁。但是,这种综合远远没有完成,因为在此过程中,社会学作出了更多靠近的努力,而经济学仍然试图在中心和边缘之间保持距离。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综合,需要经济学家表现出更多的吸收性和宽容性。
注释:
①科尔曼(1992)认为采用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这一观点,一是可以提高社会学的预测能力,二是可以提高理论的简洁性。他同时指出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收益,但可能并不是追求最大化的收益。
②三个路向划分参照了泽利泽尔的《进入文化》一文。泽利泽尔认为,“根据理论与经济学标准的接近程度的不同,或者他们与经济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的接近程度不同,现今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存在三种研究路向:扩展路向、背景路向和替代路向。”扩展路向是用相对标准的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家没有认真考虑或有效处理的问题。他们可能采取与经济学家同样的研究范式,但是将这种范式扩展到经济学家经常忽视的主题事件领域。背景路向主要研究对经济行动起促进作用或限制作用的社会组织的特征,讨论个人决策的社会背景,并增加社会因素作为个人决策的一个约束因素,而正统的经济学家则将这些社会因素存在于价格和法律之中。替代路向则与传统的经济学解释针锋相对,这种路向从文化、结构、关系等入手来分析某一现象,寻求对经济现象进行替代性的描述和解释,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有限理性个人决策理论。《进入文化》一文被收在莫洛·纪廉(Mauro Guillen)等编的《新经济社会学》论文集中(姚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标签:经济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经济社会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社会网络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