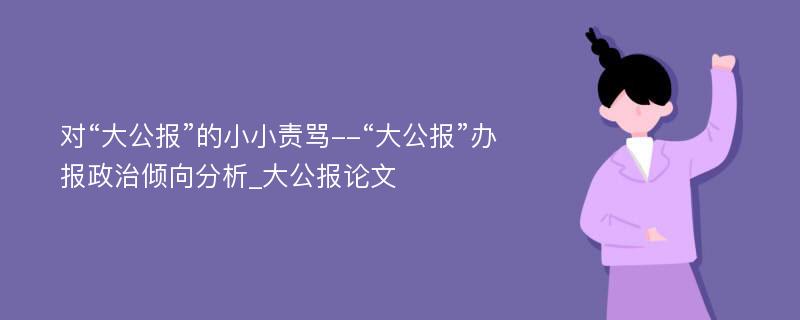
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评析新记《大公报》办报的政治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倾向论文,政治论文,小骂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以毛泽东对新记《大公报》办报的政治倾向所作的“小骂大帮忙”的论断为依据,运用大量史实,揭示新记《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并对其采取“小骂大帮忙”办报方针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
毛泽东在谈到新记《大公报》办报的政治倾向,即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态度时,说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小骂大帮忙”。
1926年9月1日,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续刊。这“三驾马车”开业伊始,由张季鸾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本社同人之旨趣》的社评,公开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作为办报方针,并为大公报社训。所谓“不党”,即“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为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这“四不”主义,是包括政治立场、新闻言论、经营方针和报纸风格的具体概括。
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论断:“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报纸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总要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总是一定阶级和政党的耳目和喉舌,这是一条真理。对大公报来说自然也不能例外。只要从大公报办报的亲蒋倾向上来分析,就不难看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大公报创业于天津,与南方的国民党势力本无渊源。蒋介石背叛革命后,1928年夏继续北伐。7月1日,蒋介石乘坐的专列到达郑州,张季鸾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蒋随行的幕僚有邵力子、张群、陈布雷,都和张季鸾熟识。不久,张季鸾又到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和蒋介石属下的国民党人作了深入的接触。在8月27日到9月3日的大公报上,接连发表张季鸾以“榆民”笔名写的6篇《新都观政记》和3篇《京都杂记》。9月1日,张季鸾在《本报续刊二周年之感想》的社评中,表白大公报两年来迭次断言北方旧势力之必败,革命势力之必成,然后说:“虽然本报非任何方面之机关报纸,今者北伐完成,党国统一,本报续刊以来之信念,可谓得相当贯彻。然其立言精神,今昔则同。”紧接着表态说:“盖本报公共机关也,同人普通公民也,今后惟当就人民之立场,以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这是它首次表明了拥蒋的态度。从此以后,大公报的亲蒋反共的办报方针日益明显。
1930年在蒋阎冯战争期间,张学良公开表示拥蒋,同年11月,张学良进关赴南京,与张学良有旧交的胡政之,先于张一日赶到南京采访迎张“盛况”,以后通过陈布雷访晤蒋介石,在谈话中,胡向蒋建议,“今日急迫应办之事,莫过于剿除匪共”、“剿共之事,军事与政治宜并重。”蒋表示采纳。蒋后来对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时,《大公报》先后发表《朱毛之祸》、《剿共与安民》等社评予以配合,进一步表明了其亲蒋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要于右任电告张季鸾,要张支持他的主张。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团结御侮的呼声四起,爱国学生纷纷组织抗日请愿,大公报面对读者的严词斥责,秉承蒋介石“不抵抗”的旨意,竟然提出“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张季鸾发表了大量鼓吹“缓抗”的社评。为此,大公报遭到社会上的唾骂,大公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装有炸弹的邮包以示警戒。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向蒋介石“兵谏”,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共赴国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大公报坚决反对“西安事变”,连续发表多篇社评,一方面吹捧蒋介石“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另一方面诬蔑这次事变是因中共的“恶意的勾煽”所引起的,并恶狠狠地说什么“中国不容赤化暴动,是拥护国家民族生存事实的绝对需要,是赣乱八年以来的活教训。”“犹如人体之不能有癌肿,中国今日亟须建国奋斗,不能容忍内部之组织的捣乱。”亲蒋反共的气焰何其嚣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局把张季鸾那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加印了40万张,派专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作为他们射向中共和张杨的“重镑炸弹”。
1940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部队损失惨重。重庆《新华日报》原有对事件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检扣,在版面上开了“天窗”。周恩来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蒋介石作愤怒的抗议。而《大公报》却连篇累牍发表社评,重弹“军令政令之统一”的滥调,胡说什么“军令必须统一,军纪必须整肃”,“必须绝对服从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即蒋介石)的命令”,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独立性,公然为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张目。
大公报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国家中心”,把蒋介石当作“堪以胜领导全国奋斗救国之任”的“最高统帅”,而竭力拥戴。1941年5月,日寇大举进攻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说:“八路军不愿和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大公报受陈布雷之托,发表《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指责“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周恩来闻讯后致函张季鸾,指出中条山并无十八集团军一兵一卒。并说:“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张季鸾随即发表《答周恩来先生的信》,正式提出“国家中心论”,坚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为正统,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面宣传“戡乱”“剿共”,阴谋发动反革命的内战。《大公报》为虎作伥,紧密配合。1945年11月20日发表《质中共》的社评。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鼓吹“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主张共产党拱手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民主政权给蒋介石,向蒋介石投降。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又发表恶毒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文章大肆渲染“苏军撤,共军来”、“国土既归来,还流同胞血”这一观点,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并诬蔑东北民主联军使用所谓“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战术,真是“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这些言论,都是替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打掩护的,充分暴露其亲蒋反共的政治倾向。
从以上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大公报都是坚定地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的,其办报方针、政治倾向都是亲蒋反共的,是“大帮忙”的。
当然,《大公报》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存在着矛盾,尤其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后期,加紧暴虐残酷的法西斯独裁,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残暴掠夺民脂民膏,“四大家族”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搞得天怨人怒,民心丧尽,在这个时候,《大公报》也曾经“小骂”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政之从香港撤回重庆,1941年12月9日由港飞渝乘最后一班飞机抵达,到机场守候迎接的人员不见胡政之的人影,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祥熙二小姐接运而去。过了几天,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通过《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反映了人民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厌恶情绪。大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文章尖锐地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文章发表后,激起民愤。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抗议“飞机洋狗事件”,当天蒋介石就把外交部长郭泰祺撤职,交通部长张嘉■于29日函请大公报更正其事,用以遮羞。
1942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饿死几百万人,活现一片人间地狱,记者张高峰写了《豫灾实录》,揭露了河南人民灾难惨况。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为河南三千万灾民呼吁,痛骂重庆灯红酒绿、物价飞腾的现实。社评中说:“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进而提出:“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收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蒋读了这篇社评,大为恼火,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并通知王芸生,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邀王访美的邀请,蒋介石不予批准,以示惩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当局抢夺胜利果实,大闹“五子登科”(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宁沪一带人民遭了殃。对于这种鲜廉寡耻的“劫收”,《大公报》严词斥责,责骂他们“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城市之一张家口,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一意孤行,要建立反动独裁的专制法西斯统治。《大公报》认为“这从政府方面看,是一个军事胜利紧接着一个政治僵局,这是很欠斟酌的。”它希望国民党“务要贯彻和平的本旨”,希望中共“必不可放弃和平到达民主的机会。”希望第三方面人士“努力斡旋,务使当前危局转为祥和。”大公报不赞成召开伪“国大”,胡政之却以“社会贤达”身分参加大会。他曾经说过,“参加国民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大公报在这个问题上拂逆蒋介石的旨意,是与国民党意见歧异的。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援引《出版法》勒令南京《新民报》停刊。王芸生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文章把这部《出版法》讥讽为袁世凯时代的产物,痛斥国民党的反动文化专制,主张废止箝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出版法》。《中央日报》立即斥责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要对王的反蒋“罪行”进行“清算”。一时“围剿”王芸生的气焰甚嚣尘上,鸦噪蝉鸣,乌烟瘴气,好不热闹。
为什么《大公报》对蒋介石采取“小骂大帮忙”的办报方针,采取亲蒋反共的政治倾向呢?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首先,大公报基本上是站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它本身是中等的民族资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志,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重压之下,在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下饱受摧残,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它绝不允许“中国赤化暴动”,也不希望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梦想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内履行民主政治,提倡国民经济,采欧美宪政之长,对外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正因为如此,它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共的“赤化暴动政略”极端反感,而拥戴蒋介石国民党成为“国家中心”;而当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卖国政策,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时,他们就又会表示微弱的“反抗”。
其次,《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办报方针的实行,又是因为蒋介石对大公报头面人物的收卖、拉拢和腐蚀。1928年7月,张季鸾在郑州首次结识了蒋介石,张季鸾又到南京住了一个多月,返回天津后就在《大公报》上称颂蒋介石是“革命英雄”,公开表示了拥蒋态度。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发出了“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通电,一面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严厉取缔共产党报刊宣传,一面嘱意《大公报》等“可以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凡弊病所在,亦请尽情批评。”蒋介石还表示:“凡属嘉言,咸当拜纳,非仅中正赖以寡尤,党国前途亦与有幸焉。”蒋介石摆出一付“礼贤下士”,“俯就舆情”,扶持“正当言论机关”的面孔,《大公报》一见通电受宠若惊,张季鸾公然表示这一通电是“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诚恳表示。”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赴宴者多为各院部会的负责官员,而主客是张季鸾。张季鸾认为蒋介石“以国士待我”,必“以国土报之”。他曾经向人表示:“国家局面无论多么困难,我一见到蒋先生就觉得有办法。”“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他俨然成为蒋介石的顾问。他可以不待通报,直接去见蒋。张常利用见蒋机会,在新闻或言论中透露一些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许发表的消息,1935年夏天,吴鼎昌去南方,在庐山牯岭同蒋介石密谈了一个星期,非常投机。这年12月,蒋组织所谓“名流内阁”,任命吴鼎昌为实业部长。这样,《大公报》与蒋介石关系更加密切。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批准《大公报》购买20万美元官价外汇,实际上等于发给他一笔巨额津贴。《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由国民党提名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所有这一些笼络人心的手腕,使《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政治倾向发生明显的倾斜,亲蒋反共的基调曾经长期支配着大公报的新闻和言论写作。
标签:大公报论文; 张季鸾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王芸生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