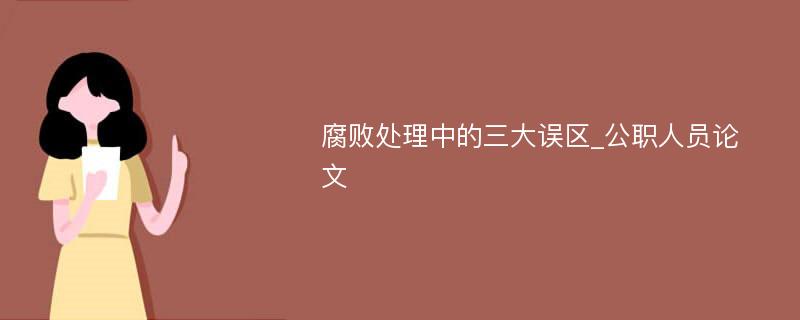
腐败救治中的三个误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反对与抑制一些国家公务员的腐败行为的措施上,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综合治理、标本兼顾的总体策略下,以制度防范为中心,以法律防范为保证,以教育防范为基础。但是从一些宣传和舆论的内容看,有的观点仍然存在绝对、片面和主观的倾向,给治理腐败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误导。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澄清,无论对于反腐败本身还是对于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事业,都是极为有害的。
道德教化万能的误导
关于反腐败,有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教育和道德教化是最为有效的办法。理由是,制度再好也要人来制定和操作。因此,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程度和完美的自我内在约束机制是防止腐败的关键。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从现实性来看,却难以让人放心。强调道德自省和教化育人作为一种约束手段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却是有条件的。针对防止人的作恶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不能无边际地指望道德教化,如果将其强调到不切实际的程度,我们的工作就有可能被带入误区。首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说,中国是一个追求以德立国,讲究自律本位的国度。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也以一贯之,保持良好。但现实的结果却总不十分令人鼓舞。从教化的内容到教化的方式到教化的关系都有值得讨论之处,以至于流于形式、有名无实和导致普遍逆反心理。官师官教、草民生徒。我说你听,我教你做。到头来施教者却不少成为“教旨”的叛逆。这些遍在的现实早已让教化哲学褪去了圣光。其次从道德教化自身性质说,它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有局限性的。它的落脚点在于觉悟的启发,而觉悟的启发总是要受制于客观存在与现实环境。从精神方面获得的道德约束力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会发生作用,甚至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但当它的存在形式与物质基础以及制度存在不同步、甚至相矛盾时,精神工作的效能就会呈现与日俱减的必然趋势。我们可以发现我国50年代甚至再往前的战争年代,精神因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那种支配作用,在今日已不再多有。恐怕不仅是一个思想道德工作中方式方法的“时代差”问题,更重要的物质基础、制度现实的建设没跟上来。现实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与思想道德教化在人们头脑中建立起来的价值坐标和期望值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削弱了思想道德育化本身的价值魅力。再次从思想道德育化防止腐败的效果说也是有限的。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者的确有之,意味着有些人能够严以律己,不染于污泥浊水。但是,衡量道德教化和自我约束机制作用的大小,不能仅从个别现象或特殊范围内来看,而应从一般情况和普遍范围来作结论。共产党人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其思想基础之坚实和觉悟意识之高尚是难有相匹配之党派的;共产党人又历来重视思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但即便这样,目前的官风仍不尽如人意。由此可见,将思想道德育化作为反对腐败防止腐败的主要途径是一种误导。恰当的定位,它可以是一道防止公职人员腐败的不能缺少的“软”防线。所谓“软”是意味着对于一种职业要求,官员可能听,也可能不听。听者自戒,不听者违规沉沦。这就需要设立制度约束的“硬”防线。所谓“硬”,是意识着所有公务员无一例外不得越线,否则就要被拉下“公仆”的位子,接受法律的制裁。只有持这样一种辩证认识,才可能真正用好道德教化的工具。
追求“运动”效应的误导
现时执政党和政府指导进行的反腐败,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这里仍有提醒避免以往“运动症”的必要。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反腐败,曾经掀起了一道道浪花。从“三反五反”到“四清”运动到“社教”运动,再到“文革”的“一打三反”运动,还有后来的“严打”斗争,可谓连绵不绝,几无中断。其中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努力,另一方面也透出很浓厚的人为色彩、群众运动色彩和主观随意性色彩。在民主与宪政的条件下,法治是一种规范化的常态统辖方式,不会产生忽冷忽热、高低不等的曲线运动状态。只有在不完全法治或非法治的情况下,官风不正的积累和惩治腐败的过程才会表现一种曲线型。病灶不能根除,毛病就要积累,公众就会怨气沸扬,继而就导致一场惩治腐败运动。可是病灶仍旧会在那里,于是,就形成了一次次扬汤止沸的循环往复。既然是以人为主观意志很浓的运动方式出现,惩治腐败的准则就不纯是法律,甚至完全不是法律。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比较明显。比如其中经常采用的“群众办案”的方法,又比如案件处理中的党内审批制度,再比如以党的文件规定斗争的基本原则等等,都不太容易体现法治的客观性,都很难排除家长和长官意志的掺合,就使惩治腐败极容易出现有失公正和走向极端的结局。不公正不是说主观上不愿这样做,而是客观上很难做得到。主要原因,本该是法律的行为,结果成为权力意志行为。法律是客观的、无感情的,而人则往往是主观的、情感的;前者可以做到一视同仁,而后者则可能会亲疏有别。因为某种需要,相同的情况,居于权位者做轻重有别的处理也并不足为怪。另一倾向走极端,也是权力主观随意性的一个特点。过去历次反对腐败的实践,都多多少少存在着失去控制、不好驾驭、经济和政治绞合一起和扩大化的现象。如在“三反五反”中,党内曾在指导思想上产生“左”的偏向,搞逼供信。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原来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到后来,就演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并采用了群众斗争形式,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再往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就更是一塌糊涂了,原本是肃贪惩腐,结果是政治斗争,成为搞两条路线斗争的借口。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反对腐败必须要纳入法治的轨道,既要排除权力意志,也要防止所谓群众意志。只有在法律这样一个恒久的、独立的、客观和规范的意志下,反腐败才能不被引入歧途,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高薪可以养廉的误导
高薪养廉的确是防止腐败的措施之一。但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工资过低是造成公职人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可以这样说,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并不一定是因为生活困难。但从总体上看,收入偏低的确不利于他们增强抵制腐蚀的能力,少数人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而陷于腐败的泥坑。应该约束公职人员手中权力的正当性,同时又要确保他们能获得与其贡献大体相称的报酬,这是所谓“以薪养廉”的意义所在。改革开放以后,机关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有过几次上调。到1998年为止,以处级职务为例,一般来说月收入到1000元左右。这里面已经包括了所有类型的补贴。与现有的国有企业职工的一般情况基本持平或略低;与其它如私营或外资、合资类公司企业相比平均相差至少在一倍以上。当然,工作与收入的相对稳定和住房、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比别的行业要有吸引力,但这些传统体制下的特权伴随五大改革的深入,会逐渐弱化,逐渐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公职人员收入水平显然是低了。另有更严重的情况是还有一些县,公职人员不能正常发工资。在现时下岗职工增多、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尚有个别农村居民温饱问题急待解决的情况下,提出高薪养廉也许不合时宜和国情。但在抑制与防止腐败的理论上,这个问题必须得提出来,相机解决。根据物价指数、行业收入比较、及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时下机关公务员工资至少不要低于1500元/月左右或达2000元/月更宜。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遇到两方面困难:一是国家财政紧张;二是中央国家机关人员过多。第一个困难需要一个长期的解决过程,第二个困难正在克服之中,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中央的支持下正由国务院付诸实施。现全国公职人员总数为3600万,其中纯粹政府公务员和执政党及民主党派工作人员大约800万, 按照人员减半的原则,三年以后分流1/2,留下400万。在这种情况下, 将公务员工资在现有基础上增加50%或待财政丰厚时上调100%是可行的。 从而在收入方面为防止腐败加一个砝码。当然,仅仅提高薪水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行为。所有政策制定者务须对这一荒唐认识保持足够警惕。高报酬的待遇只是为公职人员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增加了腐败成本,使多数腐败活动的核算显得得不偿失。但是,从实践看,这一措施的实行引发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不能轻视。首先,物质基础是高薪制的前提,国家须具备支付政府公务人员高工资的财务,这对于如我国这样不太发展的国家来说承担沉重的行政费用会有困难;其次,政府官员的高工资与非政府人员低薪的鲜明对比极易使普遍大众的心理失衡,从而在激励和吸引大量人才涌向政府部门的同时,可能会遭到公众不平等感觉的抵制和攻击,增加实施的难度。矛盾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给社会留下不安定的隐患;再次,高工资的实施在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同时,也可能因工资待遇间的落差拉大而造成官民之间隔离地带的加宽。好处是这有可能阻碍一般性的腐败如说情、开后门和普遍行贿等现象的发生,但却也有可能增加官场风气、社会等级观念和强化官僚主义作风,这本身也是一种腐败;最后,公职人员在高工资制下增加工资时,极易使他们产生权力增大的错觉。长工资加大了行政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扩大了行政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这又反过来无形中提高了政府及其人员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从而使一些公职人员有意无意地扩张手中权力,以至造成新的腐败机会。由此看来,理论界对高薪养廉的提法必须慎重,论证必须全面和客观,避免在实践中造成误导。
(《中国经济时报》98 年11月6 日)
